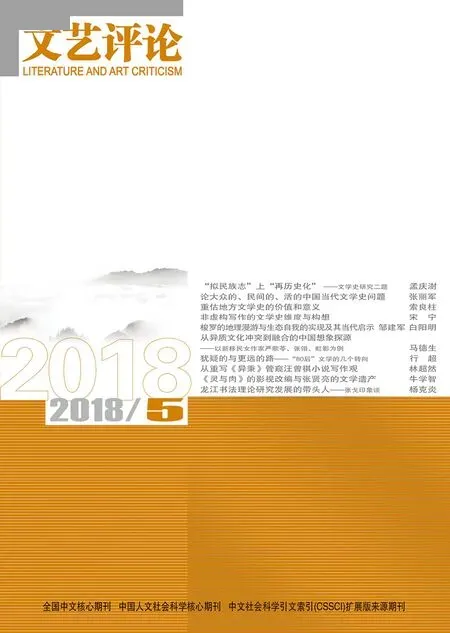试论作家批评与当代文学批评版图
○周显波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可谓是四分天下:由高校和研究院所构成的学院批评,以各级作协为主体的作协批评,在官方媒体和自媒体上发布评论的公众批评,作家在文学创作之余从事的作家批评。这四种文学批评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的版图,而四种文学批评势力的互动、互补、互相呼应是批评界的一种最为理想的良性发展格局,然而事实上构成文学批评界的四种力量的发展却是不均衡的,彼此之间也存在不小的差异。
四种文学批评形态中,当代作家批评往往是被忽视且被误解最多的。法国文学家蒂博代对于作家批评的思考非常有代表性。他在《六说文学批评》里把文学批评分为三类:“职业的批评”“自发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职业的批评”主要指学院批评。在蒂博代看来,“职业的批评”具有历史感和富有理论性,其缺点是对同时代创作欠缺敏感度,并且批评容易陷入到观念的框架中,忽略无法纳入其既有观念框架的文学现象。“自发的批评”,也被蒂博代称为“公众的批评”。在他看来,“自发的批评”受到媒体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影响,使得它具有快速性、生动性和潮流感,但是深刻性和学理性不足。“大师的批评”也被蒂博代称为“寻美的批评”“直觉批评”或“同情批评”。“大师的批评”也就是作家从事的文学批评,即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之余,自己所做的文学批评活动。“伟大的作家们,在批评问题上,表达了他们的意见。他们甚至表达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有的振聋发聩,有的一针见血。他们就美学和文学的问题,以及当代文学现象,从自身的写作、阅读体验角度发表了许多见解。”①作家批评意味着作家出于自身职业的习惯和特点,偏重从自身创作经验和生命体验的角度来思考和评断文学问题。在蒂博代看来,作家批评避免了“自发批评”流于批评对象表面和易受商业干预的缺陷,又避免了“职业批评”的刻板和观念化。此外,作家批评因其卓越的创作力对于创作、阅读美学的影响是直接而迅速的:“自发的批评流于沙龙谈话,职业批评很快成为文学史的组成部分,艺术家的批评迅速变为普通美学。”②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当代文学批评界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风景,风景表现之一就是批评界常常对作家批评忽视与误读。误读的具体表现一是将作家批评视为佐证材料,即作家批评被当作该作家文学观念和主张的宣言书,继而成为学院批评、作协批评和公众批评对该作家及其创作研究的材料,所以,作家批评所针对对象的观点和论证被忽略了。这样就顺理成章地形成一种错位性认识:作家所从事的文学批评被视作其本人创作理念的公告牌,学院、作协及公众批评于是按图索骥从中寻章摘句,以获得自己评论观点的支撑与佐证。需要注意的是,作家在批评中展现的观点事实上是该作家戴着批评家面具来发布的,是有着具体针对性的,是否能将作家批评中表达的观点与其个人文学写作展现的风格化标识直接对应,是格外需要甄别和小心对待的。当代作家批评的另一种误读则是简单地把作家批评视为写作技巧教学成果。当代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同时也是教育现象,是作家大规模进入高校。这种现象有两种具体表现。首先,一些著名作家作为教师成为高等教育体制的一员,以其擅长的写作实践能力在文学专业高等教育方面发挥作用,以试图纠正既往文学教育与实践能力培养的脱节。在此背景下,王蒙、莫言、王安忆、刘震云、阎连科、马原、王家新、毕飞宇、东西相继走入高校。其次,一部分高等院校设立的驻校作家制度,以及以请作家开设讲座、讲演的方式,让作家与高等教育直接产生联系。不论是常规性的课程教学,还是偶尔为之的讲座、演讲,作家借此生产了数量颇丰的文学批评成果,这些成果往往直接脱胎于课堂或讲座的讲稿。作家的批评对象从中外古典名著、电影到当代作家作品,涉猎广泛,但在高等教育的体系内部,同时在部分学院批评看来,这些文学批评常常被视为作家对创作的现身说法,只是作为写作技巧教学的成果,用来补充文学专业高等教育的一种方案或形式。很显然不论是哪一种误读,作为批评家的作家与作为作家的作家,前者被学院批评为主导的批评界看来,是业余的,其地位是比不上作家的创作的。
以上对作家批评的偏见或不见并非一种由来已久的观点。现代文学史上,作家以其兼具情感和理性、洞察与直觉的文学批评深刻介入到了中国现代文学进程里,从梁启超、鲁迅、周作人,到茅盾、沈从文、李健吾都能看到作家批评的身影。现代文学的崛起、转型,以及现代文学意识、现代文学美学观念的建立、现代文学作品的意义阐释模式和方法等无不与他们的批评实践相关。作家批评构成了现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力量,作家直接以大量批评实践参与进了现代批评的建构之中,也成为塑造现代文学批评范式的最重要力量。鲁迅开创的为人生批评,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分析式批评,以及李健吾、沈从文的印象感悟式批评,都深刻地影响到现代文学批评的进程,更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的重要内容。缺少了现代作家批评,整个现代文学批评史都会黯然失色。
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制度,文学组织均发生根本变化。现代文学中批评家的双重身份,在当代文学中转变为职业批评家兼行政官员的双重身份。”③整体来看,20世纪50-70年代,作协批评家成为文学批评界的主导,在这种一元化的当代文学批评图景里,作家批评分裂成两种状态:一是作家出任文化官员,其言论代表着国家意识形态,因此他们从事的批评带有浓烈的图解政治政策的色彩,其批评的个性被极力压缩、拧干。作家批评另一种状态则是传统的作家批评的当代延续,即以创作谈、创作方法论等形式问世,作家批评文本成为职业批评家的批评和研究的佐证材料。随着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的政治立场与倾向的强调,政治化标准逐渐占据最重要的位置,现代作家批评中印象感悟式的传统、为人生的传统渐渐在愈益压缩的话语缝隙里变得微弱,乃至萎缩。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伴随着国家现代化想象而逐渐壮大。20世纪80年代学院批评崛起并与作协批评一道参与共建了此时期批评界的盛况。同时,王蒙、冯骥才、韩少功、阿城等作家为代表的文学批评也成为文学批评不容忽视的重要构成,甚至对现代派文学、寻根小说等文学潮流有直接的推动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深度转型,文学批评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既有意识形态松动,卡里斯玛渐趋崩毁的大背景下,文学批评的元话语也随之碎裂,这种碎裂不仅体现在学院批评与媒体自发批评、作家批评之间,也体现在每一种批评的内部,甚至体现在批评家的文学观内部。对于批评界的不满声音也渐渐不绝于耳。1997年,《北京文学》刊发谢冕、洪子诚等学者的文章,对当代批评的状况表示忧思,他们认为“批评正在退化”,有“问题的批评”不断出现。杨匡汉先生将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批评形容为“姗姗来迟”,并进而指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便日渐失去了一条线索统筹、概括的可能,到了90年代,文学更是进入了‘无序’的状态”④。吴义勤近年更是多次撰文,指斥当代批评的“不及物”“虚热”症等特征,“当下的文学批评正面临种种诘难与怀疑,批评的品格发生了蜕变,批评的信誉也降到了冰点”⑤。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批评界出现了几种新的现象。首先,要求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分离的声音渐强。在一部分学院批评家看来,文学批评成了文学研究的副业,批评成为文学研究的衍生和附属,因此这种偶尔为之的文学批评已经与自发批评的差异不大。面对这种情况,朱寿桐等学者就曾撰文指出,要明确“建立学术研究和文学评论的区分意识”⑥,把学术研究和文学评论区分开来。当然,这种观点在中外都具有代表性,如韦勒克在《批评的诸种概念》中就持相似观点。其次,学院批评“一家独大”,进而影响作协批评、自发批评。学院批评在选择的方法路径上整体地走向了文化批评,重方法、重整体、重理论观念梳理和演绎,而相对来说,具体文学文本意义的挖掘,特别是文学技巧、方法的分析和思考在文学批评里变得日益边缘化。再次,公众批评分裂为两部分,一方面媒体吸收学院、作协批评家及其成果,以加强媒体批评话语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以网友为主体的自发批评则因为批评伦理的理解差异、对专业批评术语的隔膜和关注重心等原因,对曾被视为传统的批评权威不屑一顾。
纵观当代作家批评,就整体而言,作家在批评对象的具体艺术手法和思想两个角度入手展开了思考和批评,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作家批评的技术派和思想派,其中以技术派的队伍人数最多。作家常常在文学写作的技术手法方面解读、分析文学作品,一方面继承了重视文本开掘的文学批评方法传统,同时也发挥了作家写作经验的优势。王安忆通过多部小说的线索梳理,申明作家的工匠角色与精神,强调小说家对叙述逻辑掌控的意义。张炜在香港浸会大学所做的讲稿《小说坊八讲》中,对人物、故事、情节展开思考和分析,以一个小说家的写作经验角度来对小说内部的元素进行条分缕析的分析和思考,有力地补充了文化批评对具体文本艺术思考忽视的短板。马原在小说与电影解读中对文本中标点的使用、句子分行与叙事意义的影响,是很富有新颖性的。此外,莫言通过对文本的解读提出文学语言独创性的重要性,余华对文学语言准确性的强调,毕飞宇对小说细节的重视等等,都是当代作家对于文学经典解读在形式方面的贡献。而当代作家在思想角度解读文学现象也往往能获得独特的发现。残雪的“从心灵出发”“审视灵魂”的批评观,将卡夫卡、博尔赫斯等作家笔下的作品视为对抗世俗生活的艺术家自我的精神冒险和“突围表演”,在这种冒险和“突围表演”里,一种现代性的先锋精神就由此自我酝酿与展开,而这是最被批评家身份的残雪所看重的。思想派的作家批评家也是从作家自身的感悟、体验角度来解读文学作品,一般重判断轻论证,重感同身受轻理论框架,重现象捕捉轻归纳和思辨,但他们的批评往往在领悟和直觉里直抵事物的某些本质。显然,当代作家批评符合艾略特在《批评的功能》一文中对批评理想的期待:“最高的、真正有效的批评是在作家的劳动中,和作家的创作活动结合的那种批评。”⑦
作家批评是作家从自身的文学观、写作实践经验角度去理解、评论对象的。因此,每一次的批评旅程既是“我注六经”,也是“六经注我”。但在理解和评论之中,文本的深层意义也被渐次照亮,有关文本技法的秘密、文本意义与技巧之间的关联等也被作家所发现并论述,而后两者是文化批评和自发的批评常常忽视甚至不见的。作家批评又是一种“寻美的批评”,在作家对于批评对象“寻美”而非“求疵”的批评之旅里,印象感悟是作家批评常用的介入批评对象的路径,而达到对批评对象的寻美、审美的目的是这一时期作家批评的重要目的。印象感悟与审美批评成为当代作家批评的重要标志,也是区别于同时期其他类型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而当代作家批评对复述式和随笔式批评话语的普遍选择,风格化的批评语言,也在相当程度上有效拉近了与公众批评的距离。
我们必须承认,正是由于当代作家的批评实践,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名时代的文学批评提供了别样的风景,也有助于打破相对固化或平淡的批评界现状。
以赛亚·柏林在《俄国思想家》中把作家、思想家概括为两种思想人格和艺术人格类型:一种是狐狸型,一种是刺猬型。前者“他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组织作用的原则,他们的人、他们的言论,必惟本此原则,才有意义”,后者则“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连,甚至经常彼此矛盾。”⑧很明显,前者用一元的思想结构和观念,将诸多本来矛盾的观念合并、变形、折叠;后者则拒绝用一种固定的视角和思想方式来解释世界,纳互相冲撞的万物于胸壑之中。我们在这里借用柏林的“狐狸”与“刺猬”来描述批评家群体。学院批评、作协批评及一部分的公众批评显然属于柏林所讲的“狐狸”型。而当代作家批评则主要以作家文学创作实践生成的经验为基点,或者以创作手法、语言、技巧等作为评价的重心,或者以言志、载道作为解读目标。所以,作家批评可谓是一种“刺猬”型批评。当代文学批评界不仅需要广博知识作为底子的“狐狸”型的文学批评,也需要以作家批评为主体的“刺猬”型批评,由此才能真正做到批评话语的多元、批评类型的丰富、批评意义的深化,以及批评界的深层互补与互动。
①②[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M],赵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9页,第99页。
③方岩《批评家与当代文学批评史》[J],《文艺争鸣》,2012年第8期。
④杨匡汉《多种途径和选择的可能性——〈九十年代文学观察丛书〉总序》[A],贺桂梅《批评的增长与危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1页。
⑤吴义勤《批评何为?——当前文学批评的两种症状》[J],《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
⑥朱寿桐《文学研究:批评与学术的乖谬》[J],《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2期。
⑦[英]艾略特《批评的功能》[A],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85页。
⑧[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M],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