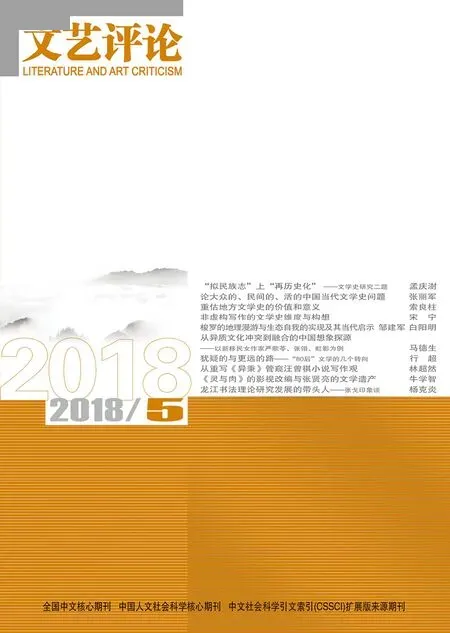从异质文化冲突到融合的中国想象探源
——以新移民女作家严歌苓、张翎、虹影为例
○马德生
“中国”一词源远流长,内涵复杂。本文所指的“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国体术语或政权意义上狭义的“中国”,而是“一个寄托有关自己民族的丰富文化想象和审美体验的总体象征字眼”①。这无疑与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内涵很相近,他认为“想象的共同体”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而小说与报纸作为重要的想象形式之一,为其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②显然,“中国”是一个超越于现实之上、蕴涵深厚文化象征与审美意义的“想象共同体”,既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里,又激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总是以巨大的热情从不同角度去想象中国。
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海外新移民文学强势崛起,其中严歌苓、张翎、虹影等三位女作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被喻为海外新移民文学的“三驾马车”。她们以开放的文化心态、独特的异域境遇和性别策略想象中国,不仅从“异域”到“历史”书写中呈现出繁复多样的形态与可能性,而且从异质文化冲突到融合中,向人性的深度和广度开掘拓展,寻找人类命运的共同性,表达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沟通、平等对话的美好愿望,凸显出她们对中国想象的新转型与新特质。本文以严歌苓、张翎、虹影小说文本作为考察对象,运用美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家国情怀的传承坚守和“落地生根”的精神诉求等方面,探讨她们从异质文化冲突到融合中想象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建构中国形象的深层根源。
一、中国和平崛起与“文化中国”的形象建构
海外新移民作家对中国的想象离不开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中国崛起直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最伟大的梦想。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成为世界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越来越激发了海外华人尤其是新移民内心深处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祖籍国的认同感。然而,崛起的中国在受到世界关注的同时,西方不断以“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无视、误读与曲解甚至妖魔化中国形象。事实上,与世界历史上凭借武力征讨而崛起的西方大国相比,中国和平崛起不仅是经济、科技等硬实力的提升过程,而且更源自于以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的自觉与自信,以及在全球化时代不断借鉴、吸纳外来优秀文明基因的尊重与包容。正如有学者所说:“这种和平崛起的意愿,主要是指中国愿意通过改变自身来推进世界新秩序的重构,表现在文化上,就是吸收外来优秀文明,活化本土文化基因,创造出人类普遍意义上的文化价值观念。”③因此中国和平崛起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崛起。文化是立国之根本,一个国家的崛起,如果没有强大文化的保驾护航,就会迷失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丰富思想资源和强大精神力量,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更是维系海外华人与祖国人民血肉联系的精神纽带。
基于此,伴随着中国和平崛起,身处异域的海外华裔学者积极倡导提出了一个跨越地缘政治的文化共同体——“文化中国”的概念。据有关学者考证,“文化中国”一词,最初来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温瑞安为代表的马来西亚“华侨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学者韦政通和傅伟勋先后将“文化中国”引入学术研究领域并得到学界广泛认同。从1990年开始美籍华裔学者、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则极力宣扬和重新诠释“文化中国”,在英语世界引起了热烈反响;他对“文化中国”的深入思考和理论建树,特别是对其内涵提出的三个“意义世界”④,被海内外学术界认定为对“文化中国”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界定和阐释。与此同时,以张岱年、方克立为代表的一批大陆学者则在国内学术界大力倡导推介“文化中国”。
纵观海内外学者的探讨,笔者认为,在中西文化冲突与碰撞的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中国”的提出与建构,不仅有助于增强全球华人的凝聚力和文化心理纽带,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吸纳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话融合中,使“文化中国”成为超越地域、政治、阶层、宗教限定的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正如华裔学者梁燕城(《文化中国》总编辑)所说:“中国是多族裔多文化的结合,同时也有千万计的海外华人,须要一个更为宽广的文化理念,可以用‘文化中国’,以别于政治和经济上的中国……当代文化共同体的文化理念,就是‘文化中国’,从精神上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带来文化上的多元和谐,建造中国人的骨气和灵魂。”⑤简言之,“文化中国”作为体现五千年中华文明之象征内涵的文化符号,是一个超越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意义世界、精神世界,是一个由不同意义和不同价值观念等所组成的话语社群或交流平台,是一个以文化和语言为纽带的“想象共同体”。所以杜维明认为,在“中国”之前冠以“文化”二字,“就是为了突出价值理念,强调人文反思,使得中国也成为超越特定的族群、地域和语言含意的想象社群”⑥。
文学作为文化的载体和“想象共同体”的重要形式之一,则是建构“文化中国”形象、增强西方世界对崛起中国正确认知的有效途径。伴随着改革开放走出国门的新移民女作家严歌苓、张翎、虹影等,以得天独厚的优势自觉承担起这一神圣使命。一方面她们身处海外,能从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获得一种新的视角和文化目光,以一种“间离”的效果来重新审视民族历史文化,重塑被遮蔽误读的中国形象,比西方人更加客观真实;另一方面她们早年都有过在国内长期生活的经历,是在中国大陆的文学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时常回到中国了解最新变化,正是这种跨区域、跨文化的特性,使得新移民女作家成为在海外最有条件、最有能力书写“文化中国”、展示中国形象的文化传播者和代言人。她们虽置身海外却坚持用汉语进行小说创作,将母体文化的影响与海外生活的感受相融合,将中国文化和异质文化相杂糅,在中西文化冲突与碰撞的全球化背景下,用文学力量传播中国文化,用文学作品展现中国文化的优秀价值,既丰富了海外华语文学的创作维度,又拓展了中国文化输出的审美路径,以其独特的女性想象和话语方式建构了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中国”。
更为重要的是,三位新移民女作家对“文化中国”的想象建构,与早期海外华人移民女作家和国内同期作家相比较呈现出不同的特性内涵。她们的创作不再过于执着地表现异域移民生活漂泊的身世之痛、断根之哀,而是逐渐从游子思乡、生存压力、文化冲突的传统主题窠臼中摆脱出来,以一种积极进取的文化自信,将小说的主题呈现转向中西文化交汇与融合的思考,转向超越地域、国家和种族的个体生命意识的关怀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未来的探寻。如严歌苓的《扶桑》《少女小渔》《小姨多鹤》《无出路咖啡馆》等,张翎《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等,虹影的《阿难》《英国情人》等中长篇小说,或直接抒写中国性格和中国精神,或通过西方人的视角彰显中国传统文化魅力,或通过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反思批判,重新确立被西方中心话语压抑的中国文化形象,或通过人性的角度反思追问,以获得文化上的自我认同,带来重新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契机等等。这些作品以深厚的社会历史和共同的文化心理属性为基础,既唤起了对中国、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多重想象和重新审视,又让中国文化以一种开放性、包容性的姿态取得与世界的平等对话,展示了全球化进程中和平崛起的中国的胸襟抱负与文化自信。
二、家国情怀的传承坚守与民族历史的深思批判
就其小说的思想文化渊源而言,严歌苓、张翎和虹影三位新移民女作家对中国的想象来自于对家国情怀文学传统的传承坚守,并在此基础上,秉承“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将笔触转向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书写。因为家国情怀更多地蕴涵在深沉绵远的历史书写之中,而“民族历史的叙述是建构民族想象不可或缺的一环”⑦。
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深入人心。家国情怀起源于士大夫的人文信仰与人生追求,并在历史文化的慢慢积淀中潜移默化地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家国情怀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之中,但随时代不断发展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现代意义上的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是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展现出来的理想追求。它是对自己国家一种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密码”⑧。它“以一种特有的信仰魅力,超越种族和民族、宗族和地域、阶级和阶层、政党和意识形态,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⑨。
新移民女作家严歌苓、张翎和虹影都出生成长在大陆,如严歌苓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参军入伍,还当过战地记者;张翎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虹影对重庆南岸贫民窟生活的童年印象和特殊身世等,都表明她们青少年时代深受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浸染。成年以后她们相继出国留学工作,又都亲身感受到中西两种文化冲击所产生的失落与焦虑。可以说,国内生活的个人经验、血脉相连的母国记忆、海外特殊的生存境遇、世界多元文化思潮的吸引影响,使得中国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历史传统和西方人文价值观念深深植根于她们的创作意识之中。因此,三位新移民女作家在对历史记忆既深情关爱又深层反思中表现出来的中国想象,不仅延续了家国情怀血脉相连的文化传承,而且不再囿于本民族立场或仅仅是一种怀旧伤感情绪的倾诉。她们试图以边缘人与女性的双重视角重新审视和想象民族历史,在强调个人、家庭与国家三位一体价值同构的基础上,更加凸显作为个体的人对共同体的一种认同与价值。正如严歌苓所说:“个人的历史从来都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属于个人。”⑩所以她们认为关注个体的命运就是关注家国历史的命运,而且对个人的情感和命运分析把握得越准确透彻,家国情怀的内涵意蕴就揭示得越生动深刻。
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以海外女性的叙事视角开掘红色历史资源,但作者却重点表现了一个为爱执着、爱一个人至死的女性田苏菲三十几年的情感轨迹和生存境遇,将红色历史内化于个人的生命体验中,构建属于女人个人的浪漫情感史,并将其提升到“史诗”层面上,凸显了在历史叙述中个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第九个寡妇》以女主人公王葡萄从童养媳到寡妇的传奇经历,重新诠绎了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末特定的家国历史,特别是对她身上体现出的坚韧旺盛的生命力、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既从女性与母性的角度彰显出潜藏于历史背后的人性力量,也渗透着西方对神秘而古老的东方的文化想象与文化期待。《金陵十三钗》则立足于南京大屠杀的创伤性记忆,在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下,通过秦淮河13个妓女保护教堂里唱诗班少女而李代桃僵、以身饲虎的壮举,揭露日本侵略者血腥残暴的罪行带给中国人地狱般的噩梦,展示了这些女性在民族国家遭受磨难、耻辱的关键时刻超越卑贱身份、杀身成仁所蕴藏的巨大救赎力量和人性深处怒放的光辉。“妓女身体成了被凌辱的中国的象征符码,并承担起呵护、修复民族尊严的历史重任。”⑪应该说,严歌苓通过塑造这些作为历史主体的女性形象,构建了一个坚韧宽容、不屈不挠、维护民族尊严的“中国”,其独特之处是“将女性之于国族史的功能、价值和意义进行了矫正与反拨。在她那里,女性为历经苦难的中华民族提供着“家/国”的温暖想象,并成为历史和国族精神的主体象征”⑫。这也是作者在西方话语背景下艺术把握“个人”与“历史”“东方”与“人性”中想象中国的重要贡献。《陆犯焉识》则以男性视角展开叙事,在反观自己家族命运的同时,重点叙述以作者祖父为原型的主人公陆焉识的悲剧人生,深刻探寻在20世纪中国动荡历史和政治变迁中知识分子个体的命运遭际、精神境遇和家国情怀,体现了作者对人性关注的悲悯包容,对民族国家历史之痛反省的责任担当。
张翎的长篇小说《金山》是一部展现百年海外华人血泪奋斗史、书写中华民族传奇与史诗的气势恢宏之作。小说既以个体和家族命运为切入点,通过清末华工方得法一家四代人在异国他乡所遭遇的悲惨处境,真实再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走向世界举步维艰的坎坷历史,屈辱悲怆,催人泪下;更记述了方氏家族成员深入骨髓的“国之不存,何以家为”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情怀,如方得法的次子锦河二战期间倾尽自己全部财产,向广东国民政府捐赠4000加元用于购置抗日所需的飞机,并自愿参战最终在法兰西战死,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心怀天下的民族正气歌。张翎的其他作品也都注重个体生命意识多向度的历史重构,以女性的自觉发掘深埋于历史皱褶缝隙中的故事,在超越种族、国别界限的历史时空下,构成共时性的人类心灵经验,如《余震》以女性主人公王小灯灵魂的痛苦挣扎,着力表现了灾难给生命个体带来的心灵创伤以及对人性宽恕美好品质的呼唤与弘扬;《阵痛》以抗战、文革和“9·11”等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书写三代女性传奇般的生育经历和命运磨难,既彰显了母性洞穿一切苦难的坚忍不拔和强大的内在生命力,也以一代代女性孕育生命的“阵痛”隐喻的家国之痛和人类之痛,构筑起社会文明进程中承载历史的丰碑。虹影的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通过私生女“六六”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饥饿屈辱和母亲苦难一生的讲述,紧扣饥饿主题,不仅将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历史在一对母女的个人历史里真诚而坦率地展开,而且把这种个人的饥饿和家庭的苦难上升为社会历史的饥饿痛苦,隐喻了中华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成长之痛,在复活了个人记忆的同时,唤醒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沉痛记忆与理性思考。
由此可见,三位新移民女作家在民族历史想象和家国情怀书写中,虽叙事方式各异,表现手法迥别,但都普遍关注历史进程中个体命运的沉浮变化和历史给个人带来的切肤感受,尤其注重表现女性个体存在的生命意识、生存状态以及她们身上蕴涵的精神力量。一方面将女性个体人生际遇和情感历程的诉说上升到民族、国家的记忆书写,显示了以启蒙主义思想反思历史、批判历史的高度与力度;另一方面将特定历史作为透视人性的场域或背景,彰显了以女性主义立场张扬人性、发掘人性的深度与厚度。在超越历史、种族和时空界限的探索追寻中,凸显对人类共同情感的体认尊重,对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理解沟通。
三、“落地生根”的精神诉求与文化身份的认同重建
受中国人安土重迁传统观念的影响,早期华人漂洋过海到海外讨生活,只是希望有朝一日衣锦还乡、“落叶归根”,这是他们去国怀乡的未来梦想和精神寄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严歌苓、张翎、虹影作为海外新移民女作家的代表,尽管出国前有着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迥异的个人经历和各自的美好梦想,但都能以“将自己连根拨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⑬的果敢坚韧精神,自觉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完成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生命的移植”。这种“落地生根”不仅仅基于居住环境、工作条件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安定、改善和提高,而且直接催生了她们在解决了生存问题后一种新的精神诉求,即对身份认同的重新思考与建构。
所谓身份,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自我的一种认定。对于移居海外的华人来说,其身份具有两个属性,一是在法律、政治层面上物理身份,即她们在外国取得合法居住权,这是可变的;二是与生俱来的中华民族身份,这是深深植根于意识深处、难以改变的的文化身份。“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又可译作身份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⑭这种早已浸入生命骨血的民族文化记忆与新的异质文化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往往就体现在海外移民对文化身份的认同上,因此海外移民的“身份”主要是指“文化身份”。随着在居住国的落地生根,严歌苓、张翎、虹影等新移民女作家以更加开放的眼光、更为宽容的心态,在文化冲突中寻求融合互补的可能性,将创作转化为一种肯定自我价值、建构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显示出她们对中国想象书写与早期移民女作家不同的新特质和时代意义。
首先,三位新移民女作家尽管描写了新移民迁入异地过程中的落地之痛、生根之苦,也展示了种族、性别、文化“他者”处于层层叠加的弱势边缘境遇中的身份“错位归属”或“无所归属”,但她们却能够从早期移民文学对于身份认同的感性倾诉中跳脱开来,冷静清醒地看待身为“他者”在异质文化冲突中所无法摆脱的“落地”之殇,并通过对个体生命经验的理性描写,走出“割不断”与“融不下”的两难境地,既表达了她们渴望尽快融入居住国主流文化的潜在意识,也体现了她们重新考量和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以获得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如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无出路咖啡馆》,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描写了“我”这样一个在异国他乡孤身闯天下的新移民女性,虽然生活在异质文化的夹缝中,但面对种族的歧视、生存的艰辛和身份认同的困惑,女主人公既不惊慌失措,随波逐流;也不封闭自守,虚妄无奈,而是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坦然正视异域生存的代价,勇敢摆脱FBI调查,毅然离开检察官男友,在文化心理、生活习俗等方面的自我调整、适应、奋斗中,努力实现自己作为“寻梦者”的人生价值,在精神向度上重塑了民族自信。实际上,在海外移民华人遭受种族歧视的背后,往往是一种身份认同上的困惑与焦虑,张翎在长篇小说《金山》中“真实地展示了方家四代人因遭受种族歧视而导致在文化身份认同上的焦虑,但从方得法到锦山和锦河、从方延龄到混血儿艾米的方家每一代人,都在思考和寻找着自己的身份与价值”⑮。
其次,三位女作家对中国的想象从踏入异域“失去自我”到夹缝中生存中“寻找自我”再到“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谁”的深层追问,几乎都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到了海外女性移民身上,并把笔下移民女性身份追求赋予其民族国家隐喻,以此来重构新移民的“中国”身份。如严歌苓的小说《扶桑》叙述北美第一代华人移民妓女扶桑被贩卖到美国西部的生活遭遇与离奇爱情故事。作者一方面以扶桑的悲苦身世、受难身体来隐喻当时遭受欺凌侮辱的中国,另一方面又以她二寸八的小脚、乌黑的发髻、迷人的挂饰、温顺的眼神等神秘的东方景观,吸引着白人少年克里斯,只是这种吸引更多的是基督教男性对弱者拯救的欲望。扶桑想要的是爱,而不是拯救,或者说根本不需要、也不想要被拯救,于是她拒绝了克里斯的求婚,最终一身锦绣地嫁给了屡遭通缉的大勇。短篇小说《少女小渔》中,身处异国的小渔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而自怜自叹,也没有因为自身文化身份的卑微弱势而向强势文化轻易低头,她始终保持着自己做人的尺度,以善良、纯真和宽容来反抗江伟的男权束缚、感化垂暮之年孤寡的意大利老头,涤净了弱势文化处境下的龌龊与屈辱。这两篇作品,形象地阐释了作者对文化身份认同的理解,同时用凝聚在东方女性身上的民族文化精神传达出对中国的认同。
张翎的小说以更为广阔的视域,着力表现了跨越文化、种族、地域的人类共性主题,体现了作家顺应时代发展全新的文化身份观。她曾一再申明:“从老一代移民到他们的后代,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是落叶归根,后来是落地生根,到现在,应该是开花结果的时候了,所以,我要在‘文化冲突’的这个旧瓶里装上新酒,让读者从作品中感受到中西文化中共通的东西。”⑯长篇小说《交错的彼岸》以巨大的时空跨度,讲述了此岸与彼岸两大家族年轻一代跨越太平洋双向寻找自我身份、寻找理想精神家园的艰难历程。主人公黄蕙宁、黄萱宁姐妹从温州到加拿大多伦多寻找另一种生活,经历一场情感纠葛后,迷茫的蕙宁独自回到故乡,但这并不是她在西方强势文化压制下的被迫回乡,也并不意味着对异质文化的排斥与断绝,而是新移民者“向内转”主体意识的觉醒。与蕙宁相比,妹妹萱宁则在多伦多站稳脚跟,让人们看到了成功融入到异质文化中的希望。《邮购新娘》延续了《交错的彼岸》的“寻找”主题。小说女主人公江涓涓作为林颉明的未婚妻来到陌生的异国他乡,本想依靠已在多伦多扎根立足的林颉明改变自己的身份,但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她与林颉明的恋爱潜伏着难以沟通的危机,于是她成全了塔米与林颉明的爱情,并凭借着自己的艺术才华和拼搏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服装设计梦,完成了她在海外身份的重要跨越。作品交织着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以及移民身份认同的焦虑,但作者无意于此,而是借江娟娟与林颉明和塔米的关系,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中西文化从冲突走向对话、从对立走向融合不可抗拒的艰难过程。
虹影与严歌苓、张翎等因移民经历导致身份认同的困扰有所不同,其私生女的身份、父爱的缺失成为虹影生命中萦绕不去的永远的痛,也是她寻找身份认同的起始点和助推力。旅居伦敦十年的离散生涯,文化的差异,精神的“无家”,使得她一方面从对自我血缘身份的寻找,开始扩展到关注族群身份的自我界定,拓展到对女性自我身份认知困境的反思,如《饥饿的女儿》女主人公“六六”等。另一方面在对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以及性别与民族、文化等问题的客观审视与大胆探究中,将自我身份的寻找上升到“文化身份”和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上,如《阿难》通过身份难辨的阿难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悲剧命运,不仅隐含了作者对文化认同与文化身份的寻找,表达了对“找得到阿难,找不到自己”的人类灵魂拷问,而且痛切地揭示了全球化和现代性的背景下中国的精神困境。备受争议的长篇小说《英国情人》(原名《K》),将时代背景设置在抗战爆发前后的中国,通过讲述闵与裘利安跨国之间迂回曲折的情爱故事,探讨“当时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是怎么样的关系”⑰。两个人的激情相遇,是他们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文化的邂逅,他们因文化差异而吸引,也因文化差异而分手。作家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坦然面对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隔膜,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寻找两者之间的契合点,表达了对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渴望。她曾表示,凭借对东西方的文化冲突和理解,我觉得自己“有这个义务或责任来写一本东西方可以相互沟通的书,或者在文化冲突不可调和的情况下,试图找到一个途径解决”⑱。
总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世界范围内跨国流动、移居的常态化,从文化的冲突、对立逐渐走向文化的认同、融合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如何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碰撞与交融中,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与自信,重塑全新的“中国”形象,当代文学尤其是小说则无疑是最生动、最出彩的重要担当之一。王德威认为:“小说家是讲述中国最重要的代言人。”⑲置身异质文化碰撞冲突中的严歌苓、张翎、虹影等新移民女作家,以女性特有的想象方式和新的国际视野,通过小说这一流行的文体超越时空障碍,书写中国故事,展现的是从异质文化冲突到融合的中国想象,表达的是人类文化之间互理解融通的愿望。从深层根源上来说,这既是她们“落地生根”后对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内在诉求,也是对传统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传承坚守,更是当代中国和平崛起对海外移民作家的激励召唤。不仅体现了全球化大背景下想象中国的一种转型与深化,而且昭示了新移民小说独特的文化价值与世界意义。
①王一川《中国人想象之中国——20世纪文学中的中国形象》[J],《东方丛刊》,1997年第 1、2辑。
②⑦[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序言。
③王京生《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解读》[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月8日第7版。
④⑥郭齐勇、郑文龙《杜维明文集》(第5卷)[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页,第409页,第430页,第439页。
⑤梁燕城《建设文化的共同体——参加政协会议后的反省》[J],《文化中国·卷首论语》(加拿大),2012年第1期。
⑧徐文秀《多一些“家国情怀”》[N],《人民日报》,2012年1月20日第4版。
⑨杨清虎《“家国情怀”的内涵与现代价值》[J],《兵团党校学报》,2016年3期。
⑩严歌苓《穗子物语·自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1页。
⑪李永东《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J],《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⑫曹霞《“异域”与“历史”书写:讲述“中国”的方法——论严歌苓的小说及其创作转变》[J],《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
⑬严歌苓《少女小渔·后记》[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页。
⑭王宁《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J],《外国文学》,1999年第4期。
⑮马德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族小说民族国家想象的路径探求——以〈白鹿原〉〈第二十幕〉〈金山〉为例》[J],《文艺评论》,2015年第11期。
⑯《华裔女作家张翎:写出落地生根的情怀》[OL],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9年8月8日。
⑰张英《虹影访谈录——关于新作〈K〉及其它》[J],《作家》,2000年第12期。
⑱虹影《谁怕虹影》[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年版,第131页。
⑲徐鹏远《王德威:小说家是讲述中国最重要的代言人》,http://culture.ifeng.com/a/20150606/43920875_0.shtml,凤凰文化,2015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