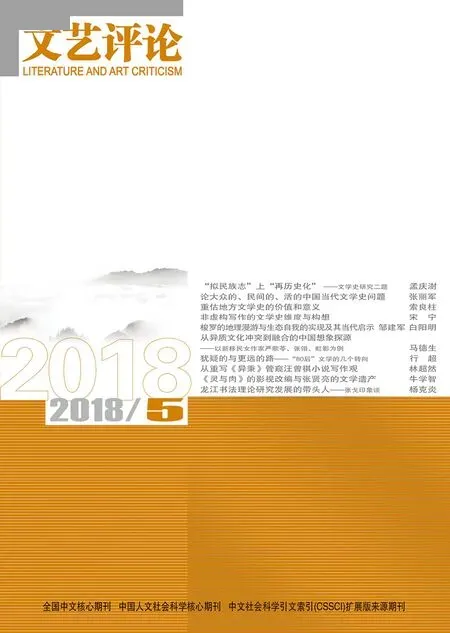非虚构写作的文学史维度与构想
○宋 宁
除却新时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对美国非虚构写作的介绍和观望,近十年间以“非虚构”为旗帜的当代文学实践,可谓异军突起,蔚为大观,随之而来的关于非虚构写作的研究,亦方兴未艾,聚讼纷纭。然而,此时提出非虚构写作的“入史”问题并非为时尚早。作为“十年一小变”的时代产物,非虚构写作已呈现从新锐、突击转为常态、稳定、繁荣发展的态势,而且从文学史角度观照当前文学现象、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也是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
一
以文学现象、思潮的维度来考量,非虚构写作毫无疑问将会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视野。首先,非虚构写作经历了一个不算太短的发展历程,并有着可预期的繁荣的发展前景,文学史叙述的脉络日益清晰可见。历史的节点是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推出“非虚构写作”栏目,接连刊登了几部重量级作品,如梁鸿的《梁庄》、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李娟的《羊道》、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等作品。之后,其他刊物和作家纷纷进行非虚构的尝试,网络和新媒体也推波助澜,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写作现象和潮流。当然,文学史还可以叙述这一创作潮流的孕育过程,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新虚构小说、新新闻写作的引入,以及新世纪以来《天涯》《中国作家》等刊物对于民间口述实录、纪实文学的关注。文学史还可以指出,2015年非虚构作家、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有力地提升了非虚构写作的地位,对中国作家也产生很大的触动。
其次,这股写作潮流激发了一场范围广、持续性强的文学论争。论争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非虚构的特质,二是非虚构的体裁归属。《人民文学》在推出“非虚构”栏目之初,并没有从内涵上界定“非虚构”:“何为‘非虚构’?一定要我们说,还真说不清楚。但是,我们认为,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其实不能肯定地为‘非虚构’划出界限,我们只是强烈地认为,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类秩序,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这其中潜藏着巨大的、新的可能性。”①文中,不同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说法固然停留在印象层面,没有正面回答非虚构的特质,而叙事史、回忆录、传记、非虚构小说、“深入翔实、具有鲜明个人观点和情感的社会调查”等文体的枚举,也没有讲清楚非虚构与“传统的文类秩序”之间的关系。之后,众多研究者围绕非虚构写作的这两个主要问题进行了论争。
关于非虚构的特质,写作者和研究者都认可它是崇尚真实、呈现事实、寻求真相,但在“真实”观上出现较大争议。非虚构写作的真实观,显然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来源于生活,又超越生活”的真实观,而是力求无限接近社会现实本身。而质疑的声音,一是从哲学上指出,语言、文学与意义、现实之间存在永远无法抵达的隔阂;二是,从非虚构写作倾向上指出,非虚构作家或口述者眼中的现实与真实,实际上具有主观性。然而,不可否认,非虚构作家直面社会历史和现实的介入性写作姿态,是时代需要的,也是令人敬佩的可贵的文学担当精神。比如,慕容雪村在《中国,少了一味药》中讲述自己卧底江西上饶的传销组织,帮助公安机关打掉传销团伙,解救了人员,并真切地呈现传销组织的洗脑过程,暴露了社会现实和社会心理问题。梁鸿非虚构书写的姿态更加复杂,《中国在梁庄》选择自己的故乡作为当下中国村庄的个案,写出了自己眼中在乡农民的种种生存状态,而《出梁庄记》通过走访调查梁庄的散布全国的农民工,触及到现实社会中的城市管理、乡村留守、北漂、生态等诸多问题。“事实上,梁鸿作为梁庄‘女儿’的叙述身份,不仅为梁鸿的‘非虚构写作’提供了进入梁庄人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的有利条件,而且为这一非虚构文本注入了饱满的生命之气。”②同时,梁庄“女儿”不仅保持着与故乡的血脉联系,而且体现着现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作为当代知识分子,梁鸿以其‘梁庄书写’诠释了她对‘新命’的担当与思考”③。也许,读者对非虚构作品的主观性、在场性生成的情感共鸣和理性认同,正是非虚构写作得以发展壮大的持续生命力所在。
非虚构写作作为新世纪重要的文学现象、思潮无疑可以进入文学史,但在安置代表性非虚构作品时必须解决第二个争议焦点,即非虚构的体裁问题。对此,大致有两种意见,一是“文体说”,即非虚构是一种新型的文体,可以与散文、报告文学等文体并置;一是“文类说”,包括报告文学、口述史、自传等各种纪实性文体,甚至以非虚构代替广义的散文,可以与小说、诗歌、戏剧并置。目前,这两种认知和实践在文学活动中一直并存。因此,不妨以入史的角度进一步讨论和构想。
二
以文体的维度来考量和构想,非虚构作为一种新型文体入史对现有文学史格局变动不大,但需要厘清非虚构与报告文学的关系。
其实,在有关非虚构写作的论争中一直夹杂着对报告文学文体的反思和再认识。进入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的发展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李炳银认为,“报告文学精彩作品的稀少,正是因为报告文学与人民的现实关注点的偏离,是作家在纷纭的现实社会矛盾现象面前把握的盲目和无力”④。丁晓原在专著《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年观察》⑤中论述了报告文学创作出现的几个主要问题,比如报告文学存在着高密度的低调作品主题、严重的模式化倾向、艺术上的大滑坡等。而近年来在鲁迅文学奖等评奖中非虚构作品的境遇,更是将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写作的文体之争推向了风口浪尖。报告文学兼有新闻文体的特征,强调客观真实,承担着特定时代的新闻功能。同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报告文学又被赋予宣传和意识形态功能。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短期繁荣也是这两种因素使然。比如,理由的《扬眉剑出鞘》写击剑运动员栾菊杰获得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击剑金牌的背后故事。这篇报告文学让读者了解到一名击剑运动员背后的艰辛付出和枯燥生活,为运动员坚韧、奉献、爱国精神而感动,并且了解到栾菊杰在国外比赛的各种情况,满足了好奇心。然而,在多元文化和新媒体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报告文学的宣传和意识形态功能逐渐显露出僵化的局限,新闻报道功能也大打折扣。“而近年的部分纪实作品穿着‘直击现实’的华丽外衣,为权势人物歌功颂德,而对底层和边缘弱势群体视而不见,放弃了对社会公平、正义和良知等普世价值的坚守,对广大读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弱。”⑥当报告文学等纪实性、新闻性文体与历史使命和时代需求发生裂变,便陷入一种危机。
而非虚构写作的兴起,恰恰试图修复和弥补这一裂痕。慕容雪村在《中国,少了一味药》的序言中写道:“我希望看到希望。这希望很简单:让常识在阳光下行走,让贫弱者从苦难中脱身,让邪恶远离每一颗善良的心。”⑦梁鸿说道:“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情景:故乡、大地,和生活在大地上的亲人们。它们正在成为中国发展中的‘问题’‘阻碍’和‘病症’,这使我非常痛苦。我必须弄清楚他们的生活、精神和悲与痛,才能够继续走下去。”⑧非虚构作者用自己看到的真实事件和人物来呈现社会底层现实,不仅仅是对底层人群的关怀,还能引发读者对现代化发展真相的思考。“我们不仅触摸到微渺而又坚实存在的生命之根,而且感受到广袤的大地上乡土中国现代性蜕变的痛苦灵魂。”⑨优秀的非虚构作品浸染着人文关怀、现实关怀,从个体、细微之处折射宏大和深刻。“梁鸿的‘梁庄书写’提供了这个时代鲜活、微观和精神深度的‘非虚构’文本。”⑩
那么,非虚构写作是对报告文学等纪实性、新闻性文体的反动而产生的具有互补性的文体吗?实际上,研究者对于两者的区分标准并不是文体因素,比如题材上宏大与日常,功能上政治宣传与个体诉求,以及写作追求上的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等等。而且,由于文学传统和当代文学体制,报告文学文体显然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却很可能吸取非虚构写作精神进行变革,所谓的非虚构文体必将消融于报告文学之中。所以,非虚构以文体入史,尽管很容易进入现有文学史格局,但便会成为一个有争议的、短暂的权宜之计,同时还会降低非虚构写作的价值和发展潜力。
三
如果大胆地以文类的维度来考虑,非虚构则可能重构文学史。以新的观念重构文学史并非不尊重史实。因为文学史家们考察文学史有着个体审美趣味上的差异,更有时代文化氛围的束缚或暗示,后来者可以不断回顾历史,阐述以往人们没有意识到的历史细节、隐含意义和变革力量。
以现代文学史上对于报告文学的叙述和评价为例。在不同时代的文学史书写中,报告文学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所占篇幅和整体评价也与时代文化氛围息息相关。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把“报告文学”作为单节出现在“第二编 左联十年(1928-1937)”的“第十章 杂文·报告·小品”、“第三编 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1937-1942)”的“第十五章 报告·杂文·散文”,以及“第四编 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1942-1949)”的“第二十章 报告·杂文·散文”中。在具体文学史书写中,一方面,由于对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切身的感受,王瑶对报告文学的界定既重视其社会内容,也强调文学审美性。即来自“西欧的报告文学”,“它不一定要有完整的故事结构和综合的典型,而是以艺术的手腕来表现某一特定的社会面或事件的过程,根据作者所体验的事实基础用形象的手法报告出来”⑪。并指出在当时中国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面前很多有体验的作者写出了报告文学,有通讯、回忆录、特写等。初期的报告文学其实是包含通讯、报告、速写、特写等一些文体在内的广义的概念。另一方面,在新中国的政治话语环境中,王瑶对报告文学评价带有政治倾向性。首先指出“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产生是“左联”倡导和推动的。之后的低谷,一是由于作家大多身处都市,不太容易和生活发生最直接的接触;二是因为国民党严苛的检查制度使得暴露现实的报告文学难以发表。但报告文学在抗战初期成为主要的文学样式,之后在解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报告文学成为宣传的有力的文学样式,内容多是来自战争前线的报道和对英勇战斗精神的颂扬,被称为“通讯报告”。王瑶高度重视和赞赏报告文学,并且把这一文体的产生、发展都和社会政治和现实结合起来论述。而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20世纪30年代报告文学的兴起并没有单独成节,而是和游记放在一起书写;在第三个十年中以“报告文学的勃兴”为题用一节篇幅讲述抗战初期报告文学发展的盛况;但对于之后的退潮和在解放区的发展一笔带过。整体上较为简略地讲述这一文体的产生和发展,但也客观地指出“报告文学以其新闻性、纪实性吸引了大批读者”,“与它的时代同命运,共呼吸,所引起的轰动性阅读效应,往往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所能达到的”⑫。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时期纯文学评价体系中,钱理群等人用“新闻性”和“纪实性”替换了王瑶的“艺术的手腕”“用形象的手法报告出来”等说法,看似更具有学理性、客观性,但也一定程度上遮蔽报告文学的丰富内涵和审美价值。
然而,仔细考察报告文学的初期形态和丰富作品,我们甚至能够看出当前非虚构写作的姿态和诉求。在王瑶的界定中,“不一定要有完整的故事结构和综合的典型”,“根据作者所体验的事实基础用形象的手法报告出来”,不正体现了当前非虚构写作的真实观和创作路径吗?从具体作品来看,夏衍写于1935年的《包身工》,那种逼近真实的写法和几次混入包身工群体的写作过程,与慕容雪村创作《中国,少了一味药》并无二致。1936年茅盾主编了《中国的一日》,这是从三千多篇来稿中选出500篇结集而成的报告文学集。茅盾在《关于编辑的经过》里说明,“全国除新疆、青海、西康、西藏、蒙古而外,各省市都有来稿;除了僧道妓女以及‘跑江湖的’等特殊‘人生’而外,没有一个社会阶层和职业‘人生’不在庞大的来稿堆中占一位置”⑬。对于这本报告文学集,当时有评论者认为,“全书最使我们感到的就是内容的广泛,这五百篇几乎包括了中国整个的面目,无论黑暗的和光明的都毫无掩饰地暴露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获得了一幅真实的中国现状的解剖图,发现了现社会的真面目”⑭。“解剖图”“真面目”的说法正是当前非虚构写作的特质和追求。还有评论者指出,“本书作者中属于‘既成作家’者为数甚微,几乎全部是各地的‘无名作家’”⑮。这一点几乎就是《人民文学》推出“非虚构”栏目时提出的“我们也希望非作家、普通人,拿起笔来,写你自己的生活的传记”的实践。
可见,以当前非虚构写作的理念和精神,可以烛照报告文学等文体在文学史上的真实形态和面貌,乃至重新建构文学史。在文学史观上,这是对纯文学的评价体系和文学史写作标准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重写文学史”大潮影响下,文学史家们尽力剔除文学的政治色彩,乃至把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文体和作品也等而下之处置,而把现代主义诗歌和先锋派小说置于纯文学的顶峰地位。“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与一时代的意识形态建构、文化思潮演进、审美趣味嬗变等,有极为密切的关联,同时牵涉到的,还有课程设置、学术眼光以及著述体例等”⑯。在去政治化的思潮和大学教育体制之下,文学史的书写从革命文学史观转换为启蒙主义文学史观、现代性的文学史观。在这一“重写文学史”的转换过程中,文学现象、思潮、流派、作家作品有所凸显,也有所遮蔽。那么,文学史如何重现复杂多面的文学原生态呢?陈平原进一步从文学史的根底上进行了反思。“从晚清到‘五四’,中国人‘文学’概念的日渐明晰,是以欧美‘文学概论’的输入为契机的。以那个时代如日中天的‘西方标准’来衡量,绝大部分中国诗文,都显得很不纯粹,或夹杂教化意味,或追求文以载道,只能称之为‘杂文学’。正是在清除‘中国文章’中诸多‘非文学’成分的过程中,中国学者建构起以诗歌、小说、戏剧为主体,兼及部分散文的‘文学’概念,并据此撰写各种类型的中国文学史。”⑰在不可能放弃文学史这一现代文化知识体系和体例的前提下,把非虚构作为文类引入文学史,可以接续传统的“杂文学”,还可以涵盖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环境下产生的各种新闻、纪实文体。
具体而言,首先,用非虚构作为文类的方案,实际上体现了把非虚构文学和虚构文学/纯文学等量齐观的文学观。非虚构并非等而下之的文类,它与虚构文学/纯文学同样具有现代精神。区别在于,非虚构文学对真相、正义、常识的追求,对现实世界、平凡人物、日常生活、个体生老病死的直接关怀,是现代文明和现代社会中更具基础性、公共性的文学担当;而虚构文学/纯文学对于个体精神自由、审美独特体验的崇尚,是文学反抗现代性的精神髙蹈。两者都是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精神支柱和人文财富。其次,用非虚构代替广义的散文,能够解决文学史书写中长期存在的体例上的尴尬。作为现代文学四分法之一的散文来自于传统诗文二分法中“文”,但现代散文发展过程又出现继承抒情传统、讲究文学性的“美文”(小品文、艺术散文)。在文学史中,作为文类的散文与作为文体的散文始终交错在一起。以非虚构代替广义的散文,既有利于艺术散文的正本清源,也有利于其他纪实性、新闻性、实用性文体的发展。再次,非虚构写作理念还能够作为非虚构文类范围内各种文体的统一评价标准。非虚构代替广义的散文,可以改变过去散文文类只是一个“箩筐”,除了小说、诗歌、戏剧“什么都可以装”,但却无法统一评判的困境。因为非虚构内含现代评判标准,可以评论纳入此文类中的所有文体。报告文学、传记、口述史、“深入翔实、具有鲜明个人观点和情感的社会调查”等等文体自然不必说,因为违背非虚构原则的创作,必将成为文学事业上的污点,美国非虚构写作发展历程中不乏此类例子。而且,对于艺术散文等文体也可以进行评判,因为非虚构的理念显然贬斥对于事件意义和人物形象的拔高、作者情感的虚假,等等。在非虚构的评价标准下,杨朔散文的虚假诗意和余秋雨的浮夸情感,都可以适当、准确地观照和批判。
因此,在当前非虚构文学理念出现的契机下,用全新的文学史观、文类观反思和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或许更能触摸文学现场的原生态,或许更能合理地评判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面貌的文学作品。当然,非虚构写作的潮流还处于进行时,本文对于非虚构的文学史构想也停留在粗疏的浅层的阶段,这有待于非虚构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相关理论的完善和历史的梳理。
①《留言》[J],《人民文学》,2010年第 2期。
②③⑨⑩张丽军《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蜕变的痛苦灵魂——论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J],《文学评论》,2016年第 5期。
④《把诊问脉报告文学》[N],《人民日报》,2010年3月25日。
⑤丁晓原《中国报告文学三十年观察》[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
⑥蒋进国《非虚构写作:直面多重危机的文体变革》[J],《当代文坛》,2012第5期。
⑦慕容雪村《中国,少了一味药》[J],《人民文学》,2010年第10期。
⑧魏如松《〈中国在梁庄〉:直击中国农民的悲与痛》[N],《海南日报》,2011年1月10日。
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36页。
⑫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6页-407页。
⑬茅盾《关于编辑的经过》[A],茅盾《中国的一日》[C],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序言。
⑭思明《一幅中国现状的解剖图——〈中国的一日〉》[J],《光明》,1936年第1卷第9期。
⑮陈落《读了中国的一日》[J],《清华副刊》,1936年第45卷第1期。
⑯⑰陈平原《假如没有“文学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09页,第109-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