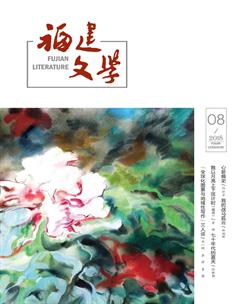我眼中的京味文学
石一枫
说实话,我本人虽然操持着一种近似口语的语言写作,而我的口语据说又是北京话,但对那种特传统、特典型的“京味小说”感觉并不格外强烈。或者说该喜欢也喜欢,但喜欢的往往是几个鲜明的人物,比如老舍的祥子虎妞儿,邓友梅的那五,陈建功那群“找乐儿”的老票友之类,这种喜欢常常源自于文学普遍范畴里的“好”,没什么来自于地域性的偏心眼儿。就像看到张爱玲写的上海女人、陆文夫写的苏州吃货,我也同样喜欢,与之相比京味文学里的老范儿北京人也没让我产生“找着亲人”的感觉。
原因很简单,那个时代的北京生活我没经历过。所谓“天篷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或者胡同口的枣树底下喝花茶一盘臭棋杀一整天的生活图景,我也只是在文艺作品里才能见识见识。老先生们尽可以抚今追昔,我要也跟着打地图炮,那就意淫得太没凭没据也太没皮没脸了。我很清楚自己连当个遗少的资格都不具备。事实上,我的童年时期基本上是在一片蓝裤子和绿裤子组成的森林里度过的,上学上的也是部队子弟学校。按当时的概念,北京西部那片大院儿扎堆儿的地方还属于“郊区”,坐地铁去趟西单都叫“进城”了。后来在东四一带上班,这才开始在胡同里穿梭,所见之人也不是坐拥朱门大宅的低调富豪就是群租在小偏房里的打工者,连说北京话的都不多见,哪有什么王掌柜、唐铁嘴、刘麻子?
以前谈到“城市和乡村”之类问题时,我说过一句实话:倘若给我空降到纽约东京,一定比扔到中华大地的某个村儿里更自在。谈到文学的地域性,我也得再说句实话:我看二环里的老北京,和看外滩的老上海、西湖边上的老杭州一样,全是些隐藏着上个时代蛛丝马迹的遗迹,同样新鲜却也同样陌生。记得以前看过某杂志组织过一批文章,找一帮北京作家写胡同,大多数人都写得温情脉脉眼泪汪汪,唯有王朔完全是一副野孩子不屑认谱牒的嘴脸,痛陈胡同里上厕所的不方便及其在胡同里打群架被人围殴的惨痛经历。在自感外化于“老北京”这方面,我想我和王朔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但和他不同,今天的我要是听说谁号称“住不惯楼房”或者“不接地气不舒服”,那么横生的就是肅然敬意与悄然妒意了,因为我知道,对方很可能已经爬上了我们这个时代资本食物链的顶端。
当然,就算并不拥有多么坚贞的文化归属感,也不妨碍我继续以“北京作家”的身份招摇撞骗,这倒不是因为北京这座城市有多宽容,而是因为北京这座城市太大也太多变了。我们都知道,除了那个仅作为历史和民俗符号存在的老北京,还有一个革命的、政治的北京和市场的、经济的北京,而后两个北京比起前一个北京,其真实性毫不减弱甚而更强。对于我来说,今天的北京更多的是一个现代巨型城市的天然样本,而这种城市总会处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就像全国各地都有装修风格、食物种类大致相同的星巴克咖啡馆,你在别处也就是“蹭蹭网,发发呆”或者跟披头散发的布裙女子聊聊人生,而在中关村的星巴克却会目睹神情亢奋的理工男喝着三十块钱的咖啡聊着三个亿的融资。要是到了东四环外野模遍地的“文化产业园”里,没签过阴阳合同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了。我们总是说《安娜·卡列尼娜》写到了多么深刻多么宏大的主题,但却总是忽略安娜自杀为什么选择卧轨。这也许仅仅因为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刚刚普及了火车,托尔斯泰就是这样直截了当地强调了安娜的故事只能发生在他的当下而非过去。同样,北京的安娜想必也是会顺理成章地“卧轨”而非投井、服毒、像尤二姐一样吞金,这也是因为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中国最为明显、强劲、不容置疑的当下性。不过话分两头说,题材的优势往往意味着题材的难度,人人都看到的东西也就等于人人都有发言权和评判权,如果你所写的北京不像今日之北京,那么任何一个非专业的读者哪怕是并不生活在北京的人都会指出你的纰漏。基于这个原因,以北京为题材写作的作家既占了这个地方的便宜,也得清楚便宜不是说占就能占的,它要求你有着更加客观、全面的观察,也要求你尽量保持一个生活中人的状态,而非任性地成为书斋里的作家。
再说回到那些京味文学的经典作品中去,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老舍之所以是老舍,并非仅仅因为他写了小羊圈胡同和一群形态各异的老市民,更是因为他所触及的往往是一个时代最主要、最无法回避的社会历史问题:阶级分化、民族救亡、旧时代的消失与新时代的来临。作为一个特殊的城市,这里的人和故事天生与时代的走向息息相关并且可以成为一个国家命运最典型的代表,也许这才是北京对于作家而言最重要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京味”如果只是作为一种腔调存在,其意义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而足够宽广、深邃和具有总体性的视野和眼界,才是这个地方文学风貌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