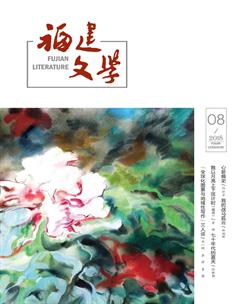没有进入写作的语言,都深陷寂寞
贾想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语言之树上的花与叶。如果要讨论全球化进程当中文学的命运,必须首先考察各种语言的命运。
全球化对于霸权国家的语种而言,是福音,是一场帮助殖民的春风。但对于边缘国家、民族、地区的小语种而言,却是一场破坏性的风暴。如今,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语言,战战兢兢地走在全球化的薄冰上,稍不留神,就要坠入冰窟,静悄悄从人间消亡。语言学家统计,平均每十四天,就有一种语言在全球化舞台上黯然谢幕。
如果一个语种足够幸运,它会在历史腹中孕育出自己的文字,自己的文学,自己的写作传统。但事实上,大部分的小语种仅仅是一种交流语言,一种“说”,没有诞生自己的文字,成就一种“写作”,进入历史的叙述。所以,对于文学,它们自始至终是“不在场”的。眼下,它们正在悬崖边上的麦田里排着队,被全球化的风推着身子,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向深渊。没有霍尔顿·考尔菲德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守望它们,阻拦它们。所以,它们只能一个又一个地朝那遗忘的深渊坠去。这坠落如此寂寞,没有丁点声音。
只能进入“说”,不能进入“写作”,也是马来西亚的华文所处的境况。马来西亚语正在同化居留地的华侨,大部分用华文写作的作家都销声匿迹了。马华作家黄锦树在小说集《雨》的后记里说:“在我们南方,没有文学并不奇怪。有,才奇怪。”他面对的,是马来西亚华文这个语种,即将丧失写作能力的危机。因此,他的充满马来西亚风情与热带雨林气质的小说集《雨》,本质上是对全球化语言风暴的一种积极的对抗,是一只拦在悬崖边的手。他让马华文学暂时留在了“写作”当中。一个语种,只要还能用于写作,那它和它所包藏的地域性文化,就是安全的。
消亡的危机,对于大陆的当代文学写作尚且构不成威胁。恰恰相反,相对于马来华文的衰落,大陆的现代汉语写作,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强悍的生长性之中。但全球化当然也对大陆的汉语写作造成了影响。只是影响并不致命,而是呈现为另一种温和的形态,发生在译介的领域。
中国对于西方文学作品的译介,可以追溯到清末民初,追溯到林纾、严复、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人。但一直到晚近,文学的译介基本是单向的,以引入为主。而且对资产阶级文学的引介一直时而放时而收,若即若离,抱有警惕。全球化进程开启以来,一种更为立体的译介才宣告开始。越来越多当代文学经典被翻译到海外,形式各样的西方当代文学作品也涌入国内。
更为自由的译介,慢慢消解了汉语与其他语种之间的边界,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汉语的个性与传统。各个语种的语法你侬我侬,互相在翻译中渗透,催生了一种杂交的“语言共同体”。表现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就是“翻译腔”的语言。或者到处是长句,或者到处是花里胡哨的想象性修辞。而马尔克斯腔、卡夫卡腔、加缪腔、村上春树腔,更是一抓一大把。这时的写作,使用的不是语言,而是语言的脸谱。本土的语法,如泥沙入海,失去了完整的形体。
这里必须重新思考现代汉语,也就是白话文,这个只有一百年历史的语种的诞生。虽然称之为“汉语”,但形成之初,白话文的语法却是“全盘西化”的激進果实。五四新文学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对古典汉语的“斩草除根”运动,这与启蒙逻辑下彻底斩断民族劣根性的精神要求是一致的。所以,现代汉语表面是现代中国的形象,其实在基因里,在血液里,是一个西方的形象。这就很容易理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为何中国的当代作家能那么迅速地掌握翻译语言,学会“翻译腔”。因为“翻译腔”的形成并非语言的抄袭,或者语言的致敬,而是语言的“滴血认亲”,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所以,本土的、最为中国的语法,早在现代汉语形成之初,就丧失大半了。
在写作中保存本土的、中国的语法,是全球化潮流下,从根茎深处保留住“中国性”或者“地域性”的法门。我认为需要守护的语法有两种:一种是古典汉语的语法,一种是方言的语法。古典汉语的语法,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一直有作家在试图恢复。比如贾平凹的《废都》,格非的《人面桃花》,刘斯奋的《白门柳》。但方言的语法,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写作者足够的重视。金宇澄的小说《繁花》和李瑾的散文集《地衣》的意义,在这个层面凸显了出来。
“小毛呀,唱得真好,唱得阿姨,馋唾水也出来了,馋痨虫爬出来了,全部是,年夜饭的好小菜嘛,两冷盆,四热炒,一砂锅,一点心。赞。”“月轮残淡,天越来越明,鸟鸣啁啁然,逐渐响亮,终于大作。”“四个荒唐子,三更流浪天。”这是《繁花》,操的是苏北方言。文白相间,气息匀畅,亵中藏庄,杏花微雨,软糯似吴人。如清水上落芙蓉,左一朵,右一朵。笑气一升,日子就度过去。笑声一停,悲哀又聚拢来。“半天憋不出几个羊屎蛋子。”“肚子里狗肠子、驴下水不少。”“种儿多了,出不齐啊。”这是《地衣》,山东“老话儿”。鲜活,荤中带咸,话糙理不糙,字字拧出油水。是有根的语言,扎在民间的黄金与粪土中,深不可测。
你隐隐感到了这两种方言似乎在对抗着什么。像一个汉服飘飘的女人走上摩登大街,以对抗席卷当代生活的时尚一般,它们也在对抗着当代汉语写作当中的某种时尚语言。这种时尚语言,就是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的前言里坦诚说出的——他所操持的“北方官话”。写作的杂语性在此被揭示了出来。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个各种语言活跃的“场所”。
北方官话这些隐秘的气质,在《繁花》的叙述中暴露无遗。《繁花》以苏北吴音为叙述语言,但时不时掺杂几句北方官话作陪衬。比如陶陶的情人潘静的普通话。于是情形被倒置了:方言反而成了主人,而北方官话成了小说的稀客。
《繁花》中最常出现的一句北方官话,是阿宝的那句来自“文革”大字报的口头禅:“我不禁要问。”这句话出现的语境是什么?是对人的强制怀疑,对人的一切言行的不信任。这个反问句贯穿小说始终,既是意识形态的残骸,也是对小说中出现的全部故事的不怀好意的质疑。问啊问,小说一直从流逝年代,问到了九十年代。问遍了世上的恶形善状,起伏冷暖。如匕首,仿佛永不会腐朽。
时代的印记烙在官话的身上。而方言留住了味道,留住了本土文化的根。因此,《繁花》与《地衣》对方言的捡拾、保存、淬炼,不仅是语言艺术方面的策略,更是一种文学写作观念的突破。这种让方言脱离“说”,进入“写作”的观念,提示我们的写作应该更加关注“民间话语”“地域性话语”“本土话语”。这是写出“中国故事”的语言基础。
一切没有进入“写作”的语言,都排着队,噤着声,在毫不知情地走向万丈深渊。它们深陷在危险的寂寞当中,等待着被关注,被打扰,被拉入这个时代喧闹的写作现场。正如废名小诗所传达的深意: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驰过,/乃有邮筒寂寞。/邮筒Po,/乃记不起汽车号码X,/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汽车寂寞,/大街寂寞,/人类寂寞。
希望这笼罩世界的寂寞,不要持续太久。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