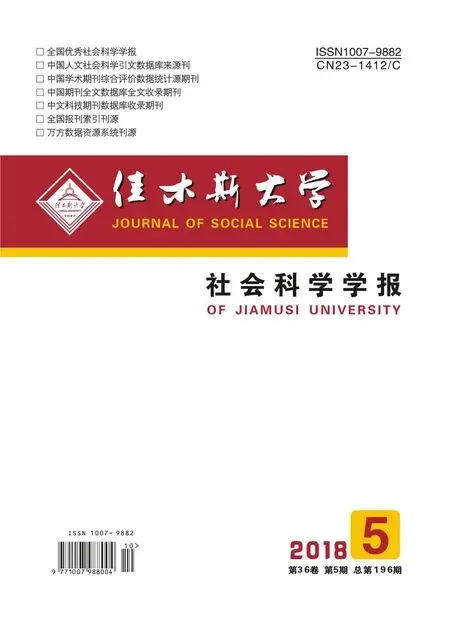美国早期禁毒立法体系与吸毒群体结构因素*
林晓东,林晓萍
(1.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2.福建警察学院 基础课教学部,福建 福州 350007)
一、早期麻醉品成瘾者人数
即使是现代社会,获取吸毒成瘾者人数的精确统计数据也非易事,更惶谈早期麻醉品泛滥时期了,这是多年来困挠美国学术界的一个研究课题。当然,在各方面统计条件均不完备的19世纪,要求得出一个精确的统计结论显然是一件困难至极之事。当时人口统计层面的技术性问题外加成瘾者参与统计活动时的消极态度,决定了依据那个时代的官方统计数据充其量也仅是基于推论而得出的非确定性结果。在不少研究者的结论中,有关早期泛滥时期的成瘾人数可谓千差百异。斯蒂芬·康铎(Stephen R. Kandall)的研究结论认为,19世纪末,美国的鸦片成瘾者数大约介于15万至20万人之间[1]36。大卫·马斯托(David Musto)则将第一波麻醉品泛滥期高峰年界定为1900年,人数约有25万[2]。美国第一部禁毒法——《哈里森麻醉品税法》的积极推动者、素有美国“禁毒法之父”美誉的汉密尔顿·莱特(Hamilton Wright)在其调查报告中推定:1909年,美国人口总数约为9,000万人,其中,鸦片成瘾者约为17.5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0.19%[3]。此外,资深美国禁毒史研究学者大卫·考特莱特(David T. Courtwright)则在其《黑暗乐园——美国鸦片成瘾史》一书中,将其结论定格在1914年《哈里森法》公布之前,推断成瘾者总数在31.3万人以内[4]9,11,13-14。
虽然在结论上成瘾者人数莫衷一是,但这些数据应该也是在现存资料基础上所能得出的比较有据可依的研究结果。以此为据,至少在1914年《哈里森法》通过前的世纪之交,美国首个麻醉品泛滥期的成瘾者数基本上可界定为15万至31万人之间,若以1909年美国人口总数9,000万人为基数,这一成瘾者数所占美国人口总数的比例约为0.167%~0.344%。尽管美国禁毒史学者将此现象称为“麻醉品泛滥”,但与近代中国遍地烟民的惨状相比,这一所谓的美国早期麻醉品滥用光景,充其量只是相较于美国历史自身的结论罢了。
二、早期成瘾者成分结构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早期麻醉品成瘾浪潮中,因病痛服药而致病原性成瘾者①人数在整个成瘾者人数中的比例远远高于康乐性成瘾者②人数。虽然具体人数比例无法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女性以及社会中上层阶级的成瘾者数曾占据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前述康铎的研究结果显示,当时美国鸦片成瘾者的四分之三为女性。这一惊人的女性占比数值意味着,在世纪之交时期,美国的9,000万总人口中,每天平均约有超过18万的女性,因其麻醉品成瘾习性而不间断地使用鸦片、吗啡以及海洛因等麻醉性药品[1]36。事实上,当时美国各地的调查数据也在很大程度上佐证了女性在成瘾者总人数中所占的惊人比例。
1878年,在1,313名密西根州(Michigan)的鸦片使用者中,女性有803人,达61.2%[5]。1880年,芝加哥市(Chicago)的235名鸦片常用者中,女性人数为169人,占比高达71.9%[6]470。无独有偶,1885年,爱荷华州(Iowa)卫生局的统计数字显示,当地63%的鸦片使用人群也是女性[7]470。需要强调的是,上述统计数据仅源自对良家妇女使用者的统计结果,却并不包含那些从事特殊服务行业诸如妓女等性服务行业女性的麻醉品滥用者人数。1880年,芝加哥市卫生局的报告指出,若再纳入良家妇女成瘾者之外的女性鸦片使用者加以统计,芝加哥市鸦片使用者的男女合理比例应为1:2[6]470。即使到1914年《哈里森法》颁布前夕,田纳西州(Tennessee)的鸦片常用者中,女性人数依然占比高达三分二之多,其年龄多集中于25至55岁之间[8]。
导致美国女性长期过度使用鸦片及其相关药品的原因很多,除部分职业女性为减缓工作压力而使用麻醉性药物之外,女性的生理周期因素也加剧了这一特殊现象的恶化。为了抑制或治疗女性成长过程中的各种妇科问题,诸如痛经、更年期症状以及其他一些常见妇科问题,女性需要不间断地从医生处获取相应于当时条件下的最佳医疗处方,长期以来为人认可的麻醉性药品所具有的特殊止痛效果自然使之成为那个时代医生开具处方时的首选药物。不难想象,该类医生处方中大幅出现的与鸦片有关的麻醉性“药品”,导致女性在长期使用处方药过程中形成对鸦片类麻醉性药物的依赖。查尔斯·特里(Charles E. Terry)因此认定,病原性成瘾现象应该是“解释这个时期女性成瘾者大量存在的合理原因。”[9]
自由无序的鸦片性麻醉品使用不仅造就了大量女性成瘾者,同时也产生了众多以成年人尤其是以中年人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乃至上层人士的鸦片成瘾者。这是早期鸦片成瘾者中,除女性成瘾者之外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成瘾群体结构的主要特征。
根据早期市政调查显示,1880年,芝加哥市,鸦片使用者中的男性平均年龄为41.4岁,女性为39.4岁[6]475;同年,爱荷华州,鸦片使用者平均年龄为46.5岁[7]17;1914年,田纳西州,鸦片使用者平均年龄为50岁[6]475。显而易见,与现代社会吸毒群体越来越低龄化的现象相比,早期麻醉品成瘾者中以成年人尤其是以中年人为主的现象倍显突出。除此之外,当年麻醉品成瘾者的社会地位及其经济状况也与如今有明显的异处。
共识机制经过了数年的发展,在经过探索和开放式创新之后,势必进入到性能安全性等的比拼之中。表1分别为PoW、PoS、DPoS面临的攻击威胁表。
1889年,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卫生局以当地医生与药剂师为对象,针对患者与药店顾客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行了一次案卷调查。其中,药剂师的回答内容显示,除去部分所属不明者,高达56.2%的成瘾性麻醉品常用者的社会地位处于中产阶级和社会上流阶层。同样地,医生的回答内容也显示仅有6%的成瘾性麻醉品常用者处于社会低层,其他的绝大部分处于中产阶级乃至社会上层[10]。
与现代社会对吸毒者的固有印象明显不同的是,即使到19世纪末期时分,在《哈里森法》颁布实施前夜,在美国不少的都市里,酗酒往往被视为地位低下者之行径,故多与低层平民关联,而食用鸦片的耽乐行为,则成为不少中产阶级乃至上流人士附庸风雅的一种时髦现象。1881年,当年的一篇文章高度典型地概括了当时美国鸦片使用者所处的社会地位:
食用鸦片并不像喝酒那般令人兴奋。较之低层民众,它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贵族的象征而更为广泛地使用于富裕阶层与受教育的群体之中。但是,没有一个阶层可避免它所带来的破坏性。相当数量的商人、律师以及医生成为鸦片“圣殿”中的牺牲品。酒鬼们的衣服或许破烂不堪,然而,那些鸦片的附庸者们则往往是一些穿戴齐整之辈。[11]
如上所述,早期麻醉品常用者主要是主流社会人群。这一群体结构决定了早期美国社会很难如现代社会一般将成瘾性麻醉品及成瘾现象视为罪恶与肮脏之物,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即使吸毒成瘾危害已被逐渐认识,有识之士也在不断呼吁,美国社会也难以对这一吸毒成瘾现象采取进一步的法律惩戒措施,不可否认,这既有整个社会对于麻醉品成瘾及其危害的认知程度的影响因素,也与社会心理状态微妙地受制于麻醉品使用群体的身份结构密切相关。毋庸置疑,在美国主流社会群体与此利益攸关,且其中又有相当部分群体视使用鸦片等麻醉性成瘾药物为时尚而依然构成成瘾者群体结构的主要成分之时,社会主流舆论很难视吸毒成瘾现象为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因而也难以针对包括鸦片成瘾者在内的成瘾现象予以真正意义上的口诛笔伐。相反地,他们更愿意视成瘾为一种“疾病”,或充其量视其为一种由不良习惯导致的较为顽固的“疾病”,故而趋向于高举轻放,不必从立法层面上对该类现象加以严厉惩戒。因此,整个19世纪尤其是世纪末期的美国,尽管舆论上的禁止呼声在不同地方日呈高扬之势,联邦禁毒法的出台节奏却大大落后于各地禁毒立法的步骤。与现代社会截然不同地,在缺乏联邦法律体系惩戒的大环境下,早期美国社会的许多成瘾者既无失业之忧,亦无家庭分崩离析之恼。无怪乎,后世的人们视19世纪的美国为“瘾君子乐园”[12]。
三、早期成瘾群体结构的变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日益增加的成瘾者人数逐渐引发社会的关注,同时,人们对于成瘾性麻醉品性质及其危害性的认知也在不断加深,同时期美国城市化带来的城市人口结构年轻化的趋势,也加速了这一时期成瘾者群体结构的急剧变化:因对麻醉性药物的危害认识渐趋提高及因高龄而逝等因素,曾经以中上层阶级女性和成年人为主的病原性成瘾者人数呈现明显递减现象,同期,以贪图享乐为目的的年轻、贫穷的康乐性成瘾者队伍则不断扩大。这一由不同群体形成的成瘾者队伍结构性占比变化,最终改变了美国主流社会对麻醉品及其成瘾现象的宽容度,继而不但影响了美国禁毒法体系的形成,而且促使禁毒法执法机构在对待成瘾现象和成瘾者问题上采取了与19世纪时期截然不同的态度与力度。
据考特莱特研究结果,1895年至1935年期间,是美国历史上成瘾高度泛滥和成瘾群体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期间成瘾者队伍的结构性变化主要表现为:中上层阶级的成年男女尤其是女性成瘾者队伍的不断缩小,低阶层贫穷人群中年轻男性成瘾者人数的明显增多。与此同时,美国毒品控制政策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由简入繁以及自轻松到严苛的变化过程[4]1。
从1860年至1910年,在农村人口仅增加一倍的情况下,美国的城市人口数量却增长了七倍之多。以纽约市为例,到1921年为止,其人口总数就从建市时期的336万人发展到618万人。与此同时,因康乐性吸毒而成瘾的城镇年轻男性也逐渐在整个吸毒成瘾者比例中呈现出持续增加的趋势。对此,当时的一些专业人士明确警告,较之从前,“年轻人成瘾者群体的比例开始逐渐增加。”[13]当年的纽黑文市(New Haven)警察署长菲利普·史密斯(Phillip T.Smith)就曾观察到麻醉品成瘾者在性别、社会阶层、年龄以及地域分布上的变化与不同阶级层次成瘾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他在1914年提到:
众所周知,麻醉品的使用习惯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曾几何时,鸦片、可卡因与吗啡的使用习惯通常源自因病服用的处方药物,而如今,使用麻醉品却成为妓女与皮条客们的一种恶习。[14]
由此可见,众多康乐性使用者的出现使当年成瘾者群体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的现象已经跃然可见,而康乐性麻醉品使用者明显的低阶层化现象也已日渐被视为一种无法容忍的社会“恶行”而被执法者明确道出。与此同时,对麻醉品成瘾认识逐渐提高,以及成瘾者人口中的低阶层化现象所带来的成瘾群体的结构性变化,也极大改变了当时医学界专业人士的固有观念。如神经学医生弗朗西斯·德肯(Francis X. Dercum)发现,在《哈里森法》颁布之前,生活在美国费城的中上流阶层成瘾者数量已经出现了较前明显减少的趋势[15]。相反地,在个别大城市里,出于康乐性目的的麻醉品使用现象以及由此导致的成瘾者人数已在成瘾者中逐步由少趋多。1917年,纽约市康乐性成瘾者数明显超过病原性成瘾者数目[16]。1904年至1924年期间,芝加哥市成瘾者群体结构变化更是显示,在病原性成瘾者日渐减少的同时,下层贫困男性则在日渐增多的康乐性成瘾者中占据了很大比例[17]。为此,考特莱特明确指出,至少到1914年《哈里森法》颁布前夕,美国的麻醉品成瘾者已明显有别于19世纪时期,即“不再集中于上层与中产阶级的白人女性之中,而是开始频繁地出现于低阶层的城镇男性队伍之中……”[4]3
四、吸毒群体结构变化的影响
上述源于早期吸毒群体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美国各地针对毒品滥用控制措施的逐渐严苛化。事实上,早在19世纪中期开始,在美国各地就已出现了在法律层面上针对康乐性吸毒现象实施不同程度控制之趋势。1875年,旧金山市颁布了最早的禁止鸦片馆令,所针对的对象显然不是早期的病原性成瘾者,而是那些康乐性鸦片烟抽吸者。尤其是,这一早期取缔鸦片烟馆的禁毒令,除了排华因素之外,其目的多来自所谓道德风俗习惯上的考虑,直指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早期外来华工,以及在社会主流阶层眼中隶属社会底层且道德堕落的白人中的男盗女娼之辈。此后的19世纪末,美国许多地方相继出台的禁毒立法,其惩治对象也多为非病原性的康乐性吸毒者,尤其是那些低阶层的吸毒者。20世纪初,纽约州法庭充斥着诸多因吸毒而违法的案例,其中许多被告就与因康乐性吸毒而违反新的反可卡因法相关。此外,纽约州的《博伊兰法》甚至直接将那些低阶层的顽固吸毒成性者扭送至流浪汉集中地加以禁闭[18]。可见,早在联邦禁毒法《哈里森法》通过之前,以厉法对待康乐性吸毒成瘾者,尤其是严厉对待那些社会低层的吸毒者,已然是美国许多地方立法目的之所在。
19世纪的美国,因其针对麻醉品使用行为以及麻醉品成瘾者的宽容态度而被视为成瘾者的乐园。如前所述,19世纪时期,病原性成瘾者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于中上层阶级人士,尤其是其中的女性使用者。在19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虽然成瘾者的种种不雅行为逐渐被其周边之人轻蔑相加,但是,当成瘾者结构依然以主流社会人群为主之时,无论是联邦还是地方,都难以做到毫无顾忌、毅然决然地举起法律惩戒大器对之加以惩戒。因此,19世纪的宽容态度也就成为当时主流社会面对众多病原性成瘾者时的一种必然选择。
20世纪的美国,尤其是从《哈里森法》颁布之后的20世纪,对于麻醉品成瘾者而言是一个严苛战栗的“古典时代”,一个完全有别于上个世纪的严厉惩戒时期。两个时代,两道风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世纪之交开始,在麻醉品知识日益丰富的美国社会中,伴随着老一代病原性成瘾者的高龄化和消逝,病原性成瘾者人数比例的逐渐减少已成历史必然。与此同时,因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而致大量底层人群与年轻人在城市人口比例中的逐年增加,也促使了至今以来康乐性成瘾者在整个成瘾者比例中的递增现象日益明显。这种此消彼长的量比关系,意味着之前成瘾者人群结构中的主流社会群体结构的高比例现象已然不复存在,而那些总是被勾勒为肮脏、喧闹、道德败坏的低阶层吸毒者形象以及各种与之相关的犯罪问题的接踵而至,激发着美国社会尤其是主流社会随时对这些凸显的社会现象喷发怒火,即使是动用法律惩戒也已无所顾忌。第一部联邦禁毒法——《哈里森法》的出现,正是发生于吸毒者群体结构发生急剧变化的水到渠成之物,一个主流社会群体逐渐淡出成瘾者人群之后的世代交接之果。
1922年至1924年间,因触犯联邦禁酒法被判入狱者的人均监禁时间为20~30天;同一时期因触犯麻醉品法被判入狱者的人均入狱时间则从1922年的10个月增加到1924年的14个月[19]472,到1928年更升至22个月[19]473。
很明显,法官与陪审员对于触犯麻醉品法者较之触犯禁酒法者严厉许多。因此,在1928年中期,联邦监狱里三分之一的入狱犯人属于触犯《哈里森法》者,其人数超过了违反禁酒法与盗车两类犯罪者之和,成为入狱比例最高的犯罪人群[20]。下表所列数据显示的是因违反麻醉品法被判入狱者数的年代变化,从中可以窥知联邦执法机构逐年增加的执法力度[21]。

早期因违反《哈里森法》被判入狱者数[19]475
对麻醉品问题危害的漠不关心或是不以为然,曾是19世纪美国历史的主旋律。导致这种现象固然缘于长期以来的惯性思维,早期成瘾者中大量中产阶级的存在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反之,长久存在的吸毒群体中的康乐性吸毒现象,伴随着世纪之交的城市化进程而引发的社会低层群体麻醉品成瘾者比例的不断增加,在不同程度上冲击着美国主流社会的传统思维。吸毒群体结构在比例上的不断变化,不仅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联邦禁毒法的立法进程,而且最终影响到早期禁毒法在执行过程中不断趋于严厉。
无独有偶,这种现象也发生于后世不同时期的美国禁毒执法过程中。20世纪后期的70-80年代,正是美国历史上集中反对快克可卡因(Crack Cocaine)的时代。在此时期,以判刑入狱作为针对快克可卡因违法者的惩戒手段,成为当年美国禁毒法的主要实施方向。其中,针对任何一个拥有50克或者以上重量的人物都将被判至少10年入监的重刑。从此之后,将违法者重刑入监,已经成为被不断扩大解释的美国禁毒法惩戒措施的主要方向,而其结果则是美国监狱成倍增长的入狱者人数。2005年,美国入狱者较之30年前增加了整整六倍之数,入狱人数达到了210万之众。莫尔的研究更是显示,2001年的某个时点,非裔黑人男性的入狱率甚至高达32%,同一时点,西班牙男性的入狱率也达到17%。与此相反,当地白人男性仅为6%,远远低于西班牙裔,更无法与非洲裔男性的入狱率相比[22]。2003年,每一天都有高达8%的美国非洲裔男性被监禁于狱中。其中,20岁后期的男性入狱率则高达12%[23]2。
与白人男性低下的入狱率相比,少数族裔的高比例入狱率显得尤为突出。结论似乎简而易懂:较之西班牙裔,尤其是非洲裔,白人守法程度远高于其他少数族裔。事实真的如此吗?事实上,无论是统计数字还是学术研究结果都已表明,答案是否定的。普罗文更是断言,少数族裔在美国长期以来所面临的种种不平与诸多歧视才是问题解释的关键所在,而法律名义下的不平等则是少数族裔入监者人数数倍增长的主要原因[23]。
五、结语
现代意义上的毒品概念并非与生俱来,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它曾以一种神奇药物的身份被长期认可。在美国禁毒法体系形成过程中,毒品之所以成为一种禁物,主要原因在于其固有的危险性或社会危害性,被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主流社会阶层逐渐接受并最终成为共同的认识,而这种社会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则基于使用者中存在着的许多边缘化人群以及社会少数族裔。美国禁毒史显示,只要主流社会舆论愿意相信这些麻醉性毒品的使用人群中存在着大量低阶层群体及其给社会带来巨大危害的可能性,禁止毒品使用以及对毒品使用者实施管制乃至惩罚也就有了大义名分与顺理成章之由。
如同普罗文所言,在美国,“在罪与罚问题上,因为信仰与习俗不同而导致的种族歧视或者种族劣势,显得尤为突出,有时甚至意味着生死攸关。”[23]2美国禁毒法体系的形成与实施过程,固然有其值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但是,一直作为弱势群体存在的低阶层群体与少数族裔却在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被涂抹以太多负面的形象并承担了超出实际存在的应有责任。作为一个历史研究对象,这种在不同层面上时时如痼疾般复发的美国式歧视,从早期美国历史到现代社会,总成为种种法律名义下的不平等现象而无处不在。忘记历史之所以意味着背叛,那是由于当既有的阴暗面被有意无意遗忘之时,那曾经的种种不平与不公依然会被不断重演而继续贻害人间。读史使人明智,本文的意义可尽在于此。
[注释]
①因病痛等各种医学上的原因而致服用麻醉品过多,从而形成麻醉品依赖症状的麻醉品成瘾者,是为病原性成瘾者——笔者注。
②因追求享受等各种非医学因素导致的耽乐性需要,致使吸毒过多而形成依赖性症状的麻醉品成瘾者,是为康乐性成瘾者——笔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