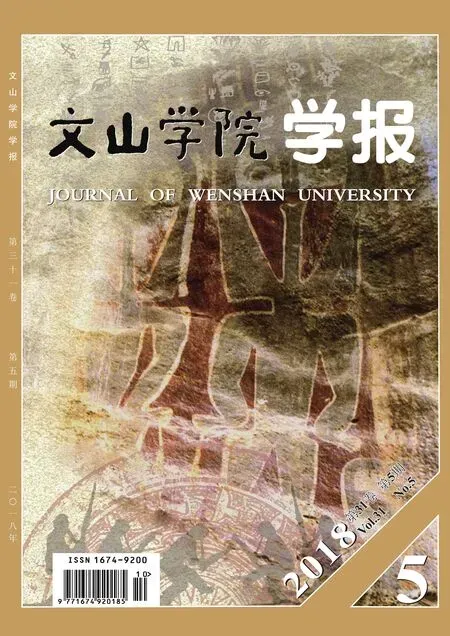文山苗族斗牛文化的内源性发展探究
李开文,张 琼,聂 鹏
(1.文山学院 体育学院,云南 文山 663099;2.云南警官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3)
斗牛是文山苗族一年一度花山节中的主要项目之一,每年的大年初六开始斗牛比赛,历来受到苗族同胞的重视。斗牛活动可以说是苗族同胞历史的活化石,是民族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也是苗族民族气质和社会特性的生动展示。“内源性发展”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社会发展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由“内源性”和“发展”两个部分组成,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原则、方式和要求,是发展的基本动力。作为一种发展概念的两个部分,二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内源性发展理论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存在着多方面的密切联系。从内源性发展的角度来看,斗牛是苗族同胞的一个群众性活动,具有娱乐与文化的双重价值。如果将内源性发展理论移入苗族斗牛传统文化的发展研究中,便能更好的探寻苗族斗牛文化的本质及发展。
一、苗族斗牛文化的内源性
(一)斗牛的祖灵意象
苗族牛崇拜与其始祖蚩尤有关。《山海经·东山经》记载:“太山……有兽焉,其状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见则天下大疫。”[1]67,100,117《山海经·中山经》记载:“鳌山……有兽焉,其状如牛,苍身,其音如婴儿,是食人,其名犀渠。”[1]38,60《龙鱼河图》说:“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身兽人语,铜头铁额,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不仁不慈。”[2]从以上可看出蚩尤正是原始社会末期被描写成“其状如牛”的人。蚩尤部落原为南方部族,后由于经济发展而向北扩张,由于战争失利,部族成员各散四方,奔回南方的部落成员后裔就有今天的苗族。因为蚩尤部族崇拜牛,因此将其装扮为“人身牛首”,牛也便成为蚩尤的象征。
现存的《花山起源之歌》中“苗家住黄河坝上,苗王名叫蒙孜尤。 是他领导真有方,人人生活不忧愁,不知哪样叫花山……族长心里多忧愁,眼泪悄悄心里流,背着大刀上山去,砍下枫树插坝上,将事告诉众苗人,这是苗家踩花山。”[3]在花山节祭祀花杆时祭师说 :“今天是个吉祥的日子,子酉是我祖, 长江是我源。千年迁徙苦, 安身在南边,祭苗族祖先孜尤(蚩尤),祭苗族列祖列宗。让他们护佑,我们岁岁平安,年年丰收,人丁兴旺,事业发达。”[4]从文山苗族《花山起源之歌》和祭祀来看,文山苗族就是蚩尤的后代。
现在的花山节是文山苗族同胞一年一度的重大节日,苗族同胞着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来到花山场。从着装上来看,苗族女性头上喜戴各种造型的银角,而银角的形状就向牛角一样,同样苗族妇女能剪出千姿百态的牛图案剪纸,并根据剪纸模样绣出五彩缤纷的水牛图腾的袖花、肩花,把牛的图案穿在身上,以此表达对祖先蚩尤的崇敬。按《述异记》记载,蚩尤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这时的牛和牛角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作战武器存在于蚩尤部落中。在现存的斗牛游戏中,苗族大人或者儿童在农闲时三三两两,以一根带牛角圆木而相抵(如图1、2)。其游戏的内在表达是为了展现出苗族男人的强壮、力量和勇武,以此延承祖先遗风。同时也是对爱情的一种表达,即强者才能获得爱情。
文山苗族对牛的崇拜,其内源性在于对祖先蚩尤的怀念,其发展原则是将牛拟人化和情感化,进而纳入到苗族宗教的审美形式及文化信仰之中。其方式是将斗牛作为一种宗教文化传承符号,在花山节反复活动,也就是反复确证。其要求是将这确证的斗牛的外在符号,转化为苗族同胞心灵上的符号。
(二)斗牛的农业意象

图1 斗牛游戏

图2 骑牛游戏
苗族斗牛与农业活动有着极大的关系。苗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历史上苗族的祖先以黍米为本,发明牛耕、种植稻米、小米等许多农作物,农业得到发展。他们钟情水牛,以牛为吉祥物,带牛角以求繁荣昌盛。为什么苗族要兴起斗牛,甚至以斗牛为最大的娱乐活动?《周易·说卦转》指出了八卦图卦位具体位置的图腾属性,“乾为马,坤为牛”。古人认为:“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牛则是开辟大地的动物,人民要靠牛来耕种。苗族喜欢牛,因为牛力大无比,是苗族农耕活动的得力助手,因此苗族的生活离不开牛。据说苗族在北方战败,不得不迁徙时,苗族在迁徙途中许多家产无法带走,只带了三件贵重物品:稻种、水牛和芦笙。以这三件物品为母体,苗族在后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开发出了发达而系统的农耕稻作文化、牛文化和芦笙舞文化。每到过年或冬至的时候都要把牛当成“神”,当成“龙”来进行祭拜,给牛喂米饭和冬瓜,感谢牛对苗族农业发展的贡献。由此可见牛在苗族社会生产、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太平广记》卷七十八引《诗含神雾》:“大迹出雷泽,牛胥履之,生宓牺。”[5]《列子·黄帝篇》:“庖牺氏、女娲氏……有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庖牺氏、女娲氏,……蛇神人面,牛首虎鼻。”《广成子传》:“黄帝以馗牛皮为鼓,尤不能飞走,遂杀之。”《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蚩尤所弃桎梏,是为枫木。”《述异记》:“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从上可以看出蚩尤族曾经信奉过龙,由于黄帝杀死了龙而打败蚩尤族,蚩尤族战败后,返祖为牛。因此后来苗族同胞便从“神牛”“神龙”中去寻根问祖。以此同时,苗家人为纪念农业上种谷子的一大飞跃,庆贺牛给人间创造的奇迹,每逢过年过节都要牵两头以上的牛来比武打斗,让苗家男女老少尽情欣赏、娱乐[6]。
从文山苗族斗牛的农业意象来看,斗牛的内源性在于苗族的农耕、稻作文化,其发展原则是将牛与人的生产劳动紧密相结合。方式是在春节通过斗牛比赛及祭祀将牛与苗族同胞的生产寓意于苗族农耕文化之中。其要求是通过斗牛将人与牛联系到一个更加紧密的空间,即生产生活空间,进而促进苗族农耕文化传承与发展。
(三)斗牛的生殖崇拜意象
苗族生殖意识源于原始社会,由于当时的生产力较为低下,人口是保证抵御自然灾害和战争胜利的基础,所以只有增加人口才能取得更多的胜利,人口繁殖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生殖崇拜逐渐演变为原始社会的一种流行风俗习惯。所谓生殖崇拜,就是对生物界繁殖能力的一种赞美和向往[7]。而苗族斗牛生殖意向具体体现为男性生殖器功能像牛一般的威猛。为此才能“多生”与“优生”,只有生的多,儿孙又健壮如牛,氏族才能壮大、发展、繁荣[8]。在苗族的“鼓社祭”中苗族把男女生殖器崇拜当作祭祀的高潮来举行。有些地方用木刻成男女生殖器,有多个男子把生殖器披在背上,相互追逐,叫做“追女”[9]。苗族认为牛是其祖先,苗族在世后人都是祖先转世投胎而来,也就是说牛死后要转世为人。所以苗族“鼓社祭”祭牛就十分讲究,要挑一头毛长得好的来祭祀。这样祖先就会高兴,就会赐给百子千孙。由此可以看出苗族斗牛的内源性在于生殖崇拜,其原则表现为对牛生殖器的崇拜,希望男性的生殖能力能像牛一样的威猛,其方式是通过斗牛及斗牛游戏来凸显苗族同胞的生命意识。其要求是通过斗牛表达出苗族人们追求生活幸福和事业兴旺发达的一种理想信念。
二、以斗牛为载体的内源性发展
如果从斗牛的一般特征来看,斗牛是苗族同胞缅怀祖先的一种祭祀活动,或者是一种古老的农耕民族的生产生活反应,再或者是苗族人们的生殖崇拜。而斗牛也只不过是他们出于仪式或娱乐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动物体育活动。
在历史中苗族是一个饱受战乱和迁徙之苦的民族,因牛的威势很大,苗族试图通过神秘的巫术——宗教力量,对异族、异族部落起到威慑恐吓的作用,对本氏族部落具有保护的神力,逐步实现本氏族对本地区的统治。在这里牛被神格化,也被人格化,按照苗族人民原始思维中部分等同于整体的观念,据此,“人=牛=祖先”。斗牛是为了缅怀先祖的一种代表性活动,用此活动的方式教育苗族后代要做一个团结的民族,要做一个敢于担当的人。
斗牛是与农业、牛耕和种植水稻有密切联系的风俗,具有明显的农业意象。斗牛可以比试耕牛的威猛与雄壮,进而达到优良品种的自然筛选,优胜劣汰,体现苗族人民充分利用自然规律,造福人类自己的智慧,这里的苗族斗牛并不是戏牛取乐,而是以斗牛的方式展示苗家人勤劳的社会特性。
苗族图腾的生殖意识源于原始社会,因为人多才能抵御自然灾害和战争,所以人口繁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斗牛中,牛的生殖器官裸露在外,呼呼生风,苗族人们认为牛的力量源泉来自于牛的生殖器官,因而产生对牛的崇拜和赞美。他们认为苗族男人的“根”只有像牛一样的强壮才能生育出强壮的百子千孙。以此体现苗族同胞尊重生命、赞美生命的民族品质。
在苗族日常道德说教的语言中,有很多用牛的意向涉指男性。“你很牛”这个词被隐喻地表示“英雄”“勇士”“冠军”“有才干的人”或者被表示为“硬汉”,再或者表示为性格的倔强、不服输、勇于战斗等,无论何种表述都与当时语境自成一体,并被大众心里所认同、接受。然而苗族男人与他们的牛的亲密还不仅仅是隐喻的。苗族男人在牛身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从购买、喂养、修饰、训练、谈论,到让牛相互试斗。正因为如此,斗牛才与主人或村寨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牛才成为主人或村寨的代表,被赋予更多的意义。苗族的男人对牛有着深刻的心理认同,不仅把牛与他理想化的自身联系在一起,甚而与其男性器官联系在一起。在生殖崇拜方面,苗族斗牛生殖意向具体表现为男性生殖器如同牛一般的威猛,隐喻男人的健康、家族多子多孙。在古时牛斗胜者,可以得到对方的稻种等物品,斗胜的牛王在苗寨众人的簇拥下披红挂彩,一路敲锣打鼓告诉邻近村寨他们的凯旋归来,胜方的主人或村寨更是满面春风,家里寨子里喜气洋洋。这时斗牛的身价也会连升几倍,附近村寨的斗牛者会络绎不绝的来道贺,并请教斗牛的相关技术。赢得比赛的牛主人或村寨会热情的款待前来道贺的人并同他们交流经验。就苗族斗牛来说其内源性更为重要的不是物质性的获取,而是以斗牛为内源传播苗族同胞共同的精神世界,即团结、勇敢、尚武、勤劳等精神特性,进而在斗牛的过程中完成其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斗牛文化是实现斗牛发展的原则、方式和要求,是斗牛发展的基本动力。
三、苗族斗牛内源性发展的思考
一个民族的文化有赖以这个民族的社会背景,斗牛仅仅对牛来说是“真正的现实”,只是动物间的一种竞技或娱乐活动,然而斗牛对于苗族整个族群来说,就是将牛和苗族同胞联系到一个更加紧密的空间,将牛与一个民族的文化联系起来。
斗牛是文山苗族“踩花山”中的重要活动之一,苗族斗牛的内源性在于苗族祖灵意象,或者农业意象,再或者生殖意象,并以这些文化构建其民族精神。但从内源性发展的角度来看,斗牛是苗族同胞的一个群众性活动,具有娱乐与文化的双重价值。苗族斗牛不可能永远一成不变,历史表明,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变化常新、与时俱进的。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如果不加以变革和创新,也就没有了生命力,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苗族斗牛内源性发展,应当是立足于苗族本土文化,以苗族本土文化为发展基础,进入苗族本土文化的挖掘、保护及斗牛文化重建和传统创造等。伴随社会的转型,生存环境的变迁,苗族本土斗牛文化更将为适应社会变化而在斗牛项目、文化与民族节日庆典方面作出种种调整,以此实现苗族斗牛内源性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价值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