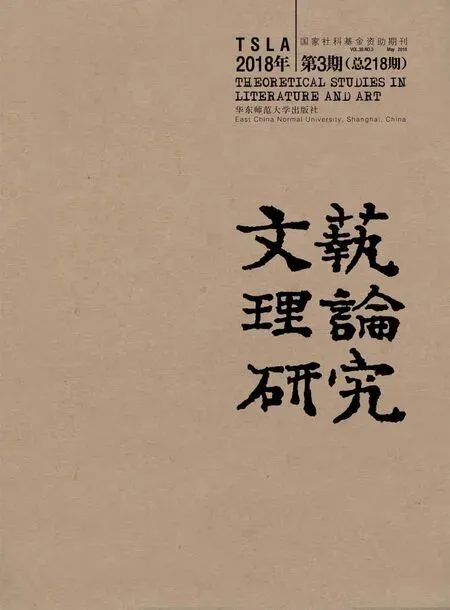从反人文主义到一种狭义的后人类:跨越拟人辩证法
张春晓
自上世纪中叶,西方知识界各学科领域不约而同地拆解自18世纪以来的人文主义大厦,进入到一个以“后-”学(post-)范式标示的阶段,后人类亦是其中之一。作为一种已经发生的境况和正在生成的思想,大量实际上是“后于”人文主义的话语众声喧哗。本文试图在与人文主义的比照中,清理出一个更为狭义的“后人类”,以区别于诸多其实是“后现代”“解构”或者“反人文主义”的思想。这样做是因为,不同于已经耗尽动力的辩证法式的批判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惯性残余,一种定位更准确的、同时坚持外在论、一元论和经验主义具身性的后人类思想才能更好地回应生物工程和人工智能时代的问题,这也是笔者认为的一个有希望的方向。
一、有关“后人类”的理解和分类
“后人类”(post-human)这个字眼,据考证最早出现在1888年布拉瓦茨基(Blavatsky)的《秘密教义》(The Secret Doctrine)一书中。而作为今天被热议的学术概念,则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也有人将其追溯到60年代后结构主义以及共同反人文主义的各种“后学”(尤其是福柯),认为后人类思想萌芽潜藏其中并且在90年代中期凸显为一个专门领域(Wolfe xii)。与它的对手——有着深厚共识的人文主义相反,后人类目前依然是一个众声喧哗的阵地,我们常常看到:有的学者认为自己的后人类主义比别人的更可取;有的被视作后人类主义的学者却是从批评它起家,并认为自己不属于这个阵营。
凯瑟琳·海勒在其1999年的重要著作《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How We Became Posthuman: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Literature,and Informatics)中,认为上世纪40年代兴起的控制论撼动了人文主义传统对于“人”的理解,成为最初的具有明确主张和冲击力的后人类思想:
首先,后人类的观点看重(信息化)的数据形式,轻视(物质性的)事实例证[……]其次,后人类的观点认为,意识/观念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再次,后人类的观点认为,人的身体原来都是我们要学会操控的假体,因此,利用另外的假体来扩展或代替身体就变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最后,后人类的观点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安排和塑造人类,以便能够与智能机器严丝合缝地链接起来。(海勒 3—4)
这是一种信息逐渐被实体化乃至本质化的过程,意识脱离肉身被抽取(即离身性,disembodiment)、转译到一种更加抽象普遍的编码中,从而可以跨物质媒介流动,操纵包括而不限于肉身的各类假体。显然,海勒看出,这无非是一种包裹着现代科学术语的升级了的主体性意识哲学,所以她旗帜鲜明地反对“后人类主义”,倡导将人的概念、边界的问题重新拉回具身性(embodiment)——即人的身体、物质现实、环境等要素中考量。其实不用人文学者来批判,1960年代控制论的第二波浪潮就已经展开了自我批判,认为一级控制系统想当然的客观性必须依赖二级控制系统来阐明,系统制订的规则、混沌无序的环境、偶发的变异因素、观察者的主观能动性等等都被统摄到“反身性”的议题下,最终在社会学家卢曼那里发展为一整套可与福柯、新实用主义和解构主义类比相通的哲学话语。无论海勒支持或反对哪种后人类主义,我们姑且可以找到一种可共享的最宽泛话题:在人与智能机器结合的背景下,曾经明晰坚固的主体边界变成了可供争夺的东西。
如果说海勒通篇大谈信息和机器,沃尔夫(Cary Wolfe)的《后人类主义是什么?》(What is Posthumanism?)则在讨论解构哲学和动物。他与海勒一同反对自治主体和离身性的幻想,但又批评海勒仅仅用具身性去对抗“后人类主义”错失了重点。为了区别于各种他并不赞同的“主义”,沃尔夫把自己的观点称为“后人类的”(posthumanist),是一种思路而不是一套教条。他强调“后人类的”不仅仅是讨论肉身和机器,不仅是关于科技生物等内容,而是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乃至学术范式:
当我们将“意义”从意识、理性、反思等闭合的形而上学领地解放出来之后,我们能够以更具体的方式去描摹人类和人类在沟通、互动、意义、社会性的意指(social significance)、情感投注方面的模式。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曾被理所当然地认定的人类经验,包括智人种正常的感知模式和情感状态;把这些经验置于其他所有生命体的整个感觉机制、置于这些生命体的“建立一个世界”的自创生方式中再语境化[……]当我们在谈论人的特殊性——在世的存在方式、认知观察描述的方式,我们也必须强调,人在根本上是一种虚拟(prosthetic)的创造物,他与技术、物质性以及那些完全非人的形式共同进化。(Wolfe xxv)
德里达的解构“破”开了人文主义哲学传统,指出其内核中非在场、非意识、非同一亦即非人的要素(诸如机器、动物、环境、符号的)反而是非源初地优先于人的,虽然没有太多积极主张,但解构主义从认识论原则上开启了不断反思既定边界、提出另类表述的必要性。卢曼则“立”起了一个既不堕回任何基础主义(foundimentalism)和“我思”哲学、又不沦为无穷后退和相对主义的“系统”。这个在多层次上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的系统具有一种“闭合的开放性”(openness from closure),可以在与环境复杂性的互动中自我修正和自我增殖(Wolfe 14、112)。沃尔夫通过语言和信息编码的优先性和外在性来质疑意识、心灵、身体的传统理解,并以机器、动物和残疾人等例证不断拆解人的概念。
最近的学者能够以后见之明更好地梳理后人类诸流派。费尔南多区别了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反人文主义与后人类主义(Ferrando)。海勒反对的那种“后人类主义”如今改个名字就明白得多了——超人类希望用科学技术提升人的身体和精神诸能力,可能导致一种“半机器半人”,所以又被国内译为“跨人”和“过渡人”(邱仁宗 李念)。它依然根植于启蒙理想,是在人类主体性的概念下各方面具体能力的补强。后人类主义则既不敌视也不赞颂科技,只是把它作为解构人的路径之一(批判动物歧视主义则是另一条)。它继承了种族和性别理论中的解构思想并继续突进,打破一切中心、边界和二元论——所以作者认为德里达是后人类而福柯是反人文主义(antihumanism),因为“人之死”依然潜藏着一个“生/死”的对立,而在后人类主义中生死的命名和对立是失效的(Ferrando)。米亚区分“文化研究的/哲学的”两种后人类主义。前者以哈拉维和海勒为代表,共同点在于通过科技来挑战人体的一致和完满;后者阵营则包括罗蒂、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德勒兹与瓜塔里等等,在心灵哲学、动物伦理、技术装置等领域颠覆人的中心地位,思考他者的意义(Miah)。
意大利人布拉依多蒂明确区分反人文和后人类。“反人文主义是个充斥着如此诸多矛盾的立场,以至于一个人越想克服它们,它就越变得不可掌控。不仅反人文主义者经常最终反而拥护人文主义理念——自由是我最爱的理想[……]反人文主义立场生成的内在矛盾的一个经典例子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解放和进步政治学。我认为它是人文主义传统最高价值的内容和最持久遗产”(布拉依多蒂 41)。反人文主义之“反”似乎总是摆不脱与人文主义的可疑的辩证综合,所以后人类必须成为另一个选项。作者借鉴斯宾诺莎的一元论和德勒兹有关生命和机器的学说,希望提出一种重写主体概念的“主体性哲学”,以此作为她自己的批判性的后人类主义。这样的后人类不去辩证地否定什么,它的主体概念建立在一元的普遍生命力之上,打破边界又不掉回到辩证综合的窠臼。不仅人类成了支离破碎的、要容忍非人东西的“主体”,人文学科也可能失去曾经当仁不让的对象——“人”(布拉依多蒂 86;250)。
至此,区分的必要性呼之欲出。一方面,后人类诸理论显然有两种倾向:一种偏重于经验,跨学科地关心最新科技成果,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动物、环保、残疾人都是亟待回应的挑战;一种则更偏向安全保守的学科领域,倚重经典、抽象的哲学资源。另一方面,后人类与反人文主义密切相关,有人重视其连续性,有人则强调其迷惑性和断裂的必要。本文认为,广义上一切挑战自由人文主义的思想,如存在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语言学、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拉康式的精神分析等等,我们的研究已经不少。那么为了更准确有效地讨论,就有必要界定出一个狭义的概念——不管其是用-ism还是-ist来指称,我们姑且称其为“后人类”。反人文主义是经由边缘他者来辩证否定居于中心的大写的“人”,最终这一辩证逻辑被解构主义的拓扑模型推至极限;而狭义的后人类之所以特别,就在于它没有继续辩证地从“人”的内部去否定和拓展,而是洞悉了这一逻辑后选择绕路而行。
二、人文主义-反人文主义的拟人辩证法
在人文主义为“人”列出的各种本质属性的清单中,理性无疑是最古老最重要的一项。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但理性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的重要内涵,这块自由人文主义的基石,却是到启蒙时代才被笛卡尔真正奠定的。“我思”意味着理性不只是一级系统水平的观察、计算、思辨,而且同时被二级系统意识到——貌似只是一个自明但空洞的意识把戏,一个没有任何具体经验内容、只是多一层反思的逻辑标识,然而这才是使人类理性有别于动物感知的关键,反思能力乃是“我(人类)(存)在”的依据和本质。“我思”也引申出黑格尔的“意识总是自我意识”以及预示着包罗万象的辩证法图景。黑格尔对“我思”的阐释修正意在避开无穷后退的恶的无限性,而保持其自我否定、自相矛盾、分裂又同一的动力,它并非与形式逻辑那种理性不相容的错误,相反却是理性能够自我增殖乃至超出主体意识成为总体性精神之旅的真正奥秘——辩证逻辑。人的成长和自我实现、整个人类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知识(特别是哲学知识)的新旧更替都被讲述为一个“异化-复归”的故事。尽管这个庞大的总体性哲学已经不限于人类-意识-主体性,但绝对唯心主义历史的红线、亦即那个具有普遍解释力的辩证法,依然与最初最简单的意识把戏分享着同样的结构。所以说,辩证法总是拟人的(anthropomorphism)。
个人施展自己能力的过程,以及族类所谱写的文明发展的历史,都是不断将意识、意志、力量向外投注到与我有别的对象,再从异化中重新认出也更加充盈自我本质力量的辩证进程。而“主体-人”始终是中心和顶端,起点和目的。外部世界的差异对象除了环境和动物,也包括人类内部的差异等级、族群与文化的差别对立。因此,“历史上的人文主义发展成一个文明化模式,该模式将欧洲的概念塑造成自我反思理性的普遍化力量[……]这个欧洲中心论的范式蕴含着自我和他者的辩证法,和分别作为普遍人文主义的文化逻辑和驱动力的、身份与他异性之间的二元对立逻辑。这个普遍主义立场和二元逻辑的中心是作为歧视的‘差异’概念”(布拉依多蒂 19—20)。
不过,辩证法的反思锋芒也终将指向人类主体性以及那个带有遮蔽性的普遍本质。海德格尔将剥离于天地万物之外的主体性的人置换为“此在”,连接回到不可被实体化的“存在本身”的母体中。结构主义语言学指出是“语言说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人类自以为优先的理性思考和赋义活动,并进而发展出拉康的“无意识的结构是语言”。马克思将人文主义诸学术、艺术以及制度实践一股脑地作为非价值中立的意识形态,最终落脚于经济基础。福柯则发展出一种非人、匿名而无处不在的“权力”概念,正是它贯穿于各种话语实践中塑造了人的主体性。上述理论的共同点都在于将人类的中心和优先地位辩证颠倒,将其根植于一个非人的、更具基础性的“大”的他者之上,指出人是由它塑造、反过来又错误地自认为优先的东西。另一方面,那些曾被作为普世理想的人所标示的“小”的他者——女人、黑人、东方人、同性恋等等——也纷纷冲击这一理想:他们被指定在等级秩序的下层,被要求向着这个最高标准生成,又永远被它隔开(霍米·巴巴almost but not enough),而今它们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差异性去挑战、扩展、丰富那个理想,却也同时拆散了它:先验的人类主体性及其建立的差异等级秩序,都被证明是一种话语建构。
反人文主义并不等于彻底驱逐了对于人的关切,相反是一种辩证升级的关切。哲学上不可被实体化的缥缈“存在”,现实中则有可能被转化为文化-民族-国家,抽象个体的人被放回集体的土壤,直至发展为法西斯这一灾难版本。马克思、后殖民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大力批判自由主义人文主义,乃是因为这一意识形态并不能真正让所有人拥有它所声称的那些美好词汇,而恰恰遮蔽和自然化了世上的不公不义。坚持一个先验抽象的自由理性的个人概念,并不足以解释和改变什么;相反,只有认清这种理想的社会政治土壤,才可能给个人带来真正的解放和福祉。左派一再地强调经济、文化、权力对于人的限定,似乎是在用某种决定论抹杀自由;然而正是因为不轻易相信先天被规定好了的本质“自由”,左派就是要在冷酷地指出种种限定之后,看看人还剩下什么能动性、由怎样的路径去追求幸福。可以说,为什么左派热衷建构论甚至决定论?因为他们对人(的自由)爱得深沉——由此可见,反人文主义和人文主义总有一种辩证的关联,而且似乎可以经过阐释而达到更高的综合:既是人文主义又是反人文主义的。譬如这份发展谱系:“通过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人文主义流派,在(现代性)上欧洲资产阶级建立了自身霸权,震动世界的革命人文主义和致力于驯服前者的自由人文主义,纳粹人文主义和他们迫害下的牺牲者以及对手的人文主义,海德格尔的反人文的人文主义,福柯和阿尔都塞的人文主义的反人文主义,赫胥黎和道金斯的世俗人文主义或吉布森和哈拉维的后人文主义”(布拉依多蒂 73)。
在这里,有必要单独提及德里达的解构哲学,这一拓扑学模型是对辩证法最深层的澄清,也是否定力量的耗尽。
笔者在博士论文《后殖民主义的二元结构》中,对于德里达做出了一种保守倾向的解读:解构并不等于简单颠倒或消极抹平任何二元论中两项的地位,它更多地是一种对辩证结构的澄清而不必然决定哪种价值判断和颠覆行动。二元论中弱势的后一项并非“简单凌驾于前者之上,因为取消前者亦是取消对立,取消后者。后者也不是第一性的,它并不能造就前者,相反,它的存在的规定性全然系于那个无力存在的前者身上,它存在的意义不在于自身,而是指向前者;前者虽然永不在场,却一直引导、规定着后者的存在,有着不可取消的重要作用”(张春晓 86)。澄清只是让我们注意到这一对“只能按此等级关系存在”的两项同时也是相互界定的两项,进而启发我们考察其被建构的历史、广泛联系并重新思考现实经验、探寻这些意义边界和关系之外的替代性表述(alternative discourse)。解构了的二元项不会继续辩证综合,“延异”(différance)也不会像海德格尔的“存在”那样成为一个新的本体论统摄概念。这是因为,在二元论的结构里,当你宣布一个作为本体的“差异”时,已然隐含参照着另一个更大的“同一”,而这种想法亦即它们两项的关系本身又是“延异”的。这就好像拉康-齐泽克频频使用的“拓扑学结构”,即莫比乌斯圈或克莱因瓶的形态,它不是平面的相对主义也不是有起点有回归的辩证螺旋,而是明明内外分明、外部又会在某个时刻突然转为内部,双方再一次翻转相通——当你想把任何“姑妄名之”的临时术语本体化,总是会一次次迷失在“姑妄名之”的永恒延异里,没有起源,没有在场,没有同一性。
澄清并不是推翻二元项的关系和辩证法的运作,只是指出它们并不以它们自称的方式那样存在;德里达的解构同样利用了否定辩证的机锋,但却不导致任何综合和同一,而是放逐到无限的差异的开放性中——在我们目前使用的思维和语言模式下,也只能这般“言说不可言说”了。德里达的解构是最激进彻底的,然而或许也是无用的,因为它只是确立了一种解构的策略和不执着于任何二元对立(最多只能是临时性的)的批判原则,一种足够大的“消极自由”,却不提供任何积极的评判标准。沃尔夫在《什么是后人类》中借鉴德里达批评生物伦理中功利主义和意识哲学的方案,但最终也承认解构只是提醒我们将伦理关注超越边界施于动物之上,至于那是什么,我们只能“保持开放”,“有所回应”,“不断更新”,(Wolfe 126)。类似的词汇譬如“未来”“将临”“无限”也是许多法国哲学家喜欢运用的。本文声称辩证法否定动力的“耗尽”,并不是说它错误、失效、应该被弃,而是说经过各种后学流派洗礼的学者们太精通辩证法的力量——同时也是陷阱——以至于辩证否定常常成为一种毫无用处的犀利:譬如讨论可以在“通过差异他者批判霸权中心——再批判将他者本质化的倾向”两面的循环往复,批评者可以掠过一切历史经验素材,用辩证法直接攻击对手认识论的漏洞,而这样貌似深刻的辩论既无助于创新理论也无助于理解现实,辩证法仿佛成了一架空转的机器。
当然,德里达并非当代唯一伟大的哲学家,只是“仿佛尽力了20世纪70和80年代的理论大创新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丧失思维能力、无差异重复和绵延不断的忧郁时代”(布拉依多蒂 7)。控制论者维纳、马图拉纳、卢曼,德法思想家如哈贝马斯、列维纳斯、拉康、福柯,大洋彼岸的新实用主义普特南、罗蒂等等,他们的学科领域、所操术语、理论思想和价值立场各个不同,但是皆不脱于语言学转向后的主体与他者、话语和世界的辩证关系。如果说话语本质总是隐喻,不同学科形态的话语无非是对于某些不可触及的“真相”的各种间接指涉,那么20世纪的理论确实呈现出某种相似的逻辑,可以类比相通,他们之间的争议和差别只是对这一大范式的修修补补。在辩证法的尽头,我们需要真正另类的经验和话语。
三、拟人辩证法的两大问题
人文主义的弊端以及反对的必要性已毋庸赘言,但本文要强调,反人文主义也应当与后人类有所区分,这不是因为它在内容上较少涉及科技,而是因为在思维方式上,许多反人文主义(譬如布拉依多蒂列的清单)暗中沿袭与人文主义一致的拟人辩证法,这一思路不能够直接有效地回应现代科技进步提出的挑战,在讨论后人类问题时还会有将人文主义偷运回来的危险。我们必须对这两大问题有所警惕——
第一,拟人辩证法之“辩证”的方面为人类本质属性提供了一个完满的本体论自证,免受任何现代科学话语的攻击。
信息科学家莫拉维克曾经畅想将人类记忆完整地提取、上传电脑并且能够下载到别的肉身,这样我们就成了摆脱肉身长生不死的存在。这种实际乃是对人文主义的最高礼赞却引起了人文学科(包括人文和反人文主义)的恐慌和抗议。在现代科学的进逼下,灵魂、意识、自由、智能貌似是人文学科应该忧虑的议题。但实际上,除了科幻和科普的阵地的热闹,在专业领域这场战争从未真正发生过。科学家和哲学家在各自安全的领域发表一些看法,认为自己自动获胜而且觉得这个问题并不真的值得纠缠。对于上述概念,人文学科内部的论争——譬如分析哲学、语言学、解构主义、精神分析——造成的困扰都比科学致命得多,而科学事实从未撼动它们,因为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操作已经构筑起一个完美的防御。
譬如,人有意识-自我意识,这是每个人一反思就明白的事实,但这种绝对的主观内在又普遍自明的简单体验,要通过科学被“转译”到其他物质媒介或语言却困难重重。我能够“看”一个冰激凌,有了想吃的“欲望”,又因吃不成而产生沮丧的“感情”。科学对此知之甚少。它勉强可以说这是几百亿神经元细胞释放的电子在流动,但不知道这些电子从何而来,为什么偏偏导致对冰激凌的意识——这种说辞不是原因而毋宁是一种同义反复的解释:当我看到冰激凌,同时脑中某个区域产生了活跃的电流,而这种神经活动目前尚不可能全盘提取和“再现”。更不用说“想吃吃不到令人沮丧”这么复杂的事情。只要坚持“意识”这个概念,它就永远不可能被科学收编,但却很容易被哲学撬动,只需要问:当你产生“冰激凌意识”时,究竟是怎样的体验?图像?味道?情感?它们又是什么?说到底我无法离开有关“意识”的话语去言说,更不可能用心灵感应传导给别人。对于像冰激凌、疼痛乃至所有意识内容,我的体验是不是你的体验?不知道。从后期维特根斯坦式的“意义即用法”的外在论语言观来看,“意识”不是对我们某种能力或内容的指代,相反它是同义反复甚至更加先行的规则,而所谓自明其实是跳过了“他心”难题却还要强行以意识为基础的。对于真正的内在体验,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确定;但只要使用“我思”,我对我的意识就是如此确定,并且确定每个人都确定——尽管没进入他的意识。以我思结构为特征的人类意识是自我论证的,无法被还原为实证科学。在科学和伦理学的进步中,意识或许能扩展到部分动物,但与花草石头毫不相干。机器可以处理声音图像,说话和计算,移动和做工,但永远不会发生的是——机器意识到自己产生意识并向人类宣布。
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自由意志。人们总不愿意听到自己是被决定的,而且这是悖论:如果你清楚认识到自己被决定,你还怎么会是彻底被决定的呢?康德把最消极形式的自由定义为“开启一个序列的能力”,即是说:人有这样一种能力,不知所起诞生一个念头,把它实践出来,在现象世界造成一系列后果。这些可见的经验后果不能仅仅在现象界里通过科学的因果链描述,其“原因”(又是一个反思得来的人类知性范畴)必将追溯到心灵中一种不可直观不可规定的物自体,即意志。意志固然会参考纯粹理性和经验,但归根结底还是毫无根据地自我决定(例如我知道作弊不对且危险,但还是决定作弊),它是从人的内部解释一个想法或实际行动时一直追溯到的空洞起点。所以脑电波也是同义反复,而非导致了某个决定的更高原因。目前对自由意志最不利的试验是:被试者两手各拿开关,随机摁下一个,脑部扫描机器显示,导致这个行为的神经活动,会比人类做出(也是自我意识到)此行动提前几百毫秒到几秒不等。然而对于这一实验该如何解释呢?提前发出的信号真的是意志的更高指挥官吗?如果是,我们可以继续问,发出的“依据”又是什么呢?随机?还是说从发出信号到做出动作的整个过程都是自由意志的同义描述、只是意识在稍后才显现?抑或与无意识有关?不得而知。其实自由意志就意味着在人的身上不断追问根据,一直上溯到不可再追问的空茫领地。或许像诡辩,但它的定义本身就是一个免于受任何其他话语决定的本体论证明。
至于智慧或智能的概念则更加复杂,涉及认知、计算、判断等一系列环节综合。著名的图灵测试认为,如果一台计算机在与人的对话中表现得几近人类,令对话人难以分辨,那么这台机器达到“智能”水平。这是科学界第一次尝试提出明确的机器-智能的定义,但图灵测试实在有太多可阐释的路径,导向不同的论点。后文我们会看到,重要的也许不是机器能否具有智能,而是人的智能可否按照机器运行的方式被重新理解。总之,根植于人文主义的诸概念在与后人类的境遇和问题碰撞时,它们没有击败对手也不会被击败,只不过自说自话再一次重申自己正确。这种论争没有对错,而是无效。
第二,拟人辩证法之“拟人”的方面使得后人类讨论混入人文主义的概念预设,自砸阵脚,而这种毛病甚至是反人文主义也难以避免的。
当某些反人文主义者批判自由人文主义的“人”时(最典型即各路文化研究批判“资产阶级-西方白种-异性恋男人”),一种常见的策略就是借用边缘他者诸如女人、黑人、无产阶级、第三世界、酷儿、动物、生态环境、机器……由于二元论一端关联的总是理念的“人”,且辩证法本就与意识同构,所以批判即便推进到动物和机器,也仍然延续了拟人化的思维惯性,譬如“我们会不会失去‘人性’?”“机器会不会控制/奴役/取代人类?”
这种提问方式有多么糟糕?被追溯为科幻鼻祖的《弗兰肯斯坦》,在人类自然完满的身体理想上撕开了第一道口子,带有部分人性的机器——进而不难令我们想象带有部分机器的“半人”——撼动了我们的边界意识。但这种忧虑终归还是建立在对机器的拟人想象上,它没有影响到“人”。即便莫拉维克欣喜于“机器取代大脑”的前景,他也并不是在真的支持机器压倒人类,相反却在巩固一种“人文为体、机器为用”的观念。《黑客帝国》的人机大战不是物理力量的对抗,而是主要发生在虚拟的计算机代码之中。史密斯——实际上是一种杀毒程序——依然要以西装革履类似FBI探员的形象出现。最大的漏洞莫过于动画片前传:未来世界所有劳动由机器人完成,为了渲染这一震撼场景,我们看到在千千万万跟人一样的机器人像法老的奴隶或伏尔加河的纤夫一样在工地上辛苦拖拽巨石,后来他们产生思想感情、反抗并奴役人类云云——等等,这真是过度的拟人想象了!不用等到未来,就在今天,运建材难道不是用吊车吗?电影中你会感到被无数机器人支配的恐惧,但现实中你并不会有被吊车支配的恐惧,这正是问题所在。
机器怎么会奴役人?只有当你早就把机器看作人。何为奴役?一个人(或者动物、怪物)把他的意志、情感、欲望强加在他者身上。许多人包括一些科幻爱好者都相信人工智能的最高境界是用硅等无机材料打造出一个拥有类似人的主观体验从而能像人一样行动的存在物。然而这不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选择,人工智能发挥作用也不需要按照内在体验去归因。机器不可能也不需要发展意志、情感、欲望这些“内心戏”,更无可能把这些施加在人类身上。机器奴役人只不过是个拟人思维的错觉,两套范式混淆产生的伪问题。正如海勒所说:“可怕的不是后人类主义,而是将后人类主义嫁接到人本主义自我观念上”(海勒 388)。抱着拟人思维,即便是反人文主义也无法在面对机器他者时勇于打开人的边界;跨过拟人辩证法,我们才来到后人类的门槛上。
四、绕路而行的后人类思想
后人类与反人文主义既区别又相关。区别在于,狭义的后人类必须与那种与拟人辩证法纠缠不清的反人文主义划清界限。相关之处则譬如德里达,在解构意义上可称为“反人文主义”,在与控制论的类比上称后人类亦无不可。他连同许多思想家已充分揭露了主体性哲学的(不)可能性,为另类话语打开了空间,可以说“反人文主义最终是一个获取后人类思想的重要源泉”。然而,解构主义始终破大于立,其他一些反人文主义思想(其实已经是后人类)对于跨学科的新议题关注不够,所以反人文的资源“根本不是唯一的,反人文主义和后人类之间的联系在逻辑上也非必要,在历史上未必不可避免”(海勒 35—36)。
本文倡导的狭义后人类主张是:首先,后人类与解构主义和语言哲学等思想一同站在澄清了的二元论的尽头,所谓“跨越”拟人辩证法不是驳倒它(否定还会被辩证吸纳),而是尽可能绕开它,使它无用。所以第二,后人类在“澄清”和“绕路”之后还必须回应现实、有所肯定,它从形而上学一元论、经验主义、现象学和语言哲学的反心灵印象的外在论、文化研究的具身性中吸取资源,协同科学阵地的控制论、人工智能、动物研究等科学话语的发展,在临时和类比的意义上联结起人类与各种非人他者,借用非人的经验来破除和重写——而不是概念内部的辩证否定——人的概念(包括各种本质属性)。本文姑且大致勾勒这种后人类思想的几个特征——
1.外在性(exteriority)
早在主体性哲学的阵营里,胡塞尔就将意向性对象从心灵图象中剥离出来,扭转了“意识如何通达对象”这种主-客观的认识论俗套;语言哲学家们同样反对心灵印象,也反对先验观念;再放宽到所有后学,无论是尊奉内在体验、外部实在还是抽象理念的“基础主义”都要被坚决拒斥。这不是意识哲学辩证地自我否定,而是一个用可观察的、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性的话语逐渐转移掉个体内在性地基的过程,只不过胡塞尔尚且推崇唯心主义的抽象普遍的理念,后来这个外在于个体心灵的东西又变成结构主义般明晰或实用主义自我指涉的语言、控制论者的二级系统、社会学家讨论的交往规则等等。后人类的外在性更多关于机器和动物,似乎没有理由不再激进一些,让人类主观体验的语词都变成自明、正确而无用的东西。
继续上文的“智能”话题。美国哲学家塞尔把图灵计算机改编成“翻译屋”:即便你投进和拿出的纸条上翻译无误,也无法得知屋里有一个真正懂行的翻译员还是依靠什么别的规则在运作。这个试验未必支持或反驳图灵,毋宁说是把图灵语焉不详的“智能”概念细化了:如果智能是让机器重现人类脑中的那一套感知思考决策过程,那么图灵是错的——机器能骗过人这个事实,不能证明它的“头脑”“懂得”了语言;如果我们放宽对“智能”的理解,则只要输入输出正确,“黑箱”里的运作与人类头脑是否一样根本不重要。人们口头常说的人工智能,严格来说包括人工智能和人工生命,而后者的研发思路显然更占主导。早期人工智能从意识出发,把认知视为独立于感觉和指挥行动的最高统帅,沉浸在用机器模拟大脑的拟人幻想里;而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在80年代另辟蹊径,借鉴昆虫的神经结构,不去划分感受、认知还是行动,而是通过各个分类系统的协同运作,使机器顺利完成与环境的互动——从结果来看非常智能,但跟“意识”没有任何关系。深蓝和阿尔法狗的区别就是典型。深蓝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穷举法,在硬件可承受的范围内计算足够多的可能性,这看上去类似我们人类头脑对棋牌游戏的理解;但即便如此,当时的深蓝也没有穷尽国际象棋的所有变化,而是针对对手棋风做了优化,所以人们认为计算机短期内不可能攻克复杂度更高的围棋。然而阿尔法狗绕路而行,设计了两个“神经网络”:“决策网络”负责计算选择下一步走法,“价值网络”在每步后预测胜利方。这套网络被输入人类棋手的三千万步走法加以训练,并且自己与自己进行大量对局。因为复杂的棋类游戏并非在无数选择背后藏着一个致胜的标准答案,而是在不断的对弈过程中变化着最优解。阿尔法狗就是通过海量实战“经验”,不只用决策网络穷举,而是让价值网络指出哪一些可能性更大,确定更精准有效的计算范围,它们相辅相成,无往不胜。这里同样有很多拟人化的字眼——深蓝和阿尔法狗都有“计算”和“选择”,但是跟人做出选择时头脑里发生的过程没有关系;“神经”也只是类比的意义上的,人类神经元的电流和计算机的算法和数据毫无关联;“价值网络”是依据经验概率来筛选优化计算的,不是人的“价值判断”。
“科幻电影通常假设计算机如果想赶上甚至超越人类的智能,就必须发展出意识。但真正的科学却有另一种看法。想达到超级智能有多种方式,并不是每一种都需要通过意识”(赫拉利 279)。反人文主义揭示出来的外在性,多少还算是与意识有关的主体间(也是“外”)关系,后人类则用更加非人的方式让意识成为布鲁克斯说的“多余的伴随物”。这一次不是让非人的东西被整合、扩充或部分地改写人的内涵,而是人的东西按照非人的模式重新理解——冒着概念失效、破碎、重组的危险。
2.一元性
后人类的外在性其实就是德勒兹的内在性,德勒兹的一元性又等于彻底的多元性,即各种后人类理论都倡导的打破一切对立和边界、只有任意和临时的类比联结。
解构、语言学和系统论的外在性,强调的是外在于意识、意志等自明自证的内在体验并使其失效,而且自我指涉也保证了“外在”并不等于依赖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同样是反对客观主义和基础主义的“外”,德勒兹使用了“内在性平面”的说法,它是“内在(心灵或主体)和外在(世界或确定性)得以被区分的预设的场所”,所以也就是“激进的外部”(科勒布鲁克 91—95)。这种“既内且外”正是德勒兹发挥斯宾诺莎而来的一元论,只有“一”——内在性也好、经验之流也好、生命也好都没有丝毫神秘主义、本体论或内心体验的色彩,反而接近德里达“文字之外一无所有”的命题:各种二元对立共同诞生于区分的时刻,在此之前没有一个在先的、可供区分的东西。但德勒兹把内在性称为内外被区分的“场所”,亦没有将其本体化之意,只是两人侧重点不同:德里达以无限的差异保证了解构的犀利,而德勒兹取消基础主义的一元论、先验的经验主义,意味着一切内外主客的二元区分和联系都只能是任意和临时的。
当我们转变思路,就会发现有价值的区分-联结方式本来就不只主体-客体、心灵-世界。光与人眼联结使我们去看,与胶片联结使其变质成像,与植物联结使其生长。德勒兹认为生命是机器,没有封闭的同一性和终极目的,只有特定部分以特定方式去联结、生成、发挥效用——原则上的一元性也就是具体实践中的多元性。就像上文《黑客帝国》的例子,为何机器人令人恐惧而吊车不会?因为我们看待机器总是以人文主义的“人-他人”或“人-工具”的联结模式。但若不再执着于“人”的优先性,盖房子就是某种机械与砖石的联结,打字就是手与键盘的联结,其中的输入法还联结到比人类智能得多的云端大数据,毫无疑问它已是我们的思维和语言的一部分——但从不用“拟人”地担心数据从电脑里跳出来绑架我们。联结打破了一切既定的对立和边界,也就是哈拉维所谓的赛博,它是“控制论的有机体,是机器与生物体的混合,既是虚构的生物也是社会现实的生物”,而“人类,就像所有其他成分或亚系统那样,必须定位在一个系统架构内,此架构的基本运作模式是盖然论的、统计学的。没有任何客体、空间或身体本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成分都可以与其他任何成分接合,如果可以为处理某种普通语言的信号建构适当的标准、适当的代码的话”(哈拉维 307—308)。
3.具身性
哈拉维的话乍看上去像是超人类主义的宣言,但她只是借鉴当时的最新科技来强调打破旧有边界、想象新联结方式的重要性。今天的科技理念和成果更胜当年的控制论,但人们并没有真的“离身”变成信息精灵操纵万物,也没有成为更加聪明有力的机器的奴隶。人只是以更加复杂密切的方式与机器、环境、动物等非人因素联结在一起,后人类必定是具身性的。
具身性首先意味着悠久的人文主义曾颁布的那些人类特质不会被剔除。作为个人内在体验,我们永远不会失去自明的认知、欲望、情绪和自由,这些经验常识在某些领域(比如美学、政治和伦理)还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只是如海勒所言,它不应被嫁接在后人类主义上。在后人类思想里,这些概念的人文主义内涵将变得无用或改弦更张。内在体验是人的黑箱,正如图灵计算机和塞尔翻译屋的黑箱。后人类主义不会用其他编码取代内在性,反而真正坚持各种内在性的不可通约,从外在的角度建立类比。所以人的心灵、肉身、文化和日常生活是依然我们思考后人类时不可脱离的土壤。
进而,具身性意味着我们能够将非人视为一种不同于主体/他者辩证法的真正伙伴(fellow creature)。还是以阿尔法狗为例。它经过大量训练找到了自己的招式,找到了职业棋手们常年都没有注意的最优解。这是一种由自我指涉的两级系统的运算增殖的结果(“自我学习”“创造”又引发了人文主义式恐慌),设计神经网络的工程师也不能完全解释。棋手反过来要向电脑学习:被认为不甚高明的点三三,似乎还有尚未被挖掘的后劲。这种学习当然不是打通人“狗”各自的黑箱,而是棋手把电脑运算出来的结果重新转化为自己头脑的理解。棋手的意识依然是内在自明的,但是以后人类角度纵观整个故事,人类智慧已然被分离打散,与机器相连。海勒对塞尔翻译屋的解读是:不管里面是真正懂外语的人还是按规则查手册者,我们都应该说,是整个房间懂外语,它比任何一个成分(大脑,翻译手册,查手册的人)懂的都多。现代人的处境就类似于翻译屋,我们每天参与到各个系统中,系统的总体认知能力都要超过个人。人类的分布式认知与更广阔的分布式认知系统(机器,环境)连成一个整体,思考由人类和非人因素共同完成。当人被视为分布式系统时,人类能力的完整表达就是依赖于系统的胶结,而不是被系统威胁(海勒 391—93)——这实在是比任何版本的主体间性都更加谦虚平和的自我表述。
“人文主义危机意味着现代人文主义的结构性他者在后现代时代卷土重来”(布拉依多蒂 53)。什么样的他者?辩证法决定了人文主义-反人文主义的每次否定更新都依赖他者。只是过去引入的他者要么是低于理念人并且像人的,所以总能被吸纳;要么是语言、权力、无意识这样先于人、非人、塑造人的大他者,但对于人的批判和理解也就到此触壁了。而在今天,我们如何处理新的他者如电脑、克隆、大数据?如果还是从意识出发并把意识结构类比地推广到他者之上,无论怎样引入他者来反对人类中心,最多止步于“人VS机器,动物,环境……”的对立且不综合。但是,这些他者不应该再一次落入辩证法的窠臼,它们要反过来启发我们以完全不是人的方式想象自身。在这种想象中,世界的存在不再是人文主义的“自我/他者”或是反人文主义的“非人大他者/人类主体”这种不平衡的二元模式,只有一个不由任何霸权话语统摄的混沌一元世界,只有漫无边际的连接和生成,只有临时性的定义、区分和类比。跨过拟人辩证法,也就绕过了一部分后人文主义的陷阱和另一部分理论标示出的极限,迎接一个已临和将临的后人类未来。
注释[Notes]
①一种说法认为源自1988年史蒂夫·妮可思(Steve Nichols)所发表的《后人类宣言》(Post-Human Manifesto)一书。转引自支运波:“《一九八四》的后人类生命政治解读”,《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7(2):119。
②中文译本的“控制论”对应的原文是cybernetics,也是后文哈拉维论述的“赛博”或“赛博格”(cyborg)亦即cybernetic organism的缩写,可意译为“生化电子人”。(参见当娜·哈拉维:“赛博宣言:1980年代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严泽胜译,汪民安主编:《生产》(第六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0页)控制论所探讨的对象主要是一套编码“系统”(system),其中流动的内容即“信息”(information),所以在80年代传播到中文学术界的“老三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三者实为一事,可以互通,名称只是显示侧重有所不同。沃尔夫在《后人类主义是什么》(What is Posthuamanism?)一书中讨论起海勒,同样提到梅西会议、维纳、莫拉维克、马图拉纳等内容,使用的全部都是“信息论”(System Theory)这一概念。
③ 其实“源初”“优先”“奠基性”等说法都容易落入德里达所反对的陷阱,它们只能是姑且运用的语言的不趁手之处。德里达一直强调差异、书写、痕迹、补充既是使在场和同一得以可能的东西,又不能被本体化、被当作更高的起源。反人文主义的后学都强调“横亘在主体‘之间’的一种关系结构,这一关系结构之于主体具有某种先在性[……]人们又把这种先行在场的结构指称为一种他性(otherness)或他在性(alterity)[……]一种异于主体、但又内置于主体之中或主体之间且支配着主体或主体间交往的力量”(吴琼 301)。不同学者对不同他者(譬如他人、语言、经济、权力等)的关注和定位不同,但德里达无疑是最为激进和彻底的之一,绝不让差异有任何确定的名称和本体化的地位。
④“通过简单的颠倒,这并不意味着能指是基本的或第一性的。能指的‘第一性’或‘优先性’是站不住脚的荒唐说法,在它试图合理推翻的逻辑中,这种说法恰恰不合逻辑。按理说,能指决不可能先于所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再是能指,并且,‘进行指称的’能指不再有可能的所指。因此,我们应该以另外的方式表达这种思想。它通过这种决不可能存在的公式来表示,但并不真正包含在这一公式中。不对符号概念本身,不对‘……的符号’这一概念进行质疑就不可能以另外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思想。‘……的符号’这一概念始终依附于此处所讨论的内容。因此,这种思想最终会破坏围绕符号概念(能指与所指,表达式与内容,等等)而形成的整个概念体系”(德里达25)。
⑤控制论学者维纳(Wiener)在其论文手稿“The Nature of Analogy”提出信息论是一种类比,“语言总是类比性的”,这一点与语言学转向后的诸多理论契合。沃尔夫也将卢曼与德里达类比,认为控制论与解构主义和语言哲学有很多可以类比相通。参见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以及Cary Wolfe. “Introduction.” What is Posthuamanism?.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0.8.
⑥参见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第254页。
⑦参见[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第9章。
⑧参见《从深蓝到阿尔法狗,人机大战20年进化了什么?》http://www.ccidnet.com/2016/0311/10108732.shtml
⑨参见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第392页。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罗西·布拉依多蒂:《后人类》,宋根成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
[Braidotti,Rosi.The Posthuman.Trans.Song Gencheng.Zhengzhou:Henan University Press,2016.]
克莱尔·科勒布鲁克:《导读德勒兹》,廖鸿飞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
[Colebrook,Claire.Gilles Deleuze.Trans.Liao Hongfei.Chongqin:Chongqin University Press,2014.]
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Derrida,Jacques.Of Grammatology.Trans.Wang Jiatang.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5.]
Ferrando, Francesca. “Posthumanism, Transhumanism,Antihumanism,Metahumanism,and New Materialisms: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Existenz 8/2(2013):26-32
“从深蓝到阿尔法狗,人机大战20年进化了什么?”,赛迪网:2016年 3月 11日,〈http://www.ccidnet.com/2016/0311/10108732.shtm l〉。
[“From Deep Blue to Alpha Dog:What Has Evolved in Man vs.Machine Competition over 20 years?”Ccidnet.11 Mar.2016.〈http://www.ccidnet.com/2016/0311/10108732.shtml〉.]
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
[Harari,Yuval.Homo Devus: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Trans.Lin Junhong.Beijing:China CITIC Press,2017.]
当娜·哈拉维:“赛博宣言:1980年代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严泽胜译,《生产》(第六辑),汪民安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90—327。
[Haraway, Donna.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Trans.Yan Zesheng.Production(Book 6).Ed.Wang Min’an.Guili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8.290-327.]
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Hayles,Katherine.How We Became Posthuman: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Trans.Liu Yuqing.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7.]
伊曼纽尔·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Kant,Immanuel.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Trans.Deng Xiaomang.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4.]
Miah,Andy. “Posthumanism:A Critical History.” Medical Enhancements and Posthumanity.Eds.Bert Gordijn and Ruth Chadwick.Dordrecht:Springer,2008.71-94.
邱仁宗 李念:“‘跨人文’、‘后人文’是对人文主义的丰富吗?——访邱仁宗院士”,《哲学分析》4(2016):152—61。
[Qiu,Renzong,and Li Nian.“Do‘Transhumanism’ and‘Posthumanism’ Enrich Humanism?—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Qiu Renzong.”Philosophical Analysis 4(2016):152-61.]
Wolfe,Cary.What is Posthuamanism?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0.
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Wu,Qiong.Jacques Lacan:Read Your Symptoms.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11.]
张春晓:《后殖民主义的二元结构:关于一种批评策略的方法论在再反思》,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Zhang, Chunxiao. “The Binary of Post-colonialism:Reflection on the Methodology of Criticism.”Ph.D.thesis.Xiamen University,2013.]
支运波:“《一九八四》的后人类生命政治解读”,《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2017):119—23。
[Zhi,Yunbo.“The Posthuman-Bio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1984.”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Social Sciences)2(2017):1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