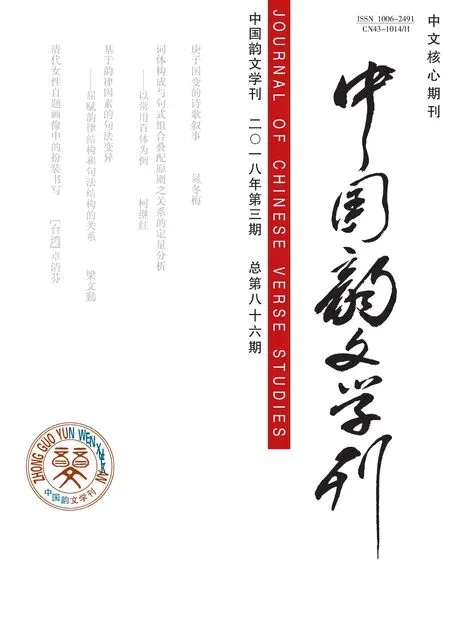清代女性自题画像中的扮装书写
卓清芬
(台湾“中央”大学 中国文学系,台湾 桃园)
一 前言
文人自题肖像的现象由来已久,唐代白居易有《自题写真》《题旧写真图》等多首诗作。明清肖像画越趋普及,自题画像或自题像赞的作品也大幅增加,不让男性文人专美于前,清代女性多有自己的“小像”或“小照”,也在自己的画像上题写诗词。毛文芳《女子写真:可视化的魅影流动》一文指出:“女性画像大量的图绘资料及其相涉的文字生产均为一种新文本,新文本的诞生,代表新的论述范畴的成立,关联着性别文化与自觉意识的女性画像文本,展现了迥异的文化新貌与新视野。”以女性为主体的画像观看呈现出双重意义,一是女性的“自我观看”,一是女性的“自我再现”。透过画像中的场景、服饰与姿态,形塑清代女性心目中理想的自我形象,也藉此建构出希望被他人认知的外在形象。无论是“观看”或是“被观看”,画像着重的是外表的视觉传达,而自己题写在画上的题辞,则表现出女性内在的精神意涵与人格特质,反映了清代女性自我认知、自我形塑、自我书写、自我定位等多重交织的心理投射。
清代女性画像有多种类型,如以母亲形象为主的课子图,以才女形象为主的诗意图等。其中“扮装”一类虽然数量不多,但颇值得留意。清代女性或因宗教信仰,或因性别意识,在自己的画像上刻意展现出佛道装束或是男装等不同于平时的装扮,无论是自己描绘或是请他人作画,均显示清代女性在个人主观意志下所刻意形塑的自我形象,而为个人画像所题写的诗词,则流露出思想的归趋与个人的志趣襟抱,可以填补向来缺乏的女性生平传记数据的空缺。
目前学界对于清代女性扮装画像题辞的研究并不多见,相关研究大量集中在明清戏曲和小说之中“女扮男装”现象的探讨。如华玮《“拟男”的艺术传统:明清妇女戏曲中之自我呈现与性别反思》、盛志梅《清代女性弹词中女扮男装现象论析》等,学位论文如蔡祝青《明末清初小说中男女扮装之性别与文化意义》、吴玄妃《晚明传奇中女扮男装情节研究》、喻绪琪《明清扮装文本之文化象征与文艺美学》、蔡宜蓉《明末清初”女扮男装”故事研究》、林仑静《明清戏曲中“女扮男装”情节之性别意涵》等。本文拟以“清代女性自题画像中的扮装书写”为题,探讨清代女性在个人生命中的角色定位以及自我认同等相关论题。由于女性肖像画的画迹留存不易,本文的研究重心并不在于画像和题辞所组成的视觉性的图像观看,而是根据清代女性自题画像的诗词作品,在“自我形塑”和“他人观看”的多重映像中,勾勒出清代女性在扮装书写中所突显的自我形象。
二 清代女性自题画像中的扮装类型与题辞内容
清代女性自题画像中的扮装类型与题辞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佛道思想的归趋
顾太清《自题道装像》:
双峰丫髻道家装,回首云山去路长。
莫道神仙颜可驻,麻姑两鬓已成霜。
吾不知其果是谁,天风吹动鬓边丝。
人间未了残棋局,且住人间看奕棋。
顾太清(1799—1877),本姓西林觉罗氏,名春,字梅仙,号太清,一号云槎外史,在诗词中自署为“西林春”,满洲镶蓝旗人。为大学士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之孙女,自幼父母双亡。雍正、乾隆时期,鄂尔泰和张廷玉两派互相倾轧,祖父鄂昌受胡中藻诗狱的株连,被赐自尽,籍没家产。鄂家为摆脱“罪人之后”,伪托太清为荣府护卫之女,冒姓顾氏,太清为其别号。道光四年(1824)为贝勒奕绘(1799—1838)之侧福晋。奕绘祖父荣纯亲王永琪,为乾隆帝之第五子。奕绘擅长诗词书法,喜爱金石书画,与太清志趣相投,时有诗词唱和,夫妻情深,由两人之名号及著作名称皆匹配成对可知。奕绘字子章,号太素;太清字子春,号太清。奕绘称幻园居士,太清称云槎外史。奕绘有《明善堂集》、词集《南谷樵唱》;太清有《天游阁集》、词集《东海渔歌》。
奕绘崇信全真教,常偕太清游览道观、讲经论道。两人与京城白云观住持张坤鹤颇有交谊,时相往来,一起参与燕九节白云观放斋以及观张坤鹤受戒等活动。奕绘有诗《燕九白云观观放斋》《白云观》《过白云观时张坤鹤老人将传道戒盖七次度人矣》《四月三日白云观观授全真道戒》《上元白云观》《四月十三雨中作是日白云观传戒余以足疾不往》,词《鹧鸪天·燕九白云观》《尾犯·闰月二十一张坤鹤道人来》,顾太清有诗《次夫子燕九白云观观放斋原韵》《寿张坤鹤五首》《游城南三官庙晚至白云观》《白云观乞斋》《二十二由白云观过天宁寺》《上元前一日同夫子携载钊载初两儿叔文以文两女游白云观过天宁寺看花作》《四月三日白云观看道场作》《四月十三听坤鹤老人说天仙戒是日雷雨大作旌旆沾湿口占一截句纪之》《四月十一白云观听张坤鹤老人说玄都律》,词《水龙吟·题张坤鹤老人小照,用白玉蟾《采药径》韵》《冉冉云·雨中张坤鹤过访》《临江仙慢·白云观看坤鹤老人受戒》《黄鹤引·挽白云观主张坤鹤老人》,两人有多首同题之作。
顾太清的道装像是道光十四年(1834)太清三十六岁时由道士黄云谷所绘,同时黄云谷亦为奕绘画了道装像,奕绘有词《小梅花·自题黄云谷为写黄冠小照》,展现了“瘦骨崚嶒心自在”富贵神仙中人的修道境界,太清有诗《题黄云谷道士画夫子黄冠小照》“三山应有路,附翼愿同归”,表明愿追随夫君修道的意愿。
顾太清《自题道装像》第一首描写双髻道服的外在装扮,由此引发云山仙界的想象。然而转念一想,即使如麻姑一样长寿的神仙,绰约酡颜亦不免鬓发如霜,青春终究难以永驻。顾太清撰写此词时已三十六岁,或有青春易逝、红颜渐老的感叹。第二首以“吾不知其果是谁”拉开了观看的距离。面对换上道装的自己,太清产生陌生化的自我疏离感,提出类似宗教性的、哲理的思维:“吾不知”是画外之我的疑问,而“你到底是谁?”是对画中之我的疑问,在这样的自我辨证中,“鬓丝”的意象再次出现,既然神仙也难驻颜,终究逃离不了衰老的命运,顾太清并不向往仙界的永恒与长生,而是肯定“人间”的意义和价值。王质观仙人下棋,棋局未终而斧柯已烂。仙界一晌,人间百年。人间诸多未了之事,且“住”并且“观看”人间未了之棋局,两次“人间”的认定,超越了仙乡之期待。
奕绘有《江城子·题黄云谷道士画太清道装像》一词题咏太清的道装像:
全真装束古衣冠,结双鬟,金耳环。耐可凌虚、归去洞中天。游遍洞天三十六,九万里,阆风寒。 荣华儿女眼前欢,暂相宽,无百年。不及芒鞋、踏破万山巅。野鹤闲云无挂碍,生与死,不相干。
奕绘在对妻子道装像的观看中,除了外形的描摹,也有逍遥的想象。荣华儿女只是眼前暂得之欢,心无罣碍,看淡生死,才能得道。与太清诗中的自我观看相较之下,奕绘的题咏蕴含了更多的道家哲理,与顾太清不慕仙道、归返人间的旨趣大相径庭,也显示了女性的自我观看、自我形塑与男性的他人观看、他人形塑的差异。
骆绮兰(1756—?)《自题归道图四首。余少时即有学道之愿,往往形诸梦寐。尘务蹉跎,忽忽逾四十年矣。今嘉庆元年六月朔日,誓将屏弃人事,悉心归道,写图见志,并系以诗》:
今年春去更匆匆,越见繁华眼越空。
绝艳名花偏着雨,无云明月不愁风。
百年尘梦随时觉,万里仙源有路通。
试向碧山深处望,玉桃香雾正蒙蒙。
狮王座下拜维摩,示我空山采药歌。
海水一泓龙偃仰,琴心三迭鹤婆娑。
蟾宫常映曈曈日,火宅能开的的荷。
纵道华胥仍是梦,梦中清况尽消磨。
幼时想着五铢衣,直到而今愿不违。
半炷香烟萦案久,三更月影透帘微。
蓬山欲到应须到,莲界知归便可归。
闲坐蒲团思往事,掉头三十九年非。
随风一路去翩翩,从此常游洞里天。
金屋珠帏无艳福,药垆经卷有深缘。
任教蝴蝶重寻梦,料得鸳鸯也羡仙。
借问大千花藏界,花开今夕是何年。
骆绮兰,字佩香,号秋亭,又号无波阁女史,江苏句容人,诸生龚世治妻。骆绮兰幼承家学,少耽书史,好吟咏,能诗善画,工写生,花鸟画师法恽寿平、文俶。所作芍药三朵花图卷,时人题咏者众。三十岁左右丈夫逝世,移居镇江,无子,课螟蛉女以自遣,并寄情于诗文书画。才情出众,深获袁枚、俞陛云、王昶、王文治等文坛宿儒之赏识,颇负时誉。著有《听秋轩诗稿》四卷,编辑《听秋馆闺中同人集》。
骆绮兰为随园女弟子,曾“与大江南北名流宿学觌面分韵,以雪倩代之冤”,与文士往来,亦遭非议:“与三先生相往还,尤非礼。”章学诚抨击尤力:“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骆绮兰撰文反驳:“随园、兰泉、梦楼三先生苍颜白发,品望之隆,与洛社诸公相伯仲,海内能诗之士,翕然以泰山北斗奉之。百世之后,犹有闻其风而私淑之者。兰深以亲炙门墙,得承训诲,为此生之幸。谓不宜与三先生追随赠答,是谓妇人不宜瞻泰山仰北斗也。为此说者,应亦哑然自笑矣。”四十岁以后,骆绮兰深悔过去求胜好名之心,转而信佛,曾作《八梦诗》,记述梦中登天、渡海、登科、从军、种田、隐居、求仙、学佛等事,袁枚亦有《题佩香女弟子八梦图》诗。
骆绮兰的《归道图》乃自己所绘,并题诗四首。第一首认为人间世事转眼成空,向往仙界的清虚自在。第二首写徜徉佛道哲理的愉悦,第三首末句“掉头三十九年非”,更有今是昨非,彻底斩断过去的觉醒。第四首则是肯定道家仙界在个人生命的意义。
当时有多人题咏此图。如赵帅《题佩香夫人皈道图》:
翩翩原是女诗仙,趺坐蒲团又似禅。
解脱半生无限苦,横琴在膝不须弦。
藁砧安在在心头,试问吟章说及不。
旷达聊为皈道计,金丹瑶草复何求。
心香一瓣奉随园,阅历都成见道言。
笑看五铢衣在体,导师是否点苍猿。
妙莲香界扫炎风,尘世繁华眼底空。
洞府不知何处是,听秋轩在月明中。
在他人题写与他人观看之中,大都肯定骆绮兰作诗的才能和文采,而这正是骆绮兰想要抛弃的。四十七岁时骆绮兰放弃写诗,只作画,前半生深为盛名所累,四十岁后决心皈依佛道,自写归道图以表明心志。
江珠(1764—1804)《陆铁箫为余作龙女授经图索赠亦以志谢》:
书卷诗篇两擅场,探微书固敌锺王。
量才陆海千年业,至孝颜瓢一味长。
甫里依然栽杞菊,草间殊肯顾猿獐。
洵知神笔能驱祟,为辅龙宫未有方。
江珠,字碧岑,号小维摩,江苏甘泉人,诸生吾学海室,工诗赋,尤长骈体文。著有《青藜阁》《小维摩集》。
江珠因病请陆铁箫作《龙女授经图》,冀求忏悔,图成,其疾适愈。此诗除赞颂陆铁箫书法造诣高妙、事亲至孝之外,更赞扬其神笔驱祟的神力。
其友张因《题碧岑居士龙女抱经图照印赠》则展现了女性他者观看的视角:
珠帘不卷坐焚香,小字维摩病合当。
要识多才天亦忌,莲台只合拜医王。
已归净土结莲胎,更向尘寰见异才。
读尽儒书千万卷,更从佛座授经来。
月容花貌称仙裳,环佩玲珑八宝装。
笑向人天诸眷属,本来色相两俱忘。
劳劳浊世厌尘氛,法界花香净许闻。
解得人生都是幻,一时苦海化慈云。
张因从江珠外表的花容月貌,环佩玲珑八宝装的穿着写起,标举其人博学以及过人的才华,因病礼佛,祈求脱离苦海。较江珠的自题之作提供更多的讯息。
刘慧娟(1830—1880)《自题归道图》:
历尽风波险,红尘梦已阑。
秦楼萧史去,墖院梵经看。
露重鸾绦湿,风高鹤氅寒。
飘飘吹缟袂,扶我上云端。
着笔凌空想,披图旧愿偿。
回头离草莽,转瞬历沧桑。
尘世光阴短,仙家日月长。
后人功行满,来访白云乡。
刘慧娟,字湘舲,晚号幻花女史,广东香山溪角乡人。顺德举人梁有成之妻,工诗词,善作赋,并精术数,著有《昙花阁诗钞》四卷。刘慧娟与丈夫感情甚笃,丈夫去世后,曾扶乩以求亡夫入梦,后果真有梦,刘慧娟有多首诗记之。此诗流露出丈夫去世后厌弃红尘之想,人世间风波险恶,露重风高,还是远离尘世,将未来依托于仙界为好。
包兰瑛(1872—?)《自题古装小影》:
珍重华严七宝装,朝来新咏玉台旁。
闺中才思虚推鲍,林下风标敢步王。
文酒尽消尘世感,绮罗不学内家妆。
昔随父宦今随婿,直把西湖作故乡。
包兰瑛,字者香,又字佩棻,江苏丹徒人。其父处州知府包星南认为“儒家女贵有士行,三百篇多载闺闼之诗,二南为尤甚,凡以为女士勖也。”手录骚选及唐宋诗,朝夕督课,吟咏不辍。包兰瑛十二岁能属对,随父宦游浙江,“每览山色湖光,觉苏、白之诗宛然在目,性灵所托,篇什日增”。惜其早年诗作毁于洪水。光绪十八年(1892)适浙江郡司马朱时帆之子朱兆蓉(1870—?),随夫宦游浙江、湖南、湖北等地。在杭州时曾与女性文友结诗社,时相唱和,其诗颇受俞樾等文坛耆宿的称赏,著有《锦霞阁诗词集》。
包兰瑛《自题古装小影》一诗,以佛教装束呈现自我形象,以琉璃、玛瑙为饰,显示庄严珍重之意。包兰瑛夫婿尝从广陵琴派释空尘习古琴,并协助释空尘校刊《枯木禅琴谱》,后成为佛门弟子。然而包兰瑛的诗词作品并无太多佛道思想浸染的痕迹,仅有游仙词五首,以及应酬诗词中对于仙界净土的描述而已。包兰瑛与夫婿伉俪相得,有“神仙眷属”之美称,诗词以咏物、记游、赠答居多,并无出世之思。包兰瑛将佛教装扮的自我形象标示为“古装”,或许意在突显出不同于时俗的自我形象,强调“不学内家妆”的出尘之感。“朝来新咏玉台旁”和“闺中才思”“林下风标”“文酒”共同勾勒出“才女”的内在自我形象。包兰瑛《锦霞阁诗词集自序》曾叙述:“幼承先君子庭训……由此遂耽吟咏”,“性灵所托,篇什日增”,“春秋佳日,遨游六桥、三竺间,一二扫眉才子,就湖上结吟社,擘素分笺,秀夺山绿,一时雅集,甚乐也”,“访坡仙之墅,睇陆羽之亭,瀹茗探幽,拈毫题壁,以是诗名走江浙,邮筒往来无虚日”。俞樾也对其诗词颇多称许:“觉清丽之中,独饶逸气。至登览、咏古、读史诸篇,精思约旨,风格不凡。”由此可见包兰瑛心目中理想的自我形象,正是“刺绣余闲翻旧稿,自吟诗句自还删”、 “三旬女壮宜干惕,一卷诗成细讨论”的才女形象,而“才高咏絮”的才女形象,在《自题古装小影》中正好占去了一半的篇幅。结尾“昔随父宦今随婿,直把西湖作故乡”,除了叙述自己自幼及长久居浙江之外,也彰显了她谨守“随父随夫”的传统妇女美德。其父包星南任职浙江郡司马、处州知府,包兰瑛随父宦浙;与朱兆蓉结缡后,又随夫赴任湖北、四川、江苏、浙江等地,“昔随亲作宦,今与婿同游”。才与德二者兼备,正是清代女性理想的自我典范。
(二) 性别的跨越
吴藻(1799—1862) ,字苹香,自号玉岑子,又号晚学居士。浙江仁和人,同邑黄姓商人妻。幼而好学,长则肆力于词,为陈文述碧城仙馆女弟子。精于绘事,善鼓琴,娴于音律,尤精倚声。尝作男子装扮,自写《饮酒读骚图》,吴藻将此一情节写入一折杂剧《乔影》之中。吴中好事者被之管弦,一时传唱。后移家嘉兴南湖,其词豪宕悲慨,晚年潜心修道,皈依佛门。著有《香南雪北庐集》《花帘书屋诗》《花帘词》等。
吴藻《乔影·自题饮酒读骚图》展现其性别意识:
(小生巾服上)【北新水令】:疏花一树护书巢,镇安排笔床茶灶。随身携玉斚,称体换青袍。裠屐丰标,羞把那蛾眉扫。(坐介)百炼成钢绕指柔,男儿壮志女儿愁;今朝并入伤心曲,一洗人间粉黛羞。我谢絮才生长闺门,性耽书史,自惭巾帼,不爱铅华;敢夸紫石镌文,却喜黄衫说剑。若论襟怀可放,何殊绝云表之飞鹏;无奈身世不谐,竟似闭樊笼之病鹤。咳!这也是束缚形骸,只索自悲自叹罢了。但仔细想来,幻化由天,主持在我,因此日前描成小影一幅,改作男儿衣履,名为《饮酒读骚图》,敢云绝代之佳人,窃诩风流之名士。今日易换闺装,偶到书斋玩阅一番,借消愤懑。
《乔影》开篇描写女子谢絮才着男装到书斋赏玩自己所绘的男装小影《饮酒读骚图》,而吴藻亦尝自写《饮酒读骚图》,清代冒俊所辑《林下雅音集》五种,收录吴藻《香南雪北词》一卷,其中《乔影》的曲子《南北仙吕入双角合套》下有“自题饮酒读骚图”等字样,所以《乔影》中的《饮酒读骚图》可视为吴藻改换男装的自我观看,依托杂剧《乔影》里的主角谢絮才所抒发的自我心声。吴藻友人多以“题吴苹香女士饮酒读骚图”为题,可以推知《乔影·自题饮酒读骚图》是吴藻自传式的书写。从书、笔床、茶灶的场景布置,以及青袍的服饰打扮可知吴藻的扮装书写是性别的越界,是闺秀形象跨越名士形象的越界,也是现实跨向虚拟的越界。吴藻借着杂剧《乔影》的女主角谢絮才,说出自己的心声:“生长闺门,性耽书史;自惭巾帼,不爱铅华”,“若论襟怀可放,何殊绝云表之飞鹏;无奈身世不谐,竟似闭樊笼之病鹤”。现实中被性别束缚的女性,看着女扮男装的自画像,企图纾解内心的愤懑。
(场上先挂画摆桌椅放酒杯桌上介)(小生看画介)你看玉树临风,明珠在侧,修眉长爪,乌帽青衫,画得好洒落也。
【北折桂令】你道女书生直甚无聊,赤紧的幻影空花,也算福分当消。恁狂奴样子新描,真个是命如纸薄,再休题心比天高。似这放形骸笼头侧帽,煞强如倦妆梳约体轻绡,为甚粉悴香憔,病永愁饶,只怕画儿中一盏红霞,抵不得镜儿中朝夕红潮。
(饮酒介)昔李青莲诗云: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等看起来,这画上人儿,怕不是我谢絮才第一知己。
(走过右边看介)【南江儿水】细认翩翩态,生成别样娇。你风流貌比莲花好,怕凄凉人被桃红笑。怎不淹煎命似梨花小。(絮才絮才)重把画图痴叫,秀格如卿,除我更谁同调。
在吴藻、谢絮才的自我观看中,“画中人”“镜中人”与真实自我,成为“对影成三人”的三重镜像。既强调女儿身的娇柔病态,又刻意突显“心比天高”的内在心志,在男子巾服的包裹下,显现出性别认定的困惑与冲击。
啐!想我眼空当世,志轶尘凡。高情不逐梨花,奇气可吞云梦。何必顾影喃喃,作此憨态。且把我平生意气摹想一番。(立中场做介)
【北雁儿落带得胜令】我待趁烟波泛画桡,我待御天风游蓬岛,我待拨铜琶向江上歌,我待看青萍在灯前啸。呀,我待拂长虹入海钓金鳌,我待吸长鲸买酒解金貂,我待理朱弦作幽兰操,我待着宫袍把水月捞,我待吹箫,比子晋还年少;我待题糕,笑刘郎空自豪,笑刘郎空自豪。
咳!一派荒唐。真是痴人说梦。知我者,尚怜标格清狂;不知我者,反谓生涯怪诞。怎知我一种牢骚愤懑之情,是从性天中带来的哟!(泪介)
此段展现“平生意气”,列举李白、苏轼、宋玉、王子乔、刘禹锡等人,欲效法青莲东坡的凌云气概,借着取笑刘禹锡不敢于诗中题糕字,反衬自己敢为无惧的豪情壮志。
【北收江南】呀,只少个伴添香红袖呵相对坐春宵,少不得忍寒半臂一齐抛。定忘却黛螺十斛旧曾调。把乌阑细抄,更红牙漫敲,才显得美人名士魂最销。
(大笑介)快哉!浮一大白。(饮酒介)(看书介)我想灵均千古一人,后世谅无人可继。若像这憔悴江潭,行吟泽畔,我谢絮才此时与他也差不多儿。
【南园林好】制荷衣香飘粉飘,望湘江山遥水遥,把一卷骚经吟到,搔首问,碧天寥。搔首问,碧天寥。
(痛哭介)我想灵均,神归天上,名落人间。更有个招魂弟子泪洒江南,只这死后的风光,可也不小。我谢絮才将来湮没无闻,这点小魂灵飘飘渺渺,究不知作何光景。
【北沽美酒带太平令】黯吟魂若个招,黯吟魂若个招。神欲往,梦空劳。(古人有生祭者,有自挽者,我今日里呵)纸上春风有下梢,歌楚些,酌松醪。
能几度夕阳芳草,禁多少月残风晓,题不尽断肠词稿,又添上伤心图照。
俺呵收拾起金翘翠翘,整备着诗瓢酒瓢,呀,向花前把影儿频吊。(收画介)
【清江引】黄鸡白日催年老,蝶梦何时觉。长依卷里人,永作迦陵鸟。分不出影和形同化了。
吴藻、谢絮才心比天高,想到自己终将湮没无闻,才学、理想终究落空,只能抒发满腹的牢骚愤懑,徒然自招其魂,自吊其影而已。张宏生教授指出:“吴藻对声名的看重与追求,也直接来自《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其生命意识的高扬和内心活动的郁勃,正是相通的。”吴藻藉屈原抒发自己郁闷不平之气,象征着女性对于自身存在不满与一味向往“他性”,正因现实中难以弥补的憾恨,只好戴上“性别面具”,聊以自慰而已。
吴藻两首《金缕曲》:
生本青莲界。自翻来、几重愁案,替谁交代?愿掬银河三千丈,一洗女儿态。收拾起、断脂零黛。莫学兰台悲秋语,但大言、打破乾坤隘。拔长剑,倚天外。 人间不少莺花海、尽饶它、旗亭画壁,双鬟低拜。酒散歌阑仍撒手,万事总归无奈。问昔日、劫灰安在?识得无无真道理,便神仙,也被虚空碍。尘世事,复何怪!
《金缕曲》:
闷欲呼天说。问苍苍、生人在世,忍偏磨灭?从古难消豪士气,也只书空咄咄。正自检、断肠诗阅。看到伤心翻失笑,笑公然、愁是吾家物。都并入、笔端结。 英雄儿女原无别。叹千秋、收场一例,泪皆成血。待把柔情轻放下,不唱柳边风月。且整顿、铜琶铁拨。读罢《离骚》还酌酒,向大江、东去歌残阕。声早遏,碧云裂。
其中“读罢离骚还酌酒”,正可呼应《饮酒读骚图》所呈现的魏晋名士形象,是吴藻跨越性别的自我形象。
女性他者的观看则有不同的角度,如归懋仪《题吴苹香夫人饮酒读骚图》:
离骚一卷寄幽情,樽酒难浇块垒平。
乌帽青衫灯影里,共看不栉一书生。
换却红妆生面开,衔杯把卷独登台。
借他一曲湘江水,描出三生小影来。
两首诗都着重在换却红妆之后,在乌帽青衫的外表下,饮酒读骚的行动中,所流露出的抑郁难平的愤懑,重点则是女扮男装的形象描摹与吴藻突显的昂扬心志颇有不同。
三 结语:清代女性扮装书写的意义
综上所述,清代女性扮装书写的意义可归结如下:
(一)服饰与心灵的越界
清代女性藉由服装(道装、男装)的越界,投射出心灵的越界。与平日不同的自我形象,鉴照出隐藏的部分自我。张小虹《两种欧兰朵》指出,以服饰形塑(make)性别、标示(mark)性别、掩饰(mask)性别的特质,女性藉由扮装,跨越并突破性别边界,呈现出独立自主的内在性格。
(二)身分的标示与转换
佛道妆束显示清代女性对于佛道仙界的追求和向往。有的只是暂时逸离生活常轨,显示内在精神的归趋;有的却是厌弃红尘俗世,皈依佛道,作为下半生另一个起点的人生宣示。
(三)自我意识的宣扬
清代女性的扮装书写,从性别局限的不满,才情、抱负、理想落空的悲慨,到佛道修行的身份转换,在在显示女性自主意识的抬头。
(四)理想典范的形塑
清代女性的扮装书写,也呈现出自我的理想典范。“才女”包兰瑛、“名士”吴藻,在自我观看、自我形塑、他人观看、他人形塑的过程中,经过自我选择、重组以及再现,呈现出清代女性理想的自我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