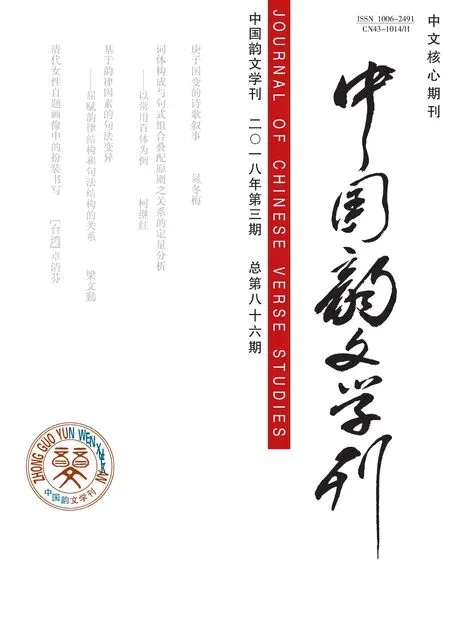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研究综述
祝秀权,曹 颖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周公之琴舞》组诗保存于已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这组诗在竹简中即命名为《周公之琴舞》,作者为周公和周成王。组诗以周公为儆诫多士而作的作为开头的诗句,共有四句。接着是周成王所作的组诗,一共九启,即九首诗,每首诗均以“乱”作结尾。周成王所作的组诗的第一首“敬之敬之”,就是《诗经·周颂·敬之》一诗。周成王所作的组诗的其它几首诗,传世典籍中没有记载。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自2012年公布以来,至今已有不少学者对其作者、内容、结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特别是《琴舞》组诗与《诗经》的关系及其对研究、认识《诗经》的价值和作用等作了多角度的研究,本文拟对迄今以来的学界研究成果作一综述和评价。
一 《周公之琴舞》文本分析
1.《周公之琴舞》的成文时代及作者
经过对清华简做碳14年代测定,确定竹简为公元前305±30年,相当战国中期偏晚时代。但竹简所记载的内容是西周初期的事。李学勤先生通过对传世本《敬之》古代注疏中有关资料的分析,推测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作期大致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期间,《琴舞》是周公及群臣向成王进谏与成王自儆之诗。李学勤同时认为,《周公之琴舞》不一定直接是周公、成王所作,有可能是诗人的代言。
李守奎认为,先秦时期瑟的出现早于琴,西周是否已经出现琴,目前没有充分出土资料的证据,故他认为《周公之琴舞》是战国时期整理的写本。这是关于《周公之琴舞》的成文时代的另一种观点。李学勤和李守奎两人的观点,大致代表了至今关于《周公之琴舞》的成文时代的研究成果和观点。笔者赞同李学勤、李守奎两位先生的结论:《琴舞》组诗非周公、成王本人所作,而是诗人根据其言辞而作,这与《周颂》诗篇的创作性质相符。《琴舞》组诗很可能是楚人的创作,因为它带有明显的楚国诗歌和文化特征。
2.《周公之琴舞》的性质和主题
马芳在研究清华简中的毖诗时认为,《周公之琴舞》与《芮良夫毖》都有明确的儆戒对象,多使用套语、格式化语言的特征。黄甜甜认为,《周公之琴舞》可能在楚国充当贵族教育中“诗教”的教本。
笔者认为,《周公之琴舞》有儆戒之义和诗教功用是无可否认的,这些楚地的诗与《诗经》中的诗一样,在楚国充当着礼乐教化的功能。它们在使用的方式上是以歌舞表演的形式呈现的,诗是服务于、从属于歌舞表演的。在这一点上,《周公之琴舞》与北方的《诗》是一致的。
关于《周公之琴舞》的主题,马芳认为它体现了西周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重视听言纳谏对治国安邦的作用;杨桦也认为《周公之琴舞》反映了修身与治国相结合,敬天保民,力行文王之德政的治国思想。
3.《周公之琴舞》的乐章结构
《周公之琴舞》共十首诗,由周公毖臣诗四句、成王自儆诗九首组成。在周公所作四句前有一个短序:“周公作多士儆毖,琴舞九絉。”成王所作九篇前亦有类似的短序:“成王作儆毖,琴舞九絉。”同样都是“琴舞九絉”,为何周公诗只有四句,而成王诗是九篇呢?
徐正英、马芳认为,成王九首诗是一组完整的组诗。因为其中的祀祖、自儆、儆臣三层意思连贯顺畅,其篇制结构也符合古诗乐以“九”成组的规则,且与传世《诗经·周颂》中组诗的原初形态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因而由短序可推知,周公所作也应为九首,那么《周公之琴舞》原诗应当为十八篇。
李学勤对此有另一种看法,他认为,通过仔细绎读可以发现,《周公之琴舞》中现有的十篇诗是前后呼应的关系,“周公作”的下一篇的口吻确实为周公儆毖多士的口吻,可以作为全诗的领首,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成王作”的后面九篇,却有一些诗篇是不可能出自成王的。如果从诗篇内容中的君臣口吻来划分,可以发现有五篇诗为周公所作,五篇诗为成王所作,分布很有规律,这显然是有意编排的结果。
黄甜甜认为,楚人视周公之诗和成王之诗为乐章,且楚人尚存《周颂》“什”的观念,所以将这十首诗放在一起,成为一组。
《周公之琴舞》组诗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构特点:每首诗开头均有“启曰”,及结尾均有“乱曰”这一种乐章标识。徐正英认为,“启曰”“乱曰”可能是《诗经》的原始乐章形态,经过删《诗》者的整齐划一,这些原始形态被修改、删除了。或由于春秋用诗风气的形成,使“启曰”“乱曰”的原始形态逐渐失去了它的意义,于是“启曰”“乱曰”乐章标识遂最终消失。
江林昌认为,《周公之琴舞》是目前所见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最完整的颂诗结构,它保留了乐舞之诗的原貌,而今所见《周颂》是供阅读的读本,已丢失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原貌。
李学勤认为,《周公之琴舞》与《大武》的结构相仿,对佚乐有重要参考价值。蔡先金认为,这种“启+乱”式的循环结构,能够反映出西周初期的诗乐面貌。
二 《周公之琴舞》与《诗经》
1.《周公之琴舞》与《周颂·敬之》对读与比较
廖名春认为,清华简成王九首诗中的第一首与《周颂·敬之》篇内容基本相同,清华简本在形式上更原始,而《周颂·敬之》篇则更规范。黄甜甜认为,简本在文意表达上更胜今本《周颂·敬之》,句式更稳定。
李守奎认为,简文与毛诗有多处异文,从总体上来看要比毛诗顺畅,并提出:毛诗可能有错简。李守奎总结了三点不同之处:首先,在形式上,简文诗分为“启”与“乱”两个部分,而今本没有;其次,今本中存在异文字,且多为同音假借。例如“陟降厥士”中的“士”旧注读为“事”,这一点与简文是相合的;最后,今本中有讹脱和错简的情况。例如“不聪敬止”“学有缉熙于光明”这些不容易理解的诗句,学者们钻研许久也不得其解,而现在通过对比便可以知道:前一句有讹脱,后一句“缉熙”错衍。
吴万锺通过对读发现,今本《诗经·敬之》篇的诗句相较于简文来说,儒家思想中的“天命”观与学习观体现得更加清晰,并且具有儆戒后世君王的普遍性意义。今本中有些词句的改变也使它们的诗义相较于简本来说变得更加深远,例如,简文中的“文非易帀”在今文中变为“命不易哉”,这样一来,诗的含义原来是对君王周成王的告诫,现在变成了嗣位者的普遍儆戒;“卑监在兹”变为“日监在兹”,原意是君王个人的自我监督,现在变成了一种督促国君日积月累、自强不息、不苟其位的含义;“教其光明”变为“学有缉熙于光明”,“教其光明”是教导至于光明的境界,“学有缉熙于光明”则变为学习要有积累而至于光明的境界。
王长华认为,简文与今文的文字繁简与用语有些差别与这两种音乐系统的不同有关系。《周公之琴舞》与《诗经》来源相同,但是却是属于两个不同的音乐系统的。
沈培通过两者的对读发现,《周颂·敬之》“维予小子,不聪敬止”,对应的简文作“讫我夙夜不逸,敬之”,两相对读可知:《敬之》当读为“维予小子不聪,敬止(之)”,而非“维予小子,不聪敬止”的一般读法。沈还对李守奎“简文与今本《周颂》的押韵很不一样”的观点提出异议,沈认为李文所说的二者押韵很不一样,其实是分析方法的不同而造成的,并非客观事实。《敬之》的韵脚与简文的韵脚并无不同。
2.《周公之琴舞》与《诗》的流传
《周公之琴舞》中成王所作第一首诗与《诗经·敬之》的不同,引发了学者关于《诗》的流传的思考,学者们普遍认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诗》在战国时是分别独立流传的。
李守奎认为,清华简的诗由于在孔子编《诗》之前就传入了楚国,是独立发展的,因而里面的诗作还保持着原始面貌,而《诗经》的编辑整理者并没有见到过这些诗。黄甜甜也提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今本《诗经·敬之》可能并不存在直接传承关系。在战国时代,由于《周颂》在春秋中期之前就已单独流传,而《诗经》在春秋晚期才最终编订完成,因此简本依托于《周公之琴舞》整个文本的形式流传,今本则依托于《周颂》。
吴万锺依据王国维提出的《诗》的流传有“诗家之诗”与“乐家之诗”两个系统的观点,认为《周公之琴舞》应属于乐家传的一种乐歌文本,《诗》在战国时期发挥的不是它的音乐功能,而是阐发诗义的文化功能。
刘丽文认为,周代有与传世本《诗经》不同的“诸侯本”存在。“诸侯本”或与传本《诗经》是同一祖本,在流传中发生变异,衍化成不同版本,或根本没有被《诗经》收入,而是成为了逸诗。
笔者认为,《周颂》和《琴舞》均非成王、周公本人所作,而是诗人根据其言辞的记录而作。它们是根据同一底本而创作的不同版本,这个底本就是西周初期周公、成王对“多士”的“敬毖”之辞。
3.《周公之琴舞》与《周颂》
《周公之琴舞》是目前所见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最完整的颂诗结构,体现了颂诗与乐舞之间的关系,学者们由此展开了对《琴舞》与《周颂》的对比研究。
徐正英、马芳认为,《周公之琴舞》展示出周初颂诗诗乐舞一体的形态特点,从它的“启曰”“乱曰”的音乐标识,题目中的“琴舞”,及前面短序中的“琴舞九絉(卒)”等提示可以看出颂诗是不同于“风”“雅”的只唱不舞的形式的。
吴万锺认为,《颂》的初期形态应是《周公之琴舞》中的这种乐章形式的乐歌。孔子很可能是把乐章形式的诗文本改为读物形式的诗文本,这样《诗》文本更易于快速传播。
李守奎通过对《周公之琴舞》的篇题、语言及毖诗的研究,得出了一些对《周颂》的新认识。如:颂诗有舞,颂与风、雅的主要区别当是演奏时有舞。颂诗分章配套使用,《周公之琴舞》使我们得以推知《周颂》演奏的情形。《周颂》中也应有以儆戒为主旨的一类诗。
王长华认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不能直接等同于《周颂》,因为《周公之琴舞》中的诗篇极有可能是由周宫廷乐师整理之后传入楚地,并非原本,将其看成是周朝颂诗的衍生文本也许更接近历史的原貌。
三 《周公之琴舞》与《诗经》两大公案
1.《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说”
“孔子删诗说”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所说的孔子删诗是否为真,一直是学者们热议的话题,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面世又掀起一波讨论的浪潮。
吴万锺认为“去其重”的“重”不是同样作品的重复,而是作品内容类似的重复。
刘丽文认为,《周公之琴舞》原诗应该是十八首,今本《诗经·敬之》是由删节和重整而来的。这种压缩篇幅、取其所需的删诗做法,是当时诗传抄中的常见现象。从《诗》的创作到编定,诗篇的数量不断增加,加起来有三千多篇是较为正常的现象。篇数太多,良莠不齐,于是孔子取其精华,剔汰归类、校订整理,最终编成了一部完整的《诗三百》。由此认为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是可信的。
徐正英也认为“孔子删诗”说可信。认为司马迁所说的孔子“去其重”还有另一层意思,即指孔子在编订《诗经》时会删除同一版本中内容相近、主旨相类的不同篇目。将简本与今本对比便可以发现,《周公之琴舞》九首诗,今只存一首《敬之》,九去其八,正等同于司马迁所言的十去其九。
谢炳军认为:“删诗”系剟去其篇数之多,“分诗”系增益其篇数之寡。《诗经》的编定属于“分诗”,而不是“删诗”。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的“去重”是“去多”之意。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不能证明“孔子删诗”说成立,迄今尚未有成王组诗为孔子所删之明证。《周公之琴舞》组诗其余诗篇未收入《诗》文本,故难以据《周公之琴舞》而论定“孔子删诗”说。笔者赞同谢炳军的观点,据《周公之琴舞》而推断《周颂》也有过“九体”诗,这是没有什么根据和说服力的。《琴舞》只是楚国人的诗歌,它必定是按照楚国诗歌的体例模式创作或加工的。
2.《周公之琴舞》与《毛诗序》
关于《诗经》的另一公案:《毛诗序》的形成时间问题,郑玄有这样一个说法:《大序》为子夏所作,而《小序》为子夏与毛公合作。徐正英、马芳认为,《周公之琴舞》的面世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周公之琴舞》中两篇短序在展现先秦时代诗序的原始形态的同时,也说明了这样一点:《诗经》原本是有序的,且《诗序》不是汉代的产物。
同时简本的短序中对其诗篇儆毖性质的判断与今本《诗经·敬之》的序文是一致的。不过简文之序只是简要说明了作者及作品性质,今本诗之序则具体阐释了诗旨。由此可以推测,《毛诗序》很可能经历了从先秦到汉代这样一个逐渐完备的过程。
四 《周公之琴舞》与楚辞
关于《周公之琴舞》流传到楚地的原因,李学勤认为与周王朝发生的王子朝之乱有关。《左转》记载:“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周公之琴舞》是专供嗣王即位这一类典礼演奏用的乐章,因而出自于王子朝等人所携往楚国的典籍也是合情合理的。
关于《周公之琴舞》与楚辞的相似之处,王长华认为,在由周宫廷乐师整理之后,《周公之琴舞》中的诗篇传入了楚地,楚国人结合楚地音乐表现形式对之进行改造,便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周公之琴舞》。笔者赞同此说,因为楚人在据成辞加工诗歌时,必然会带上楚国诗歌的特点,故《周公之琴舞》与《周颂·敬之》形式上、内容上均有所不同。
李颖依据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的“九絉”材料和传统文献,对楚辞“九体”的一系列问题,如其结构特征、发展脉络、所承载的礼乐观念等做了较为深入细致的阐释与剖析。如认为楚辞“九体”与“琴舞九絉”与古《九歌》,它们都以“九”为结构缀连成篇。这种特殊结构方式,是当时楚国一种标准的诗歌体裁样式。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琴舞九絉”就是周代的《九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