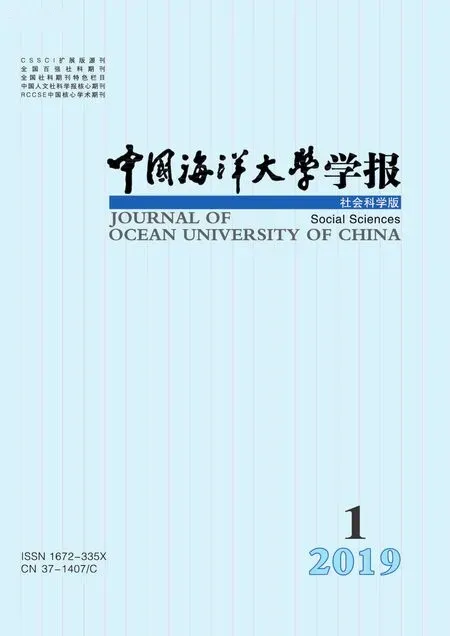区域海洋环境合作对南海低敏感领域合作的借鉴与启示
王秀卫
(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高度重视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特别规定了各国在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基础上为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进行合作的义务,[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7条规定:各国在为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而拟订和制订符合本公约的国际规则、标准和建议的办法及程序时,应在全球性的基础上或在区域性的基础上,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同时考虑到区域的特点。明确规定了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的内容。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公约、议定书已经成为国际海洋合作的最丰富、最成功的部分。2017年11月16日,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海洋局公布了《“一带一路”海上合作设想》,[注]根据该设想,我国将与沿线国家合作建设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以及中国-北冰洋-欧洲三条蓝色经济通道,并建议:推动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加强在海洋环境污染、海洋垃圾、海洋酸化、赤潮监测、污染应急等领域合作,推动建立海洋污染防治和应急协作机制,联合开展海洋环境评价,联合发布海洋环境状况报告等。此设想致力于进一步推进与沿线国家战略对接和共同行动,推动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蓝色伙伴关系,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实现人海和谐、共同发展,共同增进海洋福祉,共筑和繁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注]见《两部门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http://money.163.com/17/1117/09/D3EE1LPG002580S6.html.设想中的三条蓝色经济通道沿线既有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也有地中海、红海、波罗的海等区域海(Regional Seas),其中两条通道经过南海通达非洲、南太平洋,体现了南海这一区域海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笔者认为,要打造蓝色伙伴关系,研究沿线国家区域海洋环境保护机制,对“一带一路”海洋环境保护工作意义重大,南海作为区域海,在“一带一路”不断推进的实践中,应该也必将不断加强与沿线国家及区域的交流与合作,其先进成功经验也必将为南海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提供借鉴,促进南海海洋环境保护区域合作日渐完善。
一、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发展概况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严重海洋污染事件,1968年的“托雷一坎永”号[注]油轮在英吉利海峡触礁,有大约8万吨原油泄漏,污染了英国100多千米的海岸线,造成英吉利海峡和英、法海岸线的重大污染。事故不仅促成了1969年《国际油污民事责任公约》等一系列预防和处理海洋油污污染的国际公约的诞生,也促使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系列海洋环境保护问题的决议,[注]包括《海洋问题的国际合作》(2414号决议)、《防止开发海床所引起的海洋环境污染》(2467B号决议),以及1969年《改善、防止和控制海洋污染的有些措施》(2556号决议)等。将海洋环境保护问题作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要议题,同时,在受污染严重的北海周边国家积极促成下,《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也称《波恩协议》)于1969年6月9日签定,两个月后协议生效,成为全球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的起点。
成立于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非常重视全球以及区域海洋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在1974年即提出了“区域海洋规划”(Regional Seas Program,RSP),旨在对海洋环境和资源进行可持续的管理和利用,从而减缓世界海洋和沿海地区的加速污染和退化。[注]Brandy Vaughan,Financ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Seas Program Conventions and Action Plans,UNEP, www.unep.org/regionalseas.在UNEP推动和区域海周边国支持之下,目前全球已经形成19个区域海洋环境保护项目,共达成71个区域海洋国际条约。其中,UNEP管理(UNEP administered Regional Seas programmes)的七个区域海洋项目为:加勒比海(Caribbean Region)、东亚海(East Asian Seas)、东非(Eastern Africa Region)、地中海(Mediterranean Region)、西北太平洋(North-West Pacific Region)、西非(Western Africa Region)、里海(Caspian Sea)。非UNEP(Non-UNEP administered Regional Seas programmes)管理的区域海洋项目为黑海(Black Sea Region),东北太平洋(North-East Pacific Region ),红海(Red Sea)、亚丁湾( Gulf of Aden)、波斯湾(ROPME Sea Area),南亚(South Asian Seas)、东南太平洋(South-East Pacific Region)、太平洋(Pacific Region)。独立区域海洋项目(Independend Regional Seas programmes)为北冰洋(Arctic Region)、南极(Antarctic Region),波罗的海(Baltic Sea),东北大西洋(North-East Atlantic Region )。上述19个区域海洋不同程度涉及到143个国家,其中基本包括了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此,对上述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协定进行研究,有助于我国更好的开展“一带一路”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其成功经验也尤其值得南海区域各国借鉴。
(二)概念
所谓“区域海洋”,其实并无权威官方概念界定,按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描述,“区域海洋被认为是生态系统应受保护的海洋区域,以及海岸与岛屿国家因此而受理于国际合作的海洋区域”。[1]区域海环境保护工作尤其需要各国切实开展合作,第一,由于区域海洋往往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大陆或岛屿、群岛包围,也往往是繁忙的航道,因此,承载了较多的陆源污染和船舶污染,并且富含油气资源的海域还会存在较大的油污开采及运输导致的油污污染的风险;第二,区域海洋一旦造成污染,也会反过来严重影响沿海国的海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区域海洋的海洋环境脆弱、污染风险高、污染损害大;第三,由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一,人口环境资源情况各异,对于属于“regional common”的海洋环境而言,各国可能在开展保护的方式方法和程度等方面各不相同,甚至有的国家不愿意主动承担维护区域海洋环境的国际义务,因此,单单依赖任何一国或地区都无法根本解决区域海洋的环境保护问题。综上,将区域海洋作为海洋环境保护的重点发展领域,非常合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根本宗旨,也有利于区域各国的共同利益。区域海洋规划提出后,得到了大部分区域海洋沿海国的支持,也得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的赞赏。
由于不同区域海洋周边国家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均各不相同,因此,区域海洋环境合作的紧密程度和效果也不一样。目前可以大概将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模式分为以下几种:(一)地中海模式。[注]地中海沿岸国家较多,包括欧洲国家西班牙、法国、摩纳哥、意大利、马耳他(岛)、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黑山、阿尔巴尼亚、希腊。亚洲国家:土耳其、叙利亚、塞浦路斯(岛)、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非洲国家: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19个国家。地中海沿海国家数量众多,分处三个大洲,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大,因此,地中海的海洋环境保护合作采用了“综合加分立”模式,即签定一揽子公约,另外附加议定书,这一模式实际上也是国际环境法发展的成功经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控制臭氧层维也纳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等著名国际环境公约都成功的应用了“公约加议定书”模式,先取得原则性一致意见,然后通过逐年的缔约方大会,就不同议题进行具体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地中海模式也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推广到其他区域海洋合作项目。(二)波罗地海模式。波罗地海周边被陆地包围,有瑞典、芬兰、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德国、丹麦等国家,人口9000多万,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地理位置重要,海洋环境面临严重威胁,《保护波罗的海海洋环境公约》于1974年通过,与其他配套的政府宣言、行动计划、建议等形成了全面综合的海洋环境保护体系,在区域海洋环境保护领域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三)南极、北极模式。另有学者将南极、北极的海洋环境保护模式也作为区域海洋环境保护的组成部分,笔者略有疑义。有人认为,南海区域的海洋环境保护是以1959年《南极条约》为核心的条约体系发展起来的一个区域性法律制度,北极已经形成北极理事会(环北极国家包括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美国和俄罗斯)的“区域”治理模式,共同探讨合作保护北极环境,通过并发布了《北极环境保护战略》,签署了《北极环境保护宣言》和《北极海上搜救协定》,[2](P163)笔者认为,虽然南极、北极的环境保护模式各有可资借鉴之处,但仍应明确,南极也好,北极也罢,都不应该属于“区域海”,而是“洋”,其法律性质、法律地位有着根本的区别,不应适用《公约》123条关于闭海、半闭海的相关规定。
(三)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展望
2016年10月1日,在韩国仁川召开的第18届全球区域海洋条约和行动计划大会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布了2017-2020年的区域海洋战略指针(Regional Seas Strategic Direction),指针认为,无论是渔业还是气候变化管控,海洋和沿海地区的环境都至关重要,过去几十年,国际社会对于海洋环境的全球、区域和国内治理都日益重视,1982年里约会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从而成为全球环境保护包括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指导理念。区域海洋项目作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重要的区域环境保护机制,拥有143个参加国的19个海洋区域,对于人类可持续利用海洋和长远福祉关系重大。2015年9月,联合国通过了《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范围广泛,涉及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特别关注到海洋的可持续利用。2017年6月,联合国召开环境大会,主题也是蓝色伙伴关系和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我国作为区域大国,正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区域海洋环境保护组织开展合作极为重要。可以看到,作为全球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将会持续发力,并在“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中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生态环保合作格局发挥重要作用。
二、区域海洋环境保护的成功经验
(一)注重信息共享及及时通知
信息共享对于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至关重要,几乎每个条约中都有关于信息收集、共享和传播的条款(总条款数量达493条)。在缺乏合作的闭海或半闭海区域,虽然各国事实上地理位置接近,但由于顾及到“主权”、“信息安全”等因素以及可能存在的政治、外交矛盾,不愿意将本国特别是领海、专属经济区的海洋环境、资源信息及其动态与他国共享,对于争议海域、未划界海域就更加敏感而缺乏互信和合作,人为的海洋界线也封锁了海洋环境信息的流通和共享。因此,加强区域成员国之间,区域海洋环境合作平台与其它区域平台之间,区域平台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区域外国家必要的信息交换共享,有助于节约信息收集成本,提高信息完整性和准确度,有助于准确评估区域海洋环境与资源现状及发展趋势,并发现存在的问题。另外,区域合作的情况也应定期进行总结和通报,即形成报告机制(reporting mechanism),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定期发布“regional seas reports and studies”,201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的《关于加强区域渔业组织与区域海洋环境保护项目之间合作的建议》中第二条就提到,基于互惠的目的,加强区域渔业组织与区域海洋环境保护项目之间的数据和信息交换。
及时通知,是指当发生污染海洋环境事故或危险时,污染来源国应每一时间将污染事故原因、地点、影响范围及已采取措施等通报给区域内所有成员国,以俾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组织及各成员国尽快反应,做出正确决策,从而最大限度减少对海洋环境的危害。由于环境污染往往具有广布性、流动性,如大气、河流、海洋等均具有无法控制的整体效应,因此,环境污染或者危险一旦发生,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第一时间及时通报,并协同采取预案,以减少损失扩大,任何想隐瞒事实的侥幸心理都只会使损失继续扩大,从而产生不可逆转的危害。
(二)国内环境立法力求统一
与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公约相衔接的是各国的国内环境保护立法包括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海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法律制度。这里讲的统一是指,一方面,各国国内法都应进行制定或修订,从而使得国内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与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公约相一致。根据各国实践,无论是国家签署的国际公约在国内无须转化,直接适用从而产生法律效力,还是国家签署国际公约后,需通过国内立法转换才产生法律效力,[3]国际条约都具有较高的规范效力。以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为例,其诸多条款实际上体现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油污民事责任公约》等国际法律规范的内容,如海洋环境域外管辖权、政府对于海洋生态损害的索赔权等制度;第一方面,各成员国在具体的排海重点污染物目录、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总量控制、最佳可得技术标准等环境管理基准手段上应尽可能保持一致,否则会造成有些排污行为在某国合法,在另一国则超标而成为非法行为,不利于区域海洋环境的协同保护。如《保护黑海的战略行动计划》要求缔约方到1996年制定共同的环境质量指标,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制定统一的排放标准,另外,几乎所有的防治污染公约或者议定书都含有合作制定标准的义务内容。[4]对于一些可能会危及区域海洋整体利益的立法、决策和建设项目,应合作制定环境影响评价准则,确保各区域内各缔约国以共同的标准开展环境保护工作,[注]如《<保护和发展大加勒比区域海洋环境公约>陆源及陆上活动污染议定书》第7条。或者通过相互通知、交换信息和磋商,开展区域环境影响评价合作,[注]如《巴塞罗那公约》第16条。并以适当形式向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组织提交环境影响评价报告。[4](P271)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合作条款非常普遍,在各条约及议定书中出现达65条之多。另外,在各国专属经济区之外海域建立共同开发、渔业资源的配额制以及渔业资源共同养护等制度性协商对于区域海洋环境共同保护也非常有益。
(三)成员国执法与司法协同
在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公约及其议定书等形式的区域协定基础上,各国环境立法的协同和统一为区域海洋环境保护执法协同提供了可能。各区域组织依据本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公约及议定书,共同拟定并执行区域海洋污染控制行动计划和方案,商定具体的实施措施以及实施路线及时间,并定期审查修订,[注]如《保护地中海免受陆源和陆上活动污染议定书》第7条。笔者认为,区域海洋环境保护执法协同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渔业配额的制定和监督、休渔期等渔业资源养护和保护执法、环境事故如石油钻井平台爆炸、船舶油污泄漏、核污染等重大海洋环境损害的应急反应(response to pollution incident)、海洋生态修复等长期活动等,都极其依赖区域各成员国的通力合作,特别是政府各执法部门之间的高效信息通报和行动一致。
(四)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切实合作
海洋科研是开展其他海洋活动的基础。海洋科研对象的全球性、多学科性和高投入性等特点,决定了海洋科研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作为区域合作的基础,成员国之间开展海洋环境保护、生态修复领域的科学研究合作也是非常有益的经验,也会极大的促进各国积极、正面的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关于科学技术合作的条款在区域海洋环境保护条约中比比皆是,如《巴塞罗那公约》第12条规定:各国“同意尽可能直接合作”,“酌情通过在科学技术领域有资格的区域性或国际性组织进行合作”。《赫尔辛基公约》第24条“科学和技术合作”规定:缔约国可以直接或者通过适当的国际组织为实现公约目的,在科学、技术和其他研究领域开展合作,并且交换数据和其他科学信息,为便利研究,各国应协调各自政策以利于此种科学研究获得行政许可和顺利开展。
(五)有固定合作平台和纠纷解决机制
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条约的有效执行必需有稳定、高效的平台支撑,无论其名称为委员会、理事会还是海洋环境保护组织,都具有明确的决策机制、行政机制和监督机制,这样才能保证区域海洋环境保护目标的稳定和实现。目前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公约的执行机构主要包括“单一区域性组织”(如东南大西洋渔业组织)、“缔约国会议+秘书处”(如《巴塞罗那公约》《里海海洋环境保护公约》等)、“缔约国会议+委员会”(《布加勒斯公约》等)三种模式。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公约缔约国往往会约定纠纷解决机制,首先,友好磋商、协商解决,如果无法达成一致,则依公约可以寻求中立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介入解决,包括国际法院、国际常设仲裁法庭等机制。大部分公约都会有一条纠纷解决条款(settlement of disputes),有的甚至约定仲裁庭的组成和规则。[注]参见《2002年加勒比地区渔业协定》第30条《仲裁庭的组成》、31条《仲裁庭的程序规则》。
三、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对南海低敏感领域合作的借鉴
南海是区域海,也是半闭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规定区域海洋环境合作同时,也着重规定了闭海、半闭海沿海国家的合作义务。[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23条规定: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在行使和履行本公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时,应互相合作。为此目的,这些国家应该尽力直接或通过适当区域组织:(1)协调海洋生物资源的管理、养护、勘探和开发;(2)协调行使和履行其在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方面的权利和义务;(3)协调其科学研究政策,并在适当情形下在该地区进行联合的科学研究方案;(4)在适当情形下,邀请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与其合作以推行本条的规定。基于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公约共性的考察,可以发现区域合作的共同意愿、正确的指导思想、固定的合作平台和争端解决机制、财务机制以及全理的信息共享、立法协同、执法合作等制度的建立对于区域海洋保护合作至为重要。成功的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对于“一带一路”海上合作以及南海低敏感领域合作甚至《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都应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99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倡了“南海大海洋项目”,其从全球环境基金(GEF)获得资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向全球环境基金秘书处提交了项目开发援助建议,提议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基金《扭转南海与泰国湾环境退化趋势》项目”进行援助,该项目获得批准,参与国家包括中国、泰国、越南等七国。[5]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及外长代表于2002年11月4日在金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应该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南海低敏感领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通过举办政府间会议、制定行动计划等方式开展了一系列合作。在亚洲,中国与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越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柬埔寨、印度、韩国等签署了双边海洋领域合作文件,建立了东亚海洋合作平台、中国—东盟海洋合作中心、中国—东盟海洋科技合作论坛等合作平台。[6]在合作经费方面,2011年11月18日,中国总理温家宝18日在印尼巴厘岛出席第十四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时宣布,中方将设立3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逐步形成中国—东盟多层次、全方位的海上合作格局。之后每年中国都与东盟国家就低敏感领域合作召开专家论证会等形式的磋商。[7]
我国作为南海区域的唯一大国、金砖国家成员国、全球第二经济体以及南海争端当事国,应主动依托《公约》规定,充分借鉴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机制的先进成熟经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区域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指引下,培育南海“社区”观念,通过“一带一路”和泛南海地区经济圈建设,不断紧密与南海周边国家合作,逐渐培育国家互信,加强经济依存度,共同处理区域共同事务,保护海洋环境、养护海洋生物资源。具体建议如下:
(一)逐步推进南海区域海洋环境保护条约或协定的达成。目前,中国和东盟国家已就“南海行为准则”(COC)的案文进行了首次磋商,但结果如何尚未可知。笔者建议,在COC磋商的同时,不妨碍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开展双边、多边或者特殊领域如渔业、海洋保护区等的具体合作,并以达成协议的方式不断推进南海区域各国的互信,因此,南海低敏感领域完全可以“双轨”或者“多轨”,这也有利于发挥低敏感领域合作的正面影响,提升COC的磋商节奏,最终达成合理的框架协议,也促成南海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公约的生成。
(二)依托现有合作平台,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础上,成立双边直至多边的南海区域合作平台(如南海合作理事会[8]),内设南海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理事会,负责海洋环境监测以及环境事故预警、应急、处置合作;南海渔业资源养护合作理事会,负责天然渔业资源调查、休渔期、渔业执法合作包括争议海域的合作执法;南海环境损害纠纷解决委员会,负责组织环境损害评估、索赔并管理赔偿基金。
(三)逐步推进海水水质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统一。比较南海周边国家对于近海、远海的海水水质标准,就会发现其中差别较大。[9]以海水水质标准分类为例,中国海水水质标准将海水分为四类,[注]第一类:适用于海洋渔业水域,海上自然保护区和珍稀濒危海洋生物保护区。第二类:适用于水产养殖区,海水浴场,人体直接接触海水的海上运动或娱乐区,以及与人类食用有关的直接的工业用水区。第三类: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滨海风景旅游区。第四类:适用于海洋港口水域,海洋开发作业区。泰国分为七类,[注]第一类:保护区。第二类:珊瑚保护。第三类:自然资源保护。第四类:水产养殖。第五类:接触水的运动。(water-contact sport)第六类:接触水的运动。(water-proximity sport)第七类:工业园区。印度尼西亚分为三类,[注]第一类:港口和港口海洋。第二类:海洋游憩用水。第三类:海洋生态系统。马来西亚分为四类。[注]第一类:保护区、海洋保护区、海洋公园。第二类:海洋生物、渔业、珊瑚、珊瑚礁、娱乐和海水养殖。第三类:港口、油气田。第四类:红树林河口及河口水。越南在最新颁发的2015年《国家海水水质标准》(QCVN 10-MT:2015/BTNMT)中,依照“沿海”、“近海”和“远海”三个海域设置了3个不同的水质标准区域。并在“沿海”下按照海洋区域使用功能的不同,又划定了“水产养殖及海洋生物保护区”、“海滩及海上运动区”以及“其他区域”3个不同的水质分类标准。[注]越南将沿岸海域海水分为三类:第一类:渔业养殖区,水生保护。第二类:海滩区,水下运动。第三类:其他的地方。另外,各国具体污染物的控制限值也各不相同。
根据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的成功经验,不同的海水水质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不利于保护区域海洋环境,容易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等环境负外部性效应,应通过区域海洋环境保护平台逐步推进区域内各国采纳一致的海洋环境质量标准,并通过严格执法保证标准实施,为提高各国行动积极性,可考虑设立海洋环境保护基金,帮助行动有困难的国家或相关产业,并对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者进行生态补偿。
(四)开展协同执法行动。可以根据由易至难的过程,通过一些环境事故、环境问题的共同应对,再建立一些专项执法协同机制,如渔业资源破坏的协同执法机制,最后形成统筹海洋环境保护执法协同机制,这些执法协同机制也有利于成员国之间其它领域的互信和合作,这一点对于南海低敏感领域合作极具借鉴意义;二是司法协助与合作。区域海洋环境污染者与受害者往往可能分处不同国家,污染海域可能处于一国或两国以上领海、专属经济区或者争议海域,甚至是公海,因此,污染事故发生后,污染者、受害者、代表受污染的海洋环境的政府都可能分处于多国,各国对于发生在本国管辖海域、危害本国海洋环境资源的违法行为可以按照本国国内法实施行政处罚,对于发生在争议海域的违法行为进行适度执法。[10]另外,民事侵权纠纷的法院的管辖权以及解决纠纷适用的法律规范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复杂性。除依据既有司法管辖规定之外,如发生管辖争议,各国应就个案进行司法协调,或通过协商达成一些司法管辖方面的区域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