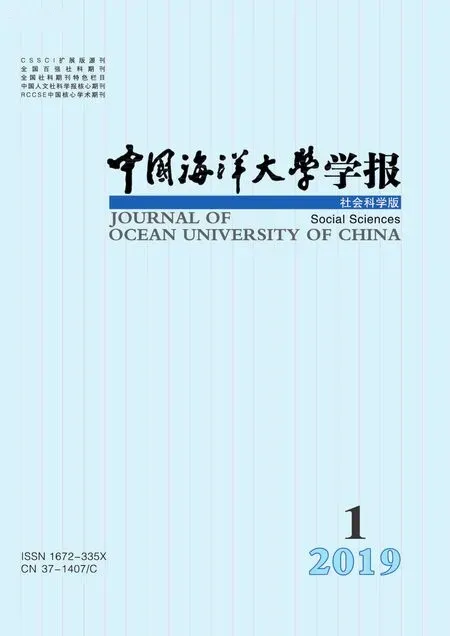从“文学自觉”到“文化自觉”的“大文学”观
——兼论先秦文学的三大景观
赵 明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由“纯文学”观到“大文学”观的置换,反映了从“文学自觉”到“文化自觉”的时代要求。“大文学”观的提出缘于对中国古代文史哲兼容的文学特质的认识;“大文学史”观是“大文学”观的历史实践形态,中国先秦时代既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也是中国古代“大文学”生成和形成的起点。揭密和展示在“源头与高峰”中某些带有基因性或典范性的“大文学”景观,不仅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大文学”的特色,而且,对于今人推助“大文学”观与“纯文学”观的对话和交流,以便更广泛地掘发与实现文学的价值和功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
一
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现实中,从精英到大众,都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对“纯文学”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提出质疑。20世纪90年代以来,原有的“纯文学”观和文学价值观,终于在“内部危机”和“外部挑战”的双重窘困中发生了动摇:“纯文学”观的封闭和狭隘,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维、观念、需求所经历的重大变化;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已引起了人们对文化与“人文”的特别关注;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因此带来的多种文化接触的大波动,更使“文化”成为世界性的一大“热点”问题。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把这种反应概括为“文化自觉”的要求。这种要求是普遍而迫切的,它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所涉及的一切领域。正如费先生所说:“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1]正是这种“文化自觉”时代的来临也使文学研究者们得以站在比前人更高更广的平台上,思考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它和文化是一种什么关系?从而以文化视野来审视文学及其价值观。是的,如果文学不甘于走向边缘,她就不应孤芳自赏于所谓“文学的自觉”“艺术的独白”,而必须回归于文化,并在文化深度与人类意识中发现自己的身份,证明自身的价值。诚然,文学是“人学”,是一种生命的“人学”表现,但是,当人由生物的人变成了社会的人,个体生命就处身在由具体文化内容“民族与时代的”构成的人文世界之中。所以,我们需要在一种由“文学—文化”或由“文化—文学”的视界中揭示文学生命的秘密。而语言视界、生命视界、文化视界,三者统一起来才是完整而广阔的新视界:语言是生命的外化形式,而生命活动则是文学与总体文化建构间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文化、生命、语言,只有构成三者彼此相互作用的张力场,方能真正深入地揭示文学的秘密。”[2](P833)近年“大文学”观和“大文学史”观的出现,恰恰反映了从“文学自觉”到“文化自觉”的时代要求,表现了学者们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深入思考和文学观换代过程中的视野拓展。
二
“大文学”观和“大文学史”观的出现,还内涵了在中西比较中对民族文学特色、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反思和重新认识。
我以为,“大文学”观和“大文学史”观乃是当代学者在“文化自觉”中对民族文学传统和民族文化特质的一种理论概括,也是对受西方影响而形成的“纯文学”观的借鉴和扬弃。与西方“纯文学”相对峙的“大文学”观,根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特殊道路以及中国古代文史哲因浑融共处而相互渗透这些特点的认识。
文化上的浑融性、综合性,曾是世界各民族远古时期的共性,如古希腊早期的“哲学”,便是全部知识的总称,而非专指“形而上”的学问。但是,知识的分化过程又是历史的必然,在这一点上,由于东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致思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存在差异。在西方,知识与学科分化过程表现得较为疾速,而在古代中国,这种分化过程则表现得相对迟缓。知识分化的“疾”与“缓”,并不说明二者有优劣、高低之别,而是在“精审”与“渊博”上各有千秋,而是各自形成了自身“特色”。就中国古代情况来说,正是由于知识分化过程相对迟缓,它在某种意义上倒发挥了“综合”“交融”固有的“优势”,它倒有利于文史哲之间的渗透由表及里,相互滋润,从而得以避免单科独进的偏执与蔽限,更有利于本身深入全面的发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载体的文史哲,长期在互涵互摄中发展,文化上形成了由早期的文史哲不分,到后来的文史哲互渗。恰恰是这一特点,不仅保障了文学与整个文化浑融共处的自然生成形态不被割裂,而且使得文学从哲学、史学等领域吮吸了深刻的思想精髓和丰富的文化营养。文史哲的长期浑融共处和相互渗透,曾使中国古代文学在疆域广度、精神深度和文化厚度等方面,显示出自己凝重而丰厚、雄浑而绚丽的风貌。这就是我的“大文学史”观。
在文史哲互动的文学建构中表述的“大文学史”观,决不是文史哲的杂凑,而是站在文学本位的立场上,以审美形象和情感表达为旨归的融化与整合,摄取与渗透,是文学价值与功能在文史哲兼容中的广泛掘发与实现。先秦时代,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开创期、奠基期,观察揭示这个时期中国文学所具有的“大文学”特质,对于理解“文学的文化本质”和救治“纯文学”的枯竭,具有寻根振叶,正本清源的意义。
三
在文史哲兼容的“大文学”中,不妨以《左传》《庄子》和“楚辞”为范例,在举隅中一睹“大文学”雄浑的风貌和瑰丽的气象。其中,《左传》代表史学的文本;《庄子》代表哲学的文本;“楚辞”则代表文学的文本。这些文本不仅已经进入了“大文学史”,成为先秦文学中的重要景观,而且,它们作为原典作品,又以其原创性、典范性和奠基性,开创了不可动摇的文学传统。《左传》是一部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层面深刻反映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大转型历程的历史名著,一向被史家视为记事客观,材料翔实,文笔生动,是先秦经典的“史学”文本,也是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历史散文巨著。在记写春秋列国史实中,作者不仅以民本主义的史学意识和广阔的历史视野,记录了“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中所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以及和这些事件息息相关的历史人物,第一次以一种自觉的英雄史观观照历史政治舞台上英雄人物的活动,举凡各国君位的更替嬗变、执政者的谋权夺势、贵族内部的倾轧争斗、侯国之间的攻伐侵掠、战场荒原上的干戈相对,无不具现其史笔之下,而且,书中对重大历史事件中历史人物精神性格入木三分的刻划和曲折跌宕的戏剧性情节的描述,更极大地增强了史笔的文学光彩。凡是读过《左传》的人,对书中某些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的形象和那些悬念迭起、引人入胜的事件情节,都会深留记忆,终生不忘。
《左传》开启了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也昭示了史传文学的一个明显特点:在叙述对民族生存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时,重视历史人物生气勃勃的创造作用,而且着重于展示人物活动和揭示其精神世界,并通过他们独特的形象和鲜明的个性,反映了华夏民族根源于自己的历史文化特点而形成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这一特点无论是在后来司马迁的《史记》还是在班固的《汉书》中都得到了继承和发挥。可以说,运用文学手段和追求文学效果的《左传》,不仅是“无韵的史诗”“历史形式的戏剧”“史传文学”的开山祖,而且更从民族精神和文学传统两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后世传记文学、历史戏剧和历史小说的发展,范型着中国文学文史结合的轨迹和方向。这是史学向文学渗透,文学向史学拓展疆域的一个显例。
再说《庄子》。在“百家争鸣”中出现的《庄子》,已显示出极高的思维水平和思辨能力,是先秦哲学的经典文本。但是,正是在《庄子》中,我们又看到哲学与艺术、哲学与“诗”发生联系的更为瑰奇的“大文学”景观。
庄子不仅是先秦诸子中最有哲学深度的思想家,同时,他还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宗师,是一个才华谲奇,想象超拔,情感奔放的大文学家。一部寻幽探奥的哲学著作,充满了激情、想象和千汇万状的形象,这就是《庄子》。《庄子》33篇,除《天下篇》可作先秦学术史著作来看,其他32篇,篇篇的不同主旨都是借助于一系列形象生动、妙趣横生的寓言加以表达,这就使全书的理论线索上缀满了形象的花结,散发出美的意绪,这岂不就是形象化了的思想,艺术化了的哲学吗?而事实上,庄子其人就是一身二任的哲学巨匠和艺术宗师。庄子论道,每每把得“道”的境界和艺术境界结合得浑然一体,如水乳交融,似天衣无缝。在广为传播的“庖丁解牛”的故事中,庄子所描述的庖丁解牛的全过程,就是极高超的艺术活动过程。庖丁所说的那种由“技”(艺)入“道”和“技”(艺)中见“道”的体验,决不是普通人的感受,而是一种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能得到的高级经验。在《庄子》中,举凡论“道”的寓言故事,如“痀偻承蜩”“梓庆为鐻”等等,其中都伴有高超的艺术活动,都表现出“道”和“艺”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联系:“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注]参阅宗白华《中国艺术境界之诞生》《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这就是《庄子》为中国艺术精神或中国艺术境界提供的经典示范,也是庄子哲学之所以能够涵盖整个中国艺术,衍射于古代美学、诗学、画论的基本原因。
前人评《庄子》,多将《庄子》中的艺术想象、浪漫情景、浓郁抒情三大特征与诗人屈原相比照,如明末的陈子龙、钱澄之等人都曾指出过“庄”“骚”异中有同,陈氏于《谭子庄骚二学序》中即称“二子固有甚同者。”不仅“皆才高而善怨”,而且“所著之书用心恢奇,逞辞荒诞,其宏逸变幻,亦有相类。”与陈子龙同时且为好友的钱澄之,也将庄骚并论,著有《庄屈合诂》,其旨意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以《离骚》寓其幽忧,而以庄子寓其解脱。”也是出于类似情怀,清代学者龚自珍还写下了“文理孕异梦,秀句镌春心。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的诗章,表达了他对“庄骚”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明清时代某些学者当中出现的这种对“庄骚”的并论,虽然有着时代和个人境遇的原因,但它毕竟触及到了“庄骚”之间所固有的联系,进而引起了后来学者对这种文化现象进行更具学理性的思考和解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刘师培。刘氏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指出:“庄骚”之所以相近、相似,乃是缘于它们同出于“以楚为中心的南方文化系统”。应该说,这种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庄骚”的共性有助于我们从文学的因素上理解庄子的特异之处。但是,哲学家的庄子为什么能够和大诗人屈原并列?被视作“奇书”的《庄子》“奇”在何处?在这个曾经使许多学者大感困惑的问题上,我最服膺诗人兼学者闻一多的一句解《庄子》:“绝妙的诗”。[3](P13)在“大文学史”观中,庄子和屈原有着同样的诗祖地位。其差别只在于:屈原是“诗之哲”,而庄子则是“哲之诗”。
《庄子》不仅体现了哲学与艺术,“道”与“艺”在最高灵境上是相通的,而且它又表明了“思”与“诗”、睿智与情感、审美与认知,在追求普遍性、深刻性、永恒性和富有意义的最深精神层次上,也是相通互融的。
“冷眼热肠”,使庄子一直在哲学与诗中间寻求美和自由的人生,从而使他的哲学洋溢着一种“诗意的光辉”,跳荡着浓郁的诗情。
思想家的“冷眼”,使庄子能够以深邃犀利的目光洞穿了“神圣的丑恶”“绚丽的卑鄙”“热烈的冷酷”“习惯性的伪善”。他发现了“人为物役”的历史悲剧,并勾划出人类困境中一幅令人不安且深思的图像。“热肠”,则使这位哲人喜怒哀乐毕现笔端:庄子谈人生,一则曰“不亦悲乎?”再则曰“可不哀邪”!这种悲悯情怀内涵着远比一般诗人更为丰富、深沉的人生体验和情感。面对人所陷入的困境,他不能不从“诗意的超越”“精神的游放”“个性的逍遥”“审美的生存”这些角度来思考人的价值和意义,他的人生哲学也因之而具有了诗意和诗性。
诗意与诗性,还特别表现在庄子“与天为徒”“天人合一”的哲学中。在庄子看来,“道”的真谛就显现在“天地之美”、自然之美中。世界不仅以其无限的丰富性和深邃性成为美的化身、自由的象征、道的体现,而且,人的生命也化入于自然之浩瀚流衍,达到与自然融通相与的境界。所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庄子,他的生命和精神就在自然山水中徜徉,“钓于濮水”“游于濠梁之上”,在“得乎至美而游乎自乐”中,进入了人与自然默然两契的境界,发出了“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的怡畅之情,把对人生、生命的深深眷恋,借助于对自然的赞美而传递出来,而他对自然的深情呼唤,也得到了自然的深切呼应。你可以看到,畅游于自然的庄子,完全是个“诗人”的庄子。而这个“诗人”的庄子,在他“诗性”的思维中,则把天地万象当成生命的存在,并把自己的生命移植给它们。来源于中国古代神话思维的“天人合一”观念,本是华夏初民以童贞意趣和诗性智慧凝结成的精神生产,而在哲学家的庄子这里,却以《逍遥》《齐物》的独特哲学,将其升华为人本体与自然(宇宙)本体同化为一的哲学思考,表达为富有诗意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名言。庄子与惠施游于濠梁之上的“鱼乐之辩”,庄周梦蝶,“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的情境,都是通过悟性思维,在“以道观物”而接通天人、物我之间内在的或精神渠道的过程中,获得了“与物有宜”“与物为春”的应会感应,这时,摆脱物累的自由心灵就会与浩瀚流衍的自然之道契合。在“吾丧我”的沉思中把握宇宙生命的律动,妙悟自然的底蕴与人生的真谛。正是庄子将人本体与自然本体同化为一的哲学思考和“天地与我为一,而万物与我并生”的悟性思维,在哲学高度上确认了“天人合一”的诗性思维,开启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杜甫)那种睿智深情,人融于物,情蕴于境的诗意。以至后世许多诗人为进入一种思与道合、神与物游的状态,不能不像苏轼所说——“逍遥齐物追庄周”(《送文与可出守陵州》)。
于此,还应提及:“诗人”庄子不仅是语言大师,而且他对语言文字的认识,表现出惊人的穿透力!庄子也许是世界上最先解构事物本相的哲人,他揭开了符号游戏中所隐藏的事物真相,一个“轮扁斫轮”的故事和由此提出的“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命题,不知启发调动了多少诗论家和诗人去探索创造“言外之意”“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意境。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文论诗学著作,都对庄子的上述命题作出了创造性的解读和发挥。
长时期来,治“庄”者曾从哲学和文学的多维角度解读《庄子》,在我看来,《庄子》既显示了文学可能臻抵的哲学深度,又显示了哲学可以采取的文学表现形式。
《庄子》所展示的“大文学”景观,涵盖了由哲学到艺术,由诗学到画论的整个文化领域。如果不了解《庄子》,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什么是中国诗学思维方式,什么是中国艺术精神。在仿效西方的“纯文学”史中,庄子是被“肢解”了的,文史哲的交融是被“割裂”了的。只有在“大文学史”观中,庄子的作用和价值才有可能得到较全面的揭示,它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才会显现出来。
最后再看“文学”经典文本的楚辞。楚辞是早已被文学史家和文化学家共同确认了的“大文学”,而且是“大文学史”中最为瑰玮奇谲、浑莽雄阔的景观。楚辞虽以“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而得名,同时它所带有的神巫气质也显示出鲜明的楚风特色。但是,屈骚的“奇文郁起”,不仅渊源于楚文化,更凭借了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诸多条件,依托了“轴心突破”的高度。所以,以屈骚为代表的楚辞,它并非是地域文化的“专利”,而是与表征“哲学突破”和显示整个华夏民族文化高度的诸子散文,在相同的精神氛围和思想潮流中产生的。与代表周文化的《诗经》相比,楚辞或楚骚是站在“神话时代”和“英雄时代”的冲突与交汇处,因而有着更为纵深的历史继承和更为广阔的文化熔铸:荆楚神话的斑斓色彩,百家争鸣的思想潮流,华夷认同的历史要求,“轴心时代”的精神高度,这些,都在楚辞的诗美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楚辞无疑是根植于楚文化的沃土而绽开的文学奇葩,但是,屈原的出现,却不只使楚辞登上了先秦文学的高峰,而且在由智慧与情感、认知与审美所共同承担和开创的中国文化史上,为楚辞争得了与诸子哲学相媲美、互辉映的地位。正如在“哲学”的《庄子》中我们看到了“艺术的境界”或“诗意的光辉”,在“文学”的楚辞中,特别是屈原的作品里,我们则同样看到了伟大的艺术或诗离不开睿智与哲思,看到了情感的升华总要伴随着智慧的进步。而“诗哲”屈原正是立于“哲学突破”所达到的精神高度,把战国时代由“百家争鸣”在哲学与政治领域建立起来的理性精神,显象于巫术感性形式中,在“惊彩绝艳”的诗篇中,交织着神话幻想、英雄精神、历史意识和哲学思考;在楚文化的情结中表现出对华夏历史文化的深切认同;在“美政”的追求中注入了鲜明的恤民、变法、强国、统一的时代内容。所以,楚辞的“奇文郁起”,屈原之“名垂罔极”,与其说是得益于楚文化的沾溉,毋宁说是依托于“百家争鸣”的精神氛围,而达到了“轴心时代”的高度。具有大时空、大场景、大结构、大气势的巨诗《离骚》与《天问》的横空出世,不仅使屈原成为中国诗史上壁立千仞、俯视百代的“诗哲”,而且也使他得以跻身世界文化名人之列,成为“轴心期”的文化巨人。
卡尔·雅斯贝斯以世界历史的宏观视野审视人类文明和文化进程,发现了这一进程有其整体性的规律:即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约在800年至200年之间,人类精神的基础同时独立地奠定于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今天,人类仍然依托于这些基础”。[4](P69-70)约当春秋战国时代,希腊、印度、中国这三大文化圈几乎同时独立形成,进入了“文化突破期”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以哲学突破为引擎和先导,扩展和辐射到整个文化领域,打破了此前古代文化数千年长期的宁静,使精神领域喧闹沸腾起来,其特点是:一方面产生了激烈的精神冲突和思想分裂,另一方面则通过不断的争论、探索和相互交流,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树立起最高的追求目标。从人类文化的宏观视野来看,战国时代的文化氛围和“百家争鸣”的思想潮流,正是华夏民族在走向融合的过程中伴随制度发生的剧烈变迁,经由自己的历史发展道路,表现出了“轴心时代”的特点。这特点之一是表现在精神的觉醒和思维的跨跃;另一点则是个人才华和个性的充分表现和张扬。开宗立派和“百家争鸣”的诸子哲学鲜明地表现了“轴心时代”的文化气质和精神风采,而屈原与楚骚,同样以其气势恢宏、气象万千、覃思深邃、激情喷涌的巨诗《离骚》和《天问》,显示出开创者呼风啸浪的精神风范和踔厉风发的个性气质。
《离骚》是自传体的巨型政治抒情诗,《天问》是一部具有哲学深度的兴亡史诗。这两部巨诗尽管体制不同,却“情”“理”贯通,神联意会,把现实与历史,人事与天道联系起来,在古今之变的大场景和天人之际的大时空中,展示了诗人精神的广度和深度。波澜壮阔、激情炽烈、想象奇拔的《离骚》表现了诗人对现实、民生、族类、政治的深情关切;而寄思深远、设问百变、穷究天人的《天问》,则以问难的抒情方式,使这种深情关切达到了眺望“历史全景”的广度和仰叩“宇宙微奥”的深度。正是在这里,屈原以其颉颃诸子的诗作,把哲学突破的文化成果全面引入到文学或诗的领域,成为令两汉赋家、唐宋诗人不可比肩的“诗哲”。
《离骚》与《天问》是构成屈原完整精神世界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是诗人情感与理智的互动,是“大文学”景观的生动展示,是时代风采与文化高度的个性体现,是“轴心时代”的艺术珍品。但是,屈原作品及其精神依托“轴心突破”而达到的眺望“历史全景”的广度和仰叩“宇宙微奥”的深度,近年却被某些热衷于“精神分析”的学者误读和曲解了。屈原作品所表现出的那种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被看作与精神疾患有关,一位著名的学者,就在他的楚辞研究中,在有关“大文学”的讨论中,把本来是依情感流动而并非完全按历史逻辑来结构篇章的《天问》,说成是屈原处于神智恍惚时的“时空错乱”,是“精神世界中紊乱状态的一种天才的表现”。[5]这种天才与疯狂并存的观点即便能够找到一些例证,也决不具有普遍意义。因此,以这种观点解读屈原的作品,令我非常怀疑它的科学性和可信性。汉人王逸关于《天问》写作缘于诗人忧心愁悴,徬徨山泽,受到楚国庙宇壁画的启示而作此诗的猜测或许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即便如此,它也不可能是诗人写作《天问》的全部精神动因。诗中错简容或有之,这在古籍辗转流传中本属正常现象,怎可据此臆断它是“精神紊乱”的产品?《天问》整体布局相当完整,结构上先问天地开辟,次问人事兴亡,全诗层次清晰,问题逻辑井然有序,诚如清人蒋骥所评:“首原天地,次纪名物,次追往昔,终以楚先。综其大指,条理秩然。”。[6](P89)珠联璧合的《离骚》与《天问》,不仅是屈原精神世界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也是诗人精神生命和文化生命的有机结合,生命高度和历史高度的统一。《离骚》与《天问》达到的高度是难以简单地从个人才具与独特遭遇上说明白的。屈原在这两部诗中所显示的生命气韵和精神现象,恰恰让我们看到了诗人作为活生生的个体生命和整个民族与时代的文化生命间周流往复的生动联系:喧闹沸腾的“轴心时代”和“百家争鸣”的思想潮流激扬了屈原的精神生命,而“诗哲”又以自己在巨诗《离骚》《天问》中所创造的精神生命,参与并充实了“轴心时代”的文化建构。
总之,先秦时代,特别是在建立了“真正的起点”,具有开创与奠基意义的春秋战国时代,在文史哲的互渗中,以《左传》《庄子》“楚辞”为代表,展示了恢宏瑰丽的“大文学”景观和俯视百代的风采。这种景观和风采不仅对中国大文学史开启了先河,奠定了始基,提供了范式,确立了走向,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大文学传统及其文化特质的认识,而且也将启发当代学者对西方“纯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的再思考:人类文明的出现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年代(包括史前时代),在一定时间和空间高度上形成的先秦大文学景观及其蕴含的深层智慧,作为“轴心期”人类的一份精神遗产,是否具有古今相通、中外共享的世界价值,从而使西方“纯文学”的精审和东方“大文学”的丰厚平分秋色,平等对话,相互交流?面对当代文学不断被边缘化的现状,我们能否从回溯“大文学”的历史中得到某种启示,并在理论探索和文学实践上,在文学与文化的天然联系和它们血肉交生的现象中,更广泛更深入地掘发与实现文学的价值与功能?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延续发展从未间断,其生生不息的源头在先秦,其俯视百代的高峰是建立了“真正起点”的“轴心时代”。通过对于“轴心时代”的历史回溯,可以发现其中某些深刻的、本源性的因素,从而“有助于我们重新点燃心灵的智慧之火,为未来的发展照亮前程”。[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