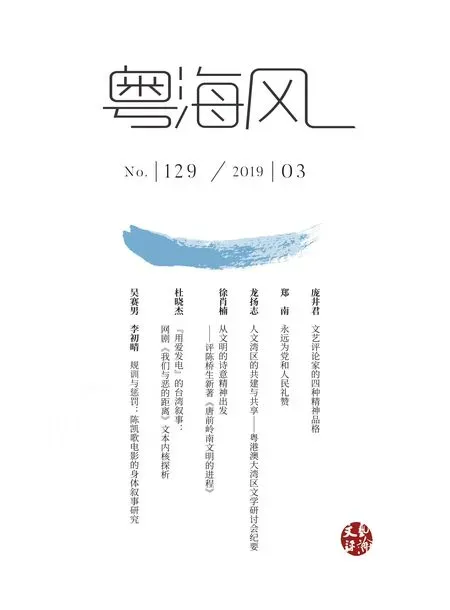穿越时空的奋斗与初心
——评瑞金三部曲之《大笔头》
文/谢珊珊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经历了一个由“共名”到“无名”的时代,90年代以来,“人民伦理大叙事”被“自由伦理个体叙事”代替。之前不被重视的日常生活,小情小爱,个人悲欢,都成了作家们书写的重点,“宏大叙事”中常见的时代主题、英雄情结、民族革命则纷纷成为被解构的对象,个人立场和“私人叙事”的回归使得文学生态更加多元,同时也让文学界弥漫颓废之风。以苏区革命圣地瑞金为背景,以爱国知识分子为主人公,横跨新中国成立后60年历史的《大笔头》在这样的文学生态背景下出版,无疑是一种回归,是革命创作主题的回归,是文学理想的回归,是失落的英雄哲学重新回归,是穿越时空初心的回归。
《大笔头》是继《大匠人》《大脚婆》之后的瑞金三部曲之一。瑞金三部曲描写的是共和国摇篮瑞金20世纪百年三代人的故事。《大匠人》《大脚婆》是以苏区革命史为题材,交织着血与火的苏区革命史,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小说。《大匠人》重点反映的则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21世纪60年的社会生活。《大匠人》通过老苏区瑞金第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辗转于瑞金、武汉、长汀、北京求学发展,历经新中国成立后各种政治运动而成长为国家一代栋梁的历程,向读者呈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编织出富有客家地方文化特色的风情画,刻画了一组个性鲜活的知识分子形象。有以长顺、道生为代表的土生土长赤脚农家子弟,有以小明、先银为代表的红军转移时留下的老区人民用自己的骨肉替换保护存活下来的红军后代和烈士遗孤,有以水芹、正金为代表的本土手工艺术的传承者。他们在成为国家栋梁之才“大笔头”“大匠人”之后,又回归家乡,反哺老区,投身到故乡的建设中去。作品通过三类青年的足迹,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热火朝天、朝气蓬勃的精神和建设场景,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忍辱负重报效祖国的情怀与初心,反映了红军苏维埃政府留给瑞金人民沉淀在瑞金人性格中的精神火种如何绵延不息,传承延续。
一、历史叙述下的文学还原
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认为,历史文献与文学文本一样,具有叙事特性的同时,也具有虚构性。换言之,文学叙述同样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文学通过题材的真实和细节的真实来体现文本所涵盖的历史、社会内容,通过个体命运的跌宕起伏折射历史时代的社会变革。《大笔头》就是在这一意义上实现了其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的统一。
历史是由数据和事实构成,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历史是经过提炼的规律,是没有个性的事实、证据,历史背后的精神,历史背后鲜活的个体生命状况则是文学所关注表现的主体。《大笔头》近50万字的篇幅,作者用近乎历史重现的方式,记录了三类不同知识分子的成长经历,并通过人物的成长足迹展示了老苏区瑞金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个人命运,客观反映大时代的各个历史画卷,以文学的方式对苏区革命圣地瑞金做了历史的还原。小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到2000年结束。这60年,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60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建设、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整风大鸣大放、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文艺“双百”方针的提出到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再到高校恢复招生考试直至确立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的今天,这些重要的历史节点,小说都有涉及。作者以大开大合的文学手法,以时间为主线,以历史事件为经,以人物命运生活为纬,再现真实的社会历史,将人物的命运置于时空变换的大时代、大舞台之下,从题材、人物、内容方面构建了文本的历史性。即使面对将文化问题政治化、将斗争扩大化等历史敏感问题,作者也没有回避,而是通过人物命运的变迁,从侧面加以反映。小说以新中国成立开篇,主人公“长顺不用再躲壮丁了”,历史与个人命运从此发生了密切关联。小说主人谢长顺的人生际遇命运,是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国家急需培养人才时,谢长顺作为优等生被保送进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当国防建设需要俄语翻译时,谢长顺提前毕业进入国务院国家科技事务局工作,并随专家组赴苏联处理翻译科技资料;当政治风云突变,整个科技局翻译处解散下放到东北农村,谢长顺又申请回江西服务家乡;当“文革”席卷全国,谢长顺又被当作白专道路的典型首当其冲受到冲击。随着国家拨乱反正走上高速发展的道路,高校恢复招生考试,谢长顺的人生才开始进入平稳发展干事业的大好季节。小说人物走过的道路,也是作者真实的人生道路,也是那个时代千万知识分子的道路。《大笔头》人物众多,事实繁复,涉及的众多人物和事件都有生活的原型,作品描写的几十个村庄、上百个人物,大多确有其人其村。当熟悉的村庄熟悉的人向你迎面走来时,带给读者的是全新的时空穿越阅读体验。作者用历史叙述的手法,还原历史忠于历史,展示一个真实的感性的历史社会舞台。正如作者所说:“本系列书分三部,一直写到20世纪。所写百年三代,涉及史事地点均属真实有据可稽。”[1]虽然作者强调“我写的不是历史长篇,描绘也不是史诗长卷,充其量只能算做鸿篇巨制的一种补白”。[2]
作者笔下,历史是鲜活的,有温度的。通读整部小说,没有炫目的文学技巧,没有过多的心理描写,也没有意识流的想象,作者基本采用的是文学的对话、场面的描写和不乏细碎的细节来构建整部小说,犹如生活的实录,试图用细细碎碎的生活场景的还原呈现历史的本真。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就在这细细碎碎的生活流的介绍中实现了统一。这是一种介乎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叙事方式。一方面它要符合历史叙事的根本规则:写的必须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而不是凭空虚构;另一方面它又要符合文学叙事的情感体验。它包含了足够的虚构与想象的成分来证明自己是文学而不是历史,同时,它又必须对历史史实抱有充分的尊重,以证明自己是历史题材的文学而不是一般的文学。作者以历史学的专业背景和文学教育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将历史与文学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作者以文学的方式还原历史,让历史鲜活生动起来,历史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发生了关联,一下亲近起来了。
二、经验叙述下的人物细节刻画
作家是现实世界与想象空间的构建者,作家也是个人经验的叙述者,小说的核心就是作家经验的表达。作家创作需要艺术想象,更需要坚实的生活基础与丰富敏感的生活体验,这是作家笔下物质材料和情感精神的生长地,是创作的原动力。恰如鲁迅与乌镇,沈从文与湘西,莫言与高密,高尔基与涅瓦大街。故乡对一个作家不仅具有地理学的意义,更有精神学上的意义,一个作家的经验和处理经验的能力,与他童年、少年、青年的成长经历有密切关系。
瑞金三部曲是作者谢万陆第一部系列长篇小说,是作者对苏区革命史的回顾与思考,是作者毕生经历与经验的回溯与叙说。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作者的故乡瑞金,小说中每一个人物都和作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作品在题材内容和表达方法艺术风格方面,整体呈现的是“经验叙述”,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作者以80多岁的高龄,以小说的形式,以一个跨世纪老人回望故乡的姿态,表达他对故乡过往历史、故乡人、故乡事的情感与体验。故乡是作者创作的原点,自我的生活经历与体验是他创作素材来源的根据地。作者半个多世纪跨越大江南北的生活阅历,一直沉淀深藏在作者内心,创作诉说的欲望一直潜伏在作者深层的内心。当老人以耄耋之年离开故乡迁居深圳,故乡血与火的历史,对故乡精神的牵挂,晚年对自身生活的总结与回望,触发老人拿起笔。他要诉说瑞金血色革命的历史,要为家乡几十万牺牲在红军转战途中的挑夫代言,要为瑞金、长汀一代又一代顽强、浪漫的大匠人、大笔头代言。
《大笔头》基本是以作者生活经历为主线,以个人情感体验为基础,用全视角的叙述方式,跳跃穿梭在不同时代不同场景,和读者讲述着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知识分子命运变迁。作品主要讲述了三类知识分子的成长奋斗历史。第一类是以谢长顺、道生为代表的本土青年,第二类是以小明、先银为代表的红军长征转移后留下的革命后代,第三类是以水芹、正金为代表的研发瑞墨的匠人堂传人。这三类人物,以谢长顺的形象最为丰满,个性特点最鲜明,人物塑造最为成功。作者通过长顺因家贫放弃考取的瑞金中学转而被宁都中师破格录取进而又被学校作为优秀学生推荐进入华中师范大学就读,最后以历史、俄语双专业优秀的成绩提早毕业进入国家机关等情节,刻画了一个忘我求学、刻苦奋发的农家子弟形象,一个率真坦诚面对政治风云隐忍负重的知识分子形象。小说通过大量的人物对话、矛盾冲突、场景介绍、细节描写,拓展作品叙述空间,通过人物的语言、人物行动与行事风格,对人物进行道德评价和心理剖析,将人物置于矛盾选择中去刻画人物的精神世界,是作品的一大亮点。例如当来自苏联的科技情报资料断流,编译处也随即撤销。面对变故,科技委编译处所有的同志都按兵不动静观变化,唯独长顺主动要求回赣南劳动锻炼,成为编译处第一个离开中央机关的人,而且再也没能回去。一个政治上单纯、个性率真顾念家乡与亲情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跃然纸上。再例如红军转移时留下的银元瑞金人民用生命保护,新中国成立后一分不少还给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运输救命粮的车队途经瑞金,虽然因故障而滞留,沿途频发的偷甚至抢粮的事件在瑞金却没有发生一起。类似的情节、细节非常多,这类带着浓重的瑞金地域色彩,有着鲜明的个人体验与经验,完全是瑞金经验的叙述。作者在这些人物身上,倾注了太多的情感色彩,以至于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似乎能听到作者与人物的对话、交流,一起欢笑,一起流泪,整部小说的创作,都沉浸在作者的个体经验中,这是小说的优点,也是小说的缺点。它给作品带来冗长有时拖沓的缺点。
《大笔头》不仅时间跨度大,人物活动空间范围也非常广。从瑞金黄柏山村的田野乡村生活到高校浪漫温情的校园、再到诡谲多变的政界风云,不同时空环境下的不同场景,都显得特别真实,富有地域特色。其中最吸引人的还是大量富有客家风情的细节与场景描写。细节是小说情节的最小单位,是小说作品中对于人物的性格、肖像、语言、行动,事件的发生、发展,周围环境和自然风景的具体描写。逼真细腻的细节描写,可以增强小说的生动性和真实感,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主题的表达,让小说的人物一下鲜活起来了。比如当谢长顺报考瑞金一中看榜时从最后一名往上翻找自己的名字而不同常人从前往后看,非常真实、准确地写出了一个孩子面对放榜时的复杂心情。当小说主人公谢长顺从宁都师范保送到华中师范大学即将离家赴武汉读书时,父亲照彬默默地进山采摘野果子给远行的儿子路上充饥时,我想天下儿女都会为之动容。这是一个赤贫父亲唯一能想到的为儿子做的。谢长顺上大学后,天天打赤脚,不舍得穿老师送的仅有的一双球鞋。当照彬奶奶90大寿时,面对满桌的珍馐佳肴唯一的评价就是“蛮有盐味”。这些细节与人物的身份经历高度贴合,一句话、一个行动就让人物活起来了。虽然有些语言、有的场景显得太实,不美,少了一些艺术的想象空间,但是还原到那个时代,它是真实的可信的。
三、时空变换下的奋斗与穿越历史的初心
作为瑞金的第三代传人,今天来读这部小说,回看故乡人、故乡事,感触良多。首先,深深感动于瑞金人民对共产党朴实的情感,跟着共产党走的坚定信念,共产党必定能决胜全局的信心。战争年代,苏区瑞金的老一辈为中国革命胜利默默付出。男子做挑夫,为红军挑担送物资几经辗转突围,几百万的挑夫牺牲在挑担送红军的路途上。女人在家打草鞋,做斗笠,纺纱织布提供后勤保障。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历史上默默的无名英雄,是革命成功的基石。在我眼里,纯净坚定,一往无前就是瑞金人的初心,重信守诺,为共产党的事业奉献,也是瑞金人、老区人民的初心。所谓初心,就是赤子之心,是不带任何杂念的信念。古语有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纯洁、热烈、美好,是人生起点的希冀与梦想,事业开端的承诺与信念,迷途困挫中的责任与担当,铅华尽染时的恪守与坚持。
《大笔头》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初心。苏区干部梅青的初心是将红军突围时交给她保管的苏维埃政府毛泽民亲手抄写的钞票准印证“准证书”保护好,交还给中央,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番薯牯谢长顺的初心是刻苦读书,抓住一切机会,回报姆妈,不给瑞金人丢脸。红军撤退时留在瑞金的后代小明的初心是不忘老区人民的养育之恩。当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父母回到瑞金将他带进京城时,他只身回到养育他的亲人身边,而且一留就是一辈子,用知识为瑞金人民服务,奉献了一辈子。匠人堂的后代传人运性的初心是创作比全国金奖作品“客家女”更好的作品,为红军做塑像“期待”,为匠人堂留下传世精品;移居台湾的瑞金传人运挺的初心是守望家乡,回归家乡……《大笔头》中每一个人的初心都是那样简单朴素,它就像一颗种子,支撑着人物长成苍天大树。正如作品所说,“人人都在期待,老师在期待学生成长,自己在期待未来……梅青在期待,凤莲在期待,翠玉在期待,自己也在期待中走到了今天”。[3]
其次,感动于父辈第二代人对家乡的拳拳之心,感动于家乡人对诺言的坚守。作者和小说主人公谢长顺一样,少年十几岁就离家求学,赤着脚,从瑞金走到宁都师范,又从宁都师范走到华中师范大学,再从华中师大走到了首都北京,进入国家高级机关。人生在这个赤脚少年坚实的步伐下,坚定、坚实,一路昂扬向前,不可阻挡。引人关注的是在这个苏区农家子弟身上,丝毫看不到贫困带来的卑微、面对困难的放弃,看不到名利场争斗练就的狡诈,看不到世事纷争的复杂,看不到人生跌宕的消沉……我想这就是老区瑞金人身上共有的进取奋发,老区人民特有的执着率真,老区人共有的真性情,这是革命老区血与火孕育的性格。这个人物身上有作者自己的影子,作者对他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小说中一直流淌的是不屈的奋斗,蓬勃生机。世界不断地在变,主人公的人生际遇生命轨迹也在变,政治风云的迭起,从宁都师范到武汉华中师大再到北京国务院科技局转而莫斯科……不变的是作者对家乡的回望与牵挂,对国家的忠诚与奉献。《大笔头》是瑞金三部曲的杀青之作。广东省委宣传部将瑞金三部曲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之作,就是对作者穿越时空的奋斗的肯定,对瑞金人民的初心的肯定。在这个时代,初心常常被我们遗忘,“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孔子说:“居之不倦,行之以忠。”当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抛开一切世俗的附加,我们所坚守的信念和本心,是最为宝贵的,它存在向善、向美、向真的追求当中。
一部小说记录了一个时代,一个人物祭奠了作者奋斗的一生。这就是作家创作的原点与归宿。《大笔头》出版于一个文学的阅读价值和社会价值、内化价值都受到严重挑战的时代,出版在文学历经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这种“递进式”的文学革命之后,出现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归于平淡、私人化、边缘化之后。当下的文坛,充斥的是私人写作、闺蜜写作,到处是眼花缭乱的商界争斗风云和情场的声色多彩。在市场化写作的背景下,瑞金三部曲的出现,显得特别孤独寂寞。从题材角度看,瑞金三部曲填补了苏区题材作品的空白,从历史角度讲,也是对瑞金苏区老百姓在历史上的贡献给以承认与肯定。《大笔头》瑞金三部曲的创作出版,就是为苏区瑞金革命史保留了历史中最生动、最有血肉的部分,填补了革命史中后革命时代的空白。
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就说过:“接触文学,接触世界文学,不啻是逃出民族虚荣心的监狱、市侩的监狱、强迫性的地方主义的监狱、愚蠢的学校教育的监狱、不完美的命运和坏运气的监狱。文学是进入一种更广大的生活的护照,也即进入自由地带的护照。”[4]文学是自由的,同时文学也是有责任担当的,应该发挥培根铸魂的引领作用。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发出的火光,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面对当下转型社会,社会复杂多元,人们价值观念分化,出版作品媚俗低级,阅读的价值和内向的价值都受到严重挑战的时代,文学更是民族精神的引领与烛照。《大笔头》的出版恰似一股清流,献给为共和国做出牺牲的瑞金人民,献给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注释
[1]谢万陆:《大笔头》,花城出版社,2019年3月,前言7页。
[2]谢万陆:《大笔头》,花城出版社,2019年3月,前言6页。
[3]谢万陆:《大笔头》,花城出版社,2019年3月,048页。
[4][美]苏珊·桑塔格:《同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