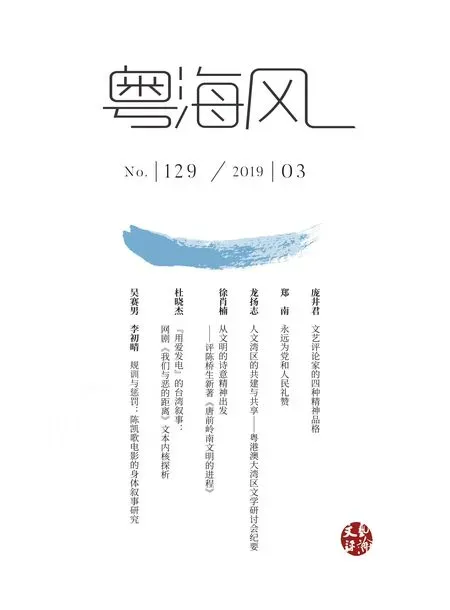惟能诚于人,方能诚于文:王干散文欣赏
文/刘根勤
王干,昔日的干兄,如今的干老,嘱我为其散文作评论。
当真是荣于华衮,然而也绞尽脑汁。
这标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浓浓的古龙味道。
原话是西门吹雪说的:“唯有诚心正义,才能到达剑术的巅峰。”
西门吹雪,是古龙笔下的剑神。他的话,就是古龙的话。
这是古龙理解的剑道,浓郁的中国风。
西门吹雪说话的对象,是叶孤城。这是当时两大绝顶高手。他们是生死决战的主角,同时也是相互尊敬的对手。
这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高冷,孤傲,像冰山一样。
但西门吹雪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叶孤城信任的人,就是陆小凤。
陆小凤不冷,很热情,性格轻松幽默,有他的地方就有笑声,武林中有名的人物,都喜欢与信任他。
热情难得,真诚更难得。
陆小凤能与西门吹雪交朋友,又能得到叶孤城的信任,他的本性,自然是真诚的。
同时,他的武功也是天下绝顶。
孔子说了:“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一个人,如果受人爱戴,他一定具备基本乃至高超的才能。
天下虽大,道理一样。
环顾当世,王干,堪称文坛的陆小凤。
陆小凤的特点,古龙迷无人不知,他的机智、武功、酒量、脸皮之厚和好色出类拔萃。他生性风流,好管闲事,喜欢喝酒,欣赏美女,更重情义。
熟悉王干的人都知道,这些特点,或者说优点,几乎就是王干的鲜活印象:精力充沛,宣泄出来,表现就是极端的好奇,好学,好玩,斐然成家,自得其乐,推己及人,助人为乐,成人之美。
可以说,除了传说中的“四条眉毛”之外,陆小凤的特质,王干同时具备。
当年王朔戏谑的“文坛奔走相告委员会主席”,固然是对王干的善意形容,又何尝不是陆小凤在古龙世界的真实形象?
不恨王干不见古龙,只恨古龙不见王干,不然当浮一大白。
7月份,我收到王干惠赠的文集,煌煌11册之巨。
满满的感佩。
所感动者,我认识王干,是在1999年,不经意间,20年了。
当时我作为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却有着浓郁的文学情结,经常跑到江苏作协去跟一批师友聊天喝酒。那时别说微信,连手机都没有,某天我经过创作室时,看到一位满脸笑容的中年人,面前放着“王干”的字牌,主动进去攀谈,结果一见如故。
王干大名,如雷贯耳。
说是中年人,当时他满打满算虚岁四十。便是到今天,他脸上还是容光焕发。
我老记得一段掌故:铁木真14岁时,父亲遇害,他流浪草原,4年间结识了许多英雄豪杰。其中一位老首领将自己的女儿孛儿帖嫁给了他,原因是:这孩子脸上有光,眼中有神。
王干出名,那是不可思议的早。
1980年前后,他已经是江苏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与评论家。后来他跟文坛大佬王蒙的传奇对话,奠定了他在文坛的资历与地位。
“二王”对话,是里程碑式的,不过那主要用于对普通读者的介绍。
我个人对王干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汪曾祺,熟悉的人,都叫“汪老”。
可以说,汪老与王干,绝对的“情同父子”。
王干从来没有这么说,但从他的文字中,这种评价绝非过誉。
汪老是性情中人,王干也是。
更重要的,他们都是里下河地区人氏。
这里文风鼎盛,乡情浓郁。
我很荣幸,跟两代文豪毗邻。我多次在媒体与课堂上说,20世纪的中国作家,能够接续中国传统的,或者与国学有关的,只有汪老与金庸,汪老隐居京华,金庸沉潜香江,南北双绝。
2000年初,我在南京听过金庸讲座,大侠才名冠世,但我深感难以沟通。那时汪老已经过世三年,每次抚读其文,想见其为人,可惜无缘拜见。
但是结识了王干,这位汪老的嫡派传人,也不枉了。
汪老当年有篇怀念业师沈从文的文章,标题是《星斗其人,赤子其人》,我觉得这个标题,用来形容王干的人与文,准确不过。不过汪老珠玉在前,我只好另起炉灶。
20年间,我和王干联系不多,但心照不宣,见面就是大酒,然后就是大作相赠。
所佩者,20年后,王干威名与日俱增,创造力更是一骑绝尘。
文坛对王干的评价,大体上几句话:说不尽,难以归类。
文学之内,他是作家,写散文,写小说。
他是大名鼎鼎的评论家。改革开放40年,他与中国文学一起成长,是记录者,更是参与者与推动者。
他还是享有盛誉的编辑,一代名编,策划无数大型活动,推出无数经典作品。
他是青年作家的导师,优秀作家的知心朋友,还是里下河地区文学青年的偶像,是汪老大纛的接力者。
文学之外,他是个高级玩家。酒量大、酒风好,他的烹饪也是一绝,藉此会遍各界英豪。他的书法有底蕴,足球篮球都好,围棋也不错。当然这是我的看法。赵本夫说,王干的围棋一般,但与那些围棋国手比如常昊、罗洗河等人的对话,非常专业。
如此旺盛的精力与创造力,已属罕见。他居然40年如一日,不能不说是奇迹。
11册文集,洋洋洒洒,叹为观止。
最好玩的还是当他的面跟别人说起他的名字,每次都说:王干,本名,非笔名。
当年的干兄,现在的干老,容颜依旧,但受人尊敬与亲爱,却是与日俱增。
关于王干的记忆与观感,满满的都是温情与热情。
文人相轻,在王干这里,是绝对不存在的。
王干身上,丝毫没有新式文人的拘谨与清高,有的是满满的烟火气。
文学于他,就如朋友,或者如一日三餐,不可须臾或缺。
又如苏东坡作文,王阳明静坐,不得不为,乐在其中。
此所谓良知与初心,正心诚意的典范。
但凡有血气之人,见之无不感兴,佩服。
王干跨界极广,这里重点介绍他的散文。
《王干文集》中,有单列的《王干随笔集》,也有散布于其他分册中的各种美文,还有特别具有王干个人标记的博客文章。
这些文章,绝大多数发表于专业报刊,许多甚至是国家级的学术与舆论平台,也有不少没有发表的,但王干个人觉得珍而宝之,不吝与文坛内外的朋友们分享。
其实,正如王干本人的“难于归类”一样,他的文章也是如此。
众所周知,王干在公众场合,算是不善言辞的。多年前,他在南京大学举办过一次讲座,我的老师钱乘旦教授主持的,他讲金庸与王朔的那段小纠纷,语速很慢,笨拙而真诚,看得出他对南大师生的尊敬。
但王干在单独沟通时,却能做到逻辑清晰,节奏稳定。当时有一位我们同级的研究生“质问”他为什么当代文坛没有大师。王干极有礼貌地说,大师并非当代就能评定的,他认识文坛上许多创作者,极有潜力,但是需要时间,他们需要时间来进步,读者也需要时间来了解他们。提问者十分满意。
讲座毕竟是社会性的场合。或者并非王干所长。
王干的强项,是作家与学者的专有空间,是朋友们的酒席,是案牍与键盘。
不管写论文还是散文,王干都是倚马千言立等可取。真如苏东坡所说的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
其他不说,只要统计一下他40年来的写作数量,绝对在千万字以上。而且高质量的写作很多。研究王蒙、汪老如此,研究莫言如此,研究铁凝、王安忆、池莉乃至后来的中生代、新生代作家,都能切中肯綮,深得理论界、评论界与创作界的共同认可。
如果按照现代的学术规范以及量化标准,王干的文学评论不一定能符合学院派学者的要求,原因就在于他的个人印记太浓。
王干的论文,带有很强的诗性特征。他研究文学,他的研究,其实也是一种创作。
研究界的风尚,是文章要不带烟火气,超凡脱俗,四平八稳,不偏不倚。这是说的好听,说的不好听,就是没有人味。科学研究或许可以如此,人文领域的观察,恰恰最需要有温度的作品。早有人说了,研究者或者评论家自己不会写好看的文章,拿什么来研究与评论别人的文章?
大多数时候,文化界总是被学术八股把持,这是无奈的现实。
王干的出现,对主流的行文,几乎是一种灾难,或者说泥石流。但对作家,对读者,却是不折不扣的清流。
王干的出现,是文坛与研究界的幸运。
以他的才情与阅历来写散文,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
王干的故乡是兴化陈堡小镇,位于里下河腹地。这片1.4万平方公里的平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地处江淮之间,水网纵横,水灾密集,战火频仍,生活艰难,这里的人民却灵性漫漶,不择地而出,无往而不利。
传说中“江北出高僧”,汪老佛性很重,这个热爱生活的老头儿,写得出晶莹剔透的《受戒》。早他两百年的郑板桥,脾气很倔,但举手投足都是才气,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便收藏了许多他的作品。
相比这些前辈,王干同样才气充沛,他更多了几分入世的欢愉,他的单纯与活力,让人忘却了他是一个文人。
然而他的确是一个文人,一个好玩、会玩更善待别人的文人。
《王干随笔选集》精选了王干的随笔50余篇。
我们挑选其中的一些篇目来分析。
《向鲁迅学习爱》《老舍与说话》《汪曾祺与生活》《王蒙的N个春天》,这几篇无疑要单列,尤其是后两篇,充分体现了他对前辈的敬意。这两人许他以忘年交,是他在文坛的伯乐。而这两位大佬对文学与文学家的责任心与热情,也在他身上得以延续。
汪老的小说好,散文更好,我最喜欢看他谈吃的作品。那种轻松写意,深得明清小品的精髓。王干得其三味。这对老少爷们可谓淮扬美食纵横京城的双璧。
如前所述,王干是玩家。随笔中谈玩或者说文体综艺的,琳琅满目,蔚然大宗。这里只列举几篇,《论麻将的无限可操性》《闲读围棋》《围棋的极限与境界——与常昊对话》《足球颂》《说谱》《伟大的嗓门报国无门》《武侠、灌水与大话》《贝哥哥的发型和县委书记的帽子》。
王干身材不高,显壮硕,足球踢得不错,听说篮球也是可圈可点,带球突破三步上篮拿得出手。人人以为他好动,没想到他动如脱兔,也能静如处子。奋笔疾书就不说了,坐下来打谱或者挥毫也都煞有介事。
还是那句话,至情至性的人,做什么像什么。
特别有意思的是,王干对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评价极高,他认为,金庸小说与四大古典名著相提并论毫不逊色。金庸去年刚去世,我不知道他之前跟王干是否熟识,有没有听到这些评价。他如果在天有灵,当为有这位知己而欣慰。
王干是顶级的文学评论家,也是优秀的社会与文化观察者。
都说评论家其实是表扬与赞美家,王干证明了真实批评的存在。他的两篇随笔,严厉批评张艺谋的审美水准,说他是“审美吸血鬼”。
他对许多文化现象与事件,不但关注,而且持续关注。他写了四篇文章谈简化字,《五十年内,废除简化字如何》《简化字是资源匮乏年代的产物》《简化字是盛世中国脸上的一颗痣 ——再说五十年内废除简化字》《简化字是“山寨版”汉字——与王立群先生商榷》。从这些标题就可以看出,他的态度严肃且专业,他指出简化字属于“权宜之计”,但难以持久。他提出“废除”的建议,但又不是一蹴而就,要从长计议。这都体现了他的责任心与专业性。
这些文章,冠以“随笔”与“散文”的名义,其实比大部分高头讲章与官样文章都更有内涵,也更有可行性。
这些文章,有两大特点:一是信息量大,从文学到文化,从专业到社会,从历史到当下,可以说是百年中国精神的全景扫描;一是性情充沛,作者的真诚、热情与深刻,汩汩而出。
提到散文,不能不写自己。王干的魅力,在于真实而鲜活。
汪老,与他笔下的苏北、云南与北京,是20世纪中国文坛的绝美风景。
王干比汪老小了四十岁。他所处的时代,更恢弘,更精微,更热烈。
因为时代的进步,尤其是交通与通讯的进步,王干的视野,比前辈更宽广。
所以他写生活,写故乡,写居住与游历过的城市,可谓最好的人文纪录。
他写魂牵梦萦的故乡泰州,写念兹在兹的江南古城,写高屋建瓴的大国首都,都别有风味。
《泰州是谁的故乡》《泰州有条凤城河》《关于泰州美食的记忆》《个园假山》《江南三鲜》《明前荼、雨前茶与青春毒药》《闲话南京》《北京的春(夏秋冬)》《在怀柔观山》《小二、点五、涮羊肉》《男人居住北京的十一条理由》《如何进入重庆》 《过桥米线和菜泡饭》。
这些文章,光看标题就知道内容。但是真看进去,欲罢不能。因为王干的观察与体验能力,的确不同寻常。
他说男人居住北京的十一条理由,颇有可观之处,关键是结尾来了一句,北京有我。令人忍俊不禁。
的确如此,“我”是世界的中心,“我”要不在北京了,北京再好,也只是回忆,而不是鲜活的“这一个”。
令我感佩的是,王干笔下的故乡,如同母亲的体温,如同启蒙老师的声音,如同初恋情人的眼神,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起点,也将是归宿。
百年来,文人对故乡,几乎是一边倒的“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现在的网络上,每到过年,都是一批学者文人如此。似乎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孤高与冷傲。他们仿佛寓言故事中的某种人,总想提着自己的头发,让自己离开大地。
王干不然,他才名早著,游遍四海,从京城到老家,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他无不倾心结纳。
不是王干没有遇到挫折,恰恰相反,他遇到的挫折并不少。他在一篇自传体小说中,提到在老家乡镇中学从教时遇到的黑暗经历,义愤填膺。
但正如一滴墨水污染不了江河湖海。王干笔下的故乡,有情有义,活色生香,流光溢彩。
泰州市委书记韩立明女士写了《泰州的海》,王干为之呼应,写了《泰州的河》。两篇文章,写出了泰州人灵魂中的诗意、灵性与豪情,可谓闻弦歌而知雅意。
这篇文章发表在《泰州日报》上,国家级的《新华文摘》闻风而来,收录了这篇文章。
王干对家乡的深情,获得了充分的认可。
这一点,他像极了苏东坡:上可交玉皇大帝,下可交卑田院乞儿,眼见得世上无一个不是好人。
王干的散文好看,王干本人更好看。
还是那句话:惟能诚于人,方能诚于文。
最真的人,最诚的文。
期待王干创作生命长青,成为“干”,也就是实践,行动,创作的王。
如此,文坛幸甚,故里幸甚,青年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