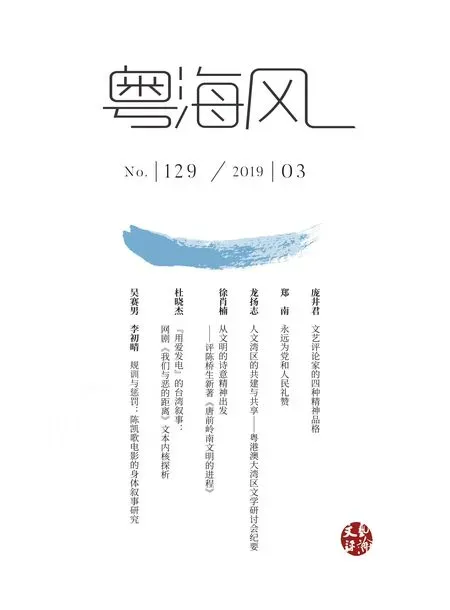当我们谈论“珠海文学”
文/郭海军 谢镇泽
一
多年来,文学创作已经安然受制于固化的文学权力秩序,由此形成期刊发表、评论裁定、评奖表彰三位一体的文学评价体系。基于这样的权力秩序和评价体系,衡量某一区域性文学创作的成果与水平,可以很容易通过相关指标得出一个量化的结论,比如本地有多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得了哪些级别的奖励等。据此,近40年来的“珠海文学”,或已成为业绩不俗的边缘性写作共同体。
所谓“边缘性”,是指远离国家行政中心区域(首都)的地域性特征,也意味着和文学中心区域的创作景况既呼应追随又独具特性的写作状态。“写作共同体”则可理解为在相对固定的地理空间内,为一个大致趋同的精神目标或基本一致的题材对象而写作的特定人群。当我们谈论“珠海文学”时,就是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谈论属于珠海市行政区域内的文学创作情状。这就与我们谈论“深圳文学”“广州文学”相同,在命名逻辑上没有区别。这样命名的最大作用,在于比较容易让人更多关注作品发表的数量和作品获奖的等级,如同关注本地区有多少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彰显的是数字化的实力。故此,“珠海文学”一类的区域性文学命名,必然会高频率地出现在新闻媒体和地方领导的讲话稿里。
然而,到底什么是“珠海文学”?或者,能不能确立“珠海文学”这样的命名?如果说“珠海文学”即“珠海作家写珠海的文学”,也许会引发专家学者们的学术性争辩,但却大体符合文学受众的认知常识。因为只有写作主体与写作客体构成直接认知和理解的熟稔联系,才能更好地反映珠海这座城市的人文蕴涵与现实面貌。可是,“珠海作家”这样的区域性命名,是“有珠海户籍的作家”的专称,还是也包括“没有珠海户籍却居住在珠海的作家”,恐怕一时难有定论。再从表达对象的层面考查,虽然文学作品不应该是历史年表,但珠海撤县建市40年来的发展历史,并未在既有“珠海文学”的具体文本中显露出清晰的艺术面影。甚至于在“珠海作家”的笔下,地名“珠海”两个字都极少出现。“珠海”成为作品人物具体活动空间或感应对象的文学书写,近年来似乎只出现在陈继明的长篇小说《七步镇》和中篇小说《留诗路》中。由此而来让人窘迫的事实,就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珠海作家”的作品,可以像邓友梅写北平、冯骥才写天津、王安忆和金宇澄写上海那样来写珠海的城市形象。即使与珠海同时撤县建市的深圳,在其城市文学映象的表达上,也有邓一光、薛忆沩、吴君等多人及两代“打工作家”的写作实绩。“珠海作家”却大抵身在珠海,心在天边。或者说,是写作者生活、工作在珠海,笔端所及都是别处故事。
所以,从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和各类传媒上下默契地希望地方文化繁荣的思路来看,“珠海文学”这样的区域性文学命名,无论数量规模还是主题意涵乃至艺术容量,都还不能构筑起众所期许的特区城市珠海的文学成就与意识形态功效。也即到目前,“珠海文学”依然近乎一种标语口号式的宣传标签。如此断论绝非个人草率意气之语,内里有着历史、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缘由。
二
一座城市作为户籍地或居住地,能否成为作家有感且有效的写作题材与故事资源,与这座城市的人文发展、历史厚度和体量规模密切相关。不管学者们怎样努力钩沉历史以锻造城市的文化内涵,人们看待珠海如看深圳一样,都是从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特区”开始予以定位。换言之,自1980年深圳和珠海先后被国家设置为经济特区起,两座城市的发展就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进程同步。虽然只有40年的历史,但这两座城市却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前沿和窗口。可时至今日,深圳与珠海在人口规模、地区生产总值等方面,已不是一个量级。若从文学角度衡之,“文学深圳”与“文学珠海”也有显明不同。相比深圳,珠海的文学话题不多,没有“打工文学”“底层写作”之于深圳的空前盛况。紧随时代脉动而发声,让深圳的文学在过去30多年里风头矫健。而珠海的文学书写,疏离于文坛热点的边缘特征却愈发强化。这种状态的另一面,则是边缘化具有的少约束和自由感,滋长了珠海文学书写的前卫性特征。不同于大多数深圳作家对社会现实与现代城市发展过程的写实性描述,珠海作家更喜欢聚力于表达关涉人类命运和个体生命的既宏大又幽微的主题内容,在艺术品质和写作技术上也更具先锋色彩。由此,决定了珠海文学书写中少有珠海城市形象的事实。
以小说创作为例:1998年,珠海作家曾维浩笔耕8年的长篇小说《弑父》面世。作者以丰沛恣肆的想象和繁复多变的结构,采用寓言和象征的体式宏观地写出了人类文明的尴尬困境。作品主题涵盖了人类生存的不同境遇,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诸多学科要面对的共同课题。10年后曾维浩的另一部长篇《离骚》,则把笔触伸向具体人物的内在情感世界。吴天成对王一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倾心爱恋,穿过了50多年的历史尘烟,具体生动地展示出人性的丰饶和温润。作者在《离骚》中表现的是对人类生存处境的持续一贯的关注,但却一改《弑父》处处隐喻象征的表现手法和否定性的主题指向,开始坚实地站在现实的地面,以民族化的立场和形式真切肯定。再如陈继明的长篇小说《七步镇》,主人公东声试图通过“寻找自我”来治疗回忆症这一精神疾患。在小说里,作家东声“寻找”自我的曲折脚迹,已经在现代和传统、个体和社会、“我”和自我的既阔大多维也具象幽微的时空中,绘制出一种让读者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精神图谱。这图谱既属于东声个人,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小说创制,还有韦驰的“存在三部曲”(《无冕之王》《矛盾症漫记》《对另一种存在的烦恼》),维阿的《不可能有蝴蝶》……
因而从整体上看,创作视野宽阔高远,文学风采姿态多变,不拘泥于时代和现实的既有境况,专注于个体化的艺术思考与探索,似乎已成为珠海作家的共通属性和不约而同的美学追求。进而,也构成了珠海作家文学书写的独特质地。晚近30年,珠海作家的写作空间宽阔而不逼仄,写作姿态优渥而不慌张,写作体式工致而不粗放。一言蔽之,特区珠海的文学书写散淡、从容,也精雅。
三
当我们谈论“珠海文学”时,我们无法避开两个重要年份——1980年和1992年。前者对于珠海自不待言,后者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和繁荣都极为重要。
1992年,邓小平在的“南方谈话”中,充分肯定了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探索性发展和示范性效应。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决定正式建立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正式转型,标志着有史以来中国社会由传统农业文明迈向现代工业文明的重大基础性转变。1992年春节后,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剧《外来妹》,把“农民工”群体在广东城市里的“打工状态”展示给全国观众,引起极大反响。也是这一年,另一部电视喜剧《编辑部的故事》,通过《人间指南》杂志的六个编辑与社会的多维接触,于更大范围显露出正在悄然变革的中国社会现实景象。这种变革的时代背景,就是片头曲唱出的“告诉你一个发现,你和我都会感动。世界很小,是个家庭”。20多年前的中国人能不能对此“感动”很值得怀疑,但世界是个家庭的确属于“一个发现”,说明中国人真正的“世界意识”或“人类意识”正在成型,尽管成型的过程痛苦而艰辛。
概括而言,出现在1992年的这四件事,含蕴着彼时一个意义丰富的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以及从国家最高管理层政治决策到普通百姓具体生存之间的因果逻辑。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经过十几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悉心探索,到1992年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格局,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基于这样的发展现实,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运动正从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发端。其中,渐变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开始由特区向沿海其他城市和广大内地扩散,并逐步构建起传统中国人新的意识形态。因而在1992年,怎样于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的转型中寻找、确定个人的生存位置和生活目标,就成为电视剧《外来妹》最主要的题旨,也形成现实中千百万“外来妹”的人生窘境。在社会的巨大变化面前,珠海作家在精神和情感层面实际上也是另一类“外来妹”,因为他们与绝大多数深圳作家一样,大都属于特区城市的“外来”移民。
以特区城市深圳、珠海等为目的地的国内大规模移民潮,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数以千万计的移民实由两类人群构成:一种是较早移居特区的“精英”群体,包括政府公务员、媒体从业者、教师、大学应届毕业生、国有企业干部、转业军人、“下海”经商者等;另一种是“打工”群体,主要是来自中西部和广东本省的“农民工”。不论哪一类移民,其“闯广东”的最直接动力,是相信凭个人能力可以得到更多更好的经济回报和更舒展更自由的自我发展机遇。“闯”既是个人行为也是群体动作,凝聚着关乎个体生存和个人命运的多种希冀与憧憬。另一方面,随着特区城市的成型和发展,一种新的现代城市文化渐渐凸显出来,形成迥别于中国传统城市的观念场域和生存空间。随之而来的人与环境彼此促进并深度融合的过程,既形成特区城市的人文发展历史,也催生了一种新的城市文化生态。
在文学上,两类移民尤其是“打工”群体,不但使深圳成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移民城市,也让深圳的文学书写因“打工文学”而声名远播。同属移民城市的珠海特区,被定义为“打工者写,写打工者”[1]的“打工文学”发声却很微弱,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以此比较,深圳的文学书写更多专注于描述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通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并以“打工文学”“底层写作”“城市文学”的递进性文学表达,刻画出当代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的现代工业城市的精神成长史。而珠海的文学书写,“精英”群体中的移民作家则成为主角。他们在感受现代都市生存观念变化的同时,也深切体会到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给传统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节奏带来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摇撼和心理落差,进而促使他们对现代城市文明作出深刻思考与自觉反省。例如陈继明、曾维浩、王海玲、裴蓓、李逊的小说,卢卫平、唐不遇的诗歌,耿立的散文,李更的随笔等众多作品,其主题指向都关涉到这样的思考与反省。
四
进一步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精英”移民作家为主体的珠海文学书写,就已经显露出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一种新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品质。包孕这种内涵与品质的各类文学体式,正在由“城市文学”发展为“新市民文学”。这样定位的现实理据,主要源自两个方面:
一是珠海作家主体写作意识的超前性。随着工业化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和渐趋完成,移居经济特区的新移民经历了近40年的心理与情感的蜕变,与也在转变中的原住民在新的现代城市文明空间里融合,形成发端于深圳、珠海等特区城市,进而扩展到广东其他城市乃至全中国的新市民阶层。这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城市社会阶层,也将成为建立在物质和知识、制度现代化基础上的文化现代化[2]的最直接表征,也即“人的现代化”。从新移民到新市民的成长过程,几近同步性地反映在深圳文学书写的各类文本中,具体表现为“打工文学”“底层写作”“城市文学”(新都市文学[3])到“新市民文学”的阶段性形态演进。与深圳作家扣紧现实发展脉搏的文学发声相比,同期的珠海作家则直接站在现代城市的立场上,以新市民的写作姿态冷静地审视时代,从人类生存的更广阔视界思考和描述“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的人性人情。
例如,移居珠海的王海玲以1995年的中篇小说《东扑西扑》为起点,在工业化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上,开始描写移民特区的年轻知识女性苦苦找寻自我精神定位的心路历程。直到2008年的中篇小说《无法闪避》,王海玲的小说在人物形象和主题意蕴上不断延伸并互为补充,形成特区知识女性移民的形象系列,进而构成了一种整体上的文学表达。虽然写的是知识女性这个特区移民群体所遭遇的生存之痛和精神迷失,但作者并未倾力于传统伦理观念上的谴责与批判,相反却表现出更多的宽容与理解。甚而至于对人物的人生选择和行动,都在不自觉中流露出一定程度的欣赏态度。以艺术的方式探寻社会转型期内生活既有的诸多可能性,以及这些可能性的边界,这种基于人生实相客观冷静进行表达的主体写作意识,显然超前于发生在深圳的“打工文学”及“底层写作”。
二是珠海文学书写主题表达的跨越性。起源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国内移民文学,因其与社会转型实验的同步,呈现出较为完整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纪实特征。换言之,早期的“打工文学”演变为“底层写作”,无非是转型之初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转型阵痛阶段,普通人包括“打工”群体生存境遇、心理状态与情感世界的形象再现。二者的区别在于,人物书写从特区城市的“农民工”扩大到农民、工人和普通劳动者,叙事空间则从深圳一城拓展到全国其他城市。可见,对“血汗工厂”的愤怒控诉、对资本巧取豪夺的泣血揭批,成为“打工文学”到“底层写作”的重要主题意涵。然而,珠海文学书写的主题表达甫一面世,就越过了“打工”和“底层”的揭露、谴责与批判,站在了“城市文学”的写作起点上。即珠海作家多从人类生存的大坐标出发,以现代城市新市民的视角,摹写新移民从传统乡土进入现代城市的心理悸动和曲折精神路径,以及现代城市市民的多维生活状态。就像卢卫平的《我拿着一把镰刀走进工地》:
秋天了,金黄的谷物/像一个掌握了真理的思想者/向大地低下感恩的头颅/我拿着一把沉默的镰刀走进轰鸣的工地/这把在老槐树下的磨刀石上/磨得闪闪发光的镰刀/这把温暖和照亮故乡漫长冬夜的镰刀/一到工地就水土不服,就东张西望/一脸的迷茫,比我还无所适从/我按传统的姿势弯下腰,以牧羊曲的/节奏优美地挥舞镰刀/但镰刀找不到等待它收割的谷物/钢筋水泥之下,是镰刀无比熟悉的土地/从此后只能是咫尺天涯/镰刀在工地上,是一个领不到救济金的/失业者,是工业巨手上的第六个指头/但我不会扔掉它/它在风雨中的斑斑锈迹/是它把一个异乡人的思念写在脸上/是它在时刻提醒我,看见了它/就看见了那片黄土地
在传统乡土社会不可逆转地走向工业化的进程中,发端于经济特区的现代城市文化也正全方位地影响和改变着当代中国。作为第一代特区城市移民,卢卫平以新市民的冷静视野,发现了“沉默的镰刀”与“轰鸣的工地”的不可融合,客观地写出了新市民的精神来路和时代发展的必然性。当然,在表现新市民的精神故乡和“进城路径”的同时,珠海文学书写的主题也指向进行时态中的现代都市生活,和由此生成的种种个体精神遭际,譬如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堕落诗》《七步镇》、唐不遇的诗歌。此外,还有曾维浩形而上地探讨人类文明困境的《弑父》,等等。
五
我们这样谈论“珠海文学”,并非要说明它有几多高明或多么富有前瞻性,而是意在界定珠海文学书写的区域特性。比较地看,深圳文学书写走过了“打工文学”“底层写作”“城市文学”等以阶段形态递进的完整路程,且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城市移民文学表达的经典样本;珠海的文学书写则仿若后来居上,直接在“城市文学”阶段才加入了中国经济特区文学也即现代城市文学的阵营。或者,亦可表述为:珠海文学书写刚一登场,就呈现出“城市文学”的形态样貌。
事实上,1983年出现的“城市文学”命名,并没有显示出彼时文学界对现代城市的准确认知[4]。因为在物质和制度层面真正具备工业文明特性的现代城市,肇始于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创立,进而成为传统乡土所代表的农业文明的前进方向和目的地。一定程度上,特区深圳的发展进程,就是中国大陆现代城市兴起和壮大的演进过程。所以直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中国现代城市的真正面貌才在越来越丰盈的文学书写中日益清晰。具体地说,特区移民文学表达的每一种阶段性形态,都对应着相关的现代城市生活内容。也即以“农民工”为表现主体的“打工文学”,是现代城市建设初期传统与现代由对立走向融合阶段的形象写照;“底层写作”是现代城市工业体制转轨时期的艺术再现,表现对象由“农民工”扩大到下岗工人和城市平民;“城市文学”则是对现代城市渐渐成型后各个领域社会生活的文学描述,表现对象由“底层”延展到“中层”,也即从普通市民阶层扩容至城市中产阶层。所以,“城市文学”作为专有概念在晚近30年逐渐得到认同的过程,映衬的是社会转型基础上中国现代化城市从诞生到成长的历史。
问题在于,随着工业化社会转型的基本完成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渐趋完善,“打工文学”与“底层写作”所承载的“苦难”“怨愤”等特定内涵已经变成历史。面对“乡土中国”转型为“城市中国”的“新时代”,疆域阔大的“城市文学”到底该怎样确定自己的形态坐标?究其实,对于“城市文学”,认同并不等于切实把握。所以,当我们说起“城市文学”的时候,更大程度上是在强调其与“乡土文学”对举的价值,关注的是现代城市移民从“他乡”到“我城”的融合。也即“城市文学”是对“打工文学”“底层写作”的内在承继和自然递进,由此构成了现代城市移民文学的最后一个阶段性形态。而在中华民族的双脚踏进工业化社会门槛的“新时代”到来之际,“人的现代化”的发展现实,正在生成进行时态的“新市民文学”。作为“新时代”第一个阶段性文学形态,“新市民文学”应该超越改革开放40年来传统乡土与现代城市之间二元对立的思维壁垒,以更前瞻的姿态、更高远的视界和更宽厚的情怀与时俱进,描画出中国人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情感际遇和心路历程。从这个角度看,珠海的文学书写既与“深圳文学”并辔同行,也因从“城市文学”向“新市民文学”的跨越而显现出不同格局和独特魅力。
另一方面,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近于功利的一城一地的区域化文学品牌倡导,显然不能再有很多很大价值。在岭南历史与文化的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这个现代化城市群中每座城市的区域性文学书写,都必将是“大湾区文学”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圳文学”如此,“珠海文学”亦如此。这也是本文采用“珠海文学书写”替代“珠海文学”的基本缘由。
注释:
[1]见杨宏海的《“打工文学”的历史记忆》(《南方文坛》2013年第2期)、《文化视野中的广东“打工文学”》(《粤海风》2000年第6期)等文章。
[2]此处借鉴了梁启超的观点。具体见1923年2月梁启超为申报馆建馆五十周年所作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一文。
[3]1994年,深圳的《特区文学》在第1期杂志的卷首语中提出“新都市文学”的概念。之后的两年里,相关的理论阐述并没有厘清“新都市”的内涵,也未产生与之相对应的作品,仿佛“新都市文学”就是“深圳文学”的新版本。但这个概念的提出,表明杂志编者已经敏锐地把握到特区人在涉及现代城市的立场、观念和态度上的无形转变。
[4]见《城市文学笔会在北戴河举行》(《光明日报》1983年9月15日)。1983年8月下旬,“全国首届城市文学理论笔会”第一次提出“城市文学”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文学界对现代城市的自觉关注。与会者给予“城市文学”的定义是:“凡是写城市人、城市生活为主,传出城市风味、城市意识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为城市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