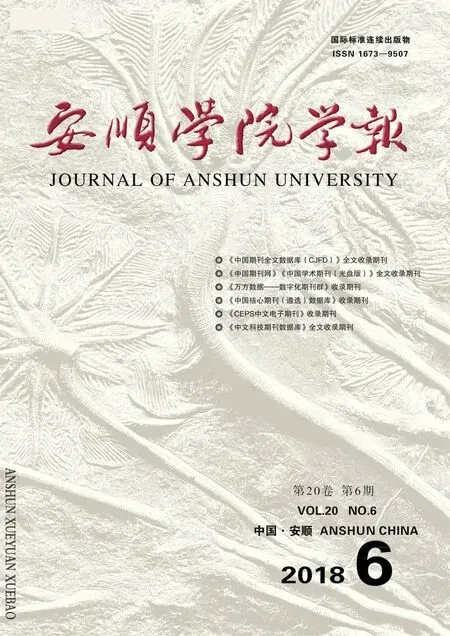汉语词汇化内涵及特征论说
张建强 刘晓蓉
(1.安顺学院人文学院,贵州 安顺561000) (2.怀化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怀化418000)
当前,词汇学家们对词汇化的研究视角开阔,成果颇丰,而且不断将汉语语义功能引入新的领域,从而使汉语的一些语意语素被赋予新的意义。如冯志伟等将词汇化研究引到计算机、数理语言、机器翻译的角度,提出了词汇化树邻接文法;杨亦鸣等将词汇研究引入神经医学角度中。对于这些语素义的延展,对传统词汇化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从而也引起很多研究者的争议。当然,要弄清这些争议的本质,首先必须要弄清词汇化的概念。单就词汇化一词本身,它是由词、汇、化三个语素构成,它们相互组合,可以形成与词汇化相关的三组概念:词汇、词化、词汇化。在汉语语意中,词是指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它是由语素构成;而词汇是词的集合,是一种语言里所有的词和短语的总和,是由词和短语组成的集合。显然词与词汇有着明显的概念差异,那么词化、词汇化的概念同样也应该会存在相应的概念差异。一般来说,词化、词汇化除了两个词的前缀不同外,两个词的后缀都为“化”,同时也应该有很多相似之处。要把握彼此之间的异同,就必须弄清词汇化的概念。文章主要从汉语语意的研究入手,通过对当前研究成果的回顾与辨析,希望能够厘清一些学术争议。
对于词化与词汇化中的“化”,从语义解释上,大多学者认为是演变、变化、变为。如董秀芳认为词汇化是指从句法层面的自由组合到固定的词汇单位的演变过程,她在《汉语词汇化和语法化的现象与规律》中总结前人经验,将“化”集中表述为:转变、变为、选择。例如:“最常见的一种是指在语言系统中将概念转化为词的过程……词汇化有时可以用来指将功能范畴用语音手段体现出来从而变为显性形式的过程……将根据表达意图对合适的词的选择称为词汇化……词汇化有时专指从语法成分变为词汇成分的变化……指从非词的单位变为词的过程,最常见的是从短语或从句法结构演变为词。”[1]李宗江指出:“两种来源的词汇单位都可能进一步发生语音和语义的变化,这种变化应该叫‘词化’……句法结构可能演变为词汇成分,这是词汇化问题,句法结构和词汇成分也可能演变为语法成分,这是语法化问题……由句法性质的单位演变为词汇性质的单位的过程和现象叫词汇化。”[2]“词化在共时层面指用词项对概念进行编码,在历时层面指各种语言材料演变成词项的过程和结果。”[3]丁丽认为:“词汇化是短语演变为词。”[4]罗耀华等认为“词汇化可以宽泛地定义为在词库中吸纳新的词汇,还被一些学者视为固化意义的发展。”[5]
对于语义研究,也有一部分学者用凝固、固定来定义,蒋绍愚指出“某些概念要素进入一个网的词义结构中,即共时词汇化,由大于词的语言单位凝固成词的过程”[6]可见蒋先生将“化”定义为进入、凝固。王寅认为:“一个范畴、概念或意义在一个语言中可用一个词语将其相对地固定下来,这可叫作范畴或概念的‘词汇化’”[7]。
从上述的这些研究来看,词汇化中的“化”,被大部分学者定义为演变、变化、变为、凝固、固定,也有少数用表达、进入、选择、吸纳来定义。而且从这些词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们多为趋向动词,几乎可以用“从某种状态到某种状态”或“用什么成为什么”来表达。详细推论,不难发现这些争议焦点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定义的角度不同。有的从时态角度出发,有的从词汇自身组成要素出发,有的从发生学角度考察等。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是能否将这些不同角度的概念统一,形成一个共识,为此,我们先来探究一下“化”的本义。
“化”在很多古籍中表达改变、变化、生成、造化的本义,“化”的其它引申义教化、消失等意义与本文的研究无关,不再赘述。“化”的甲骨文字形像二人相倒背,一正一反,似乎寓意从生到死的“变化”。《玉篇》云:“匕,变也。今作化。”“化,易也,教行也。”[8]《荀子·正名》云:“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9]《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曰:“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夫变化之为用也,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10]《读史札记》记载:“《周官·大宗伯》日:‘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化者,天之生物之名;产者,物之生物之名也。注曰:‘能生非类曰化,生其种曰产。’物固非天地之类。疏引‘田鼠化为驾,雀雉化为蛤蜃之等’以释化,仍是物生物之事,非是。《乾·彖辞》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疏曰:‘变,谓后来改前,以渐移改。化,谓一有一无,忽然而改。’疏曰:‘《易》乾道变化,谓先有旧形,渐渐改者,谓之变。虽有旧形,忽改者谓之化。及本无旧形,非类而改,亦谓之化。’”[11]以上解释中,《荀子·正名》指出了事物随着时间改变发生状变但实质没有发生变化的(即同一事物不同阶段不同名)叫做“化”,同时也指出“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即同形状而在不同处所,可能有相同名称而多种实物的情形。《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读史札记》同时解释了变与化的含义,“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是说新事物产生的过程叫“化”,而旧事物由小到大发展到盛极的过程叫“变”,“化”是量变,“变”是质变;“变,谓后来改前,以渐移改,谓之变也。化,谓一有一无,忽然而改,谓之为化”,是说新事物逐渐改变旧事物叫做“变”,新事物突然改变旧事物叫做“化”, “变”是量变,“化”是质变。撇开上述认识的差异,综合概述,“化”是指因时间、处所不同经量的积累达到质的变化。在理清其语义演进之后,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众多词汇化研究理论差异之根源。一般来说,共时词汇化和历时词汇化研究视角是因为“化”有量的积累和质的突变,量的积累过程为共时,质的突变为历时。我们认为对词汇化的研究,应该将共时词汇化和历时词汇化统一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不管是通过构词法、语法,还是组合法、句法缩减构造的词,它们都不可能一夜之间就为大家所接收,因此词汇化概念也应当描述出这两个变化过程。
首先,我们确认了定义词汇化应该用“从……变为……”句式来表达,其前半部分是量变积累中的某种语源,后半部分是质变后的词汇成分。那么量变积累中的某种语源和质变后的词汇具体内容是什么又成了我们定义的难题,词汇化是如何通过量的积累在何时达到量的变化。我们知道,量的积累过程中,只要没达到质变,事物的性质是一致的,只有达到质变事物性质才会改变。理解了词汇化的量变及质变规律,那么词汇化过程中,是由怎样一种状态演进为一种新状态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还需回到前面那些专家的定义中去。学界在对“凝固、固定”的描述中,他们往往是从词的结构和意义以及认知角度分析的。例如:“词汇化的含义是用一个词位代替一个抽象的语义构造,或者说一个概念用一个词位来词化,是范畴化和概念化的结果相对固定于词语表达之中,是复合词或新的意义在词汇层面上的规约化。”[12]这些表述中表明:词汇化的结果要求语义规约化、丧失组构性;形式要缩减;语义和形式都凝固一体,不易分开。语义规约化后各语素在词汇中丧失组构,形式缩减凝固一体不可切分是词汇化的重要标志,这就确定“从……变为……”句式后半部分内容,那么前半部分的内容刚好与之相反。需要指出形式缩减,不仅是指简单的构词要素的减少,也包括该词汇在语言单位层面的降格,如:“‘拉倒’这一结构始见于明代,清中叶前都是述补短语,……随着动作义的减弱,‘拉倒’词汇化为实义动词,表示‘完结、没了’”,[13]‘拉倒’作述补短语和实义动词都由拉和倒两个语素构词,但作述补短语时,我们可以认为是“把/被……拉倒”的一种省略。
其次,词汇化是指某种形式宽松、意义宽泛的语言组合在语用过程中台阶式地变为结构紧凑、意义凝固的词汇的过程。要把握这一概念,我们必须明确以下观点:
(一)词汇化前后都要求是语素组合。其一我们不能说某一个单音节语素是词汇化的结果,同样也不能说由多个音节组成的语素是词汇化的结果。很多双声字、叠韵、专用名词、外来音译词虽有多个音节,但它们整体表达一个语素意义,兵乓、蜻蜓、沙发、李白等词不是词汇化的结果。其二我们不能说多个语素组成的语言流体合并或成分缩略成由一个语素的词叫词汇化,例如:两个、三个分别用“俩”和“仨”表示,“不用”用“甭”表示,“不好”用“孬”表示等等。
(二)词汇化要求形式和意义都发生固化改变。一个词汇化了的语言单位,形式和意义是一个整体,很难切分,它的意义不再显现单个语素意义之和。这里的形式是指它们演变前后的语言单位性质发生了改变,一般情况是词的上级单位词组、短语、句子、跨层结构等降格而来。如果语素组合只发生形式变化而语义没有发生变化,我们不能把它叫做词汇化。例如于宝娟探讨“这不”“可不”作为话语标志词成词过程是:“这不是吗?>这不是嘛>这不是>这不”和“可不是吗?>可不是嘛>可不是>可不”,[14]“这不”“可不”在成词过程中,总体上形式在发生缩减变化,但它们的意义几乎等价。同样,如果语素组合只发生语义变化而形式没有发生变化,我们也不能把它叫做词汇化。例如:丁聪在探寻“土豪”词义演变时指出:“土豪经历了古义(地方上多金又有号召力的人)、近义(乡村中有钱有势的恶霸)与今义(气质够土,花钱够豪)内涵变化。”[15]从古义到近义,词义发生变化,但它们的构式都是偏正关系,这一过程只能说是词义引申,无词汇化过程。形式和意义都发生变化,且需要固化才能是词汇化,例如:“土豪”今义显示其构式是并列关系,其意义和形式都还未融为一体,意义还是土和豪意义之和,因此这一过程也不是词汇化。
(三)词汇化是共时和历时统一的过程,是量变和质变统一的过程。形式和意义逐渐凝固,其过程是台阶式的,同一台阶是量的积累过程,是共时词汇化阶段,不同台阶是质变阶段,是历时词汇化阶段。例如:储泽祥、智红霞讨论“战胜”的词汇化过程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过程一中句式结构关系表现为两分句的谓语,语义距离分离,句法形式往往是“……战,胜……”形式;过程二中句式结构关系表现为有标连动结构,语义距离组合,句法形式往往是“战而胜”形式;过程三中句式结构关系表现为无标连动结构,语义距离粘合,句法形式往往是“战胜”形式;过程四中句式结构关系表现为动补式复合词,语义距离融合,句法形式往往是“战胜+ 宾语”形式。[16]其实过程一、过程二、过程三可以归纳为形式宽松(结构可以切分或分属不同句法结构)、语义宽泛(表现为各自语素意义之和,语义发展不明确,所指对象抽象不具体)的过程,过程四是结构紧凑、意义凝固的过程。我们认为,词汇化一般情况下都应该经历这两个阶段。前一过程是语义和形式磨合期,不管它们经历何种变化样式,归根结底都是语素意义相加,只不过这种相加语素意义越来越不明确;形式总体上由分散到聚合或构成语素缩减。前一过程经量的积累,当社会现实所指刚好需要这一语素组合来表达,这时构词的单个语素意义脱落,而整体意义不可切分,此时我们才认为该语言组合已经词汇化了。
(四)形式变化是外在因素,意义变化是内因。意义融合、所指具体是判断词汇化的根本,语用意义变化是词汇化的根本动力;但词汇化形式的变化方向可能会出现多样性,可能会选择这一个语素组合,也可以选择另一语素组合,而且随着词义发展,组合形式还会进一步变化,形式能否切分的依据是词汇语义是否凝固。
复合构词法与词汇化既联系又有区别。如果用复合造词法构词,理论上,任何成词语素通过组合都可以复合成词,但实际上很多组合并没有被大众接受,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所指意义系统规约化指向决定。如下图所示:

图1 复合词与词汇化演变途径
任意语素组合最终发展的结果有两种:复合词和词汇,我们用这两个不同名称来归结,主要考虑语素组合演变的两种不同路径,如果最终演变成复合词,这个过程称之为构词法,如果演变的结果是词汇,此过程称之为词汇化。构词法路径有二:一是任意语素组合在语义被认知且语义凝固的条件下直接构词复合词;二是任意语素组合在语义不被认知形成形式松散的语言流体后随语用习性重新被大众认知且语义凝固的条件下也会构词复合词。词汇化的路径也有二:一是任意语素组合在语义被认知但语义不凝固的条件下构成短语,短语在发展过程中降格变为词汇;二是任意语素组合在语义不被认知形成形式松散的语言流体后随语用习性重新被大众认知但语义不凝固的条件下构成短语,短语在发展过程中降格变为词汇。词汇化和构词法表面上都是造词法,但实际上区别很大。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六书造字法中,大部分学者认为转注和假借只是用字法,并非像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这四种造字法能够造出汉字,我们同意这种说法。造字法和造词法起初有何种关系,我们无从考究,但造字的方法肯定会影响到造词法。同汉字六书造字法一样,词汇化和构词法表面上都是造词法,但复合构词法是造词法,创造出新词形式,而词汇化只是语用过程中的用词法,它没有产生新词形式,虽然可能有形式上的缩减,但缩减形式是语用流转,并非一种从无到有创造。有很多学者认为,词汇化是语法化的逆过程,是大于词汇语言单位的一种降格,这些观点也证实了词汇化的结果不是创造,是一种语用形式到另一语用形式的转变,这种变化是渐变,而非突变。正如石毓智指出:“当复合词的构造格式稳定下来以后,人们就可以仿照这种格式创造新的复合词, 并不需要每一个复合词都必须经过句法组合这一历史过程。当今出现的绝大部分跟科技发展和新生事物有关的词都是根据构词法造出来的。”[17]
——针对对外汉语语素教学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