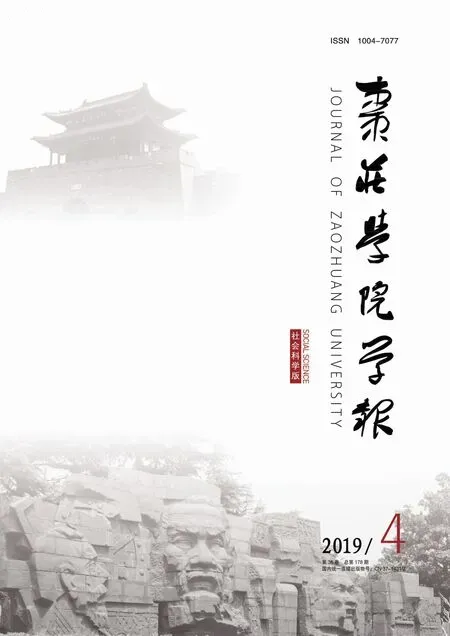叶启勋的书籍生活和情感世界
胡晨光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论起典籍传藏,多以江浙为代表;湖南地处偏远,不常被人推重。傅增湘说:“尝观古来言藏书者,咸争推吴越故家,而楚蜀之地,乃寂寂无闻。”[1](P3)民国年间,以叶德辉为代表的叶氏家族,在湖南藏书界异军突起。叶启勋是叶德辉的侄子,家风浸染之下,叶启勋继承了叶德辉喜好藏书的品格,著有《拾经楼·书录》三卷,纪其所藏善本图书百余部,傅增湘为之作序。在书录题跋中,叶启勋不仅关注典籍的文献价值,考订书籍的版本、批校、流传,且记述了许多与时代、家族、书籍生活相关的掌故,使之具有独到的文化价值。
叶启勋兄弟三人,兄启蕃、弟启发,同好购藏典籍。其弟叶启发藏书楼号为华鄂堂,藏书志名《华鄂堂读书小识》,两家藏书初未分彼此[2](P3)。叶启勋子叶云奎说:“迫于生计,伯父启蕃外出求职,以擅长珠算得任会计;叔父启发擅长国画,得任教员;父亲则得日本《汉学杂志》和南京金陵大学《国学季刊》约稿,而收藏古籍工作未尝一日稍停。”[3](P493)另据《二叶书录》,兄弟三人的善本书籍多为叶启勋购入,则叶启勋为兄弟三人中收藏典籍的主力。
叶启勋的诸篇题识写定之后曾公开发表,1934年《图书馆学季刊》发布《本刊所载〈拾经楼群书题识目录〉》[4](P420),其中已有题识四十余篇。1937年,叶氏将《拾经楼·书录》刻印于长沙;1940年时,《拾经楼·书续录》成书二卷,达二三万字,李小缘曾许为之分期刊布[5](P135),惜未见下文。启勋弟启发说:“己卯三月,定兄取劫余未尽之书编成书录,更取所作各书之题跋订为《拾经楼·书后录》。”[6](P170)可知在1939年时,叶启勋还曾编订藏书目录,亦未见流传。因此,我们在讨论他的书籍生活时,现存的《拾经楼·书录》是最为主要的材料。
近年以来,随着学界对湖湘文化的关注,针对叶启勋的相关研究渐多。姜庆刚、晏选军等学者发布了叶启勋同李小缘、商承祚、柳诒徵等学人来往的书信[7][8][9]。张宪荣和杨琦则重点关注了叶氏兄弟所撰《二叶书录》的特点和价值[10](P86~95)。尧育飞所撰数篇文章揭示了叶启勋的生平经历和学术贡献[11][12][13],且他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傅增湘旧藏《长沙叶定侯家藏书纪略》一书抄录发布[14](P191~206),为学人研究叶启勋藏书提供了新材料。以上研究对我们了解叶启勋其人其事均有重要贡献。但少有学者关注叶启勋具体的藏书活动、心态和情感,本文拟以叶启勋所撰《拾经楼·书录》为中心,勾稽其书籍生活和情感世界,求教于方家。
一、叶启勋的典籍购藏
受家族影响,叶启勋很小的时候即注重购入典籍,他说:“余年才志学,即从厂肆游。”1916年,叶氏17岁,时周銮诒藏书散出,他与友人秦更年分得之。1930年时,叶启勋31岁,他写到:“本抱残守缺之心,为启先待后之计,历十三寒暑,得四万卷有奇。”[15](P76)再至1937年《拾经楼·书录》撰成刊刻时,叶启勋自称“十数年间,聚书十万卷有奇”。则仅在1930至1937这七八年间,叶启勋就购入典籍六万卷。
(一)购藏方式
有学者总结 “购书之方式也往往因人因时而殊异。然举其大概,仍有一定之式:以购书对象论,或字书肆、贾客,或自藏家、民间;以购书类型论,或专注新籍,或钟情旧典,间或新旧兼蓄;以购书方式论,或自买,或代买,或大宗收购,或零星蓄积;以购书所得论,或系刻意寻觅,一朝释怀,或系不期而遇,喜出望外,如此等等,难以尽举。”[16](P235~236)据《拾经楼·书录》所记,叶启勋购藏典籍有得之书肆、书贾、藏书之家等方式,他钟情旧典,以自买为主,兼有大宗收购和零星蓄积。
《拾经楼·书录》记载,长沙的玉泉街旧书肆是叶启勋经常寻觅图书之处。他的藏书中,有些书就是从书摊上不经意间得来,如在“冷书摊中”得赵之谦的《从古堂款识学》[15](P70),又在“冷书摊头购得明成化癸巳先族祖文庄公刻《咏史古乐府》”[15](P138)。
但更多的好书还是直接来自于书贾处。叶启勋不惜重金、广搜旧籍的名声传扬在外,书贾常持书上门或持书单邀请叶氏往购其书。如明刻本《韩诗外传》题记载:“三月十日,估人从湘潭旧家获大批书籍归,约余往观。”[15](P17)1935年时,叶氏曾得北宋刊小字本《说文解字》,记得书过程:“乙亥夏五,湘乡估人持书一单求售,约余往观。”[15](P17)时代变动,藏书难守,旧藏书家之书,也常为叶氏所得,如于贺长龄后人处得李鼎元手批《水经注》[15](P54),于黄国瑾家得朱彝尊、黄丕烈旧藏明抄本《牡丹百咏集》[14](P202)。
“不期而遇”之外,他特别关注何绍基的旧藏,可谓“刻意寻觅”,在坊肆、书贾处见之,不惜重金购求,何氏后人何诒恺亦趋叶启勋之门求售。故叶氏所藏善本书中,何氏旧藏甚多。据叶启发所记,1929年时,兄弟二人购藏何绍基旧藏已超过五千卷:
有清道咸之间,道州何子贞太史绍基以书名重海内,而其藏书之富,人多不知,殆以一善掩众长也……丙寅、丁卯之间,太史曾孙诒恺移寓省垣,染阿芙蓉癖甚深,又沉溺醉乡,陆续举其先世所藏者售金以资所费。余兄弟每于估人手见其家藏旧本,必倾囊金购归。先后所得,以宋椠《宣和图谱》《韵补》《梦溪笔谈》,毛抄《重续千字文》为最,其余元明旧椠、批校稿本不下五千卷也。[15](P76)
何绍基以书法闻名,其藏书罕有人关注。何氏后人移居长沙,嗜好鸦片,不能守书,其书遂辗转为叶启勋兄弟所得。当然,叶启勋购求图书的方式有可能是诸多方式的综合,旧藏家之书散落坊肆或为书贾整体购去,再为叶启勋所得,也是常见的情况。在叶启勋的典籍购藏活动中,少见请人代购,多为亲自购买。
(二)与书贾的博弈
同其他商品的流通一样,在图书市场的交易中,买方和卖方也常要经历一番博弈。叶启勋在藏书界浸润多年,自然要同书商常有往来。叶启勋的笔下的书商多没有留下姓名,多以“书估”“估人”代称,其形象或阴险狡黠,或敏而好学,跃然纸上。试举一例,王鸣韶为王鸣盛之弟,有《鹤谿文稿》手稿。叶启勋先于袁芳瑛处得此书之一半,而书贾处持有另一半。“书估知余必欲得此以成完璧,始颇居奇,迁延月余,以残册无人过问,卒为余有”[15](P154),叶启勋知晓书估居奇迁延的原因和目的,但不急于入手,最终书估因书为残本难以售出,不得不售予叶启勋。更多的情况是每逢珍本,书贾常以叶启勋之面色定书之价格,“估人之黠者,每以余之面色定价之高下。此书余一见而心怦怦动矣,估人遂坚持原价,不肯减少”[15](P129)。更有狡黠的书贾不知书之价值,仅见叶启勋来购,便知书非普本,刻意提高价格。叶启勋对此深有体会,但惜书之情,不忍交臂失之。如购明本《居士集》时,“当时持此书求售,人无知者,余拟以贱价获之。不欲书估见余欲售,始知为秘帙,居奇昂价。余重其希见,乃以重价收之”[15](P118)。
有经验的书商多熟悉典籍的版本和价值,以为交易时的凭借。故有时藏家和书贾眼力精疏,在书籍交易时十分重要,稍有不慎,就会处于下风。1916年时,叶启勋在书贾处见彭文勤手校古香楼抄本《默记》,因书贾不知彭文勤之名,叶氏得以贱值二十金得之[15](P78)。又如因书贾“不知半恕道人为荛圃别号”,且不识其笔迹,叶氏得以番银四十饼购得明刊本《巽隐程先生集》[15](P142)。
有时书贾居奇过甚,索价极贵,叶氏不得不采取非常规办法,仿明人王延喆事,排印流布之以降其价。明嘉靖王延喆刻本《史记》题识记:“忆余庚申岁,有持影宋抄本唐马总《通历》求鬻者,闻出县人袁漱六太守芳暎家中,其先固兰陵孙星衍渊如观察旧藏本也,索直极昂,且不肯示人。余颇恶其居奇,乃假归,集从父兄弟竭一昼夜之力,抄写其副,急以活字排印二百部,而以原书还之。厥后活字印本坊肆风行,其人知而贱售从兄某,今得之矣。距求售时才月余耳。”[15](P38)当然,此法不甚光明正大,不足为人效仿。
亦有好学的书贾,买卖达成之后仍向叶启勋求教的。有一柳姓书贾,持一汲古阁刊毛扆校本《春渚纪闻》,二十金售于叶启勋。成交之后,“柳谓余曰:‘京估某曾见过,以无毛印疑之,今已售汝,曷告我以真假?’”[15](P85)叶启勋回复说自己曾在涵芬楼见毛扆校本《鲍照集》,以字迹推断,此本确为毛扆手校。
二、叶启勋的藏读习惯
藏书家在长期的书籍生活形成了一定的藏书和读书习俗,在这之中体现着藏书家的精神追求和情感寄托。
(一)重装典籍
叶启勋对所藏善本,常进行重装。一种情况是书籍破损或分割,必须重新装订才能方便阅读和保存。许多残缺之卷在经叶启勋之搜访和重装之后,得以破镜重圆。如宋刊明印本《临川先生文集》,“此书纸背间多朱墨字迹,盖其时用公牍废纸所印。原书装二十册,以嘉靖极薄绵纸衬订,余因其破口虫伤重装,将原衬纸撤去。惜纸背字迹因重装不能辨认,并识之以谂后之读是书者。”[15](P85)再如王鸣盛之弟王鸣韶的《鹤谿文集》手稿,1916年时,叶启勋先于袁芳瑛家得其半,三年后,再于书贾处得另一半,“因为编次,重加装订”[15](P154)。叶氏重装修补之举,不仅保证了典籍的价值,也延续了典籍的生命,其《鹤谿文集》一书至今仍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还有一种情况是善本需重装之以示珍贵。如宋刊宋印本《韵补》(是书湖南图书馆鉴定为元刻本,可备一说),叶启勋“以番饼百元得之,手自装池,以为吾家镇库之宝。”[15](P31)翁方纲手校旧抄本《瀛涯胜览》,叶启勋“特重加装饰,以待来者,知所宝重焉”[15](P56)。
(二)节日读书并作题记
据《拾经楼·书录》所载,叶启勋常在特殊节时取书阅读并作题记。以他书籍生活中相对安定的1926和1927两年为例:
1926年,正月人日,读明刻本《镡金文集》并跋之[15](P144),中秋,读赵之谦手稿本《从古堂款识学》并跋之[15](P70);重九日,读《昌谷集》并跋之[15](P111);腊八日,读《杜樊川集》并跋之[15](P110)。
1927年元旦,读汲古阁影宋精抄本《重续千字文》[15](P34);正月人日,读《后山诗注》并跋之[15](P122);元宵节,读翁方纲、何绍基批校本《宝真斋法书赞》并跋之[15](P78);中秋节,读明刻本《寇忠愍公诗集》并跋之[15](P133);腊八节,读明抄本《猗觉寮杂记》并跋之[15](P79)。
以上所举均是重要的传统节日,叶启勋在欢庆时节并不像多数年青人一般陷入欢娱,而是取阅藏书并作题跋,可见他对典籍和文化的痴迷和追求。除了在节日之外,生辰之时,叶启勋也常聚友朋,同集家中,赏鉴藏书。1929年,叶启勋自道州何氏得翁方纲、丁杰、钱馥校本《宝刻丛编》,生辰之日“友人聚集同观,午后泚笔记之”[15](P64)。1931年生辰日,叶氏宴集好友“雷丈民苏、许丈季纯、徐子绍周”[15](P27),于拾经楼西簃,同观张穆、何绍基批校之王筠《说文释例》稿本。
此外,叶启勋还有邀请名士共同鉴赏藏书的习惯,叶运奎说:“座上客有雷氏三兄弟和徐氏两兄弟等……一月数聚或连聚数日,习以为常,始终不懈。”[3](P491)
三、叶启勋的藏书心态
周少川先生曾总结私家藏书心态的类型有文化认同的心理、以读书为乐的意识、“遗金满籝,不如一经”的心态、藏书私密、祈求永保的心态、藏书公开的心态等数种[17](P134~146)。叶启勋以读书、藏书为乐,购书不惜重金,守书时轻易不外借,可见他爱书、惜书和藏书私密的心态。
(一)以读书、藏书为乐
以藏书、读书为乐的心态,使叶氏拥读藏书便不知外界之苦,“时严寒大雪,呵冻书之,不觉其苦也”[15](P120)。再如读《谷山笔麈》,他记:“严寒大雪,围炉书此,时忧祸频仍,几忘其为遁世之民,书能养性,固如是耶?”[15](P90)他在《拾经楼·书录序》中说:“唯余而立之年,半以书相依如命,流离颠沛,伴侣皆书,嗜之笃,缘之悭。”[15](P5)颠沛流离之中,叶启勋以书籍为伴侣,以摩挲赏玩藏书为生平快事。
在时代变动使得“日以读书为乐”都成为奢望时,叶启勋对此表示出无比的遗憾。1933年时,叶启勋得赵启霖手批陈奂《毛诗传疏》。他翻阅其书,见“《疏》中考证改正处颇多,校字离句甚为精博,想见前辈好学之勤劬,读经之审慎”,故感慨到:“方今经学沉晦,礼教纲常且溃决不可收拾,且兵戈水火又一再相乘,求如曩时二三老儒不闻祸乱,日以读书为乐者,殆如钧天之梦,不可期遇矣。展读斯篇,不禁为之掩卷三叹已也。”[15](P19~20)时易势移,旧学典籍承载的传统学问已经不再为追求新潮的士人所沉迷。叶氏在新学崛起的年代抱残守缺,以读书藏书为乐,颇有乾嘉诸老之风。
(二)惜书甚于惜金
叶启勋购书多不惜重金,如叶启发见有人持宋刊本《宣和书谱》求售,索值三百金,驰书上海请示叶启勋,叶启勋“亟复书如值偿之,然未信其真为宋刊,第以历来收藏家志目罕见记载,虽重值勿惜也”[15](P72)。叶启勋竟肯在未信其书真为宋版的情况下,豪掷三百金,可见其惜书甚于惜金。又如曾经方功惠、李希圣收藏的明刊本《古廉李先生诗集》一书,叶氏记其入藏过程:“先是,有人持此书至书坊求售,坊贾中固无一陶蕴辉、钱听默之流能识古书者,因其虫蚀过甚,群鄙夷置之。持书者为湘乡人,初至会城,不识途径,仅闻人言有叶某者,好书有癖,致奇书不惜重价。偶从坊间相值,遂导余至其寓所,且言坊贾之无识,并出此书。告余为其先祖亦元先生旧藏,前有亦元先生手跋,因欲留为世守,而迫于生计,故仅留手迹而去其书。其先则得之巴陵方氏者,与曩时世父考功君所言一一吻合。余亟以番饼百元易之。”[15](P144)叶德辉曾告知方功惠、李希圣藏书的渊源,故当李希圣后人持书来售时,叶启勋亟购之,且其所记“初至会城,不识途径”一语颇为得意,似称自己才是城内有见识、有资格购进此善本之人。同时该题记也点出了在当时的书籍贸易圈中,叶启勋“好书有癖,致奇书不惜重价”的形象已经被广泛认可、流传。
另一方面,叶启勋常在书录题跋中记载得书的价格以彰显自己的惜书之情。1926年,叶启勋得汲古阁影宋精抄本《重续千字文》,记得书之事:“去岁腊八,余从估人手见之,坚索白金二百,迁延月余,乃以五十饼金得之。当毛斧季售书潘稼堂太史时,其《秘本书目》记云‘精抄之书,每本有费四两之外者,今不敢多开’。所谓‘裁衣不值缎子价’也,在当年抄时岂料有今日哉?事逾数百寒暑,今日之价已数倍之,又岂毛氏所能料及哉?”[15](P34)。1927年,以50饼金得明汲古阁影元抄本《文则》一册,并说:“今此书毛《目》所估抄价只八钱耳,余乃以五十饼金易之,数十倍于毛氏估价。”[15](P163)叶启勋以自己购书的花费同毛氏《秘本书目》所载相比,衬托得书价格之高,其意在彰显自己购书不惜重金,表明自己对书籍的热爱。
(三)藏书私密
时局动荡,经历坎坷,叶启勋知书籍传藏不易,故嗜书之情更笃,虽“自诩达观”,但藏书私密的心态使其轻易不肯外借、出让其藏书。叶启勋获得北宋本《说文解字》后,时“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邵元冲夫人张默君,由省政府派人陪同来看此书”,叶启勋以“是否宋本尚不能定告之”[3](P492),拒绝了观书之请。1940年时,金陵大学的图书馆学家李小缘曾致信打探:“长沙告捷以后,日趋稳定,我兄府上藏书幸早下乡,不知近状若何,现移何处,储藏如愿转让,弟甚愿效微劳,是否有意及之乎?”[5](P134)李小缘有意代收其所藏,叶启勋亦未许之。面对各方的压力,叶启勋轻易不肯外借、出让其藏书,体现了他私密藏书的心态。
在叶氏的书籍交游中,他的做法也偏向谨慎。《拾经楼·书录》中出现最多的叶氏书友是秦更年,以秦更年为例,可见叶启勋嗜书之深。1916年周銮诒散出之书中,有明赵氏仿宋本《玉台新咏》,为叶启勋所得。秦更年坚请相让,叶启勋“固未之允”。1927年春,叶德辉过世,叶启勋前往上海避乱,秦更年“复申前议”,叶氏“未忍却箧”。1930年,叶启勋徙家至上海,秦更年“仍未能忘情此书,知余携之行笥,强让未可,割爱不能,遂请假观数日”[15](P156)。至于不肯借书的缘由,叶启勋自述到:“世父死丁卯春月之难,藏书散失几尽,从兄某则因家计,将所得斥卖罄尽,惟余此部,得保守于丧乱之余”[15](P156)。故珍密之书,不肯出让外借。
再以《广川书跋》一书为例,友人藏文征明抄本《广川书跋》,叶启勋“拟乞得之”,以补藏书之阙,结果“友人靳未许也”[15](P75)。从友人的反应中或许可以推见叶启勋平时的做法。叶启勋后得秦氏雁里草堂抄本《广川书跋》,李盛铎之子李家滂来访,“见而赞赏,坚请相让”,叶启勋亦“靳未之许,卒至面赤而去,遂秘之箧笥,不敢示人”[15](P76)。秦更年亦两次来借校此书,叶启勋均未出借,仅嘱叶启发以一刊本临校之赠予秦更年。
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叶氏与诸藏友之间断绝书籍往来,如叶启勋曾“从友人秦曼青许见黄复翁手校元本《诗外传》。适行箧中携有此本,因假归以绿笔临录一通,并影摹诸家校藏印记及题跋,附订于首”[15](P19),即叶氏与秦更年亦互有借钞借校之举。他在题识中多处记载自己不肯外借、出让典籍,源自于动乱时代保藏图书的不易,其意在彰显书之珍贵以及自己的惜书之情。其后人见之,更应宝重其书。
四、叶启勋的情感寄寓
私家藏书具有自觉自愿的特点,透过藏书家们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可以挖掘出他们的文化心态和情感寄寓。在叶启勋孜孜不倦地购求、守护、传承典籍的背后,寄托着对伯父叶德辉的怀念,对家学传承的坚守,也垂训着叶氏后人。
(一)追忆世父
叶德辉曾在苏州寄诗“阿十持本日对雠,抱经思适能同擅”[18](P238)称许叶启勋、叶启发兄弟。叶氏兄弟能在湖南藏书界产生影响,与早年间叶德辉的指点不无关系。叶启发说:“仲兄定侯及余方在髫龄,即侍砚侧。先世父时即以各书版刻之原委、校勘之异同相指示。余兄弟习闻训言,渐知购藏典籍。”[6](P169)
叶启勋能够接触学界名流如张元济、傅增湘,得以拓宽眼界,也多借叶德辉之力。在1921年时,叶启勋前往上海,获观涵芬楼藏书,“辛酉夏,余道过沪上,时大伯父由苏适来,因率余往观涵芬楼藏书,中有旧抄《鹿皮子集》,假之取读”[15](P133)。即便是在叶德辉过世之后,叶启勋避乱上海期间,也获观书涵芬楼,即“夏初,余避乱沪上,从海盐张菊生年伯元济许假观涵芬楼藏书”[15](P115)。1934年时,傅增湘南游衡山,道经长沙,叶启勋执年家子礼相见。返程时,傅氏往观叶氏兄弟藏书并选定十余部珍贵典籍,由叶启勋撰成题识寄给他,即傅氏所藏《长沙叶定侯家藏书纪略》。傅增湘还在叶启勋《拾经楼·书录》书成后为他作序,序中颇多赞许之词。
作为其后人,叶启勋常常在题跋中流露出对世父的怀念。《李文公集》题记中说:“回忆平时每得一书,必经世父鉴定跋尾,今世父殉道,不能起而请益,并以知莫氏之误,书此能不凄然乎?”[15](P109)再如叶德辉拟刻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自莫棠和傅增湘处各得一种,嘱叶启勋校订之。叶启勋记:“丁卯春正,余礼庐抱痛,闭户勘书,先世父遂以二书俾余,嘱为校记,拟付手民。未及其半而湘乱作,先世父殉道,余遁寓海滨。既痛哲人之云亡,复悲先泽之或泯,江天在望,徒唤奈何。”[15](P88)字里行间,表现出对叶德辉的追忆。叶启勋、叶启发在题跋中反复言及叶德辉的指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人传承叶德辉学术的欲望和标榜。
叶德辉在世时,叶启勋曾参与校刻《书林清话》。叶启勋的《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一书即是在叶德辉的指示下创作。叶启发说,叶德辉过世后,“余兄弟避乱申江,携大伯父手稿于行笥中,故交门友见者,无不怂恿付之梓民。”[19](P759)另外,据姜庆刚发布的叶启勋和李小缘的往来书信,叶启勋处还藏有叶德辉的未刊稿数种,并“拟为先伯编订年谱”。可见叶启勋在表彰叶德辉的学问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
(二)传承家学
长沙叶氏自叙是叶清臣、叶梦得、叶盛等人的后人。在书录题跋中,叶启勋有意将自己书写为叶氏家学的传承人,在为叶德辉校刻《郋园读书志》后,他在《郋园读书志跋》[19](P757)中追述了家学渊源,将先人藏书治学的传统、叶德辉的教诲和自己的藏书喜好接续书之,同刘肇隅、叶启崟、叶启发等人的《郋园读书志》序跋相比,叶启勋所作跋文颇有追溯自身学术渊源、传承家族学问的意味。
在典籍购藏方面,很多藏书家对家族前辈、乡邦先贤的书籍都相当看重,以之为学术传承的途径和代表。叶德辉即有意收藏叶氏先贤之书并校刻之。叶启勋时,家族遭逢巨变,时代动乱,他更重视先世遗书,以示不忘所自。叶启勋曾刻意搜求原观古堂旧藏和观古堂所无之书。每得观古堂藏书,追忆旧事,感慨良多。1933年得观古堂旧藏明影宋抄本叶氏先祖叶梦得的《建康集》,叶启勋记:
此则藏之观古堂中,为子孙青箱世守之业。丁卯三月,先世父被难,典籍散亡。此书余从冷书摊头购归,亦似冥冥中有默加呵护者。楚弓三箧,亡来已久,一旦顿还旧观,展卷相对,如见故人。特世父云亡,寒暑屡易,追怀畴昔,感痛系之。惟先世父得此书于庚子冬至后一日,是年五月为余生辰。综此三十四年间,余家变故相乘,余虽屡经忧患而酷好典籍,相依如命。此书几经展转,别六载而仍归于余,抑天公欲破余之癖,故予而故靳也耶?抑长恩有灵,祖先之眷恋余小子也耶?[15](P127)
1900年即叶启勋出生之年,叶德辉购入此书,并从盛宣怀藏抄本补全,后汇刻入《石林遗书》。1927年时,该书随着叶氏家族变动而流散。1933年,叶启勋自书摊寻得此书,展卷阅读,感慨良多,甚至有“长恩有灵”“祖先眷顾”之句。在《拾经楼·书录》完成后,叶氏序中记“非敢问世,以示楹书之世守耳”,足见叶启勋传承祖先遗书和家族学问的坚守。
(三)垂训后人
藏书家常在书志题跋中垂训后人,训诫他们珍惜祖宗藏书、好学勤勉,以求学问绵延、家族兴盛。叶启勋在明抄本《东坡先生志林》题记中记:“辛未七月,文安后人诒恺持来此书,索值至百元。彼固不知书,第以先人所遗,故要高价耳。取阅向书之有少河手跋者,乃知此书无名氏题字亦少河手迹,固即目中所载之书也,亟偿值藏之。盖自也是翁后,又递经大兴朱氏椒花吟舫、道州何氏东洲草堂珍藏矣。两家皆无印记,特志其颠末,以示子孙,知所宝重焉。”[15](P84)何绍基家族衰落,其孙持书求售,但并不确知其书渊源。叶启勋梳理是书的流传故实,垂训其子孙宝重其书,颇有引以为戒的意味。图书的收聚和传承殊为不易,书籍不仅为后人治学求仕提供了支撑,先辈们保藏图书的行为就是极好的家庭教育素材。叶氏先祖叶盛就注重蓄书之举的气度和德行,他得知藏书故家长洲虞氏家道中落,不仅不强取其书,而且举荐虞氏后人为官,传为佳话。叶启勋在题跋中也多次表露出对良好家风的重视。1926年冬,叶启勋得藏书家王时敏的手稿本《王西庐家书》一卷。王时敏在家书中常论及季振宜和钱曾的“峭刻诡谲”。叶启勋对比王时敏和季、钱二人的身后遭遇,感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强调家族教育和家风的重要。他说:
遵王为牧斋族子,生平受其提携,得附士林。后乘牧斋之丧,率族人争产,逼河东夫人缢死,其人狗彘不若,乃知西庐有先见之明……书中叙述家常,宅心仁厚,其于亲故贫窘之际,犹时时眷恋于怀,如闻当时父子絮语。其教戒诸子有“为善乃受实用”,勖勉诸儿“事事务存宽厚,念念勿蒙邪曲,培养元气,少答天意”诸语,尤见其居心慈善,不坠家风,宜乎子孙科第蝉联,及身享高寿大名,晚景无不如愿。彼季沧苇、钱遵王诸人虽事事经营,惟恐失利,而身后书籍、字画,转瞬化为烟云,子孙继起无达人,生前遗行,至今为人指斥。亦可见余庆余殃,其理信不爽也。[15](P153)
叶氏对王时敏寄语儿辈的教戒勖勉深以为然,但令人唏嘘的是,数月之后,叶德辉被杀、藏书星散。经历了家族变故、颠沛流离的叶启勋,更知图书保藏不易,1927年8月,他在明成化刊本《李文公集》题记中告诫子孙:“乡邦遗泽,由吴而湘,由湘而吴,楚弓楚得,吾子孙其永宝之。”[15](P109)
叶启勋在书录中,多有言及叶德辉之子叶启倬处。在叶盛手校明闻人诠本《旧唐书》书录中,叶启勋记:
此书出郡故藏书家,索值颇昂。从兄某知其为先人手泽,而又不惜财物,不欲致之。及归余插架,又欲乾没以去。余于从兄弟辈为最小,遂不敢争,亦不愿争也,卒为所夺。未几,从兄某豪于摴蒱之戏,尽散其藏书,余仍从估人手得之。尝考归安陆运使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沈下贤集》叶石君跋”崇祯戊寅得沈亚之集,为林宗乾没,近来林宗物故,书籍星散,宋元刻本尽废于狂童败妇之手。予生平不欺其心,自信书籍必不若林宗死后之惨”云。案林宗公以后娶妻,故致二子失爱以忧死,士论少之。而从兄某以腰缠万贯,吝不资先世父以行,致死丁卯之难,为清流所不齿,卒之及身而书籍星散,且负债累累。然则欺心之人,天理报施,固未尝或爽,其然岂其然乎?因跋是史,以垂训云。[15](P44~45)
叶启勋在题跋中多处表示叶德辉之子叶启倬沉迷赌博、售卖藏书、吝惜财物、学问粗疏,不能继承先世遗志,此处更暗指叶德辉“死丁卯之难”是因叶启倬不愿出资供叶德辉前往日本。叶启勋引用祖先叶盛的跋文,借对从兄的控诉,垂训其子孙为人端正、不可欺心。叶启勋笔下,叶德辉之子的形象可以用“吝惜财物、不学无术”来概括,因此有学者认为,“虽叶德辉生前极为自负,尝称‘湘中一省人物,不及辉之一家’,叶德辉三子,长子叶杞早夭,次子启倬、三子启慕,皆不贤肖,而能继其家学者,实为其弟叶德炯之子叶启勋、叶启发二人而已。”[20](P372)
五、余论
20世纪30年代后期,长沙时局动荡,叶启勋的藏书活动受到了极大影响。1939年长沙大火和1944年日军占领长沙给拾经楼藏书造成极大损失。叶启发云:“中日战起,东北沦亡,继而苏、皖、鄂、赣先后丧失,长沙日有锋镝之警,舟车阻塞,避地无方,余兄弟未得尽举藏书移至乡野。迄至十月,湘垣大火,拾经楼、华鄂堂均成灰烬,典籍之未携出者,同罹浩劫。”[6](P170)1940年时,叶启勋致书商承祚,提及“倭寇肆虐,长沙首被火焚,家藏典册一部分遂罹劫灰,手卷诸稿同为余烬”。另据叶运奎述,日军占领长沙期间,曾派人四处搜寻叶启勋的踪迹;长沙光复以后,又有人趁机挑衅,想要占有其书。叶启勋将书籍用皮箱装好,藏于草药铺。“长沙解放以后,父亲深感购书难,收藏难,保全更难,像此类珍贵书籍,不宜私家收藏,经全家商定于1951年全部捐献国家,现存湖南图书馆。”[3](P493)《长沙市志》载:“1951年,其子叶闿运代表父亲将拾经楼珍善本书100余种,3000多册,2.3万余卷,悉数捐赠给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现绝大部分珍藏于湖南省图书馆善本书库”[21](P578),其中不乏宋元珍本、稿抄批校本。据湖南图书馆的寻霖介绍,叶启勋、叶启发兄弟藏书全帙捐藏于湖南图书馆,至今为其镇馆之宝[22](P138~144)。
要指出的是,叶启勋并非只知赏鉴、不求治学的“赏鉴派”藏书家。他曾参与编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工作,据统计,“撰写提要359篇,其中经部110篇”[23](P344)。他还创作有《说文系传引经考证》《说文重文小篆考》《释家字义》《通志堂经解目录考证》《四库全书目录版本考》等学术作品,部分刊载于《金陵学报》《图书馆学季刊》等刊物。在时局动荡不安,学术风气转向的情况下,叶氏恪守以目录版本学、小学为主的家学,保存典籍,为文化传承贡献了力量。很多叶启勋式的末代藏书家,在动乱的战争年代,不惜一切购求、保存、传承珍贵典籍,又将之捐献公藏,使其至今能为人利用。他们虽然没有亲赴战场,但在文化领域,他们保藏典籍、传承学术的努力同样值得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