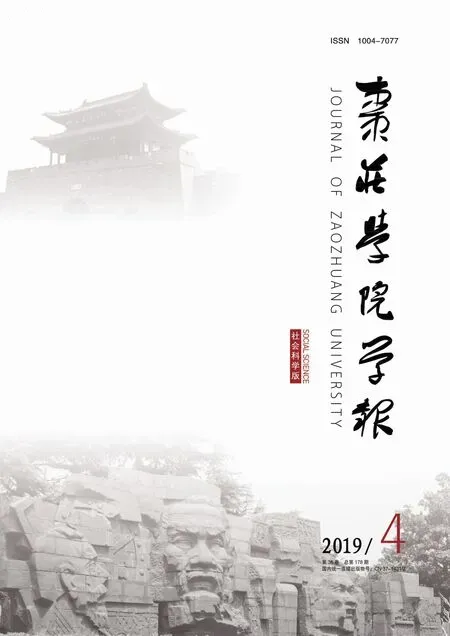“70后”作家与鲁迅的对话
张艳梅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70后”作家写作是不是受到过鲁迅的影响,影响有多大,是很难量化考察的一个话题。“70后”这一代人,差不多可以说是读着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完成语文教育的,至于后来是否系统阅读鲁迅,在生活经验、情感体验和文化态度上,是否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则肯定是情况各异。毕竟每个人走过的成长道路、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并不相同。对于中文系毕业的徐则臣等作家来说,对鲁迅的阅读显然更系统,并且是从学术研究视角进入鲁迅创作的。就价值判断而言,这一代作家是承继,还是拒斥,或是反思,是我一直颇感兴趣的话题。这样的问题即使以问卷的形式去考察,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反倒是从文本出发,尝试着去建立内在的精神纽带,对理解“70后”这一代作家的写作,或许会有某种帮助。
代际作家的研究视角,的确容易产生覆盖和遮蔽,有学者强调去代际标签,也有学者仍旧愿意以非典型代际特征去观照一个作家群体的创作,对于这个问题,我认同徐则臣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我们这一代的阅读与写作”讲座中谈到的观点:“作家的代际”是备受非议的词,人们说代际是一个伪命题。我一直认为,具体到某一代人的时候会涉及代际这个问题。历史不停地出现拐点,历史的轨迹就是按照拐点来排列的。整个历史发展的密度和节奏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恰恰生活在一个拐点特别多的频繁发生拐弯的历史内,这几十年你身上所附载的信息量,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跟生活在其他历史阶段的作家是有区别的。这个时期对你的写作很重要。即使是写清朝和明朝,你所生活的这段时间对你也是非常重要。你可以用今天的眼光和今天所受的教育,你在这样的时代所形成的对历史的看法,拿你的价值观去重新解构明朝的故事。所以对一个作家来说现实感、当代感非常重要。徐则臣认为,作家不仅会受到自己所属时代的影响,同时,也应该自觉地书写自己的时代,并且力求写出这一个时代最独特、最核心的生活和感受。
与作家们交流时,常常提到西方的文学资源,徐则臣说自己喜欢托尔斯泰,田耳更像巴尔扎克,张楚喜欢卡夫卡,弋舟的写作更接近萨特,李浩不仅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可以一口气连名带姓非常流畅地列举诸如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昆德拉、三个玛格丽特等等作家。那么,对光怪陆离的中国现实,对横陈在自己身边的世俗人生,对隐没在历史尘埃里的尖锐过往,有着独特感受力和表现力的这一代“70后”作家们,在他们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本土思想文化资源和文学经验呢?我想,鲁迅,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70后”作家对鲁迅的感情,来自于什么,幼年的教育,后天的体认,还是一种自觉的文化选择?对鲁迅这一存在,持有怎样的评判,精神认同,心理同构,还是忽略疏离?对于这个代际作家整体来说,很难有一个明晰的答案。本文试图通过几位“70后”作家的创作和创作谈,去寻找其与鲁迅在启蒙立场、文化传承和精神共名等方面的内在相通之处。
一、徐则臣的还乡与离乡
故乡还在吗?没有人知道。对于今日中国,每一天都有村庄在沦陷,荒芜,甚至消失,当年鲁迅所说的远处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现在除了荒村,还有冒着黑烟的工厂,断壁残垣的烂尾楼,还有的早已成了野草湮没的无人区。我们的故乡都去哪了?这是个没有答案的天问。近百年来,我们不断失去的包括文化之根,伦理之根,大地之根,也包括记忆之根。因为消逝,记忆慢慢就会模糊。故乡,成了永远刻在骨头上的伤口。城市化是不是必然的人类社会发展走向,至少现在看城市化是现代性的基本表征。认识中国历史进程,思考现代性确立的标准,离不开中国特有的语境。建立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西二元文化结构,传统和现代二元时间结构,民族与全球化二元空间结构基础上的现代化,其实吸收容纳了多元世界观和价值观,多重现代性话语构成了我们回应世界的复杂坐标体系。
《故乡》和《耶路撒冷》开篇,主人公一个坐船,一个乘火车,在不同季节,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时隔近百年,鲁迅和徐则臣写下各自眼中的乡土中国。一个是萧索荒芜,一个是日新月异。“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而徐则臣笔下的故乡如何呢?“泥沙的河岸变成了石头、水泥的堤坝,房屋越长越高,隔三岔五有高楼在不远处拔地而起。初平阳觉得,现在不是他们的小船进入了城区,而是运河上的生活进入了城区。”“运河南岸的花街在21世纪里雄纠纠气昂昂地往前走,一切都在变。花街在往新里变,往时髦和现代化里变,往好日子里变,新楼和新房子一觉醒来就冒出来,很多人只有穿上了品牌的衣服才好意思出门。”[1](P87)100年了,中国乡村真的现代化了吗?在急速变动的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中国真的找到安身立命之本了吗?从鲁迅到萧红,再到徐则臣,故园情怀不是单纯的人文地理图景,还是文化批判和国民性探察,以及生命哲学的载体。
鲁迅写故乡面目全非,不仅忧虑,而且伤感。“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徐则臣同样满怀感伤从初平阳回乡卖房子写起。米店老板孟弯弯的老婆尖声叫道:呀,北京人儿回来了!和鲁迅当年笔下的杨二嫂如出一辙。“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这一细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现代人的精神漂泊一直是则臣小说的母题之一。这种再次告别意味着什么?100年前,鲁迅《故乡》中的复杂情感,如今已被我们解读得支离破碎,《故乡》中的3个世界,童年桃花源,残酷现实乡,未知理想国,是乡土中国的历史脉络,也是一个根在土地的人,从土地上渐渐连根拔起的过程。那么,徐则臣水气氤氲的花街和大和堂,与鲁迅笔下五彩斑斓的海边西瓜地和老屋,是否意味着同样的文化符码?鲁迅的西瓜地,是鸟语花香的黄金世界,是人到中年历尽劫波依然残存天人合一之念;花街的大和堂,科学与玄学,传统与现代,是更复杂的合和同一。从文化意义上,我们常说,鲁迅是站在世界看乡村,是居高临下的启蒙立场;百年后,则臣是回到花街看世界,是一代人的自我启蒙姿态。《故乡》结尾,鲁迅对宏儿和水生一代抱有期待,冀望于彼此之间没有隔膜,还有一个崭新世界在前头,现在想,这已经无异于幻想国或者乌托邦了。尽管鲁迅自己并不清楚多少人能走出那条路,也不清楚那条路通往何方。徐则臣在《耶路撒冷》结尾,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算是对鲁迅《故乡》的致敬。“所有掉在地上的都捡起来”,简直是神来之笔,故乡,同样是破碎和失落,连带着精神家园,在现代化拆迁浪潮中,早已经化为粉末,大和堂终究会被拆毁,传统中国只剩下遥远的回响,那么,要怎样捡起来?
徐则臣给出了重建文化中国和信仰中国的选择。小何闹着要搬到风光带去,老何因为老伴的坟在屋后面,想留下来陪她。初看,老何坚守的是贫穷和闭塞,小何代表的是对落后乡土世界的反叛,是追赶现代与世界相融的愿望;认真想来,老何那种心怀感恩,诚意正念,宁静古朴的生存状态和生产方式,仍旧值得我们思索。所以,我们会看到《耶路撒冷》中,生活反思、历史反思和存在反思,都是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初医生和初平阳是知识分子代表,父子两个对故乡的态度相似,“和孩子在一起,哪里都一样”,卖掉大和堂,让儿子去往耶路撒冷,夫妇两个准备搬到女儿那里,三百公里外的另一座城市,开始新的生活。初平阳则感慨把年轻人捆缚在荒郊野外,整天与水草泥土打交道,不见得是对的,老何的坚守是则臣对于乡土中国最后的挽歌,父子两个人潜在的都认同了这种告别,实际上是乡土观念和故乡情怀的瓦解,乡愁隐藏在现实选择背后,倒显出了文化反思的冷静。在文化意义上,我们都是漂泊异乡的流浪者。那些精神上的迷惘困惑,寻找和创伤,感动我们的同时,也带给我们很多追问,这一代人经历的是怎样的时代,时代深处流动着那些思想的碎片,对于个体和民族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徐则臣早些年写过《还乡记》,记述了远离故乡的“我”的一次回乡之旅。在叙述者看来,农村世界已经完全“礼崩乐坏”,成了堕落和罪恶的渊薮。现代人的乡愁里包含着太多东西,文化、政治和精神乡愁叠加在一起,形成一种对时代的拒斥和疏离。徐则臣自述:“我写了很多出走和在路上的小说。一个作家最初的写作可能源于一种补偿心理,至少补偿是他写作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实里得不到的,你会在虚构中张扬和成全自己。我从小梦想在路上,到世界去,但我又是一个胆怯的人,且多少年来受制于各种环境和条件,从没有酣畅淋漓地出走过,也从未心无挂碍地跑遍世界,尽管现在我去了很多地方和国家,心里依然拘谨、挂碍和纠结——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天生就是个瞎操心的命。你想彻底又彻底不起来,那只好在小说中把自己放出去,去无限接近那个绝对的、心仪的自由和放旷。当然,写作日久,思索既深,很多问题会换个方式去考量。我发现我无法原地不动地看清自己,也无法原地不动地看清小说中的人物,我必须让我和他们动起来,让所有人都走出去、在路上,知道他们的去路,才可能弄清楚他们的来路,才能知道他们究竟是谁。人是无法自证的,也无法自明的,你需要他者的存在才能自我确立;换一副嗓子说话,你才能知道你的声音究竟是什么样。出走、逃亡、奔波和在路上,其实是自我寻找的过程。小到个人,大到国族、文化、一个大时代,有比较才有鉴别和发现。我不敢说往前走一定能找到路,更不敢说走出去就能确立自己的主体性,但动起来起码是个积极探寻的姿态;停下来不动,那就意味着自我抛弃和自我放弃。”[2]我特别认同和喜欢他这段话,觉得这真是一个智慧的哲人。
现代中国,在近1个世纪的岁月里,经历了什么?那个精神意义上的故乡,固然早已不再,而现实意义上的故乡,同样支离破碎,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路上不断抛弃和失落文化传统,码头上父子两代人的争执,妓女纪念馆,大和堂拆迁,满眼烟尘中,如何找回故乡的宁静,我们是否还需要内心安宁,那片海边的西瓜地,还有多少人念兹在兹?《耶路撒冷》从归乡写起,从卖房写起,写一代人离乡漂泊,回乡寻根,再次离去的历程,故乡是世界的起点,耶路撒冷是世界的终点,那条离乡的路,是寻找,是告别,也是思索。正如小说中的以色列教授从耶路撒冷到上海寻根一样,每代人,每个人,世界的支点并不相同。小说中的故乡是中心,面对这个离散的,碎片化的世界;而耶路撒冷是重心,是面对这个不断崩解的,充满了失重感的世界,离开,回来,再次离开,一代人的精神烙印着故乡的标记,离开那个小村,小村就是故乡,离开花街,花街就是故乡,离开祖国,祖国就是故乡。这部小说无疑是最中国的,又是最世界的。传统中国就是花街到北京,现代中国则是从北京到耶路撒冷。很难说这是一种进化论观点的线性文化史观;反过来看,完全可以看成是一种人类寻根意图的叠加。花街是充满了负罪感黑暗的人生囚狱,耶路撒冷则意味着忏悔和救赎。是现实意义上的罪乡与精神意义上的圣地,幻化出了这一代人复杂的故园寻根情结和精神疗救之旅。[3]
二、李浩的冒犯与不妥协
和李浩通信中,谈到过鲁迅,他对鲁迅的情感态度相对要更复杂些:需要羞愧地承认,我读鲁迅的书并不多。但不否认鲁迅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虽然这种影响不在文本上,而更多地集中于精神上、思考上。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国民性”认知,是我愿意向鲁迅学习的。我愿意自己能有延续,哪怕它显得创新不够——真问题和真命题也许都有“创新不够”的可能,它不是一种时代征候而往往是伴随着人类和人性的,我愿意像鲁迅那样认知它、审视它、警惕它,并在自己的写作中凸现它。把文学当作是药剂,也是我从鲁迅那里得来的,我承认我也部分地继承了这份药的苦涩感。鲁迅的诸多杂文是我喜欢的,但不是全部,我也和他有过诸多的争辩,这种争辩主要集中于“药方”上和某种的情绪上。他的杂文也让我看到另一个自己,一个我所不愿意正视的自己,羞于承认的自己,一个被我藏匿于暗处的自己,这个暗处的自己甚至比平时的自己更为强大。
对于鲁迅小说,李浩同样直言不讳: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孔乙已》等名篇是我所喜欢的,我也喜欢他的《伤逝》,那篇小说的“语调”甚至从骨子里影响着我。我不喜欢《两地书》,至今也只看过有限的几篇也已经全部忘却。我也不喜欢《故事新编》,我觉得它有些浅陋,鲁迅能够赋予的新意并不多。和同时代的国外作家比较,和那些伟大的作品们比较,鲁迅在《故事新编》里的“深刻”是有限的。但我以为鲁迅的这一尝试值得珍视。我猜测,当然只能用猜测这个词,鲁迅写《故事新编》的本意是发掘国族文化中的“故事”,用一种极具现代性的眼光来重新认知,审视和发现——就像古希腊、罗马神话在西方作家那里被反复书写并被反复注入一样。从这点上,鲁迅是个骨子里的“民族主义者”,如果我们不把民族主义狭窄化的话。他其实是试图为东方中国建立一个能与西方故事传统相匹配、相并立的“东方故事集”。然而他这一令人敬重的尝试却有草创的粗陋和勉强——我也以为这并非只是鲁迅“能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来自中国故事的限度:一是中国的故事多是散点式构成,一个个故事都是孤立性的,不像古希腊或《圣经》故事那样有延续性,它不宏大也缺乏长度;二是中国故事又多是道德故事,它对人性的复杂性指涉不够,留给重新阐解的空间不大;三是中国故事往往只重结果而少细节,重新添加“细节”的难度也是巨大的,在落实和想象之间鸿沟的弥平难度巨大。——认识到这一点,非是由鲁迅而来,而是“重述神话”的那一项目,我在思考那一项目中中国作家的书写时想到了鲁迅。我不喜欢《故事新编》,但却愿意以最大的敬意给予他的尝试。我之后的写作,可能会在某些点上延续鲁迅的想法和做法。
从这些自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李浩对待鲁迅的态度。其实无论是自觉地学习和接受,还是潜移默化的正反影响,鲁迅对于当代作家,总是一个值得考量的话题。社会生活在变,文学观念也在变,作家关注宏大的社会命题,对时代生活作出相应的评判,是文学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基础;作家关注个体生命的细微感受,同样可以落脚在现代性上,而且是基于唤醒主体意识的启蒙现代性。在这一点上,李浩的努力方向或者说写作初衷,作为启蒙者的自觉,与鲁迅息息相通。
三、弋舟的孤绝与悲剧感
弋舟说:“写作是对‘常态’的抵抗。它让我的眼睛不只是盯着微信上的朋友圈,盯着貌似孤立的一桩桩社会事件,而是极目远眺,凝望那无论白昼还是黑夜都发着光的雪山。这对视力好,对颈椎好,对清洁的精神和宝贵的记忆好,也有益于自己理解身处的这个世界是如何地‘成了这般’与‘只能这般’。‘常态’中的我,自感有如蝼蚁;工作时的我,自感有如草芥。这两者本无差别,但我顽固地觉得,草芥也许更有漂浮的姿态,也许一阵风,便能令其无远弗届,至少在假想中挣脱了沉重的拘囿与残酷的践踏。这当然是自欺,可小说家有时候就是这么依赖自我的蒙蔽。……我记录下的,就是这一年自己精神生活的轨迹,就是草芥被那阵风吹送着的旅程。为此,我再一次自我蒙蔽,认为自己也许能挽回了什么,镌刻下了什么,对那个念兹在兹却永难谋面的‘意义’,有了一个瞬间又一个瞬间的、即便是徒劳的捕捉”。[4]
弋舟小说有两个主要维度,即个人之死与时代之思。灵魂的丢失与复得,时代的质疑与省思,作为其小说世界的两面,彼此缠绕又各自向纵深处延展。弋舟对人性异常警觉敏感,小说叙事空间、城市具象空间,人物内在心理空间,统摄于精神探索、时代病象及人性观照。“刘晓东三部曲”作为弋舟中篇小说代表作,不仅体现出了巨大的思想勇气,而且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卓异的艺术表现能力。这三篇小说,涉及到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普遍的心理问题,以及有关存在的本质问题,叙事克制内敛而又让人欲罢不能,思之尤深,意味丰饶。面对如此平庸的时代,各种历史之殇,现实之痛,层叠为胸中块垒,写作者如何直面世界与自我,写出个人化的历史与历史化的个人,写出生存困扰和个人精神磨难,越过喧嚣的生活表象,弋舟,以内心智慧,执着又孤独地走在文学救赎之路上。这三篇小说,围绕疾病隐喻,寻找救治途径。围绕失踪的历史,寻找失踪的个人。出走和逃亡,都是失踪的不同方式而已,尹彧、周又坚,包括刘晓东本人,在亡命天涯的背影上,慢慢浮现出反抗和妥协两种表情。邢志平的自杀和徐果的意外死亡,则是失踪的另一种形式,几乎都可以看成是一种主动告别,从人世间更决绝地出走。伴随失踪的,是寻找和求证。《等深》是沿着寻找孩子去求证这个病态时代的来历;《而黑夜以至》是沿着寻找徐果父母和徐果死亡真相去求证究竟谁是这个时代的罪人;《所有路的尽头》是沿着邢志平半生经历去求证导致其自杀的根本原因。每个人的讲述,都是证词,并置在一起,又可以看成是所有人对自我的放弃、背叛和忏悔、救赎的精神笔录。如他在《所有路的尽头》反复引用的博尔赫斯诗句:“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因为此刻正有细雨在落下”,当生活的帷幕缓缓落下,面对自己所属的那一代人的遭遇,弋舟更愿意深入生活内部和精神视野,在历史回溯中,一点一滴呈现世界的本来面目。鲁迅笔下的路:“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正如《等深》中所言,“我们这一代人溃败了,才有这个孩子怀抱短刃上路的今天。”与《所有路的尽头》一样,这篇小说写到了风暴之后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周又坚不再对世界咆哮,安静地与世界对峙,成为一个异己分子,一个格格不入、被世界遗弃的病人。
这样的孤独者形象,在“70后”作家笔下非常多见,或许与这一代人,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年代到世俗主义年代的跌落有关。评价张楚时,我提到过鲁迅小说中的孤独者形象。魏连殳,吕纬甫,飞了一圈又回到原地的苍蝇,关在黑屋子里的一代又一代,这一代作家经历了怎样的追求与动摇,理想与幻灭,可能还需要时间给出文学的答案。写作依然是最后的抵抗,即使生活完全是苟且,永远没有诗和远方。就像张楚所言:“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会幻想着逃离此地,当他坐上火车回望故乡,肯定心怀骄傲与耻辱——骄傲是因为她终于变成了一个行动者,耻辱感则是对自己逃离的一种感伤型审判。”[5](P225)
四、李静的理解与重塑
在“70后”作家中,李静是与鲁迅最直接相关了。重新阅读、理解和认识鲁迅,对于李静来说,是“如见失散多年的父兄”。对鲁迅的接受,并不是一见如故的。少年时代,我们并不理解那个孤绝的灵魂,对鲁迅深奥的思想和奇怪的表达方式,有着莫名其妙的拒绝。尤其是他的尖锐,幽暗,冷硬,常常让人心生畏惧。李静走近鲁迅,同样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儿时的压抑和恐惧,到后来的亲切和怀恋,是在精神上找到了共鸣之后的心理认同,这种心理认同是建立在理性认知和思想历练之后的。她对鲁迅的理解,既是在生命哲学意义上的,也是在自由伦理基础上的。在与鲁迅的心灵对话中,鲁迅早年不幸的旧式婚姻,中年兄弟失和,晚年与左翼人士的冲突,看到贯穿这“三大伤心”的精神逻辑,是“爱与自由的悖论”,这是李静的发现:爱是牺牲之爱,舍我之爱,它与自由是一对难以两全的矛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鲁迅的生命姿态得到了真正的理解和呈现。
鲁迅的自我拷问:“我确实曾做过关于天堂的梦,梦里所有流泪的人都在那儿得到了安慰。为了这个梦,我曾许下天真的承诺,牺牲自由的自我,可我无法牺牲到底。因为自由的本能发作了。可我并不后悔。如果有什么可悔的,那就是我不该相信,对自由的牺牲能带来自由的结果。”“他总觉得能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堂’,但这种想法就是潘多拉的盒子——地上的‘天国’,一定是一个魔鬼人间。但鲁迅不能让自己看透这些,因为他特别性急。鲁迅不相信有来世。觉得现世如果弱者没有得到报偿的话,世界就会永远暗无天日。”这是鲁迅的爱与自由的追问,也是李静自己心里的悖论。为了自由我们到底能够牺牲什么,还是大多数时候我们都选择了放弃自由的苟且?知识分子总是怀有拯救情结,在李静看来,灵魂剖白是自救的开始,思想检视是自我认知的基础。
《大先生》[6]既是个人化的,也是个性化的,李静从鲁迅的临终时刻写起,鲁迅的现实人生场景,根本无法承载他的精神戏剧性和复杂性,剧本选择死亡与梦境交叠,以意识流结构贯穿起鲁迅生前逝后最痛苦、最困惑的心结。死亡的黑色笼罩,梦境被突显为主线,随着现实性回溯,灵魂深处的各种矛盾以荒诞诡谲的姿态演绎。李静尝试的是超越和跨越,超越时空,跨越生死,以鲁迅的思想和精神作为支点,去呈现她心目中的这样一个鲁迅,而塑造这个大先生,也是她自我观照的过程,“你究竟要借鲁迅之口说什么呢?”“可能我这个人,半辈子都在寻找爱和光。因为冷漠和遗弃比死还可怕。鲁迅说,希望人与人不隔膜,相关心,也是这个意思吧。他提醒弱者要强健,要自己去争得尊严和自由,而不是跪等强者的恩赐。实际上,这酷烈是最深最真的爱。”
李静敏锐地感受到了鲁迅内在的虚无与抵抗,那些在生命里对她构成影响的,都是独异的灵魂。共同的思想基点让她在鲁迅身上看到了自己。精神上的痛苦有着共通之处,如何克服这种痛苦,让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找到合理的出路,李静在剖析鲁迅,也是在剖析自我。在鲁迅与中国现代历史的关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与中国现代革命的关系的梳理过程中,李静从知识分子视角解读鲁迅,塑造鲁迅,试图不断接近鲁迅的灵魂和精神。《大先生》深化和延展了已有的鲁迅研究和鲁迅形象认知。鲁迅式的隐喻、寓言和反讽对当代中国作家写作影响深远,但并不是模仿鲁迅的作家真的都能够理解鲁迅的精神世界和思想构成,回到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思想文化场域中去看鲁迅对当代作家的影响,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虽然仅仅几位作家无法代表“70后”作家,我仍旧愿意以这样一种不是很严谨的有限性,去思考无限的可能性。鲁迅沉默地站在我们的精神世界深处,无论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他的影响始终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