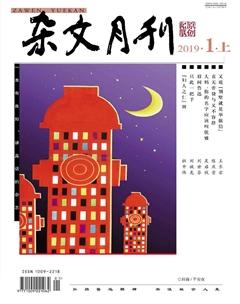由白鹳故事引发的感慨
沈栖
1993年初夏,一只浑身血迹斑斑的雌性白鹳跌落在克罗地亚老人斯捷潘维克奇的家门口。老人在救治中发现,它是因翅膀被猎枪打断而无法展翅翱翔的。这只每年都要去溫暖的地方过冬的候鸟已不能长途跋涉,只得与老人相依为命。老人为其取名玛琳娜,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般侍候之,喂鱼、散步、搭窝,让它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寒冬。10年后,玛琳娜引来了配偶(老人给它取名阿克),还生下了后代。前十几年,出于候鸟的生物本能,阿克总会在冬季来临时飞5000英里去南非避寒,之后按时返回。2017年3月,阿克却没有准时归来,之后也杳无音讯。原来,从克罗地亚到南非的漫长迁徙之路必经黎巴嫩,该国境内盗猎者甚多,阿克也许罹难了!于是,老人用阿克身上的羽毛做成一支笔,写信给黎巴嫩总统MichelNaimAoun。这封信竟然直接送到了总统手里,他特地拿着信配上阿克的羽毛笔拍照让媒体报道,整个黎巴嫩一片哗然。贝鲁特政府表示将尽最大努力支持保护候鸟行动,将偷猎者绳之以法。
这一对白鹳的故事,自然引发世人的惊叹和感慨。
全球有几十亿只候鸟,在每年秋季离开它们的繁殖地,前往更适宜的栖息地越冬,翌年春天再次返回繁殖地。候鸟随着季节更替,定期在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的集群定向移动,学界称之为“迁徙”。候鸟迁徙,其动机和形成颇为扑朔迷离,它们从远方载来神秘的信息,人类无法不相信在自然界中每个生命体都有因果关系。万里行程所构成的一幅幅多彩的“天空之城”画卷,足以勾起每个人脑海里柔情的一抹记忆。只是这种人类的记忆似乎式微,因为抬头即可望见的候鸟日渐罕迹。记得法国著名纪录片制作人雅克·贝汉曾经说过:“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一种对于回归自然的承诺。”坦诚地说,这种“回归自然的承诺”,每一种候鸟都还是至死恪守的,影响或干扰候鸟兑现这一承诺的责任全然在于人类。如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原理,栖息地的丧失乃是候鸟的毁灭性灾难。据澳大利亚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如果失去23%至40%的栖息地,将导致高达七成的候鸟死亡。2015年6月,湿地公约第十一次缔约方大会《水鸟种群估计》报告显示:全球38%水鸟种群的数量在下降,而亚洲的种群下降超过50%。
一幅“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寰宇画卷是由人类与自然界的一切生物如动物、植物、鸟类共同构成的。根据物种进化的原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鸟类也经历着“优胜劣汰”的过程,而且它还不断面临着被动物吞噬的危险。然而,人类以自己的智慧来满足自己垂涎欲滴的饕餮比动物本能的食欲来得更为凶猛。人类的物质主义使他们把鸟类作为审美对象的吸引力拗不过人类对鸟类的食欲,其“改造自然的生产斗争”使自然界的生物加速灭绝,其中鸟类的没踪绝迹远远超过动植物。1962年,美国环保学者雷切尔·卡森鉴于美国城市已听不到鸟鸣,写下了惊世之作———《寂静的春天》。其实这已是一个全球性的生态问题。
行笔于此,我忽而想起了灭绝已有百年的旅鸽。旅鸽,又称漂泊鸠,是欧亚大陆分布广泛的家鸽的近亲,也是人类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曾以亿为单位进行集体迁徙的陆生脊椎动物。17世纪,旅鸽的数量在50亿—100亿只,印第安土著用“鸟之云”来形容上亿只旅鸽同时迁徙的壮观。因为它肉味鲜美而被大量捕杀,这种肆无忌惮的杀戮仅持续了半个多世纪,1900年,最后一只旅鸽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派克镇被击落。美国人在最后一只旅鸽死亡的地方满怀忏悔地立起了一块纪念碑,上书:“旅鸽,因为人类的贪婪和自私而灭绝。”1916年8月,美国与加拿大签署了《候鸟协定》,这是第一份用以保护野生鸟类的国际协定。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说:“对于人性,道德上的真正考验、根本性的考验,在于如何对待那些需要他怜悯的动物。”积数亿年之功所育的鸟类正是需要人类怜悯并加以保护的生物之一。人们正不断理智地认识到这一点。北京奥运会赛场外形是一个巨大的鸟巢,它昭示世人:人的生命运动与鸟的生息之地谐于一体。万物灵动,何不如此?———世界的和谐和欢愉永远是由不同生命共存构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