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在注视我们
董宏君
记得梁衡看路边这些树的眼神是耐心注视的那种,不是飘忽闪过视而不见,即便是在行走之中,也是“眼中有你”的神情,平和、专注、温暖,像是看着朋友。
无疑,树是梁衡先生的朋友。这些年,他像寻访老朋友一样,走向全国各地,寻访树,寻访古树。
《树梢上的中国》里有不少篇章首发在“大地”副刊上。这几年,作为编辑,常常第一时间读到梁衡先生笔下的树,也常常免不了有些思考,甚或生出些疑惑。树,对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树和人都生长在大地之上,爱默生说“在丛林中我们重新找回了理智与信仰”。19世纪写作《瓦尔登湖》的梭罗也常常去林子中,看他那些“松柏表兄”。诗人惠特曼则在散文集《典型的日子》中描写自己如何到一棵大橡树下汲取大自然给他的补药,赞叹树给予人类泰然自若的生命启示。在他们心目中,树已成为大自然的化身,是与喧嚣不安的生活鲜明对照的无价的宁静。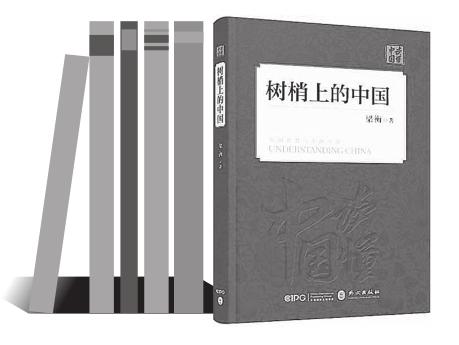
谈到树和人的关系,我必须要提到一位美国女作家——安妮·拉巴斯蒂。她以亲身经历写就的《林中女居民》系列作品,被誉为现代《瓦尔登湖》。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只住了两年,拉巴斯蒂则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直到上个世纪末一直居住在美国东北部山脉的林中小木屋里。这个经历了不如意婚姻的女人,离开她生长的大都市,来到一个叫“黑熊湖”的偏僻之地,学会了用斧头砍木头,用锯子锯木头,在多石的土地上打造地基,建造了一座只能通过小船或步行的小路才能到达的小木屋。在那里,她终于有了“一扇可以向外界敞开与关闭的门,还有可以看见优美景色的窗子”,开始尝试一种全新的生活。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她一个人劈柴做工,修整设施,打理生活,在享受宁静的同时也感受无边的孤寂。孤寂使人长于思索,找回内心。在丛林里,拉巴斯蒂找到了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如作者自己所述:“我亲密的、永久的伴侣是那些树。我对方圆四百英尺内的每一棵树都了如指掌。”她写道:
在风中,云杉发出的是深沉悲伤的抽泣声,而松树则发出略微高昂欢快的飒飒声,冷杉发出的是短暂精确而又彬彬有礼的瑟瑟声,红枫发出的是急躁不安的沙沙声,黄桦发出的则是轻柔平静的喃喃细语。
在风中,她能感受到一棵棵树的情绪,与一棵高大的白松相拥,可以带给她真切的平静。她写道:
我从触摸那棵高大的白松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乐趣。一天早上,当我用双臂抱住树干时,开始有了一种平静、健康、幸福的感觉。我这样抱了十五分钟,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着,粗糙的树皮紧贴着我的皮肤,好像这棵树把它的生命活力注入了我的身体,当我离开白松时,确实感到我们已经以某种形式交换了生命的活力。
进而,她在《汀克溪的朝圣者》中写道:“我的思想开始像树一样抽枝发芽。”
我之所以这样不厌其详地引述拉巴斯蒂,是因为我在她的带引下,第一次领悟到人对树竟然会有这样的感受,人可以与树“交换生命的活力”,以树的方式感受和思考。那么树的方式是什么方式呢?
回到梁衡先生《树梢上的中国》。梁先生著述丰富,在他的诸多著作里,都呈现出对历史的浓厚兴趣,闪耀着思想的光亮。这本《树梢上的中国》也不例外。笔墨所及,时间跨度从远古到当代,每个篇章都流动着历史的烟波,每棵树木都满载着岁月的记忆。这些树有的直接与历史人物息息相关,比如标题里就有人物的《秋风梧桐说项羽》《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沈公榕,眺望大海150年》《周总理手植腊梅赋》,还有一看标题就知道有故事的《华表之木老银杏》《死去活来七里槐》《中华版图柏》《铁锅槐》《百年震柳》《一棵怀抱炸弹的老樟树》《燕山有棵沧桑树》《带伤的重阳木》……他笔下的树也迥异于欧美自然文学的写作传统,传递出中国传统文化滋养下浓郁的家国情怀。在《华表之木老银杏》中,他一开篇就写道:
天安门前的华表庄严华丽。其演变过程颇有深意。在古代,最早是公众场合的大立木,民众有什么意见都可刻之于上,称为“谤木”;后来立于通衢及邮驿之处有指路之意;再后来立于皇城外,上卧神兽,有监督王命和政事之意。总之,立一木而观天下,申正义,明是非,鞭腐恶。公器在上,宏大庄严,关乎天下社稷。但这毕竟是一个静止的非生命之物。如果能在中国大地上找到一个有生命的华表,一株活的巨木,千年不倒,风雨无阻,静静地记善恶、写青史,那该多好。很庆幸,我们找到了,这就是山东莒县浮来山上的春秋老银杏树。
这哪里是要写树,分明是借树写史。在与老银杏相见之后,作者听这位“老朋友”讲了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涉及中国古老的成语、用典和戏曲故事,分别是“毋忘在莒”“庆父不除,鲁难未已”“捉放曹”,又和现代史上的毛泽东、蒋介石、陈毅有所牵系。梁衡先生曾先后四次造访老银杏,都是为了访这树上的故事。其中第三个故事是讲陈毅怎样在树下惩治背信弃义之徒。作者写道:“人心难免有一念之变,但总是来回反复便为不义。正当民族危亡之时,有一个人忘恩负义,叛来叛去,五次倒戈,实为史上之罕见。”此人名为郝鹏举,本为冯玉祥旧部,一叛冯投蒋,二叛蒋投汪,三又叛汪投蒋,第四次倒戈是起义投诚共产党,不料,当国民党军队开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郝错判形势,又生叛心,重新投靠蒋介石。陈毅闻讯震惊,发起攻击,活捉了郝鹏举。这个故事跌宕起伏,读来引人入胜。当这个背信弃义之徒被击毙的一刻,作者写道:“山上的老银杏远远听见枪响,长叹一声:事不过三,郝鹏举已经五次倒戈,天理难容。说什么‘千年银杏应知我,当时我就知你心不善,果然今天有此恶报。”行文至此,老银杏直接“开口”说话,读来酣畅,人心大快。这不正是作者开篇“立一木而观天下,申正义,明是非,鞭腐恶”的生动写照吗?梁衡先生在写作上一直强调要写大情、大理和大义,连他笔下的树也无一例外地体现出这样的价值取向,我想这与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深植于心的儒家文化传统与心灵历程有关,也与他新闻人的出身背景有关。他走向广阔大地的脚步从未停歇,时刻将目光投注在时代、人民、社会与心灵之上,表达他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的看法。
又想起视树为生命伴侣的安妮·拉巴斯蒂。与拉巴斯蒂为自然代言并从中寻求生命定力的视角相比,梁衡先生的视角更富有东方文化中敬天悯人的气质,这两种视角显然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与人文底色,但无论东西方,人与树在精神上的相通却是共同的。梁衡视树为平等的朋友——这位沉默的智者穿越漫长的时空,泰然地注视着变化万千的世道与人心,在孤寂中挺立,等待着与后世、后人的相遇。《树梢上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梁衡先生抱着古树的照片,照片中的他表情愉悦,完全是见到老朋友、旧知己的样子。他写道:“我总觉得,树与人是平等的,它和我们一起创造历史,记录歷史。所不同的是,它远比我们长寿,在文字、文物之外可以为我们存留一部活的人文史。”
近年来,梁衡先生提出了“人文森林学”的命题,倡议重建人与森林的文化关系,并身体力行地投身其中。这当然与梁衡先生一直以来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的理想相契合,但在我看来,《树梢上的中国》留给读者的文化价值、精神价值已远远超越了这个倡议本身,它承载着一位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记录了这个时代对无言之树的景仰,因为“无论是朝代更替,人世变幻,还是自然界的寒来暑往,山崩地裂,都静静地收录在树的年轮里”,它在“静静地记善恶”。它也让人警醒:无论面对阳光还是风暴,人,都应该像树那样顽强地站立着,哪怕沉默。
因为,树,在注视着我们。
(作者为《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