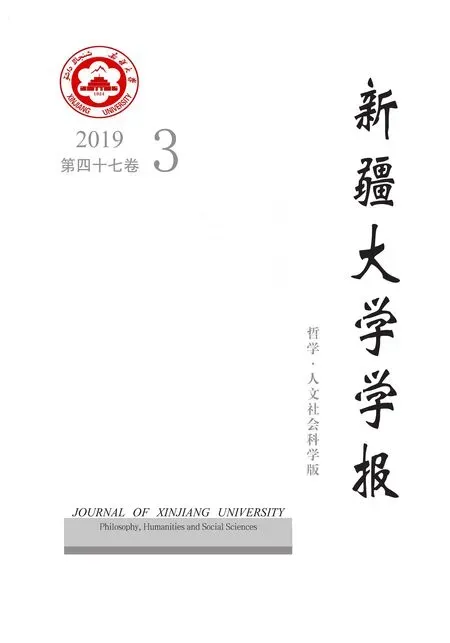马仲英第二次进入新疆相关问题研究*
黄祥深
(三峡大学民族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马仲英是中国西北近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学术界对他的关注度很高①主要研究成果:王希隆《马仲英赴苏及其下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84-88页;王希隆《再论马仲英赴苏及其下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52-55页;吴忠礼《“尕司令”马仲英其人》,《回族研究》,2004年第3期,第46-54页;袁第锐《略谈对马仲英的历史评价问题》,载余骏升主编《西北文史资料学研究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4-222页;丁明俊《马仲英事变对西北民族关系的影响》,载《丁明俊回族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48-266页;郭胜利《马仲英述评》,兰州: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但已有成果对马仲英部“三十六师”番号的获得;马仲英第二次进疆的时间;马仲英与苏联、日本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语焉不详,这不利于客观、完整的认识马仲英。文章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以上几个问题,进一步展开探讨,求教方家。
一、马仲英部“三十六师”番号的获得及影响
1928年,马仲英在西宁起事后,转战甘宁青三省,最后率众退居到甘肃酒泉、安西的一隅之地。在进退两难之时,恰逢哈密起事队伍领导人和加尼牙孜派遣尧乐博士到甘肃寻求马仲英支持,希望马仲英进疆援助哈密起事队伍抵抗新疆省军的“围剿”。马仲英为了扩大所部势力,立刻响应这一请求,于1931年5月率部突袭新疆,与哈密起事队伍联合围攻哈密,占领镇西,取得瞭燉之战大捷,但马仲英也在此战中身负重伤,不得不率部撤回安西。
马仲英第一次进疆时,所部没有番号,名不正言不顺,“乃假甘、青、宁三省联军总司令名义,谬称奉蒋总司令命令来新主持一切”[1]62。时任新疆省主席金树仁称马仲英为“马匪”,并向国民政府报告:“该匪蹂躏三省,残杀淫掠,踪迹所至庐舍为墟,民无孑遗。盘踞河西,勒捐数百万。”[1]62在金树仁眼里,没有番号的马仲英部俨然就是一支“土匪”队伍。马仲英显然也意识到部队没有番号就没有号召力,无法名正言顺的征收军粮、壮大实力。
(一)马仲英部如何获得“三十六师”番号
对于马仲英部“三十六师”番号的获得过程,各方史料记载不一。马仲英部的军需处长予扶载,“当青海军正整编马仲英队伍为其一个旅时,马仲英的旧属、陕西人士张良臣正在为马仲英队伍的番号问题加以活动,最终由西安行署批准准予马仲英第三十六师番号”[2]34。曾任马仲英部政训处主任的杨波清称,“1932年,马仲英经其亲信赵福臣在内地奔走活动,弄到一个新编36师的名义”[3]195。刘应麟称,“马步芳曾报请蒋介石将马仲英正式收编,蒋即照准,编为中央陆军暂编三十六师”[3]215。尧乐博士在其回忆录中记载“民国二十年(1931)六月初,我才走到河西第一大城——肃州,当地驻军是骑兵第三十六师,师长是大名鼎鼎的马仲英”[4]83。今人著作《新疆简史》①参见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第3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4页。和《民国新疆史》②参见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0页。都认可了尧乐博士的说法。
在这四种不同的说法中,尧乐博士的记载不符合史实。在马仲英第一次进疆失败退回甘肃安西之前,马部不可能获得“三十六师”的番号,这可以从马仲英第一次进疆仍以自封的“甘宁青三省联军总司令”得到证实。而刘应麟的说法与后来马仲英就任师长时,遭到青海军马步芳的诘问相抵触。马仲英退回安西时,青海军试图将马部收拢,遂封马仲英为青海军的一名旅长。当青海军得知马仲英获得“三十六师”番号时,就此事电探马仲英,质问“二职将孰就”,马仲英复电表示“仍就青海旅长之职”[2]34。可见,并非马步芳促成此事。
杨波清是护送“三十六师”关防到马仲英部的亲历者,在杨氏的回忆录里对赵福臣也有详细的记载。杨波清称,“赵福臣是马仲英的亲信,对马仲英的大政方针起着决定性作用。赵福臣人称赵旅长,大约是第一次变乱时的官衔,为人开拓大方,有些江湖气。是一位辈数很高的哥老会成员,与西北的一些杂牌军队有联系,他在内地的活动主要靠这些关系”[3]196-197。赵福臣还携带大宗款项到天津,帮助马仲英“潜购军火”[1]29。可见,赵福臣是马仲英对外联络的得力助手。董汉河在研究此事时也称,“马仲英第一次进疆失利后退回甘肃,当时落居酒泉的赵辅臣(应与赵福臣是同一人——笔者注),系国民军故人,与马仲杰交往密切,自愿去西安杨虎城处为马仲英活动,杨虎城正想在甘肃培植势力,便报请蒋介石,任命马仲英为国民军第三十六师师长”[5]。显然,杨波清的记载较为可信,予扶的说法因未能得到其他资料应证,只能存疑。
(二)“三十六师”番号对马仲英部的影响
这个番号对于马仲英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马仲英部获得正式番号后,即借用此名义加紧收罗人马,在酒泉整训军队,“成立教导连,自任连长,积极训练青年干部,淘汰旧式军官,军威为之一振”[2]34。一些文人政客,如曾任过县长的何铸九、高等法院院长苏子俊、进步青年苏继善等,甚至还有土耳其人凯末尔也都参与其中。③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4页。此时的马仲英“大设筵榻延揽门客,凡军政教赋闲或不得志人员,不问同教与否,甘籍与否,倘来附从,一律收容,又广招青年壮年,加以训练”[3]182。马部势力迅速扩大,为他第二次进疆奠定了基础。
国民政府授予马仲英部“三十六师”番号,表明国民政府承认这支武装力量存在的事实,其实质是为了牵制青海马家军势力和新疆省军。对于国民政府而言,给予马仲英部一个番号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国民政府不负责马部的给养,也就不管马部的生存问题。对于马仲英来说,有“三十六师”的番号即表明所部脱离了“土匪”队伍,成为国民政府的部队,故马仲英就任师长后,派遣予扶到兰州、西安、南京等地陈述整编经过,向国民政府示好,他还表示“绝对服从中央,拥护政府之诚心”[2]34。予扶在内地活动迟至1932年12月才返回酒泉,而此时马仲英正积极筹划第二次进疆。
二、马仲英第二次进疆的时间
学术界对马仲英第二次进疆的时间认识尚不一致。首先须明确的是,马仲英第二次进疆指的是马仲英率领所部再次进疆,并非指马仲英第二次进疆的先头部队。学术界对马仲英第二次进疆的时间主要有四种说法:尧乐博士载“1933年元月,马仲英亲率主力部队自酒泉西进,一路顺利无阻”[4]147;予扶载“1933年3月,马仲英率领亲自训练了一年余的战斗兵进疆”[2]35;宫碧澄称,新疆‘四一二政变’(发生于1933年4月12日——笔者注)后,“马仲英又进入新疆”[6];吴蔼宸称,“金(指金树仁——笔者注)已辞职(发生于1933年4月——笔者注)下野,马在途中殆未知之”[7]。笔者将以上四说简称为 1933年元月说、1933年3月说、1933年4月说。
笔者在查阅相关史料时发现《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收入了一封马仲英致行政院的电文,标题是《马仲英为新省民变日益扩大请派其入新抚靖致行政院电》,时间为1933年4月24日,电文称:“仲英迫于目下时势之严重及民意吁请之恳切,大难当头,势不容缓,故为尽军人之天职与报效党国起见,拟请赴新招抚靖难,期收桑榆之效。尚祈钧座迅予明令,俾仲英早日起程,则亡羊补牢,事或有济。”[8]这封电文明确揭示,4月24日马仲英尚未离开甘肃驻防区。奉命到新疆办理党务的宫碧澄在安西也见到了马仲英,他的记载更为详细,“到安西时,见马仲英的马队约4700 余人直扑哈密。同年5月5日,马仲英也亲率特务营等部队三百余人跟进。事前又邀宫碧澄谈话,劝其随军入新,宫表示:师长不奉中央命令,迳向新疆作军事行动,系环境使然。本人乃奉中央命令而来,不敢自由行动”[9]3238。可见,宫碧澄的说法与马仲英发给行政院的电文得以相互应证。
1933年4月20日,马仲英令其弟马仲杰先率骑兵一团开向哈密。5月17日,新疆省方突然接到古城驻军黎海如报告,马仲杰已抵哈密,“并贴有汉维文布告,仍系反对金氏专政为词”[9]3239。金树仁下台后,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刘文龙、临时边防督办盛世才的联衔布告也称,“金氏出走后,肃州马仲英又兴兵攻新疆”[9]3264。以上史料充分证实,1933年元月说、1933年3月说、1933年4月说不符合史实,马仲英第二次率部进疆的时间应是1933年5月。
三、马仲英与苏联、日本和国民政府的关系
(一)马仲英与苏联的关系
1933年5月,马仲英攻克奇台后,与所部人员谈到盛世才、张培元以及新疆军政上的一系列问题,他希望与苏联的外交机关取得联系。马仲英认为,“新疆远处中国西陲,与苏联几千里国境毗连,只有与苏联搞好关系,才有最现实的意义”[3]204-205。马仲英找到几位懂俄语的人与苏联驻阿尔泰领事馆接洽,他派遣马赫英和精通俄语的惠达山(原名惠树德,陕西米脂人,北京俄文法政学院肄业)前往苏联领事馆联系,但由于马仲英在滋泥泉战役中失利,惠达山投靠了盛世才,这次联络没能成功①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5页。。予扶称:“当时由于莫斯科的政策及日本势力北进与苏俄畏惧日本关系,所以苏联对马答复要有事实表现后再决定支持,同时谣传马有亲日嫌疑,所以未成事实。”[9]3407虽然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但马仲英与苏联的联络未能取得成功则是事实,这也导致此后马仲英遭遇新疆省军和苏联红军的联合进攻。
1934年1月,马仲英围攻迪化城,他认为盛世才没有援军,迪化终究会被他攻克,但是他未能料到,盛世才已经与苏联达成协议,苏联派遣以“阿尔泰军”名义的红军从塔城进入新疆。马仲英不敌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苏联红军,不得不退往南疆,苏联红军和新疆省军尾追其后“双方保持一定距离但不交火”[3]218。马仲英率部到达焉耆后,曾对斯文赫定的司机说:“北军如果没有俄罗斯人帮助的话,决不会把我赶出乌鲁木齐、达坂城和吐鲁番的。要我的部队顶住扔炸弹像下雨似的飞机、装甲车和强大的炮队是不容易的。”[10]
苏联红军追到巴楚后,即停驻在巴楚,未继续追击马仲英。苏联停止追击马仲英是为了保存马仲英部的实力,因为苏联要将马仲英“预作将来牵制盛世才的一步棋子”[9]3403。苏联学者达林也认为,“苏联政府赏识马氏的才能,并认为他是苏联在回权区域活动的一个有用人材,因此极希望保全他以供将来之用”[11]。苏联对马仲英的态度,符合苏联对新疆的政策,苏联希望它的“后门”能够保持稳定的状态,甚至在边界之外有“一个稳定的、亲苏的新疆地方政权,使新疆成为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屏障”[12]。一旦盛世才政权不再对苏联那么“友好”,苏联就需要有另外一个人物来牵制盛世才,马仲英以及还具备一定战斗力的“三十六师”就成为了苏联的预选对象。
马仲英为了保存部队的实力,同意接受新疆省军的改编,而他在所部联共党员的劝说下,下定决心赴苏。马仲英对他赴苏解释到:“我们这次出关为的是反对金树仁封建统治,解除新疆各族人民的痛苦。新疆的情况与口内不同,几千里国界与苏联毗连,各方面都需要同苏联打交道。盛世才依靠苏联打败了我们,萨比提依靠英国被我们打垮,可见苏联是真心帮助人的,英国是欺骗人的。我们要不依靠苏联,也要上英国人的大当。这个现成的事例,我想大家已经是看清楚了的,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13]马仲英赴苏之初受到了苏联方面的优待,但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最终导致马仲英客死他乡,留给后人不解之谜。
(二)马仲英与日本的关系
马仲英与日本的关系遭到部分学者的误解。民国时即认为马仲英是亲日的,因为其军队里有日本的“间谍”,更有甚者认为马仲英是日本侵略新疆的“先锋”,是日本帮助马仲英攻击盛世才的①参见郭维屏《南疆事变与帝国主义者侵略新疆之分析》,《西北问题研究会会刊》,1934年第1期,第55页。。又有人认为“此次马仲英部所领导的回民变乱,实际上即是受日人阴谋煽动的结果”[14]。当时还传言“马仲英军队在日人领导之下并有土耳其军官参加作战,拟建立一独立国家”[15]。在全国抗日救亡的大背景下,马仲英被世人冠以“亲日”的骂名。笔者认为这个骂名与事实不符,流传这些说法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
首先,马仲英部队里存在日本人这一事实,极易引起民众的误解。马仲英部队确有被称之为于华亭的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在马仲英的队伍里到底传达出一种什么信号?已有资料揭示于华亭是在酒泉被马部所获,由于没有身份证明,马部并不知道他是日本人,又因其熟悉电报业务,马部也就利用他作电务工作。②参见周东郊《盛马之争与其结果》,载甘肃省图书馆书目参考部编《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新疆分册上),兰州:甘肃省图书馆,1985年,第332-333页。纵使于华亭是日本间谍,仅凭他在马部工作的“证据”还是难以断定马仲英是亲日的。马仲英的部队有不少联共党员,但研究者不会因此就认为马仲英在甘肃时是亲苏的;马仲英队伍也有很多哥老会成员,据称马仲英本人在甘肃陇南时“入了帮会”[3]11,但这也不能认为马仲英的队伍就是帮会组织的队伍。马仲英队伍人员组成十分复杂,有联共党员、有土耳其人、有日本人,这些都是马仲英为壮大其队伍而不加选择地吸收进来,并不能将其作为判定马仲英立场的主要依据。
其次,盛世才与苏联的舆论宣传给民众造成误导。盛世才成为新疆临时边防督办后,为了消灭马仲英势力,积极利用新疆民众希望和平的愿望和全国抗日舆论的宣传,大肆渲染马仲英是日本的“走狗”。盛世才称,“日本帝国主义曾嗾使其走狗马仲英率匪军侵入新疆,企图把新疆沦亡为它的殖民地”[16]。而苏联担心日本侵略中国后会进一步威胁它的利益,马仲英队伍有日本人这一事实,促使苏联人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大肆报道马仲英是日本的“代理人”。这些宣传误导了民众对马仲英的认识,当然,也有一些民国学者并不赞同这种说法。周东郊就一针见血的指出:“盛世才为了他政治上的便益,经常指栽马仲英系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动,侵入新疆,一般人因莫知马部的真像(相——笔者注),到现在还有为此宣传所惑的,实际马氏当时匪(非——笔者注)特与日本毫无关系,反之他的部下谋士多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③参见周东郊《盛马之争与其结果》,载甘肃省图书馆书目参考部编《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新疆分册上),兰州:甘肃省图书馆,1985年,第332页。今人也指出:“土耳其人凯末尔、日本人于华亭在马仲英于滋泥泉失败后,即潜藏离去,未再继续追随,根据这种情况来看,可能马仲英尚未被帝国主义所利用。”[17]
事实上,马仲英曾发表过抗日的主张。马仲英在驻守酒泉时招集酒泉各界代表开会,表现出“抗日”的态度,他说:“如果调我去抗日,我即率领全军开赴前线,奋勇杀敌。”他对马占山的英勇抗日表示赞扬,在看演马占山的话剧时,带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3]176马仲英的抗日主张一直延续到他赴苏时,在苏联期间他仍告诫在新疆的部属,“准备抵抗大计,消极会当亡国奴”[3]176。1937年,马仲英还指示所部“只在和田留一个营或一个团的兵力,其余全部出关抗日”[3]176。
(三)马仲英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马仲英率部在西北与各方势力对抗,但他在第二次进疆后与国民政府取得联系,一定程度上认同国民政府的权威性。马仲英接到“三十六师”师长关防后,更积极地向国民政府靠拢,他派吴英琪到南京拜见蒋介石并汇报政情,吴英琪又奉蒋介石之命“往晤马仲英”[18]。金树仁下台后,国民政府派遣中央大员黄慕松进入新疆“宣慰”,试图掌控新疆政局,而马仲英进军新疆也意在控制新疆,故马仲英的行为极可能搅乱新疆局面,打乱国民政府的布局,因此国民政府“严令制止马部前进,并派胡宗南跟踪监视”,警告他“如铤而走险,即自取灭亡”[1]9。随着黄慕松入新“宣慰”以失败告终,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马仲英第二次进疆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
黄慕松仍在新疆“宣慰”时,马仲英曾派遣赵福臣向蒋介石报告新疆事变的经过,并声明三点:“确未联络共产;并未分回汉畛域;惟有服从钧座,以固藩篱、靖地方”。蒋介石“对之训勉剀示”,并亲笔函致马仲英,称:“子才师长勋鉴,赵代表来,携到手折,并晤谈一切,获悉公忠体国,融洽汉回,大义皎然,至深嘉慰……以兄明达有为,自必不肯盲从附和,与通声气,至若汉回,则更一家骨肉,亲爱有素,中央方面,倚兄为干城,尤无妄加挑拨,贻祸边陲,致强邻生心,召寇自焚之理,故经迭有以此二事相告,中皆一笑置之,从不置信。”①参见《新变消息两歧》,《申报》,1933年7月17日,第10版。蒋介石在回信中明确表明了对马仲英行为的态度。马仲英回电称:“始终服从中央,效力党国,而只尊黄使命令……至仲英则驻兵哈密、镇西、托克逊、焉耆、吐鲁番、鄯善、库车等区,听黄使之调度,以资效力,决不为个人地位而使中央有西顾之忧。”②参见《马仲英服从中央》,《大公报》,1933年7月30日,第5版。可见,马仲英为了能够长期占据新疆,表现出服从国民政府领导的一面。
1933年8月,国民政府又派遣罗文干进疆,马仲英对罗文干也表示“服从中央,结束军事,维持和平”[19]。罗文干调处新疆局势失败后,国民政府于1933年9月27日改组新疆省政府,并任命马仲英为新疆省政府委员。③参见《行政院决议改组新疆省政府》,《申报》,1933年9月27日,第6版。这是国民政府利用马仲英牵制新疆各方势力的举措,也是国民政府承认马仲英入疆合法化的重要标志。
在马仲英积极图谋攻取迪化时,他已听闻喀什局势不断恶化,遂派所部赵参谋前去探明,并就此事致电国民政府称:“哈什(即喀什——笔者注)方面等部因受英人诱惑,有独立倾向,自职部赵参谋回后,近复派委员审慎调查,如有证据确情,再电呈报,但蛛丝马迹,不可不早为防范,以免东北之继。”④参见《马仲英服从中央》,《大公报》,1933年7月30日,第5版。此举表明,马仲英十分关注喀什出现的危机,当马仲英部退至喀什时,消灭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伪政权,喀什的英国人认为此举“可视为中国政府之重要胜利”,因为“东干部落自认为中华民国作战”⑤参见《南疆之变》,《国闻周报》,1934年9月。。
马仲英积极靠拢国民政府,目的是利用国民政府的权威来加重自身在新疆的砝码,以便争夺新疆的统治地位,他不时地向国民政府汇报新疆局势,借此表明自身在新疆占有一席之地。在新疆复杂的局势下,国民政府与马仲英二者互相利用,国民政府先将马仲英部合法化,此后又将马仲英进疆合法化,这显然是国民政府欲利用马仲英来牵制新疆省当局,也是在国民政府尚无法直接控制新疆的情况下,不得不利用实力派人物互相牵制的一种无奈之举。而马仲英借此机会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试图长期占据新疆。
四、结 语
马仲英第二次进疆是在金树仁下台之后,故他失去了进疆是为“反对金树仁封建统治”的“正当理由”,其在新疆扩张自己势力的意图被充分暴露出来。由于马仲英与苏联交涉无果,失其援助,加速了他在新疆的失败。苏联和盛世才大肆渲染马仲英是日本的“代理人”,混淆视听,误导舆论,其实质是双方为自身利益而进行的一种舆论造势。依据笔者目前掌握的史料,无法断定马仲英是“亲日”分子,马仲英在一段时间内还积极靠拢国民政府,表现出愿意服从国民政府领导的态度。他以“三十六师”的番号在新疆进行军事活动,目的是为了凸显这支部队的正规性,提升号召力,借以壮大势力,通过不断强调为“中华民国作战”来获得国民政府对其在新疆活动的认可,但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