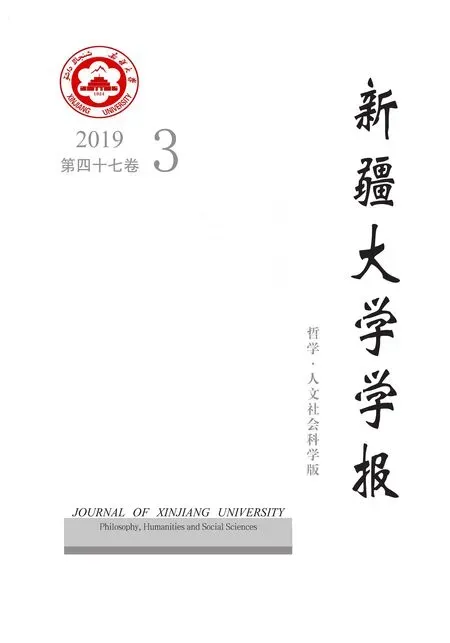差异、误读与浅层搁置
——现代性知识话语论域中文人画研究的“别样”异声*
佘国秀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20世纪初西方汉学家与艺术史家纷纷致力于中国艺术史的构建,运用启蒙理性催生的现代性知识话语言说和阐释中国艺术。文人画由于其特殊的文化身份与形式特征与西方学术话语模式产生了表层通约性。大多数西方学者过于推崇表层通约性,而忽视了对深层不可通约性的严肃思考,缺少面对差异性对话与交流的学术探索精神。美国学者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在东西方艺术交流的宏大视野中,面对文人画这一西方学界推举的范型,做出了不同的解读与建构,他侧重文人画与“空间”标准的不可通约性,强调文人画与标准的对立,具有很强的独立探索精神,但他忽视了被其认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标准”自身的适用范围,从而在文化误读中走向了学术偏执。
一、厄内斯特·费诺罗萨与文人画
厄内斯特·费诺罗萨毕业于哈佛大学,1878年在爱德华·S.莫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教授的推荐下到东京帝国大学担任哲学、逻辑学和美学教席。由于在哈佛大学期间被波士顿美术馆举办的一场“新艺术运动”吸引,并开始辅修美术,费诺罗萨终生对美术具有浓厚的兴趣,在日本期间,费诺罗萨醉心于日本传统美术,同时研究中国美术。1906年,费氏用三个月的时间将其多年的研究与实践成果写成了铅笔手稿《中日艺术源流》(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1912年由其遗孀玛丽·费诺罗萨(Mary Fenollosa)代为出版。《中日艺术源流》是英语世界最早的东亚艺术史著作。
费诺罗萨在建构中国艺术史的过程中极力贬抑文人画,将文人画视作庸俗、腐朽的儒家程式化“游戏”,在艺术自由精神和“空间”标准的度量下褫夺了文人画的艺术资格。甚至在致力于日本民族美术复兴事业时,被誉为“日本艺术菩萨”的费诺罗萨企图通过日本民族美术复兴中文人画的“不在场”,消弭其对日本绘画艺术的历史影响,此种学术偏执可见一斑。日本艺术史家大村西崖(1867—1927)在《文人画之复兴》一文中,针对文人画的湮没曾谈到:“此无他,盖明治十一年以来,我东京大学聘来讲哲学之美国哈弗大学出身之俊才,名曰意尔涅斯德·弗兰昔司科·费那罗沙(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学士,深好美术,初览浮世绘(日本一种俗画),览赏之眼渐高……所可异者,费那罗沙学士之眼识,全不能领会文人画之雅致。因此,画运振兴,文人画毫不包含在内,且以为非美术,竟使最近三十余年世之人,殆不知有文人画之存在。决非过言。缙绅之士赏爱美术者,至有‘文人画亦为美术耶?’之问,岂不可浩叹!”[1]17-19费诺罗萨的学术偏执在一段时期内遮蔽了文人画在日本绘画中的地位与价值,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一文可谓对费诺罗萨艺术史建构的解构和对文人画在历史与学术层面的“返正”。
2004年3月,艺术史家方闻(Wen C.Fong)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举办的“第十四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上做了“东方艺术、西方面貌”的演讲,其间提到:“1882年,醉心于日本传统艺术的美国人费诺罗萨在东京讲演‘艺术真理论’(‘True Theories of Art’),极力反对明治初年日本绘画全盘西洋化。他呼吁日本人在日本画(Nihonga)的基础上建立‘东方’艺术。他相信这种‘东方’艺术不但‘会成为日本艺术主流……(并可)影响全球’。可是,费诺罗萨极不喜欢受中国文人画影响的日本文人画(bunjinga)。他所倡导的日本画,是要利用西方透视、明暗法、造型技巧来描绘日本题材,画出日本品位。”[2]费诺罗萨将西方知识性话语的科学、理性规范作为衡量一切艺术的普世标准,忽视东西方艺术的差异性。在建构中日艺术史的过程中,运用其所认同的唯一正确的艺术发展之线——“空间”(spacing)提领中日艺术,由于“空间”标准在解释文人画上的“失效”,致使其极力贬低文人画的艺术身份,甚至试图抹去以中国文人画为宗的日本南画的发展踪迹。尽管费氏以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动态视野建构中日艺术史,兼以哲学家的视角切入,运用东西文化比较的方式,将中日艺术(包括朝鲜艺术)视为东亚艺术共同体的不可分割部分,并主动警惕“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但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其极力摆脱的偏谬中。面对差异性所造成的误读,费氏无法对西方绘画偏于建筑、雕塑的空间意识与文人画由书法笔势形成的空间意识进行深层考量,只是用西方普世性的标准衡量对象,而不考虑标准的适用范围,缺乏不同文明间对话与交流的对等意识。
应该指出的是,费氏建构中日艺术时怀着他国“注视者”对日本民族美术的亲善与狂热。他的初衷更多的是建构日本艺术史,但由于日本的学术传统不能不提及中国艺术,正如英文版《中日艺术源流》的代序中所说,将中国艺术纳入他的建构框架“和中国艺术本身相比,更多地是因为中国的文学资源”[3]xxix。英文版《中日艺术源流》两册,共十七章。其中中国艺术史有八章(volume.1 五章,volume.2三章)。中国艺术作为东亚艺术的主体与日本艺术的源头地位多次被肯定。文人画在有关中国艺术的三个章节中出现:第二册第十章中国的理想主义艺术——北宋(Idealistic Art in China.Northern Sung)、第十一章中国的理想主义艺术——南宋(Idealistic Art in China.Southern Sung)、第十五章现代中国艺术(Modern Chinese Art.The Tsing or Manchu Dynasties)。在这三章中,费氏以少量篇幅提及文人画(在日本艺术史部分文人画“不在场”)。从“传统儒家学养的标签”,到整个文人艺术批评的“蠢话”实质;从无任何空间感和想象力的僵化程式,到诗、书、画结合朦胧画法的幼稚墨戏,费氏用所谓的单一“空间”审美标准评判文人画,在这把科学尺子的度量下,文人画是高度特征化与形式主义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绘画艺术衰退的“罪魁祸首”。但与费氏的学术偏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三十年代美国艺术史学者卡特·达格妮(Carter.Dagny)在其《中国艺术辉煌五千年》(China Magnificent Fiv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Art)中指出:“以西方人的目光看待宋代南宗山水画,它们是难以捉摸的,缺乏西方感觉世界中的透视。但是,中国人很早就有关于透视的完美阐释理论,它们使用的透视类型是选择的结果,并非忽略透视。毕竟透视绘画是在二维平面上再现三维,二者间的协调是不可避免的。”[4]她从中西透视的差异性出发,说明文人画(南宗)空间表达的有效性与独特性,体现了较为公允的学术立场。在现代艺术的结尾部分,费氏不无偏激地说:“文人画的空洞乏味像癌细胞一样已经吞噬了所有健康的机体组织”[3]540,甚而用“我们的高标准”(our high standard)判定“自明代早期以来,除了晚明和清早期的瓷器外,中国就已经没有伟大的艺术了,进而可以说,自宋和元早期以来,中国就已经没有伟大的艺术了”[3]541。费氏小心地警惕“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倾向,试图在带有个人研究偏好的前提下给予西方和东亚艺术平等的关注,却不给予同等的尊重,这并不利于其建构平行比较与普遍联系的艺术史模式。评判文人画时所依据的“我们的高标准”(our high standard)从深层反映了费氏无法规避的优势定位:自我优于他者,以及将西方文化价值普世化的倾向。反观费氏对文人画的浅层搁置和边缘化处理,可谓“小中现大”,别有洞天。
二、文人画的“儒家文化标签”
面对异质文化时,跨文明接受者往往有三种基本的接受态度:狂热、亲善、憎恶。与其对日本艺术的狂热和沉迷相比,费诺罗萨是20世纪早期建构中国艺术史的西方学者中对文人画儒家文化身份持憎恶态度的第一人。1904年,英国汉学家波西尔(Stephen Wotton Bushell,1844-1908)出版的《中国美术》(Chinese Art)是英语世界第一部中国艺术史。在书中,波西尔尚未使用“文人画”这一概念,但却对知识精英阶层的士大夫绘画大加赞赏。1918年,美国古物收藏家、鉴赏家福开森(John C.Ferguson,1866-1945)在《中国艺术大纲》(Outlines of Chinese Art)中对中国山水画(所选范例为文人画)中的记忆性复现与想象性重构充满欣羡之情,二者都将此类绘画的精神取向与道家、禅宗相联系。费氏给文人画贴上的“儒家文化标签”是从画家身份进行勘定,本是无可厚非的。1926年,滕固界定文人画时就曾说:“……自古及今的作家,可说没一个不是士大夫。不过我觉得这士大夫画一个言辞,很可以帮助了解中国绘画发展的特质,我的意思,中国绘画上某时期在宗教影响下或在帝王影响下,作者身份是否士大夫,也必受宗教或帝王的牵制。独是士大夫自己占有了后,才得充分发挥士大夫精神,才做了士大夫社会的华表。”[5]但这一标签却成为他不加分析地否定文人画艺术价值的决定性标准,这其中包含了他对文人画特质的种种误读。
首先,费氏对画家“文人”身份的偏见。在他的理解中,文人就是接受儒家教化的知识阶层,正如他在“现代中国艺术”部分将西方现代话语对中国传统文化解释的无效性归因于儒家文化的腐朽和对自由的扼杀,用西方话语模式全面否定儒家思想文化体系,进而否定了文人、儒生这些传统文化的“卫道士”。费氏构建中国艺术史时,运用“空间”这一“高级标准”来衡量中国绘画,却在文人画的评判上使用了针对画家和画作的双重标准,通过对画家身份的否定进而否定画作。在东西文明交流的宏大视野中,面对“杂语共生”的多元文化,他追求“同”,却无法容忍导致自身话语规则无效的“异”,用意识形态标准替换了审美标准。费氏对文人的定位是正确的,生活于封建时代的士大夫阶层本身就是中国道统文化中的一分子,隶属于以儒家为主的思想文化体系。从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说来看,“……种族是艺术的‘内部主源’,而环境则是艺术的‘外部压力’。而时代则是‘内部主源’在‘外部压力’下发生作用的‘倾间’。在丹纳的体系中,时代的作用是在时间上划定种族生存和环境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一个概念”[6]。文人画家不可能脱离所处的时代,即使是他们之中的高人、隐士、山人,也都大多经历了从入世到出世的选择。如果单从文人身份来界定,从汉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画家都是文人,都是儒家思想文化体系中的士大夫。那么,为什么不将所有的绘画都称为文人画呢?这其中除了画家身份之外,还有风格因素和艺术史话语方式。儒家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使其并非铁板一块,儒家的礼仪道德维系了个体外在世界的秩序与规则,道释信仰则维持了个体内在世界的平和与安定,文人士大夫是儒生出身,但并不否认其道释信仰的共在,儒家的伦理生活与道家的超自然观念结合,构成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价值追求。费氏对儒家文化单一、片面的理解是其一。其二,他应当从绘画风格入手,抓住文人画中的线条等要素进行分析,而非由画家身份否定作品的艺术性。与费氏同一时期的西方汉学家、艺术史家认为文人画具有道家和禅宗倾向,对其所体现的艺术自由精神大加褒扬。两种方式一个是作者中心论,一个是作品中心论,判定的角度不同,结论自然相异。美国艺术史家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2014)就曾指出“文人画家所持的绘画理论反映了他们的儒家背景”[7]99,并将文人画称为“儒家文人画”,高居翰此时的界定同费氏的标准是一致的,但在分析文人画时,高居翰则以绘画风格因素为主,并未使画家的文化身份特征裹胁作品的艺术价值。
其次,费氏将自由精神与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完全对立。他认为儒家最反对表现人的自由的艺术形式,因此儒家的文人画毫无想象力与原初的创造力,是“纯技巧”。费氏夸大了自由精神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无法理解文人画所体现的艺术自由精神。他用西方文明的自由标准考量中国艺术,殊不知文人画的自由精神体现在观者与画家超越时空的对话与交流中。文人画体现的正是个体自由精神的驰骋,科学分析思维无法诠释其中的神妙,只有运用直觉,以心智推动想象,才能领悟。视觉与再现,直觉与表现在两种艺术体系中的统一性不能够简单替换。深谙中国文化的福开森(John C.Ferguson)在论及南北宗绘画时,只把二者当作山水画的两种基本类型,他指出:“中国画的真正微妙之处,基于人对天地之力量的从属地位。中国人不像我们那样自以为是宇宙的中心;他的上帝不是人格化的神。或许可用希伯来赞美诗人的话表达他的哲学:‘当我念及您的天国/您指间流出的作品/您任命的月亮与星辰/那么,人呢?/您留心的人是什么?’”[8]159“哲学思想和艺术灵感的这种结合,反映在中国人平静的生活中,他们的生活没有令人吃惊的剧变。在西方,科学的发明带来了这样的剧变:因为科学,人们发现自己不再是自然的奴隶,而成了自然的主人。中国人的精神则摆脱了物欲的重负而醉心于沉思。人不过是造物的很小一部分——他是暂时的——易逝的,而天地之道是永恒的。这种微妙的精神洋溢在每一幅山水画中。”[8]159-160儒家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体对家国、天下的责任与担当,并非扼杀个体的个性与自由,文人思想往往兼有儒、释、道的成分,文人虽身居庙堂之上,但心游天地之间,其精神取向是十分复杂的。“人文学者想要对艺术家的精神状态做出一个统一而正确的再创造和再现,这样的想法是无效的,因为艺术史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再现的形式。”[9]
费氏认为文人画是失去自由精神的“纯技巧”与造作的形式主义,也并不完全无理,可谓“只见一斑”。中国绘画的谱系式师资传授模式是子承父业,徒继师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10],继承和创新相辅相成,“各有师资,递相仿效,或自开户牖,或未及门墙,或青出于蓝,或冰寒于水,似类之间,精粗有别”[11]。当文人画的某种技法成熟后,便被追随者仿效,势必成为追捧的技巧,但不能因此将整个文人画等同于“纯技巧”。费氏所说文人画的形式主义与程式化,实则是对明清时期文人画成为审美主潮,被画界追随者所仿效的另类解读。他没有区分真正的文人画与充斥艺术市场的滥造之作,也未将艺术家与具体的社会情境联系起来,特别是忽视了明清画家被卷入艺术市场的重要事实,以其捍卫日本民族美术的偏执情绪武断地否定文人画的艺术价值,甚或造成文人画在日本民族美术中的缺席,因此才有了大村西崖在《文人画的复兴》中的唏嘘感叹。
文人画本为“词余”“墨戏”“诗极”,是文人适兴之作,抒写性灵,清标高格。文人以此酬唱赠答,不为市金。再加上文人画不受题材限制,人物、山水、花鸟无物不可入画,笔法、墨法、章法不受职业画法限制,任意挥洒,自成法格。无论从画家的创作动机、绘画的题材选择,还是画作的个性特征来看,文人画都体现了艺术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与费氏所强调的人的自由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它是儒家知识分子调适现实中失衡心态的“诗意栖居”,是超越视觉表象的文化心境的体现。而费氏以他所窥见的文人画历史中的“点”否定了“面”,用他理解的视觉表象遮蔽了文化心态,没有理解中国艺术的本质特征,机械地运用西方艺术的科学标准裁定文人画。从根本上说,他站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对立面评判依存于传统的文人画,艺术元语言的置换必然导致对文人画的曲解、误读与浅层搁置。
再次,费氏对临摹的误读。费氏对中国传统绘画的传移模写不甚了解,他以西方绘画的素描对应中国绘画的临摹,自然使临摹“相形见绌”。中国绘画具有谱系式的师资传授模式,前代大师的传世之作自然成为后学追随与效仿的对象。一般来说,传统中国画的学习经历临摹、写生、记忆画这样三个阶段,而临摹并不是机械复制。费氏简单的类比使临摹这一揣摩笔墨章法的学习方式与儒家保守的行为方式建立了必然联系。他认为“临摹”即为“转译”,就像诗人用本国语言翻译外国诗歌,文人画就是“转译”的产物,机械的“临摹”导致了根深蒂固的分类和幼稚的艺术评论。他的这一浅层比附也表现出对中国绘画基础知识的匮乏。“临摹古人名迹,得其神似者为上,形似者次之。有以不似原迹为佳者,盖亦遗貌取神之意。古来各家用笔用墨,各有不同,须于名迹中先研求如何用笔,如何用墨,依法对写,与之暗合,是为得神。若以迹象求之,仅得貌似,精神已失,不足贵也。”[12]费氏根据他所亲见的文人画“摹本”以及“摹本的摹本”,以看似实证的方式生吞活剥了中国绘画笔墨技法的基础训练,殊不知素描获得的是“形似”的技法,而临摹获取的是“神似”的气韵。谢赫六法中的“传移模写”是中国人评画的一个重要尺度,“传移模写”是“气韵生动”的基础。高居翰曾在其《图说中国绘画史》中将沈周仿倪瓒的《策杖图》与倪瓒山水画作比较,从而厘清常被人误解的中国画家的“仿古”训练是什么,这便是一个明证。
费诺罗萨给文人画贴上“儒家文化标签”,这一文化身份定位并无不妥之处,但他在文化比较研究中的自我“高级标准”暴露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本质立场。用自身的尺度衡量“他者”,以自身的类型缺位否定“他者”类型的存在价值,这无疑是盲目自信的文化沙文主义。他将文人画与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置于同一层面加以分析,混淆了身份标准与题材标准的界限,呈现出逻辑的混乱和内在矛盾性。费诺罗萨站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一个“言说”文人画“异国形象”的“他者”,赫然入目。尽管他在构建中国艺术史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但对待中西文化差异的武断方式,使他在力求折衷的建构中走向了学术偏执。
三、对“南北宗论”的全面否定
费诺罗萨认为文人艺术理论的代表“南北宗论”具有惊人的历史谬误,殊不知中国山水画的南北派与文人画的南北宗,尽管都有南北之分,但此“南北”,非彼“南北”。“……山水画实有南北二派的画法,北方人画山多用方笔、硬笔,南方人画山多用圆笔、柔笔;用墨、设色等也不同。这主要由于南北自然环境的不同。不同的自然环境在人心目中的反映,表现出来,便形成南北不同的画法。”[13]这是本来就存在的事实,南北之分包含了地域、笔法风格的丰富内涵;而文人画的南北宗则是董其昌辈为提倡文人画风,根据禅宗的顿渐之别,人为地拟构出来,并获得合法存在资格的。文人画家与山水画家、文人画与山水画交织在一起。费氏在尚未厘清两个“南北”概念的基础上,便对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进行解构,在概念的混杂、纠缠中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
第一,关于“南北宗”的命名。费氏说:“他(董其昌)给这一普遍的中国画派命名为‘南宗’,可能是因为中国山水诗和山水画起源于南方,这一传统可追溯至五世纪的陶渊明。”[3]525他认为,李思训、牧溪、马远、夏圭的北宗归属是由画院的传统决定的,“北宗”的提出是由于当时儒家势力强大的不得已之举。首先应该指出,在研究中国绘画史与中国文人审美观念变化上,“董其昌明确了正宗文人画派及其传承,把淡泊、超逸的水墨山水画定为正宗画,提高了文人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使文人画主宰明清画坛数百年之久。‘南北宗’还流传到海外,以致日本形成崇尚‘南画’的风气。”[14]但南北宗论的个人主观臆断与“崇南抑北”的倾向阻碍了绘画艺术的多元化发展,迄今为止,这还是一个处在争论中的问题。面对研究文人画无法回避的文人艺术理论,费氏仍然从否定儒家文化、否定文人与文人画的角度出发,过度夸大“南北宗论”的负面作用,无视其合理成分。从他对“南宗”命名的理解上可见他所出无据,董其昌提出“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15]677。南北宗的划分不是以地域,而是以笔法风格为标准。费氏用可能性的推断否定了文人画的立论基础。同一时期的福开森(John C.Ferguson)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很明确地指出“南北宗概念的渊源,即在于宋代两种笔法的根本分歧:强健有力的笔法与温和优雅的笔法。南宗、北宗不是地理的概念,而完全是笔法风格上的不同”[8]157。当然,与费氏存在同样误读的还有波西尔(Stephen Wotton Bushell),他在《中国美术》(Chinese Art)的“绘画”章节中也将南北宗与地域概念相联系,但他同时也强调了画法风格。
第二,南北宗画家的归属。费氏以科学、理性的视角看待南北宗画家的归属,他以京都高台寺的一幅王维山水画的山石皴法入手,断绝了王维与文人画的联系。他以地域为依据,参考画法规则,认为画家的归属存在矛盾,并且从审美趣味上将“北宗”也归入“南宗”。画家的流派风格归属原本就具有相对的模糊性,当时的画家如滕固所言有院画一派、纯粹文人画一派、还有“以文人画而参以院画体制的一派”,在南北宗的归属上模棱两可是难以避免的,董其昌的南北宗划分是其建构文人画理论的需要,他用规则与秩序将文人画放在了艺术史图式的相应位置。费氏用绝对清晰性原则衡量相对模糊的画家归属,再加上他对山水画“南北”之分与文人画“南北”之分的混淆,结果可想而知。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福开森的意见值得借鉴。他认为这两派间的区分可以忽略,只记住山水画的两种基本类型就足够了。美国艺术史家卜寿珊(Susan Bush)说:“在西方看来,艺术史就是研究艺术风格,这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定义,艺术史应当总是面临分类的问题。我们能找到同一地域作画的艺术家风格中的普遍共性。这甚至在整个中国都普遍存在,后来的画家基于同样的早期模式来确立他们的艺术。因此,从现代眼光来看,以地域区分画家存在一定合理性。”[16]294但文人艺术理论非常明确地指出南北宗“其人非南北”,费氏无视文人艺术理论本来的清晰界定,以西方的现代眼光检视文人艺术理论,没有探究不同文化模式的差异性根源,用普遍性理解否定特殊性界定,这也是异质文明碰撞中所遭遇的共同问题。费氏犀利的学术眼光无可否认,他对董其昌“崇南抑北”倾向所造成的绘画艺术多元发展受阻的状况认识十分到位。但他过度强调艺术的自由精神和个性主义特质,在精神领域中不断绕圈子,没有将艺术史建构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从而使他敏锐的洞见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费诺罗萨在建构中国艺术史时,对汉学家的文献研究和艺术史家的风格分析均持异议。他以哲学家的普遍联系思维,在东西文明比较中建构中日艺术史。全盘否定董其昌“南北宗论”,极力反对寄寓董其昌个人欣赏趣味的“崇南抑北”倾向,透见出他对艺术发展多元化的认同。但他却忽视了艺术要超出历史,首先要投入历史。他没有认识到在西方“缺类”的文人画潜在的身份认同和文化精英的精神归属感,只从权力表征的层面加以否定。“一个人的地位和他的文学素养,这在中国社会是举足轻重的,虽然是艺术之外的因素,却在最早定义文人画的时候起着重要作用。当董其昌把画家分为南北宗时,这些因素已经被编织进了中国艺术批评的肌理中——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到近现代还继续出现在中国的著作里。”[16]294费氏全面否定了构建中国艺术史无法回避的文人艺术理论,因此,他对文人画否定不是完全出于对“空间”感型的衡量,而是对儒家文化元语言的否定。
此外,费氏还指出了当时欧洲汉学家引用当代艺术批评的文献,作为评价古代艺术的“证据”,还在无意中加入了想象。这也体现出他对欧洲汉学家文献研究粗疏之处的积极反思。从总体上看,费诺罗萨对文人艺术理论的解构缺乏辩证否定精神,他解构的文人艺术理论正是建构中国艺术史的重要依据,脱离中国传统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空间”概念赋予中国艺术以历史形状,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西方现代知识性话语以科学、理性的眼光看待艺术,根据是否符合其话语方式与思维逻辑决定文人画能否进入艺术史场域的资格。
20世纪英语世界的绝大多数西方学者擢升与标举文人画的艺术价值,遵循中国文化传统,接受了董其昌的南北宗划分方法,使其成为艺术史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学者更看重异质文明碰撞时的表层通约性。通约性意味着趋同、和谐、稳定。20世纪初至20年代,战争和政治动荡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这一秩序惯常依赖的种种意识形态及其借以进行统治的种种文化价值标准也陷于一片混乱。科学好像已经衰退为贫乏的实证主义,目光短浅地忙于事实的分类;哲学在这样的实证主义与不堪一击地主观主义之间似乎已经四分五裂;形形色色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猖獗一时,而艺术则反映着这种茫然无措地状态”[17]。此时的西方学者,包括汉学家、艺术史家、哲学家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建立新的确定性。建构中国艺术史的西方学者更多强调中西艺术表层的通约性,通约消解了对立与对抗,获得了相对的确定性。毫无疑问,费氏也是其中一员。他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视野沟通了东西艺术,试图从宏观层面建立异质文明间的普遍联系。当他面对中国儒家文化体系时,外来的佛教艺术成为他运用“空间”标准建构中国艺术史的最佳切入点,虽然他部分涉及到外来佛教艺术本土化的问题,但却没有抓住中国艺术独一无二的表现方式,以至于在两种文化符码的对抗中轻易地消解了研究中国绘画无法绕开的“南北宗论”的历史价值。
四、对诗、书、画结合方式的浅层搁置
文人画“无声诗史”的出位思致以及书法性用笔构成其浑融的艺术格调。20世纪60年代高居翰曾说:“他们(文人画家)的诗、书、画活动交相作用,涵括面深广;书法家的训练帮助他们掌握画家所需要的笔法和图案感,诗的想象力又为他们提供了合适的主题。”[7]150而处于20世纪初期的费诺罗萨执拗地用科学性话语对这一深度创作进行了浅层“阅读”。他肯定了文人画的思想性与革新色彩,但却从符号与语言的共性上消解了文人画的特性,并将其不加区分地比附为在儿童画的“马”下写“马”字。在他眼中,文人画等同于“文学小品”。他界定的“文人画”已远不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文人画了。从逻辑上看,他用西方视觉艺术(造型艺术)的衡量标准扩大了文人画的内涵,缩小其外延。在他的研究中水墨山水、青绿山水与文人画这一具有包含与交叉关系的分类是导致他自相矛盾的原因之一。费氏将文人画看作与文字类同的抽象符号,而非表现性艺术。尽管他认识到文人画的表现性特征,但却将其归于幼稚的儿童涂鸦。文人画的“秃笔”“指画”等技法也被归入其中。殊不知“文人画中固亦有丑怪荒率者,所谓宁朴毋华,宁拙毋巧;宁丑怪,毋妖好;宁荒率,毋工整”[1]6。对于费氏的误读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
其一,文人画的文学特性并非体现在符号的暗示、象征方面,而在绘画的诗意追求上。文人画使观者从视觉艺术的观看层面进入到语言艺术的想象层面,在与经验世界保有距离的虚构艺术世界中实现精神的绽放,使得绘画具有了诗的品格。这种诗性品格超越了绘画与诗歌之间的媒介阻隔,使“画中有诗”,看画如读诗,视觉在有限的画面中随心智驰骋于无限的想象。文人画的文学性并不等同于文学小品,它是视觉艺术在心智层面的迁延与升华。费氏在叙述北宋以来的中国绘画时,不断以缺乏或扼杀想象力为由指责文人画,此处除了前文提及的类型划分与概念置换的问题外,还体现了他对艺术共性与个性的偏执理解。文人画的诗性特征是无法用科学、理性加以分析的,艺术家的直感是不可重复验证的,文人画有自身的诗性话语与独一无二的品格呈现方式。何况即便从表层看,中国绘画从来都不是弱文学母题,文人画无物不可入画,题材选择广泛,并不排斥文学主题。文人画又多有诗赋题赞,文学性毋庸多言。费氏将想象力与个人自由相联系,又将个人自由与儒家文化思想相对立,在否定儒家思想文化体系的立场上,否认文人画中的艺术自由精神和想象力,进而将文人画作为儒家文化生态中退化艺术的标本,这对文人艺术是极不公允的。
其二,文人画以书法入画的特点是与“书画同源”的文化传统紧密联系的。书法与画法相通,“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生”[18],“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15]674,由此可见书法的基础性地位。文人画的书法性用笔即“逸笔草草”并非是稚拙的儿童涂鸦。元代文人画趋于简笔(书法的简劲用笔),形成了显著的风格特征。费氏是英语世界中第一个指出中国字的拼画特点的学者,他认为书法就是绘画。从这一认识根源来看,书法在他的艺术论域中是缺少独立特性的。但他却认为绘画的书法式用笔消除了两者之间的界限。以书法入画并非如费氏所言消除了绘画与书法间的差异,而是增强了同源艺术的内在融合力,将书法的笔势这一动态性因素赋予绘画,使绘画除了呈现视觉图像外,还呈现了画家作画时的动作、姿态、运动轨迹。以书法入画,将创作主体与观者融入绘画中,将彼时画家身体动作的“包孕性顷刻”展现在此时观者的眼前,实现了时空的超越,赋予静态视觉艺术以动态特征。“逸笔草草”并非草率、轻忽,而是将人的自我实现与艺术创作相结合。宗白华说:“中国绘画以书法为基础,就同西画通于雕刻建筑的意匠。我们现在研究书法的空间表现力,可以了解中画的空间意识。”[19]费氏不谙中国的书法艺术,在艺术史建构中将其过滤,失掉了考量中国艺术空间感型的最佳对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漏。在西方视觉艺术中没有与书法相对应的品类,费氏的知识性话语无法阐释无任何先在经验的艺术形式,他对书法与绘画的内在联系无从下手,更不用说理解以书法入画的自我实现精神了,这也是西方学者“缺类”研究的局限所在。
费诺罗萨的《中日艺术源流》是英语世界最早的东亚艺术史专著。在宏观上,费氏使东西文化处在普遍的联系与交流中,以“空间”这一东西艺术共有的感型标准拟构了宏大的学术视野。在建构中国艺术史时,消解了不符合其话语模式的文人画在艺术史图式中的位置,全面否定文人艺术理论与文人画特质,表现出他在具体微观层面对异质文明差异性的学术偏执。他试图用基督教文明或西方文明的美学范式和学术话语给中国艺术塑型,在给予中国艺术形而上的体系性的同时,也过滤和误读了文人画与文人艺术理论。同时,还可以从费氏的论断考量特定时期部分西方人头脑中所理解的中国形象、中国观念以及中西关系。“‘艺术史’是一种表述的模式,这种模式非常好地满足了艺术批评家的需要,因为艺术批评家知道如何利用其自我实现(满足)的预言。这一类型的再现‘解释’了它(艺术史)之所以需要通过形成一种叙述方式来解释作品的原因,这种叙述方式就存在于十分合情合理的个人作品之中。艺术史就是这样通过运用一种专业性的话语——特定的艺术史话语,寻找一种不同寻常的‘真实’(真理)。”[20]但应明确的是,“真实”并非某种普世价值观的推而广之,也不是将中国艺术视为“假想的西方”,而是尊重异质文明差异性的多元“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