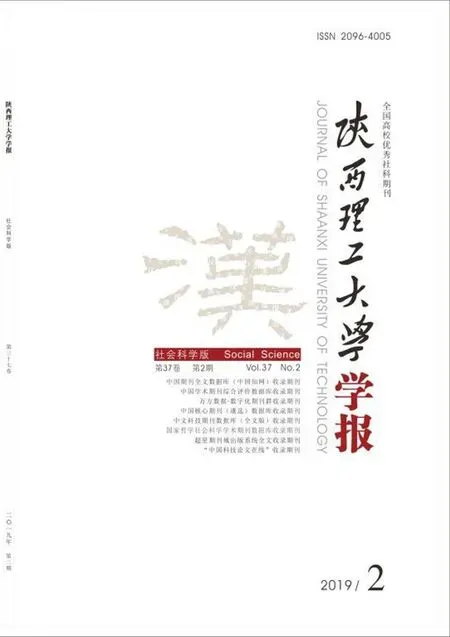文人心灵历程的艺术展示
——元杂剧文人历史剧细读
高 益 荣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程千帆先生告诫学生:“体会作者的作品,最主要的是了解作者写这个作品时候的心情。”[1]4要准确地理解、读懂古人的文学作品,必须伴随着自己的情感,细心体悟作者的创作心情,才能与作者交流,较为准确地解读出其作品的思想情感。翻开元杂剧,给人的强烈印象就是里面充满了文人的悲愤与辛酸,无论是写哪类题材的作品,文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就把他们胸中的积愤表现了出来,尤其是在写历史上的那些不得志文人时,他们寻觅到精神上相通的契合点,正如吴伟业所说“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慨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而我之性情,爰借古人之性情,而盘旋于纸上,宛转于当场……而士之困穷不得志,无以奋发于事业功名者,往往遁于山巅水湄,亦恒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2]204-205。在元代,文人地位低下,元代确实是中国读书人最不幸、所以抱怨情绪也最强烈的时代,因为儒学传统思维赋予他们的人格模式和价值体系就是“学而优则仕”,可在元代此路难以走通,于是他们胸中强压忧愤,发出悲叹:“叹寒儒,谩读书。读书须索题桥柱。题柱虽乘驷马车,乘车谁买长门赋。且看了长安回去。”([双调·拨不断])马致远巧用反衬手法,与汉代司马相如相比,告诉元代书生读书无用,因为读了书本应像司马相如那样实现理想,乘驷马大车,获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满足。然而,生不逢时,元代偏偏是个“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无名氏[中吕·朝天子])的斯文扫地的社会,于是使元代文人普遍心理上有一种失落感。他们的心理普遍经历了对仕途的热望——彷徨——超脱的不同境界,如钟嗣成的[双调·清江引]概括的:
秀才饱学一肚皮,要占登科记。假饶七步才,未到三公位,早寻个稳便处闲坐地。
即使学了一肚皮才能,具有曹植七步诗才,但在尚武轻文的元代他们也无所作为,“沉抑下僚”,于是他们在写历史上的失意文人的遭际时往往产生情感共鸣,得到情感的发泄与心灵的抚慰,故写下了大量反映文人儒士从对功名的热望到幻灭,再到自我人格复醒的心灵历程的历史剧,其中有代表性的有马致远的《半夜雷轰荐福碑》(简称《荐福碑》)、《西华山陈抟高卧》(简称《陈抟高卧》)、吴昌龄的《花间四友东坡梦》(简称《东坡梦》)、费唐臣的《苏子瞻风雪贬黄州》(简称《贬黄州》)、王伯成《李太白贬夜郎》(简称《贬夜郎》)、郑光祖的《醉思乡王粲登楼》(简称《王粲登楼》、宫大用的《生死交范张鸡黍》(简称《范张鸡黍》)、《严子陵垂钓七里滩》(简称《七里滩》)、无名氏的《苏子瞻醉写赤壁赋》(简称《赤壁赋》、《冻苏秦衣锦还乡》(简称《冻苏秦》、《孟光女举案齐眉》(简称《举案齐眉》)等十多种。这些剧目,都深深地打上了元代文人不幸的印记,寄托着他们坎坷不遇的愤激之情,巧妙地使历史人物命运与现实文人遭遇达到了为一的境界。
一、读书人困顿生涯的形象画卷
从宋及元,地位落差最大的可以说是读书人。在宋代,读书人可以通过读书、科考走上自己“修治齐平”的理想之途,尽管有时难以如愿,但只要有耐心,总会遂愿。到了元代,这条读书人已习惯的路却长时间被阻隔。因而,就深深的引起了这些“书会才人”对昔日的怀恋,对那些孜孜以求于科考的读书人更倾注以同情的酸泪。马致远的《荐福碑》是这方面的代表,它集中地反映了文人士子在元蒙异族统治下的悲惨遭遇,寄托了一代文人对希望感到茫然的感伤情怀。《荐福碑》根据宋人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二《雷轰荐福碑》改写而成,主要写穷秀才张镐的困顿人生。张镐拿着范仲淹给他的三封推荐信求人帮忙,以图摆脱困境,第一封信给黄员外,黄员外第二天就得急病死了;第二封信给黄州团练副使刘仕林,刘也死了。他已无心投第三封信了,路遇一个叫“张浩”的财主,张镐在他庄上教书,这张浩偏偏又假“张镐”之名把范仲淹推荐他万言长策所得的官职窃取了。张镐生计无着落,寄身荐福寺,长老让他拓庙中颜真卿书“荐福碑”卖钱,以解决他赴考的盘缠,可碑又偏遭雷神击碎。张镐走投无路,就在他准备自杀之时,遇到了范仲淹,范仲淹带他进京,张镐终于考中状元。此剧与其说是历史剧,毋宁说是元代文人生活贫困和追求功名的悲惨遭遇的真实展示。作品中充满了文人追求功名时的辛酸泪,张镐感慨:“我本是那一介寒儒,半生埋没红尘路,则我这七尺身躯,可怎生无一个安身处!”生活的极度贫穷,他“穿着些百衲衣服,半露皮肤”,使他心生怨愤,大声呐喊:“天公与小子何辜?问黄金谁买《长门赋》?好不值钱也‘者也之乎’!”于是他对读书人传统的思维模式发生了怀疑:“想前贤语总是虚:可不道书中车马多如簇,可不道书中自有千钟粟,可不道书中自有颜如玉,则见他白衣便得一个状元郎,那里是绿袍儿赚了书生处?”他认为“我去这‘六经’中枉下死工夫:冻杀我也,《论语》篇、《孟子》解、《毛诗》注;饿杀我也,《尚书》云、《周易》传、《春秋》疏。”因为在“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的不正常社会里,“则这失志鸿鹄,久困鳌鱼,倒不如那等落落之徒”。马致远借张镐之口,将元代文人胸中积压的怀才不遇的愤怨之情淋漓尽致地倾吐出来,确是千古奇文,如孟称舜《酹江集》眉批云:“半真半谑,行文绝无粘带,一种悲昂情怀,如寒蛩夜唧,使听者凄然,自是绝高手笔。”《冻苏秦》也是一出饱含文人为求功名充满困顿酸泪的戏剧。苏秦为求取功名,“俺把那指尖儿掐定,整整的二十年窗下学穷经。苦了我也、青灯黄卷,误了我也、白马红缨。本待做大鹏鸟高搏九万里,却被这恶西风先摧折了六稍翎。端的是云霄有路难侥幸,把我在红尘中埋没,几能勾青史上标名?”为了功名,他不但要忍受生活痛苦,“可正是酒冷灯昏梦不成,则我那通也波厅,通厅土炕冷。兀的不着我翻来覆去直到明。且休说冰断我肚肠,争些儿冻出我眼睛。”还要遭受别人,乃至亲人、朋友的讥讽、白眼。作者就借苏秦之口说出了当时社会人们对文人的篾视:“如今街市上有等小民,他道俺秀才每穷酸饿醋,几时能够发迹。”连街市小民对文人都是如此看法,足见其地位的低下:“那一个不把我欺,不把我凌?这都是冷暖世人情。”王长者给他资助的银两,因他途中生病花尽,无功返回家乡,“风又大,雪又紧,身上无衣,肚里无食”,可回到家,父母还都不理他,妻不上机,嫂不为饮,还讥诮抢白他:“你当初去时,则要做官,到今日官在哪里?”气得苏秦连连感叹:“可兀的干受了你这一肚皮腌臢气。”为了功名,他到秦国投奔哥哥张仪,张仪为了激励他,故意冷淡他,“冷酒、冷粉、冷汤,着咱如何近傍?百般妆模作样,讪笑寒酸魍魉”,将他羞辱一番逐出,让苏秦感到彻骨透心之寒,彻底体味到人情的冷暖。《渔樵记》里的朱买臣也是如此,他“幼年颇习儒业”,四十九岁了功名仍未遂,他也满腔愤怨:“十载攻书,半生埋没。学干禄,误杀我者也之乎,打熬成这一付穷皮骨。”“老来不遇,枉了也文章满腹,待何如?俺这等谦谦君子,须不比泛泛庸徒。”现实的困顿,使文人人生价值观也发生变化,对传统人生道路产生怀疑,朱买臣和张镐一样,质疑读书究竟有何用?“人都道书中自有千钟粟,怎生来偏着我风雪混樵渔?”他空学成七步才,靠卖柴为生,“他肩将那柴担担,口不住把书赋温,每日家穿林过涧谁瞅问?他和那青松翠柏为交友,野草闲花作近邻,但行处有八个字相随趁,是那斧镰绳担,琴剑书文。”这八个字放在一块,是多么大的讽刺,但真切反映了元代文人的物质地位。他养活不了妻子,妻子要求“与我一纸休书,我拣那高门楼大粪堆,别嫁人去也。”后来他一举中第,被授会稽郡太守,始困终亨,只不过是元代文人的白日梦罢了,正如清人梁廷枬在《曲话》卷二中说:“《渔樵记》剧刘二公之于朱买臣,《王粲登楼》剧蔡邕之于王粲,《举案齐眉》剧孟从叔之于梁鸿,《冻苏秦》剧张仪之于苏秦,皆先故待以不情,而暗中假手他人以资助之,使其锐意进取;及至贵显,不肯相认,然后旁观者为说明就里,不特剧中宾白同一板印,即曲文命意遣词,亦几如合掌。”[3]262其实,这种不同剧的同一情节模式安排,决不是偶合现象,它正是元代特殊的吏治文化的产物。元代前期废除科举制,广大文人大多走为吏之路,往往把功名实现的希望寄托在赏识他的亲朋好友的帮助提携上,以谋求实现他们的功名理想,因此,这些杂剧雷同的情节正是元代文人悲苦求仕路的真实写照。
二、沉浮宦海人生的理性思考
吴宓先生曾告诫他的学生说:“宦海浮沉终非学人所宜。”[4]266因为读书人大多不会权变狡诈,不会应付,圣贤孤傲耿直的人格的铸造又往往使他们在需要没有自我主见、一味附声迎合的官场文化中保持自己的个性,于是往往遭遇不幸。元杂剧的文人历史剧中就有好几种反映出仕进文人的不幸,使他们对封建官场有了清醒的认识,从而产生了背离的情绪。
如果说《荐福碑》《冻苏秦》等剧重点反映元代读书人求取功名的艰辛,那么《贬夜郎》《贬黄州》等剧则是反映了他们走上仕途后在官场遭受的打击,揭露了封建官场的腐败黑暗,从而又对追求功名思想予以否定;如果说《荐福碑》等类剧侧重情感的倾泄,那么《贬夜郎》等剧则是理性的反思。《贬夜郎》通过才华横溢、个性奇倔的大诗人李白的仕宦行迹否定了文人士子为官求宦的人生追求,歌颂了文人士子奇倔独立的人格风范。李白鄙视功名利禄,傲视王公卿相,敢于让“娘娘捧砚将人央”,高力士侍候他脱靴,他表面大醉,实际上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他一眼就看破京城“凤凰歌舞地”,不过是“龙虎战争场”,“咫尺舞破中原,祸起萧墙”,他预感到唐王朝繁华的背后隐藏着危机。高力士宣他进宫,他告诉高力士“你朝冶里不如我这里”:“禁庭中受用处,止不过皓齿歌,细腰舞,闹炒炒勿知其数,这其间众公卿似有如无。奏梨园乐章曲,按广寒羽衣谱,一声声不叶音律,倒不如小槽边酒滴真珠。你那里四时开宴充肥鹿,我这里万里摇船捉醉鱼,胸卷江湖。”他进宫后,玄宗责怪他无礼,他傲然回答是因为“玉骢错认西湖路”,是陛下马的不是。出宫时,他看到了安禄山和杨贵妃,便预感安禄安必然造反,“忽地兴兵起士卒,大势长驱入帝都,一战功成四海枯。”尽管他有如此的治国之才,可因为“大唐家朝冶里龙蛇不辨,禁帏中共猪狗同眠”,“宫中子母,村里夫妻,觑得俺唐明皇颠倒如儿戏。”朝廷的丑恶、黑暗使他对此完全失望,于是他“自休官,从遭贬,早递流了水地三千。待教残蓑笠纶竿守自然,我比姜太公多来近远。”他又归回自然,过起了自由无拘、保持个性的生活。
几个以苏轼为主角的杂剧,通过苏轼对生命及人生、官场的得意与失意的苦涩体验,展示了文人士子对入仕、出仕的理性反思,苏轼蹭蹬于仕途的遭遇正体现出元代文人对入仕的种种思考。以苏轼贬黄州为题材的杂剧有六种,就现存的三种来看,很显然,作者都不是在完全拘泥于历史事件的前提下再现这一历史史实,而是借历史之躯载现实之魂,作者各自从自己对历史、现实的理解抒发着自己的人生观、政治观。《贬黄州》是这三种剧中具有凝重历史厚度的作品。苏轼因为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王安石便“欲报复”,就“着御史李定等劾他赋诗讪谤,必致主上震怒,置之死地。”于是皇上大怒,多亏张丞相“再三申救”,苏轼免遭死罪,被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满腔怨屈:“臣上万言书谏诤,今日反受谪贬,兀的不屈死忠臣义士呵!”谪贬黄州的途中,遭遇一场寒雪,大自然的冰冷与诗人内心的凄凉相融,他想到历史上与自己有相同命运的书生:“我怕不文章似韩退之,史笔如司马迁,英俊如仲宣、子建,豪迈如居易、宗元,风骚如杜少陵,疏狂如李谪仙……困煞英贤!”“这其间骚客迁,朝士贬。五云乡杳然不见,止不过隔蓬莱弱水三千。不能彀风吹章表随龙去,可做了雪拥蓝关马不前,哽咽无言。”他同韩愈一样“欲为圣明除弊事”,却“脱离了长安市廛,须捱到黄州地面,更狠似夕贬潮阳路八千。”宦海沉浮,人情冷暖,使他内心萌发了保持自我清闲、对仕进功名冷淡的念头:“我情愿闲居村落攻经典,谁想闷向秦楼列管弦。枕碧水千寻,对青山一带,趁白云万顷,盖茅屋三间。草舍蓬窗,苜蓿盘中,老瓦盆边,乐于贫贱,灯火对床眠。”尽管他最终被皇帝招回朝廷,但人生的变故却早已冷却了他的一颗功名之心。他深有体会地感慨:“我想升沉荣辱,好无定呵。”“造化通神,镜里功名梦里身。无常忽近,一分流水二分尘。名流蜗角几时分,尘随马足何年尽?”“那里显骚客骚人俊,到不如农夫妇蠢。绕流水孤村,听罢渔樵论,闭草户柴门,做一个清闲自在人。”这里显然表现的是对仕途险恶的理性思考,与其将自己的性命系于他人、被功名牵着走,还不如辞官归隐、过着闲云野鹤的自在生活更惬意,这正表现出元代读书人注重自我的意识在觉醒。《赤壁赋》没有《贬黄州》有深度,它把苏轼被贬的原因归结为文人之间的个人恩怨。由于苏轼在王安石的家宴上,醉写艳词《满庭芳》,王安石认为它语义轻佻,“戏却大臣之妻”因而遭贬黄州,路逄大雪,“冷冻皮肤,寒侵肌肉。雪拥难行马,风紧懒抬头。我这里战兢兢把不住浑身冷,也是我官差不自由。”于是也产生了对仕途厌倦之情:“我从今后无荣无辱无官守,得净得闲得自由。”他同黄鲁直、佛印夜游赤壁,并写下千古名篇《赤壁赋》。在与大自然的拥抱中他对人世的功名参破了,“隐遁养姓名,不恋恁世情。无利无名,耳根清净。一心定,不受恁是非忧宠辱惊。”与《贬黄州》相比,此剧的重点从对官场的险恶、世态炎凉的揭露转向文人对自己轻佻性格缺陷的反省。因而,当苏轼最后被皇帝招回朝廷、官复旧职时,他发出的是从贬官中得到了反省自身的呼唤之语:“劝君莫惜花前醉,我不合开怀饮醁醅,霎时间不记东西。惹起词中意,也是我酒后非,这的是负罪合宜。”《东坡梦》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文人士子对仕宦功名的否定而归心于佛的心理历程。苏轼被贬黄州,途经庐山东林寺,特携妓女“白牡丹”拜访同窗故友僧人佛印,想劝他还俗,佛印不肯。苏轼又让“白牡丹”千方百计诱惑佛印破戒,佛印始终不为所动。相反,苏轼在梦中却被佛印差遣的“桃柳竹梅”花间四友所诱惑,多亏庐山松神怕苏轼犯错误到苏轼梦中把桃柳竹梅赶走。苏轼梦醒,与众人向佛印问禅,佛印一一解答,白牡丹被点省悟,削发为尼,苏轼也大受教育。正如李春祥先生所说:“作品保留了宋元以来‘说参请’习俗,充满了人生哲学精神。”[5]234此剧实际上是作者吴昌龄对自己仕途遭遇的艺术反思。据孙楷第先生《元曲家考略》得知,吴昌龄出任过婺源知州等小官,因此可知,此剧必然有作者的仕途真切感受。剧中的佛印与苏轼,就像苏轼《前赤壁赋》中的苏子与客,其实是作者内心的两种对立的思想。苏轼要劝佛印还俗大谈为官的好处:“俺这为官的,吃堂食,饮御酒;你那出家的,只在深山古刹,食酸馅,捱淡齑,有什么好处?”而佛印回答说:“虽然是食酸馅,捱淡齑,淡只淡淡中有味。想足下纵有才思十分,到今日送的你前程万里。”“你受了青灯十年苦,可怜送得你黄州三不归。”在佛印的一番说禅中,苏轼终于叹服:“果然是真僧,问他不倒。苏轼从今忏悔,情愿拜为佛家弟子。”作者于是借佛印之口点题:“从今后识破了人相、我相、众生相,生况、死况、别离况,永谢繁华,甘守凄凉。唱道是即色即空,无遮无障。笑杀东坡也忏悔春心荡,枉自有盖世文章,还向我佛印禅师听一会讲。”这正反映出元代如吴昌龄们的小吏在宦海浮沉中所产生的真实念头,欲进不能,最终归于佛道,求得心灵的须臾超脱,表现出他们正从孜孜以求仕宦的美梦中醒悟!
三、文人内在独立人格的赞歌
李泽厚先生说:“由于对人生采取超脱的审美态度,由于对恶劣环境和政治采取不合作的傲世态度,由于重视直观、感受、亲身体悟,等等,它们又常常使艺术大放光彩,使艺术家创作出许多或奇拙或优美或气势磅礴或意韵深永而名垂千古的作品来。”[6]217在元杂剧历史文人剧中,宫天挺的《范张鸡黍》《七里滩》就是这样的作品。宫天挺是元杂剧后期的主要作家,钟嗣成把他列在《录鬼簿》“方今才人相知者”之首,介绍说:“宫大用,名天挺,大名开州人,历学官,除钓台书院山长。为权豪所中,事获辩明,亦不见用,卒于常州。先君与之莫逆,故余常得侍坐,见其吟咏。文章笔力,人莫能敌。乐章歌曲,特余事耳。”传后的吊曲赞扬他:“豁然胸次扫尘埃,久矣声名播省台。先生志在乾坤外,敢嫌天地窄。更辞章,压倒元、白。凭心地,据手策,数当今无比英才。”[7]366可见,宫大用是一位很有才气,但久困下吏的不得志文人。他大约生活在1260年—1329年之间,而元代恢复科举制是延祐元年(1314),本来凭着他的盖世英才完全可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他也已五六十岁的人了,加之元代恢复了的科举制只不过是装饰品,收录名额很少,又给汉族文人种种的限制,更令人愤慨的是科选中权钱交易、卖官鬻爵等丑恶现象层出不穷,从而使具有真才实学、品行正直的文人往往难以步入仕途,品行恶劣但有钱财者“跛驴鸣春风”。作为“书院山长”的宫大用对奔波于科考场中的形形色色的文人是很了解的,从而使他对这条羁绊、腐蚀文人的链条认识更深刻,于是揭露、鞭挞其丑恶的东西,赞扬其优秀的东西,让文士们从外在的迷失了自我的痛苦仕进中求得内在自我独立人格之觉醒。
《范张鸡黍》是宫大用根据《后汉书·独行列传·范式传》改写的,但他在重铸历史上“名节”之士范式、张劭“独行”的品行时,给他们身上注入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即对“选举之弊”的批判是融入了他自身遭际的不平和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正如吴梅先生在《瞿安读曲记》中说:“(此剧)词中痛论选举之弊,与汉制无涉,当是影射时政。……大用生卒年虽不可考,大抵在中叶以后,则其时初复科举,僚进必多,宜其言之愤激也。”正是出于这一创作意图,作者对历史素材进行了有意的加工,既保留了范式、张劭守信重义、生死不渝的高尚品节的原故事精神,又增加了见利忘义的小人王韬,从而完成了对在丑恶现实中保持自我高尚品行、不与谄佞之徒为伍者的歌颂,以及对见利忘义、奴颜媚骨者鞭挞的主题。
范式、张劭二人情意深厚,“结为死生之交”,同游帝学,“盖因志大,耻为州县,又见谄佞盈朝,辞归闾里”。他二人约好,两年后的今月今日,范式不远千里专程到汝阳拜访张劭老母,张劭答应到时他杀鸡炊黍以招待范式。两年以后,范式如期赴约,途中遇到他的同学王韬,此人将同学孔嵩的万言书假称己作,又通过做学士判院的岳父送交贡院而得杭州佥判的官职。于是二人同行,范式知道王韬不学无术、品行不端,但却轻易得官,可见官场是多么的腐败。宫大用给范式安排了一段段饱含愤激之情的唱段,揭露官场的黑暗,科考的腐败:
[天下乐]你道是文章好立身,我道今人都为名利引,怪不着赤紧的翰林院那伙老子每钱上紧。(王仲略云:)怎见得他钱上紧?(正末云:)有钱的无才学,有才学的却无钱。有钱的将着金帛干谒那官人每,暗暗的衙门中分付了。到举场中各自去省试殿试,岂论那文才高低?(唱)他歪吟的几句诗,胡诌下一道文,都是些要人钱谄佞臣。
[那吒令]国子监里助教的尚书,是他故人;秘书监里著作的参政是他丈人;翰林院应举的,是左丞相的舍人。
[幺篇]口边厢奶也犹未落,顶门上胎发也尚自存。生下来便落在那爷羹娘饭长生运,正行着兄弟后财帛运,又交着夫荣妻贵催官运。
官场是如此的黑暗,举选是那样的不堪贤愚,其结果是“满目奸邪,天丧斯文也!今月个秀才每遭逢着末劫。有那等刀笔吏入省登台,屠沽子封侯建节。”从而使范式这样的真儒冷却了一颗功名仕途心,不愿与官场丑恶东西同流合污,于是内心保持自我人格之高洁的独立意识在觉醒。范式就说:“争奈这豺狼当道,不若隐居山林为得,吾闻仲尼有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男子汉非不以功名为念,那堪豺狼当道,不如只在家中侍奉尊堂。”因而他更看重朋友间的信,当第五伦“奉圣人的命,特来敦请”时,他却回答道:“本待要求善价而沽诸,争奈这行货儿背时也。”听着第五伦的话便睡着了,在梦中张劭便托他给自己主丧下葬。梦醒,他便去给张劭奔丧,果然,他未到张劭的灵车就不动。他亲自挽拉灵车,埋葬了张劭,尤其是他给张劭做的祭文:“维公三十成名,四十不进,独善其身,专遵母训,至孝至仁,无私无逊,功名未立,壮年寿尽。吁嗟元伯,魂归九泉。”饱含热泪,情感复杂,既有对朋友高洁品节的赞颂,也有对其怀才不遇的同情,亦不乏对造成朋友悲剧的社会的控诉。这正如李鸣先生所说:“张劭之死在剧中既象征了道德风节在现实中的摧残,也象征了文士的时代厄运。”“有了象征的功能,范式的哭吊也因而泛化,成为一曲受戕害的知识分子的挽歌。这曲挽歌中沉痛的哭诉,实际上成为对造成元代知识分子悲剧性命运的时代的控诉,成为对道德风节这一知识分子的价值原则遭到摧折的悲愤。”[8]592-593正由于《范张鸡黍》重在歌颂文人士子重义守信的名节,表现出文人士子在黑暗腐败的社会中追求完美独行的人格,所以在众多历史文人剧中它具有非常的意义。如果将它与《荐福碑》《王粲登楼》《赤壁赋》等剧作以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元代杂剧作者人生追求的心理发展轨迹。《荐福碑》所展示的是元代前期文人的悲惨遭遇,但主要是仕途困顿所带来的生计艰难,文人连基本生存的保障都没有,故满含元代前期文人士子由生计问题带来的对待功名追求的不顾自我名节尊严而孜孜以求的辛酸。《王粲登楼》中的王粲比张镐自我个性独立意识要强多了,他对自己充满自信:“我则待大走上韩元帅将坛,我负贫呵乐有余,便贱呵非无惮,可难道脱不的二字‘饥寒’?”他为人高傲,岳父蔡邕故意怠慢羞辱他,使他一气之下离开京城投奔了刘表,又因傲慢不被任用,病困交加,感伤万分,登楼作赋,以抒其怀。他在遭到荆州牧刘表侮辱后滞留荆州时反醒自己:“想当初只守着旧柴扉,不图甚的,倒得便宜。”他已表现出求得自我人格尊严的端倪,闪现出愿意远离尘世、过起田园隐居生活的念头。但王粲的怀才不遇、穷愁潦倒的人生遭际和孤傲倔强的个性体现出的是元代文人对自身处境的不满。《范张鸡黍》则把关注的重点落在对文人士子精神面貌的描写,从歌颂他们高尚品节的层面以鞭挞封建官场、科选的丑恶行径,天下无道则隐,与统治阶级持不合作的态度,表现出了文人自我人格的觉醒。到了《七里滩》,严光不愿做官,坚决回到七里滩垂钓,他把“富贵荣华”视为“草芥尘埃”,以及《陈抟高卧》中的陈抟宁肯高卧华岳也不愿留在京都为官,都表现出元代文人超越功名伦常的人格独立意识。
总之,元杂剧的文人历史剧表现出了那些在元蒙统治时期由原先受人尊敬居于中心阶层而沦落为边缘、乃至下层的失意文人的内心复杂情愫,尽管其取材于历史,演义古人古事,但无不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既有对历史更叠的兴亡慨叹,又有对现实斗争的折射,还有对文人仕也苦、隐也苦的两难心态的反映,不管写何内容的历史剧,在其中都有剧作者的影子,都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