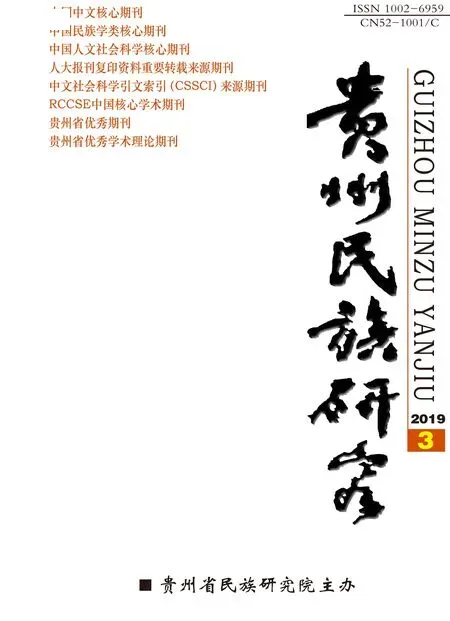贵州民族地区扶贫移民中的社会适应研究
辛丽平
(贵州省民族研究院,贵州·贵阳 550004)
一、扶贫移民的适应性问题
20世纪70时代,扶贫移民的概念在国外被提出,当初是作为环境难民(disaster refugee)的形式出现的。Frank Biermann[1]等人对环境难民定义为:因气候变化,如海平面上升、水资源匮乏或干旱等,居民被迫离开原居地,流浪他乡,从而变为难民。El-Hinnawi[2]从迁移原因的角度把环境难民分解释为:由于某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迁移;由于环境崩溃造成的迁移;由于生态环境的持续缓慢退化造成的迁移。
当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扶贫移民的定义、性质、实施方式、后续产业发展等方面,例如近年来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一是扶贫移民政策研究,代表性的学者有陆汉文[3]、郑瑞强[4]、李博[5]、龙彦亦[6]等;二是扶贫移民搬迁模式分析,代表性的学者有李垚栋[7]、郭俊华[8]、汪静[9]、严月珺[10]等;三是扶贫移民的成效、经验与政府职责,代表性的学者有叶青[11]、王红彦[12]、罗强强[13]、白南生[14]等。诸多研究均体现出社会主义中国的优越性——则从人民福祉的角度出发,直面影响人类全面发展的“贫困”主题,在当前开展的脱贫攻坚中对深度贫困区域的群众采取易地扶贫搬迁的方式,解决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而易地搬迁绝非简单的人口迁移,而往往会毁灭性地破坏深度贫困区域的现存社会秩序,使得原有的生产体系、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网络支离破碎。基于此,本研究依据长期的田野调查,深入研究贵州省民族地区扶贫移民中的社会适应,乃至扶贫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问题。
二、贵州易地扶贫搬迁任务艰巨
贵州是中国易地扶贫搬迁的主战场,少数民族地区也是中国当下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的重点区域。2016年9月22日,《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计划五年内对近1000万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实施行易地扶贫搬迁,全力帮助“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的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从地区分布看,西部12省(区、市)建档立卡搬迁人口约664万人,占67.7%。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把六盘山区等十四个连片特困地区定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仅贵州一省就包括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武陵山区三大连片特困区,扶贫任务非常艰巨。根据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2019年全国计划易地扶贫搬迁168万,贵州搬迁人数约67万人,占总数的40%。
贵州省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后,政府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了解各民族群众共同居住的需求,推动移民搬迁后各民族集聚社区的社区稳定。不仅促进了生态脆弱区生态保护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而且使搬迁群众在开始新的生活中,与迁入区其他各族群众不断相互了解、互帮互助;在安居乐业的同时,实现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共同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和谐。
在各级政府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有力保障下,贵州民族地区的移民搬迁户告别了原来艰苦的居住环境,有的进入集镇,有的住进移民小区,都拥有自己的新房子,生活条件也得到明显改善,实现了电气化生活。据兴义市清水河镇高峰村上补西组一位搬迁者介绍,搬迁前主要是靠天吃饭,只靠种地年收入不足万元,移民搬迁后大部分移民都开始从事大棚蔬菜种植,经商做生意,以跑运输,或做砖瓦工、粉刷工、修理工、装卸工、打工等为主,每户年收入均比以前大幅提升,有的甚至每年收入五六万,甚至个别年收入上十万。通过走出去,开阔眼界,发展多种经营,走上富裕道路,过上幸福生活。此外,搬迁者开始享受迁入地教育、医疗、文化资源,特别是搬迁后进入镇区或县城,孩子上学方便,父母在身边,便于照看,便于教育,有利于孩子的学习和成长;搬迁群众也开始享受城镇的现代化健身、娱乐设施,譬如经常利用健身器材参与健身锻炼,或到文化广场跳广场舞等等;同时,搬迁群众还能经常性地接受各种身体预防性疾病的检查,如心脑血管疾病检查等,做到提早预防,及时治疗。移民搬迁后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改善能够让搬迁群众享受到各种基础设施和便利条件,极大促进了他们的身心健康。
三、扶贫移民的适应性问题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为了让贫困地区各族群众早日过上小康生活,全国各地,尤其西部民族地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持续扶贫移民运动。大量搬迁群众在政府的统一组织和指挥下从生存条件恶劣地区迁移到更适合生存的新定居点。移民现象涉及生态、经济、管理等等一系列问题。其中移民迁移之后的社会稳定问题尤为重要,随着他们生计方式的改变、社会关系变迁及心理不适等等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需要加强扶贫移民社会适应问题的研究,处理好移得出、住得下、生活好等问题,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课题。
(一)生计方式适应状况
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贵州省实行了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大大改善了贫困人民的生产生活。通过相关配套系统工程的实施,有计划、分批次将贫困农户迁移到生存环境较好、交通便利、公共服务相对完善的地方安置,为他们配置生产资源,提供就业岗位,新建移民住房,配套建设水、电、路、沼气池、幼儿园、学校、医院、集贸市场等基础生活设施,有效地解决了搬迁群众日常生活中必须解决的一系列问题,明显改善了贫困群众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
其一,增加了贫困农户的家庭经济收入。贵州省民族地区实施搬迁的村寨大多自然条件恶劣,生存资源匮乏,山多地少,仅能勉强维持生存。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在搬迁出原居住地后,当地政府部门采取多样化的安置方式,积极引导农户依托调整的耕地或原有耕地发展特色种养殖业,依托小城镇、企业和旅游区从事多种产业,他们的经济来源也从传统种植业不断拓展到加工业、畜牧业、劳务输出、物流等多种行业,稳定而有效地增加了贫困农户的家庭经济收入,增强了他们自身的造血功能,贫困农户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在黔东南州的实地走访中,很多搬迁群众表示感谢党和政府,感谢国家不仅让他们住上了新房子,还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生活有了保障……这些都表达了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深深谢意,以及他们改善生活后的由衷喜悦之情。
其二,降低了扶贫开发成本,加快了各地小城镇建设步伐。通过专项资金支持,引导各地依托小城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把贫困群众集中搬迁到生存生产条件较好的小城镇,既可有效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又能增加城镇的人口和劳动力,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城镇规模,还能推动城镇加工业、运输业、服务业等产业发展,为城镇发展增添新的活力,促进城镇快速发展。贵州省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大多居住分散,而且他们的生存环境较为恶劣,或严重缺水,或山高坡陡,或水土流失、石漠化严重,或交通不便,或自然灾害频发。如果就地扶贫,无疑需要投入巨大的物力、财力、人力,将大大增加扶贫成本。如果实行易地搬迁扶贫,就可以集中各种力量,集中解决民众必需的生活、医疗、就业、教育、交通等问题,一方面降低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另一方面最大程度上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效果更加显著。过去的5年里,贵州省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不仅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而且实现了乡乡通油路、村村通公路。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当地群众创业热情高涨。课题组走进了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一个安置点的一家服装加工厂,车间里几十位易地搬迁的妇女正在缝纫机前忙碌着,这个加工厂就是由当地的社区牵头成立的,既解决了搬迁妇女自身的就业问题,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工作和家庭两不误,进而实现了易地搬迁群众搬得出、留得住的目标。当问及她们能否适应移民新居的生活时,她们说:“没有生活来源的简单安置是让人担心的,简单的说,就是安定不下来,这是一个家庭的生存问题;现在有工作就能安定下心来了……”满足的话语流露出她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文化心理适应状况
西方学者约翰·贝利(John W.Berry)最先提出“跨文化心理学”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的概念范畴。新时期,与文化适应有关的扶贫移民的心理调适事关移民社会稳定和谐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其一,在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移民搬迁后,移民原有的民族传统文化遭受一定冲击,主要体现为民族传统文化在搬迁移民的日常生活中出现弱化趋势,这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极为不利。比如在传统民居方面,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民居多为依山而建的吊脚楼、石板房等颇具民族特色的居住样式,特别是除了基本的生活功能,还有生产的功能——养殖家禽、牲畜,晾晒稻谷。然而易地搬迁后的民居基本改成了水泥房,附着于民居上的民族文化呈现出弱化的趋势。与此同时,移民搬迁安置区内的各少数民族也大都讲汉话,住社区单元楼房,民族地区原有的民族传统建筑、语言受到较大冲击,传统的民族文化特色正在逐渐消失,这对搬迁群众的文化传承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
因此,考虑到民族的风格和元素,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在民居设计方案中也应紧紧围绕这一点——凸显民族文化的气息,尤其需要注意不同民族在生计模式上的差异,通过安置点的优化、比选,就近安置,使其既方便移民生产生活,又为移民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创造了条件。使得民众的民族民间文化得到保护和传承,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服务于广大民众的日常社会生活。
其二,增进了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贵州省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后,各级政府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了解各民族群众共同居住的需求,推动移民搬迁后多民族集聚社区的社区稳定。不仅促进了生态脆弱区生态保护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而且使搬迁群众在开始新的生活中,与迁入区的其他各族群众不断地交流互动,增进了解,加深情感。比如借助众多民族传统节日活动的开展为各民族相聚、互动提供了契机,在农历三月三、六月六,布依族人民用婉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欢庆相聚,这也为当地布依族青年男女寻求意中人提供了机会,如果双方情投意合,就可以终成眷属。除了少数民族节日,还有一些汉族的节日……总之,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节日为各族人民提供了相互接触、了解的机会,也促进各民族和谐共处、共同繁荣。因此在扶贫搬迁后,搬迁群众的生活发生着可喜的变化。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少数民族同胞由于长期以来居住在较为封闭的生活环境中,形成了他们自身特有的生产、生活习惯,要在短时期内完全适应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还有一定的难度。为此,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需要进行充分深入的调查研究,不能在领导干部的任期内急于求成,而忽视了搬迁群众的各种生活诉求。
(三)搬迁移民的身份适应状况
移民搬迁后,搬迁者从主人的身份向“客人”身份的转变,使得他们在移民搬迁的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为了帮助移民尽快适应新环境,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贵州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在移民搬迁工作结束后及时开展多项后续帮扶工作,妥善解决移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如积极修缮房屋,让移民住得安心、放心,复核、公示移民人口,足量、按月发放生活补助,及时、周到办理各种接转手续。
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移民搬迁与城镇化发展相结合,帮助移民在城镇能够就业,获得安置房,并将其纳入社保、医保体系,实现搬出大山移民的真正成为“新市民”梦想。当然,移民变为市民,决非简单的“农转非”,还在于消除附着在户籍上的城乡差异。移民涌进城镇,这必然给城镇的基础设施、就业、社会稳定等带来一定压力,因而要尽力确保移民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能够享受城镇居民的待遇,尽快适应城镇生活。在移民安置点的实地调研中,许多搬迁群众道出了他们的心声:“说句真心话,住破旧的瓦房几十年了,做梦都盼着搬新家。今天终于实现了愿望,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真要感谢国家的好政策!”“从乡下人变成城里人啦”,“以前在山上居住时做饭都用柴火,用柴火做饭,灰很多,做完一顿饭,身上、头上都是灰。饭和菜炒完后要赶快盖着,要不然就会飘上灰,不好看,也不卫生。现在哪里都是干净的,那可是大不相同的”……这些搬迁者的真实心声表现了他们自己的内心感受和美好愿望,更是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理解与肯定。
贵州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指挥上得力、行动上统一,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譬如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部分预定搬迁群众意愿发生改变,导致符合条件的搬迁对象减少,可能完不成规划搬迁任务。特别是“两个五十”的限定,让部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的群众“愿搬无路”。由于扶贫系统认定考核的不同,大部分搬迁区域贫困发生率不足50%,但生存环境的确恶劣,整体搬迁愿望强烈。在易地扶贫搬迁的系统工程中,越来越多搬迁的群众面临身份转变后如何适应新环境、如何谋生等一系列问题。在贵州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当地各级政府不仅提供居住区等基本生活设施,而且大力解决移民的就业、医疗、教育、留守等问题。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的一位77岁的搬迁户常年体弱多病,平时很少出门,大半辈子只去过一次城镇,那是25年前走路到城镇医院看病。易地搬迁后,医院离家很近,走路不过10分钟。孙子上学也方便,三个孙子就在附近的学校上学。现在不像以前那样离城镇几十里,老人自己觉得真正地成了城里人。当问及能否适应移民新居的生活时,他说:“我早就习惯在这生活了。现在出门就是医院,看病很方便。现在家里虽然装修得简单,只有一些基本生活设施,像沙发、电炉子、电视机等等,但是我们对现在这个新家非常满意。这里比老家好多了,我们不想回去。我儿子和儿媳妇在楼下租了一个门面卖起了粉面,生活也不发愁。……家里的事也随时管得了,娃儿读书也管得到。儿子专心做生意,好好地干。对现在这种生活,我很满意。以前小孩子上学很远,都不方便。现在好多了。这里的条件比老家好,儿子和媳妇把店经营好,把生意做好,比在老家种地好多了。我们都希望孩子多读点书,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未来过得越来越好。”
在访谈中,这些“新市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梦想成真的感觉!一不留神啊,山沟沟里的我们也变成了城里人!”满足的话语流露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积极乐观的精神。新时期的贵州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大都依靠加快推进城镇化来实现。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如何让扶贫搬迁移民转变成为名副其实的市民、融入城市,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如今,搬迁移民已经离开大山,走进城市,如何让他们在城市住得下、活得好,已成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当务之急。贵州民族地区城镇的各相关部门需要加强对移民的生活观念、就业理念、职业技能、创业本领等方面进行教育、培训,同时要敦促企业善待移民职工,帮助他们增加收入、增强归属感,幸福、安心地在城市创造新生活。
刚刚从自然经济走出来的搬迁移民,立刻跨入市场经济中,闯荡新世界,并非易事;从移民到市民的转变,也深刻影响着他们的心态: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城市,希望生活质量的提高、子女上学便利、交通便捷、基础设施齐全,并心甘情愿地为之挥洒汗水;另一方面,由于就业压力大,城镇生活成本较高,朝九晚五的工作规律,让相当一部分人难以适应快节奏的生活,同时又受经济收入、文化程度的限制,因此他们需要建立新的生活归属感。
四、易地扶贫移民搬迁问题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进入新的社区环境,增强移民的社会适应能力,促进移民社区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重大而迫切的课题。本次调研基于贵州省民族地区的扶贫搬迁移民社区,从移民生计方式适应、文化心理适应、身份适应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可以发现:时空的辗转使得搬迁移民亦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圈,文化的变迁带来了人际关系和精神的变化。面对这种现实,需要恢复传统文化的有益因子;自觉抵制消费主义文化中的不良气息;实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互嵌,确保扶贫搬迁工程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最终形成和谐稳定的移民社区。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不仅仅是简单的人口迁移,而是彻底地改变了搬迁移民原有的社会生活环境,因此搬迁移民的城镇化适应是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同时,易地扶贫搬迁的社区治理,不能仅仅从生存、生态、经济、管理等层面去考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易地扶贫移民的社会适应性决定了移民工程的成败,这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尤其是中国西部地区的易地扶贫移民不同于工程移民,也不同于中东部地区的生态移民,社会发展程度、族群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均影响移民的社会适应过程,而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我们后续研究值得继续探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