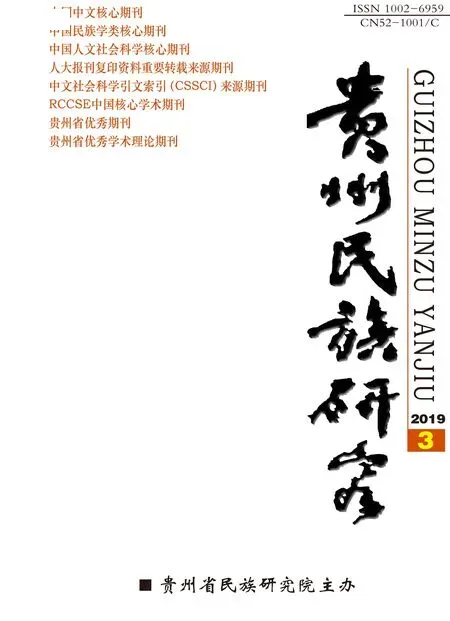景观人类学视角的非遗特色小镇建构路径探析
张霞儿
(宁波财经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浙江·宁波 315175)
一、特色小镇与非遗保护模式创新
特色小镇发源于浙江的创新型区块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在全国引发了不同的创建策略与创新路径。特色小镇既要着眼于产业,加快经济的转型升级,也要从文化与产业融合角度,“着力发展具有特色优势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信息产业、先进制造、民俗文化传承、科技教育等魅力小镇,带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就近城镇化”[1]。宁波市从自身的特点出发,把特色小镇与非遗结合起来,创新非遗传承与传承的模式与路径,为特色小镇注入了新的活力。浙江省是我国非遗大省,把非遗资源与特色小镇建设结合起来,开启了非遗传承与保护的新思路。目前,浙江省仅登记在案的不可移动文物就有7.3万多处;现有国家级非遗项目217项,非遗传承人122人;省级非遗项目1076项,非遗传承人936人;浙江省拥有的国家级和省级非遗项目达1293项,居全国首位。丰富的非遗资源,为创建非遗特色小镇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在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特色小镇创建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成为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2016年,住建部等三部委联合制定了培育特色小镇的政策,特色小镇模式得以在全国迅速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探索,特色小镇最初聚焦于产业发展。随着特色小镇的实践与理论的深入,江苏省提出了以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融合为目标,“产、城、人、文”四位一体的新模式,把特色小镇创建推向了新高度。在这一背景下,宁波市根据自身非遗积淀深厚的优势和宁波商帮文化传统,率先在全国提出非遗特色小镇概念,即以非遗为内容,以产业为平台,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非遗特色小镇创建路径,实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为发展特色小镇增添了新的元素与活力。
非遗传承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有机统一,是新的理念和趋势。非遗特色小镇创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与传承的创新,寻找到了一条非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与路径。近年来,全球对创新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探索,如何把非遗保护传承与社会经济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确保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多方关注的重要课题。特别指出的是《世界遗产公约》第20 届缔约国大会所倡导的: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应着眼于社会、经济,特别是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全新的理念为非遗特色小镇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非遗特色小镇创建作为非遗传承的新模式,既是非遗在空间上的展示,又是在时间上的延续,并通过与人的对话,使非遗传承获得了新的载体。
非遗在空间与时间上的融合,构成了非遗文化景观。这是非遗特色小镇的重要着力点。特色小镇创建一方面关注非遗传承,把非遗作为社区文化与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营造具有鲜明特色的非遗景观文化空间;一方面关注把非遗资源转化为产业资源,构建文化创意产业新业态,实现非遗与旅游业、服务业、制造业的跨界整合,打破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壁垒,构建新型产业平台,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2017年5月,宁波公布了七个非遗特色小镇名单:以元宵行会为特色的宁海前童镇;以渔民开洋、谢洋节为特色的象山石浦镇;以梁祝传说为特色的海曙高桥镇;以梁弄大糕制作技艺为特色的余姚梁弄镇;以朱金漆木雕为特色的鄞州横溪镇;以梅山舞狮为特色的北仑梅山街道;以传统家具制作技艺为特色的慈溪龙山镇。这些非遗是宁波文化的重要元素,承载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基因。但非遗特色小镇不是非遗与产业的简单叠加,而是非遗资源与现实的人群、空间、时间和产业的整合与重构,通过把非遗融入到当下生产与生活方式中,形成活化传承的文化空间。从景观人类学来看,非遗特色小镇是非遗在传承过程中,通过与产业结合,创建新的生产生活场景、空间环境。因此,基于“产、城、人、文”的非遗特色小镇模式,蕴含了景观人类学理念,注重了人与景观及其产业的良性互动,对于准确地把握非遗特色小镇的创建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化景观资源与非遗特色小镇创建
文化景观遗产是非遗传承的重要内容。我国历史悠久,具有多样性地理风貌,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景观遗产资源,是中国非遗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乡村聚落,大多地处偏远,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影响较小,保持着原生态的景观形态,是我国景观文化遗产弥足珍贵的传承基因。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第16届大会上(1992年),把文化景观遗产列入传统文化资源,被《世界遗产公约》确认为“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而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由此成为非遗保护的独特类型而受到重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把人类的建筑遗产文化景观、有机进化后的自然景观以及相关性景观归纳为文化景观遗产形态。这一界定为景观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政策依据。
景观最初是艺术学意义上的概念。19世纪初,德国科学家洪堡首次从地理学界定了景观涵义,即自然地表所呈现的地貌形态。20世纪20年代,美国学者索尔提出了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概念,它是“附加在自然景观之上的各种人类活动形态”[2],包括田野、自然风光、城市、乡村聚落、建筑等,是人类与自然互动的结果。索尔对文化景观的研究“有力地推进了把景观的研究中心从自然风貌向人类文化活动的转向”[3],开启了文化景观遗产研究与保护探索的新时代。20世纪60年代后,欧美开始从生态学、文化人类学、美学角度,对文化景观遗产进行整合性研究,丰富和完善了景观人类学的理论体系,为联合国关于文化景观遗产保护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基于景观人类学观点:景观往往是通过文化的载体呈现,景观又影响了文化的形成与演变[4]。居伊-波德在《景观社会》中提出,景观是以影像为媒介的人们社会关系。这一论断对非遗特色小镇创建提供了理论支撑。非遗特色小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性传承载体。任何非遗产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中,二者构成了不可分离的关系。事实上,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往往通过文化的媒介得以实施。因为任何文化景观遗产都反映了特定区域的文化理念、生产和生活方式,因而文化景观遗产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非遗特色小镇为非遗与地域文化的生态关联创造了原始性空间。其次,非遗特色小镇提供了原生居民、地域、文化景观遗产三位一体的保护方式。非遗本质上是文化代际传承的活态精神财富,活化传承既是非遗保护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重要内容。非遗的活化利用是社区或个人,将非遗作为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实践和文化空间不可或缺的内容。非遗特色小镇是原生性非遗社区,与其居民及其社会实践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或者说非遗本身就构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并融入于日常生活之中,历史地形成了非遗活化传承的纽带。非遗特色小镇为强化这种活化传承关联提供了文化空间,把非遗活化传承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文化景观遗产既是创建特色小镇的重要文化资源,也是构建特色小镇产业平台的基础。1988-199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启动了“文化十年”行动计划,确立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把非遗资源转化为社会与经济发展资源,是非遗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非遗特色小镇切合了当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发展趋势。如何把景观文化遗产的传承与非遗特色小镇的建设有机地融合起来,通过特色小镇这一特殊的生产与生活空间形态,达成景观文化传承与非遗保护的有机统一,在依据非遗保护的“动态本真”原则下,需要把文化景观遗产与非遗资源开发和利用,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形态有机地统一起来。因为在非遗特色小镇中,文化景观承担了传统文化角色扮演的功能,西方学者关于“环境的组构、城镇和区域的分布,都是根据空间生产与再生产中扮演的角色来进行的。”[5]此观点值得借鉴。浙江南浔古镇提供了创建非遗特色小镇的成功范例。南浔古镇有“梦里水乡”的美称,以“白墙黛瓦绿树,小桥流水人家”名闻天下,其文化景观独树一帜。习近平在2003年和2015年,两次就对南浔古镇保护与发展作出批示,提出“保护好南浔古镇”。为非遗特色小镇创建创造了重要契机,湖州市对南浔古镇的34条历史街区、237处传统民居、古桥园林进行了整修与保护,在此基础上,将非遗资源深度融入全域旅游,仅2018年就投资20亿,2017年GDP达82.25亿元,创造了以文化景观资源带动非遗特色小镇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奇迹。
三、文化景观与非遗特色小镇的空间重构
文化景观是创建非遗特色小镇的核心资源和要素,也是非遗特色小镇文化传承载体。而文化景观是通过空间形态来展示的。列斐伏尔把空间视为人类的生产关系,认为空间生产是人类文化的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具有社会-历史-空间的三位一体的维度与文化空间表征方式(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与空间再现),并以文化景观形态外显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之中。“景观因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点,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每种景观形态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6]任何非遗特色小镇建设如果离开了文化景观,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在,人们都意识到文化景观对于非遗特色小镇的重要性,但有些建设是为景观而景观,采取“拿来主义”方式,把毫不相干的文化景观“嵌入”到非遗特色小镇中,甚至用“新建古建筑”包装非遗特色小镇,不仅破坏了非遗特色小镇的“本真性”,而且误导了非遗文化传承的方向。日本景观人类学者河合洋尚在考察广东梅州客家时发现,20世纪90年代,广东省梅州市政府新建了一批原来损毁的孔庙、三山国王庙等客家文化景观,客家宗亲认为这些是“假景观”,不能获得文化认同感。可见,非遗传承中的文化景观并非仅仅是“型”的建构,更需要注入“神”的文化内涵,达成形神兼备效果,尤其是新建与重建的文化景观如何用非遗加以文化赋能,使之获得文化认同感,需要从景观人类学视角,通过对非遗核心要素的梳理,达成文化景观的形式与内容协同。非遗特色小镇建设同样存在着这一问题,即如何达成文化景观与非遗特色小镇的有机统一,需要充分利用文化景观资源去实现非遗特色小镇空间的重构。
景观人类学强调构成景观的人文因素及其历史生成动因。非遗本身就是典型的文化景观,又是具有时间与空间交织因素的文化现象。非遗对于特色小镇来说,构成了独特的空间情境关系或情境定义,“这种依靠‘情境定义’生成的意义,就是一种解释的‘框架’”[6]“空间”(Space)是景观人类学中的核心概念。传统的空间概念,主要指人占据的场所或位置的物理现实,“提到空间人们头脑中唤起的仅仅是一个空的区域。”[7]它不仅是一个地域或物理的涵义,还包含了精神活动和特定的文化特质。这种空间、文化和地域三位一体的要素,通过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融合,构成了景观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因此,景观人类学强调必须从空间、文化、地域与人的互动关联中,去发现文化景观的特质,并根据这一特质开展对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因为空间是文化景观的外显形态,承载了历史的文化记忆,使之在时间的维度上与现实形成了融合,这也正是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因。另一方面,空间也是人们分享文化记忆、开展文化对话、构建文化语境的场域,这种空间也是人从自然空间到社会空间的拓展与延伸,并由此构成了文化景观,或者说文化景观是人用文化将自然空间注入了文化内涵进行了重构。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布尔迪厄在阐述场域(field)概念时,说明文化空间是一种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构型。这种关系首先是人与自然空间的关系,但同时又是人与社会空间的关系。从这一视角出发,非遗特色小镇建设核心的关键在于文化资源的重新配置,但绝不是简单地将传统文化重新恢复,而是在原生非遗空间——特色小镇的维度上,把非遗传承及其活化利用、产业发展、文化传承在新的机制和体制中加以创新。
非遗特色小镇创建,本质上是文化景观空间的重构。因为特色小镇包含着独特的文化景观基因,如传统建筑、风俗、自然风景等,这些文化景观基因具有独特的文化识别的功能,“聚落景观的识别主要是从宏观上和整体上的识别,主要识别那些特征性强、具有可识别性、特别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景观。聚落景观识别中最具标志性的要素就是民居建筑。而民居建筑及其环境的识别又不能离开其独特的景观基因(或因子)”[8]。同时,非遗传承并非是完全将传统文化的“复古”,或是将已经灭失的古迹的重建,而是要在坚持非遗“本真性”的基础上,与时俱进、顺势而为,不断吸纳和融合当下人类文明进步的最新成果,构建具有现时社会空间和自然空间网络要素的文化景观,为非遗的创新和传统文化传承寻找一条新的路径,因此,非遗特色小镇的创建是一个文化景观重构的过程。然而,非遗特色小镇在文化空间重构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摒弃原有的传统文化元素,完全着眼于经济利益,把非遗仅仅当做是一种文化包装的资源,热衷于“新建古建筑”修建,或者在非遗保护区域内大量建设商业设施,不仅破坏了非遗的“本真性”,而且使非遗传承出现了断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对我国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称号的故宫、天坛、颐和园、云南三江并流、布达拉宫、丽江古城等进行了警告。“在经济利益驱使下毁坏性开发文化景观遗产资源,过度商业化利用,甚至在自然景观中嵌入电梯等机械装置,改变或损毁了文化景观遗产原生态样貌,形成了重申遗、轻保护,重商业开发,轻文化传承,重物质景观、轻非物质景观,重单一性保护、轻综合性保护等现象,给文化景观遗产造成了严重伤害。”[9]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认为:“乡村聚落遗传因子,是乡村民众的精神寄托,构成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家园感和归属感。”[10]另一种倾向是对非遗保护的墨守成规,把非遗文化景观视为亘古不变的“古董”,把非遗保护简单地理解为送进博物馆,完全排斥吸纳和融合现代文化元素,导致一些非遗的式微乃至濒于消亡。宁波的著名非遗金银彩绣、泥金彩漆等传承保护,都存在着这一问题,非遗进入博物馆后,失去了与当下公众对话的空间。非遗传承实际上是不断建立与当今公众对话的过程,在对话中寻找不同时间和空间语境下的话语形态,以此建构非遗的文化景观。非遗特色小镇创造了非遗与现代公众对话的空间与平台,这种对话方式创新了非遗传承机制。因此,非遗特色小镇建设是基于文化景观的整合,并对文化空间进行重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