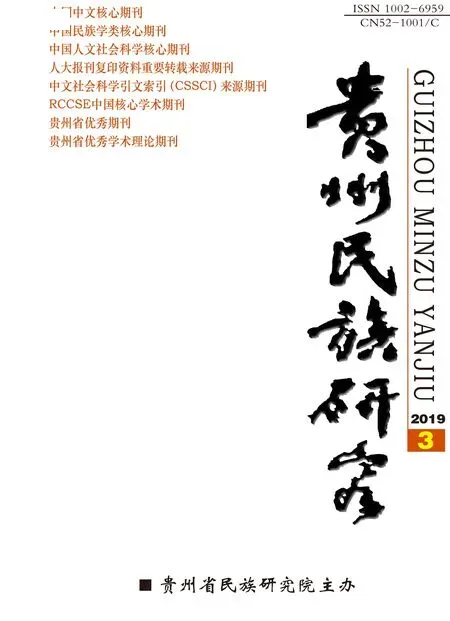抗战时期贵州少数民族对国家意识的身份认同
王立教 黎小龙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
近代中国长期受到外国侵略势力的威胁,边疆领土遭到肆无忌惮的蚕食和瓜分,这种遭遇成为当时中国人心中的一处无法愈合的伤口,特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感受尤为深重。由于他们相对于一般国人更加具备对时局的敏感性,所以他们对边疆危机的感受也就最深。尤其是抗战时期,为了救亡图存,很多人试图以自己的方法找到解决边疆危机的出路。因此对抗战时期贵州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研究除了具有学理上的意义之外,更加具有对现实的参考价值。
一、抗战时期贵州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的体认
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特殊的历史地位。众所周知,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五四运动,无论是政治事件还是社会变革,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每一次历史事件,每一个社会中发生的变化,其前奏都是源于知识分子兴起的思潮。抗战时期,边疆民族问题随着贵州成为陪都重庆的屏障而再次摆在了知识分子的面前,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贵州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群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身份认同:即民族身份认同和政治身份认同,而这两种身份认同又各自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
民族身份认同就是对贵州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自己所出身的民族的族属的认同感,这种单一的民族身份认同与“中华民族”这个国家民族身份的认同是一种有机结合,换言之,就是狭义民族身份和广义民族身份两个层面的认同。政治身份认同同样是两个层面组成的,一个层面是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两个核心政治问题——抗日战争和国民政府政权的合法性的判断,另一个层面是对当时的党派政治所持的立场。实际上,对身份认同的这种归纳和区分不但体现的是一种逻辑上的顺序,同时也隐含着有关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一条时间线索。对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的贵州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民族身份是在出生时即已确定的,他们对这个民族身份的认同则必然在他们成年前后就已形成定式,所以,有关民族身份认同的问题是在时间上最为靠前的。政治身份认同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大多在时间上比较靠后,所以当然是排在最后的位置上。
对汉族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民族认同主要表现为一种矛盾的态度,即在他们身上同时存在对少数民族的好感以及一种居高临下和猎奇的态度。一方面,他们真心实意地尊重和关心着民族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居民;另一方面,他们日常生活和研究成果中流露出来的态度又多少含有一些居高临下的蔑视和充满猎奇的兴趣。很显然,这种矛盾的态度正是他们对自己的汉族身份认同的一种直接表现。而推动民族地区发展本身又是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身份直接认同的体现,所以说对民族地区开发的态度体现为对广义民族身份的认同。因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前的成功事例,使得当时的有识之士普遍认为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开发可以有效地应对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危机,所以出于这个目的,当时汉族知识分子普遍赞同一种同化式的开发,由此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同化构想,即通过开发边疆民族地区的努力而彻底消除边疆和内地的区别,最终通过完全同一的共同点而形成不可分割的向心力。而贵州民族地区出身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对此并不完全赞同,特别是其中对于当地原住民尊严的忽视是这些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最为反感的。换言之,抗战时期汉族知识分子将汉族和中华民族等同了起来,认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就是对汉族的认同,所以在强调民族认同的问题上,汉族知识分子主张施行全盘的汉化;而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反对将汉族和中华民族等同起来,主张的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中华民族。苗族知识精英梁聚五认为“国族融合”与“民族平等共存”之间“一点也不矛盾”。唯其要做到“国内民族一律平等才说得上构成天衣无缝的‘国族’,使他无丝毫的差别……弟兄虽有高矮肥瘦不同,可是他们的地位,是绝对平等的”[1]。梁聚五认为民族平等、民族权利和民族地位,和文化同化是不能等同的,国族融合应该是国家体制上的融合。这就是抗战时期贵州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广义民族身份认同。
1939年发生的一场有关“中华民族”概念的论战中,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一个自古以来就真实存在的客观整体,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否认汉、满、蒙、回、藏这个层面的民族的存在,认为这种民族划分的概念不但不符合中国的历史,而且是外国侵略势力编造的一个分裂中国的借口。接受西方研究范式的知识分子则反对这种观点,认为“中华民族”的概念暂时还不是一个事实,中国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2]处于国家政区边缘,同时也是文化、经济、政治、社会边缘的贵州民族地区,因抗日战争而凸显为中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战略大后方,获得了超越性的提升和更为严峻的考验。在中国重心向西南偏移时,贵州各民族以积极的心态,回应了历史关键时刻的召唤,不辱使命地担当起自己的历史重任。而这一激剧变迁过程所彰显的,正是历史学家们从单一方面永远也做不到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在“现代国家”形成的“世界时间”与作为现代批判基础的阶级分野二者之间表面张力与深度合力共存一体的复杂内容。[3]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也推行了不少政策和措施,使贵州少数民族发展空间得到拓展:学生可以不受身份、出身进入学校,特别是军事类学校;杰出知识分子可以在政府和军队任职。在抗日战争时期,贵州众多的少数民族知识精英,如罗启疆、欧百川、万式琼、吴绍周、陈泰运、谢世钦、龙骧、梁聚五对国家的形势和民族状况,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他们了解本民族并主动担当民族图存的历史使命,运用本族社会的动员机制进行抗战的动员和组织,主动认同中华、自觉融入国家体制,主动担当国家使命,激发和坚定了少数民族抗日决心。[4]
这些少数民族的知识精英们并不认为自己民族的存在会使建构一个统一的国族身份变得困难。因此,贵州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文化优势,使得少数民族的身份建构与国族建构重合,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独有贡献,从而完成贵州少数民族与国家的整合,为民族的民主意识的强化提供了内生驱动力。
三、抗战时期贵州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对民众民主意识的启蒙
20世纪初叶的贵州,处于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化、转型的历史裂变期,各种外来的、国内的新思想不断冲击各种传统思想。伴随新文化运动而来的,是各种新思想在贵州的竞相传播。各种新思潮、新观念、新事物、新风尚的奔涌激荡,直接孕育和催生了一批先进的贵州知识分子。他们奔走呼号,为改变贵州的落后现状奋不顾身,认为贵州要想在20世纪之世界图存,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同时基于对军阀统治的强烈不满和变革图强的渴望,贵州有识之士,一方面倡导实业救国,希望通过开矿业、修铁路、办工厂、兴商贸来改变贵州的经济;另一方面,提倡教育救国,教导人民学科学,学民主,学文化,以图在文化教育方面改变贵州人民的思想;同时也倡导西学救国。鉴于中国当时总体落后的状况,他们希望贵州学习国外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武装自己的头脑。“五四”前后的贵州,各种思想相互冲击融合,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既有盘根错节的传统思想的存在,同时也有代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启蒙思想理论传入中国。
贵州民族社会民主革命、民主思想的传播最为突出的是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期,此时期对贵州民主思想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
第一,抗战时期贵州作为后方,东部的工矿企业、学校迁入贵州;第二,抗战时期民族教育在贵州国民政府推动下的蓬勃发展,贵州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使贵州民族社会中各族群众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贵州的各族群众思想意识上升到“现代国家”的高度。
这种变化从辛亥革命时期在贵州主要城市就已经开始出现,贵州的各族人民开始把自己作为国家的一员去关注国家的命运,并为实现现代国家的梦想而奋斗,然而这种情况只在贵州少数城市的部分先进分子中产生,还未在广大的乡村社会中出现。到了抗战时期,随着各级各类民族教育的建立和普及,贵州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深化了各族民众的国家认同,使贵州边缘地区和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萌芽了“现代国家”的意识。抗日战争的爆发,贵州乡村的民族社会被卷入到了对“现代国家”的体认中,不仅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的一员,更把自己看成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对日寇的入侵同仇敌忾,完成了贵州全民族社会从阶级到“现代国家”的升华。
清末、民国时期,贵州经济的发展使整个贵州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新文化的传播和民主思想的播布,又逐渐形成了新的文化层,新的文化层和社会经济基础构成了社会的转型,贵州社会各族的文化在这种大环境的变化影响下,整体上也发生了迥异以往的跃迁。这种变化并不是说对贵州民族社会以往传统文化的完全颠覆,实际上在贵州民族社会的传统文化中有变和不变的区别,比如服饰,经历了民国时期直到50年代,贵州各民族的服饰仍保留了各自的特点,各具特色,多姿多彩。而变化其实也是明显的,值得关注的一方面是新式教育进入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引发的文化变迁,另一方面是民主思想的传播引发的贵州少数民族思想认识的变化。
首先,是新式教育进入对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引发的文化变迁。这里所说的新式教育实际就是指不同于贵州各民族社会的传统教育模式的教育方式,因此可以说贵州接受新式教育较早的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黔西北。从20世纪初期开始,基督教在黔西北苗族地区传播,许多传教士在当地传教,还创办了教会学校来培养当地民众。如循道公会基督教在1905—1920年在当地先后创办了15所教会小学。基督教文化的传播和教会学校的兴办,使得当地的苗族社会的文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宗教信仰从原来的信仰多神的自然宗教发展到信仰单一神的基督教。生活习俗上,当地的苗族社会开始了人畜分屋居住、有病求医等良好的生活习俗;在婚姻习俗中产生了许多限制,如同村不婚、同姓不婚的规定,就是对近亲结婚的限制。教会学校把东西方文化直接传播到苗区,为苗族社会培养了一批人才,并产生了苗族的知识分子。
以上以贵州苗族为例,论述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及对苗族社会的影响。实际上对贵州民族社会来说新式教育大规模的进入是在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发展边地教育的文件,此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许多新式学校。193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贵州开办了安龙实验中学,招收苗族和瑶族儿童;到了1936年贵州省教育厅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地创办了12所省立边疆小学。除此而外,其他类型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乃至于师范教育都得到了发展。可以说上世纪30年代以来新式教育基本深入到了贵州的各民族地方,影响着贵州的各个少数民族,带来各民族社会的变化。
其次,是思想认识的变化。随着民主革命、民主思想在贵州的传播,使贵州民族社会群众的思想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许多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投身到抗战建国的洪流中,为民主国家的建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正是在这些先进分子的影响下,贵州民族社会的思想认识有了改变。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民国时期贵州的社会转型乃至于民族关系的重点主要是在贵州各族人民对现代国家的认识上,贵州人的视野和想象空间,“一个全新的‘大地域’即‘国家意识’充满诗意地萌生在中国边地小城年轻一代的心中,这意义是不可低估的。”[5]
这样贵州人在经历了同情,而后同仇敌忾的情感变化之后,在大地域的观念萌生之后,原有的民族意识、阶级意识在无形中得到了升华,一个大民族——中华民族的概念由此扎根,在此观念之下,人们认识到在某种意义上不管哪一支少数民族都是这一大民族——中华民族的一分子,都是现代国家的国民,都有抗战守土的神圣职责,因此一个“现代国家”的意识开始深深地扎根在贵州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