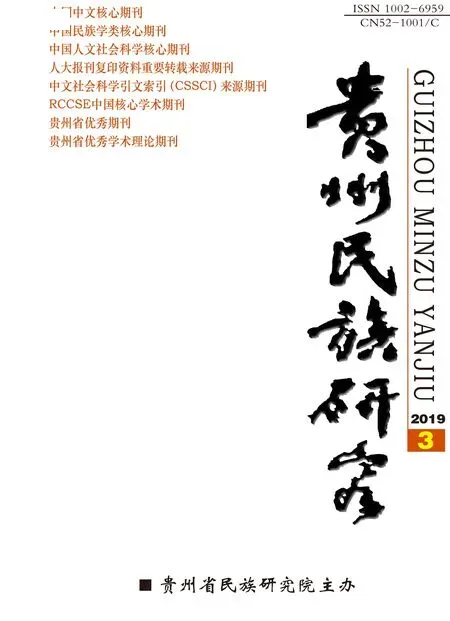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的历史演变探究
王 剑
(长江师范学院 重庆民族研究院,重庆 408100)
西南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浓郁的原始族群形态为少数民族农耕文化的凝聚和传承提供了天然屏障[1]。作为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西南地区至今保留着55个少数民族群众不同程度的农耕文化足迹和30个常住民族的农耕文化要素。以神秘宗教文化为纽带,以村寨为基本耕作单位,以原始生产为模式的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在历史岁月的打磨下具有鲜明的阶段性。一方面,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具有超凡的稳定性,比如:西藏地区以农奴制为基石的农耕文化和摩梭人原始家族式生产关系延续至“三大改造”前后;另一方面,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在历史演变中同中原农耕文明相比具有相对的多变性,比如:独龙族农耕文化在历史演变中实现了“游耕”到“农耕”的转变。此外,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又具有强烈的前瞻性,比如:独龙江流域的独龙族群众“轮歇耕作”思想、基诺族群众依据土地类型“定期轮歇”观念等同可持续发展理念不谋而合。总之,西南少数民族“依山傍水”“仰天靠地”的农耕生产即是西南得天独厚地理区位优势的映射又是西南农耕文化历史追溯的“活化石”。[2]立足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独特性的全局透析,以民族农耕生产特征为导向,审视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的历史演变,进而以历史的维度追溯农耕文化的特色与礼俗,聚焦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的典范与精髓,从而为构建民族文化共同体夯实内部机理。
一、原始混合的生产——农耕方式的渐进性分离
西南作为农耕与游耕、采集与狩猎生活方式的交汇处,在基本生活方式的选择中并非先天性以地理环境为导向,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长期处于原始母系式社会,同“男耕女织”的中原农耕文化截然不同。[3]比如:摩梭人在“舅掌礼仪母掌财”的母系式社会中主要以狩猎和采集为主,以简单刀耕火种的稻谷种植为辅。纵观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的历史演变,基本上都经历了不同生产方式混合的时期,一方面,部分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处于原始社会,社会生产力落后,狩猎、采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始终占据着物资资源获取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西南少数民族在不同生活方式和农耕要素的优化中实现了农耕方式的渐进性分离。首先,西南少数民族依山傍水的游牧生活习性逐渐转变为定居式的生活,比如:纳西族群众早期处于“渔猎时代”,在围绕玉龙山逐渐定居后,以“领主经济”为主导的农耕方式被长期固定。其次,“谷种”在少数民族原始混合的生产过程中逐渐被发现,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耕方式的渐进性分离奠定了基础。比如:北盘江流域的布依族在文学作品《茫耶寻谷种》中以传说的形式描述了布依族儿女在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期发现“稻谷种子”事迹。再者,西南少数民族在原始混合耕作方式中不断创新改造,“刀耕火种”的简单农耕方式逐渐向以石器农具为主导的农耕模式转变。[4]比如:水族群众在耕作初期通常“火耕水耨”的粗放式耕种。加之,伴随而来的农耕社会组织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由原始混合的生产向农耕方式的渐进性分离。再者,同中原农耕文化所不同的是,西南少数民族在不同“游耕”过程中对各种动物进行了尝试,最终在狩猎和农耕双重作用的影响下形成了以“牛耕”为主的农耕文化。比如:羌族“羊图腾”习俗大致与农耕有关。此外,随着中原封建政权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辖和文化融合,中原农耕技术也相继传入西南民族地区。
二、仰天靠地的生产——农耕文化自然性的合成
“天时地利”是农耕文明赖以延续的基础,是农耕文化不断沉淀的引子。虽然西南少数民族在农耕方式上具有独特采集、狩猎的混同,但是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也受自然条件和区位优势的制约,仰天靠地生产的农耕自然性成为农耕文化独特性生成的关键。换言之,仰天靠地的生产——农耕文化自然性的合成是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历史演变的主要阶段。
一是西南少数民族农耕依旧注重区位优势的选择。传统农耕活动的地理依赖性是机械化农业难以媲美的,西南少数民族在农事活动不断选择区位优势显著的环境进行农耕,特别是早期在云贵高原,以游耕为主要特色农事活动成为西南少数民族仰天靠地的见证。[5]一方面,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活动兼顾水田与旱地,在土壤肥沃的田野进行农事活动成为普遍现象,比如:佤族通常在平坦开阔的地方进行粗放式的“刀耕火种”和“挖犁撒种”。
二是西南少数民族在仰天靠地的农事活动中不断依托地理环境进行农具革新。农具革新是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历史演变的活化石,同时也是西南少数民族农事活动不断成熟与完善的结果。一方面,西南少数民族农具随着历史不断革新,成为农耕文化历史演变的主线;比如:云贵地区的怒族群众在冶铁技术尚未掌握之前,从石器时代的“石锄”到“竹锄”不断在重量和长度方面改进。另一方面,在生产力水平提升的基础上,西南少数民族在敬畏自然的前提下尝试改造农事活动的地理环境,从而也推动了农具的革新。比如:夜郎地区的侗族先辈在水资源短缺和干旱时不断改善简易灌溉工具,在历史变迁中相继发明改善了“龙骨水车”等灌溉工具。
三是祈求风调雨顺的农耕的自然性逐渐向社会性合成,成为农耕文化的重要体系。一方面,以自然崇拜为主的原始宗教形态在农耕文化的历史演变中基本确立;通过原始自然崇拜达到祈求天地风调雨顺、农事顺利的目的。比如:早期怒族群众信仰自然万物,通常由“尼玛”定期向天地祷告,祈福避灾。另一方面,西南少数民族在早期农耕活动影响下的宗教活动几乎都同农耕密切相关;比如:早期丽江一带纳西族群众在传统宗教东巴教仪式中有“祭天”“祭风”的宗教活动。总之,随着仰天靠地式农事理念的弱化,祈求风调雨顺的农耕的自然性逐渐向社会性合成,即祈求自然的农事习俗逐渐演变为具有鲜明社会属性的宗教活动。
四是以自然为出发点的务农观念的生态思维不断孕育。[6]西南少数民族在务农中长期以地理环境为主导,不断进行粗放式耕种,但是纵观西南少数民族务农观念的历史演变,由粗放式耕种向可持续发展的朴素生态思维的让渡成为农耕历史演变的主旋律。一方面,随着农耕的大幅度推广和自然灾害的濒发,以轮耕为中心的生态农业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西南少数民族通过农耕要素的节约彰显生态思维,比如:早期水族群众利用梯田进行节水,成为世界范围内原始节水农业的典范。总之,西南少数民族在仰天靠地的农事活动中不断由粗放式耕种向精耕细作转变,务农观念中的生态思维也不断显现出来。
三、村寨与家族组织——农耕文化变与迁的纽带
村寨与家庭组织是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历史变迁的纽带,特别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家族式协作耕种既可以凝聚劳动力,又可以弱化自然灾害对个体农耕户的挫伤。[7]加之,西南少数民族长期处于原始社会,以原始公社为基础的农耕组织的变迁,成为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历史演变的核心,富有原始气息的公社的确立与瓦解的同时以土地为基石的劳动关系也随之变迁。西南少数民族早期农耕组织可追溯至以母系式为中心的原始公社制,土地归公社所有,提倡共同耕作,平均分配。[8]比如:仫佬族先辈早期组织主要以原始社会公有制为主,在进入封建社会后,土地逐渐私有,以雇佣关系为主的剥削也相继出现。此外,佤族农村公社制作为农耕社会性的集中反映,在佤族村寨土地推行公私所有制,个体私有土地具有自由租赁等,而公社所有土地为公有制。在农事活动长期演变中以“珠米”和“普查”为主的阶级雏形凸显,以家庭为单位的“库普莱”则同中原自给自足的小农组织相一致。此外,怒江傈僳族“伙有共耕制”也是土地公有关系的典型,但是傈僳族在以“卡”(村寨)为单位的共同耕作历史演变中逐渐丧失原始家族纽带,逐渐演变为行政化的组织。同原始公社相对应的氏族组织也是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历史演变的起点,不过氏族组织在农耕社会的变迁中最终也被封建领主经济所取代。[9]比如:金沙江流域的普米族群众早期生产组织以氏族组织为主,在家族内部至今推崇以父系为主的家庭组织,在农耕文化演变中以氏族为单位的土地所有制也被以私有制为主的封建领主经济形式所取代。当然,在农耕文化的历史演变部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多种土地所有制并存的情况,比如:布朗族家族公有、村社公有和私人占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依旧存在,成为支撑农耕文化传承的关键。总之,以家庭组织为整体,以族群等级关系为依托的社会组织的变迁成为映射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历史演变的镜子。
四、礼俗与宗规并举——农耕文化社会性的凝聚
首先,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在历史演变中,传统礼俗始终凝聚与传承。[10]一方面,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婚姻习俗和丧葬习俗在农耕文化的历史演变中不断传承,成为少数民族农耕文化变迁原生态文化的体现。比如: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在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喜而不悲”的丧葬活动。另一方面,在农耕文化的演变中西南少数民族典型的生活习俗也得以延续。比如:白族农耕文化始终具有采茶元素的因子,在白族礼俗中“三道茶”是其农耕礼俗的精髓。其次,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在历史演变中,以农耕为主的节日习俗日益丧失原有的价值体系。比如:“添粮”本是农耕时期仫佬族群众驱病祈福的仪式,而在农耕文化的历史演变中逐渐成为宗教活动。此外,西南少数民族群众为祈佑丰收形成了庞杂的农耕礼俗,但是随着农耕技术的改进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原有节日礼俗逐渐演变为群体休闲嬉戏的活动。比如:毛南族“分龙节”、苗族“烧鱼节”等都从祈佑丰收的农耕礼俗转变为休闲活动,而直接以农耕为主的农耕礼俗在历史演变中逐渐丧失了存在的价值。比如:侗族“开秧节”在历史演变中逐渐丧失了其生存的土壤。
再者,在家族宗规中农耕文化的历史演变也被烙上了岁月的轨迹。[11]比如:摩梭人在早期农耕文化中逐渐形成了“舅掌礼仪母掌财”的家族宗规,集中反映了母系式社会农耕文化的基本特点,而延续至今的摩梭人“走婚制”也是早期母系式农耕文化的体现。此外,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的历史演变逐渐融入到文体活动中。比如:白族荡秋千源于采荞活动时的启迪,在历史演变中成为体育竞技活动,仫佬族体育项目“象步虎掌”则是农闲时群体娱乐的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西南少数民族鲜为人知的农耕精神文明。当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常见的“插秧舞”“采茶曲”等都是农耕文化历史变迁过程中不可磨灭的文化存在。
五、创新与多元交织——农耕文化演变的主心骨
创新与多元交织是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演变的主心骨。一方面,少数民族在长期仰天靠地的农事活动中,自然敬畏在基本生存的抉择中被有限地突破,传统刀耕火种的农事活动不断被创新,修建梯田成为西南少数民族农事活动创新的基本跨越。[12]另一方面,面对天灾人祸,西南少数民族在耕作类型上逐渐实现了多元化,同时不断革新农具,侗族水碾等农具不断改造与完善,极大地提高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耕水平。多元是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历史演变的关键,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融合了旱地和水田的农耕形式,在农耕文化的变迁中,狩猎文化、采集文化、渔猎文化始终相辅相成,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独特农耕文化的形成和演变提供了有益的补充。同时,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也推动了关联文化形态的发展。
总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集狩猎、渔猎、农耕、采集为一体,在农耕中稻麦结合耕作,水田与旱地结合的自然环境中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原始农耕文化,并在历史演变中逐渐实现了游耕到农耕的过渡。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历史演变的时间维度中基本同石器时代和铁器时期的转变相吻合。[13]就西南少数民族的农耕文化而言:农耕观念由粗放式耕种向生态农业观念的转变成为西南少数民族农耕文化的精髓,而农耕礼俗的历史演变成为农耕文化变迁的内在机理的完善,当然以农具革新为主的农耕要素的历史演变则成为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