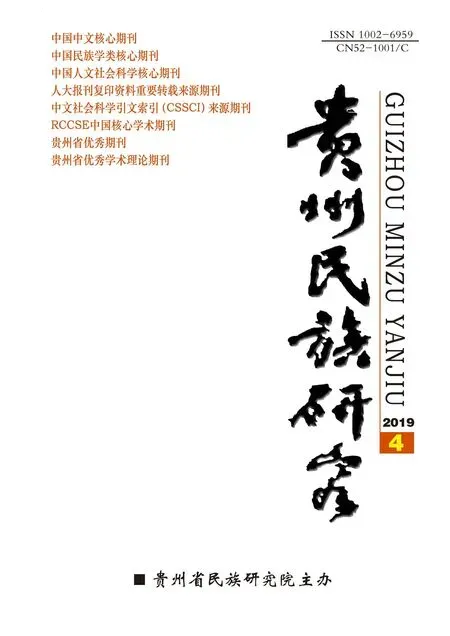民族地区廉政文化对社会法治的影响探究
李玉瑶 李景平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 710049)
廉政最早出自《晏子春秋·问下四》,是对从政廉洁的基本诉求。廉政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精髓,特别是士大夫清官情结的社会性认同与接纳,使得廉政文化同腐败相对立,延伸至社会整体治理,法治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机制,法治的刚正不阿、社会公正密切关联。民族地区在廉政文化认同与形成中逐渐将廉政同社会法治相关联,使廉政文化成为推动民族地区社会法治建设的牵引器。比如,青海藏区通过传统民族乐曲《都兰民间音乐廉政唱词选编》宣传反腐倡廉文化,特别是《十劝干部要廉政》将廉政文化同依法治国融为一体,有效地推动了都兰社会法治建设。民族地区廉政文化是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中不断积累,被大众所认同的文化形态。探究民族地区廉政文化对社会法治的影响,就要通过民族地区典型廉政文化的历史追溯与整合,审视民族习惯法框架下廉政文化的主要内容和载体,从而以民族廉政文化的习惯法摄入为切入点,探究民族廉政文化对社会法治的影响。
一、民族地区廉政文化的概述
(一)廉政与廉政文化的历史追溯
民族地区的廉政文化是社会运行机制阶级性凸显的产物。一方面民族地区生产力落后,经济驱动下的特权成为民族廉政建设的桥头堡,特别是新时期民族地区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落差始终是推动民族廉政建设的牵引器。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群众普遍具有自然崇拜和宗教信仰习俗,特别是宗教力量在社会法治中的摄入,容易造成个人崇拜和权力膨胀,使得民族廉政和廉政文化的历史轨迹基本上以杜绝特权为基本,而廉政文化则以民族宗教教义为载体。因此,民族地区廉政建设早期以杜绝专权、特权为主。比如,瑶族在“羁縻制度”的行政机制下颇为注重廉政建设,民族地区行政长官受驻军统领监督,避免民族首领的专权。在廉政文化方面以宗教文化最为显著。民族地区廉政建设中廉政基本上同奉公、社会公平、制裁公正相关联。此后,随着民族社会管理组织的完善,法治、公正成为廉政建设和廉政文化聚焦的核心。比如,西南布依族、德昂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议榔制”“寨老制”的确立,社会管理中的奉公、为民成为法治与公正所指向性的廉政建设目标,特别是后期民族地区廉政与廉政文化则以反对苛政为主,廉政文化也以反压迫剥削为主,建国以来民族地区经济腐败较为严峻,民族地区廉政文化以清廉为民为基本出发点。
(二)民族地区廉政文化的特征
民族地区廉政文化既具有文化的基本属性又具有廉政文化的特质,但是民族地区廉政文化具有自身独特属性。总体而言,首先,民族地区廉政文化具有法意志性,民族地区廉政文化基本上同民族习惯法关联。一方面民族习惯法是廉政文化的有效载体,在民族习惯法中有关廉政的要求基本上以乡约寨规、宗教教义等习惯法的形式承载。比如,独龙族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乡约寨规影响,在反腐倡廉中以禁止贪污受贿的乡约寨规以民族习惯法的形式承载,对于纳木萨(巫师)则以乡约寨规等引导着他们遵纪守法,歧视权力滥用。另一方面,以民族习惯法为主要形式的法治文化是民族廉政文化的集中反映。比如,为杜绝渎职、权力滥用维持审判公正,在原告与头人同村时以“捞水锅”的神判为主。其次,民族地区廉政文化具有家庭性。毋庸置疑,廉政文化基本以公权力性、公共性著世,但是民族地区以族规祖训为主要形式的廉政文化则以旨在引导家族内部成员克己奉公、廉洁为政,塑造家庭廉洁氛围。比如,侗族等土司家族通过族训的形式,传递祖先勤政廉洁的事迹,在祖祠祭祀中族训成为渲染廉政氛围的纽带。当然,以族规祖训为廉政依据的家族基本上以世代为官者诸多,在廉政文化中渗透着遵纪守法的君子品行和尚洁尚俭的官德。再者,民族地区廉政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廉政文化的重心先后从抑制经济特权到权力滥用,再到社会法治公平,廉政文化的载体和传播也具有时代性变迁的轨迹[1]。
(三)民族地区廉政文化的内容
民族地区基本上分布于边远山区,社会生产力落后,特别是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长期处于奴隶制社会,阶级特权和经济利益的差异使得少数民族群众在社会生活中格外注重掌权者(执法者)的秉公执法、廉洁为官的朴素廉政文化,具体表现为“重廉”“从俭”“务实”等。纵观民族地区廉政意识、清廉为政的社会评价和施政为民的信仰,民族地区廉政文化的内容主要表现为:首先,从廉政主体而言,主要为元老、族长等,少数民族地区受社会运行机制的影响,社会治理和法制裁决都基本上以元老或者社会中有威望的人掌握,特别是部分少数民族长期处于母系式社会和奴隶制社会,私权力的扩张和经济特权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在反腐倡廉的廉政建设中廉政文化基本上以限制公权滥用为主。比如,凉山彝族聚居区在涉嫌亲属利益的事务决断时毕摩作为掌权者必须自动回避,并在历史发展中成为常态化的为官者道德和社会公德。加之,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融合,中原“为政以德”官德修养,逐渐成为为官者(掌权者)自觉形成廉洁人格的关键所在[2],比如,东乡族民间就有“廉政为民,大济苍生”的传说。其次,从廉政环境而言,民族地区廉政文化以家庭廉洁、部落奉公、社会廉政为主线。以家庭廉洁为主的廉政文化基本上以族规祖训为主,一方面世代沿袭爵位的土司、名门一般以“君子修为”的官德教育后辈廉洁奉公,比如,哈尼族群众以牛石碑和祠堂训诫为载体,训诫后世廉洁奉公,对徇私枉法等腐败者禁止参加宗庙祭祀活动。另一方面,以族规祖训为廉洁规范的制度传承,以制度的形式杜绝腐败的滋生,比如,鄂伦春族群众在家庭内部私权扩张导致的违反习俗的行为也视为腐败。再者,从廉政客体而言,民族地区廉政文化涉及从政执法者的廉政、社会清廉风尚等。一方面民族地区廉政文化主要以从政者廉洁品行为主,注重廉洁、尚公的修为。另一方面,廉政文化以社会公平正义,特别是法治公正为重心。比如,彝族、侗族习惯法中基本都有回避制度。
(四)民族地区廉政文化的载体
民族地区廉政文化作为传统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始终是整个民族传统文化的混同体,或者说民族廉政文化是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关廉政、反腐文化的浓缩。且民族地区廉政文化在岁月的洗礼中逐渐刚性的习俗规范演变成为群体思维[3]。总体而言,民族廉政文化通常以民族群体喜闻乐见的音乐艺术为载体。主要表现为三类:一是直接歌颂廉政廉洁文化,使民族廉政文化通过民族音乐不断传播,比如,藏族群众说唱音乐《唱廉政、颂清风》直接从正面传送廉政文化。二是民族音乐、说唱艺术对腐败、渎职等现象的披露,以欲扬先抑的表达手法突出廉政廉洁文化。比如,苗、瑶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印制《桑江清风》使民族传统廉政文化不断深入人心。三是通过民族戏剧等形式将廉政文化让渡至社会生活的细节。比如,藏族群众通过格萨尔王事迹以戏曲形式,以英雄事迹折射廉洁重要性,突出特色民族廉政文化。
民族习惯法是民族廉政规范的法意志上升,是民族地区廉政文化的窗口,民族廉政文化基本以世代传承的民族习惯法为载体。一方面民族地区将大众喜闻乐见的反腐倡廉习俗上升至习惯法高度,使廉政文化成为典型的法治文化,比如,黎族等少数民族在祠堂、村寨石碑上以咒语的形式诅咒群体间的腐败、公权私用行为等,通过乡约寨规等习惯法的形式逐渐使得廉政成为一种潜在的社会规则。另一方面,民族习惯法通过“立法”的形式承载着民族地区反腐倡廉,特别是基诺族、门巴族、僜人等,对权力滥用、腐败、变相贪污都有明确的制裁,比如,哈尼族群众对公权私用的行为基本以逐出村寨、对于贪污严重者处以“浸猪笼”的惩戒[4]。在凉山的部分地区以实物折算贪污情节的规定至今仍在沿用。
民间谚语、传说是文化传播最为朴素的途径,廉政文化的社会认同与评价体系使得谚语、传说成为反映民族廉政文化最为显著的载体,比如,蒙古族谚语“君廉政,国运久”等都是廉政文化的基本体现。当然,廉政文化作为社会公德体现民族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基本上依托社会载体将清廉与腐败在对立、对比中呈现。
二、民族地区廉政文化同法治的关联
民族地区廉政文化同民族法治密切关联。首先,民族习惯法折射着民族廉政文化,是民族廉政文化最为丰富的地区。一方面民族廉政文化基本上以民族习惯法为载体,以廉政文化为民族地区法治标杆的廉政文化映射着民族廉政文化的形态[5]。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廉政文化推动着民族地区法治社会的推进,特别是廉政文化的法意志上升,比如,彝族群众的回避习俗从最早审判公正逐渐沿袭成为彝族刑事审判领域的习惯法。其次,廉政文化对民族习惯法的改造,严重影响着民族地区社会法治的进程,民族地区廉政文化的社会认同与接纳是推动社会法治的关键,廉政文化通常针对习惯法中的腐败、私权力扩张进行修正。再者,廉政同民族习惯法的社会混同,廉政文化对民族地区社会法治的纵横影响成为民族地区法治化建设的催化剂。
三、民族地区廉政文化对社会法治的影响
(一)民族地区廉政文化优化了社会法治环境
廉政文化对民族地区社会法治环境的优化是民族地区廉政文化对社会法治影响的基础[6]。首先,廉政文化的公权力指向性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释放着法治化信号—注重公权力的廉洁与务实,比如,积石山撒拉族聚居区为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以撒拉族党员干部喜闻乐见的廉政文化以“花儿”的形式不断在社区宣传,以干部监督机制和党员廉政约谈制为主要廉政建设的方式,不断彰显着廉政建设的法治力量。其次,民族地区丰富多样的廉政文化为社会法治建设营造了社会氛围,比如,鄂温克族以传统萨满教教义为载体的廉政文化,藏、回等少数民族以音乐艺术为载体的民族传统廉洁文化,为民族地区依法反腐,推动民族地区法治化建设营造社会氛围。再者,民族地区廉政文化为违法乱纪行为敲响了警钟,以反腐为契机的社会法治成为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必然趋势。
(二)民族地区廉政文化深化了法治的公德化
民族地区法治的公德化是廉政文化对社会环境影响的基本体现。民族地区廉政文化是民族群众赖以推行廉政建设的关键,特别是民族群众对社会廉政与腐败的对立认知与接纳是民族地区法制化推进的基础[7]。一方面廉政文化在民族地区的民族性传播和认同促进了民族地区廉政的社会公德化,使廉政的公共性逐渐突出。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廉政文化成为法治社会秉公执法、尚俭务实、施政为民的社会道德诉求,民族地区的法治转化为群体的社会公德意识。
(三)民族地区廉政文化提升了为官者的道德
廉政文化对为官者道德的提升是影响民族地区法治建设的关键。为官者的思想和道德是廉政、廉政文化的共同范畴,不同时期的民族廉政文化也基本上以社会廉政评价认同为标准衡量为官者的道德。首先,为官者理应有为政以民、士大夫清官清洁,这是民族廉政文化中对为官者思想和道德中最基本官德。其次,就民族地区法治而言,廉政文化立足个体的廉洁、为公,以文化道德的舆论压力使党员干部必然成为遵纪守法的先行者和楷模[8],比如,近年来独龙族、水族等民族地区以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制,使为官者(党员干部)自身的廉洁自律成为社会法治建设的窗口。再者,民族地区经济长期落后,经济腐败中个人经济特权成为民族地区廉政文化抑制的重头戏,比如,哈尼族群众以乡约寨规对为官者生活作风予以限制、提示,明确规定祭祀物品族长需在元老会盘算后放置,避免中饱私囊。换言之,民族地区廉政文化通过对个人作风建设的制约,强化了为官者的官德。
(四)民族地区廉政文化健全了法治的监督机制
对法治监督机制的健全是廉政文化对民族地区社会法治影响的核心。首先,民族廉政文化为法治监督树立了典范,特别是民族地区反腐倡廉和廉政建设中以监督员为监督机制的司法监督等成为推动民族地区社会法制建设的前提。其次,民族地区廉政文化制约了社会法治特权,为民族地区法治铺平了道路。一方面民族地区历史上一直沿袭族群特权,严重阻碍法治社会建设的推进,以廉政文化为基础大众性社会廉政建设有助于制约甚至取缔法治特权。另一方面,廉政文化以社会公平公正为基调,有助于法治同社会公正的法治化延伸。再者,民族地区廉政文化延伸了习惯法的机能,使得民族习惯法成为民族地区廉政建设的精神指引,有助于发挥民族习惯法在廉政建设乃至民族地区法治建设中潜在的监督机制。
总之,民族地区廉政文化以为官者思想道德、廉政风气等视域出发,以民族群体喜闻乐见的载体承载着民族地区朴素的廉政文化,以民族习惯法为主的载体性让渡,使之成为在民族地区社会法治建设中不可忽视的法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