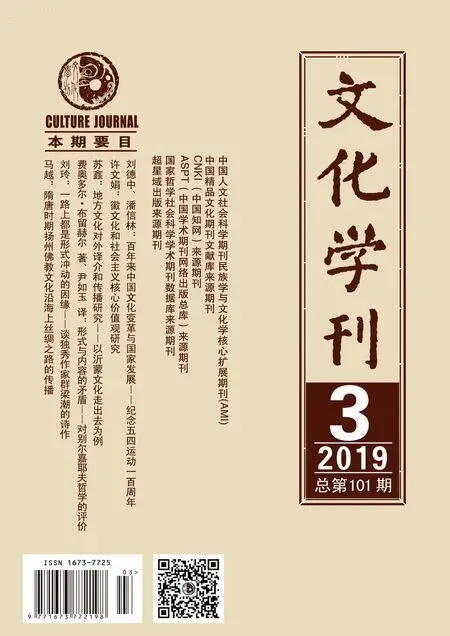论语言中反训的原因*
[荷兰]施古德 著 马爱琳 译 吴世旭 校
我们认为正是北京耶稣会的前任神父马若瑟[注]本名约瑟夫·德·普雷马尔(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马若瑟为其中文名,另有中文名马龙出,法国著名汉学家,代表作有《汉语札记》等。——译注在一个多世纪前注意到了汉语中反训(antiphrasis)或反义同词这一奇特现象。在其由裨治文[注]全名以利亚·科尔曼·贝格曼,(Elijah Coleman Brigeman, 1801-1861),裨治文为其中文名,美国派遣来华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译注于1847年翻译成英文的著作《汉语札记》(NotitiaLinguaeSinicae)中,马若瑟写道 :“很多字明显具有对反意义。这种情形被命名为反训;例如,亂(lwán)的准确意义是‘产生混乱’,但是它的喻义又与治(chi)和理(li)是一样的,后者指‘英明治理’和‘有序安排’。亂臣(Lwán-shin)是忠诚地帮助维护政府权威的人。毒(Tuh)的准确意义是‘下毒’,在《易经》(Yih-king)中它与指‘滋养’的養(Yang)同义。蠱(Ku)的准确意义是指被三个虫子即蟲(chung)腐蚀的器皿,其喻义是‘清洗’,因而又指将器皿恢复完好。清(Ts,ing)表示纯洁和干净,其反训的意义则是厕所。”[1]
1885年,阿贝尔(Carl Abel, 1837-1906)在其《语言学论文集》(SprachwissenschaftlicheAbhandlungen)第八章第313-367页中论及原始语词的反训时,提供了一份古埃及语的例子占三页、印欧语系的例子占四页、阿拉伯语的例子占16页的清单。
他试图找到这一奇异现象的原因,但并未成功。两个意义对反的词根的形似是偶然的;言说者通过身体姿势言说造成的区别;原始人没有能力想象抽象观念,除非通过对比,比如,只有从黑暗中走出来时,才能想象光明的观念,等等,他提到的这些原因,没有一个足够吸引人,也没有一个得到证明。
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原始人并非以这种细致的方式思考,就像我们现在不会如此思考一样。如果同一个词具有截然对反的意义,这是十分自然地产生的,而非通过细致的推理。这种对反意义可能是产生于把该词置于其主动或被动的形式中,产生于委婉语(euphemism),产生于讽喻(ironical metaphor),而主要的是因为具有两种对反意义的词汇的词根, 最初表示自然地从中衍生出这两种意义的其他某种东西。
以印欧语系表示“刺、挖”的词根dhigh为例。它的衍生词在德语中是Teich,Deich,在荷兰语中是dijk,在英语中是dike。在德语中,Teich意为池塘,Deich意为水坝,然而在荷兰语和英语中,dijk和dike仅保留了水坝的含义。尽管如此,在英格兰的一些特定地区,田地间的窄沟(ditch)仍被称作dike。
这个词的对反意义是非常自然地产生的。词根dhigh也存在于最初表示“挖出”的汉字剔(thik,剔骨、刺、挖出)中。为了建池塘而挖地时,挖出的土被抛堆到池塘边,形成一道屏障或水坝,所以词根dhigh就具有了双重含义,即被挖空的土和抛堆的土,因为挖和抛堆是不可分离的动作。在汉语中,兆刂剔(thiao thik)表示“切掉”,就像用雕刻刀一样,所以费克(August Fick,1833-1916)正确地从同一词根导出拉丁语fig-ra(图形,模子),fig-ulus(陶工或模工)[2],因为雕刻人像或其他图形,或者制作一个陶罐,就必须从制作图形和陶罐的木头、石头或黏土中挖掉(一部分)木头、石头或黏土。汉语中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即掘(khut)的词根,这个词根加上提手旁,表示“挖掘、开凿”。用土字旁或穴字头将其写成堀或窟,表示空的洞穴,用山字旁将其写成崛,表示陡峭的山,崛起(khut khi)表示“高高堆起,突然上升”。在荷兰,街道之间的沟渠被称为gracht,这个词在古代读写为graft,衍生于动词graven(挖),因此gracht表示“挖出”,但是街道本身也被称为gracht,正如挖出的池塘和从池塘中抛上来的土,都被称为dijk,Teich,Deich。防护沟渠的砖石墙在荷兰被称为wal;但是在大众的观念中,wal和gracht这两个词的固有意义是混在一起的,一个阿姆斯特丹的女仆会说,她把桶中的污水从gracht倒入wal(即从沟渠倒入墙,而不是从墙倒入沟渠)。
阿贝尔正确地将词汇blaec(昂格鲁-撒克逊语)、black(英语)并列起来,bleak(暗淡、浅灰)即表示“闪光”的昂格鲁-撒克逊语blican,blac则表示“暗淡”,但是为什么这些词汇语具有对反的意义?很清楚,英文black和bleak,和德语bleich(暗淡)及荷兰语bleek(暗淡)一定衍生于两个分离但同源的词根blic或blac。这两个词根肯定简化为一个 :bic或者bac,后者最初的意义是烤、烧。在汉字煏(pih)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形式,这个字古代读作“pik”,但是我们的《汉语-雅利安语》(Sinico-Aryaca)所表明的[3],在更早的时期,它读作bak,其最初的意义是“如火般蔓延、火势蔓延”;一个与梵文bhak+ta(熟的)相一致的词根,后者可能并非源自词根Bhaj,而是源自一个古老的等同于pak的词根pach。火不仅会发光(shines),而且也会燃烧(charres)并变黑(blackens)。我们把齿音r插入到意为“烤干、油煎、烧开”的词汇bhrij和bhraij中;并与意为“发光、变得暗淡”的印欧语系词汇blik,blaik,blikum结合,就变成意为发光、发亮的blika和blikja[4]。发亮的是白(white),但被发光的火烧掉的木头则是黑(black),对反意义是作为自然后果而出现的。
在荷兰的打印室内,排字工称wit(白)为黑色的铅灰空间,后者用来分离打印出来的词汇,因其比打印字母更短,没有着墨,所以在印刷纸的相应地方留有空白。在这种情况下,对反意义自然地衍生于白(white)纸上黑色(black)空间的相反效果。
同时表示底层和顶层或阁楼的德语词汇Boden,从这样的事实中衍生出其对反意义,即一个房屋的底层与其顶部都涉及安装木板。在德语中,底层以Fussboden的名称区别于顶层;但是木制地板的最初含义仍然保留在德语Tanzboden(舞蹈室)、Heuboden(干草棚)、Kornboden(谷场)等词汇中。
在很多语言中,没有表示“买”和“卖”的不同词汇,尽管有人可能会认为二者有很大差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卖家也是买家;他卖给别人的东西也是他自己从别人那里买来的。在荷兰语中,kooper(买家)一词有两种含义 :wijnkooper或houtkooper并非是酒或木材的买家,而是一个小贩(vendor)。
在汉语中,表示买和卖的词是mai,仅仅以不同的声调加以区别,即maì(买)和maí(卖)。甚至现在写成賣的出買,也是由買(maì,购买)字和出(chhut,出去)字构成的[注]賣从出从買,《康熙字典》。——原注。——再次售出买来的物品。
在拉丁语中,hostis一词表示“陌生人、客人”,也表示“敌人、仇敌”。这个词结合了哥特语的Gasts和昂格鲁-撒克逊语的Gest(陌生人或客人),语源学通常认为这个词衍生于意为“吃”的梵文ghas[5]。
这一转换并不难解 :陌生人可能是一个好的客人,也可能是一个坏的客人——敌人。在现代德语中,这个词经常有一点点褒义。
在丹麦语中,gast是指一个粗鲁的水手,在荷兰语中被称为varensgast(航海旅客);在德语中,ein schlimmer或ein b?ser Gast意为不受欢迎的访客、坏的顾客。同样,在汉语中,客(khik)字意为客人、顾客、陌生人,也表示非法占据者或掠夺者。暴客(paou khik)或“野蛮的客人”是一个强盗,刺客(tsz khik)或“持刀伤人的客人”是一个暗杀者。
在汉语中,縫 (fung)字意为“衣服的接缝”,作为动词表示“缝纫、接缝”;但同时也表示“缝隙、裂缝或木料的接缝”。手縫(Show fung)意为“手指间的空隙”;齒縫(chhi fung)意为“牙齿间的间隙”。山縫(Shan fung)意为山丘中道路或河流穿过的裂口。在这个词中,其对反意义源自即使被接缝闭合裂口或裂缝也总是依然清晰可见这个事实。这在意为“加入一个接缝”的汉语亻折縫(cheh fung)中尤为明显;合版亻折縫(hoh pan cheh fung)意为“连接两个板子并合并它们的接缝”,尽管亻折(cheh)字的准确意义是“切”或“刻”[注]亻折刻也,《康熙字典》。——原注。
意为“眼睛睁开看”的目黎(li)字和意为“闭眼”的睝(li)也属于同一范畴,因为即使眼睛闭上时,裂口或狭缝也依然清晰可见。我已经在我的《汉语-雅利安语》中详尽地阐释了词根li或ri的双重意义[6]。
汉字臭(chhow)同时意为“香和臭”[注]臭惡氣也。又香也,《康熙字典》。——原注。它最初仅仅是表示气味(smell),一种气味可好可坏;“花有味”意味着它是香的,“尸体有味了”意味着它臭了。
马若瑟已经注意到亂(lwán)字表示叛乱和良好治理。在《书经》(Shooking)中,可以看到这种意义上的乱,在《皋陶谟》(Counsels of Kaou-yaou)中 :亂而敬(lwán rl king)意为“治理而且敬畏”;在《盘庚》(Pwankang)中 :亂政(lwán ching)表示“治理的大臣”;亂越我家意为“上帝保佑我们帝国的善治”;在《洛诰》(Announcement concerning Lo)中 :四方迪亂(sz fang chik lwán)表示“整个帝国的四个分区已经开始秩序井然了”;在《梓材》(Timber of the Tsze-tree)中 :王啟監厥亂為民(wang khi kien kiueh lwán wei min)表示“君王们任命巡官是为了百姓的治理”;在《立政》(Establishment of Government)中 :丕乃俾亂(p,ei nai pi lwán)意为“让我们在治理中大量地任用他们”。
所有的这些可能在初见之下似乎相当难以理解,但这仅仅是看起来似乎如此。lwán最初的意义是“如同渔网线一样缠在一起”[注]亂紊也。参见《尚书·盘庚》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原注。无论什么被缠在一起,在它被使用前都不得不解开,然而,暂时的缠绕不会损害其原初的效用。混乱仅仅是对秩序的否定,当秩序恢复后,并不会留下一丝混乱。
下一个字也能更好地表明这种对立。汉字譲(jang)意为“放弃、退让,撤销某人的权力”,同时也表示“责骂、争吵与斥责、反驳”这些极尽对抗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人是非常礼貌的;客人绝不会优先于他人,即使拥有较高的权力,他也不会在一番争论、辩解、推让等等之前坐上主位或高坐,而在主人这边,则会请求、劝说甚至强迫其客人接受之。一个不理解中国人的外来者,听到两个中国人尝试通过争辩来赢过对方时,很可能会将其误认为是口角或吵架,说话者声音太大,姿态太鲜活。
这样的争夺之jang与放弃之jang听起来完全相同,但譲这个字却拥有两个对反的意义。事实上,jang最初表示“混乱”,因为它作为音素很明显地出现在其他汉字中。例如,与发结合成鬤字,就表示“凌乱的头发”,头发处于极度凌乱中;与土结合成壤字,就表示“密集的大众” :天下壤壤(tien-hia jiang jiang)意为“帝国中的人群”“国家的混乱百姓”;与手结合攘字,就表示“卷入”;与水结合称瀼字,就表示“泥泞、混水”;与禾结合称穰字,就表示“谷田的茂盛繁杂”;与示结合成禳字,就表示“免遭灾祸” :比如为了避免灾难而胡乱低声祈祷;最后,与言或口结合成譲字或嚷字,就恰当地表示“混乱地言说”,就像在人们放弃他们的权力或为得到它们而争吵时我们所听到的那样。在靠近厦门(Amoy)的漳州(Chang-chow),人群的嘈杂争吵仍然被称为jiáng。
举另外一个例子 :挾(hieh)字意为“帮助、支持、关爱”和与这些意义相对反的“勒索、压榨”。这个字由作为音素的手(show)和夾(kiah)构成,但它本身就具有与其衍生词相同的意义而且最初意为“用手臂拿起或抱紧”。当我们用手臂扶起一个人时,我们是在帮助并支撑他,而且我们这样做当然是因为关爱他。但是,当我们稍微加大力气抱紧他,就会夹痛和挤压到他,所以会导致他疼痛而非轻松。从这种身体上的挤压到炽烈的勒索观念,距离并非很远,而明显的反训也很容易解释。握着一个人的手是喜爱的信号,但是因为海军服役而握住他,就不能说是出于友爱而这样做。
忍(jin)同样具有表示“忍受或耐心地承受”和“残酷、冷酷、暴怒”这两种对反意义;忍氣(jin khi)意为“压抑一个人的愤怒”,但情懐忍忍(tsing hwai jin-jin)则意为“他的情感不能承受”。
如果我们看一下忍字的构成,就会发现它是由心(心脏)和刃(一把锋利的兵器)构成,即被匕首刺伤的心脏克制着疼痛(如刀刺心忍意也)。因此,其最初的意义足够清楚了,其次级意义则是最初意义的自然衍生。在心脏被刺伤时能够克制的人是一个强壮又强硬的人;对自己强硬的人常常也会对他人强硬,因为会期待他们能够和自己一样坚忍,所以就产生了同义的复合词殘忍(tsán jin),意思是“残酷”。转换成了一种道德观念,“承受”变成了“忍受”;如常人所言,内心变得“压抑”。如果内心压抑并忍受着悲痛,很容易会在哪一天爆发并发泄出去。忍耐并非无止境,长期压抑的情感最终会以大怒爆发出来。
汉字易(e)意为“从容、疏忽、冷漠”[注]易略易怠。——原注。它是怎样同时出现“时刻注意”这一反义的呢?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在其《论语》(Analects)中使用了这个字,“喪與其易也寕戚”(Song yü ki e ye, ning ts,ih),即“在丧礼中,深深哀痛比时刻注意仪式要好”。
在能够掌握孔子所使用的这种意义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注意易字的另一种意义。在《礼记》[注]禮檀弓。——原注中,易是在“砍掉、清除”这种意义上使用的 :易墓(e mu)表示“清理老坟的草木”[注]易謂芟治草木。——原注。孟子曰 :易其田疇(e ki tien ch,ow),即“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谷田和麻田得到很好的耕作”。
形容词easy衍生于名词ease,而这英语中是以动词的形式出现的,意为“缓解、减轻”。在好好除草的田中,仔细地清除阻碍谷物生长的杂草,谷物的生长就会加快,田地就会缓解(easied),因此在《孟子》的另一段提到了深耕易耨(shin king e nau)即“深耕,减少(ease)田地的杂草”,理雅各[注]全名詹姆斯·莱格(James Legge, 1815-1897),理雅各为其中文名,英国汉学家,伦敦布道会传教士,曾任香港英华书院校长。——译注准确地将其翻译为“深耕并仔细地注意除草”。
一旦这个比喻得以确立,“时刻注意”这一对反意义就成为易字的附属意义了,并在与其最初意义即“从容”或“疏忽”相对反的意义上被普遍使用。
此外,最初意为“去、离开、出发”[注]往之也、行也、去也。——原注的汉字往(wang),已经具有了“以前、过去、原先”的意义[注]往昔也。——原注。往日(Wang jih)即“过去的日子”。当一个人去另一个地方,就是沿着向前的方向,去一个位于我们前面但尚未到达的地方。所以在问何往(ho wang)或那裡往(na-li wang)即“你去哪”中和向往(hiang wang)即“意向、计划、一个人的思想方向”中,就意味着未来,因此,卫三畏[注]全名萨缪尔·威尔斯·威廉姆斯(Samuel Welles Williams, 1812-1884),卫三畏为其中文名,美国汉学家、传教士、外交官。——译注在他的字典中准确地把往字翻译为“未来”[7];因为你的想法有可能会向前也有可能向后。在雍正帝的《圣谕十六条》[注]《圣谕十六条》又称《圣谕广训》,雍正二年(1724年)出版的官修典籍,意在训谕世人守法和应有的德行。——译注(no. 16 of the Sacred Edict)中,我们可以看到自今以往(tsz kin I wang)的说法,即“从今天到未来(从此以后)”。
词典编纂者把汉字矯(kiao)定义为“改正、改正错误”和“伪造、冒充、伪君子”;其正确的意义是“把弯曲的扳直”[注]使曲者直為矯。——原注,所以在句子民彌惰怠,將何以矯之(Min mi to-tai, tsiang ho-i kiao chi)即“当人们懒惰时,我们将用什么改正他们?”中,可被扳直的东西也就是可被改正的不正当的或反常的东西;一个为了达到目的而扭曲自己的家伙,当然是一个伪君子、冒充者或伪造者,矫字的对反意义很容易就确立起来了。
跈或蹨(Nien)在汉语中意为“驱逐”和“连接”。如果回到最初的意义,就会发现它意为“踩踏、跺脚”[注]蹨蹈也。踐也。——原注。通过这样做,我驱散了我踩或跺的东西,就获得了“驱逐、赶走”的意义,但是,当我踩着另一个人的脚印,我就是跟着他的行程并在他与我自己之间建立联系。我变成了一个继续他在我前面之所为的人,如此一来,“连接某人的行程”[8]这种意义便自然地附着到了nien字中。
在意为“摆脱、扔掉”和“加入、合作”的投(t,eu)字中,这样的对反意义有更强的例证。你可以把骨头丢给狗即投與狗骨;你可以把自己扔到井中即投井(t,eu tsing);你也可以把自己扔到军队里即投軍(t,eu kiun)亦即参军或加入军队。
当处于绝望之中,你可能会把自己扔到命运的绳索之上即投繯(t,eu hwan);或者当你在战斗中被击败时,把自己扔给敌人由其处置即投降(t,eu hiang);但是你也可能把你的忧虑投入到对另一个人的信任上即投託(t,eu t,oh),意为“委托某人”。如果我们仅仅首先抓住两种截然对反的意义从中生发出来的词根的原初意义,就会明白所有这样的对反意义都是非常自然地产生的。
中国格言说到 :“在同一个树的果实中,我们会发现有甜的也有酸的;在同一个母亲的子女中,我们会遇到没用的和优秀的儿子”[注]一樹之果有酸有甜。一母之子有愚有賢。德庇时《中国格言》(Chinese Maxims)第十二条。——原注。德庇时全名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前者是其中文名。英国外交官兼汉学家。18岁来到中国,曾任香港第二任总督。此处施古德有笔误,应为《贤文书》(Chinese Moral Maxims),是德庇时编译的,出版于1823年。——校注。
这些少数例子可以为如何研究同一个词具有对反意义提供线索。但是,更多的反训是因为言语中两个强有力的因素 :委婉语和反讽。
荷兰人把他房子中最偏僻且最难看的房间——卫生间称为他的“最好的房间”,这仅仅是出于委婉的目的才这么说的。出于相同原因,中国人把这个地方叫做圊(ts,ing)即“清洁之地”,并非如中国词典编纂者所说的是因为厕所需要不断清洗[注]廁古謂之清者,言污穢常常清除也。——原注,而是因为把屋子里最脏的地方称为最干净的很好听,就像荷兰人把最差的房间称作最好的房间一样。因为人们通常不喜欢用其真名称呼丑陋的东西。我们将只引用“无法形容”词汇,一个有教养的英国人的口中不会说出这些词汇,尽管他偶尔会在散步时假装破衣烂衫的,并随意地说出它们。
在德语中,“eine saubere Dirne”可以表示整洁的女孩,反讽地说则表示肮脏的女孩。“Sauberes Wetter”表示好天气,有时也表示坏天气。当我对一个小伙子说“你是一个好(nice)男孩”时,我是故意告诉他,他恰恰是好的反面。“knave”这个词原先是一个非常高贵的名称,皇家纸牌游戏中的四大护卫就称为knaves或lads(德语为knabe,Knappe);如今这个词则意为“恶棍、无赖”。德语Bube现今意为“男孩”和“流氓、罪犯”,唯独后一种意义还保留在荷兰语boef中,它从前并没有这种不光彩的意义。
M?hreschalk或马夫源自一个男仆成为元帅或高级军事指挥官。只有法语maréchal ferrant(流浪的元帅)还能使我们想起其卑微的起源。这个词的第二部分Schalk,以前曾进入官衔并且只表示随员,已经因反讽而变得低下,意为“滑稽角色(wag)、流氓(scamp)或无赖(rogue)”。
在德语中,Dirne一词表示淑女、处女,也表示荡妇和妓女,恰如法语中fille一词有声誉良好和声誉不好之意。
进一步研究的话,更多的例子将会被引证,但我们仅仅是想引起学者对语言学研究中最有趣的部分的关注,为好钻研的人们开启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