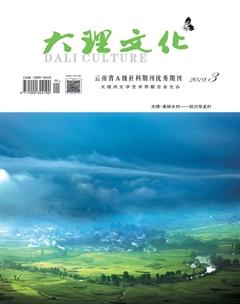那些年 那些事
那个冬天,抬头举目都有红花绿叶进入视线,因为我已经离开苦寒之地边远小县城剑川,抵达昆明。我的逐梦之旅终于由卷起裤脚的跋涉变成了击水行舟。是的,对我来说,昆明是一个码头,而我费尽心力跨了进去的大学以及将在这里的苦读,是我的舢板和对桨的划动。在这春深似海的省会城市,人生开始了又一次新的启程。
但我发现,昆明的春意不仅彰显在自然界,它已悄悄渗入人心的冻土。在1978年的那个冬天,一天下午,学校传达了刚刚闭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走出礼堂,同学们不约而同来到操场,先是艺术系的同学,继而是体育系的同学,手拉手跳起了青年友谊圆舞曲:
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
广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
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
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
……
白鸽在天空中展翅飞翔
青春的花朵在心中开放
……
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
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
优美而又燃烧着青春热情的词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望中的同学。在漫长的年月里,跳舞曾经是大逆不道的,但它却在这一刻真真切切、堂而皇之地如花朵一般绽放了。圈子越来越大,舞步由拘谨逐渐变得奔放,表情由羞怯逐渐变得自如,仿佛花瓣挣脱了一切束缚,纵情舒张……
然而,让人伤感的是,侧脸一看,与自己并排踏歌起舞的,却是一个比自己小八岁的姑娘,一缕悲情不禁在心中潜滋暗长。四年之后,也就是大学毕业前夕,我写了自己第一篇被发表于省报的散文《漫步在小翠湖》:“如果说,刚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刹那我曾经高兴过,那么开始学习后的第一天我就感到万分焦躁了。只要看看坐在自己旁边的那位比自己小八岁的姑娘,一种迟暮感就袭上心头。八年,自己拉下的距离是整整八年,这怎不使人心焦如焚?我恨不能蹬上风火轮,以最快的速度,追回那逝去的光阴。然而我很快就发现,大学并不是一座伸手就可摘取硕果的果园。它只是一叶扁舟,在求知的航程上驾驭它,需要的坚毅和勇敢,决不亚于一个水手。快节奏地进攻,向着单词、语法、公式、定律,我必须记住该被记住的一切;忘我地奋进,拨开怠惰、疲倦、悲觀,我必须驱除该被驱除的东西。”追回青春,在当时,不仅是我个人的心思,也是我们这代人最令人五味杂陈的誓言。
“在我的心目中,大学,是个很神秘的国度。从我刚开始上学,父母就天天对我讲,好好念书,好好念书,以后争取上大学。我觉得我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到大学去的长征。可是它那么远,那么远,老也走不到。从目前的形势看,也许我是永远走不到那里去了。我走得到的,大概只能是木工房吧。”在散文《悠远的芬芳——我的学徒生涯》里,我曾这么写。
其实,对于我,岂止大学,能否读初中都充满悬念。我的一篇题为《少年心事》的文章中,有这样的字句:
初中录取尚未张榜,就有人告诉父母,我被录取了。母亲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仍然不免担心。她总是对传递消息者说:“谁知道是不是真的?眼不见,心不烦。”后来我就跑到县中去看榜,不但高中了,而且是全县第一名。
考得好,是早就知道的了。我的考试作文,还被印发给全县小学生,人手一份,作为样榜。这是一位参加了阅卷的老师悄悄告诉父母的。但能否被录取,还取决于政审。母亲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点。也是这位老师说的,由于我家庭出身地主,父亲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二伯和大舅均是国民党去台人员,学校确实犹豫了很久。后来招生办公室把我的材料送到录取工作会上,(县一中)教务长沉吟了半天,说,他考得实在太好了,不录取有点说不过去。但以后要上高中就难了。就这样,我成了一名中学生。
然而,未等到考高中,“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成了一名下乡知青。
1969年1月,我被安排到剑川县最偏远的山区弥沙公社插队落户。在那贫瘠的农村,我们生活的主旋律是困苦。几块土墼在地上围个框,铺上稻草,裹一床薄薄的棉毯,就是一个回荡在山谷的犬吠伴眠的夜晚。一锅干蔓茎汤里撒几把苞谷面粉搅一搅,往往就是我们的一日三餐。有一次,在粮管所排长队领到了救济粮,我们竟在粮库外就地用三块石头垒了个灶,用随身带来的锣锅煮粥,还半生半熟,就开始狼吞虎咽。那年月,我们有时会相互用手指头按压对方的脸庞,以那个凹陷小肉坑回复原状的快慢决定谁来洗碗。因为饥饿,我们的脸经常会有些浮肿。也因为饥饿,我们变得落拓不羁,有时甚或行为无状。比之我们,村民的生活就更加窘困了。如今40年过去,“春风已度玉门关”,那里绝大多数的民众虽谈不上富得流油,也已基本衣食无虞。
山村的生活,也新鲜得像林地野莽的空气,赐予我后来写一些文章的素材。一个大队革委会主任,豪爽,却又因科学知识的缺失而愚昧。他因为担心众乡亲被一个放蛊的家族所害,竟断然和鲁莽地烧死了这家人,自己也因此被判处了死刑。可是放蛊家族中侥幸逃过一劫的桂宝,却淌着眼泪诉说哪里会有放蛊这样的事情。而那位革委会主任的儿子阿才,很善于采撷据说是会让女人产生爱怜的相思草,却又无法使自己暗恋的姑娘芹香喜爱自己……这是我的散文《玉石江旧事》的一些内容。这篇文章,曾得到著名散文批评家林非先生的评介。是的,一些沉重的悲剧和轻松的喜剧,出现在我的作品中正如出现在现实的生活。在插队落户的地方,我还结识了一个回乡知青,他一双充满梦幻的眼睛明亮清透。他爱看小说,喜欢音乐甚至尝试过创作乐曲,却终因不堪生活的困窘、家庭的重负而自杀。“梦的花环,有时也会成为致人于死命的绳圈。”这是我在《我知青下乡时的一位朋友》文末写下的话。也许,一个荒唐年代的悲摧故事,一出现实版的唐吉诃德似的悲剧,具有的意味至今仍值得咀嚼。这篇写于1988年的散文,近日在名为“美篇”的微信平台被“加精”发布后,赢得了不俗的阅读率和点赞数。
当然,在知青岁月里,最难忍受的还是前途无望。在将近五年之后,同学们先后被分配了工作,只有我一次次因政审落选。当与我同一批下乡的知青全部离开农村后,我鼓足勇气来到县知青办找军代表。他回避着我质询的眼光,面无表情地说,看看你的家庭出身、父母的现状、社会关系,什么单位敢要?你就在农村找个对象安家吧!我们可以帮忙协调一下,安排你在生产队当个记分员。这番话,无异于把我整个人塞进了冰窖。然而挫折能让自信挺立,屈辱能让人性丰满,痛苦会使理想光辉,即使在最无助的时候,我也没有忘记心中的《那人》:
逶迤站立在江岸上的圣诞树(别名:银荆、澳洲白色金合欢、鱼骨松)又如期开放了。那一片朦胧的淡黄,是被放逐的月光,是被遗弃的星星的泣泪,是黄昏忧伤的旗帜。
而那人,曾无比清晰地凸现于这一切:头一扬,两根长长的辫子荡起一抹少女的矜持,音量不高然而执拗:“不,那是一派音乐,轻盈地漫起,优美地流淌,在我们心里心外的空间,注满明快。”
她总是这样:矜持于沮丧,执拗地对一切充满希望。那是她的身影吗?如蔚蓝的鸽哨驾着朗朗的阳光,飘飞、飘飞,丢下我的阴郁以及岸的曲折。
那天,我和她,成了最后两个因血统不纯而不能被分配工作的知青。她却去为即将远走高飞的一群送行。手臂的摆动于最优雅的一刻定格。那神情,那身姿,仿佛幸运也属于她。
是的,我们曾常常并肩漫步于乡村黄昏无可奈何的宁静,让心的距离渐趋消失。什么是友谊?什么是爱情?个中的界限何其模糊,又何等地难以超越。唯青春流逝,吸饮了人生多滋多味的一杯,才痛感知音难觅,情感急于亮出谜底。
但她已经远去,成为我邈远记忆中如梦如幻的一个影子。
仿佛一切都是偶然,又仿佛一切都是必然。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年轻的心,褊狭地认为她的坦然里有着某种程度的做作和虚假……谁又说得清这是一次再难挽回的错过还是一种永远的过错?
然而此后,每当我又一次品尝到被弃置的苦味,感到说不出的孤独的时候,她却会在我的耳畔摇响银铃般的笑声:
“对别人的祝愿有多真诚,对自己的祝愿就有多自信。”
“天总会变得晴朗,快別垂落了你心的翅膀。”
她总是专程赶来向我复述这些她那天说过的话。说完了,就迈着轻快的脚步走了。走进只有她才听得到的音乐声里。走进我深深的怀想中,坦坦然然,成为一个影子。
逶迤站立在江岸的圣诞树又如期开放了。然而如期开放的决不是相逢。惆怅是春天的芬芳。缺憾才是生活的项链上最真实的环节吧?所幸的是我心中毕竟还有一个梦影,她会最及时地从一片淡黄的朦胧中凸现,教会我从被放逐的月光,被遗弃的星星的泣泪、黄昏的忧伤的旗帜的招展里,听到音乐轻盈地漫起,优美地流淌……
这是一篇散文诗,忧郁而唯美。地理背景是我下鄉之地的一段江岸。但真实的生活完全不像诗。我心中的那人,仅是我内心世界里的一个幻象,或者说,是从极度的沮丧中奔突而出的另一个自我。
1973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程序是,先由贫下中农对下乡知青的现实情况进行评议,确认表现好的再推荐参加考试,最后由院校进行选拔录取。消息传来,无异于黑屋现裂隙,漏进了一线光亮,让人振奋。
村民很善良,我获得了他们全体的联名签字推荐进入了考场。考试科目有四:政治、语文、数学、理化。由于难度未超过初中水平,考试结果,我的数学、理化均为满分,政治98分、语文95分,名列全县第一。作文则又一次被作为范文,印发全县学生学习。后来,一位到州里参加阅卷的本县教师问我,那真的是你当场写的吗?写得真好!2000多字的一篇文章,全是心里话,自然情真意切、一气呵成。我非常肯定地点点头。遗憾的是,我已记不清当年的考题以及我写的具体内容了。据说阅卷一结束,高分试卷就被各高校一抢而空,只待最后被录取。然而,张铁生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横空出世了,高分生们瞬间被贴上“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的标签,录取标准骤然转向。夜空浑浊而迷茫,途程幽暗而虚空。又一次折翼!又一次跌落!在国家民族尚处命运多舛之秋,哪里有个人的坦途?以致5年后,我才有机缘跨入高校。
如果说,1977年恢复高考的录取,还受政审因素的影响,那么,1978年的高考,不仅变各省出题为全国统一考试,政审也大幅度放开了。开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要尽快尽早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人才的支撑,怎能还受“人为胎记”的左右?恢复高考,也许就是正式拉开改革开放大幕的前奏,对个人则是一次命运呼叫转移。虽然此中小有曲折,被降格的录取也稍嫌勉强,我还是坚决而响亮地回应了那迟来的召唤,融入了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跳起的青春圆舞曲的节拍。
特别令人欢欣鼓舞的是,此后不久,父母的不公正待遇也逐步得到了纠正。具有去台亲属的社会关系,还让父母成为统战人士而受到特别的关怀和重视。
春风鼓荡而来了,暖阳不止在崎岖小径徘徊,而且让所有的枝条都挂满了妩媚。
忆当年,最值得忆念的是大河解冻时阳光的晃亮和激荡。阳光打在了人们脸上,也照进了他们心里。而文学是其中最炫目的那一道。走来了刘心武的《班主任》,驶来了舒婷的《三桅船》。当顾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声音传来时,张洁喃喃地告诉你《爱是不能忘记的》。他们的讲述、歌吟、呐喊,与滚滚向前的时代浪潮同频共振,有力地拍击着中国人的心房。对伤痕进行检视,让人性复苏,使常识归位。人的解放所经历的阵痛和欢欣,诱惑着心灵话语的释放和传递,文学已不仅仅是文学,它是创可贴、醒脑汤、能量合剂,它更是火,是电,是山谷里炸响的惊雷。
我虽然以全县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云师大物理系,但劈头而来的文学狂浪旋引我调转了船头。当初之所以选择报考理工科,源于心有余悸。父亲的被划“右派”,跟他从事文职工作有关。“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这种“不怕”,与理工科的更实用和远离意识形态有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是安全。家长的竭力主张使我放弃了自己自幼的爱好。但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决了多少人心中的藩篱,也使我有了莺梦重温的可能。我的枕边开始堆满了各种过去看不到的文史哲名著。书封上的名字是卡夫卡、海德格尔、弗洛伊德、萨特……国门打开,有新风习习拂面,让人眼界大开。
其实,对于文学书籍的阅读,早在八九岁时我就已经开始。先是《征西》《征东》《说唐》《说岳》《三国》《水浒》等章回演义,继而是《气球上的五星期》《基督山伯爵》《斯巴达克斯》等科幻传奇。“文化大革命”中最幸运的是还有鲁迅的书没被禁读,而那时期我物色到的一本破旧的《普希金抒情诗歌集》,让我对诗歌产生了宗教般的崇敬。在知青岁月,惠特曼、聂鲁达、洛尔迦曾陪伴我驱除寂寞。一本《杜诗》的选注或者选译则被我的眼睛反复揉搓。童少时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的阅读,为我在大学以不务正业的姿势向文学张望垒砌了站立的台阶。写文章皆因一时兴起,发表文章则纯属偶然。到了大四,我已在《边疆文艺》(即如今的《边疆文学》)和《云南日报》发表过一些短诗及散文。人在年轻时难免有些轻狂,我曾写道:
……
一天,一位学中文的同学来访,他一改惯常的见面捶胸擂肩、逗乐打趣的风格,一脸严肃地告诉我,他对我怀着一种嫉妒。让我大吃一惊。
其实,对他一直暗中嫉妒着的该是我。这些中国文学系的幸运儿,整日呼吸李白、杜甫的芳菲,吐纳莎翁、托公的精妙,潇洒倜傥,王子般自信、自在。而我却去赶了一种浪潮,报考了物理系。人在年轻的时候真有点缺乏自知之明。我却还在暗地里把自己自诩为一艘装备精良的舰艇,可以随意地驰骋于任一片知识的海域。后来才知道对于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我们总是无奈。在无休止的演算的间隙,在定义、定律、定理的狭缝中,我始终会情不自禁地时时向文学之境投去深情的一瞥。
于是我开始写点什么。于是我偶尔也往邮箱里投送稍厚一些的信件。
这纯粹是一种自娱,一种自慰,一种对于单相思的排遣,就像柳絮明知它传播的籽种不会萌芽生长,成为参天大树,但到了春天仍然要漫天飘飞一样。
谁知就是这样的“偶尔”,使得我的那位朋友深有感触了。
是的,就是在那一天,我的名字又一次变成了铅字。
……
这是又一次转折,又一个起点。它使我对自己有了一种新的选择。
……
有人说,在大学里对高等数学的演算、公式定理的推证,发达了我的逻辑思维,也是对文学造诣的一种加持,是这样的吗?我难以回答。但在那四年里,我对文学的痴迷日益势不可挡却是确切的事实。以中上的学业成绩从物理系毕业后,我写的文章开始在各种报刊频频露面。但真正走上弃理从文之路,是从离开中学物理教员岗位到大理州文联工作开始的。
陪老诗人蔡其矫采风是我工作调动后的第一个任务。
宽脸膛,肤色较黑,头发短而有点卷曲,穿一身工人师傅们常穿的劳动布工装,脚上的旅行鞋,灰黄灰黄,似敷了一层泥,但上衣的钮孔里,却斜插着一枝野花——是我初见他时的印象。有着游吟诗人气质的蔡其矫,也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跟我谈改革开放带来的文艺界的思想大解放,抒发因文艺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而迸发的欣喜。他与艾青交好;在舒婷脱颖而出的过程中曾給予她有力的助推;《今天》诗人群体与他有较为密切的交往,在他随身携带的相册里,甚至有他为北岛夫人拍摄的生活照。能参与优秀人物之间的砥砺交流是人生幸事,尤其在青年时代。这是他传授我的一条人生经验,极大地影响了我后来的交友观。而且我领悟到,这也就是当初考进大学的重要意义,因为那里毕竟是优秀青年的聚集地。我陪他爬剑川石宝山,带他骑自行车绕行剑湖。一路听他谈自己独特的读书体会和写作心得,深受启发。有时候我会恍然觉得,他多么像巴乌斯托夫斯基《夜行驿车》里所写的那位擅写童话的老人。是的,对于美的人和事,他有一种近乎放纵的迷恋。当然,我也看到了他性格中稍许的偏执和急躁,从而认识到名人也是人,人所具有的他们都会具有。那段时间,接待工作让我有了很多与名人接触的机会,既增长见识,学到了经验,有时也难免感受到名人的庸俗和浅薄。进而明白,成名的因素很复杂,做人其实比成名更重要。
工作之余,我主要致力于散文诗的创作。散文诗是一种以小见大的文体。我们只要读一读屠格涅夫的《门槛》,波特莱尔的《一个人身上的怪兽》,鲁迅的《过客》《影的告别》《死火》等篇章,就会知道它们所包含的思想力量和美学浓度绝不会少于一部中长篇小说。写作中,“用好动词而少用形容词,多积累名词”,蔡其矫的告诫对我很有帮助。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文艺思想的解放,作家们的笔触由对“高大全”的神化回到血肉丰满的人间,由“政治教化第一”的偏废转入兼及审美、认知、娱乐诸功能的全面。求新求变,也成为我写作上的一种导引。让熟俗的字词显现出初新的贴切;追求作品具有题外之旨和言外之意;让字里行间流动着时代在我灵魂里窖藏的淡淡忧伤。这些努力,使我为数不多的散文诗短章在结集出版后较受欢迎。那是一个属于文学的时代,作家往往就是追星的对象。我每天都会收到一些读者来信,生活中也时常会发生一些有趣的故事,和那本书有关的。这些,我在《相思草送给少男少女》中有所记录:
……
再后来一次,来的是一群少女,来找我妹妹玩儿的。她们都买到了《相思草》。一看见我,就指指戳戳,嘻嘻哈哈。待我和她们交谈起来,她们都一个个变得认真了。
“惆怅。不少篇章读后都使我惆怅。”
一位胖乎乎的,笑起来就没法自个停住的姑娘竟这样说。
我不禁大吃一惊。我的少年时代正逢十年动乱,几乎是在孤独中度过的。在那人生多梦的季节里,我的梦苍白而脆弱,往往没有盛开就萎谢了。在这群快乐的小姑娘中,我是更真切地感到了青春的美丽。
……
对于已逝的青春,谁不会燃起一朵两朵淡蓝色的相思?也许,长期以来,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心境中写作。也许由于这样,有意无意,我的献给自己青春的祭品,就成了送给少男少女们的礼物,就像常常浮现在我脸上的微笑。
由于追订数较多,《相思草》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重印了。然而,它是本来应该更好些的,本来可以更好些的呵。
如今翻看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那些作品真是太幼稚了。但那种嫩生生的、仿佛青草叶片上的晨露般的清新,是青春岁月沁出的记忆颗粒,也是年轻心灵的温热血珠,是我今天无法复制的。如果写得更多一些,如果写得更好一些,乘着生机勃发的八十年代的翅膀,在文学的天空里,我也许会飞得较高远一些。我常常因辜负了那个让人怀念的时代而黯然神伤。
1991年,我出版了我的第二本作品集《情感小屋》。由于自己不愿囿于较为局促的篇幅,以及对散文诗那种曾经繁盛的文体的创作日趋陷入窠臼的怒其不争,我已主要从事散文的写作。著名作家郭风在该书序中说, 在这册散文集中,有些作品非常接近散文诗,显得凝重、富于哲理性和人生沉味,以及具有多义性。其他一部分作品虽然行文自由,但仍然出现一种潜在的诗的力量,显示出作家表达世情的深刻和情感的真挚。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晓雪则这样评介该散文集中的作品:这些晶莹剔透、灵巧秀丽、耐人寻味的篇章,既汲取了散文诗含蓄而有节奏感等长处,又舍弃了它形式上的束缚,因而显得摇曳多姿、丰富厚实。其中也有不少人物速写类篇章,以极简练的文笔,点染人物的细微特征,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人物的心理、神态和个性。
这本书很快就脱销了。其印数虽然不算很大,但在今天绝对难以企及。
如今我虽然已出版十余本作品集,并且一本比一本厚,装帧也越来越华美,思想性、艺术性的日趋完善和成熟也显而易见,但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却似乎未能更多超越最初出版的两本书。是的,那个“像健壮的青年,有着铁一样的胳膊和腰脚”的八十年代已经不复存在。社会已不再是那个社会,人们的需求也不再是当年的需求。文学已从异乎寻常的高位跌落,成为阅读的支流乃至细末之流。启蒙的、审美的纯粹,已无可奈何地让位于娱乐的狂欢。这是时代的蜕变,也是写作者个人的悲哀,谁也说不清它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抑或退步。
回顾四十年历程,先是物理教员,继是文联干部,在后来的二十多年时光里则成了一名繁忙而需经常上夜班的报人,自己的文学创作就一直处于业余状态,作品数量较少。“一位作家,作品量多而质高才最值得推崇。可惜我难以做到,也就只好把文章尽可能写好一点了。主观努力如此,客观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在散文集《听雨》的后记里,我曾这样说。我以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一生创作量奇少却获诺贝尔文学奖为宽慰,如丝如缕的自责却又常常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我最好的球是下一个。”球王贝利的自信,是我所激赏的。而“我要唱的歌,直到今天还没有唱出,每天我总在乐器上调理弦索”,泰戈尔的这句诗,是我一直坚持的理由。
不能全力以赴,却也一往情深。不怕慢,只怕站。写,并快乐着,渐成我的一种人生观;不怕少,只怕不好。和新深美的文字相互寻觅,是我的一种价值追求。散文是熬自己的精血炼成的一颗丸子。我写故我在。我写故我不会失去灵魂的皈依。
尽管春天甚至盛夏已经过去,至少对于我的生命而言。然而春后还有夏,夏后还有秋,秋后还有冬,冬后又是春。日子就是这样,涨落起伏、周而复始。告别冬天,走过杂花生树、莺飞草长的春季,其实我们的社会生活也进入了夏秋之交。这是我的一个判断。夏秋之交,并不是一个让人喜不自胜的季节。眼前一派繁茂却良莠芜杂,收获似乎丰盈却斑驳迷离。物质涌流的同时雾霾腾起,并且向人心流泻。同路人的“三观”分道扬镳,社会的层级分化撕裂。需要梳理,需要整饬,需要涅槃,需要跨越萧瑟的轮回,重新唤起一种明澈和清丽。我一次次暗暗警醒自己,为了给这种跨越增添一点哪怕是微末的色彩,也应一手举起批判的长矛,一手摇动爱与美的玫瑰,进行属于自己的写作。但长矛之刺总是乏力,也许我不是真的猛士,不敢、不忍或者不惯于正视淋漓的丑陋和肮脏。
“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细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等候在我心路远方的是什么呢?环顾四野,我发现雾帐撩起处依然有无数的年轻人点燃了他们心灵的火把。这些才华横溢而又目光深邃的幸运儿,不像我们一样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他们的成长,营养优质而完备;他们的歌声,不仅掷地有声,而且燃跳着青铜和燧石的火焰。尽管这个世界已是五音俱发,充满喧哗与骚动。但我相信,文学是无法替代的。“他们应当比我们强,否则,我们还有什么指望。”是哪位高人智者说的。让我们把这种虚怀若谷继承下来吧。我不仅要为比我年轻的写作者点赞、喝彩,把帽子抛得高高的,也希望多与他们交朋友,获得与他们砥砺交流的機会。
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
广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
穿森林过海洋来自各方
千万个青年人欢聚一堂
……
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
让我们唱一支友谊之歌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又想起了四十年前校园里的那场舞蹈。那飞溅的欢乐是由衷的火苗,更是历史翻新的象征。走进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时代,如果年轻的朋友用一颗心又自发地跳起青春圆舞曲,我希望你能认出其中舞步蹒跚却又在沟壑纵横的脸上绽开朵朵鲜花的那一个是谁。
编辑手记:
本文的作者原因,通过追忆自己青春年代的点滴故事,向我们讲述了他知青时代以及参加工作时期的经历和心路历程,也与我们分享他创作道路上的难以忘怀的故事片段。作者在知青时由于政审不通过而无法参与分配工作,但又因高考的恢复而有了新的转机,其中的心酸与坎坷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文学创作成为作者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慰藉和陪伴。通过他的回忆,也使我们明白,一个人无法选择他所生活的时代,无论命运多么不公平,也只有勇往直前,充满希望。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我们绝不应该让恐惧或别人的期望划定我们命运的边界。你无法改变你的命运,但你可以挑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