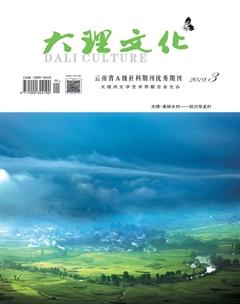染艺天工
左了
在大理恒久的时光之中,有一种独属于古法手作的传统工艺能够让你停留,那是一抹让人无以言状的蓝,也是一份令人惊喜的宝。天然形成的工巧,与“人工”相对,那个名叫周城的村庄,那蓝白相间的天空仿佛都是为了映衬人们独特的生活,穿越时光,让我们邂逅扎染,一窥这门古老技艺的魅力与神奇。
潜心造物
很多人对于大理的印象,要么是苍山洱海田园风光,要么是民居客栈青石小巷……不过,对于大理人来说,引以为豪的却是那一门传承千年从未丢失的扎染技艺。
说到白族扎染,那周城便是非去不可。
从下关出发,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之后,远远地就能看见周城静卧在连绵的苍山和湛蓝的洱海之间,那东边温柔的天光,西边氤氲的云影,周城的炊烟、清风、树影,以及白族第一大村的那些古老的故事,就像是一部浪漫电影的布景,在今天一一为我演绎和再现……
当冬日懒散的阳光从洱海的东岸一寸一寸移过来,进入周城村停好车,街道和行人也跟着一点一点披上镀金的衣服,密如蛛丝的石板路,顺着七弯八拐的巷道汩汩流淌的泉水,几缕阳光溜过了一所宅院,藏在院墙下的树叶里不肯出来。叶子显得格外的绿,而天显得格外蓝,随处可见的扎染布,晕纹变幻玄妙,周城似乎总飘浮着一股灵秀与智巧交织而成的动感,一种牵动人内心的淳朴和厚实,而这,又与这里随处可见的一块块蓝白相间的扎染布所营造的氛围不无关系,聪慧的周城人将这一片片“蓝天白云”浸入棉布。
2006年,白族扎染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年轻的段银开倍感欣慰,从事工扎染技艺至今已30多年的她,在扎染行业摸爬滚打,与丈夫段树坤一起造就了璞真扎染的盛世辉煌。
两双巧手,一块染布,承载的不只是一段人生故事,走过一段老滇藏公路,在璞真扎染厂的扎染小院里,我们的采访由段银开的一个微笑开始。
段银开微笑着说:“初识扎染,以手抵心,从此便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扎中照见初心,在‘染里执着坚守,便是一生的笃定。”
昔日,周城白族先辈们赶马驮货走夷方、下海捕鱼都成了老人摆古的话题,但周城的白族经商和从事手工艺品加工的古老传统习惯一直沿袭着,已有上千年历史的扎染手工艺在现在仍然还在大放异彩,深受人们的喜爱。
“六七岁的时候父母就在做扎染,我从那会开始就喜欢扎染,跟着他们学扎染。十四五岁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这辈子什么也不做,就专心做扎染了。”段银开看了看扎染小院里挂得满满当当的扎染布,满怀深情地说。
段银开生于1975年那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家住周城村12社,是土生土长的周城人,家中有兄妹五个,两个阿鹏,三朵金花。段银开在家排行老五,长在白族扎染世家,父亲和母亲从事扎染有六十多年,从小深受扎染艺术的熏陶。
“在爷爷、奶奶和父母亲的影响下,我自幼就很努力,七八岁开始经常模仿大人们扎花,到了十一二岁就在奶奶和母亲的指导下学会了村里一般的扎花技术,要是发现村里谁扎花扎得好,我一定会努力超过她。”段银开笑了笑,说道。
“看来,家庭环境的熏陶,对你的技艺有很大的影响。”
“喜欢扎花,我有条件,我们家有祖祖辈辈扎染的传统,不过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利用一切机会,一有时间就喜欢到村里看老人们扎花,虚心向老艺人请教。要是遇到技艺高超的老艺人,或者是琢磨出一种新的扎花方法,我会立即跑到老艺人的家中逐一求教,通过几十年的学习积累和摸索实践,周城扎染的每种手法我几乎都早已熟记于心,可以说信手拈来。”
“求学的三个条件是:多观察、多实践、多思考。看来,你很善于学习。”
“不耕耘,不播种,再好的土壤也长不出庄稼,我天天都扎花,在努力坚持做着芝麻大的琐碎之事,其实是兴趣让我坚持了下来,从小对扎染的兴趣是我最好的老师。”
在段银开看来,“扎”是一种吸引,一种投入,一件兴趣点极高的事。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段银开还记得跟着“师父”学习的那些场景。师父手把手地教,遇到难一点的技法,就不厌其烦地重复,直到段银开理解为止,像这种口传心授的带徒制也深深地影响了心灵手巧的段银开,使得先人的传统技艺得以传承。到现在,段银开在传统的30多种扎法基础上不断实践、完善后,摸索出了160多種扎法。
1990年,15岁的段银开周城中学初中毕业,在村里已经小有名气的她便以熟练工人的身份进入周城民族扎染厂工作。命运是最物质的,因为它太有力量了,人很难做命运的先知,在周城民族扎染厂的那一段日子里,段银开工作非常认真,她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向厂里的前辈学习,刻苦钻研画图和扎花技术,还有幸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仕绅老师那里当过几年学徒,获益匪浅。
在周城民族扎染厂,段银开还收获了爱情。1994年,由于情趣、爱好和理想相投,与同是扎染世家的丈夫段树坤结为伴侣。刚刚成家那两年,段树坤在扎染厂上班。当时,段树坤的两个兄弟还在上学,而扎染厂每月仅100多元工资,难以维持家用,段银开下班后便继续在家扎花挣钱填补家用,那几年她每天累得直不起腰来,但为了生活,还是坚持了下来。
随着两个小孩的出生,四处做工毕竟不是长远之计, 1999年,段银开和丈夫段树坤离开了周城民族扎染厂,本打算着出去闯闯的她,最后还是干起了扎染。两口子经过一番商量和谋划,在家里开起了家庭染坊,并在继承两个家庭传统扎染技艺的基础上,抢救、挖掘、整理、新创扎花针法和扎法达30多种,极大地丰富了花色的纹样,促进了当时周城扎染业的发展。
段银开说:“生命本是一场漫旅,遇见了,就是一个美丽的意外,我深爱着这个意外,一直以来,我的工作和生活就没离开过扎染。”
看着老一辈的阿妈们,年轻的好时光基本都是在一针一线中度过的,眼睛累花了,脊背累弯了……那段日子里,段银开和丈夫每天的工作时间达到十五六个小时,白天她要处理很多事务性的工作,到了晚上,她常常要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扎上四五个钟头。除了创新扎法,段银开和丈夫段树坤也将周城单一的蓝染加入了色彩缤纷的草木染。
随着家庭扎染作坊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段银开坦言,以往只会待在周城家里埋头扎花的她,在村里一些前辈和张仕绅老师的帮助指导之下,技艺有了很大的进步,她开始尝试着扎一些作品出来和顾客朋友交流,后来在丈夫的支持鼓励之下,段银开带着自己精心准备的作品开始走出周城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会展和交流活动。
“一幅扎染作品的诞生,需要多长时间?”我问。
“不如把这个问题换一换,问我一件作品的诞生有多艰难?出染缸即收获,自然最是激动人心。满满一染缸扎染作品,不仅是对多日辛苦的回报,更是对数月劳作的犒赏。传统扎染之美,七分人力,三分天意,充满着不可预料与惊喜,这份未知成就了世间独一无二的扎染作品。”说到技术上的问题,段银开表情有点严肃。
“一点一点地扎,一点一点的造型和线条,每次都要悉心的收缩和变化,浸染时的期待和煎熬,技艺上的考究在这里可见一斑。”我看了看段银开身后一块正在晾晒的扎染说道。
“还不仅仅是技艺,单单从工序来说……字面上短短几个字的描述,背后需要沉淀的时间有时候却需要数月之久。”段银开取下那一块晾晒的扎染认真说道。
讲到扎染的工序,段银开的话匣子有点收不住了。她如数家珍一般地向我介绍说:“一块土布,要经过8道工序,主要步骤有画刷图案、绞扎、浸泡、染布、蒸煮、晒干、拆线、漂洗、碾布等,其中主要有扎花、浸染两道工序,技术关键是绞扎手法和染色技艺。染缸、染棒、晒架、石碾等是扎染的主要工具。浸染采用手工反复浸染工艺,染色,重复染12次,现在有脱水机,一天内就可完成,漂洗2至3遍后进行晾晒,最后形成以花形为中心、变幻玄妙的多层次晕纹,凝重素雅,古朴雅致。”
据我了解,周城的扎染取材广泛,常以当地的山川风物作为创作素材,其图案或苍山彩云,或洱海浪花,或塔荫蝶影,或神话传说,或民族风情,或花鸟鱼虫,妙趣天成,千姿百态。
段银开说:“从古至今扎染都是白族人的生活必需品之一,可以说,扎染布贯穿白族人的一生。小孩出生时候使用的披肩扎上八卦图,有避邪保平安的意思;妇女平时的头巾、围巾和一些生活中的美丽饰品都要用到扎染布;在农村,老人去世以后,如果子女能够为老人准备上一套不扎花的扎染布寿衣,那是对逝者最好的尊重。”
“你们小时候,学习条件不好,在画图方面,怎么解决?”
说起儿时扎染和今天的差别,段银开颇为感慨:“因为儿时的场面非常单调,也没有什么模具,人们根据自己的想法,直接画,直接扎,产量也不大,基本上处于自产自销的状态,当时是无法想象今天这样的速度和产量的。从设计图案、选布料,然后跟着那些扎染了一辈子的白族老奶奶学习一些撮皱、折叠、翻卷、挤揪等方法,一幅作品的好坏,全凭自己的天性。在扎染的8道主要工序之中,第一步是绘图,这是扎染的基础,这一道工序通常由女性负责,在光洁的白布上印出喜欢的图样。”
“为什么扎染上的图样大多数都是蝴蝶,或各种各样的蝴蝶图案,还有各种各样蝴蝶的纹饰。”我不解地问。
段银开耐心地说:“白族的古老先民认为万物有灵,冥冥中存在着一种看不见、摸不到,但能操纵人的命运、掌握人的吉凶祸福、穷富荣辱的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神。对蝴蝶的崇拜是喜洲一带古老的自然崇拜,蝴蝶崇拜在白族审美中已经成为美的象征神,爱情的象征神,生命的象征神。”
“自然力包罗万象,而各种自然力对人类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关系也不一致,也就是说,这些图案,主要还是寓意好?或者说,具有某种神性?”我接着问。
段银开补充说道:“我个人觉得也不单纯是寓意和神性,蝴蝶造型经过上千年的发展,蝴蝶纹饰有单体蝶纹、双体蝶纹、四体蝶纹,还有无数蝶纹组成一个圆圈等等,无论是单体蝶纹还是复体蝶纹,都是朝着象征、抽象的蝶纹演变,是比现实的实体蝴蝶更高更美的艺术形象。它们都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独具匠心的艺术化的图样,因为它利用了染色时部分结扎起来,使之不能着色的巧妙原理。当然,扎染的图样中还有许许多多别的图饰,比如神话传说、民族风情,山川风物、雪山彩云、洱海浪花、三塔蝶影、蜜蜂、鱼虫、梅花、茶花、鸟雀等等,图饰丰富多彩,绚丽多姿。”
“老祖宗留下的许多传统手工艺,在我們看来繁复无比,怎样把如同白纸一样的粗布转化成耀眼夺目、纷繁美丽的花纹呢?”
段银开说:“其他地方的扎染图案多以不规则图案以及其他简单几何图形组成,而周城白族扎染的图案则取材于常见的动植物形象,如蝴蝶、蜜蜂、梅花、鸟虫以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百兽等。蓝底白花图案产生自然晕纹,青里带翠,凝重素雅,形象生动,布局丰满。
“扎染扎染,扎是关键,其关键性体现在什么地方?”我问道。
段银开解释:“扎花又叫扎布疙瘩,布料选好后,按花纹图案要求,在布料上分别使用撮皱、折叠、翻卷、挤揪等方法,使之成为一定形状,然后用针线一针一针地缝合或缠扎,将其扎紧缝严,让布料变成一串串“疙瘩”。扎布疙瘩是整个扎染工艺的重要一步,这一道工序技艺比较复杂,用的工用时也最多,按照印好的花纹纹路进行扎缝,利用扎缝时宽、窄、松、紧、疏、密的差异,造成染色的深浅不一,形成不同纹样的艺术效果,缝制时的松紧程度要有所区别,还要根据不同的花样采取不同的针法,这样才能确保成品的完整性。”
“作为白族扎染之中的核心部分,在染上有些什么讲究呢?”我带着问题向段银开请教。
段银开略作思考后,笑笑说:“周城扎染的步骤是把板蓝根的叶子浸在水里,在特制的木质大染缸里发酵成染料。先将板蓝根的叶子放入水中浸泡三天,捞出枝叶,过滤干净,这时清水变成了绿色,在绿水中放入适量的生石灰,用木棍反复搅拌使其沉淀,这时下面的沉淀物已变成蓝色的染料‘靛青,那是一种色彩饱和度很高的清靛蓝色,将扎好 ‘疙瘩的布料先用清水浸泡一下,再放入染缸里,或浸泡冷染,或加温煮热染,再用清水洗,晾干,再染第二道,可以根据蓝色的深浅选择浸染的次数,如此反复浸染,每浸一次色深一层,即‘青出于蓝。”
上千年来,大理白族扎染最重要的原料是板蓝根,这种清热解毒的植物除了做药以外,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大理人的染料。周城扎染的染料一般采用纯天然的板蓝根、臧红、黄连素、艾蒿、核桃皮、树皮、紫茎泽兰等也都能用作着色原料,天然无公害,但主要还是以板蓝根居多。
在段银开的引领之下,我们来到工坊区,有幸观看了传统扎染的部分流程。观看传统扎染流程是一种绝美的视觉体验,因为虽然缝制过程是有迹可循的,但在晕染过程也许会出现令你意想不到的变化,这一过程是前人智慧的凝聚,也是现代工艺的不断改进而形成的。缝了线的部分,因染料浸染不到,自然成了好看的花纹图案,又因为人们在缝扎时针脚不一、染料浸染的程度不一,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染出的成品很少一模一样,其艺术意味也就多了一些。浸染到一定的程度后,最后捞出放入清水将多余的染料漂除,晾干后拆去缬结,将“疙瘩”挑开,熨平整,被线扎缠缝合的部分末受色,呈现出空心状的白布色,便是“花”;其余部分成深蓝色,即是“地”,便出现蓝底白花的图案花纹来,至此,一块漂亮的扎染布就完成了。“花”和“地”之间往往还呈现出一定的过渡性渐变的效果,自然天成,生动活泼,克服了画面、图案的呆板,使得花色更显丰富自然。
段银开笑着说:“一直以来,她更愿意用‘一个扎染人来定义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潜心造物,不争朝夕,做好扎染必须修心修技,这也是扎染这一古老技艺的奇妙之处和魅力所在。用板蓝根发酵成蓝靛再进行扎染的技术,现在几乎没有人掌握这个技术了,整个村子里,只有老一辈的两三个人还知晓一些。现在有时候我们也用丝绸面料的服装直接扎染:分串扎图案犹如露珠点点、文静典雅和撮扎图案色彩对比强烈、活泼清新。正是因为这样的随机性,使得染色效果晕色丰富,变化自然,趣味无穷,更使人惊奇的是扎结每种花,有成千上万朵,染出后却不会有相同的出现,这种独特的艺术效果,是机械印染工艺不能达到的。”
返璞归真
坐在扎染小院里,迎面就是一片片染就的以蓝底白花为主的各色布料,晾晒在阳光之下 ,那些一针针一线线串起了时光的记忆,那些蓝底白花的扎染,闪现出白族先民的勤劳与智慧。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幸福;长大了,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幸福;成熟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幸福!我经常会想,当年建起这间小作坊,又守着它这么多年,到底是机缘巧合,还是命中注定?”说起自己从事的扎染,段银开不无感慨。
作为大理唯一叫“城”的村子,周城民族风情浓郁,家家会扎染。目前共有17个扎染生产户,全村人口约10000多人,其中,6000多人会扎花。2000年前后两三年的时间里,大理白族扎染迎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哪怕你是北京的,拿货也要排队呢!”段银开和段树坤说起她们在2003至2005年赚得的第一桶金,掩饰不住内心的自豪之情。
段银开和丈夫段树坤明白,只有那些热爱扎染、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的人,才可能成就一番事业,才可望拓展人生价值。那几年,璞真扎染坊赚了两三百万元。他回忆,那时订单很多,北上广深的大工厂都自己找上门来要货,而大量的订单意味着高饱和、高负荷的工作量,段树坤夫妇每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休息和睡眠时间经常只有四五个小时。
周城民族扎染厂是经营民间染织工艺品、集扎、拨、防生产为一体的村办企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辉煌,后来因多方面的原因,大理周城白族扎染仅停留在制作样品的水平上,批量上不去、长期亏损、职工怨声四起。业内资深人士戏称,大理周城白族扎染“有名气、没名堂”,企业面临倒闭。
2004年周城民族扎染厂倒闭,因为早年曾经在厂里做过工人,夫妻俩对扎染厂都有着特殊的感情,当时,夫妻俩也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于是两人暗自下决心,狠拼苦干积攒资金。
在那一段时间里,随着全村家庭作坊的兴起,段银开和段树坤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村里的好多年轻人已经不再扎花,大部分都外出做生意或者打工去了,村里仅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还在继续着扎花的工作。面对这一普遍现象,段树坤和段银开夫妇却有了另外一个保护技术人才思路,随即产生了创建一所扎染博物馆的念头,让扎染技艺既能够得到很好的展示,又能够让扎染技艺得到延续和推广,可谓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凭借着对白族扎染的这份热情,为傳承壮大白族扎染事业,那时候,我们想要筹建扎染博物馆,不仅仅是要进行单纯的作品陈列,博物馆内还配置讲解员、有活态的扎染技艺展示。我们希望通过对传统扎染制品的收集整理、挖掘、抢救,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保护、保存。”段银开笑了笑说。
有了念头,也就有了方向,通过几年的积累,以及对自己掌握的扎染技艺的自信,段树坤夫妇毅然决定,不论多么艰难也要筹资接下扎染厂。2008年,段银开和段树坤出资290万元,收购了已经倒闭4年的原周城民族扎染厂,在“璞真染坊”的基础上注册了“大理市璞真白族扎染有限公司”。
随后,夫妇俩确立了在保持和继承传统扎染技艺的同时,积极研发新产品的思路,拓展了扎染制作平台,迎得了市场,使扎染事业焕发了青春,并且逐渐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2012年,段银开和段树坤为了更好地保护收藏传承展示白族传统扎染制品及扎染技艺,多方筹集资金近400万元,修建了以白族民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为基本建筑形式的博物馆,通过对传统扎染制品的收集整理,挖掘、抢救几经失传的传统图样近2000张、模板3000多块、传统扎染品700多件,使这一大批珍贵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保护、保存。
段银开伸出自己的双手,慢慢说道:“你看我们做扎染的手,都是老茧,而且指甲盖还显得特别脏,所以年轻人肯定不愿意做啊!有些技艺,时间长了就会忘记,随后就会失传了。”
扎染博物馆里如今仍保存并在使用着传统生产工具:上百年历史的木制染缸、土制染色原料、土制棉布、染洗工具等,技艺方面主要是手工绘样、手工扎布、手工染洗、手工缝制等。扎染坊的展示区里陈列着传统的扎染制作工具以及非遗传承人段银开夫妇创作的扎染珍品。一幅一反传统蓝白相间,呈金黄色渐变晕染为底,图案反映敦煌飞天像的作品《飞天》吸引了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