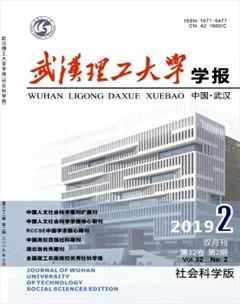“花儿”歌手在表演中的编创及其与受众的互动
摘 要: 作为活态的口传文学,“花儿”在长期的演述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特编创机制,并经过数辈歌手的传承、流布,逐渐定型,成为一种习俗惯制。从“花儿”歌手在表演中的编创、歌手和听众的互动性、歌手和听众角色界限的模糊性等三个方面来对“花儿”歌手在表演中的编创及其与受众的互动进行了分析,并通过探究“花儿”演述中歌者和受众的关系来对歌谣与史诗演唱中歌手和受众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以从理论上加深对“花儿”文化更深的理解——“花儿”有异于史诗,其在演述中,歌手和受众之间在心理和行为上都有着极为明显的互动,但在角色的区分上却较为模糊。
关键词: “花儿”;歌手;表演中的编创;受众;互动性
中图分类号: I267.2;I277.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2.0020
“花儿”是西北地区流传的一种典型的多民族民歌,它主要传唱在甘、青、宁、新、陕西宝鸡等地区,其传唱有汉、回、藏、蒙古、撒拉、保安、东乡、裕固、土等民族,九个民族共同用汉语演述“花儿”。虽然传唱地域有差异,但其共同的文化心理使“花儿”这种民间口头艺术形式数百年来一直流传下来。在数百年的演唱、流变中,它形成了一套陈陈相因的创编方式,经过数辈歌手的演唱传承与流播,逐渐定型,成为一种程式。演述中,歌手在程式的框架内,利用现成的句子和词语进行填充创编歌词。歌手的每一次表演就是一次创造,并在表演中进行即兴创作,歌手和现场的听众常常是互动的。
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花儿”的研究已近百年,硕果累累。但在其百年学术史中,从诗学角度对它进行的探讨和关注却相对较少,这种学术倾向不利于非遗“花儿”的传承、传播、保护。随着口头诗学、表演理论被朝戈金、尹虎彬、杨利慧等学人的译介和引入,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刘凯、柯杨、郝苏民、赵宗福、李言统、戚晓萍等学者①相继运用口头诗学和表演理论对“花儿”的创编模式和特征进行了逐步的分析与探讨。除此之外,还有其它口头传统方面的成果也对“花儿”诗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复旦大学郑士有教授的《吴语山歌的编创律则——以“调山歌”为例》[1]一文。下面笔者主要运用口头诗学和表演理论对“花儿”歌手在语境中的演述与受众的互动性进行分析,以期对“花儿”诗学作一尝试性的探讨。
一、 “花儿”歌手在表演中的编创②
“史诗歌手作为人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们从蒙昧时代起,便对人类心理智慧的成长做出过重大的贡献。”[2]78歌手③作为承载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他们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下,不断习得传统文化的精华。他们能在表演中习得一些演唱技艺和获得创编的灵感,因而歌手在表演中,既是歌者,同时又是一个创作者。作为一座流动的图书馆和活化石,随着演唱场域的变换,他们同时将本地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信息带到异地去。在向别人展演的同时,也在传播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此同时,也会将异地文化的精髓吸纳和扩充到自己的传统中来,以丰富自己演唱的表现力和呈现音乐文化的内在张力。而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民间诗人和歌手们正是靠着记诵和表演的方式来传承、传播文化,对他们来说,记忆几千行的诗句并非难事,并且可以随着演唱的需要和表演实践而不断得到提高。米尔曼·帕里和阿尔伯特·贝茨·洛德在对荷马史诗及口头诗人的研究过程中,解密了口头诗人在演述中快速创编的技巧,认为他们口头表演的本领是可以在实践中习得和传承的[3]。作为一种异于史诗的口头传统,“花儿”同样如此。但它作为一种短小的民间歌谣,有别于史诗的演唱,因为“花儿”在表演中,重在即兴创编。歌手在演述时,周围的观众和环境、气氛、情境都对他的创编有着重要的影响。创作中,像史诗表演一样,他们也需要听众的鼓励和喝彩,这些也会刺激歌手根据既有的主题和程式即兴而歌,创编出更为精彩的句子来。“花儿”歌手在演唱中,很多时候都是以对歌的形式出现,对歌存在着一定的竞赛意味。如果没有很高的“花儿”表演造诣,并掌握大量的程式、主题和演唱技巧,就会在对歌中败下阵来。而对于听众来说,他们可以在现场通过观看歌者的演述,习得一些演唱的技巧和程式,获得对“花儿”的节奏感、韵律感、声音的美感、句法变换的精髓,并将之运用到自己的演唱中。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歌手们在“花儿”演唱会上的对歌和表演,既为自己提供了一个与高手切磋技艺的机会,同时也从对方的歌唱中吸收一些精华,用来提升自己的创编和演唱能力。
在演唱中,歌手并不僅仅是为了现场即兴创编,他们也要顾及到现场观众的感受和欣赏口味,并根据观众的口味来进行演唱和对歌,他们常常选取生活中极为平常的感受和体验作为素材和主题进行创编。对于青年歌手来说,他们在对歌中侧重于情歌的演唱。男女歌手互相对歌,极为风趣幽默,也有打情骂俏的成分在里面。而这些关于男欢女爱的情歌极能调动现场观众的情绪,并使他们积极地加入到对歌的行列中来与歌手们进行互动,乃至在感官和精神层面上与歌手达到一种相得益彰的和谐与共鸣。歌手们通过艺术化的演唱技巧来构筑诗行,流畅地叙事。在迎合观众欣赏口味的过程中,歌手们会不断调整自己的歌词以构筑诗行和丰富主题内容,这其实也是在进行着一种隐性的互动。
口头史诗艺人在对传统进行表演的过程中,既是对传统的一种传播和传承,也为歌手们的创新提供了一种场域,一次机会。并在每次的表演中,演述的文本不断趋于定型化,这样演唱者创新的机会就较少。对我国西北地区“花儿”这种民间山歌形式来说,虽然在表演中同样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但作为一种即兴而歌的韵文体裁,它的许多文本虽然已经定型,但后辈的歌手们可以借用这些定型的句式和固定的片语进行创编,因而创新的成分还是比较多,并且每次演唱的句式在句法之间也进行着变换,将“变”与“不变”的精髓深深融入到创编中。从这一点上来讲,歌手们在演唱中的创编也基本上是一种在现有句式基础上的创造。还有一点,史诗是口头艺人们进行的流畅叙事,属于独立演唱,这个过程中,是大量的复述以前记忆的一些诗行,并在这些诗行的基础上,根据气氛和情绪即兴创编一些。“花儿”就不一样,它在演唱中,很多时候是对唱,演唱的方式就决定了它的创新和创造,创新的成分往往极大。这也是它区别于民间史诗演唱的方面。在演述中,“歌手既要调动传统的力量,也要随机应付具体的演唱场合,这需要个人的才气。他对现场和观众要有感觉,歌的好坏掌握在歌手那里,他不仅仅是个吟诵者,也是创造性的艺术家。”[2]83歌手可以在演唱中无师自通,他们拥有在每一次的演唱中根据不同的表演场合诠释传统的能力,而且传统文化也是在不同的场合中适应和保存的。
“花儿”歌手的表演并非是一种简单的重复性记忆和背诵,而是一种施展个人才情的再创造,是歌手运用一些固定的片语和句式等结构部件来进行创编。这些构筑诗歌和诗行的材料并非个人的,而是来自民族传统。虽然歌手在传统的熏陶和浸淫下早已掌握了大量程式化表述模式,但在表演中他们仍然要面临现场快速创编的压力,这些都只有歌手才能真切体会到。歌手在演述时,头脑中需要储存大量的演唱模本和程式部件,以应对在创编现场中出现的观众刁难。他们并不需要一些死板的固定模本,而完全是在一些现有句式的基础上进行的灵活变换。
歌手在对“花儿”传统进行传播和传承的过程中,也同时使“花儿”发生着一些变化。面对同一部作品或者同一首歌进行演绎时,不同的歌手每次的演唱都和第一次的演唱皆有所出入。这些也可以是同一个歌手对同一首歌进行数次的演唱,也可以是不同的歌手对同一首歌或者主题进行的演唱和传递。这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而在不断演唱的过程中,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性的复制某一部作品或者某一首歌,而是在不断地创新和创造。如“花儿”中著名的一首《下四川》,当初由朱仲禄根据陇东民歌进行改编,并用“花儿”的范式演唱出来,由张佩兰女士将它搬上舞台,走出西北,走出国门而被更多的人所熟知,现在成为一首经典的作品而被不断演绎。但在演唱中,不同歌手演唱《下四川》时,都加进了自己的理解,因而听不同歌手演唱,每次都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因为在一些关键的地方进行了改编,但风格和特色还是保持着《下四川》的特点。因为“传统正是在不断的再创造中得到保持的”[2]91。歌手们在不断的演唱中,对它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诠释也更到位。《下四川》在流布的过程中,也在吸纳着不同的传统和音乐元素,这是因为歌手们也从别的传统中吸收一些精华运用到“花儿”的改编中,用来丰富它的表现力和内在的张力。
“花儿”作为一种独特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民族民间艺术形式,它有着古老的演唱传统,而且它的演唱传统也是同地域传统文化互为融合的。在与其它民族的传统文化交流和并存中,也在凸显着自己的风格。从文化空间上来讲,它具有流动性,并不局限于在固定的单一的地域进行展演,因为“传统文化的存在并不局限于表层空间的文化展演,而是根植在民心中统一的符号宇宙”[4]。
二、 “花儿”歌手在表演中与受众的互动
“花儿”作为一种口头传统艺术,它更为注重的是在表演中表达感情和进行流畅的叙事,因而从表演的视角来“探究在表演开始时所发生的一切,以及这些变化对听众的接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就显得极为重要。这些有助于我们更深地了解在动态语境中,歌者是如何创编的?在演唱中,歌者和受众有着怎样的微妙关系?“表演理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口头程式理论对于传统语境的重视。”[3]在“花儿”会上,歌手和受众之间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歌唱者和听众的关系,他们之间具有表演场景的微妙性和互动性。在演唱和对歌中,有时听众对歌手的创作能起一定的激发作用。在歌手临场创作短路的情况下,听众可以为歌手提供一定的帮助和指导,在那种语境中,他们是互动的。因为在口头传统的那种语境,对听众和表演者都有着一定的共同制约,会促使他们在口头传统所限定的语境空间中进行思考和创作。有时歌者的演唱也能给现场的听众提供一种思考和想象的空间。这种互动性也只有在歌唱的语境中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能使歌者和听众进入一种迷狂的境界——只有在这个时刻,歌者和听众的才思才会被激发而不断涌现出来,源源不断地进行创编,这个时候他们间的互动才真正进入高潮。
“花儿会上的听众,有些是专门前来听歌的,有的是为本村的歌手助兴而来的歌迷,有些是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也有些是远处来观光的游客,有些是从事民俗文化的研究者和专家。这些听众和歌唱者之间,有着明显的感情方面的交流,对歌唱的气氛和内容方面的热烈程度,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5]听众中,也有大多数人是优秀的歌手,他们趁着旅游和观光,把此地的传统带到彼地去,也借这个机会顺便来学习和取经,他们都是非常挑剔的听众,对于歌者的演唱,从构思到歌唱的艺术水平等各个方面都很严苛,歌者的演唱和创编时刻牵动着他们的情感,歌者唱出第一句,他们会根据程式立刻想出第二句。这是因为“程式句法和主题模式是他们艺术创作、演唱、传播和创编的一部分。”[6]238他们不仅从歌者那里期待一种对于花儿结构、句法之间的变换和音调的处理方式,并且会根据他们的演唱技巧和水平对他们进行有效的评估。对“花儿”会上歌唱者和听众的微妙互动关系,笔者请教了太子山下的东乡族歌手马金山。他解释说,歌者在演唱和对歌的过程中,眼前和周围的听众有这样几种情况:第一种听众主要是听歌者演唱的“花儿”是否对称,押不押韵,歌词是否符合花儿的编创技巧。第二种听众,主要听歌手演唱的歌词是否为新词,因为在听众中,有些“花儿”造诣很高的人,本身嗓音不好,不能到现场演唱或与别人对歌,但他们从现场歌手们演唱和编创的技巧就能看出歌者的水平。第三种听众,就是听声音,主要听歌者在演唱时颤音和滑音唱得怎么样?颤音和滑音的结合怎么样?因为只有把颤音和滑音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才是一首完整的“花儿”。第四种听众,主要是听字数怎么样,字数的变化、音调和词的处理是否恰当?歌者的演唱技巧怎样?而具备第四种能力的听众,一般为“花儿”音乐研究者,或者是既懂“花儿”,又懂音乐的人。马金山的这种分析极有道理。如果没有几十年的“花儿”演唱经历和传统文化的浸淫,不会理解得这么深刻。马金山从8岁开始演唱,演唱了50多年,懂好多种乐器,能编善唱,熟悉洮岷“花儿”和河州“花儿”两种类型的演唱和創编程式,他一生参加了无数次的“花儿”比赛和“花儿”会,得过很多奖项,对“花儿”会上歌者和听众的关系了解得非常清楚,像他这样拥有经验丰富、演技精湛的高水平歌手现在并不多见——他在演唱中,不仅在叙事歌的规模和篇幅上能够创造性地扩展传统,而且在提高和加强艺术性方面也有很大的创新。笔者曾在“花儿”会现场,体察了歌者和听众的演唱现场氛围,并就一些问题咨询了跟前的观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歌手,在唱歌中也能和歌手默契配合,他们在歌手演唱的过程中,都在认真地聆听,当歌手编的歌词具有诙谐幽默感时,他们和歌手一起欢笑,如果歌手唱乏了或者临场出现演唱“短路”,听众中就会有人立刻接上对唱,歌手和听众的互动性在表演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
来参加“花儿”会的群众和听众中,有些歌迷和“花儿”爱好者们前来观摩的目的,一边是来听歌,一边是来学习。从这个角度来看,听众的目的很明确。听众在现场听歌者演唱的时候,也从歌者的演唱中吸取一些精华来补充自己演唱和编创中的不足,达到取长补短的目的。听众不仅仅是简单地听,其实听众比歌者花费的心思更多,他们不但要听出歌者演唱的各种词句,在创编和音调处理上的各种问题,而且在歌者编创歌词而思维受阻时,他们就会提供歌词,帮他们脱困解围。他们之间是互动的,听者对歌者具有援助作用。“听众和艺人的互动作用,是在共时态里发生的。”[3]因为“程式作为口头诗人的主要创作技法,深刻影响了口头传统诗歌的结构和诗学,它反映了史诗问题结构背后的口述世界的叙事现实,以及口述的心理结构。演述中,如果脱离了口头史诗传统的表演、创作、流布,脱离了歌手、听众、文本的互动关系,那么,程式便只能是一个标签,口头传统也便是一句缺乏感觉的空话。”[2]116-117而“一个经历了若干代民间艺人千锤百炼的口头表演艺术传统,它一定是在多个层面上都高度程式化了的,而且这种传统,是既塑造了表演者,也塑造了观众。属于艺人个人的临场创新和更动是有的,但也一定是在该传统所能够包容和允许的范围之内,是‘在限度之内的变化。”[3]在对歌中,当有些歌手或小组演唱完毕,听众中有些“花儿”才能极高的人,觉得他们的演唱还没有完全表达出它的真正意蕴或者歌手的演唱还不能将所表述的内容展现得非常完美时,就随口将心中想好的歌词脱口演唱出来,接着,听众中有人继续接上演唱,这样一直唱下去,将一首原本简短的“花儿”延长到了十句、十几句,甚至更长。而这些听众的才华往往也深深折服了在场的歌手。这是因为,现场歌唱的气氛、情境和歌唱的內容都深深触动、感染了在场的观众,激发了他们的灵感,导致其直接参与了创作和歌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角色并不固定,没有界限,这些都大大丰富了“花儿”歌词的内容,乃至深化了主题。
而在一年一度的“花儿”会上,有一些是来浪山和进香的善男信女,他们大都是“花儿”爱好者,其中不乏著名的“花儿”歌手。在给神灵唱过“神花儿”之后,他们就组成小组,进行对歌。对歌的往往以年轻人为主,他们喜欢对唱情歌。也有中年人组成班子在一起对歌的,他们往往以日常生活或者国家的时政为主题进行对歌。还有一些老年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生活的磨练,已经对情歌不再感兴趣,但是也以另外一种独特的方式在参与,他(她)们有时候远离人群,独自小声地在歌唱自己已逝的青春和对生活的体验、感受。这种形式的参与,也使参与的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以往来参加“花儿”会和听“花儿”的都是当地以及邻近其他少数民族的农民,但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许多中国传统文化项目被列入联合国非遗目录,导致了一些传统文化出现“研究热”,因而,更多来自城市的传统文化爱好者以及外国热爱民俗和民间文学的学者们纷纷到“花儿”的传唱地来采风,使过去单一的本乡本土听众的格局被打破,出现了听众多元化的局面。这说明“花儿”正以它独特的艺术个性向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听众展示它的文化魅力,并通过各种媒体和学术传播渠道而被更多的人所熟知。
“花儿”是方言的文学,也是传唱民族的灵魂。“花儿”从产生到流传至今,一直都用方言演唱,因而对受众的选择就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就影响和阻碍了它的传播范围和速度。河州“花儿”是以独唱为主的单声部民歌,配音容易,但在音调的处理上较难。它更容易配上音乐被搬上舞台去演唱,为了让更多的人熟悉它,就有必要对它进行改编。青海省化隆县著名的撒拉族“花儿”歌手苏平(国家一级演员)是第一个尝试用普通话演唱河州“花儿”的人,她将“花儿”进行了改编,这种改编也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得到了家乡“花儿”爱好者的认可。洮岷花儿主要以对唱为主,一般由三个以上的歌手和一个串把式组成一个班子和另一个班子进行对唱。在对唱中,串把式即兴创编,然后分头腔、二腔、三腔,分别说给歌手们进行演唱,最后集体合唱尾音“花儿哟,两莲叶儿啊”,它是一种多声部的民歌,这就给配音和记谱带来了难度,由于这些内在的因素,它的传播范围和速度受到很大的限制。
“在花儿会上,民间歌手和诗人们的即兴创作与演唱,总是要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这些因素包括:长期以来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一种演唱程式(禁忌)的制约;对唱者之间相互问答的激发作用;现场听众的反应和参与程度;赞助者对歌手的奖励和权威者的态度等等,这些因素都对歌手们的情绪和演唱的质量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5]因而,研究花儿会民歌对唱的价值,就不得不考虑演唱环境的诸多要素。“研究花儿艺术和民间歌手们的创作过程,离开了花儿会这个独特的环境和对歌时的相互激发因素,只能说是一种平面的、凝固的、书斋式的研究,而不是立体的、动态的、田野式的研究,因此,也就难以充分揭示庄稼人的文化心态和民间文化活动的深层意蕴。”[7]如果脱离了情境,就会变成一种静止的、表层的研究,而不是一种动态的、更深层次的研究。
三、 “花儿”歌手与受众角色界限的模糊性
笔者在岷县二郎山“花儿”会、康乐县莲麓镇莲花山“花儿”会、王家沟门“花儿”会、和政县松鸣岩“花儿”会现场调研时,就被群众自发性的程式表演而深深地折服与震撼。这些“花儿”会上对唱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管是歌者还是听众,他们都有参与权,人人随时都能成为歌者而参与进去对唱。他们之间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从鲍曼表演理论的视角来看,听众们都是潜在的演唱者。配角和主角随时都在更换,因而这个时候,歌者和听众的关系就更微妙了,有时候歌者扮演的角色就是表演者,但随时他们又会变为听众,而听众则变为歌唱者。他们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在二郎山“花儿”会上,笔者看到每一个歌摊上对歌的时候,刚开始是两个人在固定地对唱,等这个人唱乏了,或者听众中有人想唱了,就直接出来与歌手对唱,这个时候,听众就变成了主角,参与了间接的创作。当时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爷和一个60多岁的老奶奶在对歌,对唱了一会儿,另外一位老大爷也加入进来,这样一直对唱,这种参与的方式也极为独特。人人都可以参加表演和歌唱,就像哈佛大学东语系的赵茹兰教授当年在莲花山调查时所体会的:“听众中的人,他们随时都能成为表演者,演员和听众之间的界限不是固定的。第一个唱花儿进行发问歌手的目的,就是希望听众中能有人也用花儿来回答,从而吸引更多的听众,鼓励大家都来参与。至于这种做法能否如愿以偿,就要看个人的魅力了。”[8]而这种独特的对歌方式也是“花儿”区别于其它地区民歌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在二郎山调研的时候,顺便去了岷县县城的公园,这里也经常会有一些群众自发性地举行“花儿”会。通常在举行“花儿”会的这几天,公园里异常热闹,对歌的歌摊也非常多,而且在这些对歌的歌摊中,河州“花儿”和洮岷“花儿”歌手都有,他们都在这里尽情地表演和歌唱,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性地到不同风格的歌摊上去听歌,两种不同类型演唱风格的“花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将歌手围在中间,听他们演唱。公园里这样的圈子有好多个。在自发性的对歌中,有些歌手使用话筒,并自己配有音响,有些摊子上,听众将歌手们围成一圈什么工具都不用,两个歌手只是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对唱,或者坐在一起对唱,歌声此起彼伏,简直就是歌声的海洋,不时也有听众参与进来,进行对唱,这时歌者和听众的角色就倒换了,歌者成了听众,而听众则变成了表演者。
从“花儿”会上歌者和听众的互动关系、歌手们的创作以及在表演中歌者和受众角色的模糊性可以看出,现场语境对“花儿”的研究极为重要。要想了解“花儿”创作的内在构成机制和歌手如何运用程式进行现场创编的过程,就离不开“花儿”演唱的语境,因为从现场的情形来看,作为口头艺术的“花儿”更为注重的是表演和在表演中的创编。歌手既是创作者,同时也是表演者。根据表演理论,歌手们表演的那一刻就意味着创造。因而他们进行表演的那一刻就极为重要,只有在表演的那个语境中,才能不断地创造,歌手们的才思才会不断被激发出来。而在歌者表演中,周围的环境和情境、气氛也极为重要,这些都影响着歌手的创编。歌者在表演中,也根据现场观众的喜好而进行创编,因而就极能调动观众的情绪而参与到演唱中来,歌手的表演时时都能得到人群的回应。但“从口头程式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在研究中侧重的是文本并非语境。它的研究方法就是通过在同一部史诗的不同文本中的审慎比较考察,来确定其程式和主题。米尔曼·帕里和阿尔伯特·贝茨·洛德在史诗的研究中,虽然也注重史诗现场的实地调查研究,但他们侧重点还是放在文本上而不是语境上。”[3]他们在南斯拉夫史诗的研究中,并没有提及歌手和现场听众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以及听众对史诗文化所作出的直接的诠释和回应。从史诗的研究和演唱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歌手们进行史诗演唱的时候,歌手和听众的位置较为固定。如果歌手表演的艺术能力超强,叙述技巧高超,他们描述和渲染的气氛感染了在场的听众,听众就会集中注意力去听歌手的演唱,歌手也可以随时将歌曲的长度拉长,一直演唱到自己感到疲惫为止。而根据洛德在《故事的歌手》[9]中的讲述,如果现场的听众在歌手开始演唱时,注意力不太集中或者听众并不是很喜欢歌手的演唱,那么歌手就会在有限的时间内缩短歌曲的长度,尽快演唱完毕,这些都不是歌手才能的问题,而是在演唱中,歌曲的长短一般都取决于听众的反应。这也可以看出,史诗演唱的时候,歌手和听众虽然也有着一定的关系,甚至在情感上的微妙互动,但这种微妙的关系和互动完全是在听众对这部史诗是否感兴趣的情况下偶尔发生的,他们的互动不太明显。
“花儿”作为一种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口头演唱传统,却不同于史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歌手和听众在现场的互动极为明显和突出。因为歌手在现场的演唱就是一种表演,根据表演理论,“这种口头艺术的现场表演就是在特定情境下人们交流的一种样式和言说的方式。”[10]7歌手演唱的内容不管是爱情方面的,还是对生活的体验与感受,都能深深触动在场听众的神经,歌手们的演唱使听众不但从听觉上,而且在心里、精神上都能与歌手达到和谐、默契,也能很好地沟通与交流,融为一体,他们无论在艺术构思、情感的表现上都能产生共鸣。但相对于史诗来讲,史诗演唱的歌手和现场听众之间的互动达不到这种程度,因为现场的听众如果对史诗的演唱非常感兴趣,或者歌手的演唱技巧非常高超,史诗的内容确实能够感染在场听众的时候,他们才会随着演唱的深入进入那种即兴创作状态,但主角和配角的角色不会互换。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场的听众不会直接参与创作。因而“花儿”歌手在现场与听众的互动性以及角色界限的模糊性正是它区别于史诗的重要方面。用口头诗学理论来研究“花儿”,就要区别于史诗,不但要注重其文本的差异,而且更重要的是离不开对二者动态语境的探究,这样才能更好地解“花儿”歌手如何利用一套习俗惯制进行快速构思和创作的文化独特性,也才能对它的内在构成机制和文化内涵做出准确的透视和解析。
注释:
① 参见赵茹兰的《谈“花儿”程式表演的自发性》(《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刘凯的《西方“套语”理论与西部“花儿”的口头创作方式》(《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第2期),柯杨的《莲花山“花儿”程式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郝苏民的《文化场域与仪式里的“花儿”——从人类视野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4期),赵宗福的《西北“花儿”的研究保护与学界的学术责任》(《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李言统的《中国民歌的口头传统——“花儿”和〈诗经〉的程式比较为例》(青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6月)以及《“在场”视域下“花儿”的创作与表演刍议》(《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戚曉萍的《“阿欧怜儿”的程式和主题》(《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王军林的《西北“花儿”的程式句法与方言》(《兰州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及《莲花山“花儿”的口头程式特征解析》(《兰州文理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② 笔者在文中对“花儿”歌者程式化的演述用“编创”而不用“创作”,也是借鉴复旦大学郑士有教授提出的观点。因为口头文学从来没有定型的作品,它处于不断被修改的过程,它的创编有异于书面文学。郑士有教授在《吴语山歌的编创律则——以“调山歌”为例》(《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中对吴语山歌在演述中的内在构成机制从诗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总结出的一套分析山歌内在构成机制的理论和山歌的批评方法,对我们研究山歌内在构成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③ 歌手:在演述中,歌手既是表演者,又是创作者,是集表演和创作于一身的民族文化英雄。歌手和他们所掌握的各种演唱技艺是非常古老的文化现象。在各个少数民族中都有自己古老的神话、传说以及历史的和哲学的解释;民间歌手就是通过演述这些民族古老的文化,将他们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他们是本民族文化的活化石。
[参考文献]
[1]郑士有.吴语山歌的编创律则:以“调山歌”为例[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61-65.
[2]尹虎彬.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美].约翰·迈尔斯·弗里.中译本前言[M]//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朝戈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萧璇.国家视野下的民间音乐:花儿音乐的人类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03.
[5]柯杨.听众的参与和民间歌手的才能:兼论洮岷花儿对唱中的环境因素[J].民俗研究,2001(2):53-55.
[6][德]卡尔·赖希尔.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传统、形式和诗歌结构[M].朝戈金,主编;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38.
[7]柯杨.花儿会:甘肃民间诗与歌的狂欢节[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3):68.
[8][美]赵茹兰.谈“花儿”程式表演的自发性[J].邓光瑜,译.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3):71-72.
[9][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M].尹虎彬,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10][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M].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
(责任编辑 文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