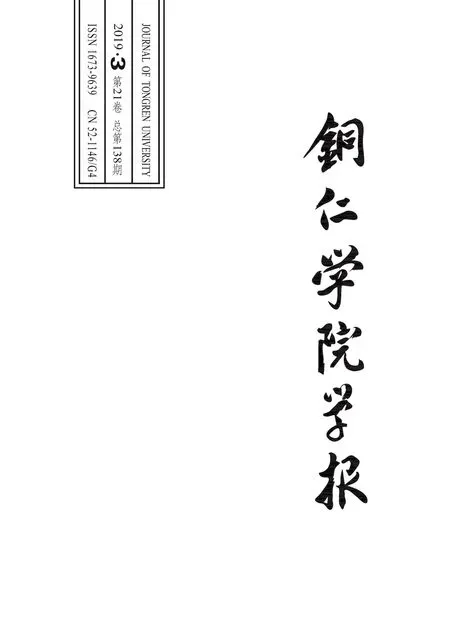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传承现状及危机
罗钰坊
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传承现状及危机
罗钰坊
(铜仁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是我国传统医药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维系土家族妇幼健康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它的传承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该体系是由传承主体、传承客体和传承场域构成的多元素、多环节组成的有机复合系统。各要素在认同、互惠与忠诚等传承机制作用下有效整合,共同促进传承体系的良性运行。现如今,现代医学的普及、打工经济的兴起、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影响着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传承体系的运行,出现了传承场域的解构、传承主体认同弱化、传承客体的濒危消失及传承机制受阻等危机。
传统妇幼保健知识; 土家族; 传承体系
《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中医药医疗服务,促进民族医药发展,并指出未来五年需“加强民族医药传承保护、理论研究和文献的抢救与整理。”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是我国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它的传承与保护是促进我国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因此,笔者选取武陵山区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传承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实际意义。从笔者对鄂西、黔东北土家族村落的调研来看,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传承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该体系是由传承主体、传承客体和传承场域构成的多元素、多环节的有机复合系统,各要素在特定传承机制作用下有效整合是传承体系良性运行的关键。现如今打工经济的兴起,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影响着传承体系的运行,出现传承危机,表现为传承场域的解构、传承主体认同弱化、传承客体的濒危消失与创新、传承机制受阻。深入地分析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传承体系与传承危机,对于我们提出切实有效的传承与保护策略,促进民族传统医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传承体系构成要素
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或地方性妇幼保健知识,是历代土家人基于特定场域形成的一套旨在维系妇幼身心健康的认知体系和实践行为,包括妇女卫生保健、幼儿养育习俗、妇幼疾病病因解释、疾病预防、诊断与治疗等知识和技能。它既是我国民族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作为一种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知识系统,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是土家人与疾病抗争的智慧结晶,为维护土家族妇幼身心健康贡献卓著。但目前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尚未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有关其传承体系的研究成果微乎其微。笔者通过深入武陵山区土家族聚居地调查、走访,认为武陵山区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传承体系的构成要素有:传承主体、传承客体和传承场域。
(一)传承主体
苑利研究员曾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就是传承人,而传承人是指“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直接参与制作、表演等文化活动,并愿意将自己的高超技艺或技能传授给政府指定人群的自然人或相关群体。”[1]他对传承主体的界定主要基于官方层面,从文化传授者角度进行定位,忽略了民间文化“传者”的复杂性以及“受者”的传承主体地位。从我们的调研来看,传承主体包括民间医生和社区大众群体两类——专门型传统妇幼保健知识传承主体(简称专门型传承主体)和常识型传统妇幼保健知识传承主体(简称常识型传承主体)。两类传承主体的传者和受者各有区别,两者的受者并非泾渭分明,比如民间医生可能从社区大众的年轻一代筛选传承人。做出分类的依据源于传承者掌握的知识稀缺度不同,分类的目的在于两者的传承机制及对知识传承的贡献度不同。专门型传承主体持有的知识更稀缺,而常识型传承主体掌握的知识相对普遍。
专门型传承主体的传者是指具有一定储量的本土医药学基础知识或拥有一套象征性疾病认知体系,持有针对某一类疾病或多类疾病的诊治技艺和疗法的民间医生。他们未必以看病行医为生,但必须得到知识生存场域内大众的认同,即习惯法赋予的医生角色。从治疗实践模式划分,民间医生有草医、巫医、术士和梯玛;从知识掌握范围划分,民间医生有全科性和专科性之别。全科性医生指擅于治疗妇幼疾病或神药两解的医生;专科性医生是持有特殊技艺疗法的医生,如专治不孕不育、婴幼儿疾病的这类人。专门型传承主体的受者主要从家族成员或具备良好品质的社区成员中筛选。调研资料显示,女性医生在专门型传承主体中占据了较大比例,并在土家族妇幼保健知识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常识型传承主体表现为同一文化区域内的集体行为,由社区群体更多的是女性群体组成。“传者”是老一代女性群体,“受者”为年轻一代女性群体。她们既是本民族妇幼保健习俗、育儿习俗等知识类型的传者和受者,同时也是知识受众。因此,她们既消费自身持有的知识,也消费民间医生持有的知识。无论哪种消费都对知识的传承和再生产起着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二)传承客体
传承客体即医药知识本身。生物学视角的医药学知识构成了传统医药知识的内核,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而构建于文化视角的巫术仪式是否归为传统医药知识尚存争议。从医学人类学倡导的生物——文化视角看,疾病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由文化建构的解释模型[2],人们的症状与治疗与某一文化体系及其被赋予的意义相关,即是一种“符号网络”[3]。也就是说,从医学人类学的观点看传统医药知识应包括两个板块——生物视角的和文化视角。同等原理,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也应包含纯草医药与基于文化信仰的妇女卫生保健、育儿习俗、巫术仪式等,前者为知识的内核,后者则是知识的外延。
草医药知识包括了妇女病、不孕不育、婴幼儿疾病的理论知识与实践,及与此相关的药物学知识;巫术仪式类知识包括了妇女孕育期、产褥期的画符、画水、念咒,婴幼儿走胎的解围仪式以及各类关煞的治疗仪式;神药两解类知识主要是梯玛、术士等在治疗妇幼象征类疾病时既使用药物又运用仪式,这类知识在土家族地区十分丰富;习俗类知识包括妇幼禁忌习俗、妇幼卫生保健、育儿习俗。禁忌习俗,譬如妇女在月经期、孕育期、产褥期的禁忌,儿童日常生活禁忌;妇幼卫生保健包括妇女生理周期和婴幼儿的饮食保健、行为保健等;育儿习俗包括婴儿出生后的一系列人生礼仪。需要强调的是,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并非一成不变,它在历史长河里不断注入新内容以满足人们的需要。
(三)传承场域
“场域”一词源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研究,他认为场域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4]133-134,其界限“位于场域效果停止作用的地方”[4]139。这就是说场域是由客观关系组成的网络体系,“网络”的延伸并非漫无边际,它存在一个边界,边界位于客观关系停止作用的地方。客观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场域类型的丰富性,但总体来说场域可分为自然生态场域和社会文化场域。在实践中,两者往往相互交融。通常而言,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自然生态场域是乡村,社会文化场域是传统村落中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后者的边界往往会随着交往圈和通婚圈的变化而伸缩。传统村落内良好的自然生态、丰富的药物资源与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长期延续是自然生态场域的一种关系表现,熟人社会则是土家族传统村落社会文化场域表现出的人际关系。接下来,我们重点谈论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存续的熟人社会呈现出的社区成员之间、医生与患者间、医生与传统妇幼保健知识间的客观关系。
“熟人社会”最初源于费孝通对中国传统农村社区社会特征的概括。“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在时间上、从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5]据土家族村落的老人们介绍,在改革开放以前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存续的社会文化场域同样表现出“熟人社会”特征:小时候家里有人生病父母都会请村落里固定的那几位医生看病,他们知晓村落内的每一位医生及其医技好坏,熟知哪位医生擅长治疗哪种疾病,诸如某位医生治愈了某个患者的疑难杂症或是将某位患者从生死边缘拉回的事迹往往通过村民茶余饭后的闲谈迅速在村内传颂。村民的熟识和信任构成了村落成员对民间医生认同的基础,也成为民间医生传承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动因之一。
与熟人社会相伴的还有面子、人情。林语堂曾说过,面子、命运和人情为统治中国的三个女神[6],可见面子、人情对中国熟人社会人际关系影响之深。对面子的重视在中国传统社会随处可见,比如某户人家办红白喜事总希望客人越多越好,甚至出现攀比,即便客人越多花费越高,但客人多意味着“面子大”、“人际关系好”,而且面子也与声望、权威、社会地位挂钩。人人都注重面子,那么如何才能有面子呢?在传统社区,控制和占有资本是获取面子的最佳途径。资本有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传统土家族村落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作为集经济、社会、文化于一体的资本形式,能为持有者赢得声誉、增添权威,即获得面子。也就是说,民间医生通过控制、占有、传承、创新传统妇幼保健知识,能够获取诸如声誉、权威等“面子”。譬如,一位治愈无数不孕不育患者的民间医生自然会得到村民的尊重和爱戴,这种崇敬与爱戴能够增强民间医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促进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传承。
支配传统社区人际交往规则的另一因素是人情。从交换理论来看,人情是基于互惠的交换,是一种不限于物资和财富的交换活动。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欠人情,总是要还的”,说明人情交换的对称性。人情交换对称性在医患关系上也有所体现:医生治愈患者,为患者排除病痛,患者未能以物质报酬偿还或物质报酬低廉,于病人而言存在一种心理亏欠,就是欠医生的人情,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的以物质以外的形式偿还,比如农忙时为医者付出劳动,在医者危难时给予帮助。农忙时的劳动力支付、危难时的挺身而出于民间医生而言是不比经济报酬差的社会资本,所以即便通过利用传统妇幼保健知识治病救人获取的经济收益低廉,民间医生仍坚持行医,将这种知识作为一种重要资本相互争夺不断传承。而如今,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土家族村落空间及支配村落人际交往的规则在悄然演变。
二、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动力与运作机制
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传承体系的良性运行,除上述各要素的相互整合外,也需要特定机制的作用。针对地方性医药知识的传承机制,有学者提出忠诚和互惠是传承必须具备的条件和遵循的基本原则,忠诚是民间医生选择传承人的首要考察因素,双向互惠基本原则的遵守是地方性医药知识得以传承的关键,并认为地方性医药知识的“传承明显体现着社会结构的对称性和相应行为的对称性”,而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结构的对称性是互惠义务必不可少的基础”,进而认为“传承中的对称性社会结构是通过师徒、医患两组关系表达的;相应行为的对称性表达则通过徒弟对师傅、医生对患者、患者对医生的互惠性行为得以实现的。”[7]显然,忠诚与互惠的传承机制充分阐释了民间医生内部传承医药知识的原则和动力。笔者认为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传承主体决定了知识的传承机制既要在医生内部寻求,也应从既是常识型传承主体又是知识受众的社区民众中考察。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传承也是依循民间医生内部与社区成员两条主线进行的。所以,笔者以为除忠诚与互惠外,认同也构成了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得以传承的必备条件,认同不仅作用于民间医生的内部传承,同样作用于社区成员的代际传承。并且认同先于忠诚和互惠,是知识传承的基础。
互惠除表现为师徒、医患互惠关系外,也适用于社区成员基于情感的知识交换、同行间的知识交换。我们可将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传承机制以图1的方式进行呈现。

图1 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传承体系运行机制图
(一)认同
认同,最初属于心理学术语,是一种从自我主体的角度进行的“自我”与“他者”的划分与归类。“作为一种自身的主观定位(subjective position),‘认同’是一种对所谓‘归属’(belong -ingness)的情感。”[8]从认同被应用于人类学族群研究之后,社会各界围绕“认同”构建出形形色色的话语体系,如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社会认同等等。所以认同是有层次的,从微观上的自我认同到宏观的国家认同层层递进。此处的认同是土家族村落内围绕传统妇幼保健知识所构建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是“自我”对“他者”的认可与区分,是一种微观层面的认同。从影响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传承的认同关系来看,它含有以下几类:社区成员对民间医生的认同、民间医生的自我认同、传承主体对传承客体的认同。各类认同相互影响、制约,共同作用于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传承。
1.社区成员对医生的认同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受众的社区成员对村落医生的认同。知识受众对民间医生的认同是促使民间医生自发、自觉地传承医药知识最直接的动力。传统妇幼保健知识是供人们消费的准公共物品,认同催生需求,需求刺激消费,消费促进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如此循环,为民间医生传承、创新传统妇幼保健知识提供了内在动力。具体的行为逻辑表现为:受众对医生的认可与否,决定了他们是否选择某位医生进行救治。若这位医生得到知识受众的认同度高,那么随着他治愈患者的增多,获得的声望、经济收益也随之增高、增多,他会更加自信、自觉地传承知识,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完善、创新传统妇幼保健知识以获得更高的威望和收益;反之,若某位医生得不到认可,前来治病的患者少,他既不能以此获得多少经济收益,又难以收获人情、声望、面子,久而久之,其自身就会失去传承知识的信心。二是有学医意向的社区成员对医生的认同。师徒关系的确立是双向选择的结果,不仅师傅挑徒弟,徒弟也会挑师傅,对师傅的医技和人品的认同往往成为徒弟选师傅的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当有学医意向的社区成员认同某位医生,这位医生才有找到知识的受者的可能,也才有将自身持有知识传承下去的可能。
2.民间医生的自我认同
医生的身份认同是民间医生对自身医生职业的认同。从实践来看,土家族民间医生有全职和半农半医之分。全职医生通常是医药世家出身,或经过一定培训,医技是他们主要的生存资本,他们的自我医生身份认同明晰,认同自己的医生职业。但对大多数土家族民间医生而言,依靠行医获得的经济收益尚不能维持基本生活需求,半农半医成为他们的生计手段。由于行医并非其唯一的生存之本,所以他们在自我身份认同时模棱两可。不仅如此,前文我们提到女性民间医生在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医生中占据较大比例,而女性医生之间的知识传承鲜有拜师仪式和繁琐程序来固化、强化师徒关系,加之传统社会对女性医生的认同度低,使女医生对自我医生身份的认同较男医生低。
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许多女性民间医生承认自己持有一些草药知识,但并不认可自己的医生身份。自己仅是在同母亲、外婆或其他女性亲属的相处中耳濡目染获得的知识,没有拜师,也不会主动收徒,如若某位家族女性晚辈对妇幼疾病医治感兴趣,教授知识未尝不可。只不过女性民间医生群体的传与受的过程是自由、松散、不确定、非正式的。总之,传统妇幼保健医生的自我身份认同会增强他们传承知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对医生身份的满意度决定了他们是否愿意传承知识。
3.传承主体对传承客体的认同
常识性传承主体对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文化认同决定了主体传承客体的态度、数量、内容、方式。当专门型传承主体对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疗效深信不疑时,才会自觉、自发地通过收徒的方式将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系统的传承下去;当常识型传承主体对传统妇幼保健知识高度认可时,才会遵循传统习俗孕育子女、遵守传统禁忌、遵照传统女性卫生保健习俗,并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将知识传给下一代,也才会在病痛难忍时选择土家族民间医生进行医治。所以说,传承主体对传承客体的深度认同是主体传承客体、利用客体的重要前提。
(二)互惠
学术界对互惠的研究早已有之,如早期的人类学家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莫斯、图恩瓦尔德、列维—斯特劳斯等都对人类社会组织的互惠行为进行过研究。从本质上讲,互惠是基于某种利益达成的交换行为。根据笔者的调研,正如上文学者所述双向互惠基本原则的遵守是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而传承表现出的互惠关系有师徒互惠、医患互惠、同行互惠、群体成员间的互惠。师徒互惠、医患互惠促进了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纵向承继,同行互惠、群体成员间的互惠促进了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横向交换。但互惠在常识型传承主体的纵向代际传承中作用表现不明显。
师徒互惠关系包含了师傅对徒弟、徒弟对师傅的互惠性行为:徒弟逢年过节为师傅带去礼物,平日为师傅家提供免费劳动力,而师傅则将自己持有的知识回赠给徒弟。医患互惠关系包含了患者对医者和医者对患者的互惠性行为:医生为患者消除疾病,患者则以物质或非物质的形式进行回赠,如金钱的回报、农忙时为医者付出劳动、在医者危难时给予帮助等;医生尽自己所能服侍患者、关心、治愈患者,患者则会发自内心感激医生,向村寨成员宣扬医生的良好医技和医德等认同的形式予以回赠。同行间的互惠以及社区成员间的互惠关系主要是基于诸如感激、情感等因素进行的知识交换。如相互熟识的社区成员间在闲聊的过程中,相互交换育儿经验、妇女疾病处置办法等都是基于情感而进行的知识互换。
(三)忠诚
忠诚是师徒纵向传承过程中,师傅考察徒弟的首要条件。只有对师傅忠诚、人品好,才有成为其徒弟的可能,而且即便师徒关系已确定,徒弟仍然需要遵守对师傅忠诚的规则,否则师傅会收回其传授的知识,使徒弟的药物失去疗效。可见,忠诚主要在医生内部传承中起作用。
由此,可以勾勒出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传承动力示意图(图2),理清传承体系的运行机制:传承主体中传者在特定的传承场域内遵循特定的传承机制将传承客体输入给受者。

图2 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传承动力示意图
三、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传承危机
从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运行机制看,其中任何一环的改变都将牵动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传承体系的其他要素,影响知识的有效传承。从笔者对武陵山区土家族村落的调研看,在现代医学的入驻、打工经济的出现、思想观念的转变、传承客体自身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传承场域、传承主体、传承客体等传承体系构成要素正在发生变化,传承机制受阻,传承面临巨大危机。
(一)传承场域的解构:现代医学的场域切割和医学场域客观关系的转变
20世纪初西方医学逐渐引入我国,新中国成立后西医西医得到迅猛发展。20世纪70年代至今我国对医疗卫生改革的探索从未停止,构建了省市县三级城市医疗卫生体系和县乡村三级农村医疗卫生体系,西医得以很大推广和普及。不可否认西医对于维护我国民众身心康健功不可没,但同时西方生物分子学和生命科学的医学观念颠覆了人们对传统医学的认知,给我国的本土医学带来巨大冲击。现代医药知识的广泛应用引起了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传承场域内各种力量构型的变更,传统社区不仅是中医与地方性医药知识的争夺场,而且已成为中医、地方性医药、现代医药三种医药知识力量相互角逐的应用场域。不仅如此,如今便利的交通及现代医学的较强可及性,扩大了医学自然生态场域的边界:当就近的医疗资源无法满足需要时,人们可以超越传统社区传统医药场域的界限,到县、市、省等医疗机构就医。这种场域切割,导致社区成员对民间医生的认同弱化。三类医药知识在同一场域内的竞争局面对地方性传统妇幼保健知识极为不利:国家的政策扶持、对现代医学科技的推崇等因素都为现代妇幼保健知识在村落社区的推广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医药作为我国的传统医学有着深厚的群众根基,地方性妇幼保健知识举步艰难。
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传承场域的解构还表现为支配传统村落社区人际关系规则的变迁——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的转变和注重人情、面子到经济理性至上。半熟人社会是贺雪峰在费孝通熟人社会基础上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自然村是熟人社会,行政村是半熟人社会[9]。这种划分并未考虑20世纪90年代打工经济兴起后农民的大规模流动。而打工经济的出现,使广大农村地区的熟人社会出现了分层,过去成员间相互熟识、彼此了解的熟人社会衍变为外出务工人员与家乡其他人的陌生而留守家中的社区成员相互熟识的半熟人社会。然而各个村寨留守家中的成员数量要远远少于外出务工人员,且前者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后者多为年轻人、中年人。所以就形成了同一村落多数成员对本村落谁是民间医生、谁的医术高明等并不完全知晓的现象,导致了民间医生很难在村落内享受到过去社会那般的崇敬和尊重,他们对知识传承的自信心大打折扣。不仅如此,受“人情”“面子”“责任感”等支配而熟人社会人际交往的规则在半熟人社会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土壤。经济理性至上逐渐代替了对人情、面子的看重。这种价值观念转变的后果是:传统医药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化的力量渐弱,“权威”“名声”“人情”等社会资本的获取更多地依靠金钱等经济资本,医药资源作为村落场域内有特殊价值的资源被争夺的局面被打破。人类擅于根据场域的变迁进行调适的天性促使他们改变生存策略——传统妇幼保健知识场域的解构必然使行动者即传统妇幼保健知识持有者在资本(不仅仅是医药资源)争夺过程中改变行为策略,放弃原有资本,寻求其他利于自身生存的资本和权力。社会文化场域的变迁引起的知识持有者惯习的改变和知识持有者争夺的资本的转移,使传统妇幼保健知识面临被“冷落”的危机,过去的医患互惠关系也难以继续维持。
(二)传承主体的锐减:认同感弱化与主体断层
传承主体对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传承的影响绝不亚于血液细胞对人体健康所起的作用。从笔者对武陵山区土家族村落的调研看,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传承场域的解构带来了传承主体锐减的危机,表现出传承主体对传承客体的认同度、传承主体的自我身份认同感的降低,传承主体出现断层。
1.传承主体对客体认同度的弱化
笔者的调研显示,常识型传承主体和专门型传承主体对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认同度都呈现出日益降低的趋势。常识性传承主体既是知识的持有者又是知识的受众的双重身份,使她们对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认同弱化也表现出双重性。作为知识持有者,学校教育、外出务工隔断了常识型传承主体传者与受者的日常接触,潜移默化的代际传承难以实现。不同于以往的母传女、婆传媳,年轻一代的知识结构更多地来自于学校教育和政府对现代妇幼保健知识的广泛宣传,她们对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知之甚少,更有甚者对传统妇幼保健知识抱以嗤之以鼻的态度;作为知识的受众,对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认同弱化主要体现在就医取向上。笔者对黔东北灯塔办事处落鹅村①的调研证实,不同年龄层的女性群体对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认同存在差异。笔者对18-25岁、26-35岁、36-45岁、46-55岁、56岁以上不同年龄层的女性各选择10位②进行随机抽样,利用问卷调查考察女性受众对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利用与认同情况,得出结果如表1。
表1 落鹅村不同年龄层女性第一就医选择情况

上表显示,该村50名女性第一就医取向选择中医的为24%,选择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医生的为16%,选择西医的为60%。可见土家族女性选取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医生的比例最低。再看不同年龄层女性对各类医药知识的选取情况,随着年龄增加女性对西医的认同度基本呈递减趋势,对中医和土家族医呈递增趋势,土家族妇幼保健知识与中医相比呈弱势。56岁以上的女性对传统医药的依赖明显高于其他年龄层的女性。年龄在18-35岁间没有人选择土家族妇幼保健医生,说明年轻一代尤其是近30年来的年轻一代对土家族妇幼保健知识的认知与认同度非常低。对于不选择土家族妇幼保健知识的原因由高到低依次是“见效慢”、“疗效差”、“有迷信成分”、“不了解”。
从笔者对鄂西兴安村和黔东北落鹅组的几位土家族妇幼保健医生的访谈来看,专门性传承主体对传统妇幼保健知识利用程度也在下降。如兴安村擅于治疗婴幼儿疾病的民间医生XCC③与笔者的对话证就实了这点:
问(笔者):您这么擅长治疗小孩儿疾病,那像您的孙子生病了是自己挖草药吗?
答(XCC):一般的小病我都是去隔壁卫生室拿点西药吃,西药吃不好嘛我就挖草药。
问:为什么不自己挖草药呢?
答:挖草药太麻烦了,又辛苦,到处找才找得到草药。西药简单嘛,见效又快。只有病严重了,西药吃不好我才自己挖草药嘛。有些病西药治得好,有些病西药治不到嘛。
有学者在对湘西土家族苏竹村传统医药知识的研究中提及该村赤脚医生彭大尧为人治病时,也是西药与草药混合使用,而并未沿袭其祖父、父亲以草医药治病的传统[10]。传承主体对传承客体认同度与利用率对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传承十分不利,因为传统妇幼保健知识只有发挥其治病救人的功效才能持久延续,缺少需求和缺乏利用都会让它逐步成为历史的存在。
2.传承主体自我身份认同感的弱化
现代医学的场域切割、社区成员对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认同下降,及基于情感、面子的医患互惠关系的转变无疑削弱了专门型传承主体对自我医生身份的满意度。日益减少的求医者、微薄的经济收益让民间医生放弃医生身份,寻求收益更丰厚的谋生手段。过去因持有医药资本满腹自豪,如今不仅自身对医生身份不满,更不愿让自己的子女继承衣钵。而年轻一代目睹了老一代医生的尴尬处境,也不愿承继老一辈持有的“无用”的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用落鹅一位土家族妇幼保健医生女儿的话讲:“草医赚不到哪样钱,有时候还讨不了好。像我外婆那个时候,你给她治了病,还有人情在。现在呢?你辛辛苦苦挖草药把她病治好了,兴许还会跟人家讲:‘我的病还没晓得是哪个治好的呢!’所以,我妈妈以前让我跟她学,我不想学,出门打工还好点。”传承主体自我身份认同的弱化,使传承主体断层在所难免。专门型传承主体的传者掌握的珍稀、奇效的单方、验方、秘方和技艺疗法极有可能因缺乏受者而濒临消失。
(三)传承客体的困境:濒危消失与创新的挑战
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传承危机不仅表现为传承场域的解构和传承主体认同弱化,知识本身也表现出诸多危机。一是药用植物日益稀缺及挖掘困难,降低了草药类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可及性。从笔者调研来看,许多传统妇幼保健医生不愿行医除上述原因外还与药物植物采摘艰苦,珍稀药材难求有关;二是社会大众对传统妇幼保健知识尤其诸如巫术仪式类、习俗类传统妇幼保健外延知识的认知误解,让许多不了解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社区成员将“传统”与“迷信”、“恶俗”划为等号,不加甄别全盘否定,其结果是社区成员对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认同弱化、民间医生对传统妇幼保健知识自信丧失;三是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口传身授的传承方式在当代难以施行,以及“传男不传女”的行业规约以及女性医生师传的非正式和相对隐性将女性妇幼保健医生排挤于以男性为主导的医学世界范畴之外,传承不稳定;四是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在新的文化场域中面临的创新与传承的挑战。如何迎合时代发展不断创新,并与现代妇幼保健医疗相互融合、相互弥补,是未来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能否存续的至关重要的一环。
四、结语
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传承过程复杂,拥有一套完整体系,这一体系包含了传承要素、传承动力、传承运行机制。传承要素的变化、动力不足,皆会影响传承运行机制,造成传承受阻、出现传承危机。针对上述危机,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是当务之急。如将西医与土家族传统医药相整合,实现“独生”到“共生”;实行数字化与档案化保护,使“无形文化”变为“有形文化”;转变土家族医生为传统妇幼保健知识主要传承与保护对象的现状,实现政府、民族医药科研机构、医药公司、高校与土家族医生多元互动式保护。
知识的长久存续是不断创新与发展的结果。在传统社会,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在与中医妇幼保健知识交流碰撞中不断调适,相互吸收借鉴并存续至今。现如今,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在同一应用场域里面临着来自中医和现代医学的双重压力。尤其是现代医药给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带来强大冲击。面临这种危机,我们应理智处理。一方面,现代妇幼保健医疗体系的构建为妇幼健康带来福利,不应被排斥;另一方面,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的精华不应被抛弃。社会各界应联手应对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的传承危机,探索创新性利用方式,提升土家族民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使土家族妇幼保健知识与现代妇幼保健医疗、中医妇幼保健能够互补、共融,共同维护妇幼健康。
注释:
① 落鹅隶属于黔东北铜仁市碧江区灯塔办事处马岩村,是一个自然村,该村居住着黄氏一族,百分之九十以上为土家族。
② 调研的时间正值寒假,许多外出打工的女性都陆续回家过年,为在不同年龄层寻找样本进行问卷调查提供了便利。
③ 访谈对象姓名大写首字母,下同。
[1] 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忧[J].探索与争鸣,2007(7):66.
[2] Ann McElroy,Patricia K.Townsend.[M].West view Press,2004.
[3] 拜伦·古德.医学、理性与经验——一个人类学视角[M].吕文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1-72.
[4] 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著.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5] 苟天来,左停.从熟人社会到弱熟人社会——来自皖西山区村落人际交往关系的社会网络分析[J].社会,2009(1):142.
[6]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台北:德华出版社,1998.
[7] 梁正海,马娟.地方性医药知识的传承模式及其内在机制和特点——湘西苏竹村的个案[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43.
[8] 范可.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J].世界民族,2008(2):4.
[9] 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J].政治研究,2000(3):61-69.
[10] 梁正海.传统知识的传承与权力[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Inheritance Status and Crisis of Tujia Traditional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Knowledge
LUO Yufang
( School of Economics Management,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554300, Guizhou, , China )
Tujia traditional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knowledg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l knowledge and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maintenance of Tujia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The inheritance of such knowledge is a complete system, which is a multi-element and multi-link organic composite system composed of inheritance subject, inheritance object and inheritance field. All elements are effectively integrated under the action of inheritance mechanisms such as identity, mutual benefit and loyalty to jointly promote the benign operation of the inheritance system. At present, the popularization of modern medicine, the rise of working economy and the change of people's ideas affect the operation of Tujia traditional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knowledge inheritance system. There are some crises, such as deconstruction of inheritance field, weakening of inheritance subject identity, extinction of inheritance object and obstruction of inheritance mechanism.
traditional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knowledge, Tujia, inheritance system
2019-04-02
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大健康产业背景下土家族传统妇幼保健知识生产性保护研究”(2017QN34)。
罗钰坊(1987-),女,重庆奉节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学。
G127
A
1673-9639 (2019) 03-0094-10
(责任编辑 车越川)(责任校对 黎 帅)(英文编辑 田兴斌)
———评《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