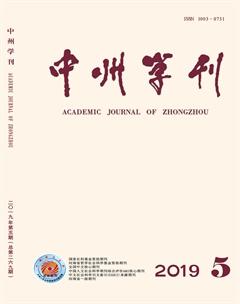冯友兰视界中的子学、经学与新子学
陆建华
摘 要:冯友兰所谓的子学乃是指先秦汉初诸子之学。子学的建构“以我为主”、无所“依傍”,是“创构”。冯友兰所谓的经学指的是从汉代到清代整个中国封建专制时期的哲学。经学的建构“以我为辅”、“依傍”于“经”,是“重构”。按照冯友兰关于“经”“子”关系的论述,应该是有“子”才有“经”,“经”只能是“子”的著作,可是,冯友兰所谓的“经”除却“子”的著作外,还包括儒家的“经”以及中国佛学家所注解、诠释的来自古印度的佛经。冯友兰认为中国新的哲学的诞生标志着“贞下起元”,意味着“重新开始”,像子学一样“创构”新哲学。这么说,这种新的哲学应该就是新的子学也即“新子学”。
关键词:子学;经学;新子学;冯友兰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5-0109-09
冯友兰在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将中国哲学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认为以人物画线,则是“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①;以历史划分,则是从春秋战国到西汉初期是子学时代,从汉武帝“独尊儒术”时期到晚清是经学时代;以哲学形态分期画线,则是上古哲学为子学时代,中古哲学为经学时代;以时间划界,则是上古时期的哲学为子学时代,中古与近古时期的哲学为经学时代。冯友兰之所以把中国近古时期的哲学依然列入经学时代,是因为“中国实只有上古与中古哲学,而尚无近古哲学”,“谓中国无近古哲学,非谓中国近古时代无哲学也”。②即是说,中国没有近古哲学,只有近古时期的哲学,而近古时期的哲学是中古形态的,所以属于经学。
由于冯友兰将中国哲学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于是便有其关于“子学”与“经学”的分析,本文意在论述冯友兰关于“子学”与“经学”的思想;又由于目前学术界关于“新子学”的讨论较为热烈,本文还试图从冯友兰的角度挖掘冯友兰心中的“新子学”,以期为“新子学”的讨论增添新的内容。
一、冯友兰视界中的子学
关于子学时代之成因,冯友兰认为是由于“自春秋迄汉初,在中国历史中,为一大解放之时代。于其时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及经济制度,皆有根本的改变”③。具体而言,则是“贵族政治破坏,上古之政治及社会制度起根本的变化”④,“世禄井田之制破,庶民解放,营私产,为富豪,此上古经济制度之一大变动也”⑤。这是说,从春秋中后期到西汉初期,中国社会发生巨变,体现为礼乐制度与礼乐文化的崩毁、宗法等级制度的破坏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政治上,代表宗法等级制度的贵族政治、世卿世禄制遭到破坏,固定化的等级结构随之荡然无存,贵族与平民乃至君与臣的“身份”“地位”不仅仅取决于先天的宗法血缘,更多的是取决于后天的人为。经济上,与宗法等级制度、贵族政治相适应的井田制度也伴随宗法等级制度、贵族政治的瓦解而崩坏,商鞅的“废井田,开阡陌”是其典型标志。土地不再是天子的“私产”,不再“国有”,人们可以通过后天的人为“私有”之。面对“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⑥的根本制度的大破坏及其造成的社会的大动荡,斯时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对此做深入的思考,并在制度层面对此做深刻反思,这种思考、反思的结果体现在哲学层面就是“子学”的诞生。这里,冯友兰从制度层面讨论子学的成因,将子学的成因深入到思想、文化赖以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制度,而没有简单地从思想与文化自身的发展角度论述之,是其过人之处。当然,冯友兰之所以跳出思想、文化自身而另觅子学之成因,其重要原因应该是子学与此前的思想、文化的重大差异。子学是对此前的思想、文化的质的飞跃甚至否定,仅从礼乐文化自身难以找到直接的根据。关于子学产生的制度根源,冯友兰是从政治制度入手,而不是从经济制度入手,因为在冯友兰看来,先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也决定着社会的本质和形态。
关于子学的诞生过程,冯友兰说,“在一社会之旧制度日即崩坏之过程中,自然有倾向于守旧之人,目睹‘世风不古,人心日下,遂起而为旧制度之拥护者,孔子即此等人也”⑦,然拥护旧制度,“必说出其所以拥护之之理由,予旧制度以理论上的根据。此种工作,孔子已发其端,后来儒家者流继之。儒家之贡献,即在于此”⑧,“然因大势之所趋,当时旧制度之日即崩坏,不因儒家之拥护而终止。继孔子而起之士,有批评或反对旧制度者,有欲修正旧制度者,有欲另立新制度以替代旧制度者,有反对一切制度者。此皆过渡时代,旧制度失其权威,新制度尚未确定,人皆徘徊歧路之时,应有之事也。儒家既以理论拥护旧制度,故其余方面,与儒家意见不合者,欲使时君世主及一般人信从其主张,亦须说出其所以有其主张之理由,予之以理论上的根据。荀子所谓十二子之言,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也。人既有注重理论之习惯,于是所谓名家‘坚白同异等辩论之只有纯理论的兴趣者,亦继之而起。盖理论化之发端,亦即哲学化之开始也”⑨。
这是说,面对礼乐制度、礼乐文化的毁坏,面对由此而来的天崩地坼般的社会巨变,先秦诸子在哲学层面围绕“旧制度”的优劣、存废“发声”,在守旧、改革、革命以及否定一切等思路中提出各自的“看法”,并由此展开对话、争论,于是,以儒、墨、道、法、名、阴阳诸家所代表的诸子之学诞生。由此也可看出,冯友兰所谓的“子”主要指先秦至汉初诸子,而非经史子集中的“子”,冯友兰所谓的子学主要指先秦至汉初诸子之学,这与传统的子学观念有区别。传统的子学是“诸子学”“诸子百家学”的简称,“一指先秦至汉初诸子百家学术之总称。一指研究诸子思想的学问,内容包括对诸子及其著作的研究,佚子、佚书的研究,历代学者研究诸子的研究等。晋以后,诸子学的研究对象有所扩大,包括后世的著名哲学家在内”⑩。这么看,冯友兰的子学仅属于传统子学中的一部分,也即传统子学中的“先秦至汉初诸子百家学术之总称”。
这里,冯友兰还论及子学的产生方式与子学的特征。在馮友兰看来,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思想言论极为自由的政治环境下,在以前的思想文化不可能被照搬照用乃至被批评、否定、废弃的价值取向下,在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的学术背景下,先秦诸子无所“依傍”,“无所顾忌”,直接表达其“主张”,并“说出其所以有其主张之理由,予之以理论上的根据”B11,也即做出哲学论述、理论证明。同时,先秦诸子以及先秦诸子所代表的各家各派至少在理论上、在社会选择上是平等的,就是说,“平等”地“发声”,“平等”地接受人们的“选择”。在此情形下,没有超越其他“子”之上的“子”,也没有超越其他学派之上的学派,更没有被定于一尊的“子”或学派。这表明,子学之所以是子学,在于其理论兴趣、理论创新方面的原创性,在于其建构方法、路径方面的“无中生有”“横空出世”,在于诸子之间、各家各派之间的平等,在于思想自由以及表达思想的自由。当然,这里所说的子学的建构“无中生有”“横空出世”,是指其不依赖于任何所谓“经典”而立论、而“发声”,但这并不意味子学与过往的“经典”不发生任何联系。
这么看,凡是通过独创发明、不依不傍的路径而创造出全新哲学的哲学家都有“子”的特质,而具有“子”的特质的哲学家所创造的哲学著作都具有“经”的性质,所创造出的哲学思想都具有子学性质。简言之,子学性质在于其独创发明、不依不傍。
对于子学特征中的诸子之间、各家各派之间的平等以及思想自由与思想表达上的自由,冯友兰特别重视。他说:“春秋战国时代所起各方面之诸大变动,皆由于旧文化旧制度之崩坏。旧文化旧制度愈崩坏,思想言论愈自由。”B12他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道:“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各家各派,尽量发表各自的见解,以平等的资格,同别家互相辩论。不承认有所谓‘一尊,也没有‘一尊。这在中国历史中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最高涨的时代。”B13在冯友兰看来,思想的平等与自由是同等重要且互为前提的,没有思想的自由就没有思想的平等,没有思想的平等同样没有思想的自由,而有了思想的平等与自由,才有哲学家之间真正的平等,也才有哲学家的“人身”自由。
关于子学时代之终结,冯友兰认为是由于“自春秋时代所开始之政治社会经济的大变动,至汉之中叶渐停止;此等特殊之情形既去,故其时代学术上之特点,即‘处士横议,‘各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之特点,自亦失其存在之根据”B14。即是说,汉朝的建立,结束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动荡,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随之正式确立并得以巩固,子学赖以生存的“土壤”随之消失,子学便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汉武帝推行董仲舒的“推明孔氏,抑绌百家”B15,标志子学、子学时代的终结。
从冯友兰关于子学时代的成因与终结的讨论可以看出,子学只能产生并存在于社会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特殊时期,相应的,子学相对于“经学”、子学时代相对于“经学时代”就是特殊的。此外,社会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特殊时期虽然表现为社会的大动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的大动荡都意味社会发生根本性转变。比如,汉代以来的历代王朝的更替,都呈现为社会的大动荡,可是,并没有发生社会的根本性转变。所以,冯友兰说,自汉代以来,“至现代以前,中国之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组织,除王莽以政治的力量,强改一时外,皆未有根本的变动,故子学时代思想之特殊状况,亦未再现也”B16。
由此可以看出,冯友兰认为哲学、思想是抽象的,但是,产生哲学、思想的“土壤”却是具体的;哲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但是,又决定于其“土壤”的状况。在此意义上,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状况对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具有决定性。
二、冯友兰视界中的经学
关于经学和经学时代,冯友兰说:“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B17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也有说明:“在经学时代,儒家已定为一尊。儒家的典籍,已变为‘经。这就为全国老百姓的思想,立了限制,树了标准,建了框框。在这个时代中,人们的思想都只能活动于‘经的范围之内。人们即使有一点新的见解,也只可以用注疏的形式发表出来,实际上他们也习惯于依傍古人才能思想。”B18
这是说,经学时代,儒家被统治者定为“一尊”,儒家的经典被统治者定为“经”,哲学家的哲学创造、哲学思想不再是哲学家个人的事,也不再是纯粹学术的事,而是被学术以外的因素也即政治因素所“禁锢”。这样,与其说,哲学家的哲学创造、哲学思想被固定在“经”的范围内,还不如说被统治者通过“经”的方式所控制。与此相应,在经学时代,哲学家即便跳出儒家之“经”去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也逃不出儒家之外的先秦至汉初其他经典——被先秦至汉初诸子的著作、思想所“限制”。“经典注释”成了经学时代的特色。于是,从西汉董仲舒到晚清康有为,历代哲学家无论是否有自己的哲学思想,无论是否有独特的创见,其哲学思想、其创见都属于“经学”,而非“子学”。因为他们都不是像先秦至汉初诸子那样“以我为主”“凭空而论”,直接地表达其思想、见解,却都是“以经为据”,受制于“经”,通过“解经”的方式曲折地表达其思想、见解。经学时代的哲学家不仅思想上离不开经、“依傍”经,就是在解经的“术语”上也离不开经、袭用经。
从冯友兰的上述表述还可知,冯友兰对经学时代哲学家所“依傍”的“经”,有其独特的理解。在冯友兰看来,这“经”并非经史子集中的“经”,也不是传统经学中的“经”,而是指儒家的“经”以及先秦至汉初诸子的著作,其中,儒家的“经”也就是儒家的“十三经”。
此外,佛学虽是外来文化,但是,中国化的佛学则是中国的。由于中国化的佛学也不是“凭空而论”“横空出世”的,而是有其“依傍”的对象的,冯友兰因而也将其纳入经学时代。他说:“不过在此时代中,中国思想,有一全新之成分,即外来异军特起之佛学是也。不过中国人所讲之佛学,其精神亦为中古的。盖中国之佛学家,无论其自己有无新见,皆依傍佛说,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佛经中所用术语表出之。中国人所讲之佛学,亦可称为经学,不过其所依傍之经,乃号称佛说之经,而非儒家所谓之六艺耳。”B19
这无非是说,中国佛教学者的佛学思想是通过阐释来自古印度的佛经而形成的,同时,中国佛教学者表达其思想时所使用的“术语”也来自古印度的佛经。这样,中国佛教学者是“依傍”“经”而立论,在此意义上,其佛学思想的建构采用的是“经学”模式,其佛学思想也就属于“经学”。只是其所“依傍”的经,是古印度的佛经。这意味着,“中国之佛学,其精神亦为中古的,其学亦系一种经学”B20。
这么看,冯友兰所谓的“经”就不仅包括儒家的“经”以及先秦至汉初的诸子著作,还包括被中国学者所注解、阐释的古印度佛经。这样,冯友兰所谓的经学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学,因为传统意义上的经学乃是指历代注解、阐发儒家经书之学,冯友兰所谓的经学乃是注解、阐发先秦至汉初诸子著作、儒家经典以及被中国佛学家所利用的古印度佛经之学问。这样,传统意义上的经学只是冯友兰所谓经学的一部分。
这么看,凡是通过注解、诠释别人的著作以表达自己哲学思想的学者都具有经学家的特质,而具有经学家特质的学者所撰写的著作都具有经学著作的性质,所研究出来的成果以及表达出来的哲学都具有经学性质。简言之,经学的性质就在于“依傍”別人的著作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
从冯友兰关于经学的论述来看,经学不具有独立性、原创性,是依附性的、缺乏盎然生机的存在;经学受制于“经”,经学的形成、发展以及经学的表达方式等都被“经”所框定。总体上看,经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相比于子学都是呆板与僵化的存在。所以,冯友兰在晚年总结道:“所谓‘经学就是思想僵化、停滞的代名词。思想僵化、停滞就是封建时代一切事物僵化、停滞的反映。‘经学和‘子学,两面对比,‘经学的特点是僵化、停滞,‘子学的特点是标新立异,生动活泼。”B21
由于经学是立足于子学而产生的,子学对经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具有制约乃至决定的作用,冯友兰谈及二者关系时用“旧瓶”与“新酒”的关系表述之。冯友兰说,经学时代“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B22;经学时代,“哲学家之新见,即此后之新酒。特因其不极多,或不极新之故,人仍以之装于上古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B23;经学时代,“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如以旧瓶装新酒焉”B24。这表明,在冯友兰的心目中,酒瓶与酒有着内在联系,其中,旧的酒瓶制约、决定着新的酒的成分与质量,子学对于经学的作用就在于子学是“源”、经学是“流”,子学决定了经学的形式与内容。
关于经学时代的中国佛学与古印度佛经的关系,冯友兰同样以“旧瓶”与“新酒”的关系论述之:“中国人所讲佛学,其中亦多有中国人之新见”,“此即中国人在此方面所酿之新酒也。然亦因其不极多或不极新之故,故仍以之装于佛学之旧瓶内,而旧瓶亦能容受之”。B25这无非是要说,古印度佛经对于经学时代的中国佛学的作用就在于古印度佛经是“源”、经学时代的中国佛学是“流”,古印度佛经决定了经学时代中国佛学的形式与内容。
经学虽然依存于子学而发展,但是,经学与子学毕竟是两种哲学,经学相对于子学毕竟有其“新意”。当经学的发展有“挣脱”子学之倾向之时,经学本应有可能获得突破、新生并发展出超越经学自身的新哲学,经学时代的哲学家却受制于经学思维,不是寻求对于子学的彻底“挣脱”、彻底突破,主动“切断”与子学的联系,而是害怕脱离子学的“保护”,反而“求助”于子学,通过子学的扩张,更准确地说,通过对子学的“扩充”式理解,使得越来越多的著作成为“经”,从而让经学中的新思想能够容纳于子学的框架之中,让经学始终是“经学”而不发生质的变化。这也造成中国哲学有着漫长的经学时代,而没有属于“后”经学时代的近古哲学。所以,冯友兰说:“因此旧瓶又富于弹力性,遇新酒多不能容时,则此瓶自能酌量扩充其范围。所以所谓经者,由六而增至十三,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受宋儒之推崇,特立为‘四书,其权威且压倒原来汉人所谓之六艺。”B26
三、冯友兰视界中的西方哲学分期与中国的子学、经学的划分
在讨论经学时代时,冯友兰论及西方哲学的分期,同时,比较中西哲学的发展历程,试图从中西哲学比较中进一步论述其经学时代以及经学时代与子学时代之差别。为此,我们有必要讨论冯友兰关于西方哲学分期的话题以及中西哲学分期的比较的话题,并且在此基础上讨论冯友兰关于西方哲学不同发展阶段的看法。
关于西方哲学分期,冯友兰认为西方哲学可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划分并不仅是时间层面的,更主要是“哲学”层面的。在他看来,“普通西洋哲学家多将西洋哲学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时期。此非只为方便起见,随意区分。西洋哲学史中,此三时期之哲学,实各有其特别精神,特殊面目也”B27。这是说,西方哲学之所以可以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这三个时期,原因在于这三个时期的哲学各有其“特别精神”与“特殊面目”,也即各有其独特的本质特征。与其说西方哲学可以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这三个时期,还不如说西方哲学可以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这三种形态。
关于中西哲学分期的比较,冯友兰说道:“中国哲学史,若只注意于其时期方面,本亦可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时期,此各时期间所有之哲学,本亦可以上古、中古、近古名之。此等名称,本书固已用之。但自别一方面言之,则中国实只有上古与中古哲学,而尚无近古哲学也。”B28这是说,中国的子学、子学时代相当于西方的上古哲学、上古哲学时期,中国的经学、经学时代相当于西方的中古哲学、中古哲学时期,可是,中国没有近古哲学、近古哲学时期,只有近古时期的哲学,中国近古时期的哲学属于经学。
关于西方上古哲学与西方中古哲学的关系,冯友兰写道:“在西洋哲学史中,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建立哲学系统,为其上古哲学之中坚。至中古哲学,则多在此诸系统中打转身者。其中古哲学中,有耶教中之宇宙观及人生观之新成分,其时哲学家亦非不常有新见。然即此等新成分与新见,亦皆依傍古代哲学诸系统,以古代哲学所用之术语表出之。”B29这是说,西方上古哲学是西方哲学的开端,相对于其后的中古哲学,是“凭空而起”“无中生有”的,是古希腊哲学家在没有任何哲学可以“依傍”的情形下“苦心孤诣”“独自发明”的产物。西方中古哲学则是对西方上古哲学的发展,或者说,是建立在对古希腊哲学的“解释”的基础上的。西方中古哲学不仅在思想上“依傍”古希腊哲学而立论,而且在其哲学思想的表述上也离不开古希腊哲学的“术语”。即便中古时期的基督教哲学以宗教的形式出现,也逃不出古希腊哲学的“掌心”。
基于西方上古哲学与中古哲学的如上关系,冯友兰同样运用他的旧瓶与新酒的比喻来论述二者的关系:“语谓旧瓶不能装新酒,西洋中古哲学中,非全无新酒,不过因其新酒不极多,或不极新之故,故仍以之装于古代哲学之旧瓶内,而此旧瓶亦能容受之。”B30这是说,西方上古哲学是“源”,为西方中古哲学提供了无尽的给养,西方中古哲学是“流”,是对西方上古哲学的诠释与发挥;西方上古哲学对西方中古哲学具有制约性乃至决定性。由上也可看出,西方上古哲学与中古哲学的关系犹如中国子学与经学的关系;西方哲学史上的上古时代与中古时代犹如中国哲学史上的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
在论述西方哲学分期时,冯友兰论及西方近古哲学。这种论述对于我们理解冯友兰所云“中国无近古哲学”有特殊的价值。冯友兰说,“盖西洋哲学史中,所谓中古哲学与近古哲学,除其产生所在之时代不同外,其精神面目,亦有卓絕显著的差异”B31,“及乎近世,人之思想全变,新哲学家皆直接观察真实,其哲学亦一空依傍。其所用之术语,亦多新造。盖至近古,新酒甚多又甚新,故旧瓶不能容受;旧瓶破而新瓶代兴。由此言之,在西洋哲学史中,中古哲学与近古哲学,除其产生所在之时代不同外,其精神面目,实有卓绝显著的差异也”B32。
这里,冯友兰认为西方中古哲学与近古哲学的差异不是时间层面的差异,而是哲学性质层面的差异,是“精神面目”的根本不同。这同时说明,西方近古哲学并不是单纯的时间的产物,西方之所以有近古哲学,就在于西方近古时期不仅有近古时期的哲学,而且这近古时期的哲学相对于中古哲学具有质的不同。
冯友兰认为,西方近古哲学是挣脱中古哲学束缚,同时也不“依傍”上古哲学的哲学,因而不仅根本上不同于西方中古哲学,而且也根本上不同于西方上古哲学,这种根本不同体现在西方近古哲学来源于哲学家的“直接观察真实”,而不是像西方中古哲学那样根源于西方上古哲学。正因为此,西方近古哲学也就不像西方中古哲学那样“依傍”于古希腊哲学,并且沿袭古希腊哲学的“术语”,而是“一空依傍”,“新造”哲学“术语”,成为不同于西方上古哲学与中古哲学的全新的哲学。基于此,西方近古哲学才不像西方中古哲学那样被装于西方上古哲学之“旧瓶”,成为旧瓶中的“新酒”,而是冲破古希腊哲学之“限制”,打破西方上古哲学之“旧瓶”,一方面自酿“新酒”,一方面自制“新瓶”。
这里,冯友兰认为西方上古哲学与西方近古哲学都属于不“依傍”任何哲学、不用别的任何哲学的“术语”的产物,都属于“无中生有”,因而都是具有非凡创造性的哲学,都是全新的哲学,这是二者的相同之处。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西方哲学的“起点”,在此之前无哲学,即便想在思想上有所“依傍”,术语上有所“袭用”,也无所“依傍”,无所“袭用”;后者产生于上古哲学与中古哲学之后,有上古哲学与中古哲学的思想可以“依傍”,有上古哲学与中古哲学的术语可以“袭用”,但是,有而不用:“一空依傍”,也不“袭用”。这么说,西方近古哲学与上古哲学就有着隐隐约约的“相似性”。如果说,西方中古哲学与上古哲学有一条“明线”相连,那么,西方近古哲学与上古哲学就有一条“暗线”相连。这“暗线”就是二者在哲学建构上的独创性、原创性。
与此对应,中国所要建构的近古形态的新的哲学也应是挣脱中国中古、近古时期的哲学也即经学的束缚,同时也不“依傍”中国上古哲学也即子学的哲学,因而不仅根本不同于经学,而且也根本不同于子学。这种根本不同体现在中国所要建构的近古形态的新的哲学不像经学那样根源于、“依傍”于子学,并且沿袭子学“术语”,而是不依不傍,同时,新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成为不同于子学与经学的全新的哲学。基于此,中国所要建构的新的哲学才能不被子学、经学等“旧瓶”所限制,而是自造“新酒”和“新瓶”。这样,中国所要建构的近古形态的新的哲学与子学都是不“傍依”任何经典、任何哲学,自制哲学话语的产物,都具有哲学建构上的独创性、原创性。这么看,中国所要建构的近古形态的新的哲学就具有子学性质。
四、冯友兰视界中中国近古哲学的缺失与经学的终结
相对于西方哲学的上古、中古、近古的分期,为何中国哲学没有近古哲学而长期处于经学时代?换言之,中国为何在近古时期没有超越经学之全新的哲学?冯友兰对此做了分析:“盖人之思想,皆受其物质的精神的环境之限制。春秋、战国之时,因贵族政治之崩坏,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皆有根本的变化。及秦汉大一统,政治上定有规模,经济社会各方面之新秩序,亦渐安定。自此而后,朝代虽屡有改易,然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皆未有根本的变化。各方面皆保其守成之局,人亦少有新环境,新经验。以前之思想,其博大精深,又已至相当之程度。故此后之思想,不能不依傍之也。”B33
从冯友兰的分析来看,哲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受制于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子学的产生与终结基于此,经学的产生与长盛不衰基于此,经学一直延续至近古时代,致使中国有近古时代、有近古时代之哲学而没有近古哲学也基于此。具体说来,中国无近古哲学,只有延续至近古的经学,原因就在于从中古到近古,随着秦汉大一统的确立,中国社会各方面都逐渐走向稳定,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秩序、制度也逐步模式化、固定化,直到近古再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并且不受朝代更替、社会“治”“乱”的影响,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古与近古时期的中国哲人所处“环境”、所拥有的“经验”的总体上或曰质的层面的“陈旧”以及“守成”心态,从而造成中国中古时期哲学的经学性质,也同样决定了中国近古时期哲学的经学性质。此外,从哲学自身的角度看,子学时代所创造的辉煌的思想“博大精深”且相当成熟,大致“规范”了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发展脉络,其本身犹如高山峻岭,令后人难以逾越,这又给后人以“压力”与“制约”,使得后人既有了“依傍”对象,又“不得不依傍之”,从而造成中国从中古到近古都处于经学时代,而没有西方近古哲学意义上的全新的哲学。此处,冯友兰是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的维度所做的分析。
对于中国没有近古哲学,冯友兰还分析道:“直至最近,中国无论在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时代。中国在许多方面,不如西洋,盖中国历史缺一近古时代。哲学方面,特其一端而已。”B34这是说,中国在时间层面身处近古时期,但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依然处于中古时期的状态,君主专制、自然经济是其典型特征。在此意义上,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近古时代”,没有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飞跃,因而没有西方近古时期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根本性变化,没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开启的民主制度、工业革命所开启的商品经济,也就没有近古哲学。这里,冯友兰是从中西比较的维度所做的分析,同时,这种比较是以西方为参照、为坐标的。
关于经学时代的终结,冯友兰写道:“盖旧瓶未破,有新酒自当以旧瓶装之。必至环境大变,旧思想不足以应时势之需要;应时势而起之新思想既极多极新,旧瓶不能容,于是旧瓶破而新瓶代兴。中国与西洋交通后,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各方面皆起根本的变化。然西洋学说之初东来,中国人如康有为之徒,仍以之附会于经学,仍欲以旧瓶装此绝新之酒。然旧瓶范围之扩张,已达极点,新酒又至多至新,故终为所撑破。经学之旧瓶破而哲学史上之经学时期亦终矣。”B35
这是说,中国在其自身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从其内部自然地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自觉地产生西方意义上的近古时期,而是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因为外在的因素催生根本性的变化,体现为政治、社会、经济、学术等的巨变,从而产生西方意义上的近古时期。随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近古时期的到来,一方面是经学的落伍,既不能解答新问题,也不能容纳新思想特别是“西洋学说”,虽然垂死挣扎,也不再能适应新的时代,被新的时代所抛弃;一方面是西方哲学与思想的进入,既不被经学所拘限,又能应对新问题、新时代,犹如洪水猛兽,不可抵挡。在此情形之下,经学这个“旧瓶”即使扩张其“范围”、更新其“形状”,也容不下源源不断进入中国的西方哲学与思想,其自身必然走向崩毁。经学的崩毁无疑就意味经学时代的结束。
由此可以看出,冯友兰在讨论经学时代的终结时依然运用了他“旧瓶”与“新酒”的比喻,只不过此时的“旧瓶”是经学,而“新酒”是西方哲学与思想。随着西方中古哲学的结束,西方近古哲学应运而生,而中国经学时代虽然结束、经学虽然被抛弃,中国近古哲学并没有应运而生,而是西方哲学与思想的涌入。西方哲学与思想既承担了打破“旧瓶”、毁灭经学的责任,又暂时承担了填补经学破灭后中国哲学与思想界的“真空”,直至中国新的哲学的建立。
考虑到西方中古哲学的衰亡与西方近古哲学的产生主要是在不受外部影响,从西方“内部”造成的,而中国经学的衰亡、新哲学的产生既有“内部”的原因,又有“外部”的原因,其中,“外部”的原因至少在表面上看起到了直接的乃至决定的作用。这意味,中国新的哲学的建构,至少一开始在多数情况下会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这么说,中国新的哲学最初的建构者多数应是有西方哲学的功底的。
中国新的哲学的建构会受西方哲学所影响,也会从子学与经学中汲取养分,但是,不会被西方哲学所左右,也不会被子学与经学所“限制”,这是肯定的。否则,它就成了中国化的西方哲学或新的经学。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不可能是中国新的哲学。从总体上讲,中国新的哲学肯定是超越子学与经学的中国所独有的新哲學。
五、冯友兰视界中中国的新哲学应是新子学
经学之后,中国新的哲学也即中国近古哲学在哪里、呈现何种式样?冯友兰说,“前时代之结束,与后时代之开始,常相交互错综。在前时代将结束之时,后时代之主流,即已发现”B36,“中国哲学史中之新时代,已在经学时代方结束之时开始。所谓‘贞下起元,此正其例也。不过此新时代之思想家,尚无卓然能自成一系统者。故此新时代之中国哲学史,尚在创造之中”B37。
这是说,在经学、经学时代即将终结之时,中国新的哲学已经孕育,只是这新的哲学处于初建之时,尚未成“系统”,更未最终“成型”,因而看不出其“式样”。不过,冯友兰在此却道出了这种新哲学的性质,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中国新的哲学既然是经学终结的产物,当然就不属于“经学”,更不属于对经学解读、诠释的产物。这么说,新的哲学与经学“无关”。由于经学是对子学、对“经”的解读与诠释的产物,所以,新的哲学不会像经学一样通过对子学、对“经”的解读与诠释而建构出来,并受制于子学、受制于“经”,否则就成了“新经学”。这么说,新的哲学与子学也“无关”。当然,这里所说的新的哲学与经学、子学“无关”,并不是说新的哲学与经学、子学没有任何联系,而是说不会受经学、子学所制约、左右。
中国新的哲学不是“经学”、经学的“附庸”,也不是新的“经学”,而且不受子学与经学所左右,也不以对子学或经学经典的“注解”、子学或经学固有思想的诠释的面目出现,这新的哲学就应该是全新的哲学。这全新的哲学无论在哲学建构的方法、路径上,还是在哲学思想内容上都应该是独创的,具有子学独创发明、不依不傍的性质。这么看,中国上古哲学为子学,那么,中国近古哲学因其具有子学性质,就可以被称作“新子学”。
值得注意的是,冯友兰用“贞下起元”表达新哲学的产生。在冯友兰看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体现为元亨利贞等发展阶段的开放式“循环”,在中国已有的哲学进程中,已经完成了一次元亨利贞的历程。其中,“元”代表子学阶段,“贞”代表经学的终结;中国哲学的新发展是“贞下起元”,从“贞”新生出新的“元”,也即从经学的终结走向新的子学的诞生,而不是从“贞”又简单地回到“元”,从经学的毁灭、终结回到过去的子学。这样,这新的哲学就是“新子学”。这“新子学”呈现的就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全新局面、壮丽画卷。
冯友兰以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确定中国哲学的分期,以子学与经学论述中国哲学的形态。在冯友兰看来,中国哲学在性质上只有子学与经学这两种形态,不会有第三种形态,因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已有的哲学要么是子学,要么是经学;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要么不“依傍”任何已有的经典而“独自生成”,要么“依傍”已有的经典而以“经典解释”的面目出现,不可能有第三条“道路”、第三种“选择”;中国新的哲学如果不“依傍”任何已有的经典而“独自生成”,无疑具有子学性质,从而成为新的子学——“新子学”,而如果“依傍”已有的经典而以“经典解释”的面目出现,无疑具有经学性质,从而成为新的经学——“新经学”。
在冯友兰的心中,中国新的哲学既然是突破经学桎梏的产物,就不可能是“新经学”,而只能是“新子学”。
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回忆道:“我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社会大转变的时代,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一个是清朝末年中外交通的时代。在这两个时代中,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起了根本的变化。这实际上说的是,中国社会由奴隶社会向封建制过渡,和由封建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过渡的两个时代,但是我没有用这些名词,因为这些名词在当时还没有确定下来。”B38在第一个“社会大转变时代”——“春秋战国时代”,产生了中国上古哲学;在第二个“社会大转变时代”——“清朝末年中外交通的时代”,应该产生中国近古哲学,但是,产生的却是中国近古时期的哲学。不过,随着经学的破灭,中国近古哲学也正在艰难的创造中。
由于冯友兰认为哲学、思想的产生取决于其“土壤”,即取决于当时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状况,有什么样的哲学“土壤”就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哲学形态,而“春秋战国时代”与“清朝末年中外交通的时代”在性质上同属“社会大转变时代”,同是政治、经济、社会巨变的时代,建立在这种时代基础上的哲学在性质上就应该是相同的。“春秋战国时代”产生的中国上古哲学是“子学”,从“清朝末年中外交通的时代”开始艰难生成的中国近古哲学在性质上就应该具有子学性质——“新子学”。
结合冯友兰关于西方近古哲学的表述,我们可知,中国新的哲学相当于西方的近古哲学,西方近古哲学的产生没用借用西方上古哲学与中古哲学的思想与术语,而是“一空依傍”,自造术语。以此类推,中国新的哲学也一定是不借用中国上古哲学与中古哲学的思想与术语,而是像西方近古哲学那样“一空依傍”,新造术语。西方近古哲学与上古哲学在哲学建构方法上是相似的,这样,西方近古哲学在哲学形态上就具有西方上古哲学的性质;中国的新哲学与中国上古哲学在哲学建构方法上也应是相似的,中国新的哲学在哲学形态上应具有中国上古哲学的性质。中国上古哲学是子学,中国新的哲学就应具有子学性质,从而以“新子学”的面貌出现。
从冯友兰个人的哲学思想的建构来看,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中没有近古哲学,为此,他以建构中国近古哲学为使命。他在晚年被自己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时,在“答词”中回忆道:“在四十年代,我开始不满足于做一个哲学史家,而要做一个哲学家。哲学史家讲的是别人就某些哲学问题所想的;哲学家讲的则是他自己就某些哲学问题所想的。在我的《中国哲学史》里,我说过,近代中国哲学正在创造之中。到四十年代,我就努力使自己成为近代中国哲学的创作者之一。”B39这里,冯友兰不仅论及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建构,还论及同时代的“他人”的哲学思想的建构。冯友兰把自己看作“近代中国哲学的创作者之一”,意味中国近古哲学的创造者不是冯友兰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冯友兰不仅把自己所创作的“贞元六书”、所建构的哲学——新理学看作是中国近古哲学,同时,也把同一时期其他哲学家所建构的新哲学看作是中国近古哲学。这其实是在说,民国时期哲学家们所创建的中国的新哲学乃是中国近古哲学。
民国时期哲学家辈出,哲学学派纷呈,并且彼此平等,相互论战,竞高争长,这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子学盛行何其相似!在此意义上,冯友兰何尝不认为这一时期的哲人是“新子”,馮友兰何尝不认为这一时期的哲人所创建的新哲学就是“新子学”。当然,民国时期的哲学家们所创建的新哲学是否都具有子学性质,是否都配得上“新子学”的称呼,那是另一回事儿,需要做进一步讨论。比如,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就曾说道:“当我在南岳写《新理学》的时候,金岳霖也在写他的一部哲学著作,我们的主要观点有些是相同的,不过他不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我是旧瓶装新酒,他是新瓶装新酒。他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并且创造了一些新名词。”B40这里,冯友兰认为自己的哲学思想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是对程朱理学的发挥、发展,因而是新的理学——新理学,但是,毕竟也受程朱理学所“限制”,相当于“旧瓶装新酒”,具有他自己所谓的经学性质,不过,冯友兰认为金岳霖《论道》中建构的哲学思想则是独创的——不仅哲学思想内容是独创的,所用以表达哲学思想的“术语”也即哲学范畴也是独创的,因而不受任何已有的哲学、经典所限制,相当于“新瓶装新酒”,具有冯友兰所谓的子学的性质。显然在冯友兰看来,金岳霖无疑属于“新子”,其哲学思想无疑属于“新子学”。
六、结语
由上可知,冯友兰所谓的子学乃是指先秦汉初诸子之学,只是传统的子学的一部分。在冯友兰看来,由先秦汉初诸子而有先秦汉初诸子之学,由先秦汉初诸子这“子”而有“子学”。此“子学”的建构“以我为主”,无所依傍,属于“无中生有”,因而是“创构”。冯友兰所谓的“经学”主要指的是从汉代到清代整个中国君主专制时期的哲学,传统的经学又只是冯友兰所谓的经学的一部分。在冯友兰看来,由“经”而有对“经”的注解与诠释,而有“经学”。此“经学”的建构“以我为辅”,“依傍”于“经”,乃至“以经为据”,属于“有中生有”,因而是“重构”。按照冯友兰关于“经”“子”关系的论述,应该是有“子”、有“子学”才有“经”与经学,“经”只能是“子”的著作,可是,冯友兰所谓的“经”除却“子”的著作外,还包括儒家的“经”,而且儒家的“经”又有从“六经”到“十三经”的发展,另外,还包括被中国佛学家所注解、诠释的来自古印度的佛经。这里,“子”始终是那些个“子”,“经”却越来越多。这是因为在冯友兰看来只要不是原创的著作、哲学就属于“经学”性质、“经学”范畴,反过来,“经学”所“依傍”的著作、对象就具有“经”的性质,就可以被称作“经”。
冯友兰认为中国新的哲学的诞生标志着“贞下起元”,这并不是意味对“子学”的复归、重新从“子学”出发,而是意味着“重新开始”,像“子学”一样“创构”新哲学。这么说,冯友兰所谓的中国新的哲学应该就是新的“子学”也即“新子学”——“新子”所原创的哲学,虽然冯友兰没有明确这么说。
注释
①②B17B19B20B22B23B24B25B26B27B28B29B30B31B32B33B34B35B36B3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3、3—4、4、5、4、4、343、5、4—5、3、3、3、3、3、3、4、5、5—6、343、343页。
③④⑤⑦⑧⑨B11B12B14B1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19、22、22、23、23、23、25—26、25、26页。
⑥《诗经·小雅·北山》。
⑩严北溟:《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第563页。
B13B18B21B38B39B40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7、187、187、186、308、215页。
B15《汉书·董仲舒传》。
责任编辑:涵 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