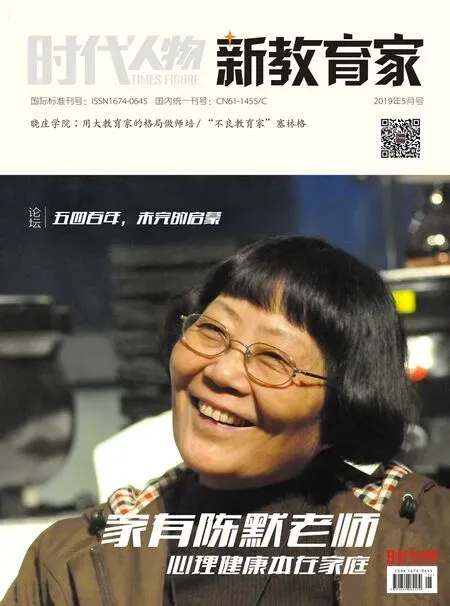隐匿在《清明上河图》中,北宋盛世下的忧愁
特约撰稿_俞希 独立艺评人

中国古典传世名画中,《清明上河图》应该是目前最为人熟知的一幅。宋代画家张择端的神来之笔,画下了一幅汴梁盛世。《清明上河图》里故事线非常多,河船酒楼,平民百姓,贩夫走卒,都是看得见的热闹和繁荣。但是,还有一些穿插在繁华中的暗线,他们不是主角,却揭示了画者真正的意图。本文就从《清明上河图》画卷的末端几个细部聊起。
画中出场的人,他们是一个时代景象的线索
《清明上河图》,宋代画家张择端的神来之笔,画下了一幅汴梁盛世。《清明上河图》里故事线非常多,河船酒楼,平民百姓,贩夫走卒,都是看得见的热闹和繁荣。但是,还有一些穿插在繁华中的暗线,他们不是主角,却揭示了作者真正的意图,那是隐匿在盛世下的忧愁。
例如:无人望火的望火楼。没有官兵的城门。无精打采的兵卒。画卷末段的十字路口,一个小两层楼的房子,招牌上写着“久住王员外家”。这是一间旅店,“久住”有“老店”的意思。二楼的窗户里,一个戴着头巾的读书人,正看书看得入了神。他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书法,桌上放着笔架。
这人来京城做什么?参加“高考”,金榜题名,迎娶宰相女儿,从此走上人生巅峰?这确实是当时众多学子的理想之路,也有机会实现。因为宋代是一个机会相对公平的朝代,不像唐朝那么阶层固化。寒门能出贵子,麻雀也可以变凤凰。这个机会就是科举制度。那时候,每年有数十万人想要挤上这座独木桥。
成功了,就像旅店外街上的那位官人一样:戴着笠帽的高官,昂首骑在马上,几名随从在前方开路,他们的帽子上有两根帽翅,这是北宋的官帽,可以横在两侧,也可以折到后面。高官身后还有两名随从,挑着沉重的行李,看样子,他似乎是要离开京城,去别的地方风光赴任。
混得不好的,就各有各的滋味了。还是在旅店的那个十字路口,一人身穿白衣,骑在马上,仆人在前领路;他似乎看到了熟人,头微微左侧,想要打招呼。但那个“熟人”,一手拎着衣摆,一手举起扇子挡住了脸,摆明不想搭理你。
这个“扇子”其实叫做“便面”,当时朝廷里党派斗得太激烈,以至于人们在街上相遇,都要以扇遮面,避免尴尬。

无精打采的衙署人员

“久住”旅店中的书生
一把“便面”,掩住多少政治浮沉和人生况味
一代文豪苏东坡也正卷入其中。因为他不单是文人,更是积极的政治人物。他当时激烈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所以,他那一派也叫旧党,代表人物还有司马光。那些年的北宋朝廷,基本就是拥护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对骂干架,轮流坐庄。而苏东坡的仕途,也随着新旧之争,浮浮沉沉,一时备受重用,一时又被发配边远之地。
这番争斗还带动了一项文艺活动。那时同党的文人喜欢搞小团体,有地位的文人,在自己家前屋后累叠湖石,栽种花竹,邀请同党中人聚在一起,赏花吟诗,抒发胸臆,称之为“雅集”。
很多名为“西园雅集”的画,就是描绘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人在驸马王诜府中的聚会。
在《清明上河图》卷尾的医馆后面,用俯瞰的视角,画了一个文人的园林,庭院虽小,但种着盈盈翠竹,中有叠石点缀,甚是风雅。汴京的士大夫好种竹,苏东坡曾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倒不知道画中的这一家是新党还是旧党?
那么,《清明上河图》中的“苏东坡们”是正得意之时,还是失意之时呢?

骑马的高官

行书罩布下,是送去要焚毁的作品。

苏东坡画像
答案就在巍峨的城门口。
画中临近城门处,有一辆独轮车,车上覆盖了一张写着书法的盖布,上面的字体行云流水,似乎是大字草书。这样的文人草书,怎么着都该被精心装裱,摆在富豪的屋子里作屏风。现在却被弃如敝屣,潦草地盖在车上。这就要怪宰相蔡京了。他猛烈打压旧党人,把司马光、苏东坡、黄庭坚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元祐奸党”,并刻石碑颁布天下,石碑上的旧党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
旧党人的著作与书法,也多次遭到焚毁,尤其是苏东坡和黄庭坚的著作,如发现收藏习用者,立即焚毁,并以大不恭论罪。所以,这些盖布,的确可能是大户人家或官府大屏风上的绢本书法,因为新旧党争,被拆了下来,下面盖着旧党人物的书籍,一起送到郊外焚烧。
蔡京也是一个书法名家,说不定这里边,还有他的一点小私心,打压政治对手的同时顺便干掉书法竞争品。
回头再看画中刚才擦肩而过的那两个人,骑马的似乎是朝中得势者,走路的文人或许就是落魄的“苏东坡们”,用一把“便面”,维护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
画中的那条汴河,不知见证了多少豪情万丈的到来,黯然神伤的离开
关于“便面”,还有一种说法,《清明上河图》画中的街道,大抵码头酒市,是脚夫贩妇、凡夫俗子谋生寻乐的场所。宋朝法令规定,“斑白不游市井”,朝廷官员不得已在这种地方出入时,必须按宋朝规矩换上便服,手中还要再加一把“便面”半掩面孔。
据说,宫廷乐师刘几常,在退朝后就会换上棉布便袍,手持便面遮掩过市,直奔开封的娱乐场所。而苏东坡被贬为元祐罪人后,曾漫步开封,手持画有自己肖像的便面,作无声的抗争。
政治失意之后,苏东坡更加醉心于佛教。他有个和尚朋友叫佛印,加上他弟弟苏辙,三人时常在一起颂诗谈禅,留下不少趣闻。
《清明上河图》中,还是在那个十字路口,一位红袍僧人和两名儒士相谈甚欢,不知是否是画家想起了苏东坡兄弟和佛印的轶事?
他们身后,一个大胡子正在肉铺门口说书,讲到精彩处,手舞足蹈。围观的人群里,有一名僧人,他的左边是一位儒士,儒士身旁的男子,头上盘着发髻,发髻上插了一根簪子,手里拿着一把鹅毛扇,这是道士的打扮。儒释道聚在一起听书,这一定不是巧合。
宋代可以说是中国思想的第二个黄金时期(第一个是春秋战国)。古代儒家学说在学者们的努力下重获新生,并且还吸收了佛教和道教的教义,变得更加人性。儒、佛、道“三教”合流,彼此吸纳,成为宋代一道独特的风景。
那是读书人最好的时代,宋朝重文,即使官场失意,也可以凭笔墨才情受万人敬仰。许多仰慕苏东坡的文人,偷偷带着他的文集出城,奉命雕刻“奸党”石碑的工匠,也不愿动工;这也是读书人最坏的时代。政局动荡,外敌环伺,士大夫的治国理想难以舒展,颠沛流离。就如苏东坡,垂暮之年等来再次启用,却在归途中辞世。
画中,不远处的城门下,正上演一场送行。头戴席帽的官人骑在驴上,对面半跪在地上的男子,正在宰杀脚下放倒的黄羊,身旁站着的人,手里似乎拿着一张祷文。这叫“杀羊祭道”,为出远门的人祈福,保佑他一路平安。
汴水边,一棵粗犷硕大的柳树下,两位文人拱手对拜,依依惜别。他们的身后,一艘船似乎快要启航。即使虹桥下险情迭出,众人喧闹如沸,他们也毫不在意。
这一去,或许就是永别。

一把便面掩住多少人生况味
苏东坡离开的时候,也无法预料自己接下来的命运。望着这奔流的河水,他说了一句:“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

河边送别,见证多少黯然神伤的离开。

儒释道聚在一起听说书,这不是巧合。
《清明上河图》卷为绢本,水墨淡设色,纵24.8厘米、横528.7厘米。此画卷是画家选取了汴梁城中的一个局部,细细加以描绘,犹如现场录像中的一段切片。从外城的菜园子,一直画到内城最为繁华的地段。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的画卷本幅上,并无画家本人的款印,确认其作者为张择端,是根据画幅后面跋文中金代张著的一段题记:“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