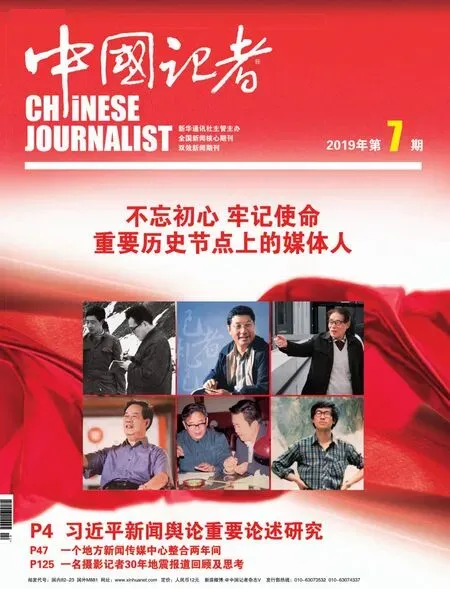梁衡:为文铸魂的新闻人
□ 文/操凤琴
梁衡崇敬范仲淹,范仲淹崇敬严子陵。范仲淹曾这样赞美严子陵:“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也借用这句话来表达对当代著名新闻人梁衡的崇敬,他受之无愧。无论人格魅力还是学识才华,或是忧国忧民的情怀,他都是中国当代新闻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之一。
我最早知道梁衡,是在1984年初中三年级的语文课本上。这一课本说明文单元中《晋祠》一文的介绍是:“本文选自《光明日报》,作者梁衡,男,《光明日报》记者。”《晋祠》里的句子“春日,黄花满山,径幽而香远;秋来,草木郁郁,天高而水清”,谁能想到这是一篇说明文的文字。正如老作家冯牧先生所说:《晋祠》作为范文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是当之无愧的,无论从思想内容、审美观点及遣词造句上所认真下的功夫都是无可挑剔的,无愧于“教科书水平”。
直到20多年后,1996年,我在《新华文摘》上读到《觅渡,觅渡,渡何处》,一口气读完,独坐久久,只有震撼!这哪是一篇普通的人物散文?这是作者与主人公的心灵交流!他对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一生的总结与评价,穿越时空,回肠荡气。瞿秋白的女儿、新华社离休干部瞿独伊后来对梁衡说:“你是我父亲的知音。”
鲁迅先生曾书赠好友瞿秋白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是瞿秋白生前的知己,而梁衡,以孤篇压全唐般的《觅渡》,成为瞿秋白死后的知己。
《觅渡》后来被刻在江苏常州的瞿秋白纪念馆。若没有与优秀灵魂同等的高度,怎能与优秀的人做知音?梁衡写秋白,就如汉代司马迁写战国的屈原:“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都是同样优秀的灵魂在不同时空展开的心灵对话。
由于同在新闻界,后来我有缘结识梁衡。借用他在《觅渡》中写瞿秋白的话,我形容这位当代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他既是一座平原上的高山,令人崇敬,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他的思想纵横交错,他的人格又坦荡如白纸。他是真豪杰!”
一
梁衡的人生之路、新闻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大的挫折,有好几次:中学时代热爱文学,17岁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却被分到档案系;正要沉下心来干专业,1968年大学毕业时,却又逢“文革”,他被分配到内蒙古偏远小县临河当农民,防汛护堤、放马。他慢慢做到县里的宣传干事、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
梁衡从25岁开始两度当记者,先在内蒙古日报,中间在山西省委工作四年,后又为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一直干到41岁。这两次记者生涯,都是在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基层,却写出不少好新闻。
他说,初当记者时,总有一种新鲜感和自豪感,仿佛周围的人物、事件都由我的笔尖来调遣,但再当下去,就渐渐觉得相反,是这些人物、事件在牵着他的笔尖。有些人他不写出来就寝食不安。他说:“有些事我写着写着心就发抖。几乎凡是我写过的正面人物都成了我的朋友,是他们教育了我,帮助了我,成就了我。我觉得自己在多年的记者生涯之后由天真变得实在,由浮躁变得深沉。”
1985年,梁衡在北京进修学习,那一年,开全国两会,山西代表团有四位全国人大代表来看他。
为何呢?这四位代表,都是梁衡挖掘出来的新闻人物,有军工厂的工程师,有种枣树的土专家,他们被梁衡报道成名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有的后来还当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而梁衡所在的山西省,经济、科研和教育水平在全国都处于下游,是没有新闻的角落,就如杜导正所说“打仗时处于不利地形”。但梁衡“土疙瘩里刨食”,一手“挖”出了四位全国人大代表,为隐者立传,为无名者传名。
我曾当面请教梁衡:您的新闻生涯如此精彩,有什么秘诀?
他说:写稿要“三点一线”。上面在抓什么、下面老百姓在想什么,你这个记者发现了什么,这三点能成一线,稿子就百发百中了。这里要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还要接地气。记者不能天马行空,由着性子写;也不能一味跟风,没有自己的思想。
说到敬业精神,梁衡有一句名言:“记者出门跌一跤,也要抓一把土。”战士要有每战必胜的信念,记者要有每采必得的思想。采访是一件很艰苦的事,一个记者如果没有这种顽强的意志和对收获的贪婪,便会平庸终生,一无所获。
梁衡在基层做记者时写植树节植树这种常规新闻,取的标题也与众不同,满溢诗情:《东一株西一株积木成林 今一棵明一棵坚持有益》。
某县公路两边栽树多,梁衡一篇300来字的新闻:《路旁就是储蓄所 一步一辆自行车——某县公路林储材百万方价值两个亿》,竟然获得“全国林业好新闻奖”,很大原因是标题跳出了例行公事写报道,把心融进来,首先想到的是这些树木为老百姓、为当地社会带来了多大的好处,提笔未成文,自己先激动了。哪个评委不赞赏这样的记者?不给这样的文章投票呢?
1982年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晋祠》,也是他在山西做记者时为《光明日报》副刊所作的一篇文章。
梁衡简介
梁衡:山西霍州人,著名新闻记者、作家、学者。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中国记协常务理事、《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小学语文教材总顾问、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著有梁衡新闻四部曲:《记者札记》《评委笔记》《署长笔记》《总编手记》;散文《觅渡》《洗尘》《把栏杆拍遍》;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政论《官德十讲》《继承与超越》《为官沉思录》;学术研究《我的阅读与写作》《毛泽东怎样写文章》等。曾获“全国好新闻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赵树理文学奖。多篇作品入选大、中、小学课本。
在新闻理论方面,提出新闻的“梁氏定义”、报纸的四个属性、新闻与文学的12个区别、新闻与政治“四点交叉统一律”等。首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在对报社的记者管理中,大胆实行稿分排行的激励机制。在文学方面开创政治散文写作,学术上首创“人文森林”新学科。
二
梁衡事业之路再次遇到挫折:是上世纪80年代、梁衡40岁左右时,中央搞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他从山西入选中组部的全国省部级干部第三梯队,一封八分钱的匿名告状信将他拉下。等事情慢慢查清、还了他清白,但第三梯队的名单里已没有他了。
人生路上,梁衡一次次掉进井底,又一次次自己抓着井绳爬了上来。他写诗自勉:
宠而不惊,弃而不伤。
丈夫立世,独对八荒。
天生我才,才当发光。
不附不屈,慨当以慷。
他说:一生绝对顺利的人,等于他没有在世上活过一回。因为除了享受,随波逐流,他没有给这个世界贡献什么、留下什么。
第三梯队名单里没有了他,他从中央党校拖着一箱书重回山西当记者。在等待调查结果的这两年时间里,他埋头读书、写书,完成了近40万字的章回体科普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近30年来,这本书再版了30次,不知救了多少怕数理化的孩子。
怎么才能当一个不平庸的好记者呢?梁衡说:是记者就要是学者。学问能拉开记者的档次。一个记者,当他只是一名“记者”时,他就只能是一个“传声筒”。一个学者型的记者,不只是传递消息而是研究问题,而且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知识广度。中年之后当他要改行,他要起飞,学问便是他飞行的翅膀。
中年之后的梁衡,从光明日报山西记者站调到新成立的新闻出版署工作,先后担任报刊司司长和副署长,从一线新闻人“改行”为全国新闻报刊行业的管理者。尽管身在官位,他却不说官话空话,不说正确的废话,他忧心为政,真情为文,一生不改赤子性情。
正如他在通讯《佩莱斯王宫记》一文中说:“权力再大,也将随生命而止。可是当他趁有权之时,选择做一点国家民族永远记住的事,这权力便转变成了永久的荣誉。“
担任副署长时,有一年,署里筹了六大卡车冬衣,梁衡带队送往贫困地区。12月寒风起,该贫困地区的地方官进京来看他,他问起冬衣的事,这位官员说:冬衣还放在仓库里,等着春节“送温暖”。他大怒,不顾“高官形象”,也不管自己与对方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指着这地方官的鼻子斥责:“你怎么知道自己早早穿上棉衣,先把自己的身子温暖了呢?!”地方官哑口无言。
在新闻出版署工作期间,某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到他办公室,送来一本装帧极其精美的大书请他“指正”,有半个茶几大小(事后称重,24斤)。本以为能讨得这位出版高官的欢心,梁衡却大怒:花这么多钱、搞得这么豪华,浪费纸张要砍掉多少棵树!
梁衡曾在《跨越百年的美丽》中这样写居里夫人:“她本来可以躺在任何一项大奖或任何一个荣誉上尽情地享受,但是她视名利如粪土,她将那些奖章送给6岁的小女儿当玩具。上帝给的美貌她都不为所累,尘世给的美誉她又怎肯背负在身呢?”而梁衡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

▲ 2009年3月27日,新中国成立以来传媒界举办的首届报人散文奖在古城西安举行颁奖典礼。《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著名媒体人梁衡在获奖后发言。(新华社记者 陈昌奇/摄)
三
2000年,梁衡从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岗位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做《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甘苦自知。他曾有一首词写在值夜班的日子——
遥夜如水孤灯照
窗外星光,桌上电脑
夜班昨夕又今宵
钟摆漫摇,键盘轻敲
闲拍电话等电稿
车声迢递,东方破晓
长夜最是把人熬
白了青丝,黑了眼梢
——《一剪梅·报纸夜班》
做副总编辑,几乎每天都是凌晨两三点签完大样才能下班,而白天又常有会议或活动,24小时连轴转是常态。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也曾说过:“我在这个吃苦受累的岗位上,苦熬了7899个日日夜夜。”梁衡与南振中用的竟然都是同一个字:熬。
梁衡熬身体,熬意志,熬思想。但就在这种“煎熬”中,熬炼出许多好文章。身在新闻界高位,他依然做淘金的苦力。在年复一年的苦活中,他淘出一座座精神的金矿:他的笔下既有普通女教师、护山老者、养猪人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小人物,也有瞿秋白、张闻天、辛弃疾、李清照、居里夫人这些古今中外的名人大家;他从早期的山水散文,到人物散文,再到政治大散文、时评杂文,创作高峰接着一个高峰。

他的诸多文章,让政治有了美感,让观点有了灵魂。他说:“为文不酸,为人不弯,才是真文人。”
他说:“我本没有写杂文的打算。我的主业是新闻,副业是散文。但因做记者接触社会,所见甚杂;后来在官场,阅人更多,遇事愈杂。看多了就不能不想,有想法就不能不说。”他的诸多文章,让政治有了美感,让观点有了灵魂。他说:“为文不酸,为人不弯,才是真文人。”
从《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岗位上退休后,2011年他上庐山采访,写了纪念张闻天的心血之作《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他的政论新书《官德》《文风四谈》《干部修养谈》《为官深思录》等,同样是丹心铸就的精品。他曾有一首诗谈为官与写作:“文章千古事,纱帽一时新。君看青史上,官身有几人。”
他自己的头衔很多,官职且不说,业余头衔每一个拿出来,都是响当当:全国人大代表、全国记协常务理事、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人教版中小学语文教材总顾问……但他自己却不喜欢拿头衔说事。他写过一篇杂文:《享受岂能是头衔?》,隔三差五就被人们改成《罕见省部级高官不吐不快》等题目,改头换面一遍遍在网上传。
四
退休后的梁衡又用6年时间写了本书:《树梢上的中国》。选材标准一向苛刻的商务印书馆,2018年出版了这本书。他一生都在永求创新。一个文科生写一本《数理化演义》,一个记者写了《树梢上的中国》这样的林业专题散文,最近又被邀请到几个林业大学去讲《人文森林学》。
为写这些树,梁衡踏遍青山。
青山在,人已老,当年英姿勃发、风华正茂的梁衡已是满头银发,但是只要谈到树,谈到他所创立的人 文森林学,依然是烂漫赤子之情溢于外。
梁衡在上世纪80年代采访过一位81岁的老人,老人备好棺材、进山栽树。他为老人写下通讯《青山不老》,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被收入小学六年级课文已近20年,成为经典。梁衡在文中说:“一个人将生命融入一种事业,也就无所谓生死了。”
季羡林先生生前这样评价梁衡:梁衡属于“经营派”,而且他的“经营派”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都非同寻常。梁衡是一个肯动脑、很刻苦又满怀忧国之情的人。他到我这里来聊天,无论谈历史,谈现实,最后都离不开对国家、民族的忧心。难得他总能将这一种政治抱负,化作美好的文学意境。
梁衡说:在“命运”这个大算盘上,人只是一颗算珠,自己无法掌控;但在“生命”这架小算盘上,人就是自己的主人。他还说:报国之心不可无有,治学之志不可稍怠。他用一生,做到了。
作为对家乡儿女的褒奖,今年春天太原市做了两件事。一是将梁衡选入课本已36年的《晋祠》刻碑于晋祠公园。这篇文章36年来让晋祠名扬国内外,不知带来了多少游人。二是母校太原十二中成立了一座“梁衡图书馆”收藏了他出版的100多个图书版本,供人研究。
——读梁衡新书《觅渡觅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