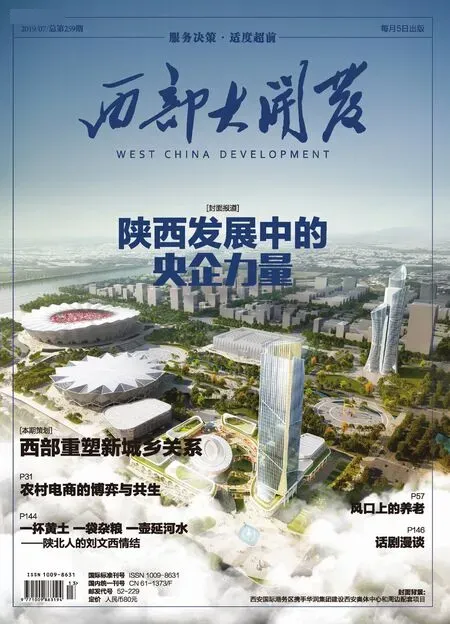话剧漫谈
文 / 本刊记者 王薇
与电影相同,话剧亦是舶来品,但相较于代表着时髦与娱乐的电影,已在中国走过100多年历史的话剧,似乎从未成为大众的艺术消遣对象。即便在文化消费如此普及的今天,话剧有了令人鼓舞的市场表现,但依然难逃小范围“自嗨”的尴尬困境。
究其原因,恐怕是话剧这一剧种的独特性使其所然。
话剧,被束之高阁的高雅艺术?
从20世纪初被引进至今,话剧已在中国走过了百余年历史。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长河中,话剧当属年轻的剧种。
有着200多年历史且被奉为国粹的京剧,在民国时期的火爆程度,从《霸王别姬》《梅兰芳》《大宅门》这些耳熟能详的影视作品中可知一二,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京剧横扫了社会的全部阶层。北京、上海、天津、武汉,这些繁荣的大城市更是戏园遍地。在当时,仅北京一地,演出京剧的就有第一舞台、文明茶园、广德楼、广和楼、燕喜堂、广兴园、广乐茶园、丹桂茶园、吉祥茶园、中华茶园、德泉茶园、天和茶园、庆升茶园等20多家戏园。
而观众对京剧的痴迷程度更令人津津乐道,有倾家荡产捧角的,有砸锅卖铁学戏的,有心甘情愿把工作辞了“专职追星”的。在电影《霸王别姬》里,葛优饰演的“袁世卿”作为民国时期的没落贵族,对张国荣饰演的京戏名角儿“程蝶衣”出神入化的精湛演技和俊美的容貌深深折服,直叹“虞姬再生”,并赏赐给程蝶衣一整盒异光闪闪的银蝴蝶首饰。这样的电影情节并非空穴来风,历史上围绕梅兰芳先生的一群超级粉丝被称为 “梅党”,国会议员、银行家、知名文人、画家、教授……出钱出力、写剧本、编唱腔、找房子,“梅党”样样都管。
如今的京剧虽然已然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它仍是象征着传统与祥和的春晚保留项目,亦是很多老百姓茶余饭后的文艺消遣。
咸丰年间,京剧开始攻占“文娱市场”,而1903年,在北京的乐天茶园,中国人开始第一次自己放映电影。1905年,中国有了第一部自己拍摄的电影,而有趣的是,这部电影《定军山》的题材是京剧,其主演更是当红京剧“名角儿”谭鑫培先生。
在当时,电影是时髦的代名词,意味着洋派、前卫、新式生活。由于受众的不同,京剧的火热完全未能成为电影走红的阻碍,电影几乎成了京剧之外最好的文娱消遣方式。据统计,1925至1927年间,上海先后成立了140家中小型电影公司。1930年之后,几乎每隔一个月上海就有一个影戏院诞生。

春柳社于1907年在日本演出《黑奴吁天录》

从1931年至1945年,中国话剧在抗日战争中浴火重生
几乎与电影同时期被引进的话剧,却与其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1907年,春柳社(中国文艺研究团体)在东京演出《茶花女》片段和《黑奴吁天录》,这一事件被视为中国话剧史的开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话剧确实在中国活跃,但主导者大多是戏剧爱好者与业余社团,演出地点也大多集中于学校、礼堂。虽然“活跃”,但其规模难以跟京剧与电影相抗衡。甚至直到1928年,“话剧”这一剧种名称才被明确确立下来。1933年,中国旅行剧团诞生,这是中国第一个营业性质的职业话剧剧团。从这时开始,话剧才真正进入寻常百姓的视野,带上了大众娱乐的性质。
但在当时,话剧能被广为传播的最大契机却是抗日战争。为适应抗战形势,形形色色的救亡演出队与抗敌演出队不断涌现出来。他们深入部队、农村、工厂,以宣传抗日、动员群众为目的,主要演出街头剧、独幕剧。所以可以说,当时的话剧更多的是一种宣传工具,而非艺术表达。
话剧的“不温不火”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京剧与电影的火热,伴随着中国近代城市化的发展。大都市的兴起,使得文娱消费成为市民生活中难以割舍的重要生活方式,而具有极强娱乐性的京剧与电影,为文娱消费的兴起担当了重要载体。而为启迪民智而生的话剧,其创作者与受众则更多局限于知识分子和学生。
当下,人们有了更多的娱乐方式。电影保持了它的传统娱乐性,并在不断走向多元与深度;京剧,因“国粹”而受人尊重,但再难回到民国时期万人空巷的热度;回顾历史,会发现话剧的每一个脚步,都伴随着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富强、民主、文明的历史进程。如今,一直在小众间活跃的话剧也渐渐开始放低姿态,很多话剧经过改编、嫁接拍成了电影,而话剧的表达形式亦是不可或缺的艺术剧种。
小圈子困境:话剧能否成为大众文化?
长期以来,话剧的剧场属性,使其始终面临着原创产量低、生产周期长、收入预期风险大等问题,这些问题引发了制作资金匮乏、人才缺失,以及自娱自乐的困境,当然,这些困境,无一不是话剧的“小圈子”所带来的。
停留在小众阶段的话剧,观众少,票房低,无法赚钱,更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宣传与巡演,自然更难获得资本的垂青。因此诸多剧组都通过自筹,或依赖各种补助。一旦资金不够,影响话剧质量的同时,更可能引发观众不满,入不敷出,注资希望渺茫的恶性循环。基于此,虽然中国各大艺术院校每年培养出大批优秀的导演、编剧、演员、幕后,但投身话剧的少之又少。
与此相对,话剧的大众化,意味着话剧题材的多元化,庞大的观众基数,资本的大量注入,以及戏剧从业者的积极性被激发等。随着时代的变迁,话剧亦在蓬勃发展。
如今,打开各类票务APP,可以看到丰富的话剧演出信息。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17年五年时间里,话剧演出场次持续增加,从2013年的1.12万场增加到2017年的1.6万场。除了不断增加的场次以外,话剧市场的上座率也不断提高。从2013年到2017年,除2014年上座率下降到51%左右,之后一直呈增长趋势,2016和2017年上座率更是直接达到了85%。相应的,观剧人数也从2014年的238.7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470.6万人,四年间观剧人数增加了231.9万人,增幅达97%。
在刚过去不久的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上,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选送的话剧《柳青》从参评的38台剧目中脱颖而出,获得文华大奖。文华奖是专业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汇聚了近年来全国艺术工作者艺术创作的最新成果。获奖作品主题无一不是意蕴丰厚、艺术表演精湛、舞台呈现精彩的文艺作品。
话剧场次的丰富与话剧奖的设置,能否印证“话剧”这一小范围内“自嗨”的剧种正在和电影一样,走向市场,走向大众?
相对于电影来说,话剧的票价并不便宜。2015年话剧平均票价高达400元,2016年平均票价为300元,2017年为350元。尽管票价略有下降,但在可支配收入并不理想的城市,话剧票价显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因此,固定的小范围群体成为话剧的主要观众。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和大麦网发布的《2017中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18-34岁的话剧观众占比达到70%,而仅女性观众就占比64%,票房贡献度几乎是男性的两倍。而在受教育程度方面,话剧受到高学历青年群体的青睐,剧场观众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高达93%。

陕西人艺版《白鹿原》为观众带来了酣畅淋漓的高水准演出
除此之外,不同于演唱会等大型演出形式,话剧类演出大多只能吸引到本地人观看。有观众在采访中说道,“话剧毕竟不像电影,一部电影同时有很多家影院都放,可以挑一个交通方便的地点去看,话剧演出基本上一个城市就在某个剧院,没有办法选。尤其是有些小众的口碑之作,并不会在全国大范围巡演。”
即便话剧在走向大众的过程中,会产生上文中的困惑,但近几年来,依然不断有优秀的话剧从剧场走上大银幕,于是,话剧的仪式感逐渐向电影的生活化渗透。这种IP的转移也为话剧团体带来了不小的收益与不错的口碑。据《2017中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国内演出市场中,剧场演出票房收入为77亿,而同年的电影票房收入则超过500亿。以开心麻花为例,《驴得水》《羞羞的铁拳》《西虹市首富》等口碑票房俱佳的喜剧电影都由话剧IP改编而来。
但将资本引入话剧并非只有正面效应,资本掌握话语权,往往使得票房与收益成为话剧成功与否的唯一衡量标准,主创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创作,使得有市场风险的艺术类话剧大幅减少。
2019年,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表演系毕业16年的沈腾成为“百亿先生(主演电影累计票房超百亿)”,这位话剧演员已经完成了向电影市场的华丽转身。然而他是否标志着话剧正从小众狂欢转向大众繁荣,尚未可知。
陕味话剧能否为陕西故事代言?
以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为代表的几代“文艺陕军”,曾经带领着陕西文学走在了中国当代文学前列,并且为陕西的艺术剧种带来了丰富的文学素材。现实主义是陕西文学的基本特点,也始终指引着陕西的文艺创作道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陕西经验”。继影视改编之后,话剧亦成为改编陕西文学的“热土”。
陕西省艺术研究院创作中心的周昊曾在《陕西话剧舞台的发展与走向》中提到,“三秦大地,孕育着独有的神韵,足以支撑‘陕派’话剧的形成”。虽然与曾在影视史上掀起“壮阔波澜”的“影视陕军”相比,“陕派话剧”的理念尚不够清晰。但近几年来,从《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到《柳青》,很多陕味话剧都登上了全国话剧舞台,赢得了诸多文艺大奖,并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这让更多的人在感受到话剧魅力的同时,更增添了对陕西文化的了解。

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推荐、西安话剧院原创排演的话剧《柳青》荣膺“第十六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
无用心 不创作?
“我要感谢你们,是你们把《白鹿原》演活了。”著名作家陈忠实曾经这样评价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而当年,面对改编巨著《白鹿原》的重任,剧作家孟冰甚至由于太过用心而动了真气,在自己48岁生日那天完稿后便进了ICU。“那年我本想利用十一假期把《白鹿原》的改编一气呵成。整整一周的时间,我清楚记得自己是渐入佳境的状态,情绪是慢慢被调动起来的。一周的时间几乎不吃不喝,即便躺下后也是毫无困意。写完一放松下来,心脏马上不行了,当天就进了ICU重症监护室。”
而孟冰对待话剧版《平凡的世界》剧本亦是如此,“戏剧压根就不能离开文学,我们喊出要回归文学,就已经说明很多年我们走得太远了,需要浪子回头。”
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孟冰用几近严谨苛刻的方式对原著进行改编创造,随剧组一起去延安采风,并先后六度易稿,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小说中主要人物和情节线索。
孟冰用“小心谨慎、如履薄冰”来形容自己的改编:“我们专门去西安拜访陈忠实老先生,他亲自带我们去塬上转,而我最感兴趣的也是他当时究竟想写什么。他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想表现民族精神剥离的过程’,其实我当时不是很明白,也是慢慢在体会,一个人的精神如果需要剥离和蜕变,想要焕然一新,必定要有切肤之痛。”

无明星 不话剧?
陕西人艺方言版的《白鹿原》在全国演出200多场,其火爆程度,从每场谢幕时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可知一二,观众们高涨的热情和感动,无不有力证明着这部话剧持久的艺术魅力。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白鹿原》话剧剧组,没有一个普通观众能叫得出名字的知名演员,这与其在表演上给观众的强烈震撼形成反差。“舞台上根本没有演员,舞台上就是一群白鹿原的生民,看完根本记不住演员,因为他们就是小说中的那个人物!”这是《白鹿原》创作团队最喜欢的一条观众留言。
对此,导演胡宗琪认为,明星不仅成本高昂,而且由于档期局限会给剧院建设和日后演出带来无法预估的困境与伤害。因此,他坚持全部选用陕西人民艺术剧院自己的演员打造《白鹿原》。他在采访中说道,“小说《白鹿原》和话剧《白鹿原》的文本所具备的文学品质,无疑已经为舞台呈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认为,只要是合格、称职的演员,有创作实践的经历和成功塑造角色的经验,有表演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就可以在导演的指导下,完成角色的塑造。从这个前提出发,演员所扮演的角色出了偏差、有了问题,其责任不在演员,而在导演。正如我一直对自己提的要求:没有不称职的演员,只有不称职的导演。”

话剧《平凡的世界》
无方言 不陕西?
《平凡的世界》与《白鹿原》,是土生土长的“陕西故事”,“土土的方言”是观众感受地方陕西文化的窗口。在陕西人艺版《白鹿原》的演员中,很多都非陕籍,但他们仍然用地道的陕西话为那片土地代言。剧中大段的台词也让饰演白嘉轩的蒋瑞征在演了近200场时,仍旧在上台前低头默戏,虽然在操着一口挂味儿的陕西话,但其实他却是地道的北京人。
而对于原本就是地道西安人的鹿子霖饰演者管越来说,他依然需要通过看资料片甚至回忆自己爷爷的状态来捕捉人物的感觉,在他看来:“鹿子霖不是简单的反派,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理想就是当族长、抱孙子,当这些都没有实现后,他开始走向扭曲的极端,宗族文化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过作为西安人,角色骨子里的那股傲和秦人思维,我都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以忠实纪念忠实”——最高的敬意就是无限接近《白鹿原》中那个原汁原味的陕西。
结语
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原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所长田本相说,“话剧是最具时代性的艺术,是最能同普通大众直接沟通的艺术,话剧曾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被引入,起到了启迪民智、匡时济世的重要作用。在民族觉醒的历史条件下,话剧作了最充分的民族表达,走了一条话剧同民族的现实和民族的艺术相结合的道路。”而当前,我们需要话剧来反映时代精神、反映人民呼声。由此来看,用话剧讲好陕西故事,亦是在用文艺来记录和反思这个时代,这是话剧的使命,也是历史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