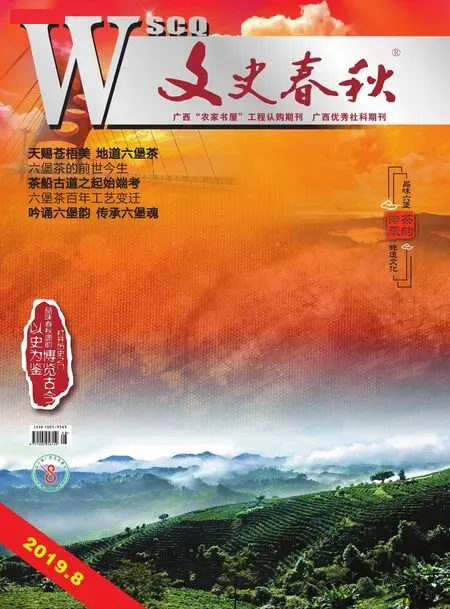六堡茶百年工艺变迁
● 彭三口

回首百年前,正是六堡茶的黄金岁月,据当年的老茶人回忆,清末民初,由于海外需求量逐年递增,六堡茶区里漫山遍野都是茶园,人们忙着采茶、制茶、炊蒸压篓、装船运输,每年数10万斤,最高峰时近100万斤(注:此数据乃六堡一区而言,真正的六堡茶连同当时贺县即今贺州市八步区水口一带,应该超过100万斤了)的六堡茶沿着六堡河、东安江、贺江、西江所构成的“茶船古道”远销南洋,以价廉物美而享誉海内外。由六堡茶而带动的如竹编、木柴、制炭、运输、杂货贸易等也出现了繁荣景象。
这100多年来,六堡茶几经沧桑,几历战火,几番盛衰,茶树被砍、被弃,茶园复垦、再荒芜,再种植、再闲置,几多曲折与磨难,历经时局动荡及战火洗礼,历经土改茶山再分配,历经复兴公社茶场,历经重振公社茶园的大生产,以及生产队建立初制厂、公社发展精制厂等等,可谓坎坷。在1937年出版《广西特产物品志略》里面有记载:“在苍梧之最大出品,且为特产者,首推六堡茶,就其六堡一区而言(五堡,四堡)俱有出茶,但不及六堡之多,每年出口者,产额在60万斤以上,在民国十五年至十六年间(1926—1927年),每担估价30元左右。”
20世纪初,正值产销巅峰状态的六堡茶到底是怎么样的?在名茶众多的中国,为何能闯出这么一片广阔的侨销市场?百年前六堡茶工艺和品质是怎样的?
百多年来,六堡茶的产区和销区(岭南及马来西亚锡矿区)如同沧海桑田,变化巨大,六堡茶多次盛衰起落,战火与自然,所幸,经过笔者在海内外多方寻找,找到了一些文献资料及六堡茶老茶实物,能比较客观地推断出当年的六堡茶种植、生产以及品质状况。
百年前六堡茶归类于什么茶
中国六大茶类分类的奠基人陈椽教授在1979年《茶业通报》的一篇茶叶分类奠基性文章《茶叶分类的理论与实际》,提出六大茶类的分类及其依据,也是中国现在六大茶类分类法的基础。
在没有六大茶类之前,人们把六堡茶归类为什么茶呢?现代渥堆工艺还没出现,当时是古法工艺,是现在很多人所说的绿茶吗?不是。
1937年由当时中华民国行政院新闻局印行的《茶叶产销》一书所绘民国时期茶区茶市分布图,图中画圈处为梧州,圈内灰影部分为当时梧州及苍梧周边的六堡茶产区,其地图中图例示意为“其他茶”。可见当时梧州及周边和以北的贺州、桂林周边已经是有别于绿茶的“其他茶”的大产区了。正因为当时六堡茶的工艺有别于绿茶,使得人们已经很明确地把六堡茶区别于绿茶、红茶、乌龙茶等等,以其特殊的工艺和品质,专门列入“其他茶”一类。
究其原因,按笔者研究,在当时六堡茶古法工艺的文献零散记载中,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一个词——“发酵”。
那么,到底百年前六堡茶的工艺是如何的?当年的六堡茶又具有哪种特殊品质呢?
“远年六堡顶好”的最早记载
1951年4月,中国茶叶公司曾派苏海文同志到苍梧县调查六堡茶种植生产情况,他写成一篇文章,题目是《介绍广西苍梧县六堡茶产销情况》,发表刊登在当年7月的《中国茶讯》上,详细地介绍了当时六堡茶的产制运销情况。这篇文章里面提到“陈茶(远年六堡顶好)有解暑祛湿的功用”,这里提到的“远年六堡顶好”估计是当时茶农间流行的一句茶谚。这是笔者所查阅到正规书籍里面关于六堡茶以陈为佳的最早记载。

1937年由当时行政院新闻局印行的《茶叶产销》一书所绘民国时期茶区茶市分布图

当年的茶票已经明确六堡茶有“藏之远年”以陈为佳的做法
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1951年4月进六堡茶区考察所写,而在1937年抗战开始一直战火不断,六堡茶的生产运销中断,要在市场上对“远年”(不是一般的陈,是时间久远)六堡茶品质形成共识,在茶区及消费者中形成“以陈为佳”“远年顶好”的观念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沉淀。由此推测六堡茶“以陈为佳”“远年顶好”这样的观念,应该起码在1937年之前六堡茶产销畅旺的时期,由广大民众在六堡茶的大量消费、存放过程中总结而逐步形成的。
笔者在慎昌老茶庄的一张六堡茶茶票中,也发现有“将其藏之远年令其气味纯和水碗红厚”的描述,可见当年六堡茶是推崇以陈为佳,有远年品质更佳的这个市场共识,可作六堡茶很早就推崇陈茶、以陈为佳的佐证。
百年前六堡茶享誉南洋
18世纪末,大英帝国的殖民发展目标向东方发展,英国人开始入侵马来亚半岛,至19世纪中期,开始了马来亚的开发。
马来亚的吸引力在于其锡矿和金矿,只是英国农场主一开始更热衷于发展热带作物,1877年更从巴西引入了橡胶,后来棕榈油也成为热门出口品。但随着大规模开发的开始,英国人很快便觉察到马来人不是可靠的劳力来源。从印度引进劳动力也解决不了问题。

马来西亚怡保的一锡矿老照片。当年,华人矿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在烈日下劳作,图中搭起的布棚就是喝口六堡茶稍作歇息的地方。

茶船古道的另一端——马来西亚的河涌当年也是运输物资的重要渠道,而船运的“耗时长久”也恰好给予了六堡茶后发酵的时间。
当时,正值中国处于清代鸦片战争前后,社会动荡,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大量沿海民众为了生计不得不背井离乡,流离海外。于是,马来亚的矿山、工厂和港口、种植园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南方华人,出现了史称“落南洋”的大规模岭南民众迁徙南洋的潮流。早期是在南洋打拼小有成就后,回老家拉上更多的同乡(壮大同乡势力)一起到南洋“发财”,也有不少“金山伯”回家乡置地起洋楼娶老婆的致富效应带动了“南洋淘金”的热潮。后来更出现了称之为“卖猪仔”的契约劳工。华人开始大量地涌入马来半岛。资料显示,截至1891年,在马来亚半岛从事锡矿生产的华人在10万人以上,此后更是几何量级的增加。
最早期,勤劳的华人披荆斩棘、出生入死在马来亚拓荒开垦,除要面对着毒虫猛兽及蚊虫蛇鼠等等的困扰,还要面对着热带病、疟疾、蚊症等等的肆虐,以及落后的卫生医疗状况,这使得华人锡矿工们几乎每天都要面对着死亡的威胁。当时的华人劳工死亡率很高。
逐步地,华人们发现有饮茶习惯的广府华人往往得以幸存,崇信中医、日常喝茶、以茶作为祛湿、调理肠胃饮料的华人身体也往往更为健康,更能适应当地湿热的气候及恶劣的工作环境,于是人们纷纷效仿,而六堡茶能消暑祛湿、辟瘴防瘟的故事也被传为美谈,被更多的矿工和普通广府侨胞所接受,“有六堡茶喝”甚至成为矿场招徕矿工的一项福利。由此,广府华侨把饮用六堡茶解渴、祛湿消暑、调理肠胃的传统带到了异国他乡,岭南喝茶(包括煮饮凉茶)也作为一种传统民俗文化在南洋得到延续。
基于这种的时代背景,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六堡茶大量出口到南洋,达到了其产销的历史巅峰期。于是,六堡茶的种植生产蓬勃发展,甚至在广西苍梧之外的地方也开始产六堡茶,如广东的四会、罗定等地也开始生产一种称作“六堡茶”的茶来供应南洋市场。(见1941年钱承绪所著《华茶的对外的贸易》)
二十世纪初六堡茶是怎样做的
现存对六堡茶工艺描述比较详细的,多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书籍期刊所刊,不过,从中已经可以看出二十世纪初六堡茶的传统工艺特征。
1934年《广西大学周刊》的一篇文章有一段对当时六堡茶加工工艺的记载:“采摘标准一芽三、四、五叶”,其初制方法是:“其土人制茶之法,将由树上采之茶叶,放入沸腾之水中,使其叶软而柔(约5分钟)即得,而置于箩中,以脚用力践踏,至茶叶卷缩为度,然后以火焙干之,干燥后以蒸汽蒸至柔后,乃置于箩中,贩售于外也。”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六堡茶工艺的显著特点:茶叶粗放的采摘——“一芽三四五叶”;杀青工序里“放于沸腾的水中”,这是后来较少使用的“撩水”杀青工艺了;“干燥后以蒸汽蒸至柔”,这里已经出现蒸汽蒸软压篓等细节描写。
出生于1929年的刘福生老人当年是军管会在梧州的干部,曾与专门从广州派来的茶业干事一起负责梧州茶厂的选址、筹建及管理。据刘福生老人回忆,梧州茶厂创建之初所使用的制茶工艺是原来私营茶庄老板黄础雄所传授的,黄础雄一直作为技术指导。
根据老人的描述,当年的生产工艺如下:也是粗采的“一芽三四五叶”,甚至其粗老程度让当时还是二十刚出头小伙子的刘福生疑虑:这么粗老的茶,能卖吗?会有人要吗?听到是销往香港及南洋,更让刘福生不敢相信。
老人回忆,首先准备一口可容纳两个人进去的大木桶状的木甑,木甑下以铁锅烧开水起蒸汽。粗老的茶叶采摘回来后,放入甑内,两人在甑内踩压。这一步相当于以蒸汽杀青,以脚踩进行揉捻。茶叶不断加入升高,人也不断踩压,最后蒸汽透顶,师傅控制好加料、踩压及蒸汽透顶时间,再把这些茶叶倒入大篓内,分3次或4次两人上篓踩实并存入茶窖之中。刘福生老人描述的是笔者所知最为原始的一种六堡茶传统工艺,似乎比起1934年《广西大学周刊》文章所描述的工艺还古老些,并更易于作为生产工艺加以规范。
一本稍后期的六堡茶《制茶手册》上注明:“杀青时应注意事项:注意不能用水潦杀青,因为鲜叶通过水潦内含有效化学成分容易溶解于水,将大大降低茶叶质量。”水潦杀青即“撩水”杀青。由此可见,当时已经注意到“水潦”“煮青”工艺的不足,开始避免使用“撩水”杀青和“蒸汽杀青”工艺了。
2003年笔者在六堡茶区采访的时候,老茶人陈振东回忆:“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茶,人人都做茶。”当时流传有这么个说法,说要分辨一个人是不是六堡人非常容易,只要看看他的脚,“脚黑”的一定是六堡人了。陈振东接着解释说,由于当时家家户户都做茶,以前的工艺做茶的时候,用锅杀青之后,要揉捻,那时多用脚踩搓揉,由于茶叶汁液的浸染,久而久之便人人“黑脚”了。这可以作为当时“脚踩”揉捻工艺的佐证。
蒸茶压篓发酵成为标准工艺
上面提到的1951年的这篇《介绍广西苍梧县六堡茶产销情况》里记载“据当地老茶工说:开始是因为方便运输,所以才经过炊制,后来就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一种制造方法”,该文的作者还感慨这种做法会“造成发酵过度的现象”使得品质降低。似乎他是站在绿茶的角度去看的。
确实,炊蒸压篓最早是为了方便运输,避免茶叶压碎并紧压提高装载量、降低运输成本。很快,在制茶的实践中,茶商们发现,经过如此炊蒸压装篓晾置的六堡茶,有一个发酵过程,更利于新茶陈化变得醇厚,于是,这种蒸茶压箩的工艺成为六堡茶的特有工艺固定了下来。
注意,这种炊蒸工艺并不是在茶农环节完成的,因此现在如去茶农家调查,纯粹茶农家庭一直流传下来,制茶都不需要这个炊蒸压篓的工序的。“炊蒸压篓”是在茶商收到茶之后,经过筛分、拣选(还未需要拼配)准备进仓以利于船运时候,才进行的炊蒸压篓晾置。
在传统的工艺中,第一次炊蒸压篓完成,就已完成了六堡茶离开产区的所有工序。当时的第二次炊蒸压篓,往往是在广州或香港的大茶商手中完成。因为,当时传统工艺六堡茶有个特点——产量少,也就导致了这家三五篓,那家三五篓,不同一批茶叶品质、香气滋味间存在差异。如果接到订单需要二三十篓以上的话,就需要将几批茶叶拼配混堆,以达到一定的产量。这时候,就需要第二次炊蒸压篓,也意味着再度发酵一次。
无可否认,当年出现在南洋华人杯中的六堡茶,哪怕是传统无冷水发酵的时期,也大多是经过了两次以上的发酵的,特别是尚未进入轮船时期的清代,由于船运的运输时间较长,茶叶在仓储、转口、运输等环节上耗时不少。经多次发酵,出现了“两蒸两晾”“多蒸多晾”的做法,有商人也看到这大大地改变了茶叶的口感和品质,于是便有人将这种传统工艺应用到生产中。事实上,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六堡当地仍然有人用这种“多蒸多晾”作为精制工艺来生产六堡茶。
在六堡当年“老字号”兴盛庄的一张茶票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清末民初(抗战前)六堡茶最为辉煌的时候,“加工蒸制”是作为一项经典加工方法印在茶票上的,以示工艺正统。
1958年前,六堡茶的精制工艺大多是用“炊蒸压箩晾置”来完成的。1958年后,才开始采用冷水发酵渥堆工艺(精制)后,运销到广州、香港等地,有按茶商要求包装“出口”,也有港商重新包装,扫上唛号,或分装成小包装,再销往南洋。

六堡老茶人车俊良演示用大蒸甑把茶蒸软杀青的工艺

六堡老茶人车俊良在按传统工艺把炊蒸好的茶叶装箩晾置
自然发酵是古法工艺的精髓
苏海文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有记述“蒸时间过久,茶叶吸收蒸气特多,水分增高,以致后发酵的时间延长;同时又因踩装不紧,在长期存放的过程中,空气内的水分继续侵入,也能使篓内的茶叶继续在发酵,因此造成发酵过度的现象。因此六堡茶,尤其远年六堡,于冲泡以后,虽有比较深浓之水色,但叶底褐黑……此即上述过程的结果。”
同样,这篇文章提到更详细的工艺:“揉捻:一般地都是在盘箕内用脚蹂踩的,因为采摘过于粗老,所以很难踩成紧细条索,大部分仍是粗松扁片及它结。”“在这一过程中,因为杀青工作不够彻底,同时又没有大晒簟做日晒工具,所以发酵现象,特别显著。”苏海文在他的文章里,多次提到这个“发酵”现象,包括“蒸茶压篓”时间久、水分足导致了“篓内的茶叶继续在发酵”,显然,苏海文是以绿茶的角度去看待这种“发酵”的做法。今天我们反过来看,导致茶水色红深浓,这其实是当时六堡茶的品质特点,也类似于以独有工艺形成“红浓”特色的雏形。而且,当地茶农茶工已经明确提出“水色味道”而不是绿茶的品质标准去要求六堡茶。
文章还讲述类似于出现前发酵的情况:“茶园距茶农的家,远的有20华里的路程,鲜叶自枝上采摘下筐,以至携返村庄为止,起码经过3小时以上的时间,同时鲜叶携回以后,茶农们并没有马上去做杀青工作,一般的习惯,都是任意堆积(很少摊开的)在地上,其堆积时间有长达一天一夜的。”“在天气炎热的时候,红变现象特别严重,这种拖延制造时间的结果,损害茶叶的品质甚钜。”也明确地提到六堡茶工艺中后发酵的情形:“在揉捻及干燥过程中,其化学变化,特别显著,即在发酵。”这些记载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另外,从现存的超过百年的老茶树我们得知,在苍梧六堡周边的五堡、四堡和当时贺县大冷水、峡尾、古仑等地,都曾有六堡茶的种植加工。
百年老茶千里茶缘
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李先生是一位手中有“百年老六堡”“百年铁罗汉”等等近一个世纪老茶的传奇老人,现年73岁。李先生回忆,这些老茶是他父亲留下的。李先生父亲祖籍是南海(一说番禺)人,早年来往于中国及马来亚经商,是个很成功的商人。据李先生回忆,他有记忆时,他父亲已经在安顺拥有了3个商铺,一间自己住,租楼下给别人做咖啡茶铺,一间做客栈,另一间是做鞋店。
除了这3家店铺,当时李先生的父亲在隔壁药材铺旁与人合作还开了一家杂货铺,其中就有做茶的销售,包括有六堡茶、六安、六安骨、普洱(宋聘号)、铁罗汉等等(是后来清点才确知)。杂货铺的经营一直不见起色,合作了很多年,据说经营状况尚可,但“一直没钱分”,于是李先生的父亲便跟合伙人提出散伙,结束了这家杂货铺的经营,清点均分了店里货物,其中就包括这些茶的存货。这些东西搬回来也没怎么动,茶叶也就丢在一旁。
这些老茶的再发现,也是有其偶然性,李先生回忆,约2000年前后,随着年纪增大,他想喝点茶,偶然翻东西,找到了这些尘封近百年的茶叶,喝了一点点。2005年,并不很了解茶行情的李先生把当年留下的一点点茶拿到当时的一个茶博会上,马上引起了轰动,很快其手中的普洱被人高价买走。李先生这才发现先父给他留下的这些茶具有这么高的价值。剩下了的那些“百年六堡茶”和“铁罗汉”,李先生很珍爱地保存着。知道笔者过来,李先生专门把珍藏的百年老茶拿出来,慷慨地和大家一起分享。

本文作者与百年老茶的主人吉隆坡李先生(右)探讨,如何从存世的老茶中研究当年六堡茶的工艺。
历经百年岁月的积淀,这个老六堡已经是陈香内敛,入口即化,色浓香沉,茶气于瞬间冲盈,给人以满满的厚重沧桑感,余韵在口,也是一般的沉郁悠远,让人感慨。一道道下来,第二道略有点点泛酸,而后又重回正道。第五道之后,便隐隐约约地呈现出原种六堡茶特有的本质韵味。之后,更是一道道的变化,层次明显,如奇妙音乐之高低起落,似远山之重峦叠嶂,感受极为精彩。
从李先生这百年老茶的外观看,也是当年粗采的做法,有揉捻不卷的粗叶,叶片扁,炊蒸压篓工艺,泡茶后的叶底乌黑柔润,仍有活性。这些珍贵的老茶为研究六堡茶百年古法工艺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临别之时,李先生还专门从罐中取出一点百年六堡茶,送给笔者,让笔者带回六堡茶故乡——梧州作为纪念,也算是百年老茶回归故土。感恩,感恩这千里茶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