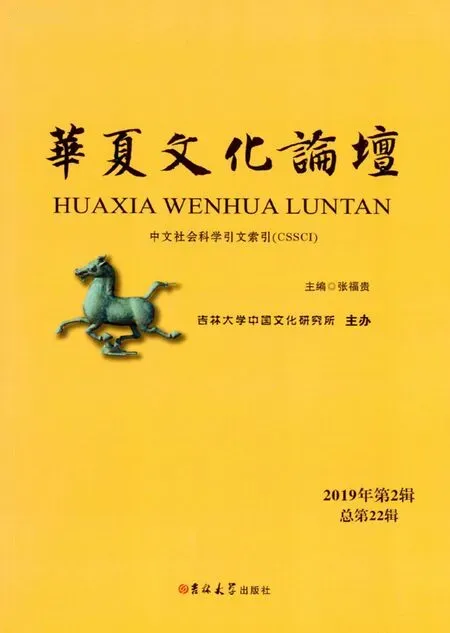伤痕文艺:“历史的终结”版的中国叙述
李 飞 张慧瑜
【内容提要】本研究从近期以来的大众文化中几个热播/热映的中国叙述文本《软埋》《风筝》《芳华》《无问西东》切入,试图对其历史脉络梳理。研究发现从《软埋》到电影《无问西东》其精神内核上可追溯到上世纪的伤痕文学。本文试图勾勒“伤痕文学”这样“历史的终结版”的中国叙述的脉络,以及为何在今天有回归的土壤,并在此基础上指出重估八十年代叙述,重建新时代中国叙述的紧迫性。
在当下,大众媒体中的中国故事与故事中的中国越来越受到关注。谁在讲述以及如何讲述受到关注的同时,故事讲述的年代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由于在不同阶段选择性拿来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性的资源,加上本国的复杂国情,造成了同一时期不同时段的历史思想意识缠绕。如何建立中国崛起时代的中国叙述,是需要建立在足够的文化自觉基础上,以中国为主体,立足中国实践,整合中西方文明融会贯通,形成中国叙述。在全球化格局中,这种中国叙述本身意味着对中国当下在世界中位置的认知与价值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安置中国过去与未来。这种中国叙述的困难,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中国”叙述的难题源自中国历史与现实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叙述”行为本身,不仅意味着如何“描述”当下中国的现实状况,也包含着如何“引导”社会发展方向,如何应对现实中存在的社会问题。
“中国叙述”已经溢出了自然主义对中国当下现实的描述的范畴,需要在历史的坐标中处理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市场商业环境下,着眼于从个体主义出发的文艺作品与文艺生产模式试图对此作出回应。近期,从方方的小说《软埋》到冯小刚执导的《芳华》,再到热播的电视剧《风筝》,乃至于更近的李芳芳执导的《无问西东》均属于这一模式下的产物。尽管这些作品分属小说/电影/电视剧等不同的文艺种类,但这些文艺作品共性在于,由于认知与格局的偏差,无法对新时代宏大的重大议题作出真正的回应,无法承担溢出文艺本体之外的功能。究其原因,这些作品是“历史的终结”版的中国叙述,是”小时代”关门自我抚摸伤口的故事。
然而,当代中国需要面临的历史挑战在于,新时代的中国面临的是华夏文明几千年之大变之际,面临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能否开创出有别于欧美霸权的新的世界文明秩序与发展道路的问题。这种宏大时代的挑战,无法用“历史的终结”之后小时代之中的小悲欢的方式来应对。更重要的是,这种“历史的总结”版的中国叙述同正处于历史巨变期的中国的现实是矛盾的,社会意识层面再次显示出其延宕的特点,跟不上社会发展步伐。那么这种“历史的终结版”的中国叙述从何而来?为何在今天有存在的土壤?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伤痕书写与消失的大历史
近期,方方的《软埋》,冯小刚执导、严歌苓编剧的电影《芳华》,电视连续剧《风筝》,李芳芳执导的《无问西东》构成了新一轮的“伤痕”书写。这一轮的“伤痕”书写,从本质上看,不过是八十年代的老人们与后来受其影响的新人在向八十年代的“伤痕文艺”致敬,是改革开放以来文艺政策中国家退出的后果。这根源在于中国处于变革时期,尽管不缺原则性指导,但现实政策落实困难重重。早在1979年理论务虚会议上,邓小平就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图以政治原则的方式结束思想混乱局面。正如后来学者观察到的:
曾经参与中苏论战的邓小平深知政治原则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政治正当性的源泉。市场和计划作为手段,完全可以采用实用主义的立场,但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于邓小平来说,则是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
正是出于对政治原则与社会主义的坚持,也在同一年邓小平曾强调文艺重心是“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然而,这种政治原则在实践中之中很容易变成教条的实践:政治原则本身是刚性的,但是新时期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之下,原则可能被现实的实践给架空。事实上,邓小平提出的文艺重心与文艺工作思想路线一开始就遭到了伤痕文学的挑战。新时期以卢新华的《伤痕》、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等为代表的伤痕作品的出现,使得“伤痕文学”作为一种文艺潮流出现,然而这并非是“我们的”当代史的文艺书写:有论者根据卢新华接受采访之际指出,“伤痕文学”的命名并非是中国原生的,而是美联社的文章经《参考消息》转载后被中国接受这一细节切入,试图阐释这套文学话语背后的帝国文化政治的全图,其中蕴含着对中国此前文艺与全球左翼文化颠覆的意图在其中。如果凭借今天的后见之明来看,这种颠覆此前情感结构的文艺实践确实发生了。除了文学外,电影领域诸如《苦恼人的笑》《生活的颤音》《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等伤痕电影,更是一改之前围绕大时代开展的革命建设叙事,而转到个人叙事上,以苦情戏的方式来展现知识分子/艺术家/老干部/知青或蒙受不白之冤,或挺身抗暴,尽展“柔软的主体性”的一面,以及大时代本身的荒谬性。文本中,代表善良/美好的主人公在歇斯底里的文革大时代碾压过来,只能成为被批判/被迫害的客体。在这种将个体美好东西撕毁给人看的悲情之中,以个体的悲剧展示时代的阴暗面,完成了知识分子对文革“浩劫”的建构,解构掉文革的复杂性与多面,并通过媒体将之变成大众的情感结构。在催泪与反思之中,文艺本身不仅没有以描写“社会主义新人”的方式来书写“当代史”,相反以个人伤痕/被耽误的年华/不堪回首的岁月等方式,向过去的时代索要历史的债务,制造现实与历史的撕裂。曾经工农兵写作班成员,在新时期纷纷以“伤痕文学”的形式再次走上了文学/文艺道路,以至于其形成了一种单一文艺形态霸权的局面,正如刘复生分析指出的,“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只有一个文学思潮,那就是‘伤痕文学’思潮”。他的这个广义上的“伤痕文学”包括了文革后期的知青民间创作一直到伤痕小说/反思文学/现代派小说/改革文学等文学样式,经历了最初将文革与文革过程分开,恢复“继续革命”到后来的“走向对一切革命价值与社会理想的否定和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全面拥抱”。在这种广义上的伤痕文学中,沿着狭义伤痕文学步步推进的反思文学/现代派小说/改革文学,完成了这种现代性的转型:狭义伤痕文学以反思文革之名试图挣脱政治上工具论之际,中国的文艺被认为是对苏联六十年代“解冻”的重演,实现向另外一种“告别大历史”,完成“历史终结”的转型,呈现“对个人的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和作家对于`主体意识' 的寻找的自觉”的特点。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文艺思潮事实上处理的是当时现代性转型的时代议题。这种延续至今的文艺创作的思想/文化本身只是一种他者思想内化的通俗体现而已。由于“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革命是中国近现代打开历史的方式,因此“历史的终结”只能在“告别革命”,以个人/人道主义/人性等完成对革命的质疑与审判,方才能够让转译过来的发达国家/地区的现代性着地。在这种告别革命之后,诉诸情绪的伤痕文学,在积极将同时代的思想讨论成果与文化讨论成果融入到创作理念中,其未来呈现出两方向发展的态势:一个方向则是在新时期文学同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所谓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文艺样态;另一个方向是文学开始脱离宏观的社会与政治,朝着越来越个人化书写与纯文学书写的方向发展,形成所谓“现代派小说”。这两个方向均将思想界讨论中舶来的人性论与人道主义变成新的书写价值标准,在政治无意识中将“历史的终结”以去政治化方式内化。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以“告别革命”的方式完成汪晖所言的亚洲版的“历史的终结”。历史的复杂性在逐步发展过程变得粗鄙起来,变成了归来的“右派”的故事:冷战背景下与尊严政治与人民是历史主体的大历史书写变成了文革十年之中上山下乡的知青,受迫害的开明干部,秉承良知的知识分子等新时期文化精英阶层的个人伤痕与情感的宣泄。这种宣泄,在邓小平看来是“哭哭啼啼,没有出息”——这位第二代党与国家的领导核心在观看了由伤痕文学代表作品《苦恋》改编而来的《太阳和人》之后,更是询问“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然而,这种“哭哭啼啼”的苦情戏的叙事,本身构成了伤痕之后“反思文学”与“改革小说”中悲情与行动合法性的来源:归来的“右派”与知青成为反思的主体(反思文学),放眼世界,将阿伦特极权主义的帽子扣在曾经的历史上,苏东剧变之中哈维尔之流对前共产党政权“后极权主义”的判断经由曾任体制内学术高官的李慎之阐释与扩散成了套在中国头上的魔咒,曾经大历史在这种当下观念的裁剪之下成了“浩劫”的记忆。同时,重回领导岗位的“右派”(改革文学)急于同世界接轨,将耽误的岁月捡回来,诸多努力不被理解,改革受诸多掣肘影响,构成了改革之中的悲情与催泪点——在《乔厂长上任记》《血,总是热的》等中不无表现了这一点。它们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定位问题的时候,客观上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另外一种重新政治化的功能。作为一种中国的回应,邓小平在《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中提出了在组织上全面整党与思想战线上“清除精神污染”。然而,针对人道主义/异化/自由主义文艺理念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当时的总书记看来有扩大化态势,持续了二十八天,不了了之。正是这个过程中,文艺完成“历史的终结”,将中国革命的大历史放逐,而这也是一个宏大叙事不断衰落,日益成为“问题”的过程: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纯文学与告别革命等“历史的终结”的意识形态观念无法撑起中国宏大的革命历史。大历史,被日益小资化的表达给排挤了。这种状况,使得八十年代国家不得不以主旋律的形式来维系主流的文艺生产。但是,随着老一辈在生理上的消亡,新一代观众审美情感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大历史与主旋律的书写越来越陷入困境之中。
历史虚无主义:“新伤痕”与历史蒙太奇
近些年来,无论是《软埋》还是《芳华》《风筝》《无问西东》这样的文艺作品,它们所呈现的“新伤痕”书写从精神内核上看,其中关于中国的叙述框架基本上并未超越伤痕文学/伤痕电影,充满了历史虚无主义。这种“新伤痕”书写的独特之处在于伤痕言说的年代与伤痕本身。“新伤痕”书写是在中国崛起/复兴的时代言说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伤痕,是一幅伤痕化的中国叙述的画卷。“新伤痕”写作的质疑者面对这种中国叙事之际,多数试图在失去历史坐标的今天重新回归历史语境。然而,问题在于,在各种戏说与伪历史充斥的当下,这种回击一般都显得乏力。这种乏力在于这些“新伤痕”书写构成的中国叙述,成功利用了新时期以来因为不作为留下的“旧伤痕”叙事长期积累的成规。“旧伤痕” 对于年轻一代而言,可能并不熟悉;但对于方方/严歌苓/柳云龙等人而言,文革以及对文革的清算本身是他们生命经历的一部分。在市场化/全球化过程中,曾经落魄的精英的后代与经历了市场化沉浮的新精英将市场经济中被放大的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作为他们裁剪历史精神与原则的时候,个人或者他们口中的“人性”被作为一切价值标准,以日拱一卒的方式完成叙事翻转。所谓“浩劫的年代”的叙述更是向前扩展到了新中国前三十年:在《软埋》之中是土改中对地主家庭的暴力,在《风筝》之中变成了新中国建立之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在《无问西东》之中更是变成了所谓的“文革前夕”的1962年;向后则延伸到了后三十年--在《芳华》之中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对越战争也成了“新伤痕”。由此可见,“新伤痕”的中国叙述中的“伤痕”已经不再停留在文革,而是扩展到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清算。在这种伤痕化的中国叙事之中,中国崛起之路不再是一个高歌猛进的过程,而是一个历史债务缠绕/内部矛盾淤积而的历程。问题在于,这种债务叙事,事实上是精英基于利己主义立场编织的。他们采用历史蒙太奇编织起一个个精致的叙事:他们将个人从大时代裁剪出来,围绕着个人而不是时代重新组织材料,展开叙事。八十年代诸如《伤痕》《太阳与人》等一度的引起争议的伤痕文学作品,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文学商业化/市场化浪潮中变成一种文学的叙事“成规”/“惯例”:《白鹿原》、《一个地主的死》、《活着》、《丰乳肥臀》等事实上是将颠倒的世界颠倒过来的历史再以“伤痕”“纯文学”之名再颠倒回去,而这遵循的依然是八十年代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逻辑--“把所有人都当人来写”。一旦“所有人”都获得了“人”之名,实际上也在冲击着此前有着明显价值判断与优劣的秩序。尽管这么做,将此前相对简单叙事所遮蔽的复杂性给解放了出来,但是这种解放同样意味着某种价值上的冲击与新价值体系的建立:“人”的叙事、人性叙事等实现的是“后八十年代”将八十年代以来价值的逆转给固定化,变成新的教条信仰。如果说五十到七十年代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新人”更多偏向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面向,那么在“后八十年代”所谓人的叙事之中则可能可能是钢铁是如何锈掉的,如何冒充钢铁等面向。这种复杂性的叙事之中恰恰将原来相对简单叙事中强烈的价值导向给淡化了,高度政治化的叙事被去政治化叙事取代。
这种“把所有人都当人来写”以一种表面上的“平等”,裁剪过来的“人”并非历史的主体,而是历史主体的“对立面”。由于价值判断的颠倒,历史蒙太奇成为他们在文艺领域将军的手法。在《软埋》之中,被当成人写的恰恰是开明地主家庭在土改中的劫难幸存者。小说中,对主家庭心灵创伤造成的梦魇的土改“创伤”,以十八层地狱的形式表达出来,而这挪用的是民间之中对极致苦难的想象,同时将从前贫农这样受苦的主体置换成为了作为良民的地主。这种对地主家庭在土改过程中极致的苦难的描述,抽离了革命建设的逻辑,采用的不过是文学工业的叙事成规:价值错位的文化精英以“揭示历史真相”之名,采取历史蒙太奇的方式将从前的受苦者从贫民替换成了地主。故事中的痛苦,源自方方对她所谓命苦的大姨在土改之中遭遇,而在《软埋》之中又因为方方个人的态度而再次被艺术加工,夸大成灭门--这种矛盾激烈程度的艺术表达。《软埋》成功地“软埋”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改”带来的人民的翻身做主,软埋掉了人民主体与那段历史。全然忽视了,如果没有这段历史,中印两个差不多同时建国的第三世界国家,印度在发展条件全面优于中国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被中国甩在后面。电影《芳华》中,编剧严歌苓曾经早恋的情感创伤带来的阴暗心理,被包裹在冯小刚温情脉脉的、五五后们的“小时代”叙事之中。同时,新时期的中越战争中解放军作战方式被历史蒙太奇地衔接上了从前日军的作战方式。战争,成为了虽在同一战壕、但由于爹不同命运殊途的新时期“新伤痕”形成的动力。柳云龙执导/主演的电视剧《风筝》则更是以谍战剧/职场剧/国共剧等多种影视文本杂交的方式完成了对曾经历史的解构,在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又颠倒回去的过程中,国共的角色在以信念与人性之名的叙事之中,出现了“我共败了”的大崩盘:情谊化/人性化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群像本身颠覆的是革命文艺之中魔窟魔鬼形象;子虚乌有的1960年代国民党女特务白毛女式叙事则完全将新旧社会两重天颠倒;“无情无义”想象替换“无私”的“我共”形象带来的是新的一轮的历史虚无主义。这恰恰是在文艺领域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方式,将曾经红色经典以及其勾连的中国革命的情感结构进一步解构。号称清华校庆电影的《无问西东》则更是采用历史蒙太奇的方式,将各种错乱时空之中的事情混合剪辑在一起。为了达到对毛时代的控诉,更是将沈阳某医学院扒坟的事件挪到了清华园,硬生生让清华来背负这笔“债务”。清华的校庆本身的历史叙述构成一种对历史叙述的结构,其中充满了历史的荒谬与虚假,以校史之名将后现代的碎片拼贴起来替换真正的历史与脊梁。人民大学孙柏副教授曾在朋友圈子中犀利指出《无问西东》的问题所在:
《无问西东》说到底不是电影技术表达的问题、不是讲故事的技巧问题,而是讲述历史的问题、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叙事(historia)的问题。所以不论是黑是赞,只就影片自身的故事层面上争它的好赖,就都说不到点儿上。看到有盛赞章子怡那段的文章,张嘴就“文革前夕”。拜托好好学点儿历史不行吗?网上百科一下下也行啊?1962年恰恰是经济大调整的一年,是艺术创作环境有所松动的一年,到1963年两个批示之后,意识形态才再度紧张起来,到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铺开,现代戏进京汇演,才能算“文革前夕”好不好?说1962年是文革前夕,就跟说1923年是抗战前夕一样荒唐。影片本身跟这样的评论倒也红绿搭配,对于它所要去处理的那个时代缺乏最起码的感知,而是一任自己沉浸在神话里,抗战时期自有日本人的入侵为我们勾勒外部,当代张震这部分可以完全是情节剧式的尔虞我诈、小人拨弄其间,惟有1962年这块是由“时代”自身的黑暗(又有一篇挺这个电影的文章张嘴就是“那个荒诞的时代”)来衬托人性(陈鹏、王敏佳)的光辉。之所以这些叙事漏洞可以被忽略、被原谅(搁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打死了人就随便刨坑埋了、死而复生之后还能神不知鬼不觉偷偷转移),是基于对那段历史的神话表述的共识。实际上,这个程序应该掉过个儿来讲才是。
正是通过孙柏所分析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教条叙事,这种带有“寻根”“反思”意味的“历史神话”完成对历史的掏空。尽管近期的《软埋》《风筝》《芳华》《无问西东》处理的叙事年代各不相同,其“寻根”的神话表述更多指向的是今日共和国之根:《软埋》的伤痕之“根”在土改,《风筝》之根则追溯到了革命时期,《芳华》在指向前三十年的同时更是指向了改革开放初期之“根”,《无问西东》寻的清华“新根”是清华的买办传统。这种“寻根”的神话表述,用一个人或一个机构的历史蒙太奇替代了整个大时代的叙事。那拾起的一片时光,也不过只是颠倒的世界颠倒过来又颠倒回去后的精英们的自我标榜,不过是八十年代种下的“寻根”文艺之后生出的跳蚤。这种“寻根”背后更多是价值的置换,而非创新。正如徐友渔曾经坦率指出的:“80年代大陆主要思想领袖、文化英雄的重大贡献其实借鉴了海外华裔学者和汉学家的观点,也谈不上有多少思想的创新。”如果徐友渔这种认知成立,那么这种状况出现,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当时现代性状况:单向度的现代化与全球资本主义中心的霸权,使得当时冷战桥头堡——亚洲四小龙因经济腾飞而成为中国发展参照的对象。在这种现代性状况之中,八十年代中国当时一些思想领袖完成的只是某种发达现代性的转译,将中国接续到所谓全球之中。这导致整个思想界,在八十年代尽管是真诚的,但是大家基本上还是外来和尚会念经,靠的是海外中国研究内化,通过他者认识自己,因而才有河殇叙事。在这种反认他乡为故乡的过程中,中国逐步完成了情感层面的自我憎恨与知识层面的和世界接轨,实现将现代化逻辑内化。文艺界的“国家退出”与党的领导事实上的淡出,使得文艺的群众性衰退,文艺越来越有江湖化态势,人民文艺衰退成为精英文艺与都市文艺。官方有些时候出于现实政治斗争需要甚至是一种默许,没有一个具有实践性瑜连贯性的认知与规划。写作关系经历了“再封建化”:人民失去了曾经群众运动时代对人民文艺反馈的作用,作家/文艺工作者在强调独立/自由创作的意义中再次成为了创作中的独裁者按照他们偏执书写,商业因素越来越渗透到整个文艺生产过程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再次变成精英主义的了,并离那个时代的人民越来越远,体验生活机制的缺乏使得文艺视野越来越局限在作者的局限之中,没有打开另类实践经验的可能。文艺越来越停留在作家/艺术工作者自己世界表达,而不是沟通另外一个现实世界。这种文艺与人民/真实生活世界的断裂恰恰是通过伤痕文学这种催泪与煽情的方式遮蔽的。在这种有利于自身的历史蒙太奇的裁剪之中,时代与历史对于主体的“孽债”被以伤痕的方式显现与表述。同时,这种伤痕文学遮蔽中国真正的问题:在哭哭啼啼氛围中遮蔽了现实中国发展的不平衡--在八十年代的双轨制改革中,这些归来的“右派”索债者纷纷在平反之后,不同程度上成为了改革的受益者与改革的代言人。在这个过程中,人民主体—工人和农民沦陷,在文艺作品中从主体的位置上跌落下来,成为改革弄潮儿们精英主义主导的科学改革需要变革的客体;军艺随着中美中苏关系的缓和与正常化,在走向了边缘与衰微的同时,也被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大院文学所解构。政治的文学化与文学的政治化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过度的耗费与透支,走向衰落。当文艺自八十年代以来完成了“纯文学”“纯电影”等转变的时候,这些文艺也就丧失了将中国社会变迁中工人/农民生存的真实经验传达,以故事的方式被社会体认。在这个过程之中,顶替文艺功能的是更为蹩脚的叙事产品—文学化/故事化的新闻,只不过历史蒙太奇连接上的是十九世纪欧美的黄色新闻传统。作为九十年代商品化过程中争夺市场与注意力的拳头产品,以星腥性著称的黄色新闻此时对于改革失调过程中带来的农村的凋敝与城乡关系殖民化视而不见,而将关注点放在猎奇与娱乐至死之上。
与此同时,九十年代以来的文艺领域市场化与商品化改革,使得八十年代以一种窄化/教条化的文化形态存在。时髦的全球化与文化产业化,强化的是冷战终结前冷战另一方文化的优势。美国基于中产阶级读者的通俗文学与好莱坞叙事替代了新中国后长期影响作家情感结构的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主义文艺,以及苏联的文艺形态。现代化的逻辑使得曾经革命史之中被贬低的清廷干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再次被抬升,被抬升到政治家/民族英雄/先知等位置;农民起义被简单视为现代化过程中的障碍;曾经构成三座大山的帝国主义与洋大人则在全球化逻辑中成为现代化代表;最现代化的是十里洋场上海,工农兵的上海则成为了历史的倒退。也是在现代化逻辑之中,历史书写完成了民国对共和国的审判:因为即便动乱的民国,还有现代化的思想与追求,还有大师与大楼的轶事,唯独共和国中政治运动使得现代化中断,知识分子颠沛流离,倍受摧残。历史蒙太奇再次衔接上的是1978年现代化重启,被剪掉的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异质性的历史。全然忽视掉的是,当代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恰恰是历史蒙太奇剪掉的胡适等自由主义被批判,上山下乡,文革十年等历史时期给奠定的,那些年代现代化的意义与合理性在破掉脏水的时候被作为婴儿一块泼掉了。
全球化的向度,使得来自全球霸权中心的价值成为了历史衡量的尺度。在这种价值之中,中国完成对民国期间略胜于己的印度的全面赶超,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实现少有的工业体系建设的事实被忽略掉了。作为八十年代末政治风波后果,政治与思想界新自由主义转入了低潮,在学界却以学者学术研究的方式再次活跃。作为风波之后残留在大陆的知识知识界的知识分子则在退隐到各自的学科领域,借着全球化的东风与商业化的互联网等再次成为知识界风云人物,在知识领域中开始争夺话语权。现代化使得前三十年成为难以言说的历史,历史的蒙太奇变成了一种学术与文艺的事实。当《软埋》《芳华》《风筝》《无问西东》等以后现代大杂烩与历史蒙太奇构成的文本,使得书写者以“纯文艺”之名成功绕过审查的环节。《白鹿原》、《一个地主的死》、《活着》、《丰乳肥臀》等莫不是以家族史/生命史的方式来对大历史进历史蒙太奇的处理。
在这种“去政治化”的文学政治之中,再次政治化的是曾经革命文艺之中作为人民对立面的阶级的翻身:这些曾经革命文艺之中浓墨重彩/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在新的一轮的政治经济变迁之中被视为逝去的精英/无辜受害者,在革命的逻辑被抽离被现代化逻辑替代后,再一次粉墨登场。在文艺之中,他们形象也在频频的翻案史学的支撑下变成依靠劳动致富,代表先进生产关系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这本身是翻案文艺试图在当下暗度陈仓所进行的修辞学意义上的概念偷换,颇具有关公战秦琼的意味。同时,在政治上,由于革命的政治让位于全球时代身份政治的焦灼,共产党员身份似乎替代了此前对革命和人民的忠诚。这种中国叙事事实上是建立在八十年代已有的刻板成见基础之上的,本身是一种观念真实的操作化。围绕着所谓个人所处“神话年代”,叙事在这里发生逆转。在新一轮的写作之中,敌我关系模糊了。那些被视为人民之敌的“敌人”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关系:他们或是早期革命成员/积极分子;或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功臣;或是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开明绅士。然而,他们支持的新中国最后成为了个人悲剧命运的来源。“新伤痕”书写则将这种洗白的逻辑通过历史蒙太奇的方式给变成可以接受的。
“无问西东”还是“一路向西”
在当前时代,诸如《软埋》《风筝》《无问西东》等文艺事件频发再次向我们提示着中国叙述的债务:是“无问西东”还是“一路向西”。在今天实践之中无论是“无问西东”还是“一路向西”均成为某种不得不正视的历史债务。这种历史债务,也正是今天中国叙述不得不承担的。如果说,此前的现代中国是自近代同西方碰撞/交锋/塌陷而在人民付出惨痛代价之后以“反认他乡为故乡”这样痛苦的文明自我否定的方式建构起来的话,那么当下崛起的中国则有必要重拾文明自我否定之中被简单粗暴遗弃的文明传统,重新思考东西与何为现代中国的问题,以生成新的中国现代文明与中国叙述。
尽管现在已经是习近平新时代了,然而在经过了自新时期以来漫长的“反认他乡是故乡”之后,思想界与文艺界还生活在八十年代思想状况的后果之中,并没有做好中国叙述的准备。中央已经意识到共和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历史不能互相否定,但是这种思想要在大众生活中扎根,需要文艺战线工作者坚持正确思想,继续坚持斗争,在多年后方才可能见效,我们当下依然生活在八十年代的思想框架的现实之中,而这本身是事实上弱化党对文艺领导的历史债务--自1978年以来,后三十年文艺领域开始了对前三十年的攻击,国家从文艺组织生产中退出。相应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相关文艺组织的沦陷。《软埋》的作者身为作为湖北作协主席,原本是体制内培育的为社会主义摇旗呐喊的文艺战线的工作者,结果加入了反攻倒算的队伍中,最后居然弄出质询政权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文艺作品,这本身已经说明了历史虚无主义已经渗透到体制肌肤里。问题同样严峻的是媒体领域。方方《软埋》的走红,严歌苓系列作品的热销,《芳华》的大卖,《风筝》的热播,《无问西东》的风行一时等过程中,媒体都扮演着重要的参数。在历史终结之后,商业逻辑主导了今天的媒体:尽管不少媒体号称官媒,党的耳目喉舌,然而到底有多少喉舌在党手中,则一直是大写的问号。这个问题同样是一个市场化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今天,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形成的债务本身已经结出了果实。如果说方方与严歌苓代表的是五五后老一代的话,那么七五后的李芳芳则以《无问西东》向老一代伤痕作家们致敬,开创了一种“没有伤痕的伤痕书写”的“新伤痕”传统——她本人并没有亲历“伤痕年代”,也没有“伤痕经验”,却娴熟通过拼贴流俗之中伤痕叙事,完成“新伤痕”的转向。这再一次提醒我们话语本身的繁衍性以及置之不理同时会使得这套话语“道成肉身”,变成某种社会事实的叙述。在今天这个传播渠道众多、众声喧哗的时代,事实本身由于传播不足,反倒不如那套漏洞百出的叙事话语。作为新一代“伤痕”书写的佼佼者,这位成长于改革年代的七五后精英比她的两位大器晚成的前辈同龄阶段更优秀,也更加国际化,也比这些前辈更具有“反认他乡是故乡”的典型性:如她在一篇采访之中所言,她从小接受的是中美教育,“家里人希望我得到中西方最好的教育,对此他们竭尽所能。”在访谈中,她所言的这种所谓中西方最好的教育,代表“中”的是本质化的“文化中国”的理解——是港台来的中文老师与繁体字。这种自小开始的经历导致她本身的政治无意识:中国在她的认知之中更多是蜗居台湾的国民党在冷战期间形塑的“文化中国”概念,而非大陆关于中国的论述。这种价值与政治上位置的选择,导致她真正想表达的清华,事实上是接过西南联大名士风流与精英主义衣钵的台湾新竹清华,而不是大陆曾被人民革命改造过,拥有“人民的清华”传统的清华。在影像之中,原本应该表达的“人民的清华”,则以事实蒙太奇的方式表现沈阳医学院的人性惨剧。在表达技巧上,《无问西东》之中,导演娴熟将老一辈的历史蒙太奇的方式发挥到了极致:她选择了能够体现清华买办性与精英主义的历史时段,采用了国民党文宣的方式,做了足够的影像的修辞。在这种历史蒙太奇之中,她忽视了清华本身的历史复杂性与弹性:尽管能指同为清华,但是所指在各个时代却是断裂的,拥有不同的精神面貌,呈现出自身的不同特点来。这位在精英主义环境下长大,并以青春片出道的导演,事实上把《无问西东》变成另外一部清华版的《80’后》。四个故事段落,只不过是四个《80’后》的可能性侧面,共同内核则依然还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想象精英的一套。影片中,买办的清华被用今天想象的充满全球化色彩的民国范与民国精英的想象替代了;人民的清华则被妖魔化的文革时代群氓暴力替代了—更为甚者,为了达成对文革时代群氓控制目的,她甚至将发生在沈阳某医学院的故事嫁接到清华大学,移花接木,从而来表现大时代之中处在暴力逻辑之下的可怕。故事的虚假被专业演员的形象与精湛演技给冲淡了,以形象的方式对历史的逻辑进行解构与替代。在这个过程之中,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本质特点,被形象逻辑与奇观替代了。
在这种表达中,二十年代的清华梅贻琦的名士风流,四十年代王力宏饰演的精英子弟都以某种去男性气质的方式表达出来。在片中最有男性气质的相反是趾高气昂,叼着雪茄的美国教官。中国的学生,教授与飞行员相反是孱弱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表明:在充满男性气质的西方殖民者面前,中国的形象就是一个“女性”,或空有颜值而无男性气质的精英。因此,导演安排沈母反对儿子投笔从戎之际说那番“你还没享受生活”,除了徒添几分遗憾几分悲情外,同时也是一种西方及时行乐价值以内化的方式传播出来。这同样也不符合国民政府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学生十万兵”的精英价值表达。尽管有文章曾经批评她采用了国民党的文宣,但必须指出的是,她对国民党价值表达同样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这种虚无主义在于她价值之中的“一路向西”。她对“无问西东”的理解中,并没有一个中国主体,因而只见“西”:代表西方的英语老师到来之后,拿着书帖的国学老先生只能黯然退场;美国飞行员教官高大勇猛成为了价值评判的标准,而中国的飞行员只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柔软的主体性”;在表现同西方化的东方—日本作战的表达段落之中,只见中国作为受难的客体与反抗的牺牲者,而不见人民斗争—这方才是真正的抗战主流;在表现中国飞行员的飞行与空战部分段落,则大量平移了日本走红电影《永远的零》之中对日本零式战机的表现手法与技巧;那些被救助的。从内容到形式再到精髓之中,可见的是一个大写的西方价值,而真正代表中国脊梁的陈鹏奔赴沙漠研究原子弹的段落却放在小时代小确幸三角恋之中,用一个因为高中老师打抱不平而被群氓践踏致死被埋后又被扒出来活过来变成无名存在的王敏佳的故事来完成对大时代的控诉—而这叙述背后历史蒙太奇的逻辑与价值标准则来自占据话语权的西方。正因为此,故事之中从梅贻琦到张震这个脉络下来,推崇的要么是被西方文化推崇的泰戈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要么是西化的价值。“无问西东”事实上要遮蔽的恰恰是政治无意识层面的“一路向西”。这种 “一路向西”的自我殖民的价值表达,将“西”放在了真理的位置上。然而,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实践经验正如汪晖所言的“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就是真理”。
这种东方学的状况,在经历了新时期伤痕文学/伤痕电影洗礼之后在文艺界越来越突出。作为情感结构上伤痕文艺之子以及改革后价值上完全接纳了冷战另一边文化成长起来的一代,李芳芳越是努力,便在技术上越是成功这种政治帝国主义中心对人们想象的控制完成得月东方学上走得越远。在访谈中,李芳芳表示其为了拍好这部电影做了好多功课,她去了清华大学的校史馆,力图想表达清华精神,拍好一片时光。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文艺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混乱,加上电影工业属性,造就了这样一部“一路向西”的清华献礼片。这导致她越是真诚,越能煽情,离真正清华精神就越远,越是南辕北辙,就越是陷入在某种单向度的现代性幻觉中不能自拔。这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后果。
结论
近几年一度热门的商业化的影视作品如《芳华》《白鹿原》《风筝》《无问西东》等依然提示我们,今天新时代文艺真正的纠结点在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仍生活在八十年代,就是说:八十年代建立起的观念仍然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基本框架。”从表达方法上看,这些文艺作品的创作者依然没能够突破八九十年代的框架,依然还活在上世界,“闲坐说玄宗”。如果说,在刚打开国门背景下,国人还缺乏文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话,那么今天中国全面复兴的新时代,则到了反思这个“告别革命”的亚洲版“历史的终结”的时刻了。
在新时代,真正问题是中国历史并没有终结,但是却被伤痕文艺的中国叙述话语却被裹挟进了历史终结的困境中。毛泽东主席当年曾要求新华社“将地球管起来”,在今天中国硬件上有这样条件的状况下,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反被我们国内某些精英共享且唯一的“彼岸想象”即美国想象管起来的世界想象。这种想象帝国主义与殖民秩序以某种文明/发展主义的叙事形态重新归来。这正是八十年代伤痕文艺的遗产。在九十年代以来,这种遗产延续着,扩大的新伤痕书写是在市场环境带来的主体多元化与表达多元化背景下完成文艺的重新政治化。原本多元化的目的是以多元化的实践加强党的领导,丰富文艺的形态。然而,由于在多元过程中,实践的复杂性使得党的文化领导权事实上遗失,使得在多元化中党反而被边缘化了,同时党与国家缺乏对中国叙述与宏大叙事在实践层面行之有效的管理。中国在追求现代化与全球化过程中,没有文化领导权的多元化使得原本过气的伤痕文学在我们崇洋媚外的全球化时代复活了过来:严歌苓多部作品拍成《天浴》《归来》《金陵十三钗》《芳华》等电影以及电视剧《小姨多鹤》,继续影响年轻一代观众的情感结构,同时也在向我们这个时代索讨历史的债务。当这位美裔华人在叙事之中向我们显示彼岸所携带的“自由民主”与知识分子世家的优越感,以阴暗的心理,阴暗的审美,阴暗的芳华的方式来表现中国历史中伤痕与荒谬之际,国内的文艺界却不断用八十年代以来那套所谓“纯文学”的“人性”的话语遗产来为之辩解。即便是《大江大河》这种叫好的影片,在再现改革过程之中也同样存在过于概念化/失实等问题,与民众生活经验与社会记忆不符。
在新时代重建中国叙述,走出历史终结的迷雾,需要的是对八十年代与伤痕文艺反思,而不是将八十年代建构成为乌托邦,更不是在乌托邦的迷雾之中将自身价值与经验束缚在债务的范畴。因为,这种中国叙述的债务,事实上是要以“哭哭啼啼”的方式将历史的终结变成绝对的价值。然而,问题是中国崛起的大历史实践正在冲破这种颓废式/教条化知识体系与叙事的牢笼。这个过程,正如汪晖所言:“不打破现代的幻觉和帝国主义强加的幻觉,我们很难把自己的历史经验开放出来,从而帮助我们在当代世界中重建我们的价值取向。”
这意味着在新时代要完成价值的重建。而我们今日生存其中的八十年代的思想框架,在去政治化过程中完成“纯文学”“纯电影”等建构的中国文艺囿于其狭隘的精英自恋的框架已经无法阐释今天历史实践状况,更别说肩负价值重建的重任。“反认他乡为故乡”的文化自卑带来的如《软埋》《芳华》《风筝》《无问西东》等伤痕与债务叙述,事实上在建构一种画地为牢的历史终结的文艺状况,里面有精英的小确幸与小时代,却没有人民与人民的历史。中国叙述需要从这种伤痕叙述与债务式叙事中走出,重新打开唯西方本位的历史的终结屏蔽掉的历史可能性。这也是寻找创造打开新时代中国叙述的关键所在。这也是一个重新发现“哭哭啼啼”的伤痕文艺叙事中所遮蔽的真正中国脊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