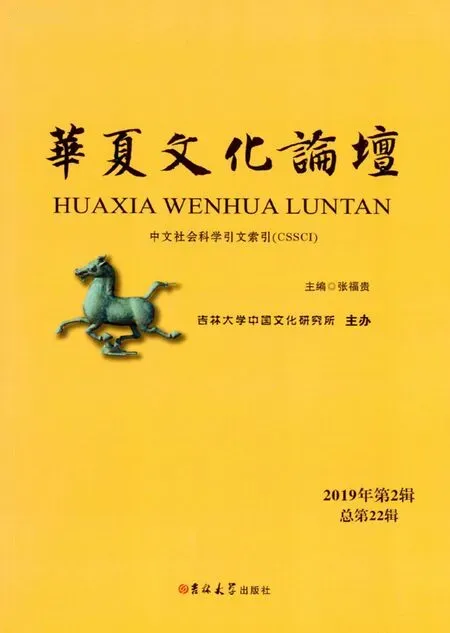清末民初西源外来词汉化的文化心理研究
张 烨
【内容提要】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社会重要的变革期,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西源外来词呈爆发式增长,它们在被纳入汉语词汇系统之前,势必要经历一个汉化的过程。本文以影响西源词汉化的四种文化心理为研究对象,考察造成影响的过程及规律,从而进一步明确清末民初西源外来词的产生、融合及定型的特征。
一、清末民初西源外来词概况
“清末民初”指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革,中外语言亦出现了频繁的接触及激烈的碰撞,由此产生相互的渗透甚至一定程度的融合,这一点在此期涌现的大量外来词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据我们有限的统计,清末民初的西源外来词共计615个,主要集中在哲学、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学领域,以名词术语居多。这些外来词在被纳入到汉语词汇系统前,势必要经过一个动态的汉化过程。从内部因素来看,汉语的语音、语义、文字等因素会直接制约汉化的过程;从语言外部来看,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虽然是不易察觉的,但往往也会对翻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即以西源外来词汉化的文化心理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中的规律,从而进一步明确清末民初西源外来词产生、融合及定型的特征。
二、西源外来词汉化的文化心理研究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随着外来文明的不断涌入,新兴外来词也逐渐增多,但其是否能留存下来往往还需要经过汰选的过程,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在于它是否与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相契合。我们知道,语言系统的演变、发展乃至消亡都不是置于真空之中,汉语在吸纳外来词的过程中,汉民族特有的思维和文化心理亦在左右着语言的走向。我们重点探讨以下四种文化心理对外来词汉化造成的影响。
(一)注重正名思想
在中国,儒教素来重视“正名”。先秦时期,由于社会变迁导致名实混乱,孔子在《论语》中则有“名不正则言不顺”的主张。到了战国,对于“名”的争论尤为核心,例如墨子认为:“瞽不知黑白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也就是说,瞎子之所以不识黑白,是因为难以从现实中选出黑白的事物。可见,正名思想要求造词不仅要名实相符,更重要的是形神兼备,让人一目了然。清末民初的西源外来词中不乏体现“正名”思想的词例。下面结合实例说明。
【维他命】
(1)紫光是维他命(vitamin)D、鱼肝油及鸡蛋,都富有这种品质。(黄成中《雏鸡的研究》)
“维他命”即维生素,源自英语“vitamin”。当时还有另一个音译形式“维太命”,但显然不如“维他命”那样,能够更明确地凸显这种物质的重要性,因为二者具有“非指人”和“指人”的差异。“维他命”在记音外还兼具表义功能,正好符合“正名”思想。试想一下,即使一个人对“维他命”完全陌生,他也会从字面上大概推知其功用,即“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而“维他命”的确是人类生存必不可缺的元素,因而这一译名十分生动形象,是准确记音又明白达意的典范。“vitamin”后来还意译为“维生素”,二者在现代汉语中都有出现,只是在使用社群上有所不同,“维他命”现在多用于港台地区。
有趣的是,在今天的一些食品、药品和化妆品中,“维他”这个形式使用得较为普遍。据我们粗略统计,已有“深圳维他(光明)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北京天天维他保健食品有限公司、21金维他、维他奶、小护士维他营养霜、维他纯蒸溜水、维他滋养因子”等多种形式。这里的“维他”作为一个语素使用,它从表面看是对汉语音译形式“维他命”的简缩,实则不然。“vitamin”在语源学中可拆分为拉丁语中的“vita”+“min”(源于“amine”),其中“vita”就是英语中的“vital”,表示的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可见,“维他”就是对“vita”的音译。像现在英语中也有“vitamilk”“vita coffee”等,可见也是把“vita”作为构词语素。
但是,还有一些外来词在引进之初用字不够精准,或者名、实之间的距离比较远,这样的词就很难说符合“正名”思想。如果一旦出现其他译法与其竞争,那么它多半摆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例如:
【水门汀】【水泥】【洋灰】
(2)坚硬的木履踏在水门汀的月台上,汇成一片杂乱的噪音,就好像有许多马蹄的声响。(郭沫若《残春》)
(3)水泥,西人名塞门得土,华名红毛泥。(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
(4)澳外风浪极大而澳内平稳如故,叠石灌以洋灰,所费不资。(沈翊清《东游日记》 )
三者均源于英语“cement”。水泥传入中国是在清末,开平矿务局曾在煤矿附近设立水泥厂,光绪三十二年(1906)让给华商经营,更名为启新洋灰厂。可见,最早占据统治地位的应该是“洋灰”,由于它是从外国传入,所以还一度被称为“红毛泥”。“水门汀”和“水泥”,前者属于音译词,源于上海的“洋泾浜”式外语,后者是意译词。虽然“水门汀”是音译,但由于“cement”本身就是加水的泥浆状物体,所以其首音节“水”多少带有一些表义属性,这要比同时期其他纯音译词,如“四门町”等好一些。不过,在与“水泥”的竞争中,“水门汀”从字面上看仍然很难与它所代表的事物相联结,所以逐渐被“水泥”取代。至于“洋灰”,它固然也是意译名,但作为一个偏正式词,其中心语“灰”很难体现出事物的本质属性,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汉语也摒弃了许多带“洋”的称呼,所以虽然它使用时间较长,但最终还是被其他形式所取代。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地区将“cement”译作“石屎”,并且今天仍在使用,从类型上来说,它应当属于音义兼译的类型。
(二)重形象性思维
众所周知,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上具有差异,西方人更注重逻辑和理性思维,而汉人更倾向从形象性思维去关注事物。汉语词汇系统中到处可见形象思维对造词活动所遗留的痕迹,如形容词“雪白”“红彤彤”等便是实例。此外,形象性思维也与“联想距离”有关,后者指的是事物本身和人们对其进行联想的距离。但是,在汉语中并非是联想距离越近的词就越容易生存下来,由于先人注重对语言符号的形象性理解,所以有些看似联想距离较远的词也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例如,现代汉语中有一类结构特殊的偏正式复合名词,如“人海”“法网”“虾米”等,它们与一般偏正式不同的是,其中心语素都是前语素,后语素对前语素起到修饰的作用。从两个语素的联想距离来看,我们以“人海”为例,“人”的联想空间很大,所以它能激活的区域非常广,而“海”与人的相关度并不是很高,所以联想距离也较远。但是,“海”本身具有一定的修饰性,所以如果把“大的、数量多的”这样的语义加入造词中,两个语素的相关度便可建立,表示“像海一样数量多的人”。对于外源词的翻译也是如此,我们知道,翻译的过程是译者的一种主观思维活动,那么汉民族特有的形象性思维便会对译词造成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
【霓虹灯】
(5)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日新月异的商店样子窗装饰。(丰子恺《商店艺术》)
“霓虹灯”是电灯的一种,源于英语“neon”。它本身属于“音译+义标”的类型,即在音译形式“霓虹”的后面添加汉语类名“灯”而构成,它同时又能体现形象性思维的特点。何谓“霓虹”?元代朱凯所作杂剧《昊天塔孟良盗骨》中提到:“做不的万丈霓虹”,这里的“霓虹”即为彩虹。由于霓虹灯闪烁时的样貌恰如天空中五颜六色的彩虹,甚为美丽,所以用“霓虹”音译“neon”,仿佛在人们面前架起了一座七色虹彩,译音又达意,而且形象生动,所以这也远较它的另一个译法“年红灯”要好得多。
【乒乓球】
(6)一直是琮琮地响着的乒乓球,突然都寂静。(茅盾《虹》六 )
乒乓球是一种球类运动项目,该运动最早起源于英国,曾被命名为“table tennis”。“tennis”指网球,所以它可以被仿译为“桌上网球”。(现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仍用“桌球”表示“乒乓球”。)后来,亦有人依据打球时的声音而创造出“ping-pong”这一名称。该运动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不过首先为中国人所接纳并借用的反而是后出现的“ping-pong”一词。这一方面是由于汉语中本来就有发音类似的拟声词“乒乓”,更重要的是,“乒乓球”很符合汉人的形象思维取向。我们知道,造词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它一定要符合某个民族的审美意趣才能存在,试想一下,当听到球类撞击在桌子上的“乒乓”声,是不是眼前也会浮现出小球迅捷、轻灵的上下翻飞的形象画面?这就类似于文学领域的“听声类形”,因而这种能体现形象化思维的词语一经出现便广泛流传开来。
(三)重视“意合”和“直觉”的思维方式
汉民族从儒家开始便重视“直觉”和“体悟”,从语言的角度来看,“直觉”思维并不需要词语具有明确的形式特征,它更多是靠读者与词语内涵之间如同“顿悟”式的沟通。此外,汉语不同于英语的一个很大特点是,前者属于“意合”式的语言,即语词的组合可以通过“意会”而连接起来,而后者则更多依靠某种形式化手段进行组合,这就是所谓的“形合”式语言。这种语言类型上的差异反映到翻译上也具有同样的制约和选择的作用。换句话说,汉语语素的结合不需要太多形式上的考虑,往往几个语素在语义上有着相关性,就具有了搭配的可能。这种语法形式上的简约性一般通过“意合”过程中的语境来填补,例如汉语中的“谢幕”便是如此。可见,在语境的帮助下,汉语语素的结合更加灵活自由。有一些好的音译词,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这一特点。
【幽默】
(7)Humor,有情滑稽;幽默。(《英汉对照百科名汇》)
“幽默”源自英语“humour”。汉语中本有表示与之相关的词语,例如“诙谐”“嘲”“谑”“讽”“调侃”等,但都很难表达“幽默”那种隐含的语义。1906年,王国维直接将“humour”音译为“欧穆亚”,但此译法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事实上,“幽默”这一词形早就存在于古代汉语中,如屈原的《九章·怀沙》:“眴兮杳杳,孔静幽默。”该句中的“幽默”是联合式结构,即“幽寂沉默”。此义一直保留到了晚清时期,直到民国初年,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中将“幽默”欧作为“humour”的音译形式,这实际上为该词形灌注了新义。如果单纯从字面来看,很难体会到该词的内中深意,但是汉语重“意合”的特点是选择的重要依据。这也正如林语堂在《答青崖论幽默译名》一文中提到的:“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部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显露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故译为幽默。”由此可见,该词的深刻蕴含如果从形式角度来看,其实是很难言明的,但是从中可以挑选出两个最具有典型性的字眼,利用一种“直觉”或者“顿悟”,无需遵守严格的要求便可表达出这种引人玩味的含义,可见是表音又兼具传义的典型范例。
【逻辑】
(8)逻辑,犹吾国之名学也。(胡以鲁《论译名》)
“逻辑”源于英语“logic”。此词的译名在我国历经了好几个阶段才得以确定。17世纪末,该词曾在艾儒略《职方外纪》中被译作“落日加”,后来到了19世纪,罗存德《英华字典》称之为“理学”,直至20世纪初,日语从被动接受汉语新词转为向中国逆向输入大量日制汉字词,该词则出现日译形式“论理学”。与之产生竞争的是严复在1902年所译《穆勒名学》中使用的“逻辑”。当然,今天“逻辑”一词已经完全取代其他译法,而这与它独特的翻译方式密切相关。“逻辑”本身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从字面来看,“逻”即“巡察”,“辑”指的是“聚集,特指聚集材料编书”,二者本身都是动词性语素,结合之后表达“依循一定的路线行动并把材料进行收集、综合、推理”的含义,而且二者共同的义素都与“思维规律”相关联,这为它们的结合提供了可能性。因而,这两个语素的结合就是依据“意合”法连缀在一起,“逻辑”在表音的同时兼具表义功能,因此一直留存至今。
(四)民族审美心理
汉民族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审美心理,我们首先对这些外来词进行了归类,有的译词从表面上看就能产生超于词义本身所具有的表达效果,这种“望文生义”属于一种“义溢出”现象。还有的词在与其他音译形式竞争的过程中,为了避免“望文生义”,从而选择偏中性的表达。从审美心理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我们一一进行说明。
首先是求雅心理。在中国,关于“雅”的论述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期,《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这里的“雅”指的是周代朝廷的雅乐,与乐府所掌的民间音乐相对,汉民族的雅俗观由此产生。在文学领域,陆机在论及艺术美的五条标准时,将“雅”与“应、艳、和”等并举,凸显了其重要性;严复关于翻译中的“信达雅”的论述更是耳熟能详。历史上,关于“雅”的词汇也层出不穷(如“雅人、雅士、雅才、雅什、雅文、雅言、雅玩、雅令、雅句、雅曲、雅号、雅服”)。可见,汉民族在发展中一直追求雅致的心理,这点在语言活动中亦有深刻体现,换句话说,人们在翻译过程中可能有意选取典雅的字眼,从而起到“避俗求雅”的效果。我们举例说明。
【咖啡】
“咖啡”源自coffee,该事物于18世纪初期传入中国,早期其音译形式众多,如“哈非、加非、架飞、迦非、茄菲、考非、喀啡、加非茶”等。值得一提的是,1866年西人撰写了一本以培训西餐厨师为目的的《造洋饭书》,该书中有这样的字句:“猛火烘磕肥,勤铲动,勿令其焦黑”,这里的“磕肥”即coffee。单从记音角度来看,该词要比“加非”等准确,但从用字角度来看,似乎很难与当时西餐的高雅联系在一起。具体来说,“肥”《说文》释为“多肉也”,在长期的使用中,逐渐与“胖”发生分工,它更多用于形容动物,如果修饰人的话,往往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如“肥头大耳、脑满肠肥”等。该字用于饮品名称中,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喝了以后会变得肥胖、臃肿的联想,这并不符合中国人的求雅心理,因而“磕肥”一词并未留存下来。日语中的coffee采用的是“珈琲”的汉字形式,二字均从王,与“玉石”相关。将其与今天汉语中的“咖啡”相比,能看出民族心理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日语更侧重采用好字眼,而汉语通过“口字旁”强调其外来属性及“入口”的特征。
与之类似的还有“olive”,我们在梁廷枏《海国四说·粤道贡国说》中发现了一段文字:“膏油之类,味美者阿利袜,是树豆果,熟后即全为油,其生最繁,以法制之最饶风味,其核又可为炭,滓可为硷,叶可食牛羊。”这里提到的“阿利袜”即为olive的音译形式。用“袜”作为音译用字,给人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感觉,更何况它还是可以入口的食物,与“袜”联系在一起,也无法带来句中所述“最饶风味”的感受,因而后期该词逐渐被意译形式“橄榄”所取代。再如“夏娃”和“厄袜”、“巧克力”和“猪古辣”,“可可”和“苟苟”,每对词中的后者均被前者所取代,这都体现了汉民族崇尚雅致的深刻影响。
此外,一些外国人名翻译亦体现了求雅心理。以19世纪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为例,例如Morrison(马礼逊),除去以“马”为姓外,其余两字颇具风雅,恰与中国文化中“知礼”“谦逊”的精神相合;再如Fryer(傅兰雅),除去“傅”姓以外,其名仿佛透露出“如兰花一般雅致”的意味。再如此期的西洋乐器的命名,由于当时人们视西洋音乐为高雅艺术,因而译字往往向“雅”而靠拢,如“violin”被译为“梵婀玲”,“piano”被译成“批雅娜”,“flute”译作“弗柳德”等。
其次是求美心理。人类对于美的追求亘古未变,汉民族更崇尚和谐、圆融的美感,这种心理在翻译过程中也有深刻体现。具体来说,由于汉字属于表意文字,受到思维惯性的影响,有的译字会带给人美感,有的则正好相反。这种文化心理会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是在翻译时会有意选取某些美好的字眼,从而更准确地表达原词;二是当出现多个异形同义词时,如其中带有造成心理反感的汉字,就可能会被淘汰。我们举例说明。
【魁英】
“魁英”即女王,是英语“queen”的音译形式。早在先秦时期,“英”便有“花”义,例如《诗·郑风·有女同车》中提到了“颜如舜英”,即女子的容颜如同木槿花一般。该义在后代得到了承用,例如“英华”言“花木之美”,“蕊英”表“鲜艳的花”,“落英”即“落花”等。众所周知,花朵具有美丽动人的特性,因而从古至今,汉语中出现了大量把女人比作花朵的例子,也正因如此,许多女性的名字中喜以“英”字为名,如帝舜之妻“女英”,再如巾帼英雄“穆桂英”等。我们再看“魁英”一词,“英”带有明确的性别标识特征,且能让人联想到美艳如花的特性,再加之“魁”本身具有“魁首、头领”的含义,这恰与queen的语义相合,因而虽然从译音的准确性来说,“魁英”不见得忠于原词,但却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翻译过程中的“求美心理”。与之类似的还有“雪丝黛”(sister)、“安琪儿”(angel)、“蜜斯”(miss)等词。
受到这种“求美心理”的影响,很多译词虽产生较早,但仍可能被更富有美感的形式而取代。例如由林纾译于1895年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其主人公Marguerite Gautier被译作“马克格尼尔”(后文基本简写为“马克”),虽然从译音角度来说较为精准,但似乎难以体现作品中女主角的柔美形象,因而后来的译本一般译为“玛格丽特·戈蒂埃”。其中“玛”从王,表玉石,汉语中用“玉”部字作为女性名字的例子比比皆是,如“琳、环、玫、瑰、珍、珠、玥、玲”等,很显然比中性的“马”更具有女性气息,此外,“丽”表女性美丽、漂亮的用法古已有之,可以说,该译法充分展现了翻译过程中的求美心理。再如美国作家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其父将其音译名“珀尔·赛登斯特里克·布克”改作“赛珍珠”,该名比较符合中国人的认知,且能使人联想到珠圆玉润的美感,这也与求美心理息息相关。
与之相对的,清末民初的一些国名翻译,不仅不会带给人美感,甚至还会反其道行之。如“莫三鼻给、危地马拉、厄瓜多尔、老挝、怯尼亚、不丹”等,虽然有的译名从记音角度来说较为贴近原语(如“莫三鼻给”),但从译者故意选取一些“坏字眼”(如鼻、危、厄运、怯)也不难看出当时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对一些小国、弱国的轻视态度。在这些译名中,只有“莫三鼻给”和“怯尼亚”上世纪6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进行了调整,分别译作“莫桑比克”及“肯尼亚”,其余基本仍保留原始译名。
最后是求吉心理。一方面,汉民族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人们历来向往“福禄寿喜”,在语言活动中也多喜用吉祥、喜庆的字眼来表达这种心理。另一方面,如果原词所代表的事物本身是人们排斥的、厌恶的,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人们会在译字选取上有所体现。
我们对建立的西源外来词语料库进行了粗略统计,发现从双音节到五音节的外来词中,均有采用吉利字眼的外来词,而且屡见不鲜。例如,“吉士(cheese)”“智利(Chile)”“阜利通(feuilleton)”“康邦宜(company)”“哈利路亚(Hallelujah)”“康门尼斯姆(communism)”等。这里值得一提的是“golf”,它早在19世纪便已有译名“高尔夫球”,且使用频率较高,但鲁迅著于民国中期的《南腔北调集》中却将其译作“高而富球”,如“富翁胖到要发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从此主张运动的紧要”,这不得不说是作者刻意为之的巧思。我们知道,“高”“富”在汉语中都属于偏吉利的字眼,但用在该句中很明显意在讽刺。试想一下,富翁们直到发病才会想到花大把银子去打只有他们能享用的“高而富球”,这难道不是可笑可叹吗?这里如果采用“高尔夫球”,势必达不到同样的文学效果。
此外,晚清时期的国名翻译也能折射出“求吉心理”。例如“Holland”,它曾有两种音译形式“和兰”与“荷兰”,二者从表音的角度来说完全一致。相对来说,“和兰”产生更早。明万历年间《崇相集选录》对“和兰”有这样的介绍:“红夷,自古不通中国,与佛郎机接壤。时驾大舶,横行爪哇、大泥间。及闻佛郎机据吕宋,得互市香山澳,心慕之。万历二十九年,忽扬帆濠镜,自称‘和兰国’,欲通贡……”众所周知,“夷”在中国古代是汉族人对异族的一种贬义的称呼,由于荷兰人“长鼻赤发”,因而被称为“红夷”。从这个称呼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对入侵中国的荷兰人抱有一种既鄙夷又厌恶的态度。由于“和”在古汉语中有“和平、和谐”之义,显然与人们对“Holland”的认知不符。从“求吉心理”出发,人们也不希望给侵略国赋予这样的名称,所以虽然“荷兰”产生较晚,但在19世纪的文献中已有逐渐取代“和兰”的趋势。与之类似的还有“意大利”和“义大利”,“义”自古便有“道义、义气”的含义,所以“义大利”带有一种“美化”的意味。但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人们对这些侵略者抱有本能地排斥和反感,因而“意大利”这种偏中性的翻译更适合表达人们对“Italy”的主观态度,这可能也是后者逐渐取代前者的原因之一。不过,今天台湾地区仍沿用“义大利”的翻译方式。
三、结语
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在语言活动中,尤其是在外源词的翻译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论是自主创制新词还是对外源词的多种译名形式进行汰选,都是文化心理与汉语词汇的一次碰撞与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可能是潜藏的、难以察觉的,但最终定型后的外来词实则是汉民族文化的思维结晶,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语言与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