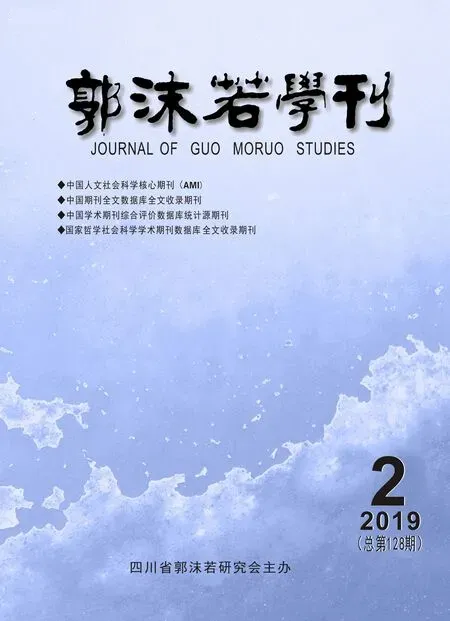郭沫若归国抗战真相
廖久明
(乐山师范学院 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四川 乐山 614000)
《同舟共进》2018年第1期发表的《郭沫若归国抗战始末》尽管写得有鼻子有眼,实际上却从头错到尾:郭沫若不是1927年3月20日而是30日到朱德家并于次日写作《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1937年7月27日回到上海后,8月2日出席中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举行的欢迎宴会应该是郭沫若归国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8月7日前往蓬莱大戏院观看《保卫卢沟桥》专场演出最多算第二次——该日中午还参加了上海留日同学救亡会会员举行的欢迎会。也许是人们对该问题非常关注吧,这样的文章却流传很快、很广:百度、搜狐、新浪微博、道客巴巴、铁血社区、金月牙、济南文史、旺旺网、历史之家等网站迅速转载了该文。查读秀,竟然还有4篇基本同题的文章:《郭沫若归国抗战始末》(崔力明,《济南文史》2004年第2期)、《郭沫若归国抗日始末》(杨柳枝、刘小梅,《文史春秋》2004年第7期)、《郭沫若归国抗日始末》(杨柳枝、周敏之,《党史天地》2004年第12期)、《郭沫若抗日归国始末》(赵英秀,《兰台内外》2008年第2期)。看来,为了不让“三人成虎”的谎言继续流传下去,2008年便开始研究郭沫若归国抗战问题的笔者确实有必要写作文章指出其错误。由于该文的错误实在太多,一一指出太费事,现在仅就“郭沫若归国抗战始末”的以下内容提供一点材料和看法:一、郁达夫1936年底到日本去的原因和情况,二、郁达夫1937年为郭沫若归国事所做的努力及所起的作用,三、抗战爆发前王芃生的情况及在郭沫若归国问题上所起的作用。笔者对吴基民反复炒冷饭的做法已非常不满,所以决定不引用他的“小说家言”,只针锋相对地直接引用笔者认可的材料并发表自己的看法,有兴趣者请自己去看他的文章。
一
应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邀请,在日本国1936年度“对支文化事业”项目资助下,时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兼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主任的郁达夫以文化视察名义、时任福建省政府技术专员兼福建省立医院筹备处主任的黄丙丁以医学视察名义,于1936年11月12日抵达长崎,13日两人一起抵达东京并入住万平酒店,14日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致函宫内省图书寮介绍郁达夫前去参观,15日两人一起拜访留学生监督处、中国大使馆等,16日郁达夫去拜访佐藤春夫。郁达夫去拜访时,恰遇佐藤要去参加改造社发行的《大鲁迅全集》翻译碰头会,郁达夫希望与故旧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会面,于是一道前往。看见郁达夫后,山本决定当天晚上举行欢迎会,于是马上派人去叫木村毅、林芙美子等郁达夫的旧友,又觉得应该请郭沫若来,所以立即派—名职员前去。由于郁达夫还未去拜访郭沫若,于是借机同车前往。当天见面及晚宴的具体情况可参看郭沫若的《达夫的来访》、小田岳夫的《郁达夫传——他的诗和爱及日本》(中译本收入《郁达夫传记两种》,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作者参加了该次宴会),从略。
在日本期间,郁达夫还与郭沫若见了6次面:11月24日,郭沫若参加了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举行的欢迎郁达夫的宴会;11月29日晚,郁达夫邀请郭沫若与其子阿博、阿佛到东京神田大雅楼吃饭,怕郭沫若着凉,郁达夫在一家洋货店里买了一条骆驼绒的颈巾送给他;12月6日,郁达夫单独前往郭沫若家,两人在江户川大堤上“并肩而行”:“用着母国话谈着些无足轻重的往事。然而这在我是十年以来所未有的快活”;12月12日,郭沫若赴日比谷山水楼参加中央公论社嶋中雄作为郁达夫访日举行的欢迎宴会;12月16日,郭沫若应日本笔会之邀,出席为郁达夫举行的晚宴;12月17日晨,郭沫若往东京送郁达夫去京都,等郭沫若达到车站时,火车的哨子正响,“由三等列车赶过二等列车,在每个车门和窗口上都没有看见达夫,我还以为他是临时改了期。开动着的车子和我擦身过着,在最后的一等车的车尾的凉台上才看见了达夫。他一个人立在那儿,在向着人挥帽”。关于郁达夫12月6日单独前往郭沫若家的情况,笔者曾有如下推测:“一、郁达夫此次前来,一定是找郭沫若谈论非常重要并且极其秘密的事情,否则没必要‘断然拒绝’自己‘最崇拜’的佐藤春夫的好意,同样没必要‘要求到外边去散步’,结合郁达夫的‘在抗战前—年,我到日本去劝他回国’的说法可以知道,此次谈话一定与郭沫若归国问题有关;二、郁达夫劝郭沫若归国不是奉命而来,而是出于友情,并且是到日本后才决定这样做的,否则郁达夫不会说自己‘打算到欧美去游历’——一个奉命敦请别人回国的人是不可能说自己打算出国的;三、郁达夫和郭沫若的谈话纯粹是朋友式的、漫谈式的,不但郁达夫劝郭沫若归国,郭沫若也劝郁达夫‘与其为俗吏式的事物所纠缠,宁应该随时随地去丰富自己的作家的生命’。”
二
郁达夫1937年5月18日给郭沫若的一封信是了解郁达夫为郭沫若归国事出力情况的最为直接的材料,现抄录如下:“前月底,我曾去杭州,即与当局诸公会谈此事,令妹婿胡灼三,亦亟亟以此事为属,殊不知不待伊言,我在去年年底返国时,已在进行也。此事之与有力者,为敝东陈公洽主席,及宣传部长邵力子先生,何廉处长,钱大钧主任,他们均系为进言者。我在前两月函中,已略告一二,因事未成熟,所以不敢实告。大约此函到后,南京之电汇,总也可到,即请马上动身,先来上海。”根据该信可以知道,郁达夫“去年年底返国时,已在进行”。信中“年底返国”的情况为:郁达夫1936年12月17日离开东京前往京都,12月19日由神户乘“朝日丸”启程往台湾,22日抵达基隆,12月29日乘“福建丸”离开高雄告别台湾,12月30日抵达厦门。信中的“前两月”为3月。关于3月的情况,郁达夫在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同事蔡圣焜是这样回忆的:一天上午将下班时,郁达夫手拿一卷宗袋走到蔡圣焜办公桌前叫他代拟函稿。蔡圣焜打开卷宗一看,原来是绝密文件。一张是时任福建省主席兼驻闽绥靖主任陈仪写给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当时的院长是蒋介石)的信稿,请他向蒋介石请示可否允许郭沫若回国居住,另一张是何廉很快写来的复信,内云:蒋介石同意郭沫若归国,但不得有“越轨行动”,在福州居住由陈仪监视。郁达夫叫蔡圣焜根据陈仪手谕代拟一封便函告诉何廉:已经择定乌山路从前蒋光鼐任福建省主席所住私邸(已属公产)为郭沫若住所,并负责保护与监视。蔡圣焜拟好便函后交给了郁达夫,以后情况就不知道了。根据5月18日信可以知道,郁达夫应该将便函寄给了何廉,同时给郭沫若去了一封信,“已略告一二,因事未成熟,所以不敢实告”,此事最终不了了之。根据郁达夫的《回程日记》可以知道,信中的“前月”实为1937年4月28日至5月4日。具体情况为:4月28日,郁达夫从福建马尾出发,前往杭州参加航空学校毕业典礼,4月30日到达杭州。在接下来的4天时间里,郁达夫曾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国民党宣传部部长邵力子、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长由蒋介石兼任)周至柔等党政要员一起宴游。其中与钱大钧一起宴游的次数最多:5月1日,“中午约慕尹主任夫妇在楼外楼小饮,适逢力子先生自上海来,遂邀同席,至午后三时散”;5月2日,“晚上由绍棣作东,约慕尹主任夫妇在三义楼吃饭,饭后并去东南日报馆看演《狄四娘》话剧,至十时始散”;5月3日,“傍晚,钱主任约去王润兴吃晚饭,同席者皆航空健将,饮至九时左右,乃大醉”。尽管郁达夫在这几天时间里与这么多国民党高官一起宴游,但是在笔者看来,5月18日希望郭沫若尽快回国的“南京来电”应该与钱大钧没有关系,与邵力子则可以肯定没有关系。理由为:一、从郁达夫1937年5月1日的日记可以看出,邵力子只是临时参加,并非郁达夫事前邀请。在“小饮”过程中,邵力子完全可能出于礼节口头答应,但他没有必要因为自己口头答应了便来蹚这趟浑水,尤其是在西安事变之后——西安事变发生时邵力子是陕西省主席,蒋介石对邵力子在西安事变前后在西安的表现有所不满。二、根据何廉进言的原因可以知道,他是在蒋介石谈到“牯岭国事会议”时提到郭沫若的,属于他职责范围的事情。三、从郭沫若在《在轰炸中来去》中的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邵力子确实没有参与“进言”:“力子先生问了我回国时的光景,又谈了些宣传工作的情形,谈了有一个钟头的光景,才起身作别,我送他下楼时,他看我穿的是寝衣,生恐我着凉,向我关照了好几次。我觉得就好像见到了我的一位长兄一样。”如果邵力子进言了,在谈到郭沫若“回国时的光景”时,在谈了“一个钟头的光景”的情况下,他完全可以顺便提及此事。
在笔者看来,不但5月18日的“南京来电”与郁达夫活动的关系不密切,就是3月份蒋介石同意郭沫若归国也与“牯岭国事会议”有关:1937年2月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闭幕。会后,蒋介石接受了中央社记者关于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的提问。在回答集中人才这一问题时,蒋介石如此说道:“从政治方面说,中央十年以来,延揽党外有能力之分子,不知凡几。事实上对于民国十三年以前之各党派,早无歧视,更无排斥之意。尤其是对国内具有真实学问与爱国热忱之知识分子,与大学教授,更是虚心咨访,极意尊重,切望其在教育文化上、在政治经济各种建设上尽量贡献,培育有用之青年,完成建国之大业。所以集中人才一层,可以说是中央一贯之方针,今后必更进一步的期其充分实现。凡真正爱国而愿在同一目标之下为国家尽力者,自必与以尊重,且亦欢迎不暇。”次日,《大公报》以《蒋委员长发表重要谈话:中央尊重言论自由谈话集中人才致力建设政治犯悔过自新可予宽免》为题发表了蒋介石的谈话。很明显,郭沫若属于蒋介石所说的“具有真实学问与爱国热忱之知识分子”,所以,在蒋介石指示翁文灏、何廉起草参加“牯岭国事会议”的人员名单时,他们把郭沫若写了进去,蒋介石看见后说:“啊,好得很,我对此人总是十分清楚的。”蒋介石还问郭沫若现在哪里,何廉说1933年在东京看到过他,但不知现在何处。由此可知,何廉将郭沫若写进参加“牯岭国事会议”人员名单,是由于当时的形势变了:“中央尊重言论自由谈话集中人才致力建设政治犯悔过自新可予宽免”,而不是由于郁达夫的活动。陈仪给何廉写信,应该是陈仪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回到福建后,对郁达夫说起蒋介石的谈话以及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也有可能是郁达夫看见《大公报》,于是郁达夫请陈仪给何廉写信。如果陈仪参会时就对何廉说起过郭沫若归国事,那么,陈仪就不会在信中请何廉向蒋介石请示可否允许郭沫若回国居住,何廉也不会这样回信:蒋介石同意郭沫若归国,但不得有“越轨行动”,在福州居住由陈仪监视。由此可知,当接到陈仪来信前,何廉已经将郭沫若写进参加“牯岭国事会议”的人员名单,并且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所以,当接到陈仪来信后,立即前去请示并很顺利得到许可。
在1937年5月18日致郭沫若的信里,郁达夫还如此写道:“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属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我以奔走见效,喜不自胜,随即发出航空信一,平信一。一面并电南京,请先取消通缉,然后多汇旅费去日,俾得早日动身。强邻压迫不已,国命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外患,当系目下之天经地义,想兄必不致嫌我之多事也。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对兄有所表示,万望即日整装,先行回国一走。临行之前,并乞电示,我当去沪候你,一同上南京去走一趟。这事的经过,一言难尽,俟面谈。”为了郭沫若归国,郁达夫5月19日还给郭沫若的七妹夫胡灼三去信一封:“来函拜悉。扇面待空—点后再写。沫若事,已向中央说妥,取消通缉,并命即日来华供职。弟昨已有信发出,嘱中央多汇点款去。中央恐他疑虑,要我写信给他,我曾写去两封快信。你接此信,望亦去一快信,使他得安心回来。只说郁某决非卖友之人,可以回来矣。”尽管如此,结果却是:“郁君自福州亦曾有信来(五月十八日),唯所言事,以后迄无消息……”对此,郭沫若回国后曾问过郁达夫。郁达夫的回答是:电报是陈仪要他打的,自己也把郭沫若的回电给了陈仪,自己也不知道没有下文的原因。郭沫若在《在轰炸中来去》中的以下文字为我们提供了线索:“今年五月(按:当为农历),在庐山,和慕尹(按:钱大钧),公洽(按:陈仪),淬廉(按:何廉)诸位谈起了你,大家都想把你请回来。但关于取消通缉的事情,不免踌躇了一下:因为如果早取消了,恐怕你不能离开日本吧。”正因为如此,在6月23日向全国231位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各院部主管人员、在野各党派各社团领导人员、高等教育和学术界知名人士、新闻出版界人士、工商财界人士发出参加庐山谈话会的邀请函时,名单中没有郭沫若。所以,郭沫若归国事再次不了了之。
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抵达上海时,郁达夫前去迎接,其经过为:“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直接帮助了我行动的是钱瘦铁和金祖同。瘦铁在王芃生的系统下做情报工作,他曾经把我的意思通知当时在国内的王芃生,得到了政府的同意,他便为我负责进行购买船票等事项。祖同便奔走于东京与市川之间传递消息。当然大使馆方面也是知道情形的。一切的准备停当了,我于七月二十五日破晓离开市川,在东京和瘦铁、祖同取齐,乘快车到神户,改乘加拿大皇后号回国。祖同是一同跟着我回国的。在动身之前,我曾关照大使馆,请拍一电报通知达夫。因此我在七月二十七日到上海时,达夫竟从福州赶来迎接了我。”遗憾的是,等郁达夫到达码头时,郭沫若已经离开,于是立即赶往沈尹默所在的孔德图书馆。见面的情况为:“鼎堂进来了,他看见达夫,只是紧紧地握着手,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三
看看1937年7月21日写作的《归国谣·本意并序》便知道,抗战时期担任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将主任的王芃生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人物:“奉召赴西安陈事毕,旋请准辞职。以个人资格为攻心缓兵之宣传。并奉命续作观变审机之研究。于丁丑五月十五日成总合报告,推论倭祸难免,战机不出七月。嗣于六月十九日,由沪电牯岭,陈报倭即将发动。适卫戍司令部张外事股长将赴日本有所谋,过访问计。告以不如速赴平津侦察,即将有变!不两旬而芦沟桥祸作,皆不幸而言中。及读庐山谈话,知大计已决。归国以来,心如悬旌。至此始定。歌以颂之。”根据《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9卷可以知道,“奉召赴西安陈事毕”的情况为:1936年12月1日,“电召王芃生来洛”;12月2日,“电南京陈主任布雷、张部长群,告以请芃生兄即来洛陕一叙”;根据12月9日《华清池王芃生来电》可以知道,时任驻日大使馆参事的王芃生所“陈事”为当时日本的国内形势:“南京外交部并请转许大使。两电敬悉:。密。俟谒呈院座,彼议会开幕在即,内阁对交涉无法答辩,加以增税及安定生活与议院改革等难题,即政变预测所由起,因此对华不免恼羞成怒,似回到交涉初期空气恶劣时。馆电所预测,将藉故以海陆军进据要地,为现地保护或保障占领,一面在华北急煽浪人杂军作既成事实,相度内外情势,或将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而惹起正面冲突。现有此征兆否,倘我方此时除开华北防共及其他难题而故将轻易者作一小段落,使彼有词拖过,议会必所乐从。故答复川越备忘录之希望及其程度,已成目前我方决和战之一关键,拟即评呈请示,此时日情演变必速,请随时查察密示。”王芃生“奉召赴西安陈事毕”后,被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辛树帜请去讲演,所以西安事变发生时在武功,逃过一劫。根据王芃生自己写作的《归国谣·本意并序》可以知道,他“请准辞职”后,“以个人资格为攻心缓兵之宣传。并奉命续作观变审机之研究”,直到抗战爆发后的7月21日,国际问题研究所尚未成立。王芃生主持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成立时间迄今尚无定论,由此可知王芃生及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多么缺乏。
关于王芃生在郭沫若归国问题上所起的作用,陪同郭沫若归国的金祖同(殷尘是其笔名)写作的《郭沫若归国秘记》应该相对可信,现抄录于后:“我怂恿他(按:郭沫若)快把走的主意打定了,他叫我把这事到东京后和几个朋友去商量,使他怎样可以脱身;我当时就推荐叔厓先生,因为在几天前他曾同我谈起鼎堂先生回国的问题,他告诉我他在五月里回国的时候,在南京遇见了王某某,知道这时国内的国共合作的声浪已渐渐地高了,王某某在最高当局面前提起过鼎堂先生,后来,因为没有下文,又因他急急地要到日本,便请他在南京多住几天,等他上庐山去请示得到确实的消息后,再托他到日本去告知。”对该段文字,笔者现在的看法是:1937年5月15日,王芃生的“总合报告”完成后来到南京,请求何廉将其转交给蒋介石,两人谈到了郭沫若归国问题(更有可能是何廉在谈到“牯岭国事会议”时说起郭沫若归国事,因王芃生曾任驻日大使馆参事,愿意居间帮忙);5月17日,何廉在蒋介石谈到“牯岭国事会议”时再次说起了郭沫若归国问题并得到许可,于是于5月18日“电请陈仪就近征询达夫意见”;何廉得到郁达夫“请先取消通缉,然后多汇旅费去日”的回电后,将其相关情况告诉了王芃生,并说自己不久将前往庐山,届时将会为此事向蒋介石请示;王芃生于是告诉钱瘦铁,“请他在南京多住几天,等他上庐山去请示得到确实的消息后,再托他到日本去告知”;何廉到庐山后,与张群、钱大钧、陈仪等人谈到了郭沫若,都想把郭沫若请回来,但是,“关于取消通缉的事情,不免踌躇了一下:因为如果早取消了,恐怕你不能离开日本吧”,所以王芃生一直没有给回到日本的钱瘦铁去电报,钱瘦铁也一直没有去看郭沫若。关于王芃生为郭沫若归国事当面向蒋介石进言的时间,笔者曾有如下推断:“7月23日,王芃生在蒋介石召见自己时谈起了郭沫若,蒋同意郭沫若归国并愿意支付旅费,王芃生于是给钱瘦铁发电报并汇去五百元。所以,如果王芃生确曾为郭沫若归国事当面向蒋介石进言的话,那么时间应该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具体时间当在7月23日。”
郭沫若归国抗战不但是他本人的重大选择,并且可以据此了解西安事变前后至卢沟桥事变前后中国的内政外交,所以非常值得重视。对此,有兴趣的人除看看本文引用过的武继平、李丽君及笔者的文章外,还可看看笔者的以下文章:《郭沫若归国抗战缘由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9期)、《郭沫若归国抗战陈布雷“起了关键作用”考》(《励耘学刊(文学卷)》2015年第2辑)、《论可能考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以郭沫若归国问题考证为例》(《郭沫若研究》2017第1辑)、《“郭沫若归国谁相迎”相关问题杂考》(《郭沫若研究》2018第1辑)。这些文章当然不可能尽善尽美,但它们的作者都是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在研究该问题,而不是以讹传讹。如果有了新史料,至少本人愿意修改自己的观点(与发表时的文章相比,本文中的个别观点便有所修改),这便是笔者至今尚未将自己的这些文章结集出版的原因:由于郭沫若曾经写作《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并且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他的归国要得到蒋介石首肯应该是肯定的,笔者想看看蒋介石原始日记中有无相关记载,然后再结集出版。就本文所写三件事情而言,第一件基本可为定论,因为有档案材料为证,第二、三件缺乏核心问题的档案材料,所以仅具可能性。在《郁达夫1936年底的日本之行与郭沫若归国关系考》中,笔者以回忆材料为主考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郁达夫此次赴日目的不是奉命敦请郭沫若归国,而是到日本后看见郭沫若的情况后才临时提起。”看看武继平、李丽君分别根据日本外务省解密官方档案写作的《1936年郁达夫访日史实新考》《郁达夫1936年访日新史料》可以知道,笔者的推断是正确的。尽管有着成功的案例,笔者仍然不能肯定主要根据回忆材料推断的第二、三件事的结论完全正确,所以只能说具有可能性。在笔者看来,在这些文章发表之前,吴基民不断炒自己的冷饭还情有可原,因为他有可能不知道相关情况;在这些文章发表以后,正确做法应该如其他作者一样不再老调重弹。遗憾的是,吴基民却继续炒自己的冷饭,这就不可原谅了:如果因为不了解研究现状而炒冷饭,笔者想问的是,在写作之前,难道不应该了解一下研究现状么?如果看过这些文章还要炒自己的冷饭,笔者想奉劝一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