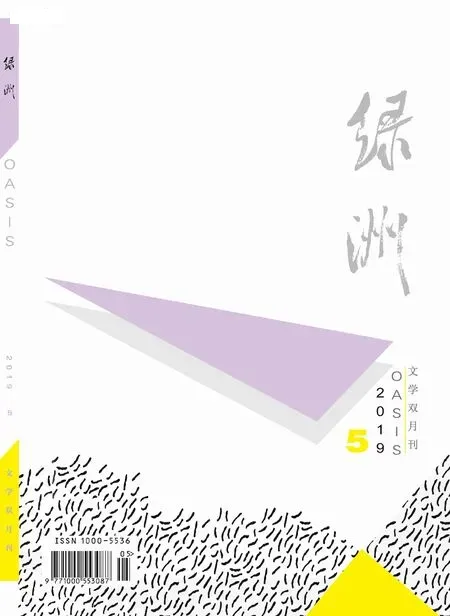时光之门
段景
一
1983年的秋天沉郁深长,这一年我哥十八岁。在北亭农场,那时候我们的家只有两间平房,家里四口人明显不够住。我和爸妈挤着睡在里间,我哥住在外间,他住的那一间屋子兼具客厅、餐厅的功能,吃饭的时候,我们一家围坐一张八仙桌。他的床紧挨着餐桌,也是狭窄的单人床。桌子的左手边摆放一排简易沙发,沙发是请农场里的木工师傅做的。沙发的拐角处是炉子和火墙。而我逐渐长大长高,这意味着我需要离开父母的房间,需要有一间单独的房子。
在那时候,盖房子不是一件小事,酝酿了有一年之久,哥哥开始实施这项对他来说有些复杂的大计划。他白天在青年连上班,那几年青年连的主要工作就是修北亭农场的公路。每天的下午时间,他就开始筹备盖房子的事。他去我家院子对面的荒地上挖了一个大坑,将坑里的土挖松,用水泡上泥土,饧上两天,就像发面的时候需要饧面一样。两天后,水泡的泥土饧好了。他将麦草撒到泥上,让泥土和麦草融合,不断地用手把泥土混合成一个一个泥团。我家的院子和那个泥坑中间是一段马路,他把泥团运送到靠近院子的路边。当年九岁的我,看着我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有些担心,那些未知的困难像一团雾一样困扰着我,对我哥能否盖成一间房子,我有些担心。路边林带里的杨树不太粗壮,灰白色的叶片被风撩拨得啪啪响。空气中会有一些百无聊赖的气息,那时我感觉盖房子是一件漫长的工程,而之前的筹备工作也有了焦灼和深沉的意味。我坐在林带边的土埂上发呆旁观,哪怕是最微小的犹豫和怀疑,都能改变盖房子这个决定,但心底里还是希望房子能够盖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让阳光透过窗帘,坐在书桌前写字读书,那是九岁的我心底最为渴望的,这意味着我将有了一片独立自由的天空,那时会有恣意的云朵漫游其间。
哥哥开始最核心的工作就是打土块,他用一个木制的模具,将泥团放进模具填满压磁实,模具一次能承两块泥团,我看着他有些费力地把模具抬起然后迅速地扣下去。恰好有一只蛐蛐从此地经过,它匆匆忙忙地走过泥坑,沿着模具的边沿小心翼翼向前行进,可是蛐蛐脚底一滑,跌进模具里的泥团沼泽,随着它的身体挣扎越陷越深,陷落到比黑暗更深的深处。打好的土块都要经过晾晒,阳关将它们晒得干透。如果恰逢一场雨,就让人心烦了。雨从天空飘下的时候,老天并不知会你一声,一如风的任性,说来就来的雨并且会越来越急。我和他忙碌地在院子里找到塑料布、油毡布之类的东西覆盖到土块上。反反复复地经过四个多月,打土块的工程总算完成了。
第二年的秋天,我哥约上他的两个兄弟,开始挖地基,砌墙。墙一天一天地在长高,今天的墙长高了五层,而我明天再去看时,它又缩减了一层。如此反复,折磨着我的耐心。这是一项巨大而漫长的过程,我的耐心逐渐消磨成了漠然。我依然像个旁观者,从房子旁边经过穿梭。哥哥建房过程缓慢但未曾停歇,他在盖房子的间隙,也抽空去别家的院子看一看,他在计算窗户的位置,或者怎么出房檐。都是第一次,难免手忙脚乱,首尾难相顾。这项工程终于到了尾声阶段,就是给房屋上梁。房顶上的人用绳子将木头拉上去,放到适宜的位置,然后用树枝和麦草交错覆盖。院子里,哥哥穿着黑色胶筒,踩在麦草和泥土混合的泥团里,他用耙子将泥巴混合,将铁锹铲起草泥扔到房顶上,房顶上有人最后将草泥抹平。房子就快盖好了,可我们还要等待一扇门。
后来我哥他在乌市五建朋友家的院子里,看到一扇铁门刚好用的上。朋友答应把这扇门送给他。但如何将这扇门运回来,他颇费周折。那天他坐在公路边等着便车。夕阳很快落下来,天空暗下来,等待的时间漫长,心情也黯淡得如同昏黄的灯火一般。当一辆深绿色的解放卡车远远地驶来,在他眼里如同行驶过来的希望。他快跑着冲到路中间,张开双臂拦车,车终于停下来。在他百般恳切的诉说下,司机师傅好心同意帮他拉门回家。回到北亭农场的时候,天完全黑下来了。我哥把门挪进院子的时候,我和父母刚吃过了晚饭。炉子里火委顿了,只有残存的火星透着余温。
我住进的那间新房子,正午的午睡时分,偶尔就能听到一只蛐蛐的鸣叫,它是陷落在泥团沼泽的那一只么?我们每天感受和接纳的阳光是一样的,温暖簇新的时光是一样的,他们漫过时间的流水不断延伸向前。
我从那个院子里退出来的时候,那扇时间的门刚好已经关上。我注意到哥哥续建的那间房子,靠近窗户的墙面有一些倾斜,窗台上留有一个小铲子和一些干瘪的葫芦籽。院子里有一些衣服晾晒在铁丝上,萦绕在烟囱周围的炊烟还未飘远,一切都慢下来。而我想重新回到那个地方,回到那个已经不存在的院子里,收集一些风和阳光的喁喁絮语。
四十岁的我在回忆里搜寻这间房子和院子的时候,它们早已不存在了。父母先后离开我们近十五年,那个被称为家的老房子也已经被树木、花园取代。当年我哥在盖房子时,物质和金钱对我们家都是匮乏的,他所有用于盖房子的材料,都需要自己去大自然里寻找并创造。一块土块,一截木头,一块砖头,一些麦草,构成这间房子的结构和肌理,它伫立在那个泛黄的八十年代,为我们遮风挡雨。然后就请阳光进来吧,一束光照在书桌上,照进我的童年时光。在我眼里这间房子的建造完成漫长而又艰难,它深刻地划进我的生命年轮,再也不会遗忘。
当那些过去的事物,阳光、空气、树木、云朵、甚至是呼吸的节奏,抑郁的黄昏,稠密的叶片,不断地冲击我的心,在现实的精神的空间里徘徊留连的时候,我欣喜自己已经打开了一扇过去的时间之门,在那里我看到了心灵深处所有珍惜的事物和留恋的人,他们在另一层次的时间和空间里活着。此时,划过阴沉的天空,有一束光亮照着他们。
二
1971年9月,母亲她坐在农场的那家老院子里纳鞋底,她身后的院子,四周围合着简单的篱笆墙,一些零星的牵牛花互相缠绕着盘旋而上。在微凉的风里轻轻地摇曳。这是她来到北亭农场的第九天。
她一边忙着手里的活计,一边在想心事。银色的顶针,随着她穿针引线的手,在黄昏的微光里熠熠生辉。她的心确实有些烦闷和惆怅。舅舅写信告诉她,让她来新疆的北亭农场。说是这边给她找了对象,人老实有工作,就是年龄大些,比她大十岁,她来新疆后也能安排上工作。去舅舅家接她的男人,却让她失望了。男人沉默地坐在那里,灰白的头发稀疏,眼睛细长的倒是很温和,身材瘦长。她就这样目测了一下,就知道这个男人比自己大不止十岁。在后来的日子里,母亲才确切地知道父亲比她大二十岁,并且是不识字的文盲。她从自己的老家辞去小学老师的工作,来到这偏远的农场,找到这样一个男人作为归宿,心里总是不甘的。
1979年5月,母亲带着我去连队里的戈壁滩捡柴火,父亲在后面推着拉拉车(手推车),那一年我五岁。农场的冬天屋子里都需要架炉子、烧火墙取暖,去年拾的柴火快用完了。干旱的戈壁滩上,遍布梭梭和红柳,春天的红柳花在荒漠深处怒放,她们自顾自地生长,恣意的树干有的匍匐在地面,有的旁逸斜出。我就在这红柳的花丛中闲逛,捡拾随便就能遇到的枯枝。父亲拿着砍刀,从梭梭树的根部砍断,砍下来的枯枝条经过简单的捆扎,母亲把捆好的柴火放在手推车上。我穿着印着花朵的衣裳,追逐着风滚草,在风里跑。母亲就站在那里,远远地看着,我跑到了记忆的岸边。母亲的黑发辫依然,时光静止了,风还在吹着远远的炊烟,从天边漏进来的微光照着父亲弯下的脊梁。我就这样安静地看着,记忆深处母亲的目光回望着我,望见我的戈壁、沙漠;望见老房子屋顶的炊烟轻轻地飘散,望见沙漠深处的一朵红柳树花开了又花落。
1990年8月,那一年我在阜康县城上高中。高考落榜,那天我独自一人拿着行李回家。此时的我就像被梦想抛弃的人,原本想凭着高考之路进一所大学,从此可以远离农场,但是这个梦在这一瞬间碎了。我拿着行李沮丧地走进院落,母亲坐在院子里正在缝补一件衣服。母亲并没有责备我,她放下手上的活,看了我一眼,平淡地说,明年再考吧。这一句不经意的话,似乎在安慰我。我进了里间屋子,把头埋在被子里,像被解脱了一般哭起来。
多少年以后,我依然想回到那个黄昏。我曾经想奋力逃脱的地方,竟然回不去了。而那个在夕阳里缝补的母亲,把我的旧时光用秘密的线连缀起来,固执地出现在我一场又一场的梦境里。她温暖的目光不断地回望着我。而我曾经执着地想远离的故乡,被记忆的线牵扯着,月光如水,漫过那条小渠,让我停靠至光阴的小站。
父亲去世十六年,母亲也去世了有十年了。当我三十而立的时候,真正体味了孤独的滋味,亲人们远离了我。而我只能在梦里寻找他们的影子。我虚构了这样一个梦境。2015年9月的午后,母亲她在院子里喂鸡,父亲把一蒸笼馒头架到锅上。炉子里的火烧得正旺,父亲用那双苍老的手不断往炉子里续柴火。三岁的女儿,拿着几片苜蓿叶子伸向鸡笼,遥远的鸡鸣叫醒了春天里的花,摇摇摆摆学步的女儿,走过晨光下的小桥,母亲的目光回望着我,不断地投向外孙女的身前或身后。女儿一会又会粘着父亲,摸摸他的脸和胡子,她说胡子扎扎。我转身走到时间的门外,看着他们,我的笑里藏着伤感的泪水。
我试图隐藏自己,却被抛在了回忆的河流里。孤独地漫游在这个世界之外,只有我知道,这是我用文字编织的一个梦,让我早已去世的父亲和母亲在这一场好梦里相遇,让他们在这里与他们未曾谋面的外孙女相见,在这个虚构抑或更真实的世界里,和他们的亲人一直相亲相爱,相守到老。
我站在时光的台阶上,月光凉凉地照着那个不变的镇子,他们在记忆的背后看着我,看着我们一起种下的树长高。看着我和亲人们在尘世的笑混合着泪。我让那些文字,紧紧地挨着,组成一行行温暖的句子,铭记那些泛黄的旧时光,那时母亲在清晨点燃的炉火还未熄灭,隔着光的布帘子被她轻轻地卷起,而我无法越过那道窗,我向着时光之外的你们伸出手,此时我的掌心握不住一粒发光的尘埃。
三
院子外面的林带里,衰败的杂草之间,一些新鲜的绿芽冒出来。春天已经在荒芜深处酝酿了很久,空气也变得暧昧潮湿起来,一些生命的芽在暗处延伸和展开。
冬菜都储藏在菜窖里,那个储藏菜的城堡里,土豆被排列在菜窖尽头,胡萝卜也可以紧挨着它们。白菜很白,是蔬菜里面的胖子,它们被围拢着紧紧挨在一起,在土地的深处依偎相伴在一起。小时候,我个子不高,胆子也小,并不敢独自下到菜窖的黑暗之处。我只是在菜窖口的上面,探着头往下看,母亲在里面将一棵白菜或一兜子土豆递给我。我接过菜,安静地等待母亲从菜窖口的木梯子上爬上来,那时她的头发依然乌黑,攀爬的动作也熟练和从容。我终究也想像不出有一天衰老会爬上她的额头,白发会从她的青丝之间秘密生长。
父亲常常在马圈里忙碌,北亭农场里三十多匹马都集中圈养在这里。父亲即使回到家里,他身上也有草料和马圈里的味道。春天里,天气暖和起来,马圈东侧尽头值班的房子里也不用架炉子了。父亲在忙碌着准备草料喂马时,我在房子里休息,有一副马鞍挂在墙上,侧面墙挂着一盏马灯,父亲晚上喂马时用它来照明。那些马儿咀嚼玉米粒和油渣时清晰的脆响声,在我的耳朵旁汇聚成一曲美妙的音乐,听起来那么妥帖和满足。即使过去三十年那些声音和气息依然深刻地印在心灵的某个角落,如同一粒秘密的种子一般,它们在暗处悄然生长,滋养着我的情感和语汇,让我在词语的森林可以随意采撷,并在某一个春天复活,那些回忆被我的语词延伸蔓延开来,攀上春天的枝头;那些被春风催醒的柳条牙尖,飘扬不散的杨树花絮绵绵不绝。在回忆的深处,打捞出来的旧物,还安静地放置在原来的位置上,一束马灯的微光穿过时间的河流,照着墙壁上那一道缝隙的暗影。
春阳斜照,时光再长,我的个子逐渐长高,也敢独自下到菜窖的深处。一个冬天过去后,那些放在菜窖尽头的土豆和胡萝卜根部都冒出了新芽,好在附近的菜园里已经开始弥漫着绿茵茵的生机,不久以后,就能有新鲜的蔬菜成熟起来。我看着这些土豆的小绿芽,竟然萌生出一些怜惜的爱意。有多少未知的事物在黑暗里生长,春天里万物都在苏醒,即使藏在黑暗深处的一只土豆,也用它生发的新芽,发出它对春天的回应。
距离我家菜窖不远的地方,是隔壁李家的菜地,菜园里的蔬菜长势喜人,那些逐渐浓郁的绿慢慢地从菜园里漫溢出来,李家的菜地也在朝着更远的方向生长。有一天父亲去菜窖边,看到李家的菜园又悄悄向前延伸了几十米,慢慢逼近了我家菜窖的边缘。父亲没有下菜窖拿菜,就返回了自家的院子。我很少看见父亲生气的样子,在我眼里他总是沉默着忙碌,喜或怒很少能从他的表情里感受出来。但那一天他真的很愤怒,他开始在我家院子里靠近李家窗户的下面,深挖地面。母亲问他,做什么呢?他也不说话,一锹土和另一锹土挖出来被他不断抬起的手臂扬到高处。我给母亲说了父亲生气的由来,李家为了扩大菜园的面积,菜地的边界快要挨着我家的菜窖了。以后他家的菜地一浇水,我家的菜窖肯定要塌了。这件事最后在我们的劝说下,父亲也没在李家窗户下挖菜窖了。李家的菜园也退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我和李家孩子依然在一起上学,在李家的窗户下面玩髀矢。
冬天的时候,每家窗户上都安装了厚的棉布帘子,为了挡风。李家一间屋子的窗户在我家院子里,同样,我家的窗户在他家的院子里。每天清晨,我比早起的阳光晚一些,卷起李家的棉窗帘。李家的二儿子是我的同学,他也会卷起我家窗帘。我们每天卷窗帘这个动作越来越娴熟,配合也越来越默契。每天照进屋子的阳光,越来越同步,而我们的友谊也越来越紧密,不用打开窗户说话,只要轻轻敲三下墙壁,就定好了出去玩耍的约定。以至于到了后来,我们一同长大到十八岁的年纪,隐约听说李家二儿子有了女朋友,我莫名地感到了失落。那些两小无猜的时光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父亲工作的马圈西侧的院墙下面有一堆麦草,那里曾是我们玩耍的地方。三五个顽皮的孩童从墙头跳下,跳进麦草垛的漩涡里,进入那个童年时光的漩涡里。我回头看见那个还是年少的我,在温煦的阳光里,被风吹乱的发辫上,还挂着一些草屑。我的小伙伴们都远去了,而我一直留下来躺在草垛上看云。那时候天空高远,变幻的云朵流动着,自然里的万千形态,被云朵这支笔轻易的描画,我的生命中那些消失的年月,在记忆的空间里继续生长,在我凝望天空时的瞬间被筛选下来,那些被选择的时间流过记忆的沙漏。
那个跑过树林,渠沟,摸过鱼,玩过泥巴的我,就留在一卷昏黄的时光胶片上,我听见那只老旧的胶片机艰涩地旋转,那部老电影的主角竟然是我。农场里的房子都是六十年代建造的平房,那时的房顶都修建成圆拱的形状。原初时,一排房子就是十户人家,中间没有院落的分割。孩子们可以尽情地在门前奔跑、玩耍。后来每户人家都会添丁,增加人口。每家每户又延伸搭建出房子,最后每家围合成各家的院落。那些落地的新生命,那些在院子里奔跑嬉闹的娃娃们和院子外面林地里的树一起长高长壮。长大后我们都想尽力挣脱出这个农场,为了去更广阔的天地。我们没有想到重新回来的一天,那些留在年少时光的自我,再也追不回来。那只记录时光的笔,用谨慎的语词写出一些模糊的意象,她想还原的人、事物,都被这只笔涂上了温暖的调子。两只麻雀站在院子外面的一截电线上,两个灰点逐渐靠近,抖了抖身上的羽毛。站在年少时光之外的我,闻见童年里那棵沙枣树的花香。那种花香比别的香味浓郁,那些像星星一样的花朵,把昏黄的月光涂亮了。春天的雨还没有下来,隐藏在云层后面的雷声,将天空的蓝压低了。那些在柳条上恣意生长的牙尖,带着一些新鲜的味道,生长的力量沿着根脉探入土地的深处。
我不知道我家的菜窖里,没有被取出的那些土豆,萝卜最后去了哪里,它们在黑暗里延伸的根脉向着虚无的更深处,那个储藏菜的城堡消失了,而那棵蔬菜新生的根芽却在我心里慢慢地长,它们一点也不着急,从星星点点,长成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我心里复原出一段完整的童年生活,包括院子门前那根电线杆的位置,都分毫不差。我在门前两棵榆树上搭上了绳结,我坐在那个春天的秋千里,身体飞起来时看到云朵很低很轻很软。脚下的水渠里,有清澈的水流慢慢流过岁月。那棵榆树上被打过节的地方,是不是有些疼,树木的那个位置明显比别处粗大,那是因为我为这棵树留下的疤,它感觉到疼痛的时候,会记得那个懵懂的少年么?
我看见屋子里,清晨的微光照在母亲黑色的头发上,她拿着木梳在梳理头发。手上有一些皱纹和沟壑,那些劳动和时间磨砺留下的痕迹。我看见母亲把一侧的头发分成三股,她将三股头发绾过来又绕过去,那两条长长的黑辫子,是我记忆里反复出现的梦境,那个梳头发的母亲就坐在镜中。那个年轻的背影,被青丝缠绕的女人还未老去。这样的隐藏着蓬勃的生命力的影子,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温暖着我。这是我怀念母亲的特殊的方式,仿佛她从未离开我,从来都没有在我的生命里消失过。
在父亲马圈尽头的屋子里,我沉浸在美梦里,我依稀看见那盏马灯昏黄的光晕里,父亲在给马儿喂食夜草。那匹红棕色的马头高扬,身上的毛色油亮,它深棕色的眼睛沉静如水面。在它嘴里咀嚼油渣、玉米粒混合散发出的食物味道,马的牙齿洁白,它摇晃着身体品味着食物的清香,品味着黑色静寂的夜晚。那些在夜里吃夜草的马,后来都长得越来越健壮,它们挺阔的身姿行走在农场的田间地头。我内心有一些小小的自豪和满足,那是我的父亲喂养出的马。
春天里,万物静默如谜,一些未知的懵懂的种子在土地深处,悄然地复苏并生长。它们撑开泥土的缝隙,时间的缝隙,努力地向上生长。我开始遥想一片麦地的金黄,和煦的风吹过,麦浪翻涌。那些在土地深处,种子的激情,它们无声无息在泥土深处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