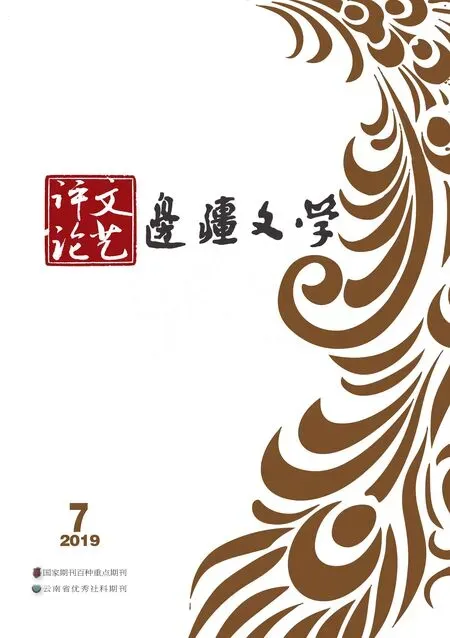当前云南摄影缺什么?
……………………………………………·朱运宽
“除了海洋和沙漠,地球上的地质地貌、自然景观,云南应有尽有”——这是云南旅游、摄影的“关键词”和“广告语”。云南不缺摄影资源。19世纪中叶以来,云南一直是海内外摄影家、探险家、人类学家、植物学家趋之若鹜的“秘境”、“隐藏的土地”。上世纪90年代,由于省文联、省摄协先后与石林、元江、大理、丽江等四个州、县联合主办了四届国际旅游摄影艺术节,云南率先被东南亚摄影家称为“摄影的天堂”。这一时期,云南本土摄影也曾出现了一次高潮:罗锦辉的《彩泉》1992年获联合国环境署“人与自然”金奖 ;陈安定的《血缘》1995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家庭年”影赛金奖;吴家林《云南山里人》(组照)1997年获美国“琼斯母亲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堪称出现了“《山茶》人文地理摄影现象”;云南的《山茶》杂志于1990年代改版为《山茶—少数民族民俗实录》,图文并茂,成为最早走“人文地理”路子的杂志;《山茶》杂志坚持 “第一手亲见亲闻”的理念、形成了有云南印记的 “记者的敏锐、学者的内功、作家的文笔、摄影家的图片”的办刊风格和海内外作者群。《光明日报》摄影美术部主任徐冶生前多次说:在上世纪80、90年代及本世纪初,当时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大地》、香港的《中国旅游》等人文地理杂志,几乎每一期都有云南人文地理的内容。诗人于坚认为,现在全国人文地理杂志越来越多,证明当年这一批理想主义者的声音已被广为接受。2002年3月,时任《摄影之友》执行主编那日松,派了女记者吴欣还来昆明采访,后来在《摄影之友》花了8个页面发表了《你要做人文地理摄影师吗?——昆明人文地理摄影座谈》的记录。2003年8月,《摄影之友》又以《云南摄影的“爆炸现象”》为题,对云南摄影群体予以报道。2007年,为纪念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50周年而编辑的《开拓与发展—中国摄影论坛文选》,收入了《定格三迤情 镜头写九州——云南摄影事业发展巡礼》,对云南摄影发展予以了关注。
近十多年来,随着人民群众“大旅游”时代的到来和数码摄影、手机摄影的大普及,海内外的摄影人、观光客像水银泻地一样涌入云南大地。“地球是园的”,“秘境”云南如今很少有秘境、“隐藏的土地”已不再隐藏。云南摄影家“近水楼台先得月”资源优势已不复存在。许多拍摄云南题材在海内外摘金夺银、发表有影响的摄影专题的摄影家,却不是云南人。
在2004年第21届国展、2006年第7届中国摄影艺术节上,耿云生先后实现了云南摄影界在全国影展“金奖”、摄影“金像奖”的“零”的突破。2007年,云南取得了22届全国摄影展“两银一铜七幅入选”的历史最好成绩。但在近年来的13、14届两届中国国际摄影展中,云南摄影界“全军覆没”;在25、26届全国摄影展、15、16届中国国际展中,云南也只有一些作品入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这正是云南摄影的症结所在。
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云南为一个实例,分析其中起起落落的原因、寻找差距和努力方向,对云南和其他地区或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在频繁举办一系列大型摄影活动的情况下,云南缺少更多大作品,需要提倡摄影人的文化自觉,呼唤更多摄影精品、传世佳作的诞生。
党的十七大以来,“如何保持云南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力”,成为摆在云南全省宣传、文化界的一个课题,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为此曾展开了全省宣传、文化系统的大调研。2012年7月,中国摄影家协会制定了到2020年中国摄影发展的总体目标,提出要跻身于国际一流,中国摄影必须具备的12项要素之一是:“摄影各大门类的生产创作繁荣,创造出代表当今时代的经典作品和具有广泛影响的一定数量的一流精品”。(中国摄协:《2012全国摄影工作会议主题报告》)
近年来,云南的摄影活动、摄影事业虽然在较高的层次上又有较大发展,但发展与差距、机遇与挑战、动力与压力并存,创作上有数量缺质量,出现了四个方面不相对应、不相匹配的“四多四少”的状况。
(一)近年来云南大型国际性影展、影会活动多、影响大,但代表性、标志性的精品少;
“一多”:近七年来,大理国际影会已举办了七届、 “百名中外摄影家走进红河”采风活动在红河州泸西县举办、第7届及第9届国际民俗摄影“人类贡献奖”分别在昆明和香格里拉举办、魅力罗平国际摄影节、西双版纳“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哈尼梯田国际影展相继举办;改写了云南过去连两年一届的全省性影展都没有的历史,打造了有影响的摄影品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1年9月中旬,昆明市政府参与主办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民俗摄协举办的第七届世界民俗摄影“人类贡献奖”的颁奖活动,影展收到117个国家的摄影人投稿的4万多幅图片,评选出160组图片,在昆明举办的“人类贡献奖”展览堪称拍摄国家最多、题材最广、观众最多的影展;34个国家的获奖摄影家云集昆明,昆明摄协也同期主办了《云南表情》专题展。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战略规划助理总干事汉思博士撰文评价:此次在云南的活动,“这将是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少数民族文化力量和文化多样性的里程碑”。(见《第七届国际民俗摄影“人类贡献奖”颁奖活动指南》)2015年9月,第九届世界民俗摄影“人类贡献奖”展览及颁奖仪式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举办,这是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全球系列活动之一。
“一少”:近年在重大国际影展中获奖的不多;2003年,吴家林的代表作“拉家常1999成都”,被世界著名摄影大师卡迪尔.布勒松收入《布勒松的选择》影展及画册。该影展画册是布勒松亲自挑选从1888年至1999年间他欣赏的全世界85位摄影家及其代表作品。2006年,他的作品被列入世界摄影大师系列作品集-袖珍摄影黑皮书《吴家林·中国边陲》在法国出版。2014年4月,尹永宏的作品《尼泊尔小火车窗前的孩子》荣获第十届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2013)年度新闻照片肖像类银奖。2015年11月,尹永宏的作品《在沙漠中玩耍的孩子》获第十届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一等奖。2016年5月,昭通陈忠平、周雄、宋大明3位摄影家的作品在OPEN COLOR国际影展中分别获2金1丝带奖。
(二)单幅佳作、单幅获奖作品多,云南的单幅佳作当以数万计。而成组的、形成个人风格、连续长期追踪拍摄、个人辨识度高的作品或专题作品少;同质化、雷同化的拍摄现象较为普遍。
(三)摄影展览、影赛多,为参与某一区域主题、或某一行业、企业影展的作品多,但一些摄影人为这些影展所左右、放弃个人的追求去迎合评委的口味而拍摄,这些作品立足在拍好“一张‘沙龙片’”的基础上,作为实施个人长期的拍摄计划、具有思想深度和人类普遍价值的摄影作品或专题作品少。
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仅云南省、昆明市摄协与各州、市、县、企业合办摄影展览22次。这种每年频繁举办的摄影创作、展览活动,为每一个县都积累、建立了摄影、旅游的图片库。摄影是地理发现的“眼睛”,而地理发现是开发景点、推动旅游的先导。历史作证:云南的许多景点、热点、民俗都是摄影人最早发现、“第一时间”宣传出去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30年代杨春洲拍摄石林,他是海内外拍摄、宣传石林的第一人。上世纪90年代,先后500多位海外摄影家参加了四届云南国际旅游摄影节,他们诗意的表述是:“我们背着相机包而来,把云南的山山水水背回去”。云南摄影、旅游的五大热点:滇西北、哈尼梯田、滇东北、东川红土地、普者黑,都是摄影炒热的,其他如罗平万亩油菜花、轿子雪山、玉溪金柿美、秘境昭通、普洱茶乡;民俗活动如弥勒“祭火”、怒江“澡堂会”、哈尼族“十月年”“长街宴”“嘎汤帕”、元江“赶花街”、沧源“摸你黑”、墨江“双胞节”、楚雄“赛装节”、盈江“天灯节”、孟连“神鱼节”,等等,摄影都是宣传最早、宣传频率最高、覆盖面最广的艺术门类,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云南现有4个世界自然或文化遗产、1个世界地质公园、4个世界湿地、5个5A级及40个4A级景区、60个魅力小镇,都有数不胜数的精美图片。从滇西北的贡山县到西部边陲盈江县,都出版了摄影集或举办了摄影展。摄影与旅游“双赢”的“云南现象”已在全国摄影理论界引起了关注。
2010年,当云南发生百年未遇的大干旱时,近200位摄影人深入旱区,拍摄了1万多幅记录旱情、全民抗旱的图片,省文联、省摄协与中国摄协联合在线上线下举办了抗旱摄影展并编辑了摄影集,不仅配合了全省的抗旱工作,还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历史影像,其中有100多幅作品被中国博物馆、省档案馆收藏。2010年10月,省文联、省摄协举办了《开放的云南——摄影家眼中的桥头堡》展览并编辑了摄影集;我省摄影家拍摄的东南亚和南亚作品参与三届东南亚和南亚摄影展、参加西南六省区摄影联展,增强文化的辐射力、影响力,很好的配合了“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但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影展中,云南一批有潜力、有实力的摄影家找不到自己、被影展牵着鼻子走,云南摄影界整体的摄影水平与国际摄影水平,与国内广东、浙江、河南等摄影先进省份的差距正在拉大。云南摄影界要提倡“不在滇池边打擂台,要到天安门广场、到黄浦江畔显身手、到世界平台显身手”。
(四)采风、创作、联谊活动多,理论研讨活动少。
影友们相聚在一起、在交流“朋友圈”更多是相互讲好话,真心话、批评性的意见、建设性的意见听到的不多。一位哲学家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一省一地的艺坛比较可怕的状态是批评界的“无语”、“缺位”。一个诚实的、有追求和探索精神的摄影家对于理论界的沉寂就像处于一个寂寞的、令人窒息的环境中。我们需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评论人才、需要“挑战性的批评家”。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中提到了《浮士德》,十分有意味的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创新理论问题上也谈到浮士德,他写道:“如果在我们的思想里是一种心理上的完美境界或涅槃境界,那么我们就必须再叫一个演员上场,让一个批评家来提出几个疑问以便让思想再度活动;叫一个对头来注入一点痛苦、不满、恐惧或憎恶,以便感情再度敏锐化;这就是《创世纪》里蛇的工作、《浮士德》里梅菲斯维特尔的工作……”。(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梅菲斯维特尔帮助浮士德结束了灰色的书斋生活,把他变成青年,重新生活了一次。批评家的评论,就像在平静的湖水中投进一个石子,泛起理论、思辨、争鸣的“涟漪”。一个地区摄影创作处于“瓶颈”状态、一个摄影家的“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一个创作者的心理因孤独、封闭而造成的麻木、停滞的“超稳态结构”,都需要评论家来打破这种种的局面。
第二、在多层面、多样化发展群众摄影文化的同时,云南缺少更多摄影大家,需要呼唤更多有代表性的、标志性的摄影家的出现。
几年前,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现在有6千多万人用单反相机、数亿人用卡片机、近10亿人用手机在拍照;多年以来中国就一直是世界最大照相器材消费国,进入了“全民摄影”时代,仅中国摄协举办的一届全国影展就收到19万、国际展收到10万多图片,这种现象仅中国才有。云南省的一个县级的影展一般也能收到2、3千幅以上的作品。在影像爆炸的局面下,要建设摄影大省、摄影强省,需要更多有代表性的、标志性的摄影大家的产生。
中国摄影家协会制定的到2020年的总体目标的又一项因素是:“拥有世界级摄影大师和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摄影领军人物,以及众多高水平专业队伍”。(中国摄协:《2012全国摄影工作会议主题报告》)
从云南摄影队伍的结构分析,大体并存着四种层次:
(一)具有高水平的摄影“大家”。
摄影大家是能站在历史、思想的制高点上、学养深厚、跨越几个世代的摄影集大成者。他们对国内外摄影史,摄影流派、代表人物、代表作品有较深的理解,有较强的精品意识和自觉的摄影文化观念,经过数十年的执着创作,有一定数量的摄影作品、摄影专题、摄影集在国内外摄影界得到广泛认可,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少数职业摄影家、独立摄影人、自由摄影人,他们是摄影艺术的献身者。
(二)有一定专业水平的摄影家。
他们对国内外摄影流派、代表人物、代表作品有一定的了解,有较强的创作潜力、创作实力的一批全国、省、市摄协会员;以及因工作、职业需要的一批摄影师;他们热爱摄影艺术、创作勤奋,对摄影技艺十分娴熟,有一批自己拿得出手的摄影作品,在省内影展中也频频取得好成绩。
(三)“快乐摄影”的“发烧友”。
云南摄影人骨子里有“艺不惊人誓不休”精髓的不多,大部分仅停留在“快乐摄影”层次。如今,“大旅游”、“大消费”的时代,摄影的“四养”:“养眼、养肺、养心、养人”,使旅游式的摄影和摄影式的旅游已密不可分;这批“发烧友”为快乐、为友谊、为健康、为丰富充实生活而摄影。更多的“发烧友”流连于自我欣赏、自娱自乐的状况。
(四)一批爱摄影的名人、名家、企业家及领导干部。
诗人于坚出版过类似“照片背后的故事”的《暗盒笔记》,多次办过个展,在他的《众神之河》、《印度记》、《昆明记》、《建水记》等人文地理著作中,也可欣喜地看到他的摄影作品。对于大多数名人、名家及领导干部来说,摄影是一种生活方式,陶冶了自己的审美品位和情趣;他们很少参加影展,也很少发表作品,追求摄影过程的快乐。
专业性的摄影家与“快乐摄影”的“发烧友”之间的区别在于:
(1)拍摄题材、地点选择的区别
“伟大的风景是为平庸的摄影师准备的。”摄影家特别是摄影大家不是哪里好看就拍哪里,而是戴着“发现”的眼睛,去开垦摄影的“新大陆”、处女地;而“发烧友”更多是趋之若鹜地去拍摄影的“热点”、“焦点”,去热门旅游景点“打卡”。
(2)拍摄目的、方法的区别
文化自觉的摄影家心里清楚这张图片拍下来是干什么用的,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纪录类的摄影家一般是长期拍摄自己感兴趣的专题作品;“发烧友”到一个地方往往是为了拍好一幅或几幅打比赛的“沙龙”作品;摄影家追求拍到精品,“发烧友”拍到或拍好即可,能发微信交流、获得朋友点赞就满足了。
(3)个人风格的区别
在“拍什么”、“怎样拍”,在拍摄机位、使用镜头、取景构图、瞬间把握、后期制作、影像呈现、图片品质等方面,两者相去甚远。
(4)拍摄周期的区别
两者在摄影的终极目的不同,完成摄影作品、专题、摄影集的周期不同。摄影家通过长期拍摄一个专题,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大时代中国急遽变化的社会风貌、日常生活、人间百态。摄影的最高的呈现方式是出版个人专著。而摄影发烧友到一个地方往往只希望拍到几幅自己满意的“糖水片”。
(5)个人情感投入的不同
摄影家往往对拍摄的地方产生浓厚的、持久的兴趣,完成一个摄影专题需做大量的功课,拍摄需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深厚的人文关怀,因而作品凝聚着摄影家的生命气息和个人风格。
一省一地的摄影事业可以四种摄影状态各得其所、各美其美、和谐共存、共同发展。云南摄影“金字塔”的“塔基”越大、越牢固,“塔尖”也就越高。
然而,在“全民摄影”、“融媒体”、“自媒体”的语境下,每一个爱好摄影的人都应该有一个自我诘问 “什么是摄影”、“我为什么摄影”、“我选择成为什么样的摄影家”?你选择什么,你就是什么。“取法于上,仅得于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立足于创。我们应该呼唤、倡导摄影队伍多出大家,去实现艺术和生命的更大价值。
第三、在观念守旧、题材撞车、手法雷同的情况下,云南摄影缺少创新动力,需要呼唤艺术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足很有关系”。
(一)必须观念更新。
当今“读图时代”,影像无处不在;几年前,国外一本书上说,全世界一年正式发表的图片有15亿之多。文化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而摄影的纪实功能是最难出新的,拍摄梅里雪山有多少照片,有人说数十亿。10个画家同时画梅里雪山,有10种画法;10个摄影家同时拍梅里雪山,很难有10种拍发,如用接片、星轨、隔时摄影、多次曝光、日出日落加渐变滤镜等手法,至多是景别、影调、效果的差别。云南摄影人一般还停留在“见子打子”、“看山是山”的层次,要逐渐通过内心感悟、个人视觉、独特表现进入“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的境界;要打破依赖摄影资源优势、用“脚”不用“脑”、重复别人、重复自己的惯性思维。
一个人可以坚持一种风格拍下去,做到极致,也可以成功,如陈安定长期用中画幅相机、在农村家庭布光,拍高品质的一个个少数民族家庭。而作为一个摄影群体、有数千名会员的摄影协会,就需要探讨摄影语言表达的丰富性和摄影表现的可能性。摄影有多少创新手法;摄影和语言的可能性有哪些?
传统的摄影艺术强调“美有规律”,注重光影、构图、影调;强调有序、对称均衡、“黄金分割率”;现代、后现代艺术主张“艺无定法”,强调非传统、反传统,可以无序、不均衡、不对称构图。现代、后现代艺术注重“反向思维”、“逆向思维”;传统观念认为摄影应该用“减法”,现代、后现代认为可以用“加法”,注重前景的运用、强调此人物与彼人物、此元素与彼元素的关系;传统纪实摄影注重“决定性瞬间”、“典型性瞬间”,现代、后现代摄影可以拍摄“非决定性瞬间”、“非典型性瞬间”;现代摄影手法多样:慢门、红外、反转片负冲、复制经典、场景再现、延时摄影、后期制作、PS改天换地、新闻摄影与美术作品综合媒介、多媒介等等。传统的摄影注重宏大叙事、强调客观,而现代摄影注重细节、强调内心感受,表现上“以小见大”、“以景喻情”、“细节决定命运”。2007年,我省姜德同获22届国展的铜牌奖作品《还是一个好》,是他避开贵州摄影展盛大的开幕式,而拍摄了会场周边一位农村妇女背着一个小孩,给怀中的另一个小孩擦屁股的画面。
摄影人个体比其他艺术门类更需要投注时间、精力、体力、金钱。可以说,摄影队伍是一支最“三贴近”的队伍,摄影人可以说是月月“走基层”、月月“三贴近”;热爱云南、走遍云南的摄影人不在少数。但深入生活不是目的,走遍云南也不是目的,“出精品才是硬道理”。
(二)必须题材创新,避免题材撞车、创作同质化。
“集体无意识”是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之一。外国人有的一个人一生只做一件事、几代人只做一个行业,而云南摄影人喜欢“跟风”、“扎堆”、“一窝蜂”;哪个地方办影展,大家都一窝蜂去;围绕着几大热点,大家“扎堆”都去拍雪山、梯田、红土地。 徐冶说:“不要在一个地方拍一百张图片,要在一百个地方各拍一张图片”。“有摄影人的地方就有广东人”,在广东,谢墨去泰国潜海拍珊瑚礁,王琛赴非洲上天拍火烈鸟,孙承毅20年来拍遍世界雪峰,王石登世界七大高峰拍世界冰峰,蔡焕松10次去拍印度。广东摄影家拍摄的题材是最外向、最广泛的,我们云南除金飞豹外,摄影家中几乎没有人有这个条件。在艺术上,你“做不到鹤立鸡群,就要鸡立鹤群”,云南摄影的一大优势是人文地理摄影,这在全国一直是处于领先的、最抢眼的位置,在全国报刊发表人文地理摄影专题的在全国不算第一,也在前三位。云南独特的区位优势,比别的地方更容易去东南亚、南亚拍摄创作。
云南摄影界应处理好深挖本土摄影题材与“走出去”的关系。现大多数摄影家还在上班、工作,难以有整块的时间走出去拍摄外面的世界。哈尼族摄影家罗涵对哈尼梯田有特殊感情,在上世纪90年代去拍摄哈尼梯田数十次,一到星期五下午就开车直奔元阳、红河或那诺梯田,虽也拍摄了一些风光佳作,但辨识度、个人风格不高,他反思自己的创作,认为是创作上走了弯路。近10多年来罗涵、官朝弼深挖博大精深的哈尼文化“一口井”,到摄影人涉足不多的元阳县老勐、金平县农村深挖哈尼文化题材,拍摄、出版了几个立得住的专题。罗怀学的老家是金沙江畔的绥江县,在得知修向家坝水电站,沿江380米以下的集镇、景物将被淹没的情况后,从2006年开始利用节假日,返回故乡拍摄金沙江即将逝去的景物,2018年自费出版了摄影集《故乡》,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忆。
(三)必须手法创新,克服创作手法雷同化。
现在,“全民摄影”时代,给人的印象是什么题材都可以入画摄影,好像一切人都可以摄影,什么人都可以办展览,但“一流的资源要靠一流的创意来激活”;只有审美理想的闪电照亮自己拍摄的素材,图片才能成为作品、成为精品。
有一次,在云南民族博物馆举办“香车美女”轿车展的影展,我遇到云南个性鲜明的画家曾晓峰,请他一起去看,他看了几幅后,可以说是拂袖而去,他说:“整个展览怎么像一个人拍的”。一位著名摄影家也说:“云南摄影人表达的方式一个样,看云南一个人拍的照片,就等于看了100个人拍的”。
“拍什么”、“怎么拍”,如何创意、如何完成、用什么设备完成,就决定了一幅作品、一个专题水平的高低,这也是艺术家与“发烧友”的区别。有无个人独特的发现、有无艺术个性是技术摄影还是艺术摄影的分水岭;创意水平的高低影响着图片品位的高低。云南摄影家追艺的《云龙古桥》(组照)、宋宝耀及吴世平的云龙县城、诺邓村夜景,采用几小时曝光加闪光灯闪几十次沿途打亮建筑物的方法,把古桥、千年诺邓村和云龙县这么一个边陲小城,拍得美轮美奂,县里领导称赞这些图片“为云龙做了最好的灯光效果图”。王华沙的《影子—滇西抗日的老兵们》(组照),在后期制作技法上有新意,图片抠去了人物衣领、衣物等部分,仅留下一张张脸谱悬浮在黑底的背景中,一个个老人虽进入耄耋之年,目光依然炯炯有神,再现了当年抗战的那种正气、勇气。李自雄的《南方的情人》(组照)来自在滇越铁路上听到一个老人年青时在碧色寨火车站上见到一位城里来的姑娘,当时他对这个姑娘一见倾心;就这么一次偶遇,故事的主人公从此把这个姑娘想象成了自己的恋人,幻象到了乱真的程度,以至终生未娶。李志雄以创意与情景再现相结合的方式,聘用一个穿着中山装的土气的小伙子,抱着两个塑料女衣模特,在碧色寨车站拍摄不同的照片,表现了上世纪50年代这一啼笑皆非的故事。在这个展览进门处的白墙上,写了T.S.艾略特的一句话:“我们叫做开始的往往就是结束。而宣告结束也就是着手开始。终点是我们出发的地方。”这一句话对这组“观念”作品,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杜建明创意拍摄的《大理国际影会开幕式》,用了360度拍摄、后期制作完成的。孙红军用隔时摄影拍摄风起云涌的红河哈尼梯田。李雄春在接片拍摄大理“红龙井”、高空拍摄石林接片、几十张接片拍摄昆明建筑群夜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
(四)在拍好专题摄影作品上下大功夫。
近年来,云南摄影家在专题摄影方面也取得骄人成绩。杨长福60多年来拍摄滇池。杨干才、王毅夫妇五年扎根边境曼蚌村拍摄《蜕变》,记录了这个山寨从刀耕火种种植旱谷到水田的出现、从祖先居住的茅草房到住上了石棉瓦房、从世世代代用点“明子”照明到通电用上电灯、电视等的“蜕变”过程。吴家林拍了4个州市的摄影集、2015年72岁时又用23天拍摄滇越铁路,出版了《吴家林 走滇越铁路23日》;布雨青四年走遍长江拍摄《徒步长江》 ;2007年《解读云南的多维视野》13位云南摄影家联展在平遥及云南省博物馆展出;王艺忠长年拍摄《生活在“金三角”的人们》、《象奴》;陈云峰十多年拍古镇、古桥、古建筑;徐晋燕长期拍茶马古道;欧燕生长期拍少数民族题材;李跃波长期拍泸沽湖摩梭人、茶马古道;刘建明、董胜数年拍“金三角”禁毒;刘建明、黄国强长期拍摄农村集市;罗怀学长期拍布朗山;耿云生在完成《乌蒙矿工》之后又拍摄出版了《哈尼山民群像》;潘增良拍摄昆明公安、家乡抚仙湖、《城市化革命》,出版了《瞬间 昆明公安影像》;沈安波拍摄古镇;孙大虹举办了《毛主席是我们家里人》摄影展,并出版了摄影集。濮演拍摄布朗山和老挝、缅甸村民;李植森长期拍茶叶;许云华长期拍生活在佛教地区的人们;孙沁南长期拍摄大理民居建筑;《云南摄影家系列丛书》的 30位摄影家的作品出版;鲍利辉拍摄《临终关怀》和印度题材;马克斌拍摄欧洲;尹永红、阮卫民拍摄孟加拉专题;张缘子出版了《佤山纪实》等等,在云南,这样的摄影家为数不多。孙沁南说,6届大理国际影会的举办,推动了大理摄影界观念的转变,拍专题已成为圈内的共识和方向,2014年5月,大理摄协与上海华侨摄影协会交流时,有5位摄影家展示了各自不同的拍摄专题。
摄影家应该和作家、其他艺术家一样可以揭示深刻的社会问题,也可以表达与人性、与生活有关的主题。现全省有自觉专题摄影意识的摄影人不多,我们在提倡创作精品的同时,应引导、倡导广大的会员自觉投身到专题摄影当中。一个人拿出一、两张好的照片不难,但是拿出具有个人辨识度的专题就很难了。专题摄影是一个摄影人记录历史、记录大变革时代人与社会变迁的一种文化自觉,是一个摄影家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区分究竟是严格意义的摄影家还是影像生产者的试金石。有没有自觉的专题意识,或者有没有几本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专题摄影集,是摄影家与影像生产者、摄影匠人的一个分水岭,任何一个中外摄影家的名字都是跟自己的摄影专题联在一起的。
我们要在云南影像史上留下几幅图片或者几个摄影专题,就要有艺术“殉道者”执着的精神,“深挖一口井”,进行时间的积淀,量的积累,再到质的升华,所以我们要不抛弃、不放弃,耐得住寂寞。专题摄影在云南是非常有优势的。经过10年、20年、若干年的努力,每个人只要有这种付出,必定会在云南影像史上留下一些精品。
(五)关键组织、成事在人,造就省、州两级高层次领军人物和云南多梯次、多世代、高素质的摄影队伍。
要推动云南摄影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应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思想。现昆明、玉溪、曲靖、红河、大理、昭通、西双版纳、迪庆已形成摄影群体,有代表摄影家和一批代表作品;普洱、德宏、临沧、保山也开展了很多摄影活动,聚集人才、锻炼队伍。
徐晋燕曾说过河南人是靠“头”(指思索、创意)摄影,云南人是靠“脚”(指寻找、行走)在摄影。云南摄影界应在实践中进一步造就省、州两级高层次领军人物和云南多梯次、高素质的摄影队伍。领军人物应该熟悉世界摄影创作的流派、风格走向,站在全球、全国摄影文化的的思想制高点上,来观察、分析、指导本土的摄影创作,他们应该既立足本土,又放眼天下,有较深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创作经验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及奉献精神。要造就一支风格各异、阵容整齐、多梯次、高素质的摄影队伍;近20多年来,一直担当云南摄影主力的40后、50后、60后的摄影家,年轻的都已经50多岁了,相当一批创作的高峰期已过,他们有的身体欠佳、有的家庭负担重,年轻一代有一些摄影佼佼者,但更多的青年摄影爱好者在为房子、车子打拼,立志终身摄影的不多,摄影队伍“青黄不接”现象严重。我们要造就一大批摄影人,这些人既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既能爬大山出大力流大汗,又能勤于动脑善于思索勇于创新;既懂艺术,又懂技术;既行万里路,又读千卷书;既能前期得心应手拍摄,又能后期游刃有余创意制作;要呼唤摄影理论人才的脱颖而出;还要呼唤、造就一批既懂艺术,又善于经营的复合性人才,搭建摄影作品与文化市场的桥梁。
更多的精品佳作理应出自本土摄影家之手,然而,近年来,外地人、外国人拍摄云南题材的作品在全国、全球获奖的比比皆是。几年前,我参加了昆明摄协与广东顺德摄协的交流活动,广东在中国摄影界是“摄影强省”,在中国摄影展览团体总分有“六连冠”的好成绩,在与广东摄影家的广泛接触中,我再一次感到我们云南摄影人在摄影创作理念,题材的开放、外向型观念,对器材的精通和后期创意制作的娴熟等方面有很大差距,这制约着我省摄影的发展。艺术交流不能在一个封闭、单一、“近亲”的环境中进行,我们应创造条件,“走出去”、“请进来”,在更多样、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中外艺术交流。著名摄影家吕楠在昆明客居18年,他的摄影理念及对世界摄影文化的了解,对昆明摄影圈影响很大。著名摄影家李泛对曲靖市摄影协会的工作给予很大的帮助,尹永宏取得的成绩,与李泛的指导分不开。
在图片泛滥的当下,大浪淘沙,经历史、人民的检验,最终留得下、传得开的才是精品,这不是少数人说了算、也不是一时的知名度所能决定的。现在摄影越来越难拍,就在于摄影的门槛太低,拍照的人太多;现在摄影越来越难,难就难在一个摄影人能留下的作品少之又少。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目前艺术创作有“高原”缺“高峰”的论述,我有一次深刻的感悟:2014年12月,云南省政协书画室组织特聘艺术家学习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到剑川县采风,我一人爬上了剑川的“千狮山.满贤林”山顶,受到了深刻的启示:“千狮山.满贤林”岭高箐深、怪石嶙峋,石雕艺术家们依石岩的形状雕刻成或立或蹲或站的狮子模样,爬山时,体现我国9个朝代的、大大小小的3,200多个不同风格、不同纹理的石狮子因地制宜、随山就势分布在山箐小路的两旁,我多花了近两个小时,一个人爬上山顶,看到雄踞在山顶的、世界上体积最大的狮王,这是一个有意味的意象、一个有启示象征:顶上的“狮王”象征艺术的“高峰”,而遍布山腰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狮子好像艺术上的一个个“高原”;“狮王”在最高峰,我们有志气、有抱负的摄影人,要脚踏实地,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的高峰,才能看到无限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