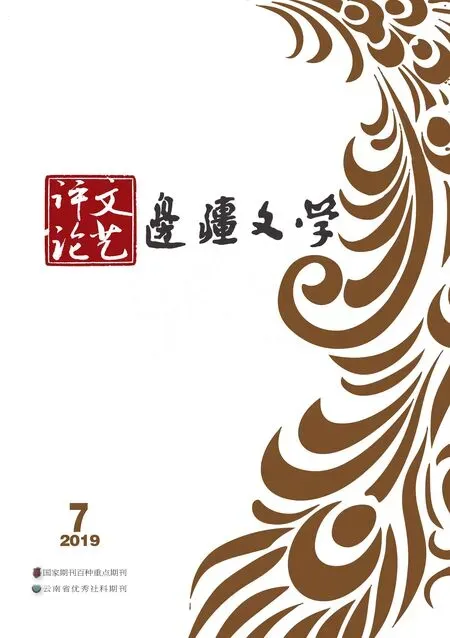民间文学中的家国情怀
——云南各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感初探
……………………………………………·于凤麟
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因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深层的基础。冯天瑜把文化认同解释为一种肯定的文化价值判断。即指文化群体或文化成员承认群内新文化或群外异文化因素的价值效用符合传统文化价值标准的认可态度与方式。经过认同后的新文化或异文化因素将被接受、传播。
民间文学是以面对的口头传播方式,在特定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时间里,由群体创作群体传承的一种文学样式,她与族群日常生活融为一体,成为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产生于原始社会的精神民俗,迄今存活于云南各民族的民间口传文学,因其原始性大都具有原生形态的天然特色,从这类原始文学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族源神话、人物传说,还是祭祀歌谣,其讲述内容大都反映出与中华文化存在的天然联系,而这种从文化上作出的阐释与价值判断被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
云南各民族民间文学中的文化认同,主要体现于四个方面:
一、民间文学,多元文化的交融与整合
民间文学是人类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云南各民族民间文学中所反映的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与其历史文化息息相关。
云南的26个民族交错聚居于这块山峰耸峙、江流奔腾、大小坝子星罗棋布的红土高原上。早在远古时期,云南就和内地有着密切的联系。到战国时期,楚将庄乔入滇拉开了开发云南的序幕,秦开五尺道置吏,至汉代已正式在云南设置郡县。从可以考证的历史来看,云南早在新石器时期便有了氐羌、百越、百濮三大族群的活动,氐羌族群发源于甘青河湟地区,其中一部分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华夏族,其余部分则在西南地区形成氐羌族系的各个民族。氐羌文化具有西北内陆文化、黄河流域文化的特点。氐羌系各民族中流传的火的传说和对虎的崇拜即是例证。另一个族群是以“魋结”“断发”为特点的百越族群,即今日的傣、壮、水、布依族的先民,古书称“编发之民”。他们的先民来自东南沿海工。至今保留有水文化、蛇图腾、纹身等习俗。百越文化呈现出鲜明的东南沿海以及太平洋文化圈的特点。属于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的佤、德昂、布朗族是古代的百濮族群。百濮族群自古与老挝、越南、缅甸跨境而居。他们以种茶、木雕而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德昂族至今流传着以茶为民族的独特的创世神话,佤族以木鼓、石洞为神圣之物,可以看出百濮族群如今所保留的习俗就是他们先民的文化象征。在偏远的云南,历经2000多年的沧桑,汉民族逐渐成为主体民族,汉族进入云南,它的文化、生产科技当然也传播到了云南。唐宋之后,苗、瑶、蒙、回文化也进入了云南。
把云南文化放到一个更大的范围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云南文化处于多种文化的交汇叠合的区域。云南文化处于中原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的边缘.又是中华文化与东南亚文化,西南亚文化,乃至印度文化的交汇点。这一文化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则属于太平洋文化圈。
不可否认,虽然云南文化与上述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又相对封闭于一个交通不便,信息隔阻的环境之中。从民族看:除回族,蒙古族进入云南较晚,其它民族主要由古代的氐羌系民族、百越系民族、百濮系民族这3大原始族群在迁徙,流动中不断分化,融合而来。各民族之间互相交错,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总体格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交错的文化土壤中,积淀于民族心理中的文化共识与文化归属,通过集体无意识的民间文学得以表达、流传与发展。
二、族源神话,来自同一族群的身份认同意识。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上,人们的血缘意识极强。来自同一民族、宗族或家族的身份认同和源于同一社会群体的文化共识,历来是连接各色人等的最强有力的纽带。
在云南各民族中,普遍流传着民族起源同一的神话,把不同的民族视为同祖的兄弟,自己是各民族兄弟中的普通的,甚至是略为弱小的一员。这类神话又通常是接在洪水泛滥、兄妹成婚繁衍人类的情节之后讲述。彝族神话史诗《梅葛》讲格兹天神因人心不好,要换人种,使洪水泛滥,只剩下兄妹二人。后来兄妹成婚,生下葫芦。天神用金锥、银锥开葫芦:“戳开第一道,出来是汉族,汉族是老大,住在坝子里,盘田种庄稼,读书学写字,聪明本领大。戳开第二道,出来是傣族,傣族办法好,种出石榴花。戳开第三道,出来是彝族,彝家住山中,开地种庄稼,戳开第四道,出来是傈僳,傈僳力气大,出力背盐巴。戳开第五道,出来是苗家,苗家人强壮,住在高山上。戳开第六道,出来是藏族,藏族很勇敢,背弓打野兽。戳开第七道,出来是白族,白族人很巧,羊毛赶毡子,纺线弹棉花。戳开第九道,出来是傣族,傣族盖寺庙,念经信佛教。出来九种族,人烟兴旺了。”
傈僳族的神话在洪水泛滥和兄妹成婚后,兄妹种出了一个神奇的大瓜。他们向菩萨要了一把大刀,劈开大瓜,先出来二个鬼,一个被砍死,一个逃跑了,大瓜里还有三隔人,怒族、独龙族、傈僳族、纳西族、白族,彝族……所有的兄弟民族都从瓜里出来了,他们各自唱着本民族的歌,成双成对的回到洪水前的居住地去了。后来,夫妻两人教他们播种、薅草、锄地、吃熟食、炼铁、制造工具、盖房、织布等,各民族和睦相处。
独龙族神话照例讲洪水泛滥,兄妹成婚,生下九男九女,分别成了澜沧江、怒江、独龙江、金沙江、狄子江、狄布勒江、狄麻江、托洛江和恩梅开江等九条大江的主人。这就是后来的汉、怒、藏、白、纳西、独龙等和僜人。类似的神话还可以在云南的纳西、白、傣、景颇、拉祜、哈尼、佤、布朗、阿昌、壮等民族中找到。这就说明,民族同源神话在云南确有一定曾遍性。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同源神话紧接在洪水神话、兄妹婚之后,甚至可以说是与之连为一体的现象。可以看出这一主题在云南民族中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洪水神话又称人类再生神话,它对于原始民族的意义恰如氏族社会中的“成年礼”一样。之所以要举行隆重的“成年礼”,就是要使个体的心理“断乳”、成熟,从而成为氏族社会的合格成员。“成年礼”亦称“再生礼”,意义即在此。同样,对氏族社会说,人类也有自己的童年期,也有种种的无秩行为,也需要“再生”。洪水泛滥后,云南民族神话中的民族同源主题就是提供了各民族和睦相处的行为规范,映射着云南各民族族群认同、和谐共生的文化心理。
三、人物传说,源于群体文化认可的社会共识
人物传说,就是有关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传奇性的故事。曾经在云南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都有大量传说流传在各民族之中,其中诸葛亮的传说在云南流传较广,影响很大。
在清代的《滇南杂志》《普洱府志》等云南地方史志中都有诸葛亮传说的记载。《普洱府志》载:“城南六茶山中,登其上可俯视诸山。于此祭风,又呼为孔明山。”孔明山在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象明乡境内,这一带有古代普洱茶的“六大茶山”。基诺山就在孔明山北部,是“六大茶山”之一。在这一带的基诺族、汉族、彝族、傣族中,至今都盛传着不少与诸葛亮有关的传说。
孔明山上有所谓“孔明祭风台”,传说“六大茶山”之地名是以诸葛亮遗物来命名的。西双版纳一带还有许多风物都与诸葛亮有关。基诺族传说成年男子上衣背上的“八卦”图是由诸葛亮发明的,还传说诸葛亮送给他们茶籽、棉籽,基诺族才学会种茶、种棉,又叫他们照自己的帽子盖房子;傣族传说他们不会盖房子,诸葛亮将帽子扣在地上,让他们照着帽子的样子学会盖房子,傣族孔明灯也是由诸葛亮发明;普洱城边的洗马河相传是当年诸葛亮洗马的地方;哈尼族支系爱尼人的《哈尼族的房子与茶树的传说》也讲到,爱尼人的房子是照着诸葛亮的帽子式样盖的。
据史料记载,诸葛亮当年并没有到达这些民族地区,但是由于蜀汉王朝实行“南抚夷越”政策,团结南中(即云南)民族上层人士,缓和民族矛盾,同时又将先进的生产技术经验、文化传授给各民族,促进了边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从文化上获得了云南各民族的认同,所以深得民心。以上传说反映了历史上中原与云南边疆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关系,对以后中原内地与西南各民族的团结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统一意义深远。在以上的传说,没有更多地突出诸葛亮的军事、政治才能,而是歌颂他给各民族传播先进文化、创造新文化的丰功伟绩。诸葛亮,在民族文化深层心理结构中,已成为一种文化象征,一种符号,正如亨廷顿所说,不同民族的人们常以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即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并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
彝族《八擒诸葛亮》的传说,便很能说明这一点。云南滇中、滇西、滇东北地区都流传有诸葛亮七擒彝族部落酋长孟获的故事。但在武定彝族中却与以上的传说不同,流传着《八擒诸葛亮》的故事。传说诸葛亮第7次被擒后仍然不服,还嚷着要与孟获大干一场。孟获笑着放走诸葛亮及其兵马,双方摆开阵势,堂堂正正地开战,孟获与诸葛亮阵前单挑,诸葛亮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取胜,最终被孟获再一次生擒。孟获在中军帐戏弄诸葛亮:”你还有什么本哪,不妨再使出来看看!”诸葛亮从怀中掏出一根谷穗,孟获哈哈大笑:“大刀大斧尚且奈何不了我,何况一根小小谷穗!”说完又是一阵仰天大笑。可笑声未落,却见诸葛高闪电般出手,将谷穗一下子扎在孟获的心脏上。这柄小小的“谷穗剑”终于使孟获倒下,降顺了孟获。[]
诸葛亮的传说中,是云南各民族一定社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大众所需要的社会理想化身,具有突出的民族性和理想性的特点。同样一个诸葛亮,在不同民族的传说中形象有差异,都赋予了各自的民族性、传奇性,对本民族更具有特殊的人格魅力。如布朗族中流传的诸葛亮传说,他们称诸葛亮为“召玛贺”意思是“传说中的智者”。临沧永德布依族有喝野金银花茶的习俗,传说是诸葛亮发明的。而勐海县南糯山的茶树传说是由诸葛亮送给爱尼人的手杖长成的。楚雄牟定县一带的彝族、汉族中也流传着许多关于诸葛亮的传说,其中《望子洞》的传说最为感人。传说诸葛亮因思念远在成都的儿子,便用鹅毛扇煽出一个山洞,洞与成都相通,从洞中诸葛亮可见到他的儿子。
四、丧仪古歌,叶落归根的血缘观与文化归属的伦理意识。
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民族注重血缘观念和乡土观念,其传统葬礼上的“送魂”恰恰在于把祖灵所在的阴间与祖先所居住过的故乡等同起来,“送魂”赴阴间也就成了“送魂”回老家。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叶落归根”的血缘观念使“老家”这一概念强化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身份认同,也使社会成员之间更具有了文化意味上的归属感。
云南各民族丧葬仪式中普遍存在的“送魂归宗”仪式,实际上起着联系、加强民族感情的催化作用。这与各民族的发展史息息相关。云南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迁徙史,其中属于氏族羌族系的彝、白、纳西、哈尼、傈僳、拉祜、独龙、怒、阿昌、基诺、普米等族系由中原西迁,陕甘青高原迁来;苗族系由湘、黔、川迁来;瑶族系由两广迁来。属于百越族系的壮、傣、布依和属于百濮族系的佤、德昂、布朗等族,虽大部是土著民族,但历史上也曾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迁徙。任何迁徙经历,都是该民族难以忘怀的“历史情结”。那以成遥远记忆的祖先故地和流离颠沛的迁徙经历,通过史诗、古歌代代相传,使人们铭刻在心、梦萦魂牵。通过送魂归宗,既抚慰死者的灵魂,又促进想象力的驰骋,把祖先故地和彼岸世界联系起来进行美化、渲染,从而引起人们对本民族之根的历史追寻,增强民族的内聚力,其丧葬仪式活动中人们的社会身份认同和文化价值共识的意味更为明显。
仪式活动所体现的强烈的群体意识、群体“寻根”归附感,它们可说是后来的民族意识乃至国家意识最古老的根源。例如,普米族在丧葬时除了唱《指路经》,还要举行“给羊子”仪式,巫师向死者交代魂归故里的路线,并杀一羊子给死者带路。其具体的路线是:先去亲族放骨灰的地方告别,再去大岩洞休息一晚,然后一直朝前,过浪放,经左所,绕泸沽湖,到永宁坝子的拖七别七,在那里的大核桃树下住宿一晚,然后骑上骏马,驰过草原,跑过木里。马蹄掀落的石头要闪开,晃悠悠的桥上要踩稳……;再往前走有三条路,低处白色的是野兽的路,走不得;高处黑色的是山神的路,走不得;中间绿色的是普米人的路。……往北去转过岩石,到了波浪卷着波浪的大江边,你就骑着皮囊渡过去,再往前进就是普米族祖先居住的地方。由此可知:第一,普米族系从中原北方迁徙而来,用皮囊“渡过了波浪卷着波浪的大江”南下,直至永定泸沽湖一带。第二,杀羊子带路,骑马过草原,当是普米族先民古代游牧生活的反映。
景颇族在老人死后的送魂路线,大致方向是沿恩梅开江东岸北达甘青高原。据历史文献记载,秦始皇时氐羌南迁就有景颇祖先在内。在景颇族举行盛大歌舞“木瑙纵歌”时,巫师带领景颇族男女所走的蛇形路线就是表示其迁徙路线。而史诗《木瑙斋瓦》里也唱述了景颇族从北方南迁的历史。
永宁纳西族在火化死者之前,要唱《达魂歌》,并举行“洗马”仪式,其意义为:永宁纳西族的祖先是从遥远的北方迁来的,途中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人死后灵魂要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路程也是十分艰难,需要好马驮死者的灵魂。当巫师达巴在主持仪式中象征地洗刷马时,要夸赞马说:“天上雷声快,没有你跑得快;燕子飞得快,哪会有你快;老虎、豹子快,比不上你快。”意在让马能顺利地把死者的灵魂驮到目的地。从所在村子出发,历数几十个地名,指出经过的山、河、沟、坡、村、桥等,最终为祖灵所居的“司布阿拉瓦”。此外,布朗族的《叫魂歌》、景颇族的《丧葬歌》、傈僳族的《丧歌》和拉祜族的《丧歌》等等,也要在葬礼上唱述这一类仪式古歌,并举行送魂仪式。这些送魂路线都反映了先民是由北而南逐步迁徙的。在这里,巫师实际上是进行一次严肃的民族传统教育。在唱诵古歌的过程中,整个民族沉缅于缅怀祖先的肃穆气氛中,每个成员十分具体地感到自己从属于民族群体。认祖归宗,他们虔诚地跪拜于创世祖先的神力之下,为自己是这个群体的一员而庆幸、自豪。这样,就促成宗教感情向民族感情的转化,既巩固了宗教意识,也增强了民族的群体意识,并使二者融为一体,共同构成民族内聚力的核心。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将受孕、出生、成年、结婚、死亡称之为“人类生活上的重要危机”,而葬礼的社会性仪式活动的一大功能,便是借助原始宗教将这一重大危机神圣化。通过史诗、古歌和与之相伴的仪式将芸芸众生聚集在共同始祖的旗帜下,使社会契约公开化、神圣化,增强了人类群体的向心力、凝聚力,从而转化为最强有力的一种社会控制。
千百年来,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以朴素的语言、丰富的内容、多变的形式诉说着历史的变迁、文化的记忆,构建着各民族间密切交往、相互交融、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精神家园,呈现出鲜明的家国情怀和文化同源的归宿感。家国情怀往往表现为情感和理智上对共同体的认同、维护、热爱,并自觉承担共同体责任。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这个“共同体”既是“家”,也是“国”。因此,家国同构这一中华传统文化成为维系云南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精神纽带。从这不难看出,基于文化同源、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家国情怀是达成国家认同的逻辑前提,同时更是云南民族边疆地区实现长治久安、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文化保障和精神支柱。恩格斯说: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因此,在当今世界文化多样和价值冲突加剧的背景下,构建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增强文化认同,培养共同体意识,对于国家安定团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 冯天瑜主编:《中华大化辞典. .P20.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
[2] 赛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引论 .旗帜与文化认同. 周琪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3] 参阅施惟达 :《悠远长存的神话世界》.张文勋主编:《滇文化与民族心理》.P30-33.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
[4] 赛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引论.旗帜与文化认同.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5] 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P26.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6]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77-78页.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7] 恩格斯 .《德国民间故事书》.《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4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