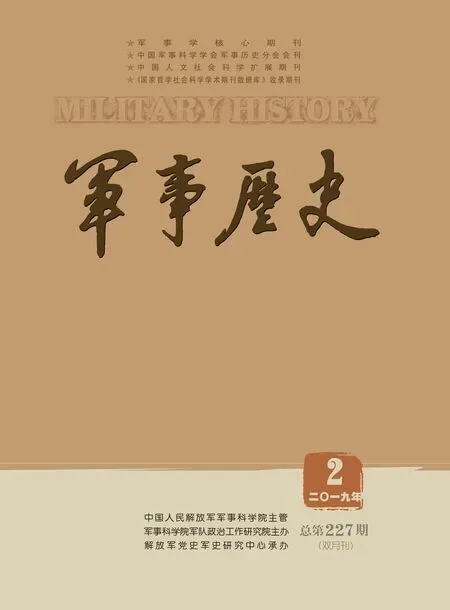中唐南衙卫军制度变革探析
——府兵“番上宿卫”的衰落与“彍骑”之制的兴起
唐朝禁卫军有北衙和南衙之分。①参见《新唐书》卷50《兵志》:“夫所谓天子禁军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者,禁军也”,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30页。北衙禁军具有皇室私属性质,其组织结构、兵卒来源及权责归属等问题较为复杂。南衙卫军则由宰相管辖,分为十二卫、左右千牛卫和左右监门卫。其中,南衙十二卫分领地方军府。唐朝府兵制因袭隋朝②参见《新唐书》卷50《兵志》:“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而备于隋,唐兴因之”,第1324页。,府兵的重要职责之一便是定期轮值京师,称“番上宿卫”。因此,府兵是唐初南衙卫军的主要来源。然至高宗、武后时,“府兵之法寖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宿卫不能给”③《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26页。,遂于玄宗开元之际以招募的“长从宿卫”取代了番上的府兵,“长从宿卫”其后更名“彍骑”。“彍骑之制虽暂”,“其关于中古兵制之演变者至巨”。④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0页。
府兵制是西魏宇文泰创立的兵制,历经西魏、北周、隋、唐四朝,学界前贤已对其起源、发展及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欧阳修在《新唐书·兵志》中评价府兵制“虽不能尽合古法,盖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后世,子孙骄弱,不能谨守,屡变其制”⑤《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23页。,之后南宋陈傅良所撰《历代兵制》及明清诸家的考证不断深化着对这一中古兵制的研究。谷霁光、唐长孺、陈寅恪、岑仲勉、冈崎文夫、菊池英夫等近现代中外史家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有了重要进展。毛汉光、张国刚、谷川道雄等当代中外学者则结合新材料不断修正传统观念,力求创新性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学者对府兵制和唐朝府兵“番上宿卫”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差异:前者无论在横向上还是在纵向上都更为宏观,而后者则更为具象,其着眼点是府兵制在唐朝禁卫军中的应用和变革。
此外,学界对唐朝禁卫军的研究成果亦颇为丰富,尤以对北衙禁军的研究为重。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①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1页。中讨论了唐初北衙禁军参与政变的问题,其后学者还就北衙禁军演变、宦官监军及中晚唐神策军等问题做出了探讨。相比之下,学界对南衙卫军的研究程度不及北衙禁军,除岑仲勉、谷霁光等学者在研究府兵制②参见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时简略提及南衙卫军的职能外,杨鸿年曾在其论文《隋唐金吾之职掌》中专门探讨了南衙卫军中金吾卫的问题。张国刚在《唐代禁卫军考略》一文中主要介绍了南衙十六卫的职能,提及府兵“番上宿卫”制度的衰落以及“彍骑”制度的兴起,但并没有作进一步探究。戴均禄在其硕士论文《唐代前期南衙禁军研究》中就南衙卫军制度沿革以及上番折冲府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对番上府兵宿卫不给的原因仍遵循《新唐书·兵志》的传统观点,且没有比较“番上宿卫”的府兵与“彍骑”的异同。
本文将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唐南衙卫军中府兵衰落与“彍骑”兴起的问题,尝试在《新唐书·兵志》所言及的原因之外,探寻其他原因,并将前后两种兵卒类型进行对比,以揭示“彍骑”之制对南衙卫军以及整个唐朝社会的深远影响。
一、“彍骑”之制缘何替代府兵“番上宿卫”之制
府兵“番上宿卫”制度瓦解的直接原因是宿卫兵源不足、折冲府无兵可交,迫使中央采取新的征兵方式。而宿卫兵源不足则有中央难以完全控制地方军府、边疆防务较重和府兵制自身缺陷三方面原因。
首先,唐朝中央难以完全控制地方军府。张国刚认为“唐代不仅西北,而且在东北、江南,折冲府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到中央宿卫,而是在地方服役”③张国刚:《唐代府兵渊源与番役》,《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且宿卫京师的府兵大部来自关内、河南、河东道等地。由此可知,只有京畿附近的府兵才需承担宿卫京师的职责,而大部分的地方军府根本不具有此项职责。那么,既然唐高宗、武后时出现宿卫府兵不足的现象,为何不能扩大宿卫府兵的征召范围呢?这是基于府兵制可以较好地维护中央集权的认识,但其后出现的新兵制愈来愈具地方性,直至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其实在府兵制下,唐朝中央也没能完全控制地方军府。南衙十二卫主要管控京畿附近的番上府兵,而西北、东北和江南等地的军府则有较强的地方性和灵活性,宿卫府兵兵源不足,应当说与中央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有关。
其次,唐高宗、武后朝以降,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防务较重。这也导致府兵抽调困难,南衙卫军兵员不足。吐蕃于唐朝西南边境多次进犯。据《新唐书》载:“(高宗)仪凤元年……闰月己巳,吐蕃寇鄯、廓、河、芳四州,左监门卫中郎将令狐智通伐之。”④《新唐书》卷3《本纪第三高宗皇帝》,第72页。“(高宗)永隆元年……七月己卯,吐蕃寇河源。辛巳,李敬玄及吐蕃战于湟川,败绩。”⑤《新唐书》卷3《本纪第三高宗皇帝》,第75页。“(武则天)天册万岁元年……七月辛酉,吐蕃寇临洮,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以击之。”⑥《新唐书》卷4《本纪第四则天顺圣武皇后》,第95页。此外,唐朝的东北边境则屡遭高句丽挑衅,“(高宗)龙朔元年,大募兵,拜置诸将,天子欲自行,蔚州刺史李君球建言:‘高丽小丑,何至倾中国事之?有如高丽既灭,必发兵以守,少发则威不振,多发人不安,是天下疲于转戍。臣谓征之未如勿征,灭之未如勿灭。'亦会武后苦邀,帝乃止。”⑦《新唐书》卷220《高丽列传》,第6195~6196页。因此,繁重的边防事务亦是南衙卫兵补给困难的原因之一。
除上述原因外,府兵制自身的局限性也是王役不供、宿卫不给的重要原因。
其一,府兵制以均田制为经济依托,正所谓府兵之置,“始一寓之于农”且“居无事时耕于野”⑧《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23、1328页。,它具有兵农合一的性质。谷霁光先生在《府兵制度考释》中提到,“均田制的施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府兵自备资粮提供经济条件”①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第204页。,因此在唐朝中叶均田制衰落以后,府兵制亦难维系。
唐初至玄宗开元年间,庶族地主相继兴起,土地兼并加剧,私有化程度提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最高统治者为了打击关陇旧族势力,扶植庶族地主,大举赐田,另一方面是土地买卖兼并日趋激烈,豪富之家众多。“均田制本身,通过反复还授,就成为土地私有化的一条自然通路”②胡如雷:《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 280页。,而土地私有化的提高又不断加速着均田制的瓦解。
此外,户籍管控也一直是唐朝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防控逃户的奏表屡见不鲜,“军府之地,户不可移;关辅之民,贯不可改”③《唐会要》卷85《逃户》,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561页。,正是户籍对均田制和府兵制重要性的阐述。凤阁舍人李峤于武后证圣元年上表称:“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粮苟免岁时,偷避徭役。此等浮衣寓食,积岁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或出入关防,或往来山泽。”④《唐会要》卷85《逃户》,第1560页。可见初唐时自耕农逃匿现象就已屡禁不止,安史之乱后更甚,于府兵制而言,这造成了卫士亡匿、宿卫不给的后果;于均田制而言则是丧失了施行条件,并瓦解了府兵制的经济基础。
再者,魏晋时期的战乱导致北方大量土地荒置,政府对这些无主荒地的重新分配是施行均田制的前提,但安史之乱后,因战争而被弃留的土地却没有成为政府重新施行均田制的基础。这是因为在魏晋时期,政府对北方土地的控制和分配是以原有地主定居江南为前提的,北方均田制的施行是与江南的开发同时进行的。而唐朝中期,因战乱背井离乡的土地所有者大多会在日后返乡,“地主政权就必须为外逃地主保持其土地私有权,而不能任意处理这些土地”⑤胡如雷:《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第279页。,所以唐政府并没有因此获得大量可控土地,均田制实难继续。
其二,府兵制下,民众生活负担沉重。府兵制寓兵于农、兵农合一,旨在减轻国家的军事负担,削减财政开支。谷霁光先生指出,“就府兵来说,自备资粮出于其家,基本上是一户养一兵”,无异于将“国家养兵的负担,直接加于或转嫁于农民身上”⑥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第207页。,沉重的生活负担自然会产生大量逃避兵役的现象。
府兵制下民众生活负担沉重可从三方面来看。首先,应征者需自备粮食、马匹和武器等物资。《新唐书·兵志》载:“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凿、碓、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毡帽、毡装、行縢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⑦《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25页。对于小生产者而言,这无疑是沉重的经济负担。
此外,番上宿卫和戍守边疆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于百姓而言,延误农时和丧失精壮劳力都是对家庭经济收入的沉重打击。而一旦被征发,就意味着长达四十年的兵役期限⑧参见《新唐书》卷50《兵志》:“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第1325页。,征镇宿卫,皆由府籍调发。据谷霁光先生考证:“府兵赴番占去劳动时间,就不能不加强劳动强度,以至将田地佃与他人耕种”⑨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第205页。,而这样的生产方式再度加剧了小农经济的脆弱性。
再者,府兵制下的奖励机制,不强调对军功卓越者的经济报酬,而是通过加官进爵的方式,给予其社会地位的提升和认可,即勋格。换言之,府兵制下人们应征入伍的动机主要不是出于经济目的,而是为了获得荣誉。即便政府承诺对军功卓越的卫士给予授田的奖赏,在后期的施行过程中,也很难落实,“授勋过多”往往成为勋田少授或未授的原因①参见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第203~204页。。
最后,初唐统治者在征召宿卫兵员时,虽尽可能依据“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②《唐律疏议》卷16《擅兴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02页。的原则,但制度与现实之间总有差距。即使在初唐,府兵征召也会涉及底层贫苦百姓,即“武德以至贞观府兵之徵召已及于下户”③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第18页。。而后,随着土地兼并加剧,中唐以降,“人户浸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盖得非当时之实”④《旧唐书》卷118《杨炎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322页。。户口的减损,加剧了政府对底层兵役的征发,而这种征发无疑会大大加重人民的生活负担,使府兵制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其三,府兵制废弛还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唐初,鲜卑之风犹存,从上到下的整个唐朝社会都充斥着尚武情怀,军功仍被看作是贵族子弟进阶的重要因素,然而,随着社会的稳定发展,科举制进一步完善。“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废武备,销锋镝,以弱天下豪杰。于是挟军器者有辟,蓄图谶者有诛,习弓矢者有罪。不肖子弟为武官者,父兄摈之不齿。”⑤《唐会要》卷72《军杂录》,第1300页。由此可知,最高统治者开始注重文学教化,悉除剽悍尚武之风,并且引领了整个上层社会的崇文风气。人们纷纷以科举入仕为正途,而渐疏于武事。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番上卫士的社会地位也日渐下降,“至是卫佐悉以借姻戚之家为僮仆执役,京师人相诋訾者,即呼为侍官”,因此“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浸堕,为人所贱,百姓耻之,至蒸烫手足以避其役”⑥邓广铭:《隋唐五代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68~69页。。此种社会氛围进一步加速了府兵制的瓦解,此后卫士亡匿、宿卫不给的问题就已经迫在眉睫了。
于是玄宗“(开元)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兵部尚书张说置长从宿卫兵十万人于南衙,简京兆、蒲、同、岐等州府兵及白丁,准尺八例……至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始名彍骑,分隶十二卫”⑦《唐会要》卷72《府兵》,第1298~1299页。,至此,宿卫府兵由彍骑替代,募兵制也由此代替征兵制成为补给南衙卫军的主要方式。
二、府兵“番上宿卫”之制与“彍骑”之制的对比
府兵“番上宿卫”之制与“彍骑”之制的对比,也是征兵制与募兵制的对比,这不仅是京师宿卫军前后称谓的变化,也是京师宿卫军招募方式的变化。宿卫军招募制度的演变,直接影响到京师驻军的兵员结构。
魏晋至唐初,府兵制的发展趋于完备,其征召原则和奖励机制,“较好地解决了兵役义务与权利的均衡问题”⑧丁朕义、梁逵:《中国古代兵役义务与权利探析》,《军事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首先,府兵制下的兵员征召以“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⑨《唐律疏议》卷16《擅兴律》,第302页。为准。于此,唐长孺先生考证称:“贞观五年,富室强丁尽从戎旅,而余丁则配司农将作以服徭役,是富人充兵,贫人服役,犹存旧风。”⑩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第17页。可见府兵制注重兵员自身的经济实力,身体素质以及兵员家庭的人口结构。尤其是宿卫京师的府兵基本由京畿附近的军府提供,这就避免了更远地区的百姓舟车劳顿、疲于奔命。因此,这种以均田制为物质保障,具有坚实经济基础的兵制,既可为南衙卫军提供稳定且高素质的兵员,又可以较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其次,在奖励机制方面,府兵既可因功“获致勋阶”⑪,也可获奖勋田作为经济补偿,但经济奖励始终是辅助手段,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勋阶的获取才是番上府兵主要争取的奖赏,
⑪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第203页。因为轮值京师的府兵不仅居于京畿附近,而且家境相对优渥。因此,“唐代前期的府兵制度是典型的重视身份性兵役制度”①张国刚:《唐代兵制的演变与中古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主动应征者大多是那些不事农桑,出身贵族的官宦子弟,他们从军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荣誉和社会地位,将从军经历作为进阶高位的政治资本。
据此,唐前期府兵“番上宿卫”之制的优点即得以体现,它不仅强调农业生产对军事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而且注重考察兵员的家庭状况,既为社会上中层人士提供获得荣誉和官阶的途径,又避免使下层民众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但后来,府兵制日渐崩坏,唐高宗时,“州县发遣兵募,人身少壮,家有钱财,参逐官府者,东西藏避,并即得脱。无钱参逐者,虽是老弱,推背即来”②《旧唐书》卷84《杨炎传》,第1892页。。由此可见,家境优渥者开始大量逃避军役,宿卫京师与镇戍边疆的兵源皆难得到有效补充。于是,征兵标准开始下移,底层民众被迫应征,履行府兵制下的兵役义务。由此造成兵员素质下降,百姓负担沉重。而这一切都使政府不得不出台新的征兵措施。
“彍骑”之制较府兵“番上宿卫”之制而言,首先缺乏稳健的经济基础。其兵员招募方式没有同农业生产建立直接联系,只是单纯依靠政府的财政支出。因此,在“彍骑”之制背后的募兵制原则下,政府的财政状况会直接影响国家的军队建设。为补充南衙卫兵,“长从宿卫”和“彍骑”的招募都给唐朝政府增加了财政压力。其次,虽然“长从宿卫”和“彍骑”的招募地区与宿卫府兵大致相同,即京畿腹地,如开元 “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③《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26页。,但招募而来的“长从宿卫”和“彍骑”却分布于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中。“彍骑”之制不如府兵“番上宿卫”之制那样注重兵员的出身及家庭状况,其招募范围包含了下层民众。第三,“彍骑”的奖励机制也异于“番上宿卫”的府兵,后者由于自身经济状况较好,因此更加注重荣誉的获取和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前者则只注重获取直接的经济酬劳。唐朝政府改以雇佣方式充实南衙卫军,应募者则从兵农合一的府兵逐渐演化为职业军人。
综上所述,自府兵之法寖坏,南衙卫兵兵源不足,唐朝政府便以雇佣的方式招募“长从宿卫”和后来的“彍骑”。从兵员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来看,府兵应征是义务,国家拥有无偿征召府兵之权利。但在“彍骑”之制下,参军成为一种谋生手段,民众有权从中获取报酬,入值京师不再是一种义务性劳动。从兵员应征的目的来看,府兵“番上宿卫”时期,官宦子弟以提升社会地位,获取政治资本为目的,贫民则为义务所迫;而“彍骑”之制下的职业军人则以赚钱谋生为目的。再从唐朝政府的征兵标准来看,唐前期府兵征召主要以“富室”和“多丁”为据,随着府兵之法寖坏,兵役征发不再苛求府兵才能,而是以数量达标为目的。但是,“彍骑”之制下,唐朝政府作为雇主比以前更有发言权,此时募兵,多看重士兵的身体素质和武艺而不看出身。同时,军人作为一种职业具有比以前更大的吸引力,下层百姓开始应征,这虽然给军队管理带来一些问题,但总体上有利于内部竞争的加强,使兵员素质获得提升。
三、“彍骑”之制代替府兵“番上宿卫”之制的影响
“长从宿卫”和“彍骑”的招募,标志着以职业军人为主的南衙卫军开始产生,而以前兵农合一的生产战斗模式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由于兵员招募方式的改变,势必导致兵员结构的变化,而兵员结构的变化也势必会对唐中后期南衙卫军的发展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唐前期府兵制下的南衙卫军,主要以社会中上层人士为主。府兵虽有内外府之分,但内府三卫和外府卫士均从官宦子弟及殷实之家遴选兵员④参见张国刚:《唐代兵制的演变与中古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这在某种程度上闭塞了下层百姓参军入伍的道路。但此后“彍骑”之制和募兵制的确立却极大改变了这种情况,“通鉴于开元十年九月书:张说建议请招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①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第29页。。因此在“长从宿卫”及此后“彍骑”的招募过程中,只看兵员武艺而不问其出身,这就打破了上层社会对行伍之职的垄断。此外,从军入伍所带来的经济收入,也会对底层民众产生巨大吸引。至此,兵源开始下移,白丁和市井之徒得以大量供职禁军。
此类白丁和市井之徒大多出身贫寒,“彍骑”之制和募兵制的确立,为这一社会群体提供了合适的就业机会,使他们得以凭借自身体格和武艺养活自己。就这一点,募兵制只重才能不问出身的招募原则,有利于提升南衙卫军的战斗力,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城市的治安管理。
但随着“彍骑”之制和募兵制的发展演变,南衙卫军内部腐败滋生,“自天宝以后,彍骑之法又稍变废,士皆失拊循”②《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27页。。再者,朝中重文轻武之风日盛,宿卫军士之地位日下。南衙卫军的招募、训练和管理皆有松懈,于是有些仰仗自己卫军身份的兵卒为乱一方,也有一些挂名军籍以避税的市井白丁混入南衙卫军的队伍,而后者通常带来更为恶劣的影响。他们横行于世,鱼肉百姓,为非作歹,却因军队管理腐败,而无法受到有效管束。如《唐语林》所记:“京城恶少及屠沽商贩,多系名诸军,干犯府县法令,有罪即逃入军中,无由追捕。”③《唐语林》卷1《政事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页。《文献通考》亦有所载:“长安奸人多寓占两军,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谓之纳课户。益肆为暴,吏稍禁之,辄先得罪,故当时京尹、赤令皆为之敛屈。”④《文献通考》卷151《兵考三》,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539页。由此,南衙卫军日渐疏于训练,管理松懈,很难形成集团战斗力。天宝末,“六军诸卫之士皆市人白徒,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角抵拔河,翘木扛铁,日以寝斗,有事乃股栗不能授甲”⑤《唐会要》卷72《军杂录》,第1300页。。上述情形体现出,唐中后期,南衙卫军内部腐败横行,纵使以北衙禁军为主的皇室亲兵有所扩大和发展,中央与地方的军事力量对比也已然发生变化。
“彍骑”之法于天宝后逐渐废弛,府兵“番上宿卫”之制亦不复存在,唐南衙卫军的军事实力再度被削弱,“其后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⑥《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27页。。
但迫于边境战事,统治者虽认为中原太平,却不得不在边防用兵,起初为了充实南衙卫军而采用的募兵制,被推广到地方“长征健儿”的招募中,募兵制与节度使制结合起来,唐朝逐渐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而关辅地区则等于全无装备”⑦邓广铭:《隋唐五代史讲义》,第70页。,这样的军事力量对比势必导致地方割据的进一步发展。正如《新唐书·兵制》所言:“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势使然者,以此也。”⑧《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28页。藩镇和方镇节度使逐渐从军事统帅变为集政治、经济、司法大权于一身的地方统治者,他们拥兵自重,不仅割据一方,更觊觎皇权。至此,唐朝初年以关中兵力制驭四方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虽然“彍骑”之制的实行时间较为短暂,但其以雇佣方式征兵入伍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当时南衙卫军兵员不给的燃眉之急,更对后来的兵制变革产生重大影响。玄宗之际,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当是中古兵制变革的重大事件,而“番上宿卫”的府兵被雇佣而来的“长从宿卫”和“彍骑”所替代,也是中唐南衙卫军制度的重大变迁,细考两种制度嬗变之间的历史状况,由此可窥得中古社会的发展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