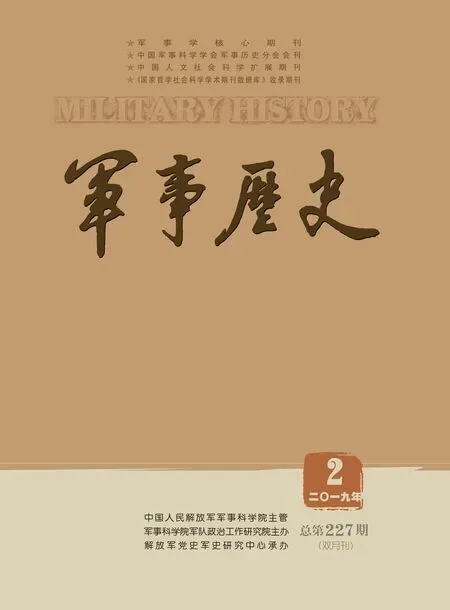论拜上帝教对太平天国兴衰的影响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农民打着宗教旗帜的反封建反侵略的人民革命。它对中国传统价值准则从根本上起了瓦解作用,使数千年来中国社会郁积的不满在中国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得以总爆发。本文分析不同时期拜上帝教对于革命运动的作用和影响,旨在表明作为太平天国主导意识形态的拜上帝教,一方面它承担革命的理论外衣,对于动员和组织人民起来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它毕竟不是从新的经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科学世界观,以之为指导必然注定这场革命难逃旧式农民战争的历史命运。太平天国“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拜上帝教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地分析与总结。
一、拜上帝教的创立及其对早期太平天国革命的作用
(一)洪秀全对拜上帝教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精心设计。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洪秀全大量吸取基督教特别是《劝世良言》中的思想资料,以我为主,对其进行了新的解释和发挥,充分体现了洪秀全把拜上帝教作为农民革命意识形态的政治需求和主观意图。
洪秀全极力把基督教的独一真神跟中国古代的“上帝”“天”等概念相比附,说“上古中国同番国,君民一体敬皇天”①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3页。。这种把西方基督教的“神”同中国经书上的“上帝”相混同的做法,对于使传教活动取得合法空间、以皇上帝取代中国人旧的偶像、弥补拜上帝教理论肤浅和贫乏的弱点都是较为有利的。不仅如此,他还充分利用极具地方化的宗教形式——降僮,使拜上帝教在广西当地立足。
基督教教导人们寄希望于来世,欺骗人们忍受现世的苦难生活。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与之有所不同,他把天堂分为大天堂和小天堂。天上的叫“大天堂”,是革命战士死后灵魂享乐的地方;地上的叫“小天堂”,是革命战士为之流血奋斗所要建立的人间乐园,是“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类理想社会。洪秀全还试图把在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延伸扩展到现实社会生活中,衍化为政治经济平等的观念。这样做就是以现实的天堂和人间的平等,鼓舞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打开奴隶枷锁,为实现人间现实的幸福、建立新的国家而奋斗。
“基督教的社会原理把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的一切无耻行径,不说那是对原罪及其他罪的公正处罚,便说那是主用他的无限智慧对被救者布置的考验”①《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武剑西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93页。。拜上帝教初创时也完全重复基督教的教义,主张接受现实命运,忍受压迫和剥削。但这种宣传逐渐与后来的革命实践发生尖锐矛盾,在严酷的斗争现实面前,洪秀全不得不改造这种教义,进而宣传反对消极厌世、逆来顺受。他说:“过于忍耐和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②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864页。为增强反清色彩,洪秀全把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罪恶抽象为阎罗妖的罪行,刻意塑造皇上帝与阎罗妖的对立。通过这些做法使拜上帝教的皇上帝俨然成为一个洋溢着反抗封建压迫精神、高举反清旗帜的战斗之神。
(二)以拜上帝教为太平天国革命意识形态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在对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作翔实研究后曾精辟地指出:“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活跃于整个中世纪。革命反对派随时代条件之不同,或者是以神秘主义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公开的异教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③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01页。洪秀全时代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崩溃,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尚未形成,既无条件产生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也无条件接受刚刚诞生在西方国家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革命又急切需要思想理论武器去动员和组织人民参加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因此,正是这种客观的政治需要和社会力量的推动,拜上帝教应时而生。它先以公开的异教形式出现在广西山区,创立基地,传播教义,聚集教众,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之后,再导向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最终目的。
《周易·观封·彖传》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纵观中国古代历史,“神道设教”是历代政权和农民起义者惯用的意识形态手法。秦末陈胜吴广的“鱼腹丹书”“篝火狐鸣”;汉末张角利用太平道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宋朝方腊利用摩尼教发动团结大批民众造反;元末韩山童以白莲教组织黄、淮群众,“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明代李自成编造“十八子主神器”的歌谣;等等,莫不如此。众所周知,洪秀全不是做了宗教家后思想起了变化才走上革命道路的,而是在经过鸦片战争的大教育,对封建社会黑暗考试制度的愤恨,决心走革命的道路之后,为着进行革命而特地去创立上帝教的。封建统治者利用“神道设教”来维持统治,谙熟中国历史的起义者反过来利用“神道设教”而发动起义,这在意识形态策略上是没有质的区别的。
(三)为着农民革命而定制的意识形态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具有重要作用。拜上帝教的教义虽然简单,但却以宗教和神话的形式表达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政治合法性,表达了太平天国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正义性。根据拜上帝教的教义,“天”的代表者就是独一真神“上帝”,信教者必须独尊上帝、力遵天诫,不得信拜偶像邪神,否则就是违背“天道”。在拜上帝教的神话中,洪秀全一方面揭露了清朝统治者违背天道的罪行,一方面把自己说成是上帝次子、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从而取得了“替天行道”的合法地位和政治依据。
革命初期在与清朝的对立形势中,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袖的权威既不能从朝庭中获得,也暂时无以从革命实践中取得,因而同样只能从宗教的教义中获取。所以,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教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做出了独出新意的创造。他以超人间力量的形式,维护古代中国皇帝“上天承运”的神话故事,赋予皇上帝全知全能的本领,证明自己“真命天子”的神圣地位。特别是他大力宣称皇上帝创造了整个世界,人世间的贫富贵贱、死生祸福,国家民族的盛衰兴亡,无一不是皇上帝精心安排的。这样的教义再辅之反孔批儒、摧毁偶像,以及杨秀清利用降僮巫术宣传洪秀全为真命天子下凡等行为,用以充分证明太平天国运动及洪秀全领导这次运动的神圣性,从而树立非凡的权威。
革命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便会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在宗教的价值引导和热情催化下,拜上帝教所凝聚的起义者,释放出了极大的革命力量。洪秀全经常以教主的威严、宗教预言的方式,号召人们以坚定勇敢的行动去迎接起义、战胜黑暗。他在《原道醒世训》中大声疾呼道:“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惟愿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正是由于洪秀全怀着推翻清朝、开创新朝的宏伟抱负,动员和组织群众起来战斗,拜上帝教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精神原动力。
二、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国兴盛时期扮演的角色
“宗教是观念、情绪和活动的相当严整的体系。观念是宗教的神话因素,情绪属于宗教感情领域,而活动则属于宗教礼拜方面,换句话说,属于宗教仪式方面。”①《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363页。洪秀全把这三者都注入革命的内容,在观念上把基督教的平等教义发展成农民朴素的平等思想,在情绪上把基督教的宗教狂热发展成农民群众的造反欲求,在仪式上把基督教的戒律仪式发展成起义队伍的严格纪律。因此,由拜上帝教所产生的宗教观念的凝聚力、宗教热情的鼓舞力、宗教戒律的约束力、宗教仪式的感染力、宗教氛围的统慑力,犹如催化革命运动的“兴奋剂”,为太平天国的兴盛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凝聚人心的“思想旗帜”。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指出:“农民们无在这样可怕的压迫之下受着折磨,可是要叫他们起来暴动却不容易。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困难无比。农民世代相传,习于顺从;在许多地区,已经戒绝使用武器;剥削的重担随主人之不同或轻或重;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一切。”②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8页。要使安静的、不曾逾越地方关系和地方眼界范围的农民起来革命,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了解、共同的心愿来唤起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宗教乃是最合适的。拜上帝教正是以其战斗性、现实性、平等性的革命内容,反映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群众的政治要求。在这面思想旗帜的感召和鼓动下,千百万农民参加了反清斗争。太平军所向披靡,席卷桂、湘、鄂、赣、皖、苏等六省,直至建立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权。
洪秀全从天下一家、凡间皆兄弟的宗教理想着手,对现实世界进行变革;起义后又制定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宣告平均分配土地、共同从事劳动、彼此支援帮助、规定副业生产。尤其是它否定私有财产,主张消除贫富差别,倡导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希望把无人不饱暖建立在无处不均匀的分配基础上。这是把中国农民起义和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加以理想化的结果,虽然具有极大的理想性、虚幻性和欺骗性,但同时又具有极强的引诱力、号召力。例如,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中就强调:“普天之下皆兄弟,灵魂同是自天来。上帝视之皆赤子,人自相残甚恻哀。”他还要求大家从思想道德上“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以达到“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大同世界。这种互相帮助、团结平等和安宁幸福、自我道德修养和严明的纪律等,与一般盗匪类会党形成鲜明对照,极大地吸引了广大民众,出现了“人心摇惑,附丛者益多”的可喜局面,实际上也是民众渴望社会稳定、生活良好、免灾避祸心理动机的真实写照。
一个并非科学的信仰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人呢?表面上看是拜上帝会众只知道“拜会”可免蛇虎咬人,可除灾病,有衣有食。实际里却是因为太平天国顺应了清政府腐朽没落、广大农民要求土地革命和变革社会现实的历史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拜上帝教适应农民的觉悟程度,通过各种手段收拾人心,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把群众团结在周围,把他们从传统信仰中争取到新的信仰上来,使起义的行为蒙上神的保护、受命于“天”的色彩,充分发挥了宗教的渗透影响作用,达到了其他意识形态所难以替代的鼓动性、激励性、团结性效果。
(二)激励战斗的“冲锋号角”。拜上帝教以各种精神手段激励人们为理想而献身、奋勇投入推翻“阎罗妖”(清朝)的战斗。自金田起义时,洪秀全就为农民队伍提出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的革命任务,提出了“同打江山,共享天福”的战斗目标。而每逢遇到巨大艰难的时候,他们还用拜上帝教的各种“说法”来鼓舞群众斗志。如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八月,太平军被清军封锁在桂平县紫荆山区内,形势十分危急,军心发生了惊慌。于是天王下诏说:“天王诏令各军各营众兵将:放胆,欢喜踊跃,同心同力同向前,万事皆有天父主张,天兄提当,千祈莫慌。”拜上帝教这种布道或鼓动人心的方法被称为“讲道理”,在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往往如同犀利的战斗号角,激励将士万众一心打破难关,取得胜利。
拜上帝教的祈祷和礼拜等仪式的反清政治色彩也十分明显。一个外国传教士就曾觉察到祈祷文的主要目的“就是交战胜利,恢复江山”。这些宗教仪式与基督教完全不同,目的是借助于上帝的力量,以鼓舞士气,动员将士奋勇杀敌。正是靠着宗教信仰与组织的力量,太平军人人都充满着宗教的牺牲精神,每遇战事,莫不勇往直前,置生死于度外,并且相信死后得进天国,可以享受永生的快乐。
(三)维系团结的“社会水泥”。统一和稳定是社会管理的基本要求。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可以为之发挥出“社会水泥”的作用。①参见尼斯科·波郞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王宏周、马清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13页。太平天国运用拜上帝教的各种戒律严禁军队滋扰民间,借以巩固其组织,维持其治下社会的秩序。初创时期,拜上帝教只有简单的洗礼和崇拜仪式,并无严格的礼仪制度和言行规范。此后,洪秀全以“摩西十诫”为蓝本制定了10款天条,作为教众的纪律规范和生活准则,战时则成为严格的军事纪律。后又制定了《行营规矩》共计10条。这些军律无不是从基督教采取而来,处处充满着宗教的意义。起义后,太平军更是规定杀“妖”取城所得财物尽缴归天朝圣库,严禁私藏私带金银财宝,严禁奸邪淫乱,违者斩首示众等严格军纪。
拜上帝教十分注重进行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他们采取特殊的宗教形式对加入太平军的秘密社会、土匪、教门群众进行教育。早在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对接纳天地会分子就提出“舍邪弃旧而皈依真教”的要求。后来在行军作战中同样注重对加入者进行宗教洗礼和严格的军事训练,以使他们在战争中“多闵不畏死”。拜上帝教如此之重视宗教活动以及思想教育,使广大太平军将士团结一致、奋不顾身,也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中国农民保守、散漫的生活方式,从而成为凝聚在宗教精神下的一支革命大军。
三、太平天国后期拜上帝教与皇权的争斗及其影响
在一定社会上层建筑中,占主流的意识形态总是与相应的社会权力结构相配合而发挥作用的。否则,必然引起社会的动荡。
(一)太平天国上层建筑中神权与皇权的复杂争斗。太平天国自起事以来其内部就有着两套权力系统:一套天上神权,一套地上皇权,两权交织,互相争斗。太平天国以拜上帝教为思想指针,因此神权是太平天国权力体系中的首要动力。创教之初,洪秀全是理所当然的教主,拥有至高无上的神权。但一次意外事件却改变了这套权力系统的结构。1848年,杨秀清和萧朝贵以降僮的方式染指了拜上帝教的最高神权(即二人分别称自己是天父、天兄的化身)。这虽然使洪秀全的权力被削弱,但从革命运动发展的全局看,拜上帝会众的信心反因“天父天兄下凡”下达旨意而增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洪秀全不得不默认了杨、萧的神权。而这一妥协得以延续,也是自起义以来太平天国中神权与皇权共存的根本原因。
太平天国建立政权后,一套与神权并行的世俗权力也在运行着。在这一权力体系中,洪秀全是奉天承运的人间君主,是政权的代表,权力涵括了太平天国的各个领域,正如洪秀全自称的“普天之下通是爷哥朕土”“天下万郭人民归朕管,天下钱粮归朕食”。但洪秀全在世俗权力中的地位并不是绝对的,拥有“最高神权”的天父杨秀清一再把神权的手伸到了世俗中来,进一步制衡和压抑他的权力。由于杨秀清担任着军师(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军师制),主持军政事务,所以他既掌握着最高神权,又实际地掌握着世俗政权。洪秀全的天子地位虽未动摇,但贵为君主的权力却被架空了。
(二)拜上帝教无力为太平天国权力结构提供合理解释,预示天国内讧的必然性。在中国,神权必然要依附于君权。这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文化中的一般规律。符合这种规律的才能长治久安,否则就容易自乱阵脚甚至覆亡。这是因为,与西方的封建社会相比,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要淡薄得多。像西方那种由教皇给国王加冕的事是不会发生的;相反,中国历史上某些佛教、道教的头面人物倒要受皇帝之封方能称之为正统。农民起义者开始时虽以神权来号召,然终究也是权宜之计。神权从来都是君权的附属物,谁能打平天下谁就“君权神授”。这样,在传统中国,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之于君主统治而言:君权才是目的,宗教则是手段;君权是实,宗教是虚。朱元璋作为元末群雄角逐中的胜利者,在建立政权后不让白莲教的神权凌驾于自己的君权之上,就是这种典型的做法,也是遵循了一般规律的。而在这点上,由于拜上帝教本来就是“神道设教”这一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产物,没有从根本上扫除传统政治文化,所以它当然在天国的神权与君权争斗中显得苍白无力。
以此观之,太平天国在建立政权之后对神权不仅没有淡化反而不断强化,因而在洪、杨之间形成了二元化的权力结构。其间,要么是洪秀全除掉杨秀清以壮大他的君主权力,要么是杨秀清推翻洪秀全而自立为君主,已逐渐酿成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果。而历史事实正是这样发展的。经过天堂上兄弟们的血腥内讧,杨秀清的天父权力终被世俗的君主权力所颠覆,洪秀全则玩弄君权的神威以最不明智的方式和最惨重的代价解决了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实现了权力结构由二元化向一元化的回归。
(三)拜上帝教作为宗教意识形态在后期强力推行,加速了太平天国的衰亡进程。天京事变后,拜上帝教陷入困境,其思想凝聚功能日渐弱化,原来的教义和理论因领导集团的自相残杀而支离破碎。天国军民对拜上帝教普遍失望和冷漠,加之军事形势逆转,天国面临空前危机,军民思想更加混乱。洪秀全采取各种措施重新整合天国政治、军事和思想以挽救危局。但在意识形态上他仍然坚持以拜上帝教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进一步强化拜上帝教的神学体系,并配合强化中央集权和天王专制的手段,在军民中强力推行拜上帝教。这种执迷不悟、逆时代大势而动的做法,虽进一步神化了自己和洪氏王朝,形成神权和皇权的紧密结合,但也加速了天国神话和政权的彻底破产。拜上帝教的功能也因此发生质的变异,由动员和组织军民投身反清革命斗争的精神武器,蜕变为洪秀全加强皇权的理论武器,最终变成麻醉别人、也麻醉自己的精神鸦片,助推天国的历史走向终结。
四、拜上帝教作为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教训与启迪
拜上帝教从作为发动群众革命的舆论工具,到沦为腐蚀革命事业的精神鸦片,中间的教训与启迪十分深刻,值得人们为之深思。李大钊曾说:“他们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①《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541页。梁启超说:“洪秀全之失败,原因虽多,最重大的是他那种‘四不象的天主教'做招牌。”②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2页。
(一)太平天国的失败首先是非科学意识形态的失败。恩格斯早就说过:“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66~667页。马克思也曾指出:“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页。拜上帝教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意识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相杂揉的产物,它用神学观点解释战争胜败的原因,预言革命发展前景,回答前进中所碰到的难题。它把一切都归之于上帝安排,抹煞人的主观能动性,认识不到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本质,找寻不到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以这种落后的理论指导革命战争,去面对强大的敌人,焉能不败?
19世纪中叶,中国封建主义的统治日薄西山,面对列强入侵,封建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伴随着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封建制度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在推翻旧的统治阶级的同时,建立一个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政治体制。但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却试图在宗教旗帜下,用绝对平均主义的政治纲领,去实现乌托邦式的小农理想;又按照他们的小农理想,去建立一个新的封建王朝。这种旧的生产关系的翻版,既不能代表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因此尽管天国的理想深入人心,然终究理论落后于时代和形势,仍避免不了被淘汰的结局。太平天国的失败深刻地说明:不结合中国实际,没有新的经济基础作依靠,不解决时代提出的根本问题,任何理论都将是“镜中花”“水中月”,是地道虚假的意识形态。无怪乎,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批评“太平天国实质上乃是一种完全空洞的运动”①《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40页。。
洪秀全等人用以凝聚人心的拜上帝会虽来源于西方的基督教,却揉进了浓厚的中国封建迷信色彩。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缺乏与中国社会现实相一致的理论依据和精神指向,它在起到与历代农民起义一样的借神起事的作用之后便黯然失效,甚至成了促其走向败亡的精神催化剂。而太平天国把这种宗教迷信作为军队教育的精神支柱,更是缺乏恒久激励的动力源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天堂的理想无法实现,宗教迷信的欺骗性和天国理想的虚妄性,也就必然为人们所识破。实践生动地表明,宗教的迷狂是不可能铸就持久共同理想的。
(二)太平天国的失败也是非科学意识形态策略的失败。意识形态是具有强烈历史继承性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历代封建政权藉以教化和规范臣民思想行动、培育忠君爱国政治心理、巩固朝廷万世一系统治的成熟官方意识形态。洪秀全领导建立了新朝,以拜上帝教的教义和纪律为新朝官方意识形态。但无论从内容的丰富性还是从制度的成熟性来看,拜上帝教实在难以与有着两千年发展传承历史的儒家思想相比拟,在实践中明显不能适应新朝的政治需求。这迫切要求天国领袖对传统儒学和拜上帝教进行新的综合创新,以新的意识形态作为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准则,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和强化新朝统治。但是,洪秀全对以儒学为重点的中国传统文化采取的策略却是:以对物质武器的批判,代替科学的批判武器;以对儒学采取简单粗暴的批判手段,代替对孔孟学说进行系统深入的理性分析和科学借鉴。这无疑是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关键失策之处。而作为上述失策的重要后果是,文化人极少参加太平军。太平军中知识分子奇缺的可悲局面,给农民运动发展带来了严重损害,使他们最终未能战胜用传统文化武装起来的清朝军队,成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统治者。
(三)太平天国的失败还是非科学意识形态政策的失败。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践证明,意识形态的建立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构筑工程,必须破立结合,重在建设。然太平天国为推行拜上帝教,采取了文化专制政策。按照洪秀全的规定,凡不拜上帝者,或拜一切邪神、妄题上帝之名者,都是死罪。信教与否,竟成了是否犯罪的标准。他甚至还将一切“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对此,马克思尖锐地批评道:“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立。”②《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137页。无疑,太平天国在这儿的失败之处,也应是后人引为鉴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