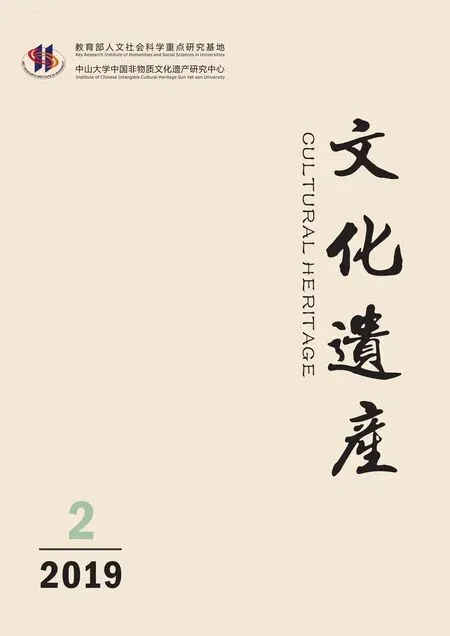论演戏酬神对清代禁戏政策的消解*
张天星
清代是中国古代禁毁戏曲最频繁的朝代,清代统治者把观念性禁戏与制度性禁戏相结合,将禁戏力度和规模推至高峰。但是清代禁戏为何屡禁不止、愈禁愈演?这是清代戏曲研究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目前,学界认为清代禁戏屡禁不止现象的主要原因有:观众喜爱观剧[注]张勇风:《中国戏曲文化中的禁忌现象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第264-277页。;清朝对社会监管力度减弱、社会道德观念松动[注]刘 庆:《管理与禁令:明清戏剧演出生态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23-246页;金坡:《愈禁愈演:清末上海禁戏与地方社会控制》,《都市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作为主要消费群体的商人偏好淫戏的娱乐诉求[注]魏兵兵:《“风流”与“风化”:“淫戏”与晚清上海公共娱乐》,《史林》2010年第5期。;夜戏难禁是由于乡村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崛起、日渐奢靡的消费文化以及利益驱使的复合产物[注]姚春敏:《控制与反控制:清代乡村社会的夜戏》,《文艺研究》2017年第7期。。这些观点皆有根有据,丰富了对清代禁戏屡禁不止现象的认识。但综合来看,仍缺少风俗视角,特别是演戏酬神习俗的视角。有学者认为清代行政权威力量无法同约定俗成的民俗民风相对抗是迎神赛会难以禁止的根本原因[注]荣 真:《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研究—以三皇和城隍为中心》,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6年,第98页。。该观点启示我们:清代禁戏屡禁不止与风俗习惯关系莫大,因为迎神赛会,一般皆要演戏。于此,本文从演戏酬神习俗着眼,考察清代演戏酬神如何能消解官方禁戏政策,以深化我们对清代禁戏屡禁不止现象的认识。
一、习俗相沿,消解禁令
演戏酬神是通过演戏的方式祈神、敬神、酬神,根据演出场地和目的一般可分为庙会戏、还愿戏、行业戏和祠堂戏四种。演戏酬神在清代一般例所不禁,要因有四:其一,演戏酬神源于先秦已成定制的赛社习俗,风俗相沿,根深蒂固,难以革除;其二,清代统治者倡导神道设教,“‘神道设教’,通行于古今中外。清史或近代史表明,满洲列帝,对这一点格外认真。”[注]朱维铮:《重读近代史》,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180页。清代官员发现百姓“多不畏官法,而畏神诛;且畏土神甚于畏庙祀之神。”所以要有意提倡,培养百姓的鬼神敬畏意识,“司土者为之扩而充之,俾知迁善改过,讵非神道设教之意乎?”[注](清)汪辉祖:《学治臆说》,见《官箴书集成》第5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28页。其三,演戏酬神的娱乐功能符合圣人一张一驰之教,有利于社会秩序稳定;其四,演戏酬神的商业功能有利民生。从这些因素出发,清代官方对演戏酬神一般采取例所不禁的管理政策。雍正四年(1726),朝廷承认民间演戏酬神的合法性:“在民间有必不容己之情,在国法无一概禁止之理。”[注](清)蒋良骥撰,鲍思陶、西原点校:《东华录》,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447页。乾隆元年,乾隆朱批否定了广西右江总兵潘绍周请禁赛神的奏折:“民终岁勤劳无一日之乐事,岂非拂民之性哉?将此谕亦告督抚知之。”[注]哈恩忠编选:《乾隆初年整饬民风民俗史料》(上),《历史档案》2001年第1期。乾隆甚至批评奏请禁迎神赛会,“属不经之谈。”[注]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清实录〉广西资料辑录》(一),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3页。在不碍农事、无妨治安、不演违禁剧目的前提下,演戏酬神“不在禁限”。[注]丁淑梅:《中国古代禁毁戏剧编年史》,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66页。由于清代官方对演戏酬神采取宽禁政策,加上多神信仰遍及华夏、观剧娱乐蔚然成风,清代中后期演戏酬神相比前代,愈加繁盛,因为祀神不演戏,“无以体神心而娱神志。”[注]杜海军辑校:《广西石刻总集辑校》(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77页。清代中后期也是官方禁戏最频繁的时期,令统治者始料不及的是,如火如荼的酬神演戏却成了消解官方禁戏政策的“化骨绵掌”,从根本上抵消禁戏法令,造成禁令难以执行。措其大端,主要表现在搬演夜戏、喜演情色戏、妇女观剧、偏好地方戏等方面。
(一)夜间酬神习俗消解夜戏禁令。清代禁演夜戏属全国性法令,雍正十三年(1735),朝廷首次颁布夜戏禁令。乾隆二十七年、嘉庆七年、嘉庆十六年,清廷又先后重颁夜戏禁令。清代之所以禁演夜戏,要因有二:一是道德风化之忧。夜晚观剧,男女混淆,危及男女之防的伦理道德秩序。二是社会治安之虞,“恐致生斗殴、赌博、奸窃等事。”[注]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第20页。清代地方官把禁止夜戏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不唱夜戏,地方可省无数事端,村邻可免许多拖累。”[注]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第103页。对不实力奉行查禁夜戏的地方文武官员,《钦定吏部处分则例》规定:“罚俸一年” 。[注]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第20页。但实际执行中,夜戏禁令屡被演戏酬神者违反,寻其要因,除乡村夜戏监管较城镇松懈、民众夜晚娱乐需求驱动等因素外,夜间祀神习俗与夜戏共生亦关系莫大。
清朝各地一般皆有夜间祀神传统,夜戏亦如影随之。元宵节一般认为源自先民岁首用火祭祀、驱邪避难的仪式,元宵习俗的基本面貌于隋代定型,唐代元宵金吾不禁成为传统:“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注]陈伯海:《唐诗评汇》(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27页。降至清代,元宵持续时间比明代更长,有的为15天,有的甚至达到19天。元宵节前后,夜戏盛行,相沿成俗,如乾隆三十五年《光州志》、乾隆《蓬溪县志》、嘉庆十五年《绩溪县志》等方志的“风俗”或“时令”卷,皆有张灯演剧的记载[注]彭恒礼:《元宵演剧习俗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48页。。清朝中后期,其俗不让前代。绍兴元宵节前后,各庙皆张灯结彩,兼有演戏敬神,“通宵达旦,热闹非常。”[注]《兰亭问俗》,《申报》1898年2月12日第2版。安徽祁门元宵前后“行傩演剧。”[注]周巍峙主编;卞利、汤夺先本卷主编:《中国节日志·春节·安徽卷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174页。南昌每届元宵前后,赌赛灯戏,更有扮演高脚戏,卜昼卜夜,举国若狂[注]《春灯类志》,《申报》1880年3月11日第2版。。元宵之外,各地酬神夜戏名目亦复不少,嘉定县城每逢丰稔之年,必于二月中赛迎灯会,抬阁搬演杂剧[注]《宝灯类志》,《申报》1885年4月17日第3版。。温州东岳庙元帅会每于三月三日夜出庙,又须十余日方能蒇事,所到之处,悬灯结彩,百戏杂陈[注]《赛会纪盛》,《申报》1882年6月2日第2版。。甚至官方还是夜戏酬神的组织者,在广东海阳,正月有青龙庙安济王会,迎神出巡,“大小衙门及街巷各召梨园奏乐迎神”“凡三夜,四远云集”。[注]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第7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5页。为俯顺民意,地方官还要维护治安、保障夜戏秩序。厦门中元节各处盂兰盆会称为普度,每值普度,金吾不禁,道路为戏台拦阻,全街大小戏台至少十余处,举国若狂,彻夜通宵。官方派遣文武委员,按段梭巡,维持治安,并不禁止[注]《秉公无私》,《申报》1893年9月11日第2版。。厦俗四月十五日为五殿阎王诞辰,各酒馆饭店因每年宰杀鸡鸭,深恐愆尤,每届是日,拦街搭台,搬演夜戏,“笙歌彻夜,裙屐如云”。[注]《鹭江谈屑》,《申报》1892年5月28日第2版。厦门官方对拦街搭台、酬神夜戏的许可,是法令对人情习俗的屈从。一旦夜戏酬神成为向例,官方禁止,则会遭到地方力量的抵制,禁令遂成具文。宁波城内,每于九月迎赛大庙菩萨,并循例搬演夜戏。1878年,宁波知府谕令只许迎神,不许夜演,当菩萨驾驻醋务桥行宫时,年例该处于九月十三、十四两日夜演。该处某巨绅并不赴府署商请,公然违令,于十三日当街搭台,雇班夜演,观者塞途。观望者闻之,十四日夜纷纷开台,城中夜戏竟达十余处[注]《违禁夜演》,《申报》1878年10月15日第2版。。“某巨绅”之所以敢公然违抗夜戏禁令,除了自恃其势力外,显然还有夜间酬神习俗的凭借,纷纷开台,则法难责众矣。1888年九月,宁波城内夜晚舁神出巡、搬演夜戏的习俗仍在循例举办[注]《甬上近闻》,《申报》1888年10月28日第2版。。演戏酬神之所以能突破夜戏禁令,民众夜间娱乐欲求虽说是违禁的动力之源,但夜间循例酬神才是合理借口。官方若不能革除夜间祀神习俗,则禁止夜戏不亦难哉!
(二)酬神演戏兼具的娱神娱人习俗消解情色戏禁令。情色戏属于所谓的淫戏。从一些禁令、日记、报刊、小说提及的演戏酬神剧目中,可知一批违禁的所谓淫戏在酬神剧场上盛演不息,如《卖胭脂》《杀子报》《翠屏山》《珍珠衫》等[注]《演戏酬神》,《申报》1896年3月26日第3版。《戏场肇祸》,《申报》1895年8月14日第9版。《古潞杂言》,《申报》1897年6月23日第2版。《潞河锦缆》,《申报》1897年5月13日第2版。《戏场肇事》,《申报》1898年10月31日附张。,它们基本属于包含情色关目的爱情剧,甚至神庙剧场,生旦“相搂相抱,阳物对着阴户,如鸡食碎米,杵臼捣蒜一般”,[注]齐文斌主编:《明清艳情禁毁小说精粹》卷3《妖狐艳史》,延吉:延边出版社2000年,第181页。当众宣淫。但这仅是冰山一角,酬神剧场还上演许多今天已不知名目的荤戏和淫秽关目。清代道德之士指责酬神剧场“淫戏”风行:“闻各处演戏敬神者,靡不点粗俗淫荡各剧。”[注]《论酬神宜禁淫戏》,《申报》1892年12月4日第1版。并痛心疾首地呼吁不要“点淫戏敬神明。”[注]鸳湖知非氏:《淫戏为害》,《申报》1879年6月25日第3版。此类指责虽不乏偏见,但许多也确属实情。
撇开情色剧目和淫秽关目娱乐性强、戏班和伶人迎合观众趣味不谈,搬演情色乃至淫秽关目还是先秦祀神娱神和婚恋礼俗的遗存,源远流长。先秦社祭除土地崇拜外,在交感巫术的启示下,还融入了生殖崇拜,先民认为社祭时男女交媾可以促进风调雨顺、土地增产。社祭中有神附体的尸,《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记载鲁庄公不听曹刿劝谏,到齐国观看社祭,其实是想观看尸女表演,“所谓‘尸女’,即女人呈裸体,献身生殖神,可与任何人进行性交祭祀。”[注]陈炎主编:《中国风尚史·先秦卷》,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15年,第280页。尸女献身于神,既是生殖崇拜,也是娱神方式。原始巫术认为神与人一样有癖好,有情欲,祭神要投其所好,当然需要以色相媚神娱神。春社之日是男女奔者不禁之时,燕、齐、宋、楚等国神社祭祀时,“男女之所属而观”。[注](清)毕沅校注,吴旭民校点:《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6页。所谓“属而观”,就是男女青年集在一起观看性交表演,然后分散择偶野合[注]宋公文、张君:《楚国风俗志》,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62-263页。。伴随伦理道德观念渐渐加强,此类性表演在秦汉以后的社祭中慢慢淡去,但从未消失,在部分地区的演戏酬神中仍属保留节目,即神爱看戏,且喜看荤戏。山西上党奶奶庙的喜神不仅爱看戏,而且要看荤戏,即表现男女调情故事的喜剧,如《闹五更》《秀才听房》之类的剧目[注]刘文峰:《志文斋剧学考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第208页。。神庙在搬演荤戏时,要提前清场,不让妇女和儿童观看,因为这些荤戏多私媾之事,妇女儿童不宜观看[注]曹飞:《敬畏和喧闹:神庙剧场及其演剧研究》,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第140页。。潞城县贾村碧霞宫(俗称奶奶庙)演剧的习俗是先在庙内戏台开演约一个小时的队戏,然后庙外戏台的大戏才能开演。队戏表演中总要加入一些内容粗俗、表现男女性爱的荤戏,“一般不准妇女、小孩观看。”[注]段友文:《黄河中下游家族村落民俗与社会现代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03页。湖南沅澧地区在求子、上锁、婚丧寿庆、禳灾祛疾、祈蚕等的仪式中,都要搬演情色内容的荤戏,以便向傩神祈求[注]王荫槐:《嘉山孟姜女传说研究》(下卷),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1页。。诸如此类说明,演戏酬神中两情相悦乃至猥亵鄙俗的表演习俗渊源有自,它是上古祭祀以色娱神和生殖崇拜风俗的遗存,“当戏剧脱离祭祀仪式,走出神庙时,插科打浑、猥亵俚俗的一面依旧保留不变……荤秽表演仍然比比皆是。”[注]白秀芹:《迎神赛社与民间演剧》,中国艺术研究院2004年博士论文,第34页。貌似庄严的酬神剧场,并不排斥情色表演,甚至色情表演还是必备节目。今天看来,清代酬神剧场流行的“淫戏”,一类属于爱情戏,可以通融;一类则是低俗淫秽的荤戏,尽管有上古遗风,但大庭广众,公开搬演,的确诲淫。官方和道德之士指责演戏酬神“所演之戏,半多淫靡”[注]《云间雁信》,《申报》1890年9月8日第2版。,不无道理。
(三)全民参与酬神习俗消解禁止妇女观剧禁令。清代禁止妇女看戏的禁令、行动、族规、闺训和社会舆论纷纭:“清代禁毁戏剧观演活动,有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对妇女观剧的禁阻。不但家训闺箴、女德女教中充斥着妇女勿看戏的言论,官方文告、朝廷谕旨也屡屡禁止女性观众出入戏场。”[注]丁淑梅:《中国古代禁毁戏剧编年史》,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20页。北京、苏州、杭州等城镇戏园直至清末仍禁卖女座,上海租界戏园售卖女座还曾引发过激烈争论。但有清一代,妇女出入酬神剧场风气之兴盛,远迈前朝。清初王应奎见到的江南旷野演戏酬神“观者方数十里,男女杂沓而至”,“约而计之,殆不下数千人焉”。[注](清)王应奎:《柳南文钞》卷四《戏场记》,转引自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这种情形在清中后期愈发不可收拾,戏曲繁盛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南方省份姑且不论,以京畿地区为例。京畿风气素称良谨,演戏酬神时,妇女观众如痴如狂。1891年3月,通州东海子街演戏祀神 ,“妇女观剧,另有看台,粉白黛绿咸得列坐其中,大家闺秀则障以虾须帘,花枝隐现。”[注]《潞河鲤信》,《申报》1891年3月23日第2版。1893年3月28日,通州北街恭祀水火二神,雇京都义顺和班演戏四日,“檀板甫敲,簪裾纷至,看台三百余间,尚不能容。”[注]《潞水春鳞》,《申报》1893年4月11日第2版。可以说,从北到南,由城镇到乡村,在坚持男女分区的前提下,清代妇女可以自由出入酬神剧场。孕妇不宜看戏听曲的禁忌也被一些妇女抛之脑后,如腹大如瓠、即将临盆的妇女,也彳亍观剧[注]《平山堂茗话》,《申报》1893年7月27日第2版。。更甚者,竟有观剧妇女于剧场产子[注]《戏场产子》,《申报》1874年1月27日第3张。。如此风气说明:演戏酬神,妇女往观,乃清代妇女休闲生活之常态。
妇女参与全民酬神传统悠久,相沿成俗。上古社祭家家参与,人人踊跃,一国之人皆若狂,妇女概莫能外。春秋战国时期,燕、齐、宋、楚等国神社,每届社祭,都活跃着女性身影:“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注](清)毕沅校注,吴旭民校点:《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6页。社祭从一开始就没有排斥女性。其俗代沿,当社祭成为民俗节日之后,妇女还能偷得一日闲,外出游乐,唐代妇女每逢社祭:“今朝社日停针线,起向朱樱树下行。”[注](唐)张籍:《张籍诗集》,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第78页。直到晚清,全民迎神赛会的传统仍盛行不辍,如1889年四月初八日,天津府县牒请城隍厉坛赦孤,神鬼出巡,“道上游人如蚁,大家闺秀,则靓妆艳服,掩映于湘竹帘前,而小家碧玉,则露面抛头,几于在坑满坑,在谷满谷。”[注]《鬼会》,《申报》1889年5月21日附张。迎神赛会,倾城妇女外出游观,沿袭的正是传统习俗。
一般认为,迎神赛社兴起于宋代,作为集体狂欢活动,妇女不但参与其中,而且还可出入赛社剧场,刘克庄《闻祥应庙优戏甚盛》二首之一云:“游女归来寻坠珥,邻翁看罢感牵丝。”[注](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21,清抄本。《即事》三首之一云:“抽簪脱裤满城忙,大半人多在戏场。”[注](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21,清抄本。明代开始,礼教对妇女的禁锢趋于严格,尽管有等文人呼吁禁止妇女看戏,但官方禁止妇女看戏的法令并不多见,明代妇女看戏所受阻力相对较小,如杭州春台戏“士女纵观,阗塞市街。”[注](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366页。苏州春台戏,“士女倾城往观,岁以为常。”[注](清)褚人获辑撰:《坚瓠秘集》,见《清代笔记小说大观》(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945页。入清以后,演戏酬神,妇女往观,从未间断,并随着频繁的演戏酬神而观剧机会更胜前朝。妇女往观演戏酬神,一般能得到官方或家人的许可。清代北京、苏州、杭州等城镇的戏园,皆禁售女座。但这些地方,妇女偏可以观看庙社演戏,如“杭垣戏园禁妇女看戏,惟庙社演剧,则不在禁例,而妇女之伴绿携红,约群同往者,固不特小家碧玉,巨室青衣等而已也。”[注]《妇女观剧受辱》,《申报》1874年12月17日第3版。说明杭州地区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皆可观看庙会戏。1890年秋,黄梅知县先期出示,严禁妇女看会,以免滋生事端,会期已过,方准妇女入庙观剧,“连日鬓影衣香,粉白黛绿,呼姨挈妹,络绎于途。”[注]《柴桑秋色》,《申报》1890年10月16日第2版。清代官员对妇女出入酬神剧场的允许,是对千百年来全民参与赛会习俗的遵行。
(四)演戏酬神偏好地方戏消解了地方戏禁令。清代中期开始,伴随地方戏的兴起,出现花雅之争,官方和正统文人从坚持雅正文化政策的立场出发,对地方戏实行查禁抑制的管理政策,“直到清代后期的同光年间,执政者始终严格查禁花部乱弹、地方戏等,查禁滩簧、花鼓戏、评弹的禁令屡屡颁行。”[注]赵维国:《教化与惩戒: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禁毁问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1页。宁波串客、髦儿戏、花鼓戏、采茶戏、蹦蹦戏、东乡调、滩簧、香火戏、黄梅调、七子班等地方戏既被官方频繁查禁,也被道德之士口诛笔伐。令官方和道德之士意想不到的是,由于酬神剧场是地方戏观演的重要场所,例所不禁的演戏酬神反而为花鼓、采茶等地方戏提供了大量演出机会。如官方查禁的采茶戏,南昌、新建等县属各乡,“借口春赛秋报,或遇神诞,”雇演采茶戏[注]《移风易俗》,《申报》1899年5月12日附张。。嘉道以来,福建官方严禁七子班,但在厦门等地演戏酬神的竞争中,雇七子班相对便宜,“其无力雇官音大班者,则雇傀儡戏及本地七子班以代之。”[注]《鹭岛纪闻》,《申报》1887年5月23日第3版。七子班也从未缺席泉漳地区的演戏酬神活动。花鼓戏是清代中后期官方查禁次数最多、查禁地区最广的地方戏,也是愈禁愈演。湖北楚北、武汉各乡间如值岁收稔丰,农民每于上元节敛钱玩灯、演唱花鼓,谓可保一方平安,“此风由来久矣。”[注]《禁演淫戏》,《申报》1882年3月21日第2版。江苏华亭县乡村春间迎神赛会搬演花鼓戏的传统始则于乾隆年间,光绪初年,仍盛演不衰[注]《(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二十三《杂志》,光绪四年刊本。。花鼓戏等地方戏既有参与酬神的传统,又能谐于里耳,且戏价更廉,场地要求不高,“小班价廉,乡间易演。”[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页。在官方禁阻和舆论的打压声中,酬神演戏为地方戏提供了大量堂而皇之的演出机会。
酬神演戏偏好地方戏根源于酬神赛会的乡土情结和传统。演戏酬神的表演人员来源,不外三种:一是外聘戏班,二是本地土班;三是民众自演自娱的扮演。不论哪一种来源,都面临一个“谐于耳”即民众听得懂的检验。并且既曰演戏酬神,不仅要谐于民众之耳,而且要谐于神之耳,“凡神依人而行,人之所不欣畅者,神听亦未必其平和也。”[注](清)江永:《律吕新论》,吴钊等编:《中国古代乐论选辑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年,第388页。所以演戏酬神要尽量入乡随俗、采用地方民众皆能听懂的土音,而这正是地方戏之优长。又者,汉代以来,民间迎神赛社中社火表演传统从未间断,与社火关系密切的采茶、花鼓、秧歌等地方戏,自然而然融入到迎赛队伍之中,成为迎赛习俗,或用“小童扮演地戏,杂入会中”[注]《杨王庙会》,《申报》1876年3月14日第2版。,或花鼓、秧歌等竞相出会[注]《都门纪事》,《申报》1885年7月25日第2版。,或唱滩簧、演傀儡相互比赛[注]《芜湖琐缀》,《申报》1886年8月26日第1版。,或敲锣前导、演唱花鼓[注]《袁江尺素》,《申报》1885年4月20日第2版。。迎神赛会有扮演地方戏传统,观众甚至神灵有地方戏偏好。于是,被官方查禁和舆论抨击的地方戏纷纷在演戏酬神的剧场上搬演。迎神赛社不仅是地方戏滋生、成长的温床,而且还是地方戏遭遇禁阻时的护身符。
二、利益裹挟,对抗禁令
酬神演戏对清代禁戏政策的消解,不仅表现在习俗和法律的冲突上,还表现在观演者、组织者乃至监管者的多种利益诉求与禁戏政策的抗衡上。在这些利益诉求的驱动下,例所不禁成为违禁观演的幌子,“有司官差役往查,辄托名酬神愿戏,或又称春祈秋报,农民例申虔福。”[注]《违制演戏》,《新报》1881年6月14日第2版。法难责众,禁管困难。
其一,全民藉演戏酬神的娱乐需求对抗禁令。清代从官方到民间,从封疆大吏到里巷细民,从行业会首到庙祝观主,无不借故演戏酬神、享受观剧之乐。每逢官方认可的神诞乃至祈雨禳灾,演戏酬神,官员亲自参加,奉行如常[注]《演戏酬神》,《申报》1880年10月28日第2版。。官员升迁、军队检阅,也多演戏酬神之举[注]《演剧酬神》,《申报》1886年11月17日第3版;《茸城雁帛》,《申报》1886年11月9日第2版。。民间庙会戏、行业戏、祠堂戏、祈雨戏等一般按村社行业,摊派戏资,全民参与、藉酬神以满足娱乐之需。摊派遵循一定标准,乾隆四十五年樊先瀛《保泰条目疏》提到,山西乡村戏会,按地亩人丁牲畜摊派戏资,“由来已久。”[注]丁淑梅:《中国古代禁毁戏剧编年史》,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12页。芜湖中江一带渔户每届仲夏醵资演戏、以邀神贶,所费是按照春末夏初所捕鳗鱼的尾数抽厘[注]《渔家乐》,《申报》1894年7月15日第3版。。清末民初河南怀庆府地方演戏酬神,敬火神按房屋多寡摊派;敬关帝、财神由店铺捐资;敬土地、龙王按地亩多少分摊;敬老君、祖师由工匠出资;奶奶会按儿女多少或向求儿求女者征收;牛王会由各饲牛户分担;马王会则为“马出钱、牛管饭”。其他逢节日演戏均按地亩、人口分担[注]王建设:《从豫西北遗存古戏楼看清末民初怀庆府地区戏曲活动》,《戏曲研究》2012年第3期。。分摊戏资是民众融入村社集体或行业组织,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重要途径。晚清不少教案的导火索即是由教民不愿摊派戏资而引燃,说明试图与全民性演戏酬神对抗的后果往往是极其严重的。[注]需要注意的是,戏资一般并非单独收取,在农村,戏资往往和看青支更、演戏酬神、修理庙工、村庄团练等费用一起收取,如果个人不缴纳这些费用,属自绝于村落族群之举。。酬神剧场,举国若狂,清初但凡某处演戏酬神,“哄动远近男妇,群聚往观,举国如狂”,[注](清)陈宏谋辑:《五种遗规》,北京:线装书局2015年,第252页。清代中后期酬神观剧更加兴盛,“远近来观、万人空巷”[注]《上海巡局琐案》,《申报》1892年4月19日第3版。“男女老幼、人海人山”[注]《平湖秋月》,《申报》1893年8月19日第3版。面对这种狂热的观剧享乐场面,禁阻无异于焚琴煮鹤、大煞风景,殊招人怨。
其二,集体性演戏酬神的组织者众多,各怀利益以对抗禁令。集体性演戏酬神组织者主要有士绅、地保、差役、会首、执事、庙祝、棍徒、班主、商贩等,藉演戏获利者不乏其人。据目的之不同,可将他们分为三类:一是清正廉明的组织者。演戏酬神是基层社会或行业生活中的公益盛事,一次成功的演戏酬神活动,既可展示族群、村落或行业的凝聚力,也可彰显组织者的领导魄力,进而提高组织者在基层社会的威信和声誉。为了赢得和保持良好威望,他们会认真循例组织好每一次演戏酬神。二是从中敛钱的组织者。演戏酬神的费用或按户醵资,或从族群、村落和行业公款中拨设专款,组织者则可乘机从演戏酬神费用中敛钱肥己,“科敛民财,半充囊橐。”[注]《禁搭台演戏告示》,《中国古代禁毁戏剧编年史》,第334页。他们会积极张罗、奔走前后,甚至对不愿醵资者,“逞凶吓唬。”[注]《广东海康县北和圩碑禁戏文》,《中国古代禁毁戏剧编年史》,第498页。藉庙观演戏酬神、增加香火钱的庙祝观主也可归于此类,他们会因演戏酬神之际大获香资而欢喜无量[注]《帝京杂记》,《申报》1886年5月4日第2版。,鼓动附和。三是开场聚赌的组织者。清代赌风极盛,“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编氓徒隶,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注](清)钱泳:《履园丛话》,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78页。演戏可以招集多人,聚赌抽头,“欲图聚赌,必先谋演戏。”[注]来蝶轩主:《请弛青浦县属朱家角镇戏禁意见书》,《申报》1911年6月25日第3张第1版。于是,棍徒“借各庙神诞为名,妄称酬应演戏,因而大开赌场。”[注]《道札严禁演戏赌博》,《申报》1906年10月16日第17版。赌棍人等也是演戏酬神的积极组织者。当然,这三类组织者并非判然区分,现实中,组织者为敛钱、为声誉、为聚赌的目的往往兼而有之,他们或为地方实力派、或本就是不安分之徒,一旦遇禁,常会鼓动观众,与禁阻者为难。因人多势众,官府往往只得折中妥协、息事宁人[注]《众怒难犯》,《申报》1878年6月1日第2版;《穗垣琐事》,《申报》1884年9月13日第3版。。
其三,禁戏的监管者常藉酬神演戏牟取私利,知法犯法。清代基层社会禁戏的监管者主要是绅士、差役、地保等,他们藉演戏酬神谋取私利属普遍现象:有的绅士和县差营役得规包庇,致使府县对违禁演戏毫无闻见[注]《高安赌风甚炽》,《新闻报》1907年7月19日第4版。;有的府县差役向诸班主收取规例,预为关照[注]《演戏纪始》,《申报》1882年3月11日第2版。;有的州县衙门差役常持十禁牌下乡开展禁戏等事,实则藉以敛钱,地保也从中勒索[注]《地保勒索》,《新闻报》1897年9月17日第9版。。在清代禁戏告示和舆论中,对绅士徇隐、差役包庇、地保容隐之类的警告和指责不胜枚举,组织者、观演者和监管者串通姑纵、中饱隐瞒,“比比皆然也。”[注]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16页。说明从官府到民间对此现象皆心知肚明,只是力有不及而已。监管的乏力和故纵,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演戏酬神成为违反官方禁戏政策的温床,禁者自禁、演者自演。
由于集体性演戏酬神一般多或少地裹挟着娱乐、酬神、声望、敛钱、陋规、赌钱、商业等多种利益诉求,一旦开演,任何禁阻都可能致干众怒,清代中后期,禁戏活动中经常发生殴差抗官的群体事件,原因即在于此。1895年秋,袁州游桥地方藉赛会演戏聚赌,差役得贿包庇,袁州知府惠格只得亲自带领亲兵数人往禁,赌徒恃众拒捕,观众一呼百应,将亲兵殴成重伤,惠格头额也被击破、血流如注[注]《太守被殴》,《申报》1895年11月5日第2版。。清人认为春祈秋报、村社演戏赛会之事,有管理之责的地方官最害怕“逆民志而启争端。”[注]《论南昌大傩》,《申报》1879年7月9日第1版。可谓一语中的。当演戏酬神成为民众堂而皇之的习俗和多种利益诉求的集合体之后,官方禁戏法令就会被消解乃至公然违反,“乡村信神,咸矫诬其说,谓不以戏为祷,则居民难免疾病,商贾难免风涛,是以莫能禁之。”[注](清)汤来贺:《内省斋文集》卷七,清康熙刻本。官方和道德之士只能徒唤奈何。
结语
演戏酬神对禁戏政策的消解不尽上述,还包括女伶演剧、男女合演等禁令的违禁,特别是活跃在酬神剧场上的民间小戏,在剧种、剧目、女伶登台、男女合演等方面,较全面地挑战官方禁令:“春秋佳日,乡间报赛,演戏酬神,所演淫戏,亦时有之,甚至有一男一女,扮演花鼓淫戏,万人空巷,举国若狂。”[注]《论淫戏之禁宜严于淫书》,《申报》1896年9月15日第1版。违禁的花鼓戏在酬神剧场搬演,女伶登场,甚至男女合演。当然,演戏酬神也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向禁戏法令的遵从,如酬神剧场严格男女分区观剧、一些地方立碑禁演夜戏或花鼓戏[注]徐宏图:《浙江戏曲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年,第238页;周立志编著:《史说益阳》,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4页。、组织者承诺不演戏聚赌和扮演淫戏[注]来蝶轩主:《请弛禁青浦县属朱家角镇戏禁意见书》,《申报》1911年6月25日第35版。等,但笔者认为相比演戏酬神对禁戏政策的消解而言,此等举措收效甚微。有研究者认为,古代迎神赛会具有强烈的狂欢精神,表现出反规范性,对传统规范“具有一种潜在的颠覆性和破坏性。”[注]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02年,第134页。此有以之言。本文探讨可见,作为迎神赛会衍生节目的演戏酬神亦具有反规范性,主要表现为对官方禁戏政策的违反。更关键的是,地无论东西南北,人无论男女老少,一年之中,酬神观剧竞繁,成为戏曲观演常态,组织者、观演者和监管者的酬神、娱乐、敛钱、聚赌、陋规等诸多利益诉求又裹挟其中,法难责众。各地酬神演戏“殆无虚日”“无日无之”[注]清人常用“殆无虚日”“无日无之”来形容各地演戏酬神之频繁,如:“浦郡自二月以來,城乡村镇演戏祀神者殆无虚日。”(《古潞近闻》,《申报》1887年5月22日第11版)“杭垣各社庙台戏无日无之。”(《台戏弛禁》,《申报》1878年6月6日第2版)地搬演,意味着官方禁戏政策也被常态化地违反,国家法令的强制性、规范性、普遍性被撕裂的千疮百孔,相关禁戏法令焉能树立权威、认真执行?
演戏酬神对清代禁戏政策的消解,本质上是习俗与法律之间的矛盾。习俗是法律的基础,在社会秩序的维护上可以对法律起到辅助作用。习俗一旦形成,就融入人们的意识和行为之中,历久相传,具有牢固性,法律很难渗入习俗的内部、规范习俗。习俗对社会成员具强烈的行为制约作用,具有刚性,在法律实施中突显阻碍作用,特别是当习俗成为惯例后,就会“以不同意的方式来对抗偏差。”[注][德]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页。如果立法没有考虑到习俗的牢固性和刚性,当法律与习俗发生冲突时,民众会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习俗,由此导致执法成本提升乃至法律根本无法执行。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清代官方对演戏酬神一般采取例所不禁的管理政策,是对习俗的尊重,却没有顾及到演戏酬神本身与搬演夜戏、喜演情色戏、妇女观剧、偏好地方戏等习俗同生共长、难以剥离,而这些习俗与官方相关禁令又是矛盾抵牾的,由是造成习俗对抗禁令,加上打着例所不禁幌子的多种利益博弈其中,更增加了禁令的执行难度。清代演戏酬神对禁戏法令的消解也启示我们,法治渗入习俗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立法和执法应充分考虑到习俗的刚性,既要看到习俗与法治存在转化互补之处,也要看到二者相互冲突的地方,实现法治与习俗的良性互动。国家法治如此,文艺管理的立法与执法亦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