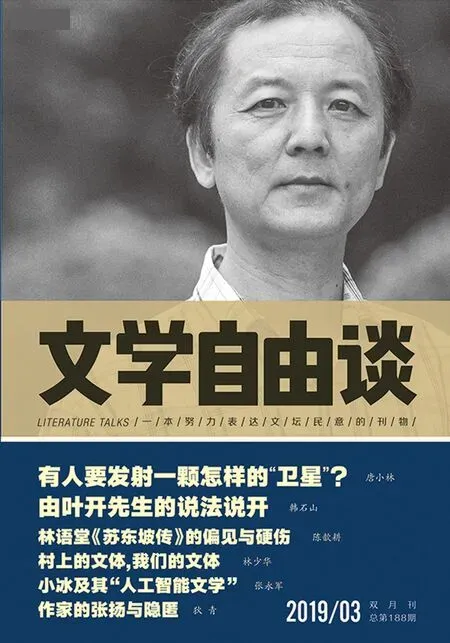欧美文学中的男家庭教师
□刘世芬
欧美文学的许多名著中,都有一个出场不多但又颇耐人寻味的角色——不是管家,不是保姆,不是车夫,不是园丁,更不是厨师,而是孩子的家庭教师。
相对于家庭女教师对欧美文学的“贡献”,家庭男教师“有故事”的似乎不多,但即使只有少数作品,比如《红与黑》《九三年》《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仍以极大笔墨渲染了一个个形象各异的男家庭教师形象,而这些男家庭教师已经从“路人丙”晋升为男一号。这不得不让我检视自己以往对家庭教师的偏见——“家庭教师”,并非只是女性的代名词啊!我发现,男家庭教师貌似沉默,然而一旦“讲”起故事来,似乎比家庭女教师更“有料”。
司汤达的《红与黑》,奠定于连在维里埃市长德·莱纳先生家里的地位的,是刚到市长家时别开生面的“考验”。于连对孩子们说:“先生们,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教你们拉丁文。”——我在这里自作主张“截断”一下,拉丁文为何如此影响十九世纪的欧洲?你看于连因为懂拉丁文,几乎被维里埃市甚至整个法国宠起来,以至当谢朗神父带他到市长家时,市长夫人竟把八十岁的谢朗神父当作孩子们的拉丁文老师——你怎么能要求她把乳臭未干的于连想象得那么博学呢?
是的,看于连在市长家的架势,以及人们对他的欢呼,彼时的拉丁文直接就代替了“博学”这个词。放在历史长河中,当基督教普遍流传于欧洲后,拉丁语更爆发其影响力。从欧洲中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叶的罗马天主教,拉丁语成为公用语,学术论文也大多由拉丁文写成。罗马帝国崩溃后,虽然拉丁语作为口语很早就消失于民间,而它作为教会、学术和文化的专用语言却延续了一千多年。十九世纪的法国的确存在着拉丁文崇拜,掌握拉丁语已经成为法国精英的象征。拉丁文有着极高的学习难度,由此可见于连的聪颖,他自幼跟谢朗神父学习拉丁文,可谓青出于蓝。
懂拉丁文已经至高无上,引起轰动的是于连对拉丁语《圣经》的倒背如流。看他初到市长家时对孩子们的“开场白”——“这是《圣经》,”他指给孩子们看一本三十二开黑面精装的小书,“我要常常让你们背诵,你们让我来背背看。”
对于市长家的所有人,接下来的一幕无异于好莱坞大片:于连让最大的孩子阿道夫随便翻开一页,随意找一段,把第一个字告诉他,他就一直背诵下去,直到喊停为止。果然,阿道夫念出一个字,于连就背下一整页。阿道夫把《圣经》翻到了几处,于连都背得像法语一样流利。这让于连大出“风头”。几个目睹这一场景的仆人瞬间被于连 “镇”住,发出一阵阵低呼。“考验”继续进行,于连又让市长的小儿子也随便指一段,他接着又背出了一整页。恰在这时,维里埃市的两个重要人物——瓦勒诺先生和专区区长夏尔科·德·莫吉隆先生来访,他们目睹了这一精彩场面,于连也由此赢得了对他称呼“先生”的尊重。他的名声在城中迅速传播,至此,于连的家庭教师地位固若金汤。
才华,对于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已不必多言,若是这个男人还英俊漂亮呢?至此我们知道于连是如何被一点点“宠”起来的,一直宠到天上。他敢与德·莱纳先生叫板,对市长一家人“沉着脸,不冷不热”地“应付”,利用自己在这座城市的名声鹊起巧妙地给市长施加压力。当德·莱纳先生提出签订两年的合同,“不行,先生,”于连冷冷地回答,“您要辞退我,我不得不走。一份合同拴住了我,您却不承担任何义务,这不平等,我不能接受。”
司汤达如此铺排于连的不可一世,绝非仅仅针对于连的学生。他后来再也没有渲染于连的拉丁文,而是说明一个道理:有才华的漂亮的男人历来是为女人准备的。于连这个家庭教师并没当太久,很快就由他生命中的两个重要女人——德·莱纳夫人和德·拉莫尔小姐——拖入不归路。征服小小的维里埃市长以及夫人对于他已经绰绰有余,下一个目标,对巴黎的挑战,才更有“戏”。
司汤达让于连在离开修道院去巴黎之前,让他对自己的家庭教师身份做了最后确认:他深夜来到德·莱纳夫人窗前,爬上高高的梯子与夫人幽会;白天,夫人把他藏在一间无人的客房里,然后把孩子们带到窗下,于连在二楼的这间密室偷偷地看了他的学生最后一眼。这可以视为他对学生的留恋和思念。
离开市长家,于连的家庭教师职业彻底结束。在巴黎,尽管他有过私人秘书和军官的短暂生涯,但说到底还是家庭教师这一角色奠定了他的才华,衬托了他的个人价值,从而开启了在巴黎的人生道路。
在雨果的名著《九三年》中,西穆尔登曾是革命军总司令郭文的家庭教师,但其实他身兼多职:老师,教父,父亲,朋友。
西穆尔登在乡村里当过本堂神父,他品德高尚又具有真知灼见,有着一颗纯洁善良然而又有些忧郁的心。教士的生活让他成为一个执拗倔强的人。他善于思考,博学多才,通晓各种欧洲语言,始终保持理念的贞洁,但这种压抑也潜伏着某种危险。
在郭文家族,家庭教师堪比父亲一职——郭文是个孤儿,只有祖母和一位常不在身边的叔叔(朗德纳克)照看他。祖母去世,叔叔在凡尔赛宫担任要职,并经常去军队视察,留下他独自呆在荒僻的城堡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家庭教师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父母,西穆尔登对他的学生也兼有这种精神上和肉体上深挚的父爱和母爱。老师给了郭文教养、思想、学问,对这个孩子视如己出。然而,岁月流变让西穆尔登不得不离开已成年的学生,家庭教师的使命已经完成,学生也将去从戎。郭文被任命为上尉,出发去某地驻防,家庭教师只能回到教会,从此失去了学生的音信。
是战争,把朗德纳克、西穆尔登、郭文三个高贵可敬的灵魂聚合到一起。朗德纳克侯爵身怀王室的高傲与枷锁,他跳进火海救出三个孩子,宁愿被捕。正如一名士兵给他下的结论——“真是个好家伙!我甚至忘记了他所做的种种恶行”;西穆尔登在和平时期是革命与善良的传播者,而在战争开始后,他是革命的坚决执行者,他压抑了自己的良心与仁慈,崇尚暴力,认为这不是一个温情的时代。他是彻底的革命者,活在毁灭的快感中。可是由他一手调教的郭文,却是满身的勇敢、慈悲、正义,他说:“我们在打仗时,必须做我们敌人的敌人,胜利以后,我们就要做他们的兄弟。”他年轻有为,思想深邃。看见叔叔朗特纳克侯爵火海救人的英勇行为,平日的仁慈终于汇成一片天地,骑士精神已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情愿用自己的头颅去换取叔叔的性命。
放走侯爵之后,西穆尔登与他的学生有过大段对话,面对比自己更彰显人情味的学生,骨气卓绝、冷峻逼人的老师难免失望:“作家信奉良心导师的时候过去啦。郭文,你知道,我们说狄更斯温情脉脉,在某些时候并不是一个褒义词。”
“我知道,老师。也许您更喜欢古希腊罗马的人吧。可我呢,我更喜欢现在的人。普通人。也就是说,普遍的人。”
“郭文,有时候我觉得你应该去学哲学。”
“也许吧。”郭文笑了笑。“不过,谁叫您来我家当家庭教师,抱我在膝上念书的时候,念的头一本便是文学呢。”
在地牢里两人的彻夜畅谈,无疑是整部作品中最出色的章节。他们一同进餐,谈到共和国,谈到人类……最后,老师按法律处死了学生,而后开枪自杀。这样的结局,情理上难以接受,艺术上却登峰造极。
郭文在《九三年》中是个完美的人物,他的思想属于雨果,他的选择也是雨果的选择。我甚为喜欢郭文那句话:“人生下来不是为了拖着锁链,而是为了展开双翼。”最后,西穆尔登流下谁也不曾见过的眼泪,两人都为自己的原则付出了生命。师生之间的看似反逻辑正反映了人性的觉醒和人道的胜利——谁说不是老师当初教育的结果?师生二人两颗纯洁美好的灵魂一起拥抱着上了天堂。尽管我最爱的还是郭文。
现实生活中,西穆尔登是有原型的——雨果幼年时的家庭教师拉里维埃尔。雨果的父母很早就分居了,父亲在军队与一个名叫托玛斯的小姐同居,雨果和两个哥哥跟着母亲生活。最后一次父母决裂时,雨果的父亲驻防西班牙,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巴黎,住进斐扬底纳胡同12号。这是一座古老修道院的底层,有一个大大的花园,雨果曾写过一首诗:
在我金色的童年——唉!它转瞬即逝,
花园、老教士、母亲是我的老师
……
教士,熟读塔西陀和荷马的慈祥老人,
而我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
这首诗中的“老教士”就是一名神职人员,后来脱离教会,与他的女仆结婚并办了私墅,被雨果的母亲请来教孩子们。老教士教雨果拉丁语和希腊语,拉丁语紧凑的形式吸引了小雨果,他喜欢这门结构缜密、铿锵有力的语言。在老教士的帮助下,雨果翻译了许多当时的诗歌和历史著作。说老教士启蒙了雨果的文学道路,或许并不为过。
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里,男家庭教师的“戏份”也不少。成为基督山伯爵的爱德蒙第一次见到昔日恋人美塞苔丝时,盛赞她的儿子阿尔贝:“爱德华小主人刚才那句关于国王米沙里旦司的话,是尼颇士(罗马历史学家)说的”,“从他这句引证上来看,他的家庭教师对他没有疏忽”。
这部书里,关于男家庭教师,最为精彩的章节还在于,为了扳倒残害自己的仇人检察官维尔福,基督山伯爵特意找到维尔福的私生子贝尼代托,而伯爵安排给他的新名字则是安德烈,并把他包装成一个贵族公子哥——卡瓦尔康蒂少校、一个意大利绅士的儿子。为此伯爵虚拟了一个情节:“安德烈”五岁时让一位“奸诈的家庭教师拐走”。十五年之后,伯爵让“安德列”重新“回到”社交界时,他“让”年轻的子爵身边“总是跟着一位非常严厉的家庭教师”,于是那个劣迹斑斑的少年再来到银行家腾格拉尔身边,诱惑他的女儿,以及来到检察官维尔福身边充当“富二代”时,他的身份是这样的:曾被他的保姆掉过包,或是被他的家庭教师丢失过……这种身份成功地骗过维尔福,以这种小悬疑迎来最后审判“安德烈”时维尔福困窘尴尬的大精彩。
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克利斯朵夫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家庭音乐教师。当时,新寡的克里赫太太,离开了丈夫曾供职的柏林,带着女儿弥娜搬回到她的出生地。当她在市政音乐厅观看了克利斯朵夫的演出,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深深的崇拜,决定聘请克利斯朵夫来到家里担任女儿的家庭音乐教师。然而,少不更事的克利斯朵夫面对这对美丽的母女,产生了“少年维特”那样的烦恼和冲动。那母女俩营造出的一道爱怜的光映在他心上,那像花一般柔和细腻的手指,以及微妙的清香在他周围缭绕,使他迷迷忽忽,经常犯晕。
少年克利斯朵夫自然不懂得女性心理。他情窦初开,常常被这两位美丽的邻居搞糊涂,一时分不清自己“爱”的是少妇还是少女。他先是迷恋上那个风韵别致的母亲,可是当他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出现在弥娜面前,他发现自己又爱上了这个美丽单纯的姑娘,只要听到她亲热的一言半语,或是看到可爱的眼神,他就快乐之极。
而罗曼·罗兰还真的让这一对异性师生萌发了爱情。这种关系被母亲发现后,她大发雷霆,辞退了克利斯朵夫,不许他再进家门。克利斯朵夫不能忍受这种失恋的痛苦,虔诚地表白他真正、狂热地爱着弥娜,并请求与弥娜结婚。然而“财产”和“门第”的铁墙终究还是挡住了他对弥娜的爱情。初恋的幻灭让他想到自杀,这是他遇到的最凶险的关隘。这之后,他的少年时代结束了。
克利斯朵夫又多次当过家庭音乐教师。单纯鲁莽的他面对的是一个个狡诈的音乐掮客,他们深知这位头发极像贝多芬的小家伙绝非等闲之辈,庸俗的市侩们无一例外地总是重挫他的锐气,而他那过度的梦幻色彩又让那些人频频得手,所以他的理想主义不得不一次次面临死亡。
命运的最后,为了照顾死去的好朋友的弟弟耶南,克利斯朵夫仍然到一个个家庭做音乐教师,过着潦倒的生活。在巴黎的“五一游行”中,他和耶南走散。耶南死了,他也流落到德国边境的一个村庄,遇到老相识勃罗姆医生。在医生家担任音乐教师,竟导致他与医生的妻子阿娜产生了灵魂的交融和惊颤。这最后一段爱情神奇地呼应了第一段和弥娜的爱情。
是否异性师生之间很难平淡如水?包括一直暗恋他的女学生葛拉齐娅最后的爱恋表白。但他与这些女学生因不同的原因在爱情死亡的道路上殊途同归,无一修成正果。
相对于以上几部巨著中的家庭教师,《战争与和平》中的男家庭教师都没有走到前台,但看得出,四个上流社会的家庭都请着多名男女家庭教师。男教师来自欧洲不同的国家,例如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皮埃尔,从十岁起便随家庭教师到了国外。在全书开头别祖霍夫的家宴上,“一名德国男家庭教师极力记住种种肴馔,甜点心以及葡萄酒,以便在寄往德国的家信中把这全部情形详尽地描述一下”。不仅如此,当管家给大家斟酒竟把他漏掉时,他气愤极了,“他所以恼火,是因为谁也不了解,他喝酒不是解渴,也不是贪婪,而是由于一种真诚的求知欲所致……”
《复活》中的一个陪审员彼得·盖拉西莫维奇就曾是聂赫留朵夫姐姐家的家庭教师,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当聂赫留朵夫调查政治犯的时候,他发现了平民出身的纳巴托夫曾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活,因向农民朗读小册子和在农民中创办生产消费合作社被捕。《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小儿子谢廖沙经常“由家庭教师领着走了进来”,但托翁并未安插安娜与孩子的男家庭教师的故事,而是寥寥几笔从谢廖沙眼里感知母亲与情人渥伦斯基的关系:“他清楚地看出来他的父亲、他的家庭教师和他的保姆都不喜欢渥伦斯基”。《叶甫根尼·奥涅金》中奥涅金的家庭教师是一个“敷衍了事的法国人”。《名利场》中的几个上流社会家庭“一向请着第一流的男女家庭教师”……
纵观欧美文学中的人物关系,家庭教师这一角色,无论男女,他们位于一个个家庭单元,与这个家庭构成一种特别的纽联。包括家庭女教师在内,作家真正的目的并非展现他们如何授道解惑,甚至连他们教学的场面都吝啬得不给几笔。一部洋洋几十万言的鸿篇巨著,对家庭教师的本职工作——教学,只是蜻蜓点水般地“象征”一下,而他们的命运,他们与“家庭”各成员,以及进而扩大到与外部社会产生的各种际遇变故,才是作家真正的着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