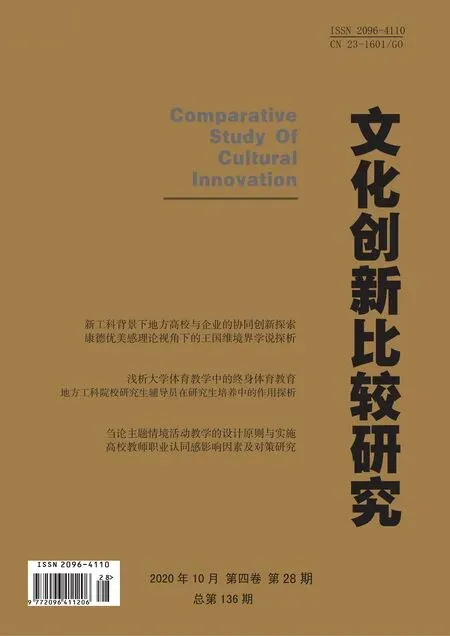康德优美感理论视角下的王国维境界学说探析
——以《人间词话》为例
徐沁蒙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日照 276800)
“境界”在汉语中有多重含义,其在词义学的本意是指土地与土地之间的界限,1901年王国维在金栗书局出版的《日本地理志》一书的翻译中初次使用“境界”一词就是采用了这层含义,到了作者在创作《人间词话》时期,“境界”一词就被赋予标准的含义,既可以作为衡量诗词的标准,境界是气质神韵之本,是关于美感的本质性存在。对于王国维境界学说的分析视角广泛,在其他文章中有作者就叔本华对于王国维美学形成的直接作用,或王国维美学中所蕴含佛学思维进行阐述,然而就西方美学对于王国维的作用而言,康德美学思想产生于叔本华之前,叔本华关于艺术品与事物自身现实关系等思想受康德启发颇深,因此以康德美学理论出发更能看出其对于王国维境界学说形成的源头性影响,且叔本华是从体验美的各个方式出发,对于正确获得美感进行论述,而康德将美直接划分为崇高感与优美感与王国维所谓“壮美”与“优美”更为契合。
康德美学中的优美感与崇高感总是相对应出现,他在论述两者的区别时提出:优美感本身依赖于语言的修饰,要求创作主体字斟句酌,言辞准确、传神精辟。境界作为自五代至北宋时期诗词评价标准,是优美感在语言领域的表现形式之一,要求作品无关于创作者与审美者自身利害关系以体现优美感的无目的性;通过表达自身真情实感而非模仿他人,体现自然的优美感;通过境界的内在神韵与外在对应优美感的含蓄性与表现性。
1 优美感的无目的性与境界的非功利性
王国维的美学观作为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受到西方理性主义思潮,特别是康德与叔本华的影响,其中康德美学也强调了审美的非功利性。他指出审美愉快是自由的,这是其审美超功利思想的核心[1]。“凡是我们把它和一个对象的存在之表象结合起来的快感,谓之利害关系[2]。”然而审美过程作为愉悦的感受与轻松的体验,应该无关乎利害关系,应该是一种自然静观。优美感更是如此,它不仅是崇高感在空间上的停顿与补充,更因其自身的吸引力与诗意充分展现了各类艺术形式的美学境界。这要求创作者按照自身的真实感受与想象加以修饰、美化;还要求审美者根据自身的审美体验做出客观公道的评价。达到朱光潜先生在《论优美感与崇高感》的序言中翻译的境界:“美之所以为美,关键就在于它是‘无所为而为’”[3]。
1.1 创作者的非功利性
《人间词话》一书中,王国维最为推崇的文人莫过于李煜,他在第十五则中这样描写:“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4]。”伶工之词为了取悦他人而百般求全;士大夫之词却可以直抒胸臆的感时伤世。可见他将李煜视为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词人,并在之后的第十六则当中具体分析了李煜不同于他人的长处:“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5]。”李煜出生自宫墙之内,目睹过尔虞我诈却保持直率一腔赤诚,相较于《红楼梦》《水浒传》等现实主义作品对世俗社会的直面冲击,李后主的诗词更因其涉世未深而弥足珍贵。这是诗人之所以为诗人的两重条件,从客观角度来说要广泛深入的接触社会,积累素材以求作品平铺直叙又真实动人; 从主观角度来说要坚守天真,不忘本心,知世故而不世故。
1.2 审美者的非功利性
王国维曾说:“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意思是说政治家要着眼于当朝当代的具体人与具体事例做出自己的判断,以保障公平公正;而文人学者的创作要通古晓今,借用从古至今历朝历代的经验从整体上加以诠释。因此政治家与词人的不同,不仅是社会角色与分工的不同,也是眼光的不同,世界观的不同。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和不愉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做出评判的。这样一个愉悦的对象才能被称为美的[6]。
在康德看来,美感一方面的确是对自然的静观,但是由于他只是出于主观的形式而不受感官对象的限制,所以是一种对自然的无涉功利的自由观照[7]。优美感的无目的性,体现在境界领域,不但要求创作者摒弃自身利害关系,也要求审美者群体的客观公正。
2 优美感的自然性与境界的真挚性、独特性
康德早在论证世界发展的动力时就提出过自然原则:在道德层面的“原则”之后,存在另一无形式存在的规律和根本目的,即“大自然”。正是这一终极目标如是合规律地推动着世界发展的同时,也让这一推动过程产生的效果合乎情理之中[8]。可见任何人为创造美的行为要符合规律就要符合自然原则要求,作为美的结果,境界需具备真情实感,彰显真挚性;作为美的途径,境界因创作主体的不同因人而异,不可模仿,因而具备独特性。
2.1 境界的真挚性
境界是中西观念融合的结果,而在中西观念融合的最深处,康德的影响始终是挥之不去的[9]。理想的境界是真挚与深沉的结合,其中的“真”便是真情、真切,作者曾在评价纳兰容若时指出:“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10]。”纳兰性德所思所作都是直观、率真的情感表露。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第五十一则中通指出纳兰容若作品中没有被繁复晦涩的用典手法或是刻意为之的矫揉语言破坏自身美感,因此充满切切真情。
康德赋予艺术创作以自然原则,在他看来“想象力(作为生产的认识机能是强有力地从真的)自然所提供给它的素材里创造一个像似另一自然来。”[11]可见,创作是在现实基础上的加工与夸张,是离不开事物本来面目的,优秀作品中的艺术化处理使人仿佛阅读真人真事一样自然而然。这便是境界的真挚性与“自然”优美感的不谋而合。
2.2 境界的独特性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第四十五则中对于北宋豪放派词人作品进行横向分析:作者指出与苏东坡、辛弃疾相比,姜夔的作品虽然做到了清新脱俗,然而没有两者的高雅风格,最终只是如同雾里看花。究其原因,词人自身的品格胸襟决定了其文章的水平高低,王国维在第四十四则中具体作出说明:“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同样是北宋时期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专长通过大场面的描绘营造旷达境界,辛弃疾侧重于寓情于景,表达内心壮志豪情。倘若没有二人的独特经历与气魄,试图通过字句和文体上的模仿达到他们的高度,只能是望洋兴叹、东施效颦。可见创作主体不同,其境界高低有所差异。
康德在《论优美感与崇高感》一书当中通过性别差异对比,得出女性更多具有天生优美感而男性更容易展现崇高感的结论。倘若男性与女性的角色颠倒,男性出于好奇模拟女性体态作风,或是女性为博得社会地位以男性标准要求自己,美的不同表现囿于主体自身因素的限定,因而特定境界的营造具有独特性,即使被他人模仿的也丧失了原本的优美感。
3 优美感的内外兼修与境界的神貌并存
康德从内在与外在两种层次诠释优美感的表现。含蓄美是优美感之于静谧的深思与无穷的想象。星空就曾带给康德关于宇宙与现世无限遐想; 现象美是优美感之于容貌的展现与气质的优雅。康德眼中女性生而具有天然的可爱,她们依据本性自发追寻美的事物,因此优美是内在与外在的双重结合。
王国维所评价的理想境界也是神貌并存的:“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神为貌的优美渊源,貌为神的优美形象。含蓄性境界精深幽微展现内在优美感;表现性境界准确直观展现外在优美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第六十则指出说词人对于世界的观点和人生的看法必须内外在相结合加以考察,注重内在境界,作品才会真实,“故有生气”;注重外在境界,作品才有风格,“故有高致”。优美的境界塑造依靠神韵与表象的相互呼应,又在表象中蕴含深意。
3.1 内在优美感:境界的含蓄性
境界之于神思便是含蓄的内在优美感。苏轼作为宋词豪放派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其恃才放旷的豪气让人望尘莫及。王国维曾说他的作品“雅量高致”其根源在于苏轼的旷达词风在于神韵、风骨。无论身居高位时“会挽雕弓如满月”或是虎落平阳时“一蓑烟雨任平生”,都不磨灭内心傲骨。辛弃疾在《中秋饮酒达旦》中通过“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 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引发了诗人带有思辨性的哲学思考,我们所见到的月亮来自何方?去往何处?是否如同我们见到的这般模样?王国维对此评价为:“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此处词人没有止步于对中秋之月的直观描绘,而是于情于景触发了创作者的无限想象与思考,将情境上升为含蓄境界,其内在优美感跃然纸上。
3.2 外在优美感:境界的表现性
康德美学中的优美感与崇高感总是相对应出现,境界作为自五代至北宋时期诗词评价标准,是优美感在语言领域的表现形式之一,纵观“境界”一词的词源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其在词义学的本意是指土地与土地之间的界限,1901年王国维在金栗书局出版的《日本地理志》一书的翻译中初次使用“境界”一词就是采用了这层含义,到了作者在创作《人间词话》时期,“境界”一词就被赋予标准的含义,既可以作为衡量诗词的标准,“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又不局限于字句在文辞上的片面意思,是评价作词人风骨造诣是否做到不入俗套、气韵兼备,“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