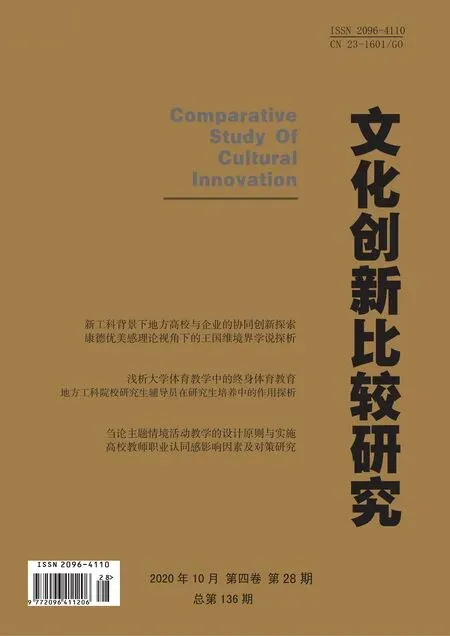中西翻译文化视角下的现代翻译补偿分析
禹琳琳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河南郑州 450046)
补偿作为一个和翻译密切关联的范畴,目前大多学者在研究和教学阶段多半偏重翻译实践,重实践轻理论的现状将现有补偿理论局限在了研究者的翻译总体理论框架中,从而多侧重一般性问题,而补偿问题的特殊性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翻译补偿已经引起不少理论家的关注,但由于补偿本身具有明显的定向性和特殊性,每一个语对(language pair)之间的补偿也呈现不同于其他语对的特殊性,同时同一语对不同取向的补偿又具有其各自的特点,对此问题中西方翻译研究者需要通过系统对比分析找出各层次间在语法范畴、词汇、语音、修辞及文化等领域的差异和空缺,然后才得以在目的语中探索功能对等的补偿手段。
1 中西方补偿研究对比
西方学者研究的总体趋势是为了逐步走出传统译论的随想性和臆断性,甚至神秘主义的阴影,使补偿研究向科学、系统、规范的目标逼近。奈达作为现代翻译理论先驱,在1993年出版的《语言、文化与翻译》中讨论从功能视角对补偿问题进行阐述,即补偿要建立在功能对等基础上,通过对同构缺失的补偿来达到功能的对等。乔治斯坦纳则对翻译补偿做了更多的阐述,他认为翻译是由4 个步骤组成的过程,这4 个过程分别是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斯坦纳把翻译建立在人类的语言交际中,他认为语言永远处于流变中。而纽马克的补偿思想则以文本功能为基础,并同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相结合,他提出了表情(expressive)、信息(informative)、呼吁(vocative)来对不同文本进行了分类。纽马克用隐喻来说明他的补偿思想,认为“常用隐喻只有其形象在相应的、可以接受的搭配和固定搭配范围内转换,才能翻译准确。”所以说纽马克是把补偿建立在文本和功能基础上,力求补偿和简洁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
国内的补偿研究则是出现在20 世纪80年代后,王恩冕提出了语境中语义等值的补偿,他主张“用译入语语言形式补足在转换原文语言形式时造成的语义损失”。柯平认为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差异使源语符号和译语符号几乎不可能在指称、 语用和言内3 个意义层面上一一对应,所以“补偿照字面直译原文将会造成原文意义的丢失”,所以补偿更应按译语规范在特定语境中确保最重要意义的最大等值。而孙迎春则认为译者任务是尽可能忠于原文,将语言风格、艺术特色、表现手法上的损失降到最低,他主要从艺术角度出发,对音律、修辞及语言表达方式等进行补偿的探索。屠国元则更为看中文化的移植,认为语言与文化共存,因此更要在翻译实践中侧重在传达过程中做出的妥协和采取的补偿。
翻译补偿作为翻译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不能完全参照翻译的一般原则,也不能任其自由发展,根据补偿所遵循的“需求”原则、“相关”原则、“重点”原则、“就近”原则、“等功能”原则、“一致”原则来分析语言层面和审美层面的补偿,将中西翻译补偿领域的研究有更全面的认识[1]。
2 语言层面的补偿
语言层面的补偿设计到词汇、 语法和语篇的补偿,翻译中常常需要采取多种手段进行补偿。词汇在翻译过程中最易损失,针对词汇层面的补偿分为整合补偿和分立补偿。整合补偿目的是让补偿内容与原文内容自然的结合成有机的整体,并且不暴露补偿的痕迹。整合补偿的方法有很多,如增益、具体化、概略化和增加对比度。我们以最常见的增益为例。
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寝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赵飞燕立着舞的金盘。
On a table stood an antique mirror that had once graced the tiring-room of the lascivious empress Wu Ze-tian. Beside it stood the golden platter on which Flying Swallow once danced for the emperor’s delight.
在此例中,武则天在中国是非常著名的女皇帝,但在英语中却无人知晓,译文中在修饰武则天时用了the lascivious empress(淫荡的女皇),这样给外国读者很好地介绍了中国历史知识。并且译者在“赵飞燕立着舞”后增加了for the emperor’s delight(为了愉悦皇帝)。此处增补内容非常有必要,西方读者对我们古代人物非常陌生,译文解释了赵飞燕是古代皇帝身边的舞女,因其善舞,被人称为“飞燕”,这里的“飞燕”是人们根据其曼妙的舞姿取的绰号,译者在此处未按照其真实姓名处理,而是意译为“flying swallow”,很好地将赵飞燕的人物特点代入到像轻快的小燕子的情景中,更帮助外国人准确理解和把握。另外,增加对比度也旨在保证译文对应词的预期效果接近原文,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
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
That kingdom-quelling beauty dissolved like the flower of foam.
In the foreign palace, Xi Shi, didi you yearn for your old home?
Who laughs at your ugly neighbor with her frown-and-simpler now,
Still steeping her yarn at the brook-side, and the hair snow-white on her brow?
此例来自红楼梦中林黛玉所做的诗 《西施》,第一句中的“倾城”专指绝色美女,译为美艳全城的美女。译者将其译为kingdom-quelling beauty,将美貌无双的美女形象描画的更加突出。而在原诗中,其表层意思是用一城的人来衬托一个绝色美女,两者间的对比度在古代来看差距比较大,但是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并不明显,但若用一国的国民来衬托一个美女,两者的对比程度就明显加深[2]。
再如,文学作品中常用的人称称谓语“小姐”,在其对应的英文中 “小姐” 多被翻译为girl 或者Miss加姓氏,不过这里的人称翻译是不能体现尊卑贵贱的身份,如果将“小姐”这个称谓放入我们古代文学作品中,其身份即变为传统官宦士绅家里的女孩,在这种语境下,用“Princess”来替代“小姐”,使其与少爷、老爷并置,与女婢小厮相对,能很好地显示富家小姐和贫家女孩的差距。
除了整合补偿外,词汇层面补偿还有分立补偿,这种方法主要依靠标记来向读者明示补偿内容,这里原文作者和译者的身份泾渭分明。分立补偿分为文本内注释和文本外注释,主要作用是既有解释,又搭配着评述,对不熟悉外国文化的目的语读者透彻理解原文大有帮助[3]。
除了词汇,语法的形态、语序和虚词会在翻译过程中发生损失,当翻译在综合型和分析型语言间进行时,形合和意合产生的落差就成为语法补偿的重点。英汉互译或者与其他语种间互译,应注意汉语中隐含的语法关系需转换为目的语中有相同功能的语法范畴,异类补偿成为英语等译成汉语时最主要的手段。异类补偿是使用与原文文本不同的手段对原文对应成分做出补偿,这种补偿可分为时间副词补偿、助词补偿、被动意义词汇补偿和复数意义补偿。
语篇补偿是一项难度较大的课题,一般人们倾向于把语篇看作是大于句子的单位,同时语篇研究涉猎语用学领域,因为翻译损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个语种间的社会文化冲突造成的,这类补偿主要涉及逻辑连接补偿和人称指称补偿。我们以最典型的逻辑连接补偿为例。
子曰:“有德者必有信,有言着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The master said,One has accumulated moral power will certainly also possess eloquence;but he who has eloquence does not necessarily possess moral power. A good man will certainly also possess courage;but a brave man is not necessarily good.
此例中文中没有使用任何连接词,主要是靠语义来连贯成篇。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常用的骈偶对句,这种句子通常表达两种意思:要么是同义,要么是反义,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等,但英语中这种骈偶句式特别少见,英语国家读者更习惯通过形式衔接来判断相邻句子的含义,所以说必要的衔接手段会帮助目的语读者更轻易地捕捉到原文隐含的逻辑关系。所以例句在译文中增加了连接词also 和转折连接词but[4]。
3 审美层面的补偿
除去其他题材中常用的语言层面的补偿,在文学作品中,特别是中西方诗歌中,审美的补偿更是决定了作品是否能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如果按照诗歌的字面去翻译,诗歌的逻辑命题还涵盖在内,但原文中创造的美妙意境就会荡然无存,无数的经典诗句都变成了普普通通的家常话。审美要素在文学作品中至关重要,林语堂认为“文章之美不在质而在体。体之问题即艺术之中心问题。”。审美补偿主要涉及审美形式的功能补偿、 审美形式的价值补偿及审美形式的行义统一性补偿[5]。
审美形式的功能丧失形式多种多样。例如,英语中含有大量的头韵押韵形式,在James Joyce 的Ulysses 中含有大量的头韵。
比如:He was but eleven months and nine days old and, though still a tiny toddler, was just beginning to lisp first babyish words.
其中tiny 和toddler,begin 和babyish 就 是典型的头韵,头韵分布在重音上,通过轻重音节的变化使听觉和视觉都可获得明显感受,古欧洲时期的诗歌就主要以轻重音和头韵来表现音乐性。而汉字则多为表意文字,无内在的轻重音之分,最理想的补偿手段为双声联绵词,在上述例子中,为实现原文头韵的审美价值,译者将tiny 和toddler 译为“趔趔趄趄”或“趔趄”,将babyish 译为“咿呀”,这种叠韵联绵词很好的弥补了两种语言互译过程中产生的损失[6]。
审美形式冲突造成的损失比审美功能丧失要严重得多,因为一旦审美形式与目的语冲突,则会给读者带来消极影响,甚至让读者滋生逆反心理。对于这种冲突可使用两种补偿手段,一是用减译方法来消除影响,二是用目的语文化中的客体来替代源语文化中的审美客体。
比 如,I’m too old a dog to learn new tricks.(Maugham, 引自孙迎春《损失、补偿与“雅”字》。
此例中“我”自称为“old dog”,在原文中这里运用的隐喻没有贬义,但若是直译为“老狗”将直接与汉语的审美情趣发生冲突,故译文中“狗”的隐喻只能通过减译手段来保留客观的指代意义,避免给读者造成负面的心理影响[2]。
审美形式的形义统一性丧失主要体现在源语的形式与语义呈现统一,而在目的语中难以找到对应成分导致不可译,这种不可译多是由于音韵、语音、文字形态和语义在语言内部形成特有的、 不可分割的组合形式。这种情况下最理想的补偿就是在不影响总的功能的前提下,在语篇层面进行补偿。
吾看诸葛亮如草芥耳,何足惧哉!
He’s a straw reed to me.I fear him not.
《三国演义》属于严肃的文学体裁,语言形式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译者多使用现代读者不难理解的古词或古语法,如fear him not 等,所以说古语补偿还是以传达原文审美价值,体现古雅厚重之美[8]。
4 结语
中西方翻译文化中补偿作为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但某些已广泛采用的概念仍缺乏准确界定,并且研究者的注意力多放在补偿策略上,很少去涉猎“超额补偿”现象,在翻译实践中确立切实可行的补偿原则对补偿手段进行规范将变得非常必要,不仅要发挥中西方文化补偿的积极作用,同时最大限度避免补偿带来的消极后果。